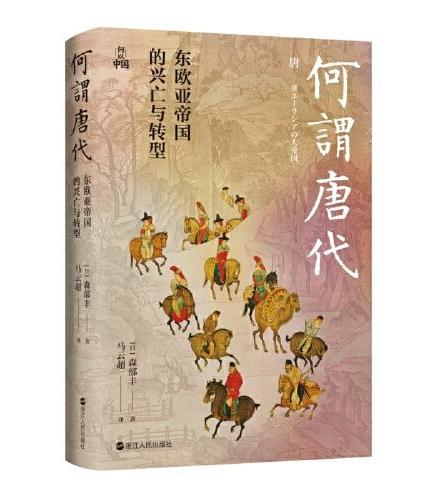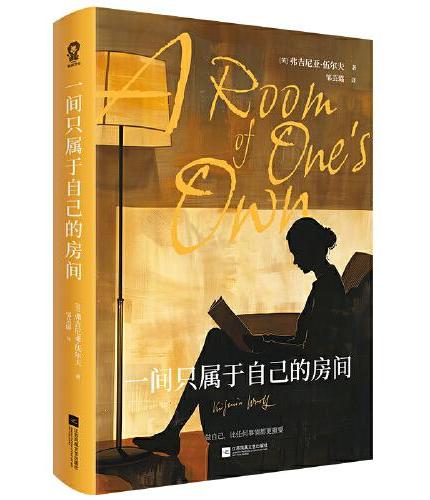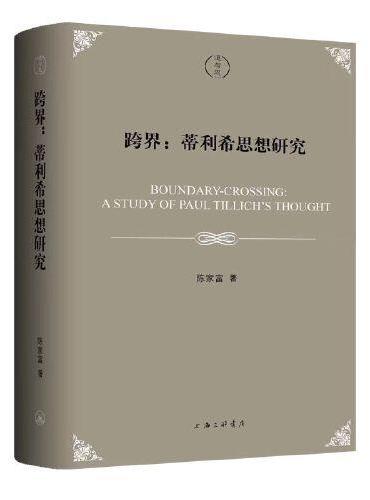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无端欢喜
》 售價:HK$
78.2
《
股票大作手操盘术
》 售價:HK$
55.2
《
何以中国·何谓唐代:东欧亚帝国的兴亡与转型
》 售價:HK$
89.7
《
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 女性主义先锋伍尔夫代表作 女性精神独立与经济独立的象征,做自己,比任何事都更重要
》 售價:HK$
45.8
《
泉舆日志 幻想世界宝石生物图鉴
》 售價:HK$
137.8
《
养育女孩 : 官方升级版
》 售價:HK$
51.8
《
跨界:蒂利希思想研究
》 售價:HK$
109.8
《
千万别喝南瓜汤(遵守规则绘本)
》 售價:HK$
45.9
編輯推薦:
自传性随笔集全译本首次面世
內容簡介:
1935年11月,菲茨杰拉德在经过深沉的反思之后,开始撰写他取名为《崩溃》的系列自传体文章。这些文章翔实生动地记录了菲茨杰拉德的社会活动和内心活动。他自状其过,以令人震惊的客观态度无情地解剖、深刻地反省着自己的过去,探查着自己性格中的诸多缺点,把一个真实的自我毫无遮掩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關於作者:
F.S.菲茨杰拉德(Francis Scott Fitzgerald,1896-1940)是20世纪美国最杰出的作家之一。1896年9月24日生于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一个商人家庭。后考入普林斯顿大学,但中途辍学。1920年出版长篇小说《人间天堂》,一举成名,之后寄居巴黎,结识了安德逊、海明威等多位美国作家。1925年《了不起的盖茨比》的问世,奠定了他在现代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成为20世纪20年代爵士乐时代的代言人和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之一。其他代表作还有《夜色温柔》《末代大亨》《漂亮冤家》《爵士乐时代的故事》等。
目錄
献诗 1
內容試閱
我逝去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