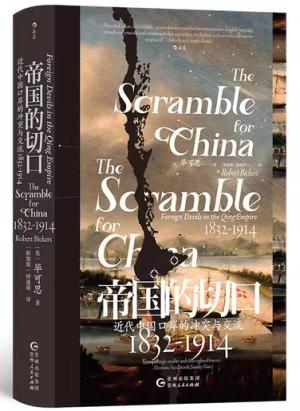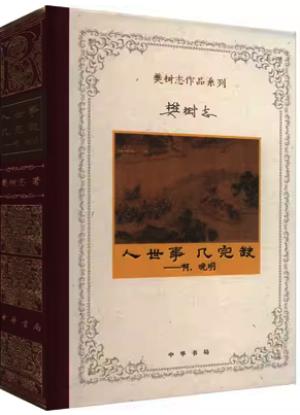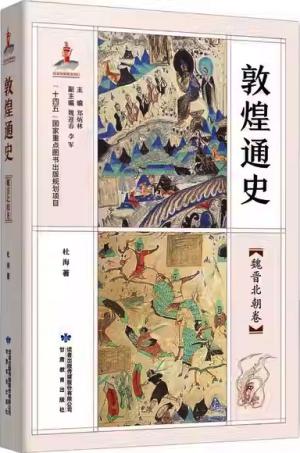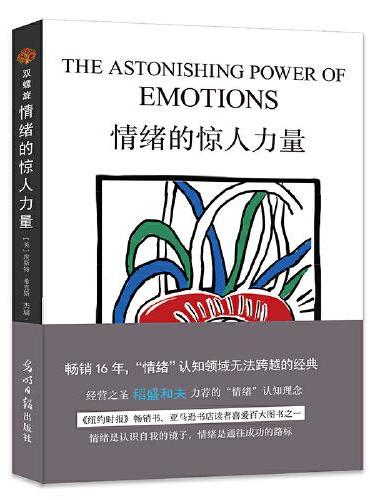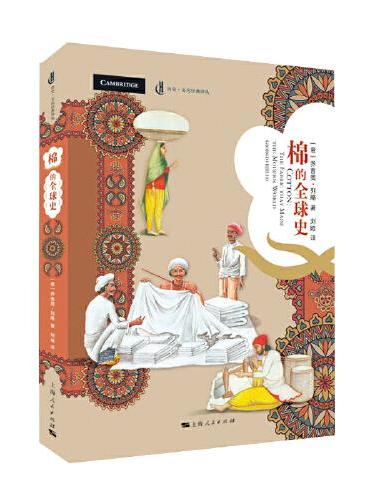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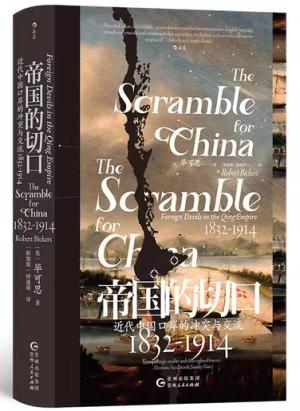
《
汗青堂丛书138·帝国的切口:近代中国口岸的冲突与交流(1832-1914)
》
售價:HK$
12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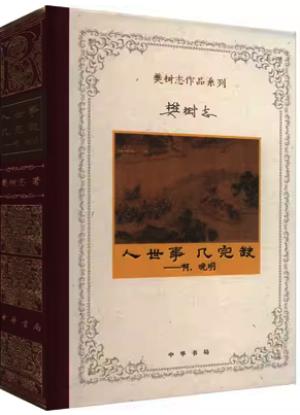
《
人世事,几完缺 —— 啊,晚明
》
售價:HK$
115.6

《
樊树志作品:重写明晚史系列(全6册 崇祯传+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明史十二讲+图文中国史+万历传+国史十六讲修订版)
》
售價:HK$
498.0

《
真谛全集(共6册)
》
售價:HK$
115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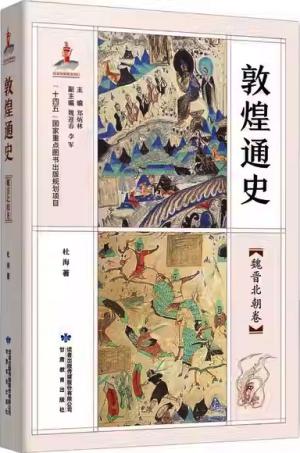
《
敦煌通史:魏晋北朝卷
》
售價:HK$
162.3

《
唯美手编16:知性优雅的编织
》
售價:HK$
5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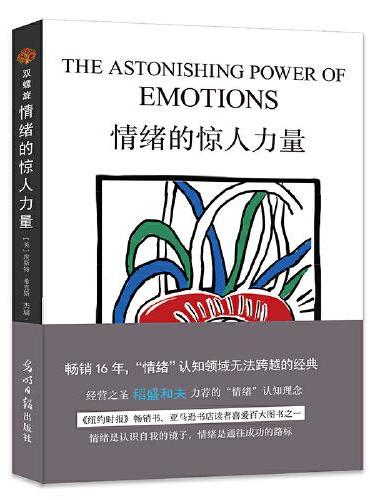
《
情绪的惊人力量:跟随内心的指引,掌控情绪,做心想事成的自己
》
售價:HK$
5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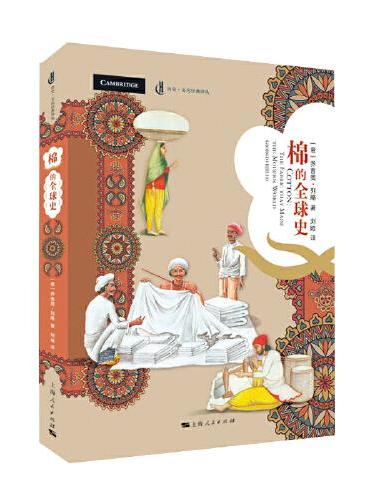
《
棉的全球史(历史·文化经典译丛)
》
售價:HK$
109.8
|
| 編輯推薦: |
《茶山》为诗人、散文家雷平阳深入云南茶山地区调查的非虚构作品,既基于大量调查所获资料信息,又旁征大量的历史文献、学术研究成果,叙事流畅,不事雕琢,将历史和现实交织一起,呈现出对普洱茶山和制茶历史文化的生动而深刻的立体叙述。这是一份充溢着茶香的礼物,更是人们感知云南普洱茶文化的一座桥梁。
编辑推荐
《茶山》是一部具有云南茶文化历史的维度、人文的厚度及精神的高度的以人文地理笔记形式所呈现的高水平的长卷文化散文。既具有茶文化研究的严谨性,又富含田野考察的丰富细节,更呈现出云南独具特色的茶文化奇观,具有文学的、茶学的、人类文化学的重要价值。
|
| 內容簡介: |
|
《茶山》是著名诗人、散文家雷平阳时跨二十余年,对云南易武、倚邦、习崆、布朗、南糯、忙糯和大雪山等古茶山的体察记录与文化论证。作为茶文化研究者,作者集文学创作与茶文化生态学研究于一身,涵盖从西双版纳到临沧等古老茶区的著名茶山及其文化生态,集文学、文化人类学和茶学之大成。此书为作者茶山书写文字的精微之作,全方位展现了普洱茶核心产区的精神档案和茶山画卷,是人们探知澜沧江流域茶山文明和云南少数民族茶神奇观的bi备之书。
|
| 關於作者: |
|
雷平阳,当代诗人,散文家,一级作家,现居昆明。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暨“全国文艺名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诗歌创作委员会委员,中国诗歌学会常务理事,云南省作协副主席、诗歌创作委员会主任。著有《风中的群山》《天上攸乐》《击壤歌》《云南记》《送流水》《修灯》等诗歌、散文集四十多部;曾获人民文学奖、人民文学年度诗人奖、诗刊年度大奖、十月文学奖、华语传媒大奖诗歌奖、《钟山》文学奖、花地文学排行榜诗歌金奖、中国诗歌学会屈原诗歌奖金奖和鲁迅文学奖等重要奖项;有众多作品翻译为英、法、西、葡、波兰、俄、日、韩等语言。
|
| 目錄:
|
01 倚邦、易武记 /001
02 习崆山中的对话 /035
03 南糯山记 /045
04 大雪山上的茶祖 /079
05 巨石上的曼糯山 /111
06 西定巴达:佛陀的茶园 /131
07 布朗山记 /149
08 布朗山续记 /175
09 忙糯的香炉 /203
|
| 內容試閱:
|
四
一辆运载钢筋的卡车开上山来,其沉重、猛烈的引擎声,在午后曼糯大寨的乡村公路上就像饿虎的咆哮。山西诗人石头、岩迈和我等一行人,受不了它在身后的追随,索性走上一条分岔的草径,躬腰朝着山里行去。除了芭蕉和少部分乔木还泛着绿色,山坡上已是枯草和灰色玉米叶的王国。古茶树没有想象中那么状如密林,它们身上长着苔藓和石斛,零零星星地散布在向阳的洼地或斜坡上。香樟、榉木、栗树穿插其间,感觉就是盘腿而坐的罗汉群里多出来了一些站立的道士。
山上是清静的,就我们几个人。坡地上那些人们留下的痕迹,石砌的沟沿,树干上的刀口,人工挖出的无用的大土坑,丢弃的矿泉水瓶……也是清静的,其突兀的本质已经融入河山变异的人类的单向运动之中。荒芜,孤悬,处女地,乌托邦换身为异托邦,异托邦又沉沦为习以为常的人人得而诛之的热土。无论你有着怎样的出世之姿,有着怎样的铁石心肠,你都很难无视人们对一片片净土的剥皮抽筋和毫无节制的榨取。所以,当你发现那轻微的人与山峰之间的擦痕,人因为劳作的艰辛而对土地报以的一出出小小的恶作剧,你肯定不会站在河山雄阔的立场上对人们进行偏执的审判。一切都是清静的,当我们坐在枯草丛里眺望勐往平坝上待收的甘蔗林、反光的池塘与房顶、乡村公路上飞奔的车辆时,进入眼帘的万事万物也是清静的。包括头顶上的云朵,耳畔与芭蕉叶上若有若无的风,烈日与流水,洞穴与高丘。
我曾经到过北方、江南和沿海地区不少的小镇。在这些小镇所印制的地方性文字读物中,无一例外地会列数它们史上文治武功的风流人物、风云际会的史诗性舞台和笔墨反复点染的自然奇观,目的均是为了将一个小地方扩充为时间的故宫或重现小镇往昔一瞬即逝的某个神迹。自满与自傲的文字中间有肃穆、庄严的精神史,但往往也尘土飞扬,处处结了蛛网,腐朽的气息迷雾一样弥漫着、升腾着,对应着现实世界中无处不在的平庸与低俗。在使用文字的过程中,人们一方面破旧立新,敢于与天斗与地斗,孔庙遗址上建宾馆,祖坟之地修社区;另一方面又拒绝赞美这一切海市蜃楼般的物质天堂,频频地转过身去,让灵魂回归农耕文明时代的不复存在的古老家园。热爱的,就是鄙视的;拆除的,就是珍怜的。人们置身于一座座自己与自己决斗的广场上、深渊里。但是,无论那些文字如何的虚拟与粉饰,人们记忆中那一个个天堂里的小镇,作为历史中枢的小镇,再也不可能因为仿古建筑业的勃兴而恍兮惚兮地拔地而起。拆除即终止,倒塌即消失,因为人们早已魂不附体,所作所为皆是灾难性的梦游与自焚。
顺着岩迈指示的方位,在阳光与云朵交织的景象中,我和石头隐隐约约地看见了曼糯山中和山外三条闪光的河流。曼糯山与澜沧山之间的那条名叫“南点河”,释迦牟尼用手杖疏通的河流;坝区里那条名叫“南往河”,释迦牟尼种满稗子的河流;我们正在前往的、已经听得见水声的这条名叫“南叫河”,最宝贵的水,是从释迦牟尼脚趾间流出来的河流。小说家苏童在一次论坛上说我是“狂热的地方主义者”,我欣然接受了这一对我的戏谑性的角色定位,尤其是此时此刻,当我置身在这样的三条河流之间,感觉自己进入了那四条河流护卫的天堂。南无阿弥陀佛。岩迈不需要撕裂自身就安身立命于现在与过去融通的茶树林中。南无阿弥陀佛。我和石头不需要去陈述性的文字中间寻找镇静剂,就可以看见未来的时空里已经高悬着无数诱人的发光体。
我们气喘如牛,要去拜访的就是南叫河。它在一条整体山脉突然凹陷进而形成的幽森的山峡中。山峡两边的坡地像一本静谧的翻开的经卷,朝南的页面上耸立着巨石,一棵棵麻栗树、大青树伸着曲曲弯弯的苍老枝条;朝北的页面则已改造成台地,秋收之后,稼穑退隐,杂草和长着白穗的山茅草显示着土地未经改造前的面貌。河面的闪光点断断续续,大部分的空间被山茅草、构树和藤蔓所遮掩。那偶然形成的小瀑布,远远望去,像谁家娇野的媳妇在山涧中洗衣晾晒在岩石上的被单或白裙。我们看见了河流,可这一箭之远的距离,在沟壑间上下起伏,行走起来是如此的遥远,甚至多次偏离了方向。这正如曼糯山上原来信仰原始宗教的布朗人,当他们的祖先在天地之间塑造出了80多个鬼神并虔心敬拜之时,南传上座部佛教却给他们的祖先带来了让鬼神遁迹的另外的光,而他们的祖先也欣然地接受了这“文明的宗教”。自明朝中后期开始建庙、赕佛,把本来由原生诸神和众鬼掌管的万物心悦诚服地敬献给释迦牟尼,痴迷地朝着光源处匍匐行进,历经了数百年的往生、超度与再生,他们的祖先以及他们以为自己就此生老病死在了人类梦想的终极之处,生命永远隶属于通往释迦牟尼的那一条小径。然而,那一场文化浩劫并没有漏掉这片山野,寺庙被拆毁了,老佛爷还俗了,菩萨被扔到了密林的深处,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徘徊在通往寺庙的那一条条小径上。是继续向推倒的菩萨垂首,还是将统称为“代袜么·代袜那”的山神、水神、棉神、火神、寨神、木神、鬼神、谷神、保护神、天神、猎神、船神和路神等众善之神一一请回?1995年,有几个人从四川和贵州来到了曼糯山上,带来了即将洪水滔天的世界末日的噩讯,也带来了耶稣将派直升机来将人们接到天堂去的喜讯。当时曼糯大寨90户左右的人家却在徘徊之中抽身相信了噩讯与喜讯,因为有“兄弟姐妹”帮忙干活,人们将所有的家畜、农具和粮食都卖了,加入了世界末日前的狂欢并静候着蓝色天空里飞来一只只天堂鸟……
直升机并没有从天而降,上帝在这种以其之名而展开的带有迷信与幻觉色彩的宗教行动面前始终保持了沉默。所以,随着那几位“传教士”作鸟兽散,像做了一场美梦,人们醒来之后,第一眼,看见的仍然是环绕山峰的三条河流和释迦牟尼应许他们的一片片茶园。
五
去南叫河的路上,长期在五台山一带行吟的石头,按照其惯于独行的秉性,在距河流所在山峡一公路处的岔路口停了下来,四面望望,选择了刺藜交错的那条草径,一个人循着清冷的水声,消失在了几棵泡桐树的后面。岩迈虽然祖上是“龙头”,世袭似的做了村民组长,可他的汉语远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流利,与我在山道上做喘息式的交流,越发显得费劲、艰涩,所以,他尽可能地回避我的诸多提问。当我们来到相对宽敞、没有沟壑和树木遮蔽的山峡的边坡上,他的脚步哐啷哐啷地有力,朝着河流就是一阵向下的奔跑。而我只需望着他的背影行走,不再次迷路就可以了。
距河流近了,山上的一条条小径逐渐汇聚到一起,形成一条脚印重叠、路幅加宽、路面结实光滑的道路。道路两边,开垦出来的耕地上种着油菜和荞麦,在油菜与荞麦的中央,偶尔会有小屋那么大的巨石,而每一块巨石旁,也照例会有用木棍支起来的祭台,一个个盛祭品的竹篓因为祭日未至而空着,只有竹竿上悬着的黄色经旗在微风里轻轻拂动着。不难理解,在信奉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同时,其实布朗人仍然没有彻底丢开万物有灵的宗教观,繁杂的有着具体指向的俗务促使他们一直有求或感恩于原始宗教中掌管具体事务的众多鬼神。比如住在石头里的山神可以让这片荞麦丰收;比如木神可以让树木笔直地生长,使之成为房屋的栋梁;而水神负责灌溉又得祈求它千万别将整条河流带到一片有限的耕地上来。
南叫河上,人们用几根圆木和几十片木板搭建了一座桥。河是一条小河,从山峡里的石砾与灰泥间流淌下来,水并不清澈,其平稳的河床上淤泥冻结了碎石,呈灰白状。岩迈沿着朝南的页面继续攀登,我站在桥上10多分钟,无所思,亦无所想,只觉得它与南糯山、布朗山和勐宋山众多的溪流并没有什么不同,甚至难以与那些落满鲜花的溪流相提并论了。不过,这说的当然只是外象,当一条河流通往神灵,来自释迦牟尼的脚趾间,它即使流淌着肉眼里的滚滚浊流,必然也会汇聚成甘甜的牛奶海。之后,我扒开河岸上已呈败象的山茅草、枯藤,踏着泥泞,走到河边并蹲了下来,用手掠水,本想洗洗脸上的汗渍,一转念,又没洗。这也才发现,南叫水的水其实是清澈的,无尘的,我所看见的灰白色,不是来自水本身,而是来自河床的淤泥与石砾。
在一块有三层楼高的巨石下,我赶上了岩迈。在旁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我用衣角擦着汗水,见他把鞋子脱下,放到草丛里,赤着脚就去到了巨石下方。巨石所在处是一个有着50度左右的斜坡,四周全是几百年上千年的榕树,它们撑开的古老树冠互相组合在一起,将天空隔在了更高之处。因此,巨石显得阴暗,裹在一层厚厚的苔藓内,有几束偶然透过树荫的阳光照射其上,倒像是它自身有着几个灯孔,向外喷射出几根光柱。我一点儿也不觉得突然,赤着脚的岩迈,一脸虔诚,闭目,合掌,在巨石下跪倒,头颅垂入草丛,口里似乎还念诵着什么。时间持续了10分钟左右,他站起身来,这才招呼我脱鞋走过去。巨石的下面有一口水井,他一边用竹瓢舀水,一边说,这口井里的水永远保持在同一个水位,谁也舀不完。他没有明确告诉我那是南叫河的源头,但我认定了那是源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