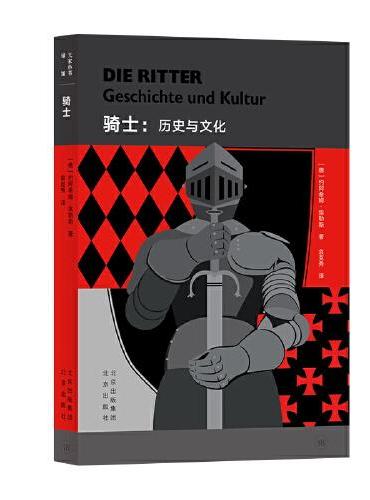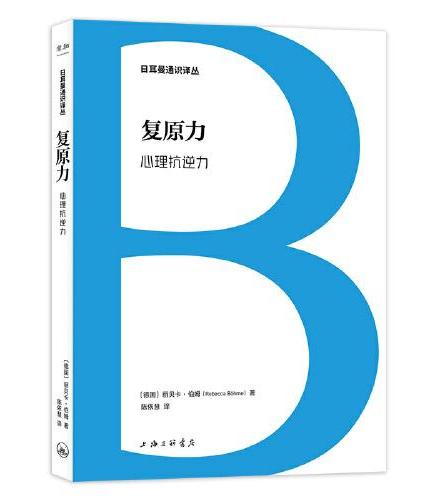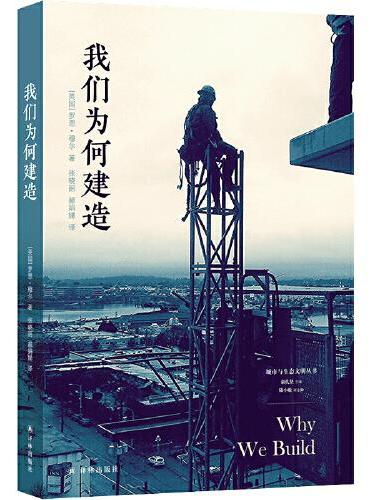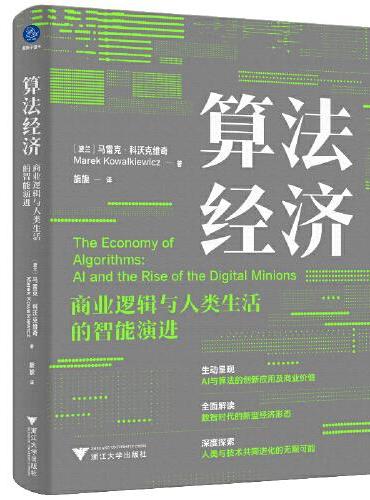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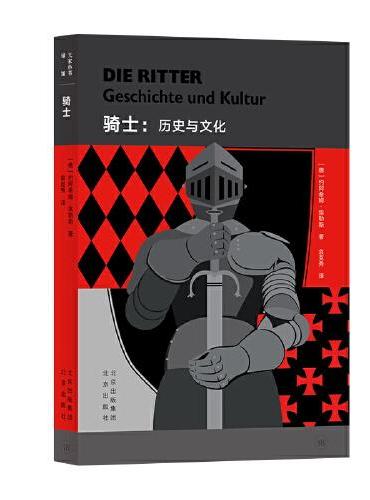
《
大家小书 译馆 骑士:历史与文化
》
售價:HK$
56.4

《
没有一种人生是完美的:百岁老人季羡林的人生智慧(读完季羡林,我再也不内耗了)
》
售價:HK$
5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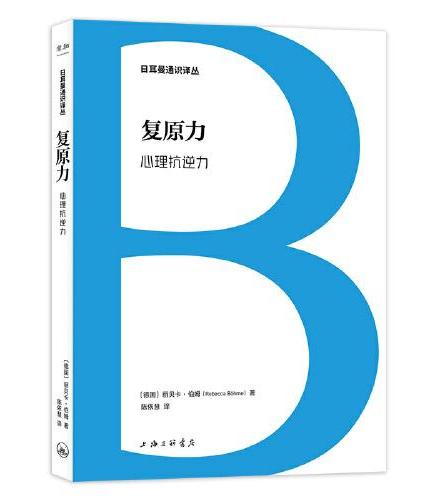
《
日耳曼通识译丛:复原力:心理抗逆力
》
售價:HK$
34.3

《
海外中国研究·未竟之业:近代中国的言行表率
》
售價:HK$
13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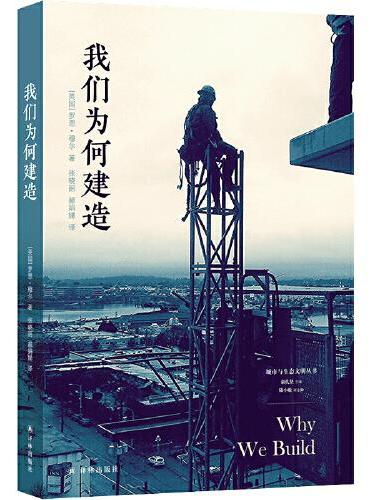
《
我们为何建造(城市与生态文明丛书)
》
售價:HK$
8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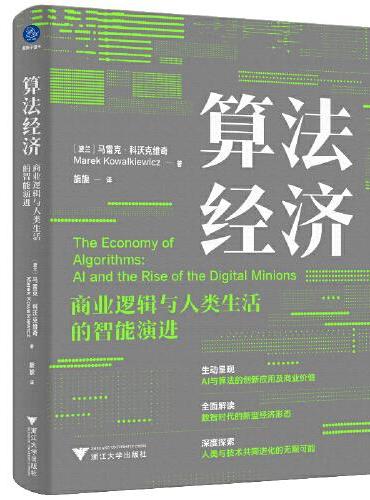
《
算法经济 : 商业逻辑与人类生活的智能演进(生动呈现AI与算法的创新应用与商业价值)
》
售價:HK$
79.4

《
家书中的百年史
》
售價:HK$
79.4

《
偏爱月亮
》
售價:HK$
45.8
|
| 內容簡介: |
对梁人来说,他们的时代充满了崭新的开始,“新变”,及能量充沛的创举。他们生活在现下,完全沉浸于“此时与此地”,投入地经历每一个时刻。他们在智识上极为精微渊雅,精神上却又相当天真。对梁朝的文化精神好的概括,不是“颓废”,而是“康强”。
梁朝覆灭之后已经过去了许多个世纪,它光辉灿烂的文化成就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份重要的遗产,但这又是一份让人感到不安的遗产,因为它和当代文化政治纠结在一起,展示了一些长期以来存在于中国文化中的问题。曾经一度数量庞大的文本现在只有零星的残存,南方帝国的辉煌就隐藏在这些断简残篇之中,后人从自己的目的出发对之进行诠释,这些带有隐含的动机与偏见的诠释更加扭曲了它们的光芒。
——田晓菲
在烽火与流星照耀下的国土,一半隐藏在阴影里,这正好是对萧梁王朝的好象征。本书试图为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勾勒一副肖像画,不仅探讨梁朝的文学作品,更旨在检视梁朝文学生产的文化语境,就此提出一系列具有内在关联的文化史和文学史问题。
|
| 關於作者: |
|
田晓菲,1971年生于哈尔滨,在天津长大,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中国文学教授、哈佛东亚地域研究院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古文学和文化、书籍史及比较文学。著有《秋水堂论金瓶梅》(2003)、《“萨福”: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2004)、《赭城》(2006)、《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2007)、《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中国的行旅写作》(2011)、《赤壁之戟:建安与三国》(2021)等。参与撰写《剑桥中国文学史》《牛津中国现代文学手册》,合编《牛津中国古典文学手册(公元前1000 年—公元900 年)》并执笔其中部分章节。2012 年度获哈佛大学卡波特奖。
|
| 目錄:
|
引 言
章 梁武帝的统治
登基之前的岁月
想象的族谱
梁朝的政治文化
“皇帝菩萨”
后的岁月
第二章 重构文化世界版图(上):经营文本
文本生产与传播
书籍收藏与分类
文学与学术活动
第三章 重构文化世界版图(下):当代文学口味的语境
“文化贵族”的兴起
文学家族
虚构的对立
萧统和萧纲:个案研究
梁代的文学口味
第四章 “余事”之乐:宫体诗及其对“经典化”的抵制
刘勰的焦虑
博 弈
体痈:关于徐摛
北人的裁决
“主义”的陷阱:解读徐陵《玉台新咏序》
春花飘落始自何时?
断桥与六尘
第五章 幻与照:六世纪新兴的观照诗学
蜡烛小传
梁前关于灯烛的诗文
洞察现象界的真谛:佛教的“观照”
观照的诗学
水,火,风:体验幻象
烛光下的棋盘
第六章 明夷:皇子诗人萧纲
少年时代
年轻的雍州刺史
人生的转折点
春宫岁月
感知与再现
末 年
第七章 “南”“北”观念的文化建构
南北之争
征服者的文学观
想象北方:边塞诗的诞生
造作的雄健:“北朝”乐府
采莲:建构“江南”
表演女性:吴声与西曲
第八章 分道扬镳
幸存者的回忆录之一:颜之推
幸存者的回忆录之二:沈炯
幸存者的回忆录之三:庾信
尾声之一:杨柳歌
尾声之二:真正的结局
结语/ 劫余:梁朝形象的浪漫化
参考文献
|
| 內容試閱:
|
造作的雄健:“北朝”乐府
北方的雄健形象,在一组所谓“北朝民歌”中得到加强。这些歌诗其实属于“梁鼓角横吹曲”,收入僧人智匠(约六世纪中后期)的《古今乐录》,保存在《乐府诗集》中。鼓角横吹曲乃“军中之乐”,在朝廷仪式中,或者作为皇家仪仗队的一部分,由宫廷乐师在马上演奏。鼓吹有时也作为高级荣誉赏赐给诸侯王或大臣。
现代学者往往继承传统说法,极力强调这些乐歌的“北方性”,把它们视为北方特质以及北方少数民族精神的反映,与南方温柔细腻的汉文化形成对比。这种二元对立观却没有考虑到这些乐府诗的音乐分类在歌辞的选择中起到的作用。换句话说,“鼓角横吹曲”既是军乐,自然一定要歌咏战争、武勇和对兵器的热爱,因此,被包括在“鼓角横吹曲”中的乐府也就不宜被视为“典型北方音乐”的代表。
在我们详细分析这组乐府诗之前,需要强调两点。,对很多歌诗的来源我们不能确知(有些很有可能的确来自北方),也不打算勉强论证这些乐歌“实际上”都是由南方乐师创作的。本节的重点,在于探讨南人在选择、演奏、保存和传播这些乐府的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简单地把这些乐府当成“北歌”处理,而必须认真考虑南人的中介作用,这在传统文学史叙事中是一个被忽视了的问题。归根结底,我们不应该追问这些歌到底是北歌还是南歌,而应该问为什么南方人要选择在南方的宫廷演奏这些歌。第二,音乐和歌词的问题应该区别对待:即使这些歌诗的音乐可能来自北方,歌辞本身却不一定来自北方。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没有确定不疑的文本依据证实这些乐府的来源。
因为梁鼓角横吹曲充满北方地名,有些学者试图以此来证明这些乐府来自北方。但是前文对边塞诗的讨论已经告诉我们在诗中运用北方地名不能证明任何东西,从未去过北方的南方人照样可以写出以北地为背景的诗篇。“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常常被人用来当作鼓角横吹曲源自北方的证据,但这两句诗引发了很多问题。在南北朝时期,没有哪个北方人会以“虏”自称,因为这是汉族对非汉族、南人对北人的蔑称。有的学者以为这首诗是从鲜卑语翻译成汉语的,汉语翻译者因此选择了一个贬义词来翻译鲜卑歌者的自称。这一解释不是完全没道理,但是只引发了更多问题。为什么一个鲜卑歌手要唱出这样的句子?这首歌的基调是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自豪和对汉儿的蔑视,还是对自己“不解汉儿歌”感到自卑与焦虑,还是遥望洛阳的孟津河,看到“郁婆娑”的杨柳,与北地家园形成对比,从而产生望乡情结?我们可以为这首歌设想出很多种语境,但是没有一个标准答案。重要的是问一问:在众多北歌中,梁朝乐师为什么特地选择这首歌为梁朝贵族演奏?南方人为什么喜欢听到“虏家儿”“不解汉儿歌”的宣言?如果梁人把这首歌理解为鲜卑歌手自豪的宣言,为什么还要把它包括在梁朝的军乐里?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虏家儿”虽然不解“汉儿歌”,汉儿却可以理解“虏儿歌”,并从而感到一种文化优越性。这也许正是南人要把这首歌包括在鼓角横吹曲里的原因之一。归根结底,这些歌是否“来自”北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认识到它们是“关于”北方的:它们代表了梁朝人对北方的想象,对“典型北方人”的想象。
《古今乐录》编于568 年,因此568 年是这些乐府的创作下限。但除此之外我们对这些乐府的创作年代一无所知,可以基本确定创作年限的是《高阳乐人歌》—如果我们可以相信“高阳”乃是智匠所说的北魏高阳王元雍(?—528)的话。汉代宫廷乐师李延年据说曾经受到西域“胡曲”的影响,“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以为“武乐”,时至魏晋,仍有十首流传。其中《折杨柳》和《陇头》二题都出现在梁鼓角横吹曲中。无论如何,我们在阅读这些乐府时应该记住,这些歌从曲到辞,哪怕是同题歌辞,都未必来自同一个历史时期或者出自同一个人之手。
下面,我们且来具体检视一下梁鼓角横吹曲中的一些曲辞,以见鼓角横吹曲的来源混杂,未可简单地以“北歌”一概而论之。
梁鼓角横吹曲的曲题为《企喻》,共四章。“企喻”通常被视为鲜卑语的音译,也曾出现在北魏宫廷乐《真人代歌》里,只是我们不知道同题梁曲的歌词是否与《代歌》重
合。《旧唐书·乐志》言:“梁乐府鼓吹又有大白净皇太子、小白净皇太子、企喻等曲。隋鼓吹有白净皇太子曲。与北歌校之,其音皆异。”“音异”可指音乐的改变,也可指歌辞的改变。
下一曲《琅琊王歌辞》共八曲,第八首云:“谁能骑此马?唯有广平公。”《乐府诗集》卷二十五称广平公为姚弼(?—416),然考四至六世纪之间曾有数位广平公,未详孰是。《琅琊王歌辞》首描写一个男子对其武器的热爱:
新买五尺刀,悬著中梁柱。
一日三摩娑,剧于十五女。
这种夸张的阳刚色彩,建立在对沉迷于醇酒妇人的“孱弱”男子形象进行颠覆的基础上,很容易就可以拿来代表南人想象中的“典型北人”。然而,我们同样不难想象,一个善于戏剧化地表现雄豪之气的南方诗人如吴均,可以轻而易举地写出这样的歌辞来。
在没有其他佐证的情况下,仅仅从文本上来看,我们往往很难分辨《琅琊王歌辞》的来源,比如第二首:
琅琊复琅琊,琅琊大道王。
阳春二三月,单衫绣裆。
“阳春二三月”的字样在南方乐府中极为常见,比如系于谢尚名下的《大道曲》就是以“阳春二三月”开始的。这让我们对《琅琊王》的曲名发出疑问。在东晋南朝,当人们听到或者看到“琅琊王”一词,直接的联想恐怕不是别个,而是“琅琊王氏”。另一方面,“琅琊王”也可以指称诸侯王。虽然琅琊在江北,但是在南北朝时期,“琅琊王”引起的联想还是主要与南方相关。东晋诸帝,包括晋元帝在内,有六位在登基之前都曾被封为琅琊王,在这一时期,皇子被封为琅琊王可以说具有相当的政治重要性。所以,我们实在不必像有些学者所做的那样,努力在北朝寻找琅琊王的踪影,何况北方原本也找不到那么多的琅琊王。即如投奔北魏的司马楚之(?—464)被封琅琊王,还是因为他的晋朝宗室背景。北魏的另一位琅琊王元绰,是535 年受封的;北齐的琅琊王高俨(557—571)则是569 年受封的。从时间上来看,他们不太可能是梁鼓角横吹曲中《琅琊王》一曲的始作俑者。
下一曲《钜鹿公主歌辞》,题下三曲,每首两行七言,读起来比较像是一首歌的三节,而不是三首独立的乐歌。《旧唐书·乐志》没有解释它们为什么“似是”姚苌(330—394)时歌,但特别强调“其辞华音,与北歌不同”。
下两曲均题为《紫骝马》,但智匠称后曲“与前曲不同”。我们现在仅从曲辞上已经不大容易看得出两曲的差异(都是五言四句),只能推测说,差异大概表现在音乐或演奏方面。关于《紫骝马》有两点值得注意。一,前曲六章,后四章“十五从军征”云云读起来好似一首十六句的五言诗,有清楚的叙述脉络;相比之下,后曲是一首简单的情歌,与无数南方乐府极为相似。二,《紫骝马》这一乐府诗题在梁朝开始出现于宫廷诗中。萧纲、萧绎兄弟都曾以此为题赋诗,萧纲的《紫骝马》乃《和湘东王横吹曲三首》之一。梁鼓角横吹曲中的《紫骝马》,从乐曲到曲辞,都未必起源于北方。
下一曲《黄淡思》,曲名意义难晓。智匠怀疑“黄淡思”源自“黄覃子”,李延年所造曲之一。《晋书》记载了一支四世纪时流传于荆州的乐曲,题为《黄昙子》。《黄淡思歌》都是情歌;其中第三首则描写了一艘豪华的广州龙舟:“江外何郁拂,龙洲[按洲、舟在中古汉语里乃同音字]广州出。象牙作帆樯,绿丝作帏繂。”
《东平刘生歌》仅三句:“东平刘生安东子,树木稀,屋里无人看阿谁。”据《乐府诗集》卷二十四:“《乐府解题》云刘生不知何代人,齐梁已来为《刘生》辞者,皆称其任侠豪放,周游五陵三秦之地。或云抱剑专征,为符节官,所未详也。按《古今乐录》曰梁鼓角横吹曲有《东平刘生歌》,疑即此《刘生》也。”南朝乐府《西曲歌》中有《安东平》曲:“东平刘生,复感人情。与郎相知,当解千龄。”(这里的“东平刘生”可以视为刘生其人其事,也可以视为曲名)“东平刘生安东子”和《安东平》曲分明有渊源关系,而且,从现存资料来看,对《刘生》这一乐府诗题的兴趣是从梁朝才开始的。谭润生因为《刘生》作者多为梁、陈人,又因为梁元帝《刘生》把刘生描写为长安游侠儿,所以断定此“刘生”非鼓角横吹曲中的“东平刘生”,实则东平刘生又何必不能周游长安,又何况所谓的东平刘生本来就可能是传说人物呢?《刘生》作者几乎全都是南方人,正好说明“东平刘生”本是南方诗歌题材。
梁鼓角横吹曲又有《折杨柳歌辞》五曲与《折杨柳枝歌》四曲,前文所引“我是虏家儿”即其中之一。其首,“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蹀座吹长笛,愁杀行客儿”,《旧唐书·乐志》记载略有不同,并云“歌辞元出北国”。然而乐府旧题本有《折杨柳行》,可以上溯到公元二三世纪。《晋书》提到西晋太康(280—290)末年京洛流传《折杨柳》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辞,终以擒获斩截之事”。南方乐府的《西曲歌》中《月节折杨柳歌十三首》,每首都有“折杨柳”的迭句;《读曲歌》中也可见到“折杨柳”字样。可见《折杨柳》恐怕只有在“源出中原”的意义上才能说是北曲。
《幽州马客行》可能是另一乐府旧题。保存在《艺文类聚》中的《陈武别传》提到休屠胡人陈武从其他牧羊儿那里学会了很多歌谣,如“太山梁父吟、幽州马客吟及行路难之属”。关于陈武的记载甚少,我们只知道他大约是四世纪人。诸葛亮(181—234)据说好为《梁父吟》;东晋时袁山松(?—401)则曾经润饰过“旧歌《行路难》曲”。《幽州马客行》共五曲,其中第三、四、五首都是情歌。谭润生在《北朝民歌》一书中把这些歌定为北歌,但相信它受到了“南方影响”,因为其中有“郎着紫袴褶,女着彩夹裙”“黄花郁金色,绿蛇衔朱丹”字样。谭氏以为这样“宛曲巧艳”的字句“已失率真之情”,并因此断定“此歌辞曾受南方民歌之影响”。这样的论点表明南方代表文化/ 北方代表自然这样的二元观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当代文化想象,以至于学者们想象出来的北方必定寒冷、荒凉、野蛮、单调,就连一点点色彩的存在都被视为南方的影响。这实在是一种无视历史事实的天真态度。
以上的分析向我们表明,梁鼓角横吹曲中包含的乐歌,从曲到辞来源都很复杂,往往难以辨别南北。但是,人们往往执着于传统观点,不去反省有些观点反映出来的文化、地域、民族与历史偏见。著名学者刘大杰的一段话很具有代表性:“北方的情感多是直率的热烈的,没有南方那种隐曲细密的手法。北方人并不是不讲恋爱,但是他们的表现方面是与南方不同的。”刘氏又引梁启超论“北歌”的话作为佐证:“他们[按指北人]生活异常简单,思想异常简单,心直口直,有一句说一句。”〔2〕事实上,不是北人“思想异常简单”,倒是这样的观点显得“异常简单”,也把复杂的社会现实与文学现象简单化了。
还有时,南朝乐府与北朝乐府之间的“差异”被理解为民族差异:学者一方面夸张了鲜卑民族的单纯、天真、“缺乏文化”,一方面把汉民族想象为羞涩、含蓄和扭捏。这样的环境决定论和民族决定论观点实际上充满了不自觉的民族偏见和文化偏见。要是我们能够抛开先入为主的成见,对现存的文本进行检视,我们就会发现这些观点缺乏足够的证据。
即如《幽州马客行》的第三首:
南山自言高,只与北山齐。
女儿自言好,故入郎君怀。
谭润生氏根据诗的、二句,即断定这是北歌,不解何故,大概是因为看到“南山”“北山”的字样,联想到了南方与北方;但这种联想,只能说明是“南方”=“女儿”/“北方”=“郎君”的传统文化想象在作祟。再说,如果北山/ 南山代表了北人/ 南人,北人歌手又何必称南山“与北山齐”呢?南人又何必认同“只与北山齐”并把这样的歌收在他们的军乐里呢?
如果说歌中情愫热烈奔放,代表了“典型”北方女子的声口,则我们可以拿这首歌比较一下系于东晋著名作家孙绰(314—371)名下的《碧玉歌》:
碧玉破瓜时,相为情颠倒。
感郎不羞难,回身就郎抱。
或者南朝乐府中的《孟珠》:
望欢四五年,实情将懊恼。
愿得无人处,回身与郎抱。
或者《前溪歌》:
黄葛生烂熳,谁能断葛根?
宁断娇儿乳,不断郎殷勤。
这后一首歌似乎歌咏的是发生于婚姻之外的两性关系:女子向情郎发誓,哪怕离弃娇儿,也不离弃情人的爱宠。这样的歌辞,其直率热烈,是丝毫不逊色于“南山自言高”一曲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首系于北魏胡太后(?—528)名下的《杨白华歌》,据说是胡太后为了她叛北入南的情人而作,歌辞充满了缠绵温存: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
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
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
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
很多学者因为觉得这不符合北方女子“直爽坚强”的传统形象,遂不得不强作解释说这是受到了南方文化的影响。然而,这种“北人必定如何,南人又必定如何”的笼统概括其实是过于简单化的思维方式。我们需要认识到,“南/ 北” 的文化形象在南北朝、隋唐时期逐步建构,渐渐深入人心,现代学者和读者对“南/ 北”所做的文化联想,无不承自这一时期。
在南北朝时期,南人出于政治需要,把北方的形象塑造为蛮荒、朴野、自然,这些价值观本身即存在褒贬暧昧之处。南人之本意,在于强调北人之疏野,以求突出南人之文明,以正统汉文化的传人自居。南人自视等同于“文化/ 文明”(culture)的代表,置北人于“自然”(nature)的地位,这正与南方贵族把南方本土社会身份低下的女子(“小家碧玉”)塑造为热情洋溢的“自然”形象遥相呼应。在这一公式里,我们可以说:
北方鲜卑=“低级”文化=“自然”=南方平民女性
南方汉人=“先进”文化=“文明”=南方贵族男子
但是“自然”(nature)本是一个意义暧昧、可褒可贬的范畴:从否定方面来看是粗疏野蛮,从肯定方面来看是质朴天然。因此,在初唐时期,作为征服者的北人接受了“自然”的定义,但着力消解其“荒蛮”的一面,强调其“质”的一面,这样一来,虽然继续把南人置于“文”的地位,文/ 质的二元对立却产生了新的意义,在“质”映照之下的“文”,已经不再是完全积极的“特权概念”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