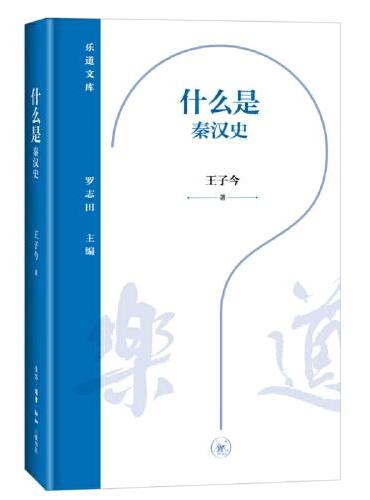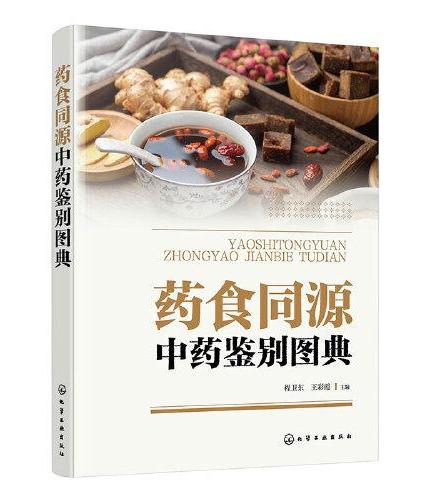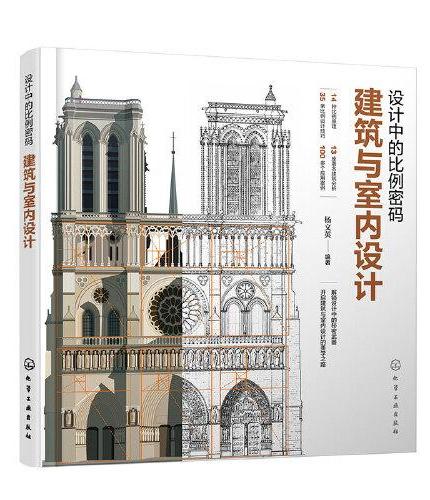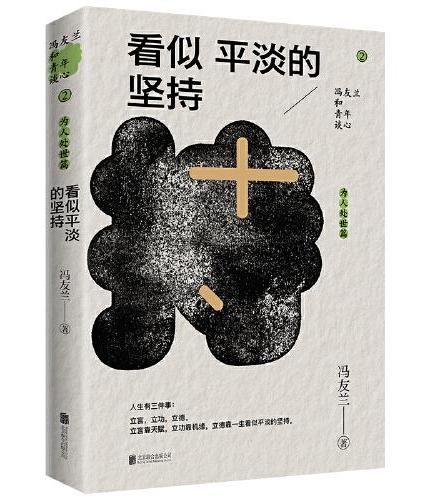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读书是一辈子的事(2024年新版)
》
售價:HK$
7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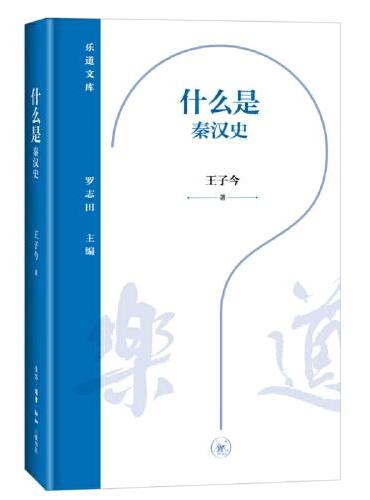
《
乐道文库·什么是秦汉史
》
售價:HK$
80.6

《
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 : 自由、政治与人性
》
售價:HK$
109.8

《
女性与疯狂(女性主义里程碑式著作,全球售出300万册)
》
售價:HK$
1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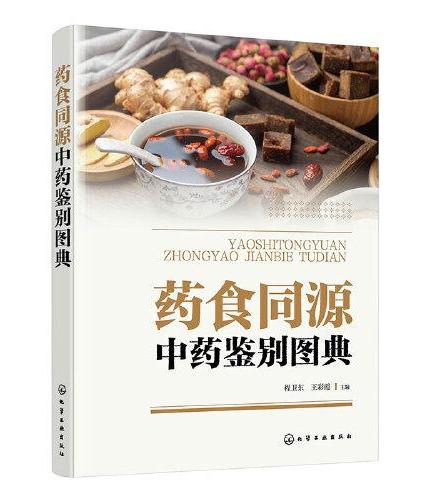
《
药食同源中药鉴别图典
》
售價:HK$
6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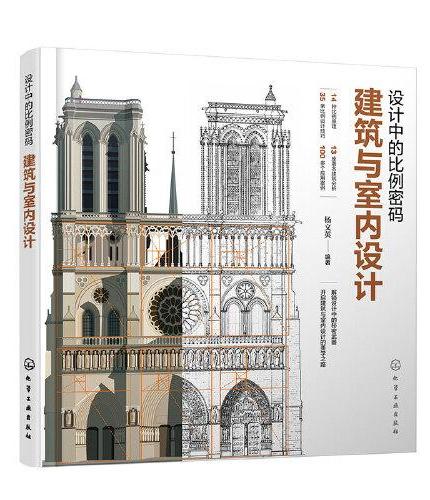
《
设计中的比例密码:建筑与室内设计
》
售價:HK$
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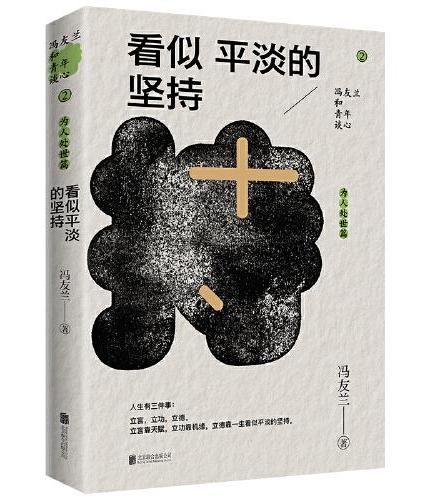
《
冯友兰和青年谈心系列:看似平淡的坚持
》
售價:HK$
55.8

《
汉字理论与汉字阐释概要 《说解汉字一百五十讲》作者李守奎新作
》
售價:HK$
76.2
|
| 編輯推薦: |
贝兰凭借广博的历史知识、强大的分析能力,理清了错综复杂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将美国内战、俄罗斯废奴、德意志帝国建立按照时间切面有机联系在一起,揭示了林肯、俾斯麦、亚历山大二世成为被历史选中的改革家的必然原因,以及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同时,作者以详实的历史细节、丰富的情景和对话描写,塑造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将三巨人的果敢无畏、深谋远虑,乃至造成改革局限的性格弱点予以充分表现。这本专攻1861—1871年改革时期的“断代史”以广博的视角、扎实的知识和生动的叙述,成为广受读者欢迎的历史普及图书。
此外,本书展示了政治、哲学和艺术相辅相成的作用,强调了时代对艺术的塑造,以及艺术对政治的影响。书中详实生动地描绘了托尔斯泰、瓦格纳、尼采、惠特曼等文化人物在那段惊心动魄岁月中的活动与见证。作者通过这些关键人物将三个国家的历史进程、改革进展糅合在一起,“每一个人物都是这篇绚丽华章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所以读起来跌宕起伏,毫不枯燥”,具有非常强的文学性。
|
| 內容簡介: |
1861—1871,在历史星河中格外耀眼。林肯、俾斯麦和亚历山大二世在各自的进改革,铸就了自由的国度,也见证了强权新哲学的兴起。
美、德、俄三国的革命都以自由之名进行,方式却迥然不同:林肯要给予美国“自由的新生”,废除了黑奴制度,为美国跃居世界头号强国开辟道路;俾斯麦以“铁血”推行强权,统一了德意志诸邦,为统一德国的崛起扫清障碍;亚历山大二世“自上而下”改革,打碎了农奴制的枷锁,使俄国走上现代强国之路。改革巨匠们以各自的风格塑造了美、德、俄,使三国走上了自由、专制、革命三条不同道路,并奠定了当今世界的格局。
贝兰理清了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内在逻辑,将美国内战、俄国废奴、德意志帝国建立按照时间切面有机联系起来,揭示了林肯、俾斯麦、亚历山大二世被历史选中、成为改革巨匠的必然原因,以及重大事件的发生规律。
|
| 關於作者: |
|
迈克尔·贝兰(Michael Beran),律师,畅销书作家,多篇文章见于《纽约客》《华尔街日报》《国民评论》等报刊,著有《胡蜂:美国贵族的辉煌与不幸》(Wasps)、《☆后的贵族:鲍勃·肯尼迪与美国贵族的终结》(The Last Patrician)、《杰弗逊的恶魔:一颗不安分的心灵》等作品。
|
| 目錄:
|
致读者
前言 三人之死
第一篇 坠入深渊
第一章 绝境边缘的三个民族
第二章 叛逆者现世
第三章 针锋相对
第四章 自由宣言
第五章 蓄势待发
第六章 暴力
第七章 烟尘初起
第八章 强弩之末
第九章 厉兵秣马,背水一战
第十章 迟恐生变
第十一章 王牌在手
第十二章 天意已决
第十三章 自由气息
第十四章 雪上加霜
第二篇 改革的高潮
第十五章 不论权属
第十六章 恐怖的大屠杀
第十七章 尘归尘,土归土
第十八章 未来斗士
第十九章 国魂不死
第二十章 那位勇者
第二十一章 权势与魅力
第二十二章 鼓声沉闷
第二十三章 奇耻大辱
第二十四章 生不如死
第二十五章 血腥杀戮
第三篇 自由与恐怖
第二十六章 走向深渊
第二十七章 时机未到
第二十八章 原形毕露
第二十九章 不成功,便成仁
第三十章 下台!下台!
第三十一章 恶魔之酒
第三十二章 新的世界已到来
尾声 得之不易的自由
译名对照表
|
| 內容試閱:
|
致读者
埃德蒙·威尔逊所著的《爱国者之血》是一部关于美国南北战争的文献,其中有这样一段,威尔逊将亚伯拉罕·林肯与奥托·冯·俾斯麦、弗拉基米尔·列宁相提并论。
19世纪,统一的动力格外强劲,并自此持续保持着强劲的势头;要理解南北战争对当今时代的意义,就该将亚伯拉罕·林肯跟其他献身类似事业的领袖联系起来……林肯、俾斯麦和列宁都是才智非凡、性格极其强韧的人物,他们既有历史的想象力,又有强大的意志力。他们都是不同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认为理想高于一切。三人都是孤家寡人,他们专注于自己的目标,一往无前。他们都不喜欢哗众取宠,无人在意声势排场:就连俾斯麦都曾经口出怨言,说自己做不了朝廷重臣,他令格兰特和其他人相信—他本人也一定真心实意地如此认为—他其实不是君主主义者,而是共和主义者。他们各自都统一了有如散沙一般的人民,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
我试图比较三位改革政治家,相比威尔逊,我的落脚点更偏重改革特征以及改革方法的区别。毫无疑问,林肯、俾斯麦和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所导致的(间接)个人经历,对我影响颇深。我的祖父卡尔·贝兰生于哈布斯堡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统治时期。他来自一个德国—捷克—克罗地亚复合家庭,上世纪初,一家人生活在奥匈帝国的克罗地亚。俾斯麦的普鲁士军队在萨多瓦击败了奥地利,为俾斯麦的改革铺平了道路。四十年后,卡尔·贝兰和家人移民到了美国。
我祖父的堂兄留在了欧洲,他亲身体验了这场改革带来的影响。约瑟夫·贝兰是一名罗马天主教神父,在萨多瓦以西七十英里的布拉格教授教牧神学。20世纪30年代,他被任命为学院的院长。贝兰的传记作者记述了1939年的一天,德国坦克的隆隆轰鸣和德国军靴的踏地声“透过沉闷的窗扇,传进了教会学校”。“这是反基督的象征。”贝兰神父平静地说,说完他继续讲课。1940年6月,他被盖世太保逮捕,1942年秋天,被送到了达豪,囚犯编号是35844。共产党领导者沃依特赫·卞凯克在他的《达豪回忆》一书中写道:“据我所知,贝兰神父是狱中秀、品格尚的人之一。”这位瘦骨嶙峋、衣衫褴褛的神父于1945年5月被释放,解救他的是美国军队—林肯改革创建的共和国所拯救的公民。感恩弥撒后,贝兰神父回到了布拉格,1946年12月,他被任命为布拉格大主教,圣维特大教堂的波西米亚都主教。后来,他遭到了俄国人的迫害—他们所服务的那个政权,倘若亚历山大二世当年改革成功的话,根本就不可能存在。1978年冬,我们全家赴苏联旅行,途中,我亲眼见证了贝兰主教晚年生活的这片土地是何等荒凉贫瘠。当时我家住在伦敦,刚读完罗伯特·马西的《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我觉得,父母是被我对俄国的好奇心打动,于是带我去亲眼看看这个国家的。
而我母亲的家庭经历却迥然不同。外祖母家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家住南七街413号—现在这所房子已经不再属于格雷厄姆家了。转过一个街角,就是南八街430号的林肯家。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伊利市,外祖母家的房子里塞满了关于林肯的纪念品,其中包括如今挂在我家客厅里的那幅总统画像。
从这个小小的方面,就能看出不同类型的政治家产生的不同影响。我父亲的亲人被迫逃离故土,我祖父的堂兄差点在集中营里丧命。我母亲的家庭在斯普林菲尔德与伊利市蓬勃兴旺,并未受到任何权力机构的侵扰。
分析现代自由政权起起落落的书成百上千,它们也描述了独裁政权的出现;但我认为,从来没有一本书特别重视1861年至1871年间的几场改革,这个十年构成了人类自由编年引人瞩目的篇章,也见证了恐怖和高压统治的新哲学的出现。
三人之死
在三位改革领袖中,有两位死于非命。
位是被一颗0.41英寸口径的子弹射穿了头骨,而后便溘然长逝。子弹穿透了大脑的软组织,在靠近一侧眼眶的地方爆开。这位美国总统被人们送到附近的一栋屋子里,第二天早晨7点刚过,他便停止了呼吸。随即,他的心脏也停止了跳动。
第二位目睹了自己肚腹被炸开,肠子横淌过大街。大块的血肉掩映在白雪中。俄国沙皇被哥萨克骑兵放在雪橇上拖回宫中后,便撒手人寰。
在这三位改革领袖中,寿终正寝的只有德意志首相,他享年八十三岁。
根据皇室和东正教的礼制,俄国沙皇的遗体被送往祖辈们长眠的墓地。然而,在圣彼得堡几乎看不到任何悲恸的迹象。亚历山大二世在世人的厌弃中与世长辞。他那革命性的政治才能,换来的却只是忘恩负义,而他的葬礼也是纰漏百出。敛尸官对着这位沙皇的遗体——或者说遗体的残余部分——绞尽脑汁,后他决定,将支离破碎的下肢切除。殡葬人员为如何处理遗体大伤脑筋,与此同时,大臣们则为另一个问题烦恼不已——大批外国政要乘坐专列,从华沙和柏林来到圣彼得堡吊唁,这些人该如何安置才好?德意志皇储竟然只能屈就住在一间画廊里。
一个更微妙而棘手的问题是来自沙皇情妇的。通常来说,沙皇的遗孀是主要的送葬人,但这一次,情况有些复杂,因为亚历山大在原配玛丽皇后去世后没多久,就跟这位情妇结婚了。第二次婚姻是秘密缔结的,加之是贵族和庶人之间的通婚,所以新娘无法得到丈夫的公开承认。在这场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当中,这位年轻的女士,叶卡捷琳娜?米哈伊洛芙娜,成了声誉扫地的一方,毫无疑问,这对她来说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因为她不是个交际花,甚至也不是一名女演员。人称“卡佳”的她,其实是俄国古代贵族的后裔。然而,尽管血统高贵,她却没有王室或皇家的血统。而在俄国,皇家成员必须与王室结婚,连沙皇的侄子亚历山大大公都说,这是“一条冷酷的法令”。相传,亚历山大曾经下定决心,打破这条陈规旧俗的桎梏:他想将他的婚姻公告于天下,让卡佳登上后座,将皇后的冠冕戴到她栗色的发间。但是,一切都还没来得及发生,他便在圣彼得堡的街头横死。
卡佳被赶到了一边,她爱人的遗体被护送着穿过人群,穿过面无表情的俄国民众,送到彼得保罗要塞,俄国沙皇的地下墓室里。卫兵和牧师,主教和神父,手持刀剑和权杖穿过整座城市。正午的阳光在圣以撒大教堂的金色穹顶上闪耀。然而,在历史的转盘上,黑暗已经降临。随着亚历山大的辞世,罗曼诺夫皇朝开始黯然衰落。
葬礼当日,卡佳蒙着厚厚的面纱,跟宫廷中的其他人一起,在冬宫宏伟的楼梯脚下等待着。她带着她的三个孩子,他们都是已故沙皇的后代。那个八岁的男孩格奥尔基,人们叫他“戈高”。旁边是他的两个妹妹,奥尔佳和卡佳。他们注视着新任沙皇——他们同父异母的哥哥——一阵风般狂奔下楼梯。亚历山大三世跟他的父亲一点都不像。已故的沙皇长相英俊,一双充满智慧的眼睛微凸。马克?吐温曾在克里米亚半岛见过他,觉得他“身材十分高挑……他是个长相坚毅,却也和蔼可亲的男子”。而亚历山大三世却恰恰相反:身形臃肿,头脑简单。他的身边站着妻子,新任皇后,丹麦的达格玛公主,一个娇小的黑发女子。光彩照人的年轻皇后从大理石地板上翩然而过。此时她全然不知自己的命运将比卡佳更加悲惨——晚年的她啜泣着坐在一节火车车厢里,眼看着她的大儿子——后一任沙皇尼基——被人带走,后来他被幽禁至死。
当沙皇夫妇走过来的时候,卡佳掀起了面纱。就在那一瞥之间,新任皇后看到了她满是泪水的脸庞。尽管依然年轻貌美——卡佳跟达格玛一样,时年三十四岁——这张面孔的主人现在却已经是个继母了。侍臣们都屏住了呼吸。亚历山大在世的时候,他坚持要达格玛和其他大公夫人像传统上对待皇后一样,对卡佳行礼。可现在,角色却对调过来。达格玛成了皇后。如果她硬要正式地伸出手,应该顺从谦卑地行礼的人就变成了卡佳。但此时,新皇后并没有坚持维护自己的皇后威严。她并不像一位皇后,而是像个普通女人一样拥抱了卡佳。有些旁观者便贸然得出结论,认为新任沙皇和皇后心地柔和,自此之后,卡佳将被视为皇室的一员。然而,新任皇后突如其来的同情,其实只是出于好心的一时冲动,而不是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这也并不意味着她真的认同了公公的情妇的身份。皇室成员们走出冬宫,登上皇家马车。卡佳并未受邀与他们同行。
马车一路驶往彼得保罗要塞,大雪纷纷扬扬。沿途列队站岗的士兵们穿着厚厚的大衣,可还是冻得直打哆嗦。纷飞的大雪中,马儿们拉着镀金的皇家马车挣扎前行。后,队伍终于抵达了要塞。在一座小教堂里,皇室成员们目睹了庄严华丽的一幕。身披黑袍的修士们手持点燃的蜡烛,吟唱着《圣经》的章节。烛光在罗曼诺夫皇室的大理石陵寝上闪闪烁烁。然而,此情此景并无已逝者的意味。亚历山大自己的人生篇章都被精心隐藏了,生亦如是,死亦如是。
只有新任沙皇似乎还想细细端详已故沙皇的遗体。人们看到,亚历山大三世一再俯身,上前亲吻父亲了无生气的双手。然后,人们将棺木封敛,放进了墓穴中。哀悼的人群依照古老的习俗将沙土和树叶抛撒进墓穴。
故去沙皇的葬礼只有冷冰冰的仪式礼节。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遭遇谋杀的总统被运往坟墓的仪式却是临时草草举行。当时群情激愤,民众的狂热甚至到了病态的地步。许多美国人渴望亲近他的遗体,适当程度的接触是允许的,或者有可能是已故总统所在党派的成员所鼓励的,因为他们知道,牺牲就是一种强大的宣传。在纽约,林肯的遗体一度被放置在市政大厅,连棺盖都是打开的,有些前来哀悼的民众会试图碰触或者亲吻这位死去总统的面庞。由于太多哀悼者带来的尘垢,遗体已经呈现出一种不自然的暗沉颜色,变得有些发黑。一位入殓师数次被传唤来,擦拭掉总统面上覆盖的油脂,将严重下垂的、几乎包不住牙齿的下巴合上去。遗体已经变得不像样子了。
然而,单纯朴素的乡下人挽救了这种局面。火车载着总统的遗体,飞驰着穿过乡村,春天的花朵正在盛开,在远远的交叉路口,在孤独的小村庄里,在荒芜的农场边缘,美国民众站在铁轨边,向被害的总统致敬。许多人用手帕抹着眼泪。妇人们的怀里抱着婴儿。小学生们手里握着镶黑边的美国国旗。在煤气灯照亮的火车站站台上,成群的少女围在一起唱赞美诗;她们穿着圣洁的白色衣袍,胸前垂下黑色的肩带。有些哀悼者拿着手写的标语牌:“向值得敬佩者致敬”“英雄烈士”“华盛顿,国父;林肯,国之救主”“人虽死,言犹在”。
联邦政府专门征用了一节火车车厢来运送林肯总统的遗体。林肯生前就常常乘坐这节车厢;它装饰得相当舒适,有一间会客室和一间卧室。为了安放他的遗体,车厢已经罩上了黑纱,所有窗子都挂上了黑色的窗帘。护送总统遗体的,有总统的家人、朋友、高官,还有来自美联社、《纽约时报》、《费城问询报》、《波士顿每日广告报》和《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深夜,列车穿过纽约州中部,车上的人都被等着一睹总统灵柩的群众的数量震惊了。在孟菲斯和沃伦斯的小镇上,哀悼者们手持火把站在路旁。凌晨3点钟,火车到达了罗切斯特,遇到了市长和大批民众。
不久,已逝的总统就来到了伊利诺伊州。一个标牌上写着“回家”,另一个写着“安息”。在芝加哥停留之后,列车穿过大草原,来到了斯普林菲尔德——这里是伊利诺伊州首府,林肯总统的故乡。人们把他的遗体带到议会大厦,在那里供公众彻夜瞻仰吊唁。第二天中午,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灵柩被抬下台阶,放入灵车。众多哀悼者开始吟唱——
天主的孩子们,前行路上温柔歌唱:
赞颂救主的丰功伟业、万丈荣光。
我们正沿着父辈们走过的路途,回到主的身旁:
我们即将目睹,他们如今何等喜悦欢畅。
灵柩被运到橡树岭公墓,放置在石灰岩的墓室中。
在这三位改革领袖中,只有德意志首相免于死于非命。这未必是一种福气,因为奥托?冯?俾斯麦同样饱尝了死亡的痛苦。林肯和亚历山大都是在权力骤然殒命的;只有俾斯麦活到了功成身退,了解到被历史抛弃是一种什么滋味。新德意志皇帝的登基,为他的高官盛誉画上了句号。俾斯麦一手打造了这个帝国,威廉二世刚刚戴上皇冠,就急于除掉国中的这个老臣。这位年轻而独裁的皇帝神经质的兴奋、变化无常的想法、轻率不得体的演说——半是路德教会的布道,半是专横凶暴的长篇大论——给一名观察者留下了“癔症患者的印象”。沙皇尼古拉二世,被谋杀的亚历山大沙皇的孙子,也是个蠢货,人称“威廉的表弟”。“他简直是疯了!”尼古拉大叫。
俾斯麦从权力跌落,无法再认真对待这位疯狂的皇帝。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对一位君主屈膝是件危险的事,特别是像威廉这样易怒的君主。年轻的君主顽固不化,他的军事演习和计谋都一无是处,这一点俾斯麦明白得太迟了。新皇帝刚愎自用,骄傲自负。他佩戴黑鹰和骷髅徽识,自诩普鲁士军国主义的象征。他还有一个同样令人不安的习惯:他竟然喜欢抚弄卫兵的小胡子,卷起卫兵的胡子梢。但是,军旅精神只是造成威廉脾气古怪的部分原因,在这位耀武扬威的军人脑袋里的某个地方,骄傲退却了,他变成了一个小心翼翼的艺术爱好者。在波茨坦洛可可风格的宫殿里,阅兵场上的死板严苛消散无踪,来访者们惊奇地发现,他变成了一个细腻敏感、酷爱艺术的年轻人。
俾斯麦一生克服过许许多多困难,但是要搞定一个穿着长筒军靴的审美家,哪怕他再足智多谋,恐也力所不及。某天早晨,年轻的皇帝出现在位于柏林的首相府邸门口。他要求知晓俾斯麦的行动。首相从床上爬起,满心郁闷地走下来。“俾斯麦大概只得如此,”威廉说,“他得克制自己,忍着不把墨水瓶砸到我脑袋上。”俾斯麦并没有朝他扔墨水瓶;他将自己的恶意用一种喜欢的小花招表达了出来。他丢下一只公文包,然后假装不想让皇帝看到其中一份文件。这下子不知所措的变成了威廉。他的好奇心战胜了矜持,一把从首相手中抓过那份文件。从那份文件中,威廉得知,俄国沙皇长篇大论地谈他,称他为“一个不讲信义的蠢货”。
俾斯麦表达了他的观点——但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不久之后,他就被从办公室赶了出去,他怀着苦涩的心情登上列车,离开了柏林。“荣光无限的国葬。”他注视着窗外士兵们身上的羽饰、头戴的鸵鸟羽毛说道。一开始他还确信,政府一定会气急败坏地请他回去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召令却始终未下达。这位老人一直梦想着能够重回威廉大街——柏林的权力中枢。他筹谋规划,但是他的野心失去了效力。俾斯麦的晚年是在徒劳无益的愤愤不平中度过的。他虽然被困在轮椅上,可身体的虚弱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头脑。他的思路依然无比清晰,直到后他都沉浸在仅剩的一点欢愉,就是仇恨当中。后回光返照时,他用力挥舞一只手。“那,”他宣称,“绝无可能,基于国家理念。”这位政治领袖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曾经制定和打破过太多规则,或许他期望可以通过这种宣言来逃避死亡的命运。
若他真的这样想,那他的确未能成功。六个小时之后,他溘然长逝。
三人之死迥然不同,但三位领袖的一生被一条共同的线索联系在了一起。在短短十年之间,他们解放了千百万灵魂,重建了自己广袤的祖国,并永久地改变了国家的政体。
林肯解放了一个被奴役的人种,改造了美利坚合众国。
亚历山大斩断了禁锢农奴的锁链,给俄国带来了法制。
俾斯麦推翻了狭隘的日耳曼众王,打败了奥地利皇室,终结了拿破仑的帝国,令德意志实现了统一。
三人铸就了20世纪争夺世界霸权的三个超级大国。他们也为人类的自由做出了巨大贡献。作为三人中影响力小的一位,俾斯麦理清了征战不休的国家的一团陈旧腐朽的乱麻——当时整个国家到处是公国和独立领地——并令这片凋敝已久的土地繁荣昌盛。林肯和亚历山大解放劳工的行为正像史册记载的一般伟大。1861年初,俄国境内有2 200万农奴。同一时期,美国有超过400万男女及儿童奴隶。十年之后,他们都被解放了。
自由的国度是如何铸就的?自由的国度又是如何瓦解的?林肯称他的改革是“自由的新生”。俾斯麦曾提及改革是通过“铁与血”来实现的。亚历山大实施了一场他称为“自上而下的”改革。他们的改革都是以自由之名进行的,不同程度上促进了人、物和思想更自由地流动。他们的改革在不同程度上都基于18世纪英国改革的基本原则——正是这些原则使得英国在当时成为有史以来为自由、为繁荣的国家。就连对英国的自由理论嗤之以鼻的俾斯麦,也深谙贸易自由的好处,虽然他本人绝非一个自由贸易主义者。在他当政时期,工业蓬勃发展,鲁尔区的矿山和烟囱为他治下的社会提供了煤炭和钢铁,成就了德意志的繁荣昌盛,这比“铁与血”更加重要。
自由的新机制,尽管肇始于英国,却通行于全世界。它的核心理念是,上帝赋予所有人基本的尊严,虽然这一理念在现实中尚未完全实现。对这一真理,亚伯拉罕?林肯笃信不移,他认为它“适用于任何人、任何时期”。在19世纪的头几十年,这一自由机制有望像蒸汽机——该时代另一项开创性的发明——一样出口海外。所有人都拥有生存、自由和享受工业成果的权利,这一信念在德意志的莱茵河、俄国的涅瓦河、美国的波托马克河和英国的泰晤士河两岸被迅速唤醒。
接下来,一些事情便水到渠成地发生了。
在三位改革伟人对自由国度开疆拓土的十年间,其中的一位成了自由国度的敌人,还有一位变得心灰意冷。正是在此时,诗人马修?阿诺德声称,热爱自由国度的人们“迷失了未来”。林肯曾说,自由的“萌芽”将会“成长和扩大为全世界人类的自由”。然而,这萌芽却在世界性的灾难中几近夭折。在这场全球危机中,自由国度受到了强权政治的新思想的挑战。林肯称,这种思想的道德词汇出自“豺狼词典”。在这十年间,人们见证了自由的胜利,也见证了反革命运动的兴起,时至今日,这场运动依然影响着世界。
这就是那十年发生的故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