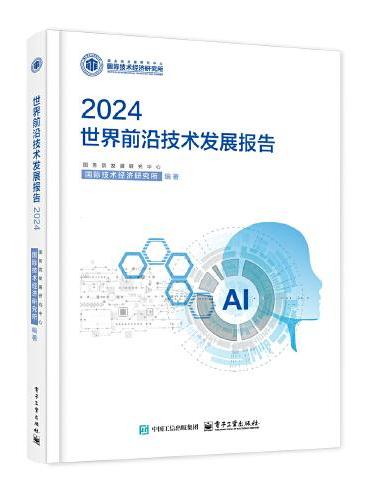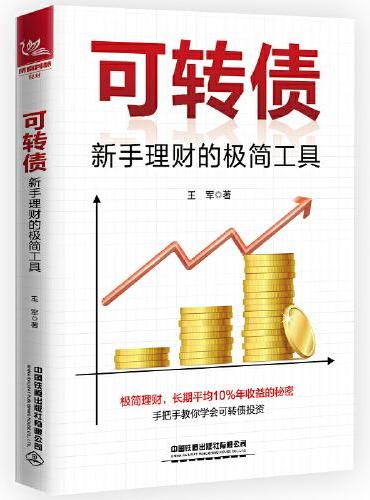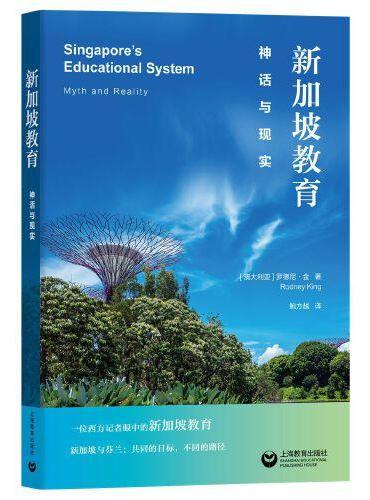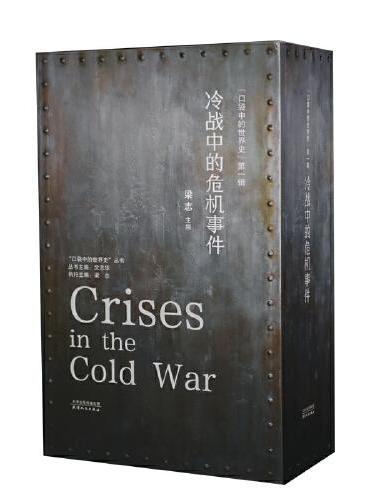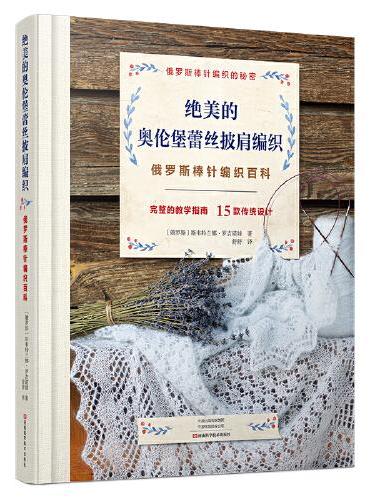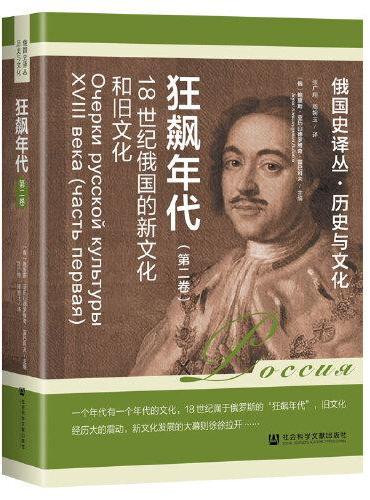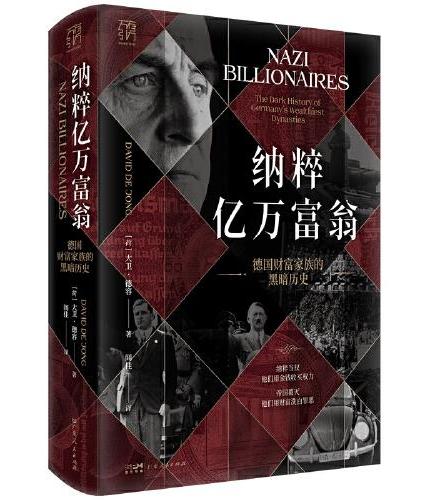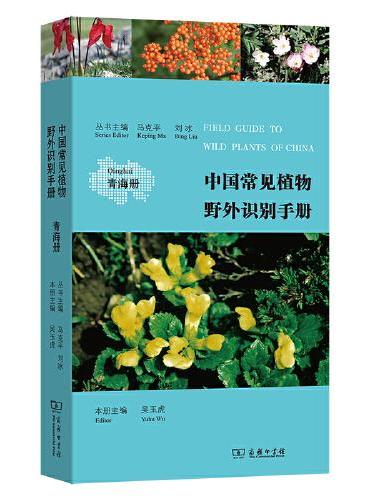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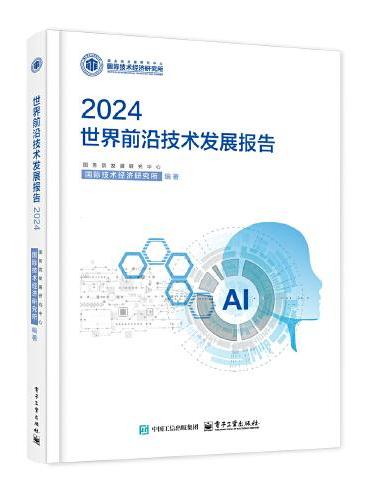
《
世界前沿技术发展报告2024
》
售價:HK$
18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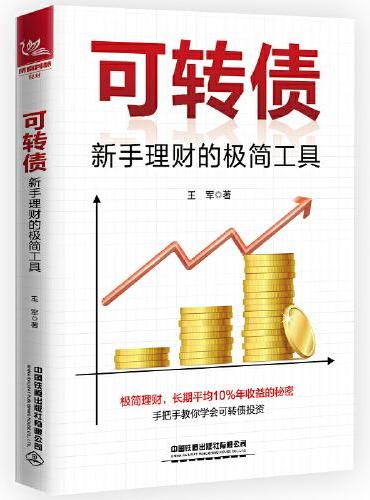
《
可转债——新手理财的极简工具
》
售價:HK$
6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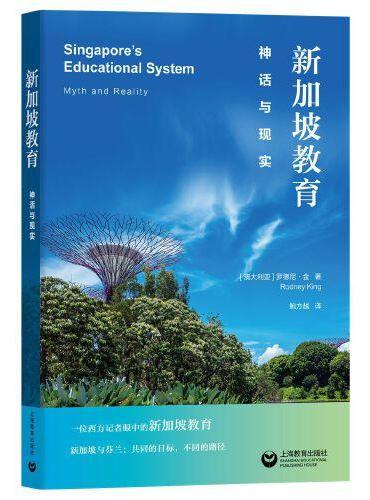
《
新加坡教育:神话与现实
》
售價:HK$
9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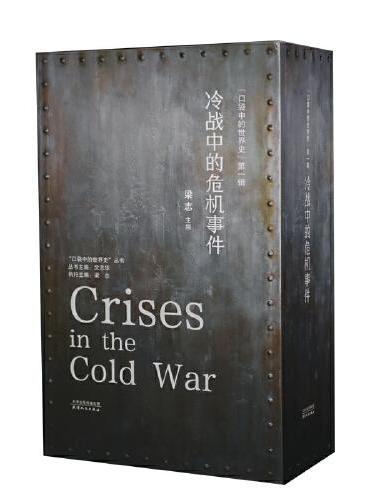
《
“口袋中的世界史”第一辑·冷战中的危机事件
》
售價:HK$
29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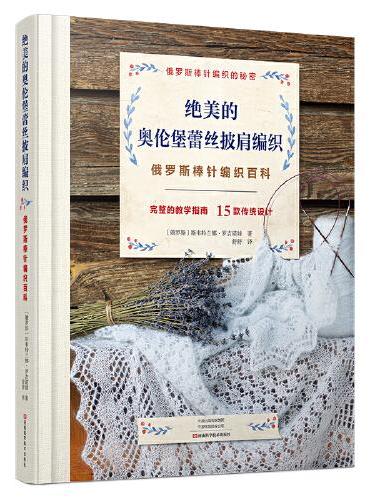
《
绝美的奥伦堡蕾丝披肩编织
》
售價:HK$
17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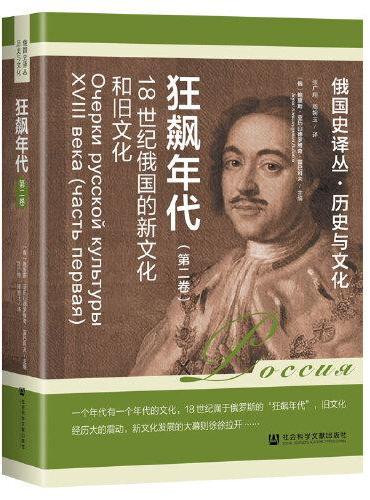
《
狂飙年代:18世纪俄国的新文化和旧文化(第二卷)
》
售價:HK$
17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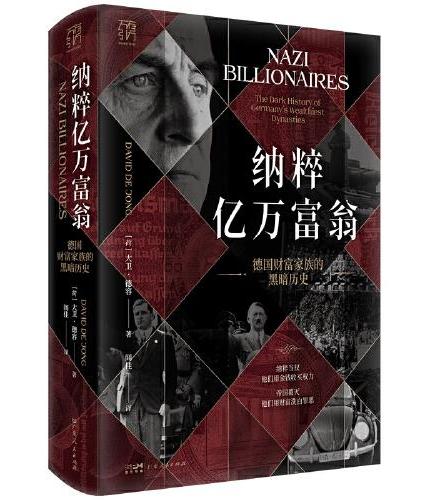
《
万有引力书系 纳粹亿万富翁 德国财富家族的黑暗历史
》
售價:HK$
1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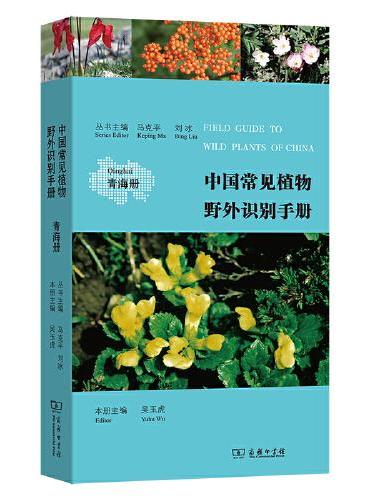
《
中国常见植物野外识别手册:青海册
》
售價:HK$
76.2
|
| 編輯推薦: |
她做的,只不过是为自己而活。
民国初年,才华洋溢的现代诗人徐志摩、林徽音、陆小曼的恋情成为社会话题,到几十年后看来,仍然有其时代意义。相形下,遭受与徐志摩离婚家变的元配张幼仪,始终听不到声音,本书揭开了历史尘封的一角。
|
| 內容簡介: |
|
张幼仪在不重视女性的传统中国社会长大,离婚后力争上游,成为上海的银行家、服装公司的总经理;而他的后辈,在上一代在东西方冲突的恩怨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张幼仪和张邦梅各自为中国妇女的经历书写了值得记忆的一页,对生活在现代的女性而言,更是一件宝贵的礼物。
|
| 關於作者: |
|
张邦梅,张幼仪的侄孙女。出生于波士顿,毕业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修中国文学;哥伦比亚大学法律硕士,曾于纽约担任律师。
|
| 目錄:
|
目录
楔子
第一章 一文不值
第二章 三寸金莲
第三章 福禄寿喜
第四章 嘉国邦明
第五章 女子的教育
第六章 腊雪寒梅
第七章 不三不四
第八章 如君之意
第九章 小脚与西服
第十章 贤贤妻子
第十一章 诗人哟
第十二章 感伤之旅
第十三章 尴尬地位
第十四章 尾声
后记
附录:纪事表
简体字版编后记
|
| 內容試閱:
|
楔子
那口从中国带来的雕花桃花心木箱,依然立在爸妈家的客厅里。爸妈家在康涅狄格州,那所房子是我长大的地方。箱子又黑又亮,上头刻的一只虎爪紧抓地面,在摆着由埃姆斯和勒柯布西耶设计的家具的客厅一角,对我频送秋波。我走向箱子,把玩箱上繁复的铜件,再阖上厚重的盖子。箱里什么都有:中国的秘闻,樟脑的气息,和在另一个时间地点穿着的衣物,其中有奶奶的绣花丝袍,爷爷的无尾晚礼服、白色晚宴外套和马裤,阿嬷①许妈针脚可爱的围裙,妈夏天到香港买的几件修身高领开衩旗袍。迅速翻弄这些衣服,我对它们如数家珍。我不假思索地将它们折了又叠,这是从小做惯的事。爸教过我怎么折旗袍,折时要注意领子,那是旗袍最重要的部分。我还记得自己曾因爸这么懂女人的衣服而感到尴尬,但他告诉我,那是小时候从他母亲那儿学来的。
此刻,我发现了我要找的东西,是一件黑旗袍,姑婆张幼仪晚年的她是我的明镜与良师开的云裳服装公司里曾卖过的那种款式。从小,我就拥有这件衣棠,有一天,它从爷爷奶奶自上海带来的家当里冒出来。虽然衣服上没贴标签,但一天午后,我们在家中的箱子里翻翻寻寻时,幼仪一眼就认出了它。这是我店里来的。她说。那高兴的口气,仿佛遇见了老友。打从那天起,我就把这衣服当做幼仪的,而且毫不犹豫地接受它的存在,就像接受她晚年对我的馈赠一样。是这件衣服把我们牢牢系在一块儿,载着我们跨越了岁岁年年。
家里大部分亲戚,我似乎生下来就认得,但认识幼仪姑婆的情况却不一样。我清楚记得初见面的情景。那是 1974年,当时我九岁,我们张家人一如往常,在四姑婆位于中央公园西路
(Central Park West)的公寓聚首。四姑婆自 1954年移民纽约后,一直是位成功的服装设计师。她穿着剪裁考究的旗袍,头发用假髻挽得高高的,脸上抹得苍白,还搽了鲜红的唇膏。
我最怕到她家聚会。她老是把哥哥、姐姐和我叫到房间,问我们为什么没变胖些、瘦些、聪明些,或是手脚怎么没变麻利些,嘴巴没变甜些;当我们回答得结结巴巴时,就用上海话笑我们。在四姑婆面前,谁都不许戴眼镜,连妈也包括在内,她受不了别人这副丑样子。
①
即奶妈。译注
初遇幼仪那晚,我和家人一起被引进四姑婆的客厅,一眼就注意到有位戴副大眼镜的陌生人坐在四姑婆坐的双人椅另一头。她仪态端庄,没有架子,和雍容华贵的四姑婆似乎截然不同。我很诧异这陌生客竟被允许不摘眼镜。
爸向我们几个孩子宣布:这是你们的二姑婆,也就是张家二姐,刚从香港到这儿。
我羞怯地靠近幼仪,在郑重与她握手之时,目光穿透那副眼镜,直入她的双眸。眸中闪着熟识的光芒,好像她自某个遥远的地方就将我铭记在心似的。我记得自己当时立刻有种可以信赖这位女士的感觉。
她住在曼哈顿北部东区的一所公寓里,第二任丈夫过世后,才从香港搬来。张家人给她起了个诨名叫亲伯伯,显然是调侃她有几分男子气。我注视着她的短发和深色裤装,喜欢从她身上传出的信息:我讨厌裙装,过去人家老喊我野丫头。虽然爸妈从未提起,但我从同辈堂亲和姑姑们那儿听过她离婚的暧昧传言,他们用一种暗示着丢脸、可悲的口吻,谈论她离婚的事。我直视她的脸,想要搜寻丢脸或可悲的信息,却只看到平静和智慧。初次相见的那晚,我并没有和她说上几句话。虽然我经常在后来的家族聚会中看到她,但直到五年以后,才开始与她交谈。
1979或 1980年的夏天,爸打电话给幼仪,邀她来康涅狄格小住数日。他俩显然在之前的一次家族聚会上讨论过这趟远行的可能性。 1940年出生的爸,从孩提时代就和幼仪很熟,那时爸家住上海,转角就是幼仪家。 1949年以后,爸和家人便辗转到香港、东京、巴西圣保罗,然后到美国。幼仪也在同年离开中国大陆,前往香港,在那儿认识第二任丈夫,一直住到 1974年他去世为止。
初访康州的幼仪带来了粽子的食谱和制作材料,妈和我在幼仪监督之下,把肉馅和糯米准备好,然后将大片竹叶放在水里泡软待用。第一个粽子包出来以后,幼仪宣布我们的努力成功了。此后每年夏天,幼仪都会带份新的食谱来,有一年是饺子,还有一年是虾酱。她会在我们准备做菜时仔细监工,然后给我们的成品打分。我喜欢她那种从容不迫、细心周密的方法。我们煮东西时,她就夹杂着英语和中文告诉我中美与古今之别。我在家是讲英语长大的,读高中时才开始学中文。幼仪与我交谈时,从来不讥责我太美国化,或是用我不可能了解她所说的中国的口气。张家这边的亲戚中,没有人是以这样轻松的态度和我说话的,连我自己的爸和爷爷奶奶都一样。
当时处于青少年时期的我,正陷入强烈的认同危机。身为张家第一代在美国出生的人,我徘徊于两种文化之间,却不知如何取舍。身为华裔美国人的我,渴望拥有可以让自己认同的国家,想要追求一个和自己的过去毫不相干的未来。我热切盼望了解自己的出身,却又对自己的传承感到羞愧。
1983年,我开始在哈佛大学就读,由于东亚研究系声誉卓著,便选为主修科系。本想借此达到了解中国的目的,却因为要系统分析中国的政治和文化传统而产生困惑。令人气馁的是,我所学的东西并未引起我的共鸣,而主修其他学科的同学却暗示我天生就应该具备有关中国的知识,也让我深恶痛绝。如果我对中国的了解比不上我的同窗(他们大都是美国人),那我出了什么问题?难道我不够中国?我经常如此戒慎恐惧。
那年在研读中国史概论这门课(同学都戏称这是稻田课)时,无意中在一些课文里发现张家人的名字,他们经常被与五四时代(约1919至 1926年)相提并论。这个时代见证了传统儒家文化在西方思想引领风骚之下所经历的剧变。 1919年5月 4日,天安门广场发生了中国史上第一次拥护民主的示威活动,五四之名由此而来。这个时代的贡献之一,是产生了新文体和新文学。我的两位伯祖张嘉森和张嘉璈①,也就是张家人口中的二哥和四哥,因在政治界与银行界的成就而为人所褒奖。我自小就认识二伯祖与四伯祖,他们于1970年代中期过世后,每次我去旧金山探望爷爷奶奶,都会到他们位于加州一座山边的基地致敬。
令我惊讶的是,姑婆张幼仪也因为和徐志摩离婚而被提及,后者是将西方诗律引进中国现代诗,并协助创办影响文坛的《新月》月刊的浪漫诗人,名噪一时。他们的离婚事件常被称为中国第一桩现代离婚案。
大学第一个暑假自校返家后,我热切等待幼仪来访。她在我眼中是位值得尊敬的长辈和不谙世故的移民,这位女士和我在阅读课本时所想象的女中豪杰,会是同一个人吗?她到访的第二天,我便拿出提到她名字的书本,央求她从头告诉我她的故事。
第八章
如君之意
一位历史学家在报告中提出,徐志摩离开中国前往西方的时候,和其他同一社会阶层的年轻人没有两样。时值二十二岁的他,正在寻求救国之道。他本来打算放洋归国之后,要接管家中事业,或加入政府官僚体系。可是,根据这位史家的看法,徐志摩此番西行,也在内心注入了改变个人作风的欲望。他信奉着自己心目中西方的精髓,并致力于成为他所推崇的西方优点与特质爱、热情、坦白的活化身。
我常问幼仪:难道你不气徐志摩吗?
我知道自己左右为难。我对他对待幼仪的态度很反感,但又不能自控地崇拜他本人和他的作品。他是某个精英同志会的一分子,其中成员都是改变中国旧貌、身为过渡一代的学林俊彦。而作为张家第一个在美国出生的人,我盼望自己也能像他一样,成为同时接受中学与西学灌输的人。
可是,幼仪并不承认她的感受,我猜是因为一个循规蹈矩的中国女人不应该心生怨恨。
徐志摩怀着进入金融界、成为中国的汉密尔顿( Alexander Hamilton)①的抱负,远渡美国。这期间,他甚至给自己取了
Hamilton这个洋名。他在克拉克大学那自我约束的日程表,一显雄心大志和对国家的责任感:
六时起身[同居四人一体遵守],七时朝会(激耻发心),晚唱国歌,十时半归寝。日间勤学而外,运动、跑步、阅报。
徐志摩滥耻发心,或者说是号召本人和同齐一起行动的欲望,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在历史课本里读过中国人的国耻观念,并得知了共产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原理:儒家思想不能抵御外侮、保护中国。我是在美国长大的中国人,自己的种族身份又遭人取笑过,因此对羞耻心毫不陌生,但也惊异于这种感觉何以与徐志摩相仿,竟然大到可以让我想象自己堪为我这代华裔主要喉舌的程度。
徐志摩以优异成绩自克拉克大学毕业后,于 1919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修习政治学。然而,他发现美国不合他性情,便于 1920年中途辍学,冲动地转赴英国。他写道,那是我正感着闷想换路走的时候。②没过多久,他就强化了自己那套将对幼仪造成激烈影响的爱情信条。
②
美国政治家。译注
②见《我所知道的康桥》。初载于 1926年 1月 16日、 25日《晨报副刊》。编注
第八章
如君之意
一位历史学家在报告中提出,徐志摩离开中国前往西方的时候,和其他同一社会阶层的年轻人没有两样。时值二十二岁的他,正在寻求救国之道。他本来打算放洋归国之后,要接管家中事业,或加入政府官僚体系。可是,根据这位史家的看法,徐志摩此番西行,也在内心注入了改变个人作风的欲望。他信奉着自己心目中西方的精髓,并致力于成为他所推崇的西方优点与特质爱、热情、坦白的活化身。
我常问幼仪:难道你不气徐志摩吗?
我知道自己左右为难。我对他对待幼仪的态度很反感,但又不能自控地崇拜他本人和他的作品。他是某个精英同志会的一分子,其中成员都是改变中国旧貌、身为过渡一代的学林俊彦。而作为张家第一个在美国出生的人,我盼望自己也能像他一样,成为同时接受中学与西学灌输的人。
可是,幼仪并不承认她的感受,我猜是因为一个循规蹈矩的中国女人不应该心生怨恨。
徐志摩怀着进入金融界、成为中国的汉密尔顿( Alexander Hamilton)①的抱负,远渡美国。这期间,他甚至给自己取了
Hamilton这个洋名。他在克拉克大学那自我约束的日程表,一显雄心大志和对国家的责任感:
六时起身[同居四人一体遵守],七时朝会(激耻发心),晚唱国歌,十时半归寝。日间勤学而外,运动、跑步、阅报。
徐志摩滥耻发心,或者说是号召本人和同齐一起行动的欲望,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在历史课本里读过中国人的国耻观念,并得知了共产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原理:儒家思想不能抵御外侮、保护中国。我是在美国长大的中国人,自己的种族身份又遭人取笑过,因此对羞耻心毫不陌生,但也惊异于这种感觉何以与徐志摩相仿,竟然大到可以让我想象自己堪为我这代华裔主要喉舌的程度。
徐志摩以优异成绩自克拉克大学毕业后,于 1919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修习政治学。然而,他发现美国不合他性情,便于 1920年中途辍学,冲动地转赴英国。他写道,那是我正感着闷想换路走的时候。②没过多久,他就强化了自己那套将对幼仪造成激烈影响的爱情信条。
②
美国政治家。译注
②见《我所知道的康桥》。初载于 1926年 1月 16日、 25日《晨报副刊》。编注
我儿子徐积锴出世以后,徐家对他宠爱有加。用上等棉布做成的襁褓包着他的身体;他刚哭个几下,用人或奶妈就会过来安抚。他头一个玩具,是一根象牙刻的小如意,如意就是如君之意的意思。他爷爷奶奶声明,他们这个独孙比世界上所有的大财大富加起来还要宝贝,而且用一百个徐家亲戚送的贺仪,给他打了把小铁锁。这把用金链子挂在他脖子上的百家锁代表的意义是:以一百个亲人的祝福,把他的命锁好;也告诉大家他带给家人的喜悦。
我们给他取名叫积锴,借是良铁的意思,因为铁这种金属象征刚强、正直、果断、公平。他事事好问的天性,逗得家里每个人都很欢愉,所以阿欢(意思是开心)很快就成了他的乳名。徐家老奶奶一定要我们常带他回去探望,老太太也不再天天缝鞋子,而改缝娃娃的衣服了。
我生产以后身子虽然很虚,但是不久就恢复了元气,而且等着照顾自己的儿子。可是,我很快就发现,我这个母亲的角色受到了严格的限定,就和我在徐家应对进退的行为一样。阿欢是属于徐家的,老奶奶、老爷,还有老太太要监督他的养育过程,只准我偶尔照顾。我抱他的时候,公婆就纠正我的姿势;我给他洗澡的时候,保姆又在我身边晃来晃去。到了夜里,还有个奶妈睡在他小床边的地板上。
妈妈告诉过我:到徐家后绝不可以说不,只能说是。
所以我并没有反抗公婆的做法。但我现在才发现,我为了讨好公婆放弃了一切,包括出门、求学,甚至育子。我很庆幸我儿子和儿媳妇现在住我附近,而且我们可以时常见面。可是在阿欢生命里的头七年,我没有按照一个母亲应当的做法给予阿欢照顾。
阿欢出世百日那天,有个用人在他面前摆了个盘子,里面装着一把量身尺、一个小算盘、一支徐志摩的毛笔,还有一些铜板。我们围在阿欢身边,看他第一个会抓起哪样东西,从而预想他日后的方向。起先,阿欢好奇地盯着整个盘子,他的眼睛几乎还分不清什么是什么。然后,他瞪着算盘(商人算账的工具)发呆,又瞧了瞧那把裁缝师用的量身尺。最后,他的目光盯住盘子正中的一样东西,着迷了一会儿,就伸手去抓。那是徐志摩的毛笔。
多聪明的男孩子啊!我感到很自豪。他刚才的举动意味着他以后要成为一个读书人,就像徐志摩和我的兄弟们一样。
老爷突然兴奋地把阿欢腾空举着荡来荡去说:又一个读书人!我们家孙子将来要用铁笔廖!他引用重要政府文告里常用的一句话,对老太太夸口说:铁笔不改。他的意思是希望阿欢有朝一日会撰写政府律令。
几个月后,也就是 1918年秋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我们又庆祝了一番。二哥自德国归来以后,在上海办了一份独立的报纸;1919年,他与梁启超等人打算组成非正式代表团开赴巴黎,为和会做些工作。我正好回娘家探望父母,所以在二哥行前不久见到了他。
二哥想知道:你什么时候到西方与徐志摩团圆呀?
我听了诧异地看着二哥。徐志摩去美国已经半年了,我从没想过要与他团聚,因为我以为我的责任就是和公婆待在一起。
你已经对徐家尽到责任了,二哥这么说,好像他听到了我的想法似的,现在你应该跟丈夫在一起,甚至可以到西方求学。
像新式女子那样到西方求学?像徐志摩和我哥哥一样学习外文?这意见引起了我的兴趣。然后我想到了公婆。徐家会让我去美国吗?他们会替我付学费吗?于是我告诉二哥,只有在徐志摩来信要我去的情况下,徐家才可能让我去,因为他们不会拒绝儿子。
二哥向我打包票说:徐志摩会来信要你去的,他会希望你了解西方。
二哥和徐志摩是挚友,所以我相信他说的话,而且兴奋地怀着憧憬,回到硖石。我嫁到徐家差不多四年了,而徐志摩放假时我和他共处的时间,加起来大概只有四个月。我渴望能像眼哥哥弟弟聊天那样,和徐志摩交谈;我想帮他忙,助他得到成功与荣誉。有一次,我幻想我们像伙伴一样待在简朴的家中,他正研究学问,我准备两人的饭食。还有一次,我幻想自己穿着西服,抱着书本,和徐志摩并肩走去上课,就像以前我和大姐在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一样。
现在,每次家人朗读徐志摩的家书时,我就等着听他在结尾提到我的部分。他的来信上头收信人总是写着父母的大名,在信尾才问起我和阿欢的近况。这是很孝顺的做法,因为夫妻在公婆面前应当保持距离。有一回,徐志摩要求我整天跟着阿欢四处转,然后写下他说的或他做的每件事情。还有一回,他要求看看阿欢的画和他刚开始学写的毛笔字。可他还是没有来信要我们去。
1919年春天,中国得知了在巴黎协商的和约条款:作为同盟国之间秘密协定的一部分,山东(孔子的出生地)将被割让给日本。中国多年来对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憎恨,因为同盟国背信弃义事迹的败露而被触发。 1919年的5月 4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有大约三千名学生举行了一场群众示威活动,要求政府拒绝接受和约条款。他们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还我山东!抵制日货!
第二天,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纷纷加入了当地的示威行列,广泛的抗议工潮也随之形成。爱国主义的浪潮就此袭卷全国,数以千计的工人碰面讨论抵制日货事宜。 6月 5日这天,上海大约有两万名工人号召罢工,这事件波及许多企业,日本人拥有的一些棉纺厂也跟着遭殃。
老爷暂时关闭了上海的几家店铺,待在硖石家中阅读报上的报导。学生和工人最终赢得了斗争的胜利,政府释放了被捕的学生,同时表示中国不接受这项和约。
从欧洲回来的二哥对示威活动的成果感到兴奋。后来他问我:徐志摩来信要你去了没有?
我摇摇头。
他说:他这么久没写信给你.定是出了什么岔子。
二哥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突然想起大概一年以前徐志摩对我说过一些话,那时我还没怀孕。他说,全中国正经历一场变局,这场变局将使个人获得自由,不再愈发屈从于旧习俗。他好像关在笼里的动物那样踱来踱去,说他要向这些使他无法依循自己真实感受的传统挑战,成为中国第一个离婚的男人。
我记得我虽然对他这番说辞感到吃惊,可是我既不担心,也不懊恼。我小时候听说过的离婚事件只有在女人失贞、善妒,或没有好好侍奉婆家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当然,这些事情我都没做过。我还听说,女人离婚是件丢脸的事,娘家会不想让她回去,所以她只有三个选择:卖娼、出家和自尽。我不相信徐志摩会逼我走上这几条路,我了解他的背景和家庭。
所以,我既没有仔细听他说什么,也没把他的话当真。我以为他只是准备去西方了,所以假装表现得很西化。
可是,听二哥这么一说,徐志摩的话又在我耳畔响起。看到一波接一波的学生示威活动,我明白徐志摩说的没错:一场推翻传统的运动正横扫全国。我以为徐志摩没有写信给我的原因之一,或许是他不认为我想去西方,再者就是他不能把我这乡下土包子带出国。
我从不敢问公婆我能不能到海外去,二哥就说他会帮我问问老爷。老爷到上海谈生意的时候,二哥经常与他碰面。在他们接下来一次碰头的时候,二哥就说:如果徐志摩继续在国外读书,而幼仪留在硖石的话,他们两人的心就要愈分愈开了。
老爷回答:她要跟老太太做伴,还得照顾娃娃。
徐家人非常保守,所以不想让我到海外。他们认为我应该待在家里,信奉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当然,他们这么想有一定的理由:一个啥事不懂、又啥事也不想知道的女子,比起时时在求知、老想知道更多事情的女子好管太多了。可是这是过时的观念了。他们并不明白,如果我晓得一些事情的话,对他们的孙子会更有好处。如果我读些书的话,就可以将所学传授给我的小孩,做个更称职的母亲。
趁徐家人慎重考虑我该不该去西方的时候,我乞求老爷给我请个老师。老爷的哥哥有几个还没出嫁的女儿也想求学,我就和这三个年纪比我小的女孩一起上课。徐家决定让我去和徐志摩团聚的时候,我已经读了一年书,但这个决定和我进一步的学业没有一点儿关系。我想,我公婆之所以决定送我出去,是因为他们也怀疑徐志摩出了岔子。他放弃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业跑去欧洲,已经让每个人大吃一惊了。他的来信中透露出不安和忧郁,令他的父母感到忧心。
我为愿望的达成感到欢喜,只是得把两岁的儿子留在公婆身边。另外,徐家让我得跟着某一家人一起成行。男人单独远行已经不妥了,女人单独这样做就是涉险。幸好有个从西班牙领事馆来的中国家庭(先生、太太和两个小孩)①准备前往马赛,于是我们搭上同一艘轮船一起旅行。一路上我完全不用照看小孩,只是坐在自己的舱房里。
①指刘崇杰一家。刘崇杰(1880-1956),字子楷,福建闽县(今属福州市)人, 1920年开始担任中华民国驻西班牙(时称日斯巴尼亚)兼葡萄牙特命全权公使。陈从周编《徐志摩年谱》中作刘子借。编注
夜里,我躺在船舱中的床上,琢磨着第一眼看到徐志摩的时候要有怎么样的举动。想起我与他之间长期保持沉默(他一开始就说我是乡下土包子?)
,我心情非常沉重。我和婆家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已有五年了,却一点也不了解我的丈夫。我试着告诉自己,我们之间的距离还不至于隔得太远。在船上,我记起自己辛辛苦苦跟着老师上课的情形,心想也许徐志摩会注意到我现在的学识有长进。我也盼望能到西方努力求知,学习英文。
同船的其他乘客得知我出国是为了与丈夫团聚,都说我福气真好。他们说,你丈夫要你去真是太好了!我听了无言以对,因为我心里明白,徐志摩并没有要我去,我是被婆家送去的。我想,我公婆同意让我去的理由,只是在提醒徐志摩对家里的责任。
三个星期以后,那艘船终于驶进了马赛港的码头。我在甲板上探着身,不耐烦地等着上岸。然后,我看到徐志摩站在东张西望的人群里,同时心凉了一大截。他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了条白色丝质围巾。虽然我从没看过他穿西服的样子,可是我晓得那是他。他的态度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不会搞错,因为他是那堆接船人当中唯一露出不想在那儿的表情的人。我们已经很久没在一起了,久到我差点忘了他一向是那样正眼也不瞧我一下,将眼光直接掠过我,好像我不存在似的。
在海上旅行了三个星期,我感到地面在我脚下晃动,时是其他事情一样也没变。等到我站在徐志摩对面的时候,我已经把脸上急切、快乐、期望等种种表情收敛住了。在那一刻,我痛恨徐志摩让我变得如此呆板无趣。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情况一直是这样。我凭什么以为我们会有话可谈,他会尝试让我觉得我是他世界里的一部分呢?
他说他想看看巴黎,于是我们就从港口直趋火车站。连坐火车的时候,我们也很少交谈大概稍微谈了点我旅行的经过和婆家的情形。我们抵达巴黎的头一站是家百货公司,他和售货小姐帮我选了些外国服装。而我从硖石的商人那儿千挑万选、上岸前一天晚上小心翼翼地在船舱里摊开打算穿的衣服,全都不对劲了。
我不晓得徐志摩讲的是哪国话我猜一定是法文,虽然我不认为他懂法文不过,他和正在为我挑衣服的售货小姐聊了起来。他一边摇头,一边冷冷地上下打量着我说,不行,那件洋装不好。另外一件怎么样?他把洋装贴在我身上这是我抵达欧洲以后,他第一次碰我。当我看到镜中的自己穿着那袭修长的洋装,感觉到腿上那双线袜的触感和脚上那对皮鞋的紧密时,我都不认得自己了。我们还买了一顶帽子搭配这套服装。到欧洲的第一天,我穿着新衣,和徐志摩一起照了几张相,寄给老爷和老太太,让他们看看我们一同幸福地住在异乡的模样。
接着,我们又搭乘飞机由巴黎飞往伦敦,那飞机小得我非与他双膝交叉对坐不可。以前我从没搭过飞机,因为晕机吐在一个纸袋子里。我并不害怕,那只是因为空气不好,机身又颠来颠去的缘故。我吐的时候,徐志摩就把头撇过去,嫌弃地摇着头说:你真是个乡下土包子。
话才说完没多久,他也吐了。事实摆在眼前,我带着小小的怨气,轻声说:哦,我看你也是个乡下士包子。
徐志摩有两个朋友在伦敦机场和我们碰头。巴黎和伦敦之间每天的班机服务显然是在一年以前才开通,他的朋友急切询问我们这趟飞行感觉如何。徐志摩突然之间变得生龙活虎,兴奋地用英文和他们聊了起来。他们也是中国人,我们本来可以都讲中文的,可是徐志摩不想这么做,所以他们气个人就这样把我排除在了谈话之外。其中一个朋友每分钟都停下来把裤子技高,另外一个朋友老是皱起半边脸,紧张地抽搐。
剩下我们两人的时候,我对徐志摩说:这就是你朋友啊!可是他又丢给我一个空洞的眼神,掉头走开了。
到了伦敦,我们住在一个俱乐部里,好像城里所有中国人都在这儿了。那段时间,我们很多人都住那儿,大家互相熟识,都是为了某个理由来伦敦求学。那些认识徐志摩的人见到我都睁大眼睛,仿佛很惊讶似的。徐志摩这时候在伦敦已经住了一年,正在伦敦经济学院修课。
我们和每个人都讲中文,吃的也是中国菜,连徐志摩都好像脱去了那层洋里洋气的外壳。他会小口小口地喝茶,有时候还换上长袍到楼下吃晚饭,我们和其他中国人统统在那儿用餐。也许他在吃中国菜的时候比较喜欢穿中国衣服吧,我也搞不清楚。
饭厅的隔壁是间休息室,每个人吃过晚饭,都到那儿聊聊政府和政治,诗词和文学,其中也有少许几位女士。我话不多,就坐在那儿听人高谈阔论。有几个人知道而且景仰我二哥和四哥,就来告诉我。
还有一个人问我打哪儿来,我告诉他从硖石来,他就问我是哪个人家,我告诉他是徐府。他说:哦,徐府有个叫做徐申如的人。
我说:对,他是我公公。
他又说:哦,徐府很有钱,是浙江省最有钱的人家之一。
讲这种事情非常奇怪,因为中国人认为谈论金钱是很没礼貌的。我不知该如何答对。
停了半晌,我才说:大概是吧,我们年轻人不插手生意上的事。
我知道,既然我到了西方,就可以改变我的行为举止了。我可以上街,看自己想看的东西,可是我没去。一直到今天,我还是不明白,为何当时除了整天等着徐志摩,我什么事也没做。就算可以自主行事了,我甚至连想都没想过。
他一直在忙自己的事,好像我不在那儿似的。他冲进冲出,安排这安排那。他就要成为康桥大学王家学院的文科特别生,打算搬到康桥去,要租房子,还要筹划旅行的事。徐志摩叫我待在房里别管他,所以我就坐在伦敦市中心的中国人俱乐部里,觉得若有所失,因为其他中国人全都有事情要办,有功课要完成,连女士们也一样,而我却无所事事。徐志摩隔一段时间会回房间,而他回来只不过是为了要再离开。每次他发现我还在那儿,就露出惊讶的表情。我心里应着:我会去哪儿?说不定他以为每次丢下我不管,就可以凭意志力让我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起先以为是我不能自立,才让徐志摩对我退避三舍的,可是事情并不如此单纯。他每天早上都穿着浆得笔挺的尖领衬衫和钉了三颗扣子的毛料夹克,行为举止也像这些穿着一样洋化。对我来说,他就是个外国人:言谈间加重语势时,手堕拿的是一根燃着的香烟,而不是一把折扇;喝的也是加了糖和奶的淡色浓茶。
有一次,徐志摩把一个名叫狄更生(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的人带回家,称他为Goldie。我知道这是安排徐志摩到康桥大学读书的人之一。当他用英文和狄更生交谈时,他的确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跟朋友在一起的徐志摩总是那么样的快活,但我能看出他特别喜欢狄更生,虽然我只看过他们两人在一起一次。我看到他手舞足蹈,听到他言语中满是崇敬。当他送走狄更生返回屋里面对我的时候,又露出全然不屑的神色。
于是我对徐志摩起了反感。虽然他从不辱骂人,可是平常一到晚上,他就不高兴看到我在那儿。当阳光普照、他不必和我长时间待在一起的时候,他就对我摆出平和甚至愉快的态度。到了黄昏时分,某种忧郁的神情仿佛无可避免地降临到他脸上。当黑夜来临,他向朋友道过晚安之后,他好像又敏锐地察觉到了我们厮守的命运。自从我到欧洲以后,我们又自然而然地成为没有感情的夫妻。有一次,他和我一起躺下后,他的呼吸声不但没有缓和下来,反而因为觉得挫折和失败而扬起在这世界上,他最想做的事便是摆脱我,却败给了我的肉体,并对我们要在一起这件事感到气馁。
早在伦敦时期,我就怀疑徐志摩有女朋友了。有一次,我们搭乘一辆公共汽车我想是前往南安普敦( Southampton )访友时搭的那辆吧我一个人坐在靠近年尾的位子上,徐志摩和一位男性朋友坐在车子前头离司机不远的地方。从司机那面大型后视镜反射的影像中,我可以看到徐志摩和他朋友正在深谈。在某一时刻,徐志摩一边示意他朋友别开口,一边指指坐在后面的我。而我直到那时才发现,自己一直在观察他们。我想知道,徐志摩还有什么想瞒着我的事?
同时,我也好奇,他为何会为了瞒住我这件事而心浮气躁。也许他对这件事的处理方式是很西化的,但在中国,男人纳妾是很正常的事。他父母替他挑选大太太,也就是元配夫人,他自己物色小太太,也就是妾至于娶几个,就看这男人有多大财力了。元配夫人不能反对他娶小老婆,她其实有义务欢迎小老婆入门。妒是七出(男人可以体弃女人的七个理由)之一。
男人纳妾的理由有二,主要理由是大太太不能生儿子。就拿徐志摩老师梁启超的元配夫人做例子吧。她没生儿子,只生了个女儿,生的时候年近四十岁,正和梁启超住在日本。由于无法履行对梁家的责任,她就回国挑了个小老婆,带着这个二太太一起回日本。这位大太太被教养得很正统,知道她对梁家的责任。
男人纳妾的第二个理由是他想拥有她。老爷就是想拥有很多女人东西南北各有一个正如徐家用人说的那样。他可以轻而易率地邀请这些女人中的一个到家里和我们住在一起,而接受她则是老太太的责任。
那天坐在车上,我讨厌自己心里难以平抑的失塑,试图盯着车窗外的风景看。我早该料到徐志摩有女朋友的,要不然过去他在国外那两年,为什么没来信要我去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