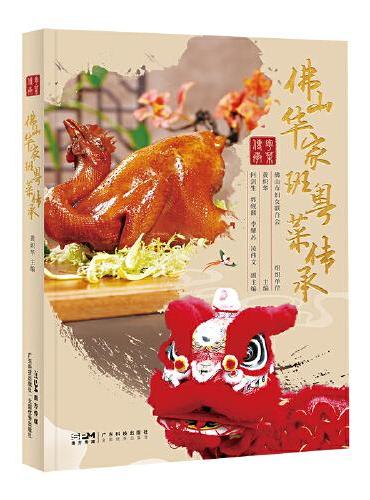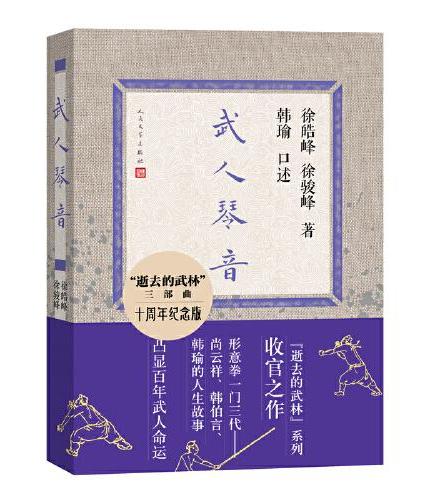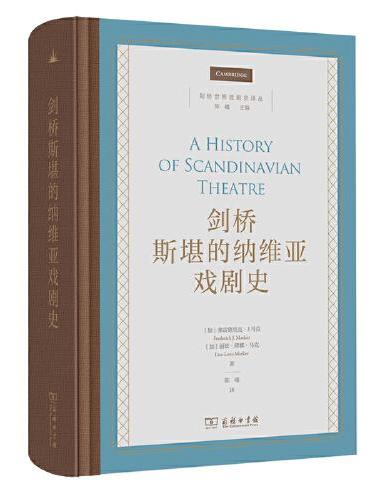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惜华年(全两册)
》
售價:HK$
70.3

《
甲骨文丛书·古代中国的军事文化
》
售價:HK$
99.7

《
中国王朝内争实录(套装全4册):从未见过的王朝内争编著史
》
售價:HK$
244.2

《
半导体纳米器件:物理、技术和应用
》
售價:HK$
177.0

《
创客精选项目设计与制作 第2版 刘笑笑 颜志勇 严国陶
》
售價:HK$
6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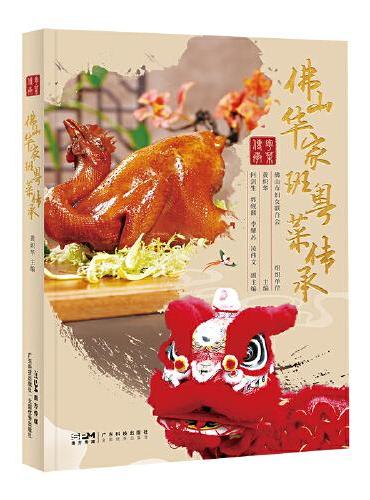
《
佛山华家班粤菜传承 华家班59位大厨 102道粤菜 图文并茂 菜式制作视频 粤菜故事技法 佛山传统文化 广东科技
》
售價:HK$
2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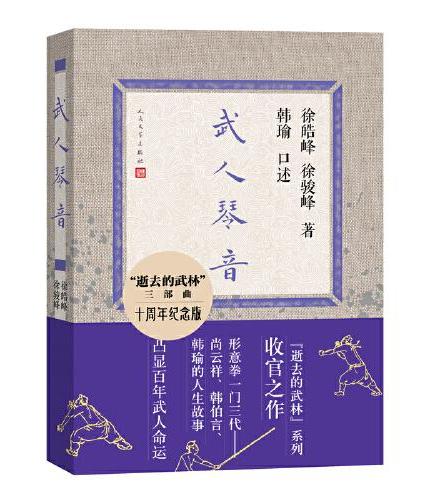
《
武人琴音(十周年纪念版 逝去的武林系列收官之作 形意拳一门三代:尚云祥、韩伯言、韩瑜的人生故事 凸显百年武人命运)
》
售價:HK$
4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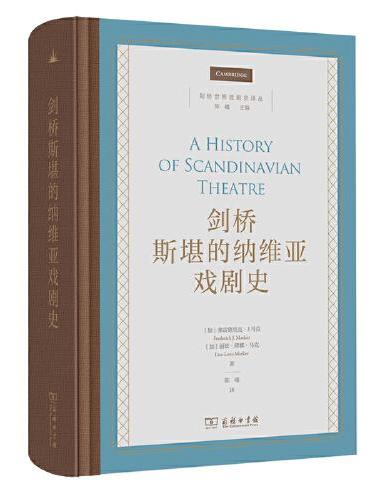
《
剑桥斯堪的纳维亚戏剧史(剑桥世界戏剧史译丛)
》
售價:HK$
154.6
|
| 編輯推薦: |
这是颜长江的三峡,是他收入近万幅胶片和六十万字日记随笔中的三峡;这也是所有中国人的三峡,是藏在历史沟壑中为无数文人骚客咏叹的三峡。虽然,现在,这一切都在水底了,但没去过的人,后世的人,通过这本书却可以想象水底下曾有如何的活的世界、好的故事,想象屈原当初顺着这条溪谷走出家乡的情景……
愿,山高水长,江流有声。
|
| 內容簡介: |
本书是关于长江三峡市库区沿岸的故事
合集,以地理为顺序写川江蓄水前的沿岸风物,
即长江犹是流水的最后年华。这些短章,主要
写作于2005-2010 年,部分为近作。前半曾在
《万科周刊》之《山峡》专栏刊登,后半曾在
《城市画报》之《涉江抽思》专栏刊登。
|
| 關於作者: |
颜长江,广东梅县人。1968 年生于湖北省秭归县。1990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现居广州,任《羊城晚报》图片总监。出版有《广东大裂变》《最后的三峡》《三峡日志》《我就是为它而来》等著作。2002 年至今,“三峡”“夜间动物园”和“纸人”系列摄影作品在中国平遥、北京、上海、广州、连州和韩国首尔、法国巴黎、日本东京、瑞士伯尔尼以及
意大利等地展览,被上海美术馆、广东美术馆、旧金山M0MA、重庆美术馆等机构收藏。
|
| 目錄:
|
目 录
序 7
三游洞 16
三斗坪 24
桂林村 32
乐平里 44
归州新镇 54
秭 归 62
我和哥哥去泄滩 76
巴 东 82
火焰石 92
碚石夜话 97
青 石 106
大 昌 116
龙 溪 126
大溪上下 132
夔门奏乐 138
2002 年1 月在奉节 143
2002 年10 月在奉节 152
万世桥 158
坝 上 163
故 陵 168
云 阳 174
云安镇与述先桥 182
下岩寺 190
古佛寺 196
无名之桥 201
利济桥和海安桥 206
西 沱 212
上祠堂 220
临江渔父 226
悟惑寺 232
涪 陵 238
龚 滩 245
龙门桥 252
一段无人理会的江流 261
洛 碛 268
王爷庙 276
佛 堆 284
木 洞 291
鱼 嘴 300
寸 滩 305
后 记 316
|
| 內容試閱:
|
桂林村
大约是1996年的一天,在广州,旅居法国的摄影师曾年,得意地告诉我:他这次拍摄了长江边上一个古村,全是大宅门。
我有点不信,我也来往过几回,怎么没看到过,三峡边上哪还有完整的古村落?
他说,他就是在江船上看到的,阵阵飞檐啊。于是上去,还撞上两家人因出殡打架,差点把自己也卷了进去。那村叫桂林村。
我想,他是法国来的,文章要登在《巴黎竞赛》给法国人看,没有点古老的情调是不行的。一定很好,一定要去。
1997年,我很荣幸也很幸运地看到了桂林村。
那时刻,好像已经很遥远。但我仍清晰地记得,那两天的美好,和轻快。
桂林村,在秭归县境的兵书宝剑峡南岸坡上。对岸即北岸,有巨大的滑坡痕迹,从峡山之巅直下千米滑入大江。那是1985年,大滑坡把新滩古镇整体推入长江。新滩没了,文艺一点的朋友们,大多知道还有个桂林村。
在上孝码头下船后,向着上游那桔林掩映中的青瓦白墙行走就行了。也就两三里吧。那种在林中掩映的飞檐、封火墙,非桂林村而何?我们在山路上走着,早上的空气是那么的清新,夹杂着桔树的芳香,和玉米叶随风而兴的声响。移民刚开始进行,一切尚保持原貌,土地,房屋,树林。
走在一个上坡,路边田地之中,突然见到一个石砌的池子,七八平方,一半盖有石板,一半露天。一头猪正趴在石栏上,对着峡江吼叫。这好像在兆示着什么?
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你这猪有房有院,正是十多年后,广州地产的广告词形容的:独立别墅,无敌江景。
桂林村,猪圈离宅子都是有一定距离的。要说这秭归,真是屈子昭君的故里,人们都清爽得很,爱干净。
村外第一户人家,很一般的土房子。一个壮男路过这里,背篓打了个杵,停在稻场上歇息。背篓上是一大捆青青的花椒树枝。
这位兄弟叫熊辉权,桂林村四组的人,“自家的花椒树,砍了当柴烧吧。”他属于移民,以后准备“后靠”,但也在恩施买了房子。水淹上来之后,仍会守在这里,“守到老人过世吧”。然后就移往恩施。“最不习惯的是看不到大河了!”
大河?“就是长江,我们喊大河的。”
我后来也把长江叫作“我的大河”。起源于此。
他说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就是心里有些惭愧。”大约是指离开家乡的心情。
这屋门上有几个油漆大字:135M上2.5米。
屋边有一块自留地,上面大朵的葵花稀疏几棵,晨风中艳丽地摇曳,一个老太太正在忙活。上前问候,老人家说自个儿叫杜祥凤,就住在这房子里。生有五个儿子,三个姑娘。大姑娘移民到了枝江,二姑娘到了猇亭,三姑娘在宜昌打工。这些都在三峡外的平原。儿子中,老大本来就在宜昌工作,老二去了董市,老四去了潜江,也是在平原。老幺在屈原镇深山中。三儿媳住在这里。二线才移民(2002年前)。“我72岁了,我不走!水淹到这里再说!从小就在这里,不习惯走。”
“我有些惭愧!”又是惭愧这个词。“一场空,都走了!”继续前行,翠绿的玉米秆子那边,封火墙优美地立着。就那么一两幢,都有七八米高,长宽十多米。走在屋边,赞叹了一番,却没有多逗留,因为这预示着更大规模的建筑群还在后面。果然没几步便看到链子崖的土黄色背景前,树林掩映着的桂林村。走上青石板的巷子,立刻觉得走进了清凉。
怎么说呢,桂林村长宽约二百余米,在一个坡上,除了西侧临江边有一栋三层水泥楼作为小学校舍外,均由密集的古建筑组成。整个村的主干道是两条青石板路,交叉成一个十字,竖的一条,通向江边。都是四合院,没有一栋小房子,也没有一栋不精细的。一堵又一堵的封火墙,几十几百个飞檐落在这山水之间。每个院落构造大致一样,长宽十多米,大致是个正方形,内里多为两层木楼,雕花栏杆。青石条为门,上面顶个木制的阁子装饰并遮阳,门面都像牌坊似的,在天宇下惊心动魄地立着。
很明显,这村不是一般人能建出来的。十年之后,我断定,三峡古建以此为最,有名的大昌、宁厂等古镇,建筑也是远不能和这里比的。即便安徽的宏村、西递,大院也未必比它强,何况,它是在壮丽的西陵峡口子上!
后来读陆游《入蜀记》,我很惊喜在这里和陆游有了交集。他说:“滩上居民皆利于败舟”,可贱卖船板,做各种买卖。现在读到光绪年间英国人立德的日记《扁舟过三峡》,书中有一张他夫人拍的照片,一看竟是兵书峡背景前的桂林村全景。这村在1883年与1997年间几乎毫无变化!
这张照片的标题为“退休帆船船主的家园(兵书峡入口)”。立德提供了一些详细资料。这里有传奇的引水行当,均是当地人,由官府发给牌照。指导帆船过一次滩,报酬是一美元,甚或三五美元,而当时峡江纤夫拉两个月纤(一次宜昌至重庆的行程),不过20美分报酬而已!可以说,引水一年,就够造一座宅院了。
桂林村和新滩镇,不知蕴含了多少历史传奇。
然而村里很安静,人们看上去很悠闲。轮船时代之后,桂林村与一般的峡江农村没有不同了。当然,生活的韵致还是在的。人们
穿着整齐,房舍收拾得干净,玩玩猫,撒撒网,对着江峡,沉思。
竖巷尽头,一个老太太坐在小板凳上,手持针线,在鞋垫上慢慢地绣花。这个位置,也让她不时抬起头来,看一看江景和过路的人。一只猫在她周围转悠着。逆向的阳光从江上方打入这深巷中,打到她身上。那光,就是时光。
问一问老人家,她说鞋垫是给孙子们做的。我说要买,她死活不卖。问问她家,她说就是最下边的那栋。我一听喜出望外,那一栋相对独立,离大江才三四十米,是最舒服的一栋。
老人家带我们下了阶梯,跨过她家玉米地,来到这大宅前。门未锁,她就坐在青石门槛边,继续绣花,让我自个儿看。也是两层的木楼,梯子和一些栏杆已有些朽了,却也没怎么修补,看上去二楼久无人住。房子看得我垂涎欲滴。问一问老人,这大宅竟然就她一个人住。
老人说她叫杜远翠,这房子是土改时分的。她的丈夫“被国民党整死了”,她独立抚养一子一女。丈夫以前是当老师的,她也做过体育老师,后来又在矿上过磅,再后来从香溪矿务局调往河南平顶山矿务局,儿子、女儿女婿就都到了平顶山,自己老了就又回来了。现在不用别人养,自己养自己,矿上每月寄钱来。房子自然要搬迁的,县上说要作为文物复制,已来过几趟测量了,一砖一瓦都不能动,云云。
她未来的家,是后靠上山。
告别老人,又在村中闲逛。村中有座南坪小学,占据着村中最为宏伟的院落,坐落在村中突出的一块台地上,门前有大树一棵。这建筑,在立德的照片上也清晰可见。一楼是办公室,二楼有女生宿舍,秀气的女孩儿们拎着水桶热水瓶什么的从木楼上走过,使这楼有与众不同的青春气息。房子还附带一道四五米长的木制廊桥,跨在沟上。这廊桥也自然是其他房屋没有的。
与肖前进校长聊起来,才知道这座与众不同的建筑叫作江渎庙,中国四大河神庙之一,又叫作杨寺庙,紫云宫,公元1170年,陆游就来到这里游览过。当时这庙刚刚修好,叫江渎南庙。北岸还有一座北庙。这庙用作学校,从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了。因为移民,学生在一天天减少。
这庙和校舍虽在135米之上,但地基却在下面,水淹上来会危及安全,因此仍属于第一期移迁对象。新校已开始设计,长江委(全称是长江水利委员会)将它安排在山梁上,因为其他地方都是滑坡体。但村民们认为那里太远,又没水,本村几百年都没有滑坡了,如果滑坡,整个村也会没有了,意思是学校不应太远,应与村庄共生死。因此,全体村民已于昨日写了报告,要求就在桂林村上方建校,准备立即上送……
水看来是个问题。我们看到学校也雇了个老校工,是位五十来岁的妇女,背着个大木桶,装七八十斤水,从江中爬上来一轮轮背水。
她说,学生用水,老师喝水,都是她背上来,一天八趟,还要给学校煮饭,一个月120元而已!这水也不是任何人都会背的,一般是中老年妇女才会背,年轻人都是挑。“背水没得巧,只要屁股留得好。”她得意地说。
陆游当年的日记也对庙旁的背水妇女作过描述。这种生活方式千载未变。
太阳西斜,兵书宝剑峡上空开始酝酿出一些红色。这里的男孩女孩都生得秀气好看,这一点很难描述,只要想想屈原、宋玉、昭君都出自秭归就明白了。让人难忘的是那些女孩,都着个花布背心,修长的胳臂,总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持一只花碗,把指甲花放在里面不停地捣着,捣出一碗红色的水来。每个女孩的脚趾、手指甲上都涂得红红的。那个美丽动人!
此时,江渎庙前,女孩们围成一圈,互相勾着腿,喊着口诀,转圈儿跳着。看见我们,更是兴奋,不停地跳和唱,咿咿呀呀咿
呀……
那时我还没有多少在乡下借宿的经历,但从到达开始,就暗下决心不走了。傍晚,我们又去到杜老太太那里,她考察了我很久,终于同意。那木门厚实高大,几乎赶上一个小城的城门,大家使力关上,只听见吱呀的一声大响,门才合拢,这才放下了心,门,隔绝了外面厚重宏大的历史与风景。
躺在床上,我有些激动,终于住上这最后的古宅了。高高的窗子,明灭着过往的船上探照灯的余光。这个时节,夜里的三峡也成了繁忙的大街,旅游船头尾相连。此后十几年都难再有这种盛况。谁都知道将要发生什么。
次日早上,与杜老太吃了早餐,我们就告别。我要给钱,杜老太执意不收,我坚持,她只好收了二十五元,然后又送我一样东西,竟是刚完成的一双小小的虎头鞋。
她的指甲上,竟然也涂满浅红。
在剧变之前,桂林村好像还是那么舒缓。
她像江上人一样,习惯了风浪,以至于无所谓地从容?
这里大事太多,名人也如过江之鲫。
对门的新滩滑坡体,如同孙悟空,五百年闹一回,宋朝1032年左右滑过一次,断航23年,形成了青滩。关于这青滩的诗,有240多首,但没有李白杜甫的,唐朝一首也没有,而范成大、苏轼、陆游都有。江渎庙的建立与此有关。陆游当时在这座新庙里看到一块
碑,上面说公元1051年,归州知州赵诚组织人用了80天,疏通了此滩。又过500年,明嘉靖二十一年,公元1542年左右又崩了一次,断航82年。后来一位官员捐资,在冬季枯水季节,用木炭烧红巨石,然后泼上醋,石头裂开。就用这种方法勉强疏通了航道。
又过了443年,1985年5月12日凌晨3点,再次大滑坡,主要是采煤导致山崩。幸亏预报准确转移及时,新滩镇1730人无一死亡,但瞬间造成长江断流,涌浪36-70米高,翻小船96艘,死了十余人,断航12天。
上方的链子崖,现在还在闹着。这次,我从桂林村向西走向这座孤峰,山体最大位移竟达67毫米,持续不断。现在正花巨资
整修,用一条条几十米的钢钎打进峰体,锚进大山。如果这峰垮台,三峡工程还不知敢不敢开干。
大约半个钟头,就登上了两三百米高的崖顶,近看了那条十几里外就可见到的大裂缝。裂缝宽约两三米,深百余米、几十米不
等。往下望,似乎觉得随时会山崩地开,有些心慌。
从来没有这样走近过一座活动着的大山,好像接近了山的灵魂,触摸到了它的生命。这崩山之危与其说是天灾,不如说是人祸,当你触犯它,打击它,千百年岿然不动的老老实实的山也会发怒。这样的事实已经在新滩一带演绎过多次。我感到这里的山水人都永远地在活动着,拼杀着,暂时和平之时,便有世外桃源;一旦山崩地裂,它便玉石俱焚。人们在交响乐般的大背景中,与自然血肉相拼,吼出那悲壮激烈的号子来,而上得岸后,竟又能建立起小夜曲似的村庄。也许正因为生死无定,人们才懂得生活。
我看到大景无边,江山如画。我再一次俯瞰桂林村。在移民面前,在要拆的村庄里,在链子岩顶上,我的心情都是那么明亮。那时我真是蠢,真没想到这些意味着什么。我怎么也想不到,现在有多么美,以后就有多么痛。像一场没有结局的爱情。
我回来后三个月,1997年的10月,大江截流,前去采访的摄影师,如李洁军、张新民、方迎忠等人在我的介绍下都去过桂林村。李洁军告诉我,他去的时候,杜远翠老太太已搬到高处,房子正在拆,真没想到有这么快。
2002年1月,再度入峡。路过新滩,往上一望,桂林村荡然无存,心里咯噔一沉。
2002年10月,我从下游入峡,采访了浩大的大坝,然后入住秭归新县城茅坪。根据报上的消息,江渎庙已在茅坪凤凰山上复建成功。我决定去看看。
租了辆摩托车,从新城向江边山上驶去。凤凰山不高,一条土路环绕着它。在摇摇晃晃中,下方灰黄的三峡大坝也对我摇摇晃晃着。拐一个弯,走到大江南岸一侧,便看见它们立在那里。它们就是取自桂林村的建筑们。
爬上去。看见最外侧的是江渎庙,脚手架已清除,已告完工,看上去比原先要新一些。另一侧是七八栋民宅,都搭着脚手架,
复建了个七八成。每栋旁边立着个大红牌子,上写“郑万隆老屋”之类,全部姓郑。杜远翠的房子似乎并不在这里。
没什么人来,我走上立在平地上的廊桥,走进江渎庙。我看着每一处细节,眼睛一闭,就是兵书峡的夕阳里,荡漾起女孩儿们的笑声,咿咿呀咿咿呀……
我告别。我看见了活生生的建筑的木乃伊。没了那环境,人们,地气,它们就是永远不得安息的木乃伊。
第二天早晨,坐了秭归县的班船“凤凰”号上行。到新滩镇下船,租了过渡的小轮,让船把我们扔在当初桂林村下的江边。
我又走上青石板路。这路都不那么清晰了。到处是瓦砾,做地基的青石板看来也撬走了,只有地基的护坎还在,村中间的那条
水沟还可以辨出。桔树在废墟间生长。大树是没有的了。毒日之下,我还能回想起当初的格局—那一天是多么清凉。一个村庄可以这样干净地拔除,像移走一堆积木!
没想到山的凹处竟还有一栋老屋残存,门面也还过得去,还有些彩绘颜色,可见当初是桂林村的穷人家,只能画上几笔,所
以我完全记不得它。叫了几声,主人夫妇迎接出来,表示欢迎。
这是栋没有天井的老屋,规模很小,两侧墙壁应坍塌过,胡乱砌了些土砖,难以挡风遮雨。男主人很瘦,头发仿若道士,说祖上
穷,房子算差的。因为后靠宅基地没划好,他们就还没搬。
吃了桔子,喝了茶,我们又往高处的新房子走了去,找到一条土公路。一位摩托仔告诉我,杜老太也在上方建了房子,她还珍
藏着来自广州的报纸。
一路上因为清库和修公路,当初的田园景色,那几步一换的乡村图画都已荡然无存,只有连片的荒坡了。我对那田园和植株的热爱,简直超过村庄。我想起这里遇到过的那位老人的话:一场空……
上了艘小船。又投上游去了。这半年在三峡来来回回,一场奔波,一场徒劳。像是坐个船在大江中捞一根稻草,却怎么也捞不到。
谁掠夺了我们的沉醉?我宁愿当初没有遇见!我现在只想说一句套话:我们会永远记住她。
我一张全景照片也没给她留下。我,很惭愧。
乐平里
香溪,是屈原的路,也是昭君的路。
我想直到死去,我都会常常回想起,2002年5月26日那天,我顺着香溪走向乐平里的每一个细节。
到现在,这竟然是十年前的事了,然而清晰有如昨天。下面的文字,也是2004年写的。它同我这两年的三峡文字很不一样,现在我话不说多,沉郁顿挫,自以为味道十足。所以想改掉。
但是,我又从当年的文字里看出一个主题—青春!我的文风,香溪的气质,急流的三峡,和屈子昭君的曾经少年,都竟然,青春。
于是还是保留吧,这青春的文字——
现在,这一切都在水底了。没去过的人,后世的人,永远想象不出水底下曾有如何的活的世界,好的故事,想象不出,屈原当初顺着这条溪谷走出家乡的情景。总之我感到幸运。我能在5月26日那天,触摸到香溪那几乎最后的温婉的脉。那天早上,我和黎文、曾翰从归州出发,大江东去,战车轰鸣,路面坑洼处处,两边乱草疯长,我们行驶在一条被人遗忘的公路上,驶向将被世界遗忘的地方。
十几里后,就看到已失去建制的拆得乱七八糟的香溪镇,看到香溪入江口那清浊分明的一线。以前江上往来时让我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香溪镇,此时已乱壁残垣,尘雾阵阵,人们都灰头垢面。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果然有人在我前面对“美人”下手了。好在从镇东边望下去,香溪还在,她有不见底的蓝,平静丰盈。昭君像正亭亭玉立地站在河对岸。
北望溪谷,东岸是大山脉直入云霄,西岸则是土山逶迤,一条公路通向兴山县昭君村和神农架,路边民居星星点点。香溪,本身就是一条奇妙的地质分界线,一边是石一边是土,一边是高山一边是人间,虽然不如小三峡神农溪那样峡壁对峙而成著名风景,但却形成了最美的人间。
沿溪向北。司机小伍说,自从三峡上马后,近五六年来,这条著名的公路就不再维修了,到现在是勉强通行,如果不是运矿的人和老板主动拿石头补补填填,恐怕早已报废了。田园虽破,犹可想见当初沿这条精致的柏油公路与溪并肩穿行在田园风光中的快意。不久便见到一座长长的铁索吊桥。吊桥上下起伏,其下溪流清清,河中一块千来平方的洁白的石滩上,有位青年几乎裸体,撒网舀鱼。
实在太美了,要是哪一天从溪上游水下江那就太过瘾了。来到对岸,上了一小坡,就看到一块平地,那就是王家祠堂的废基。我们又来晚了。要是祠堂未拆,该是多好的一幅景色:香溪,吊桥,飞檐……
继续前行,一个多小时后,吉普车艰难奔到游家河,又是一座吊桥。对面有一个狭窄的缝隙,如同天斧把大山一劈到底,那就
是七里峡了。
过了吊桥,坐上摩托,沿着简易小公路进七里峡。峡如一线天一样,只有十来米宽,幽深秀丽,飞瀑高的有百余米,而大山直上千多米,直攒天顶,磅礴至极。摩托车手十分老练,高速行进,下俯深溪,我们心惊胆战,有时就闭眼,听天由命,心想真死在屈原故里,也不算太冤。到了极险处,公路突然钻进隧道。
隧道是人工凿出的,洞壁岩石犬牙交错,洞口洞中水帘阵阵。出洞之后窄峡突然断绝,眼前突然开朗—土地平旷。
屋舍俨然。
心,一下子竟然极其平静。
没几步到了“乐平里”牌坊,下了车看了看,是20世纪60年代的朴实风格。想必“乐平”的意思,就是“快乐地生活在平地上”吧。眼前的乐平里,四山环合,平地约两千亩,中间一条笔直的清流。山坡上屋舍整齐,均素瓦白墙,上锥下方,没有拖沓的偏屋,各自独立,分布合理,整齐干净。我们惊呼为简约主义杰作。
沿溪上行,平坝左侧上方有一山包,其上有平台,屈原庙简朴优雅地立着,右上有一山包,其上亦有平台,即是屈原出生地香炉坪。
我们在香炉脚下唯一的小街停下,钻进小店找饭吃。小店有堆得整齐的新家具,方桌方凳,椅子板凳,样式恍若宜家,厚实方正,榫头严丝合缝。我广州来的两位兄弟左摸右看,赞不绝口,恨不得带回去。
这一番下来,就觉得不难理解这地方为何能养育出屈原了。朴直高洁,是它的美学风格。直到现在,乐平里都有一堆农民诗人。
这里好像没有时间的概念。然而山外巨变,像一把剑悬在我们头上,催促我们赶路。屈原庙前,乱草疯长,看来没有多少人来。小庙朴实无华,庙祝正在下面条做午餐,大桌之上满布墨渍,放着一叠他写的书法。老人姓徐,屈原乡人,毕业于新中国成立前的秭归师范学校,现为退休老师。他的字不错,大多写的是《桔颂》。为何只写此篇,我忘了问他,现在回想起来,无他,《桔颂》是屈原直接描写家乡风物的作品。
《桔颂》也是屈词中唯一没有悲剧色彩的作品,清新如乐平里。我也估计这诗是屈子少年时在这里的作品,那时他还不知道,这世界有扼杀少年的癖好,以后他将不复青春。
向徐先生说要买一幅《桔颂》,他怎么也不说价钱,只说随便给一点,我就放下了20元。徐先生又掏出钥匙,打开主厅,汉白石的屈子像立在我们面前,头顶瓦片透下了点点光线,应该是仿陈洪绶的《屈子行吟图》而造。陈老莲笔法老辣苍劲,颇得屈子之神。汉白石材质也适合他—没有人比他更适合用这个形容词:洁白。
这座简陋的庙,别无长物,然而有这么一尊像,也就足矣。我们对着屈子拜了几拜,便转身下山。又到七里峡,再一次惊心动魄。下一次来,也许三峡水库水已漫到这简易公路,四乡游客坐着游艇,轻易可到这乐平里。屈原的家园会成为一大旅游胜地,只是损失了屈子的七里路。
我放弃了上游三十里的昭君故里—一年后去了,那里溪流更加清浅。与屈原昭君当初走出的方向一样,沿香溪向南,好不容易才等到一辆过路的客货小车。由于人多,我和黎文坐在车斗里,旁边不时挤上乡民。这样眼前没有遮拦,美丽的香溪和路旁的废屋几可手挽,我们呼吸到山溪的清新空气,也吞食着不时扬起的漫天灰尘。乡民们互相并不认识,但他们很快聊了起来。话题都是移民。
对面一个脸色蜡黄的大嫂,开始小心地询问我们的身份,后来又掏出一叠盖着公章的纸,在摇晃的车斗里开始絮说起来。我始终无法认真倾听,因为这样的絮说我已听过很多,她不说话我也知道她想说些什么。由于堵车,这条路走了很久,两个多小时,她也就絮絮叨叨这么久。初来的黎文,没经历过这些,他的神情越来越严肃,一直听到面目呆滞。我大致记得一些,归纳于此吧—
……我家六口人,两老,两小,小孩都在读中专……我们没赶上第一批外迁,因为我们觉得可以后靠安置,但现在又不给宅基地了,一家人的房子又拆了,只好住在窗棚里,你看,这路上很多人都搭着棚子住(她手指向时不时出现的窝棚)……补偿我家八万元,所有算在内(她提到柑桔树是数十元一棵),安置在外面,要交很多手续费,万把块钱(她一遍遍地给我们算账)……平原上的安置点我都去看了,给水田宅基地,但也要不少手续费,当地也靠这个赚钱。当地人也欺负移民(同车人就此问题议论起来,都有些不踏实)……如果去了,各种费用之外,剩下的钱盖了房子也就没有了,你看我这人,智商也不是很高,也不会做生意,种田也不赚钱,以后怎么办……申请不到宅基地,还是得外迁,办完所有接收手续,要盖十八个公章,我这就是归州镇跑章子去的……我们家就在前边,已经拆了,等下你们就可以看见……
我在这里要强调一点,几乎所有移民都会像她一样,有一句通用句式,这一句不是口头禅,因为很诚恳:国家搞建设,我们要支持,但……
我也在此向这里的乡民表示敬意。因为他们诉说之时仍有一份克制,有一份尊严,多少让人想起,当初的屈子,就是要投水,也在无人处。就像这位女士一样,她的眼泪总在打转,但始终忍着不让出来。
据黎文说,后来她突然指了指路边的一处废墟,说“那就是我的家”,然后眼泪终于流了出来。
那曾是多好的一个家。行走香溪道上,2002年,我感到有一丝惊异,几许疯狂。一路的风景,伴着一路废墟,一起展开,一直摇晃。
在摇晃中,我看见废墙上,一树树月季花犹自盛开,收拾得很好的庭院,依稀还有几分风采。想当初从自家院里对着香溪的美景,这是何等的所在!
我看见一堵石砌的猪栏上,未搬的猪探出半身,几欲坠落,观看着香溪的美景。我看见公路中间被弃的沙发开了个焦黑的洞,毫无理由地独自燃烧。
像一场电影:灰尘总在车尾巴后呼啸,人在无言地移动,狗在追着我们跑……
我有一种想嚎叫的感觉。车停香溪废镇,我们下了车去找船。那位大嫂也下了车,说赶到归州镇也办不成事了,且在镇上的亲戚家借宿一晚。夕阳映红了废墟,香溪旧港今晚不会有船靠岸。
本来停靠这里的大船比归州还多的。我们心绪不宁,决心尽快离去。找车并不容易,正在着急的时候,小伍沾满灰尘的吉普竟然
在满是灰尘的街道上出现了,上面坐着镇长,他说香溪里有一处滑坡,刚看过回来。我们挤在里面,向长江上游奔去,乐平里和香溪在我们身后消失,就像当初在屈子身后消失一样—那一天可能也是这么晴朗,桔子花在香炉坪上飘香。楚王的命令已经到达,年轻的屈原脸上写满向往。他戴上高高的“切云”之冠,然后穿上宽大的长袍。他知道乡亲又要笑他奇装异服,然而他热爱这一身盛装。他挂上心爱的长剑,走过飘香的桔林。他想起他为这桔树写的诗,那诗仿佛预测了今天的心境。他感到自己获得了满身的香氛,在乐平里的溪边款款前行。他来到溪流的入江之口,呵,浊流里洗了洗脚,清流里洗了洗缨。他再一次看一看西边的巫山,那里是西王母女儿瑶姬的所居,她每天在山峰间播云,和其他神奇浪漫的事。他看一看东边的峡谷,感到路漫漫其修远,又感到都城就在眼前。回首那香溪里回家的路,他心想哪一天一定会回来……事实上他永远不能再回来!!!
很多人就这样不会再回来,回来也不再会是当年的那条路。
我走的时候,就知道我会再回来。2002年10月18日,我在三峡狂奔两周之后,一片茫然。我于是急急奔到归州下船,租车奔到香溪。在那美丽的沙洲上,在洗衣乡亲们的笑声中,我脱得只有内裤,一下跳进那河里。看上去昭君般温柔的河,原来是那么冷,那么急!
我游的时间很短,但我想我可以不用再回来。我的小四轮司机乔梅邀请我到高山上她家玩。当晚在院子里,乔家请来山民们陪我喝酒。话都记不得了,只记得有个高瘦的农民,以贩卖桔子为生,长得像林子祥,整晚沉默不语,偶尔讲一些收成和价钱的事。他端着一搪瓷缸子酒,听着我说了半天,突然平静地说了一句话:
“这就是人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