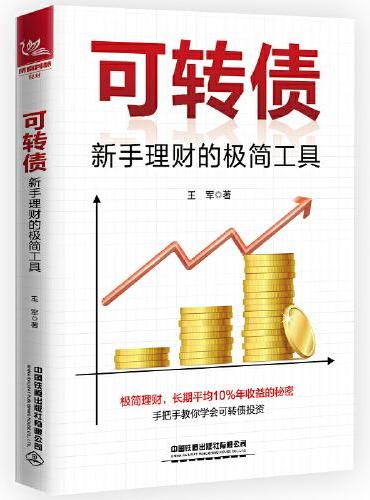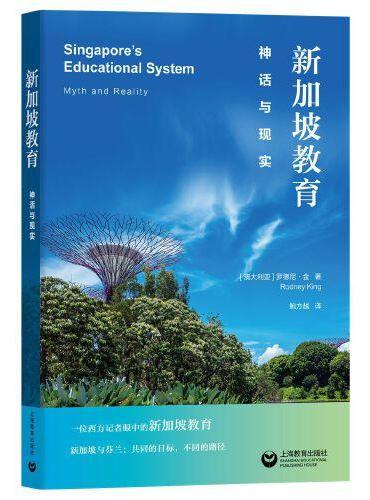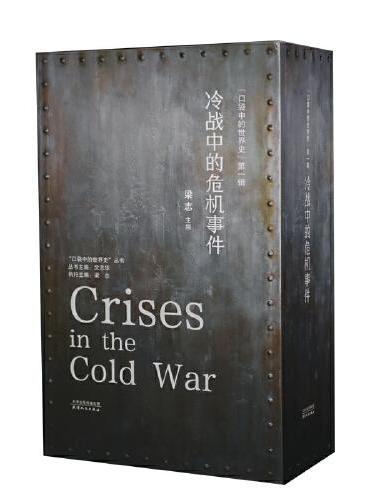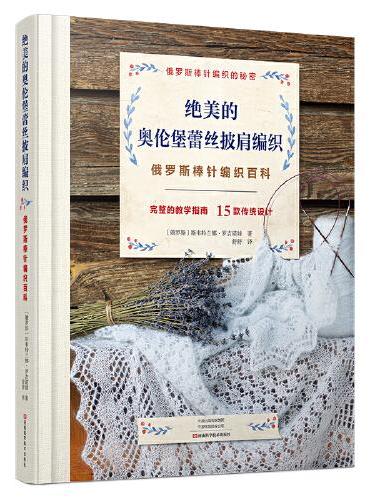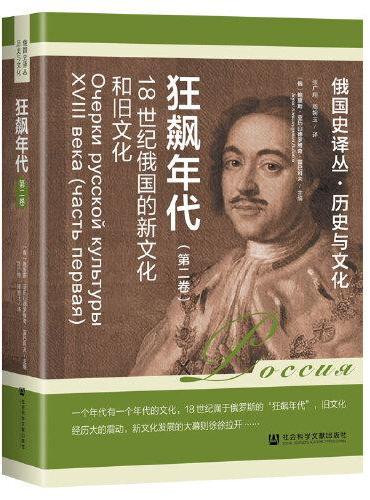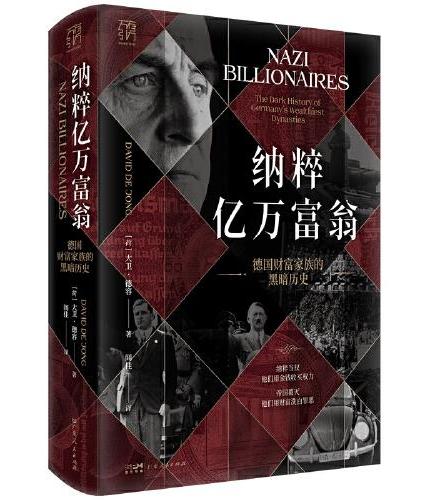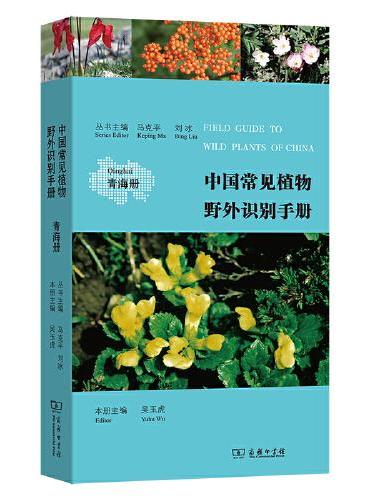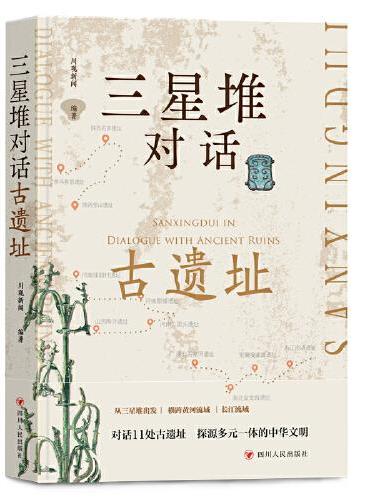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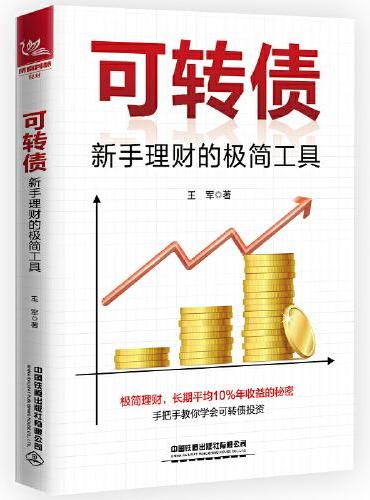
《
可转债——新手理财的极简工具
》
售價:HK$
6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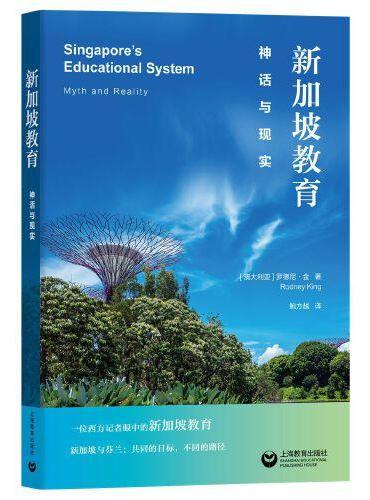
《
新加坡教育:神话与现实
》
售價:HK$
9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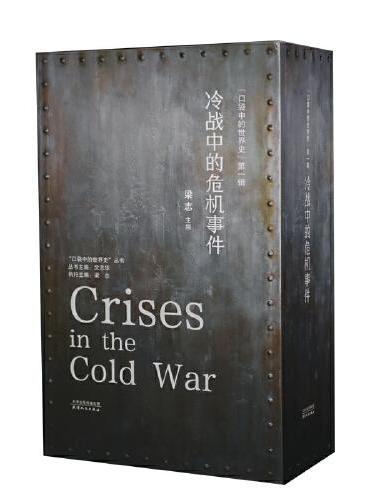
《
“口袋中的世界史”第一辑·冷战中的危机事件
》
售價:HK$
29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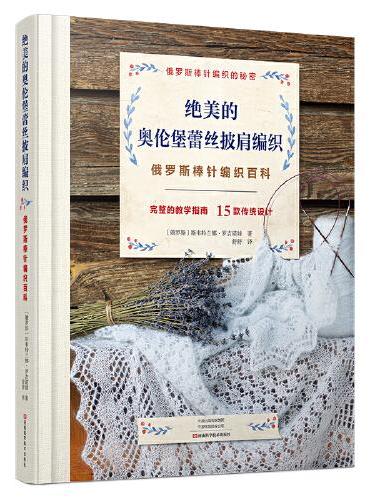
《
绝美的奥伦堡蕾丝披肩编织
》
售價:HK$
17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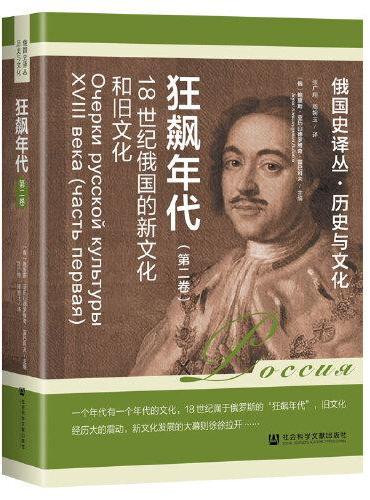
《
狂飙年代:18世纪俄国的新文化和旧文化(第二卷)
》
售價:HK$
17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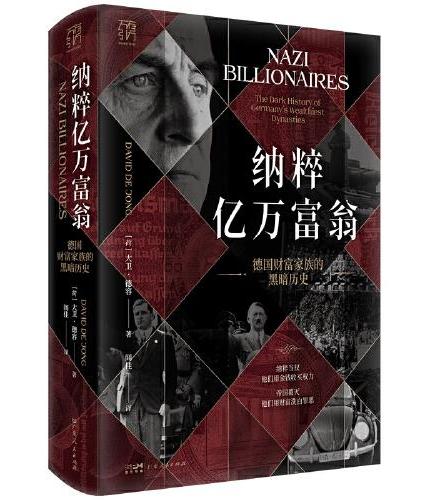
《
万有引力书系 纳粹亿万富翁 德国财富家族的黑暗历史
》
售價:HK$
1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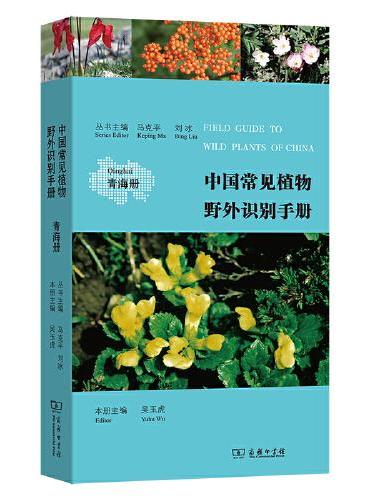
《
中国常见植物野外识别手册:青海册
》
售價:HK$
7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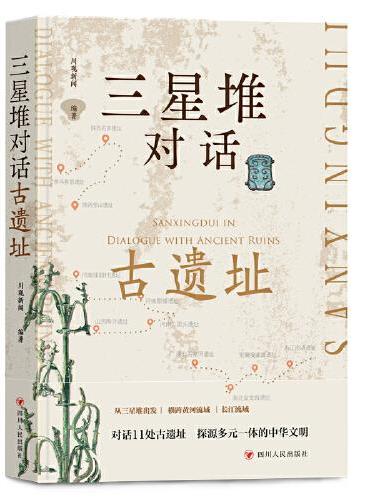
《
三星堆对话古遗址(从三星堆出发,横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对话11处古遗址,探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
售價:HK$
87.4
|
| 編輯推薦: |
1.《何有此生》,一部感动中日两国的感恩与励志之书。
2. 一位执著的日本老人,用五十年人生回报中国人十五年的养育之恩!
3. 一部个人史,书写了日本少年在中国北方农村长大成人的传奇经历:作为侵略者来到中国,战败后离开亲生父母,与中国养父母、师友、玩伴有着感人至深的亲情故事,真实展现不分国界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普通中国人身上的人性光辉。
4. 日文版上市后三个月内加印两次,更多日本人正在被改变。
5. NHK、朝日新闻、东京新闻、法新社、新华社、人民网、人民日报、环球时报深度报道,开启感动之旅。
|
| 內容簡介: |
他是一名“老日中”,即日本的日中友好活动家。
他曾与唐家璇同场做过翻译。唐家璇主动介绍他说:“中岛先生长期从事日中友好工作。”
他始终对中国怀抱感恩之心,愿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中日两国友好做见证。
中岛幼八,曾作为日本遗孤在中国生活十五年。一岁即随父母来到中国东北牡丹江省宁安县。战后,他没有随亲生母亲返回日本,而是凭着自己的意愿,和中国的养父母一起,度过了典型的中国北方农村的童年生活。他的养母和养父都是勤劳淳朴的中国农民,这塑造了中岛幼八朴实坚毅的性格。十六岁回到日本后,中岛幼八凭着这种性格成功地适应了日本社会,并始终实践着自己终生为日中友好而努力的人生理想。
|
| 關於作者: |
|
中岛幼八,1942年生于东京三田。一岁时全家移居中国东北,抗战胜利后由中国养父母抚养长大,1958年回国。1966年进入日本中国友好协会总部事务局,主要从事翻译工作,全面投身于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群众运动。之后也一直从事日中翻译工作,为两国的交流服务。六十九岁退休,七十岁开始撰写回忆录《何有此生》,完成日中两个版本。
|
| 目錄:
|
致中文版读者
第一章 全家去中国东北 战争的迷途
第二章 濒危 “这条小命,我拉扯!”
第三章 遣返 争子、夺子始末
第四章 起死回生 春回沙兰大地
第五章 成长 上学读书
第六章 陈家养父丧生于疯狗
第七章 桂芳姐姐 巧遇日本姑娘
第八章 新的养父 难忘的人们
第九章 1950年 知悉日本情况
第十章 开拓团的孤儿们 日侨注册
第十一章 愉快的学校生活 难忘的老师和同学
第十二章 接生婆的骄傲 “俺儿子是日本人!”
第十三章 农业合作化 土地、牲畜集体所有
第十四章 放牛娃
第十五章 发大水 “天塌下来你能跑得了吗?”
第十六章 传统的春节 乡下的生活喜气洋洋
第十七章 再次起死回生 在养父母的怀抱里
第十八章 沙兰小学毕业 我被强制送回日本?
第十九章 离开沙兰 初次看到外面的世界
第二十章 移居太平沟林场 森林小火车的汽笛在山间鸣响
第二十一章 又上学读书 幸遇终生恩师
第二十二章 与第三个养父一起度过的日子
第二十三章 转七峰小学 在新天地里的奇遇
第二十四章 人生转机 回日本的心情开始启动
第二十五章 无暇告别 上路回国
第二十六章 东归 乘“白山丸”
第二十七章 尾声
悼念
附录 我和中岛幼八 梁志杰口述 仇庆林整理
|
| 內容試閱:
|
致中文版读者
日语中有一句名言:“养育之恩大于生育之恩。”(生みの恩より育ての恩)我回顾了自己的人生,无论从实际情况来说,还是从我的亲身感受来说,完全证实了这句名言的正确性。我已年过七十,体质甚佳,在两年半的时间里,写出自己的回忆录(日语版和中文版的两个版本)来,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归根结底,这是中国养育我的结果。
因此,在这里我首先要说一句心里话:谢谢,中国!
我要写回忆录的动机,不外乎是这句心里话推动了我。所以,我所写的并不是我,而是一把屎一把尿拉扯我长大的中国养父母,以及老师、同学和乡亲们。在写作过程中,我痛感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没有把他们写好。我不是以写作为业的人,也没有学历,在中国读到小学毕业,回日本后只读完了高中课程,并且是半工半读的夜间高中,因而表达能力自然差劲。何况回日后时达五十六年之久,中文表达能力自然落后。各位中文读者读起来一何有此生 一个日本遗孤的回忆定很吃力,在此一并致以歉意。
我首先写了日语版原稿,在此基础上写了中文版原稿。两个版本在情节上基本一致,个别地方做了增减。为了使日语版读者能够理解我的成长过程,写的日常生活——吃、穿、住、行以及中国的习俗,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过于啰唆。另外,面向日本读者,我着重写了与日侨有关的人物和事情,目的是想让更多的日本读者理解我们这些遗孤是在中国人的人道主义精神下得以活下来,所以没有做任何删减。
我与各位读者有着共同的心愿,那就是希望日中两国人民永远友好下去。为此,我认为增进双方的相互了解是最关键的。这样两国人民才会不受任何干扰,而互相信任下去。相反,如果缺乏信任,那就必然要产生误会或误解,从而导致冲突或纠纷。
从1945年8月15日算起,已经过去七十年了。为使两国人民友好相处,增进相互理解,不使灾难的噩梦重演,这本回忆录如能起到一些好作用,则是我十分欣慰的。
第四章 起死回生 春回沙兰大地
我管养母叫“妈妈”,平常简称叫“妈”的时候也有,在日语听来有点洋气味儿,但在中国,这是传统的叫法。那个时代中国的妇女差不多都没有自己的名字,一般是丈夫的姓加自己娘家的姓,再加一个氏字。譬如我妈是陈孙氏,后来才改为孙振琴。
对养父我叫爸爸,简称叫爸,这也是传统的叫法,我爸全名叫陈玉贵。独生女儿叫陈桂芳,年龄比我大一轮,我叫她桂芳姐姐。
把我抱过来的时候,养父也不太同意。在那一贫如洗的年代拉扯一个孩子比养活一个大人还不容易,这对养家糊口的一家之主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对操持里里外外家务的女方来说,也深知持家的不易。但慈母的爱心胜过一切,所以她毅然地抱养了我这个濒死的日本孩子。她本人自打懂事时起就丧了父,随母改嫁到老孙家。
她从小尝尽人间的苦,也养成了对他人的爱心。
养母是老式的接生婆。过去中国农村没有产院,也没有什么接生员,养母本着她生有的爱心,不知接了多少孩子诞生于世,这使她懂得了生命的可贵。我这个幼小的生命也是在她的爱心下获得成活的机会。
养父母给我起了个中国式的小名叫“来福”。这个名字寄托了养父母的希望,直到我上学前大伙儿都这么叫我,也有的时候只叫福儿。我清楚地记得在我回国后,第一次访华时,我从天津给养母挂了长途电话,由于信号不好,接通之后只听到那一端养母嘶哑地喊“来福,来福”那微弱的声音。过了这么多年,依然留在我的耳边。
上了学以后,我有了个学名,叫陈庆和。尽管这样,像刚才说的,过了好多年,养母仍然不叫我学名,一直叫来福。如果养母现在还健在的话,她老人家仍然不会改变,会照样叫我来福。
这两个字寄托了她对我的希望。
关于年龄的问题,一般日本遗孤回来寻亲时因为没有准确的生日记录,大都采用所谓推定年龄。而我虽不知道自己的准确出生年月日,挑担小贩老王把我接过来时生母告诉他的三岁就成了年龄的依据。但是我的日本名叫什么,却没有传过来。
我被抱到养父母家以后,语言也由当初的日语,很快就改为 汉语。
沙兰镇这个小镇,四周由土墙围起。好像是日本在东北地区建立伪满的傀儡政权,为了便于统治,把散居的当地居民,全部集中到土围子里边居住。所谓土墙,只不过是挖土垒成的墙,墙外边是挖土堆墙剩下的壕沟,兼备防御性。已过多年,土墙越来越矮,不过,壕沟有些地方还是比较深的。土围子四周各有一座门,称为东、西、南、北卡门。过去也许有过门,现在只留下一点痕迹,成为道路的缺口。出了东卡门,就是一个陡坡,称之为东岭。从这里可直达东京城,是通往火车站的要道。
镇的东、西、北三面都是岭,形成一个簸箕形盆地。大体上是四方形的土围子围起来的这个小镇,便坐落在盆底。沙兰河从小镇的西北角流进来,向东南角流出,与牡丹江汇流。小河,规整地把小镇分成了两个正三角形。
走出南卡门,则是一片开阔的火山熔岩覆盖的平川,一望无际,一直延续到南面的山根,当地称它为南石岗。虽是平川,坑坑洼洼的熔岩形成的地表没有土,不适合耕作,只能长一些灌木,还有狼窝等野兽的藏身之地。在远离几十里地的西边远处,尚留有远古时期的几个火山口,形成地下森林。当地对这个奇观,已经熟视无睹。谁也没去认真琢磨过火山爆发流出的熔岩垫平了这个石坑子,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质现象?南面的山脉顶峰叫老黑山,这可能是山北这一带人起的名字,因为从北边看上去山背面一直是黑的。当地的习惯,看风水的时候,中心点都要对准老黑山的山尖。闻名的景区镜泊湖如项链一般,绕在老黑山的山脚下。
沙兰又叫沙兰站,站是驿站的意思,清代时,西自吉林、东至宁古塔(宁安的古称)是一条交通要道,沙兰是其间几个驿站之一。据说过去在这里设有管理驿站的衙门机构。日本人进来后,驿站的衙门被撤销了。但是,它作为交通的要冲,继往开来,支撑着沙兰的繁荣。
从东卡门进来往街里走,过河之前,道北有一片庙宇,当地叫东大庙,是镇守沙兰的土地神。前后排着三栋朝南的庙堂,里边立着一些色彩鲜艳的雕塑像。我小的时候,还看到过有人在那里烧香跪拜。以后逐渐没人信,香火也就断了。到了夏天,荒草齐腰深,破砖烂瓦满地皆是。有时大蛇挂在屋檐下,晦气阴森,无人敢进。合作化的时候,这里改成了仓库。我回日本的时候,庙宇已经不复存在。
东大庙的东邻是一片大菜园子,姓罗的老两口儿种菜,人们叫它罗家菜园。为了防偷菜,罗家养了几只狗。这几只狗,以后竟成了我家的祸根。
道南对过儿是地主陈家的宅院;东院靠墙根有长工们住的长条房子。我家住在正房的西头,门前隔着一条很窄的通道,面前就是西厢房的山墙。东厢房住的老胡家,我后头会说及。窄小的过道通向西大院,那里曾经住着地主陈玉喜一家。养父陈玉贵和他们是叔伯弟兄,但人家是地主,养父给他们当长工。养父母成婚后,也跟别的亲戚一起,住在西院长工房子的南北阁大炕。
土地改革前,一夜之间,大地主全家都跑了,无影无踪,丢下了大宅院和东院的三栋长工住的房子。陈玉喜还有个弟弟,叫陈玉风,是村里的中医大夫,他没跑,留在村里,也是个很歹毒的大夫。养父对他恨之入骨。
土改以后,打长工的佃农分到了土地。我家分的地在东岭顶上,田垄很长,是比较大的一块地。养父很高兴,还立了一块牌子,标上自己名字。这块地在东岭的上边,往下可以俯瞰整个沙兰盆地。远望出去,南石岗及其南边像展开的屏风似的老黑山俱收眼底。
我家虽然有了土地,但没有其他农具、牲畜等生产资料。播种前需要耙地,使土地松软,只能借用别人家的牛,用来拉钉齿耙。这耙地像在大地上扫描似的,来来回回地耙。为了使钉齿耙能够较深地耙地,上边需要有些重量。养母带着我站在钉齿耙上,手扶立杆,对我来说,既好玩儿,又能帮上忙。
在谷雨种大田的时候,气候已经比较暖和了,我也高高兴兴地跟养父母一块下地。在种谷子的时候,先在田垄上蹚成一条小沟。往小沟里播种子,这是养父的任务。他老人家肩上挎一条细长的口袋,里边装满谷种子,口袋的一端系在空心的木制管子上,管头的出口用枝丫堵着。对准小沟,用细棍边走边敲打管子,里边的谷粒儿均匀地被震出来,撒到田垄的小沟里,养母随后用脚盖上土。我们叫“点葫芦”的这个播种工具可能今天已经进入农具博物馆了,但敲打时的声音在田野上回响,在我的记忆里不次于八音盒的旋律。播大豆的时候,养母在田垄上按一定间隔挖小坑,养父随后点上大豆种子,用脚盖上土即可。这是单调的动作,没有任何旋律。
无论播什么种子,我都帮不上忙。我的记忆之中,最好玩的是听鸟叫。地上到处都是播种的声音,天上能听到百灵鸟的叫声。在广阔、瓦蓝的天空中,多么好听啊,可就是看不到那百灵鸟在什么地方,长的什么美样儿。我问养母哪里有鸟呀?养母说:“福儿,你在地上给它做个窝,它就会下来了。”我就用土块堆砌起来给鸟做窝,盼着百灵鸟,却始终没有鸟飞过来,我的一天也就这样结束了。
夏季的一天,大人在拔草,我在地边上午睡。养母为了不让我被蚊子叮,便把蚊香放在我身边。这蚊香是用艾蒿编成绳,晒干后点火烧的,不会灭。我睡得很熟,翻身时碰到了蚊香,火烧到我的衣服上,把我烫醒了。我一下子哭了起来,养母听到哭声,看到冒烟,赶紧往我这边跑,还喊我往她那儿跑。遇到一起后,养母赶紧把烧煳的衣服扑灭了。养母麻利地把活儿收拾一下,提前带我回家,到家后又马上在烫红了的地方抹了药。养母做什么事都是雷厉风行,真像刮风似的,呼一下就行动起来。
在这个时期,我们家还没有牛或马等牲口,都得靠养父母自己的身体拼死拼活地干庄稼活儿。养母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庄稼活儿就得靠自己,一颗汗珠儿掉下来摔八瓣儿。”我也深有体会,庄稼是靠汗水长的。
我稍微大了一些,有一年夏天干旱,不下雨,村里动员大伙儿去东大庙拜神求雨。我也跟别的孩子一起,头上戴着用柳树枝子编的圆套儿,混在人群里,和大家一起上大街,呼喊求老天爷下雨,感觉很好玩儿。
回家时,本以为养母会夸奖我求雨,做了件好事。没承想她老人家完全相反,不但没夸,还数落了我一顿。
“什么求雨求神的,老天爷能给你下吗?”她每天和养父一起,从附近的河里挑水往地里浇。他们除了自己的汗水以外,什么都不信!神啦,鬼啦,对他们来说都不值得信。这一点,至今对我影响很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