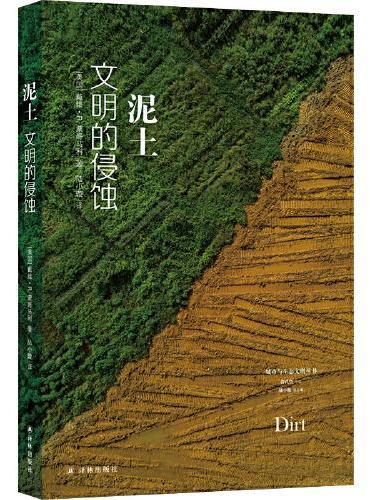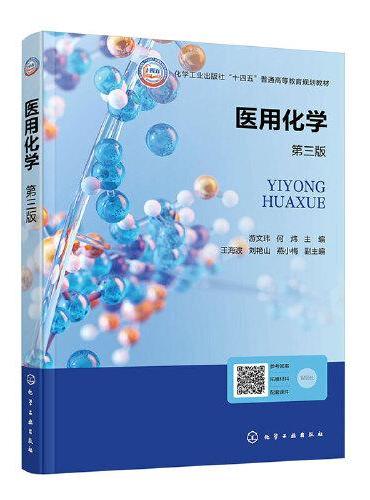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家书中的百年史
》
售價:HK$
79.4

《
偏爱月亮
》
售價:HK$
45.8

《
生物安全与环境
》
售價:HK$
5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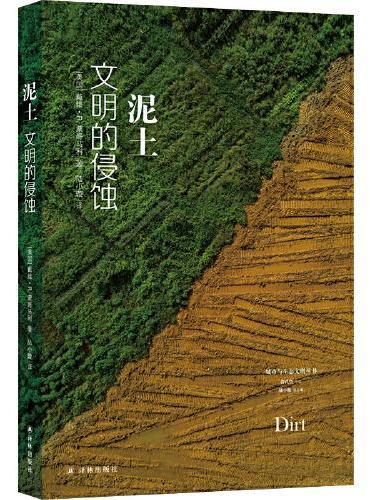
《
泥土:文明的侵蚀(城市与生态文明丛书)
》
售價:HK$
8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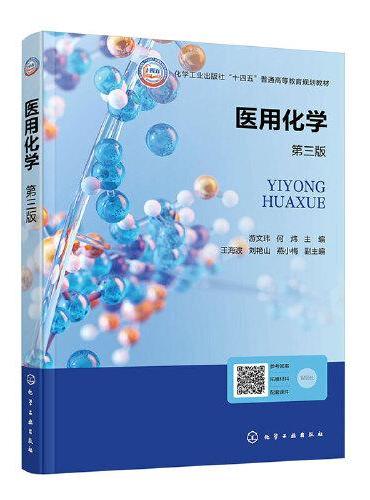
《
医用化学(第三版)
》
售價:HK$
57.3

《
别怕,试一试
》
售價:HK$
67.9

《
人才基因(凝聚30年人才培育经验与智慧)
》
售價:HK$
103.4

《
深度学习详解
》
售價:HK$
114.8
|
| 編輯推薦: |
◎艾柯《开放的作品》出版后于在西方文化界引起了一场巨大而持久的争论,这场争论持续了好几年,成为西方走向非传统的“人文学”的美学起点。
◎《开放的作品》列出了萦绕在艾柯学术生涯各个领域的最核心的哲学概念:没有任何一种意义应当是绝对的。从《开放的作品》开始,艾柯之后的每一部著作都探索着如何取消绝对化的概念,打破封闭的语言与文化系统,以及塑造一个开放的、不断运动的人类社会的方式。可以说此书是理解艾柯的文学作品与文艺思想的关键与入口,要读懂艾柯此书不可错过。
|
| 內容簡介: |
《开放的作品》是艾柯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是当代意识理论的革命性标志作品,以及讨论语言技术和20世纪先锋艺术的思想意识作用的坐标。艾柯作品理论中的“开放性”这一重要概念在西方文本理论中具有重要意义。
《开放的作品》中涵盖了十二音体系音乐、乔伊斯、试验文学、非形象绘画、运动艺术、电视直播的时间结构、新小说派以及安东尼奥尼和戈达尔之后的电影、信息理论在美学上的运用等。
|
| 關於作者: |
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享誉世界的哲学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符号学家、美学家和小说家,20世纪后半叶最耀眼的意大利作家,当代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经典小说《玫瑰的名字》在全世界销售了1600万册。艾柯的学术研究纵横古今,小说随笔睿智幽默,著作横跨多个领域,并在各领域都有经典建树,“欧洲知识分子以书架上放一本艾柯的书为荣。”
艾柯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至今出版的各类著作已达140余种,主要作品有:《误读》《带着鲑鱼去旅行》《开放的作品》《玫瑰的名字》《傅科摆》《昨日之岛》《波多里诺》《植物的记忆与藏书乐》《别想摆脱书》《不存在的结构》《悠游小说林》《中世纪艺术与美学》 《符号学理论》等。
|
| 目錄:
|
第一版序
第二版序
《开放的作品》:时代和社会
第一章 开放的作品的艺术理论
第二章 诗的语言的分析
第三章 开放性、信息和交流
第四章 视觉艺术中的开放作品
第五章 事件和情节
第六章 禅和西方
第七章 关于关注现实的形式模式
附录:伊甸园语言中美学信息的诞生
译者说明
|
| 內容試閱:
|
时代和社会
来自作者
1958年到1959年,我在米兰电台工作。在我的办公室楼上两层是音乐节目编辑室,当时的负责人是卢恰诺?贝里奥。经常来的有马德尔纳、鲍莱兹、布瑟和施托克豪森,这里人来人往,人声嘈杂,一片混乱。那时,我正在研究乔伊斯,晚上常到贝里奥家,卡西?贝布里安做的是亚美尼亚饭菜,完了之后就读乔伊斯。正是在那里产生了录制乔伊斯的想法,录音节目原来的题目是“纪念乔伊斯”,这是在电台广播的一档节目,每期45分钟。一开始的时候是朗读《尤利西斯》的第11章(这一章叫《塞壬》,是拟声的狂欢),用3种语言朗读,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后来,因为乔伊斯自己说,这一章的结构是卡农赋格,所以贝里奥开始在原文上加上赋格音乐,先是英语加英国音乐,然后是法语加英国音乐,依次类推,一种像多种语言的马尔蒂诺?坎帕纳罗和拉贝拉伊西亚诺的节目,像交响乐一样的效果(但一直是只有人的声音)。后来贝里奥只就英文原文展开工作(是卡西?贝布里安说的),挑选出一些音素,最后组成了一种名副其实的音乐作品,灌制成唱片时用的仍然是《纪念乔伊斯》,但这同原来的电台节目已经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一种解说加评论的内容,对作品逐段进行评论。就这样,在这种气氛之下,我发现,电子音乐家们,或者说一般的新音乐家们的经验是一种典范,是各种艺术的共同倾向的典范。我还发现了同当代科学发展的相似之处……简单说来,贝里奥在1959年问我能不能为他的杂志《音乐会见》(总共只出了4期,但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写一篇文章时,我拿出了1958年在国际哲学大会上的报告,开始写《开放的作品》中的第一篇文章。后来又写了第二篇,以及一些争论性的注解(比如同费代莱?达米科就进行过激烈而又激动人心的争论……)。尽管有所有这一切,但我当时还没有想到要写一本书。是伊塔洛?卡尔维诺想到了写书的事,他读了《音乐会见》上的文章,问我能不能抽出一部分来让艾瑙迪出版社出版。我答应说可以。我又考虑了一番,从那时起,我开始计划出版一本完整的书,对开放的作品这一概念进行系统的总结。与此同时,我在《韦里》《美学杂志》等杂志发表了一些文章。这些是从1959年开始的,到1962年,一切还远未结束。同我一起工作的瓦伦蒂诺?邦皮亚尼那年对我说,他想出版这些文章中的一部分文章,他看过了这些文章。我想,在等待出版“真正”的书的时候,我可以先凑成一本试探性的书。我想用“当代艺术理论中的形式和不确定性”作为书名,对书名历来十分敏感的邦皮亚尼几乎是很偶然地翻看了几页后说,就叫“开放的作品”吧。我说不行,我想把这个书名留给将来那本更全面的书,如果现在用这个书名的话,到那时就不好办了。他说,等我写出更全面的书的时候,我可以找到另一个书名,现在用“开放的作品”很合适。于是,我写完了关于乔伊斯的文章,它就占了书的一半,再加上以前的几篇文章,又写了序言……简言之,书出版了。我发现,另外一本书我不能再写了,因为这个题目只能这样来论述,只能由这些作为建议而写的文章组成。书的题目成了一个口号。我的抽屉里还有有关那本再也没有写出来的书的很多卡片。
另外一个原因是,《开放的作品》出版后,我开始了另外的工作,即进行辩论和自卫,这场斗争持续了好几年。一方面,《韦里》杂志的朋友们、后来的“63年集团”的核心集团非常赞同我的某些理论立场,另一方面是另外一些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人被如此激怒,好像我在侮辱他们的母亲。他们说,不能这样谈论艺术,他们对我侮辱谩骂。那是非常好玩的年代。
《新法兰西评论》月刊上刊出的那些文章也引起了入门出版社的弗朗索瓦?瓦尔的兴趣,他希望这本书在意大利出版之前我先翻译出来。于是,翻译很快开始,但用了3年的时间,修改了3遍,瓦尔几乎是逐字逐句在认真推敲,甚至就每一行给我写3页纸的长信,提出很多问题,或者是我到巴黎去进行讨论,就这样来来往往一直持续到1965年。那是一次从各个方面来说都非常珍贵的经历。
我记得,瓦尔对我说,他感到很有意思,我探讨的问题是从信息和美国语义学(莫里斯、理查兹)出发的,法国的语言学家们、结构主义者们对他们也很感兴趣。他问我,是不是认识列维–施特劳斯。我从来没有读过他的任何东西,甚至对索热尔我也只是因好奇而略读过一些其作品(偶尔看过一些,贝里奥对他很感兴趣,是因为他的音乐节目而对他感兴趣。我相信,他甚至抄下了索热尔的《河流》,这本书还在我的书架上,我一直没有还给他)。就这样,在瓦尔的催促之下,我开始研究那些“结构主义者”(自然我已经认识巴特,他是一位作家,又是一位朋友,但他最后是在1964年作为一位符号学家和结构主义者而出名的,在《交流》第4期发表了他的作品)。对我最大的三大冲击差不多都是在1963年:列维-施特劳斯的《无法交流的思想》、雅各布森在《子夜》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以及俄罗斯的结构主义者的作品(托多洛夫的作品还没有翻译过来,当时只有厄利克的那本经典著作,现在我正在为邦皮亚尼出版社翻译)。因此,在1965年的法文版中(后来是在这一意大利文版本中)加进了很多涉及语言结构问题的注解。但是,《开放的作品》是在另一种环境之下写成的,尽管我后来在修改中加进了“语音和语义”,但这一点仍然可以看出来。我把它看作前符号学的工作:涉及的是我只是到现在才开始慢慢接触的问题,在学习了一般符号学理论之后才接触的问题。在认识了《符号学初步》的巴特之后,我再也不会对《文献的欢乐》的巴特那么满腔热情了,因为他认为他超越了符号学问题,将它引导到了这样一个点,我正是从这一个点作为出发点开始起步的:说明一篇文章是一部使人享乐的机器(正如后来说明这是一种开放的经历一样)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问题在于将这架机器拆卸开来。我在《开放的作品》中做得很不够,我只是说存在这一问题。
有人很可能会问,我现在有了符号学的经验之后是不是能够重写《开放的作品》,最终说明这一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在这一点上我是很厚颜无耻的,是坚决的。我已经这样做了。这就是《伊甸园语言中美学信息的诞生》,后来附在我1971年出版的《内容的形式》一书中。只有短短的16页,但我觉得没有再多说的必要。
来自评论界
《开放的作品》于1962年6月出版。翻阅一下报刊就可以看出,从该书出版消息和出版社的公报可以看出,对这本书的所有的评论都发表在7月和8月,发表评论的有欧杰尼奥?蒙塔莱、欧杰尼奥?巴蒂斯蒂、安杰洛?古列尔米、埃利奥?帕利亚拉尼等。秋季开始后跟上来的有埃米利奥?加罗尼、雷纳托?巴里利、姜弗朗科?科尔西尼、兰贝尔托?皮尼奥蒂、保罗?米兰诺、布鲁诺?泽维等等。60年代初期,各家日报对书籍出版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关注(只有《国家晚报》每周有一份附刊),考虑到这一点,再加上作者当时还只是在一些专业杂志读者的小范围内比较出名,如此快的评论说明,这本书触及了要害。如果我们把最初的评论分为3类(积极的评价、猛烈的抨击和平心静气的探讨性的讨论),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在这3种情况中,《开放的作品》都可以说是一场争论的起点,这场争论波及了60年代意大利的整个文化界。下面辑录的这些材料难以照顾到就《开放的作品》展开的所有的争论和所有的参与者的文章,这场争论中发表的文章至少有上百篇,我们选择的只是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
同意者。反应最快的应该是欧杰尼奥?巴蒂斯蒂,他的《绘画和信息》(载1962年7月17日《世界报》)宣布,“这是最近几年来最激动人心的一本书”。他指出,在文化生活中,由于一种内部的相互抵触,“在一个场合(这里指的是艺术史机构)无法充分探讨的问题,在其他场合引起了争论”。在这里,正是美学以新的光辉照亮了当代艺术现象。巴蒂斯蒂对艾柯的概念补充了一些非常清晰的看法,同意者们的文章的特点正在于此:以这本书作为出发点,将话题扩展开来。这方面的典型是安杰洛?古列尔米的一篇长文(《作为开放作品的今日艺术》,载1962年7月号《当代》),这篇文章一开始就写道:“如果我们自己有幸来写这本书,我们当然希望有此福气,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文章的对象是……一些现象……在其中通过作品结构最清楚地反映出来的是世界结构的或然性这一启示。”文章接着还指出,《开放的作品》的立场还是理性的、传统的,仍然想通过阅读先锋派艺术作品来恢复一种对世界的‘观点’,在这里,当代文化的特点通过先锋派艺术表现出来,这一特点就是没有任何结构‘观点’,没有存在形式,拒绝任何法则或者规则。现在我们不去探讨古列尔米所提出的所有论点,但是,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他是如何看待《开放的作品》的,他把其他人的看法远远抛开,其他人在这本书中看到的是非理性的立场,是抛弃任何评判和任何秩序,是将先锋派艺术(好的)同传统艺术(封闭的、坏的)绝对对立起来。古列尔米反对这种令人愤慨的简单化,同意——虽然是在消极的意义上——这本书中事实上所强调的各种模式之间的联系,多少世纪形成的模式之间的联系,同意这本书的如下观点:将艺术作品理解为对不同的演绎开放的信息,但又要受结构规律的约束,这些规律会以某种方式对阅读进行约束和指导。如下这些人很快就指出,这本书会引起争论:菲利贝托?蒙纳(《电影选择》1962年9月号)、乔治?德玛丽娅(《咖啡馆》1962年10月号:“邦皮亚尼出版社出版艾柯的《开放的作品》之前,对先锋派艺术的谈论部分说来还是模模糊糊的……但到了现在,《开放的作品》出版了……先锋派艺术家将很难再关在他们的‘特殊性’之中说:‘我与此无关’了。”)、埃米利奥?塞尔瓦迪奥(《神经精神病学和心理分析年刊》,1963年第1期)、沃特?毛罗(《晚间时刻》1962年8月号:“这本书从某些方面说将成为时代标志性的作品,会使当代艺术理论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一些学者看出了关键之点,即在方法学上的新东西。埃米利奥?加罗尼(《国家晚报》1962年10月16日的书籍副刊)指出,这本书以不同寻常的方法谈论美学,将关于艺术的论述向关于其他学科的论述开放,使用了一种“语言—交流”的方法。但加罗尼不同意使用信息理论的某些方法,这一点在以后于1964年出版的《艺术的语义学危机》一书中进一步谈到,这使艾柯在后来出版的《开放的作品》的序言中特别作了说明,接受了这一批评。在同一时期,格劳科?康邦在《文汇》周刊(1962年9月16日)谈到这一周刊(1962年7月26日)发表的加埃塔诺?萨尔韦蒂对《开放的作品》的长篇评论时重申,《开放的作品》的方法学的关键应该是形式和开放性、有序和偶然、传统的形式和含糊的形式之间的辩证统一,所有这些因素不是被看作历史性地发生的,而是被看作在当代的每一部作品中存在的辩证的对立。“对结构或‘传统’的强烈要求,无形化或者‘非形象化’的要求正是乔伊斯作品的要害之点,从中可以看出当代艺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所趋向的一种状况的典型状况,艾柯只是指出了一种明显的真实情况。”
结束关于《开放的作品》的第一阶段论争的是雷纳托?巴里利,他在《韦里》杂志(1962年第4期)上发表的文章说,艾柯“受到这样一种方法的影响,这一方法上个世纪以来已经成为欧洲最优秀的文化的方法,可惜战后意大利文化界对此一无所知。这种方法将其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形式、材料的组织方式、结构模式和使材料具有秩序的方式之上”。这同理想主义对形式的注意正好相反,理想主义关注的是不能构成历史的个人的、不可重复的、特殊的问题。而在新的前景之下,“所谓形式是指一般的、多主体之间的共同立场……是一种在一个时期、一种环境内的共同机制,它能够、应该说是必须构成历史……总之,正如他自己所指出的,这是在确立‘文化模式的历史’”。
巴里利的评论指出了方法上的一些方面,这些方面后来成了艾柯研究的问题:对社会机制现象的关注、非理想主义的欧洲文化手段的使用、结构问题、对艺术的关注,这里所说的艺术不是指创造的奇迹,而是指材料如何组织。仔细观察可以看出,这些方面正是引起反对和拒绝的那些问题。《开放的作品》反对的正是克罗齐的传统,这种传统仍然在滋育着人们不注意的意大利理想主义的评论界和哲学界的立场。
拒绝者。历数对《开放的作品》的拒绝情况很有意思。要想找到近几年来另一本受到如此激烈抨击的书,那就只能是桑圭内蒂的《意大利的诡谲》一书了。阿尔多?罗西在《国家晚报》上撰文说:“我想起了一位权威的诗人说的一段话,其大意是:你们告诉那个打开作品又合起书本(那几乎就是在出牌,在打牌,或者在以左派的方式治理国家)的年轻作者,最终他将走上讲台,他的学生们在学着读了十几本杂志之后将在短时间之内变得如此能干,以致将取代他,占据他的位置。” 1962年6月23日的《问题》周刊(《开放的作品》刚出版几周)上刊登了一篇没有署名的文章,谈到了“小人物们的哲学家恩佐?帕奇”,指出:“选择《开放的作品》这一书名就是一种赎罪的行动,就是作者的一种抢先发言的企图。他的头脑中会闪出这样的怀疑(但愿事实会否定这一点):打开这本书感到很晦涩的人事实上是不是会很少。”在《问题》周刊(1962年12月15日)上刊登了乔瓦尼?乌尔巴尼的争论文章,文章的题目是“原因的原因”,文章说,由于艺术作品的“存在”被使之成为科学的试图所取代,将作品解释为总是想要说出别人的某些东西,这样一来似乎是,“统一的断语意味着……不可否认:作为研究对象的作品是非艺术的”。乌尔巴尼正是对这一前景感到担心,所以带着挖苦口气承认说,这样就会有很多好处,其中第一个好处就是,无需再进行评论,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发表与他人不同的意见。“坏处现在则只有一个,但这一个也无关紧要。这是这样一本书……它使意大利那些最懒惰的评论家们感到高兴,它以这样的说法来安慰他们:如果对一部艺术作品的所有评判结论都是错误的,其间的原因在于艺术作品本身,而不在于那些不善思考的伟大头脑运转不灵。总之,作品本身是(讲了些愚蠢东西的)原因,寻找存在愚蠢的其他原因毫无用处。”
福尔图纳托?帕斯夸利诺在《罗马观察家报》(1962年6月13日,题目是“文学与科学主义”)上写道:“作家们一旦脱离了与现实的正确关系,就会躲藏到科学和哲学文化的树林里,埋头致力于荒唐的选择,埋头完成美学以外的任务。他们所想的再也不是在诗意或者艺术方面成功的作品,而是满足‘现代世界’、科学、技术的要求的作品,或者说是开放的作品。”他说,这本书是一本指责拉斐尔的作品是“闭合的”作品的书(“至少根据著名艺术评论家阿尔甘在介绍艾柯的这本书时所作的评价,拉斐尔的作品属于这样的作品。”),但这位作者承认,艾柯是在为这样一种艺术作品创建理论,“这种艺术作品永远像现实一样开放,但是,这种直觉来自认知适应事物这样一种认识论的原则,而不是其他如托马斯之类的来源,他(我们的这位作者)顺手拿来托马斯的思想精华,尽管他否定这一思想的理论和方法学的价值,而在以前他是承认这种价值的”。
最愤怒的指责是一位叫埃利奥?梅尔库里的在《电影评论》(1963年3月号)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这份杂志的一位重要撰稿人是阿尔曼多?普莱贝。梅尔库里在这篇题为“作为荒唐作品的开放作品”的文章中一开始就引用了荷尔德林希望回到“非形象”的诗,献给“厌倦了形而上学乐趣、没有在《开放的作品》中给我们提供的世界中迷失的艾柯”。对这位“米兰新资本主义的美好灵魂”还献上了歌德的这句话:“他着迷似的眯着眼看着远方,想像着云彩之上和他相同的某种东西。”他说:“这一简单真理尽管构成人的力量源泉,但从来没有迷惑过人,不像现在这样迷惑人。”梅尔库里引用马尔科姆?劳里、卡夫卡、帕斯卡尔、克尔恺郭尔等人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指责这本书被动地接受混乱和无序,指出:“艾柯这本平庸的书……向我们建议,人的唯一的道义,注意是‘唯一的’,是接受这种局面,接受这种基本的非理性。”
那篇指出西方理性立场同东方立场有所不同的关于禅的文章,也被看作是呼吁运用新理论,引用胡塞尔或者科学理论被认为是“没有头脑”,开放的概念被说成是“美学神秘主义的沉重遗产”,艾柯被指责为“给一些没落浪漫主义的理论戴上客观美学规律价值的大帽子,如果这些理论的创立者们在同自己的矛盾中创建了这样的理论之后都无法在其指导下创作出作品来,这些理论早已没有什么价值了”。另外还写道:“我们知道,《为芬尼根守灵》是艺术上的失败之作,那么我们只要这样说就够了:乔伊斯在这部作品中所表达的理想再也不是我们的理想。”最后,在《开放的作品》出版后又在《梅那波》杂志第5期上发表了文章(在这一版中将此文加入书中),反对之声就更加强烈了。维托里奥?萨尔蒂尼(任该刊副总编)在1962年11月11日的《快报》周刊上发表文章谈到先锋派的“运动”美学,还提到了马查多,“即使是最反常的口味也总是会有一些小律师愿意去为他们的古怪言行辩护”。萨尔蒂尼谈到“无赖青年的进步”时写道:“在《开放的作品》中,艾柯为先锋派的最后成果辩护,但又找不到真正能在形式上完全为其辩护的论点。”在艾柯看来,“艺术不是认知的方式,是‘世界的补充’,是‘自主的形式’,也就是说,是一种不同的消遣。艾柯评论了桑德拉尔的这些诗句:我遇到的所有女人屹立在地平线上,她们在雨中信号灯前带着悲愤和忧郁的目光,指出‘诗人使用红绿灯是合理的,就像古希腊诗人阿喀琉斯在诗中使用盾一样’,像这样的做法还有另外的实例,荷马甚至描写到了生产过程。艾柯承认不想到红绿灯就无法产生爱意。对此我无法理解。”最后,拒绝的高潮是卡洛?莱维,《再生》杂志(1963年2月23日)附加的一本小册子是他写的文章,题目是“圣巴比拉,巴比伦”。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开放的作品》的精神同米兰新资本主义的精神是一回事:“我多么爱你,米兰的青年人(我多么爱你!多少人,都是一样)。我多么爱你们,你们那么亲切,一清早就从家里出来,空中还弥漫着雾气,那是从鼻孔出来的雾气(背后是屋脊),从嘴里出来的是烟气,雾气将人包起……我多么爱你,艾柯(Eco),我的米兰的反响(eco),还有那些问题,你想同大家完全一样,普通的,普通人中的高傲者,B该是多么好,它比A低,因为C和D太混乱,那是欠发达地带,但像罗科那样可不行……发动机隆隆响,办公室就在附近,艾柯说了些什么?一切都安装到已经谈了很多的语言中……(安装进、关进马厩和由词语和名词构成的肥沃的、发酵的、令人高兴的大粪坑),我们同局势异化……但反响需要很多,需要镜子(回顾的镜子,诱惑人的镜子),放到分化的、缺乏联系而瓦解的局势面前,以便给我们一个‘有机的’形象,带有它的所有‘结构联系’的形象。为了这一跳跃(都是在那面镜子立起来之前进行的),为了同这面镜子一起跳跃,为了超越这面镜子而跳跃,需要恩典,需要上帝的恩典!……我多么爱这个米兰的年轻人,爱你的雾气,你的摩天大楼,你的守时的习惯,你的问题,你的异化,你的镜子,你的反响,你的迷宫。这么晚了你还在你的卡片上打孔,我已经躺到我的暖暖和和的床上……你也在敲门,老迈的米兰年轻人,带着你的卷宗,你把我叫醒,告诉我说,心怀着爱和痛苦写不出诗来,怀着恐怖、骄傲、病痛、愤怒、教授、发明者、引导者、译述者、引诱者、吓人者、作恶者、保守者、耕作者、教练、异化者、孢子、小时、小时和小时才能写出诗来。”
国外的反应
《开放的作品》被译为法文、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罗马尼亚文、波兰文,部分译为英文。由于各国文化界的情况各不相同,在各个国家引起的反响和兴趣也各不相同。在一些政治局势不稳定的国家,比如1968年的巴西,对开放的要求是在非常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待的,被看作明确的革命寓意(见乔瓦尼?库托洛和奥布拉?阿维尔塔写的序言:《前景》,1969年):“我们觉得,这样的努力是可能的、合适的:比如说,用艾柯提供的解释手段来理解和前瞻性地评价那些震动全世界的大学和工厂的事件以及至少是现在在法国的那些非常猛烈非常复杂的游行示威活动。我们面对的难道不是《开放的作品》在社会和政治组织中引起的最初的争论吗?”
要说典型,自然应该考虑法国的情况。这本书于1965年底在法国出版,引起了广泛的兴趣。
最先发表值得关注的意见的是米歇尔?泽拉法,他在《新观察家》周刊(1965年12月1日)发表的文章说,艾柯“比那些可以称之为行动者和组合学者的美学家们更深刻,更有说服力……因为艾柯先生从总体出发历史地看待‘开放的作品’这一问题,即把它看作我们西方文明的一个自有的现象”。
在1966年3月5日的《世界报》上,雷蒙?让指出,这一作品非常重要,因为它理解我们时代的艺术。让保罗?比埃尔在1966年4月23日的《左翼报》谈到:“这本书非常难读,但非常重要,据我们所知,这是全面分析当代艺术的设计和方法的最早努力之一。”它“正确地、明白无误地”表明了“我们时代的艺术的深刻进步作用”。唯一不一致的声音来自罗歇?朱德林,他在《新法兰西评论》月刊(1966年6月1日)发表一篇文章中说:“不啰嗦一大堆废话就能点亮电灯该是多么玄妙莫测啊!伟大的艺术既不是封闭的,也不是开放的。它们现出微笑,这种特有的微笑并不是尽善尽美的东西,因为它既有一半是笑,另有一半是漠然的无所谓。”而在比利时则完全是一面倒的极高的评价。弗朗索瓦?冯?拉埃尔在《现代语言评论》双月刊(1967年1月)写道:“在评论思想的巨大十字路口,出现了一位对自己的时代和自己时代的人进行评论的最现代的伟大分析家,他在分析自己的时代时通过自己的直觉发现了未来评论的预兆。莱辛起过这样的作用。艾柯是不是还要为我们起到这一作用?”
这本书其他文字译本的出版使有关评价的归纳更可以扩大,这些评价显然并非完全都是同意的意见。但现在可以说的是,这本书成了人们不得不引用的作品之一,在这本书的作者发表有关符号学的作品之后,这本书是很值得再加研究的作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