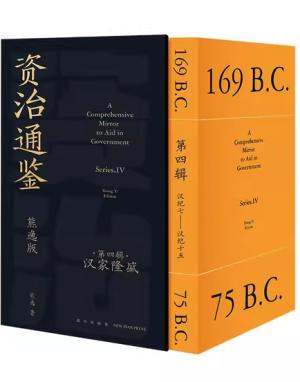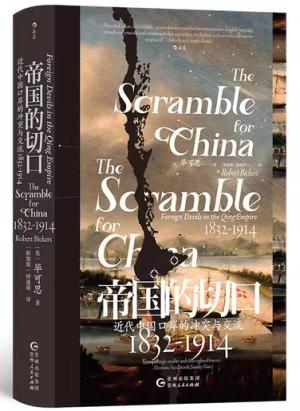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希腊文明3000年(古希腊的科学精神,成就了现代科学之源)
》
售價:HK$
82.8

《
粤行丛录(岭南史料笔记丛刊)
》
售價:HK$
80.2

《
岁月待人归:徐悲鸿自述人生艺术
》
售價:HK$
59.8

《
女人的中国医疗史:汉唐之间的健康照顾与性别
》
售價:HK$
10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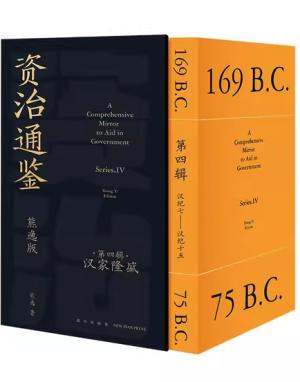
《
资治通鉴熊逸版:第四辑
》
售價:HK$
458.9

《
中国近现代名家精品——项维仁:工笔侍女作品精选
》
售價:HK$
66.1

《
宋瑞驻村日记(2012-2022)
》
售價:HK$
1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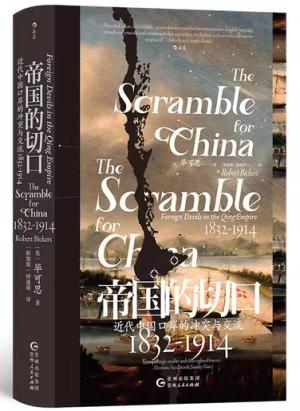
《
汗青堂丛书138·帝国的切口:近代中国口岸的冲突与交流(1832-1914)
》
售價:HK$
124.2
|
| 編輯推薦: |
二十世纪主流文学大师
中产阶级的精神路标 《纽约客》短篇圣手
与卡佛共同引领文学的极简时代
创作巅峰期的短篇精华独家呈现
? 安?比蒂《纽约客》作品第一次全集出版
? 关注“迷惘的一代”心灵之路,注视他们的回归与新的困境
? 最圆熟细腻的文笔描摹婚姻、男女的苦痛与进退维谷
|
| 內容簡介: |
《洛杉矶最后的古怪一日》是安?比蒂《纽约客故事集》的第三部,是她跨越新世纪,把中产阶级推入全新领域的短篇作品集。
她的年轻人步入了中年,她的人生体验愈加深沉,无论是饱受创伤,对生活无计可施的单身母亲,还是受男人掌控,精神肉体伤痕累累的女人,抑或是无爱婚姻中木讷前行,心灵无所依托的男人,再也没有无需知道去向的旅行,再也没有不由分说的任性,再也没有随时重来的爱情。当迷惘的一代人最终确定了站姿,全意接受婚姻、事业与家庭的规约,比蒂仍然站在他们身旁,讲述他们的困境,言说他们的苦痛。
|
| 關於作者: |
|
安?比蒂(Ann Beattie),美国著名短篇小说家,与雷蒙德?卡佛齐名的“极简主义”大师。《纽约客》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作品四次被收入欧?亨利短篇小说奖作品选集,并入选约翰?厄普代克编辑的《二十世纪最佳美国短篇小说选》。比蒂善于描画美国一代城市人的情绪状态与生活方式,帮助中产阶级认识了自我,对于他们的成长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乃至被视为其精神路标。
|
| 目錄:
|
玛丽的家
霍雷肖的把戏
第二个问题
赞拉
世上的女人
洛杉矶最后的古怪一日
查找和替换
兔子洞是更可信的解释
压顶石
诱鸟
|
| 內容試閱:
|
玛丽的家
我的妻子,玛丽,打算办一个晚会—一个有人承办饭菜的晚会,她要邀请新老朋友和左手边的邻居们—我们跟他们有来往。承办人快到的时候,莫莉?范德格里夫特打来电话,说她女儿烧到华氏一百零二度,她和她丈夫来不了了。我看得出来我妻子安慰莫莉的时候有些失望。然后,电话打完没几秒,莫莉丈夫的汽车就开出了车道。每次听到车子疾速开出,我的第一个念头总是有人离家出走。我妻子的猜测要实际些:他是去买药。
我妻子自己就在我们和好后这三年中出走了两次。第一次,她盛怒之下一走了之;第二次,她去怀俄明看朋友,把一周的访期延长到了六周,尽管她没有真的说不回来,可我就是没法说服她订机票,也没法让她说她想我,更不用说爱我了。我是做过一些错事。我给自己买昂贵的新车,把旧车淘汰给了她;我赌博输过钱;我有一百次回家太晚,误了吃饭。但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妻子。是她在我们打算离婚的时候搬出去的。我们和好以后,又是她飞车离去,以此结束我们的争吵。
这些事在人心中载沉载浮,一点小节就会让我想起她每一次出走,或是威胁出走的情形,或是她想要一件我们买不起的东西时,会用一双我形容为“震惊的兔子”式的眼睛瞪着我。不过大多数时候,我们还是努力振作。她一直在找工作,而我下班直接回家,我们一起解决电视遥控器的矛盾:我让她用一小时,她让我用一小时。我们一晚上看电视的时间尽量不超过两小时。
今晚不会看电视了,因为有鸡尾酒会。这时候,承办人的车已经并排停在了我们的房前,承办人—一个女人—正把东西搬进屋里,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在给她帮忙,估计是她儿子。她有多愉快,他就有多消沉。我妻子跟她拥抱了一下,两人都笑了。她跑进跑出,把盘子端进来。
我妻子说:“不知道我该不该出去帮忙。”随即自问自答道:“不—她是我雇来做事的。”然后她暗自微笑起来。“很遗憾范德格里夫特一家来不了了,”她说,“我们给他们留点吃的。”
我问要不要用音响放点音乐,可是我妻子说不要,说话声会盖过音乐,要不就得把声音放到很大,会吵到邻居。
我站在外屋,看着承办人和那个男孩。他进门时伸直胳膊拿着一个餐盘,小心翼翼的,像一个孩子手持着让他有点害怕的小烟花。我看着的时候,玫太太,那个我们不来往的邻居(有天晚上我们睡觉以后,忘了关前廊灯,她叫来了警察)和她的两只玩具贵宾犬安娜克莱尔和埃丝特从我们屋前走过。她假装没有注意到一个承办人正把晚会食物端进我们家。她能一眼把你望到底,让你觉得自己像个幽灵,连她的狗也炼就了这种眼神。
我妻子问我最想见到谁。她知道我最喜欢斯蒂夫?纽荷尔,因为他是这么滑稽,不过为了让她大吃一惊,我说:“哦—能见到赖安一家挺好,可以听听他们的希腊之旅。”
她对此嗤之以鼻。“等到你开始关心旅行的那天再说吧。”她说。
她和我一样,对争吵同样负有责任。她的话里带着刺。我尽量使用礼貌的语调和措辞,而她却毫不客气,轻蔑地哼哼鼻子,再来几句尖刻的话。这一次,我决定置之不理—就是不理睬她。
起初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妻子要和那个承办人亲亲抱抱的,但是后来她们聊天的时候我记起了我妻子是几个月前在亚历山德里亚的一个送礼会上遇到她的。她们俩朝一个女人直摇头—我没见过那个女人,所以她一定是我妻子以前工作时交的朋友,她们俩还说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医生会让生产持续六十多个小时。当锡纸从魔鬼蛋 上揭掉的时候,我听明白了,那个女人现在没事了,她离开手术台前结扎了输卵管。
男孩没说再见就回到了车里。我站在走道上,望着门外。他上了车,用力关上车门。他身后,太阳落山了。又是那种过去曾会让我着迷的橘粉色落日。但我马上从门口走开,因为我知道承办人要出来了。事实上,如果我不必跟她寒暄客套,反而更好。我不大擅长跟不认识的人找话讲。
承办人把头探进我所在的房间。她说:“祝晚会愉快。我想你会很喜欢那个火辣辣的豆泥蘸酱。”她微笑着,还出乎我意料地耸耸肩。似乎没有理由耸肩。
我妻子托着一盘肉片从厨房出来。我主动要求帮她拿,她却说自己很挑剔,情愿自己来,这样她就知道她都把东西放哪儿了。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就不能看看桌子,看自己把东西放哪儿了,但是我不宜在她干活儿的时候提问,她会发脾气,情绪急转直下。所以我出去了,在门廊上看天色渐暗。
承办人开车离开的时候按了按车喇叭,出于某种原因—也许是因为他坐得笔直—那个男孩让我想起在去华盛顿的高速公路上,有一段路面是为车里至少有三名乘客的车辆保留的,于是附近的人们都去买充气玩偶,给它们戴帽穿衣,放在座位上。
“玛丽?维罗齐和她丈夫试验分居,不过今天的晚会她还是会跟他同来。”我妻子在过道上说。
“你何必跟我说这个?”我说着转过身,背朝夕阳,走回屋里,“这只会让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感到不自在。”
“哦,你能挺过来的。”她说。她总是用这个词。她递给我一摞纸盘,叫我分成三摞,放在桌子外侧。她叫我把纸巾从厨房柜里拿出来,沿着桌子中央放几叠,放在插雏菊的花瓶之间。
“维罗齐的事情不要让别人知道。”她说着端出一盘蔬菜。蔬菜从碗中央到边缘展开,菜的颜色—橘色、红色和白色—让我想起天空和它几分钟以前的样子。
“还有,”她说,“请你不要一看到奥伦的酒杯空了,就忙着给他添上,他在努力戒酒。”
“那你来好了,”我说,“既然你什么都知道,所有的事都你来。”
“我们每回招待客人你总会紧张。”她说着从我身旁擦了过去。回来的时候她说:“那个承办人活儿干得真漂亮。我要做的只是把大菜盘洗干净放到门廊上,明天她来拿。岂不是很妙?”她吻了我的肩头。“要打扮一下了,”她说,“你准备穿你现在身上的这身儿吗?”
我穿着白色的牛仔裤和蓝色的针织衫。我点头说是的。让我惊讶的是她没有异议。上楼梯的时候,她说:“我无法想象这种天还要开空调,不过你看着办吧。”
我走回门廊,站立片刻。天色更暗了。我能看到一两只萤火虫。邻家的一个小男孩骑着单车经过,满眼闪亮的蓝色,后面有辅助轮,把手上系着飘带。那只杀鸟的猫走过。大家都知道我曾把水枪灌满水,趁没人时对着这只猫射水。我还用水龙带喷过它。它在我们草地的边缘走着。我对它的心思了如指掌。
我进了屋,看了一眼餐桌。楼上,淋浴喷头的水在流。不知道玛丽会不会穿她的吊带裙。她的后背很美,穿那种裙子很好看。虽然她那么说,但我的确是旅行的—而且喜欢旅行。五年前我们去了百慕大,我在那儿给她买了条吊带裙。她的尺码从没变过。
餐桌上,有足够喂饱一支军队的食物。半个掏空的西瓜,里面放着西瓜球和草莓。我吃了一颗草莓。还有看起来像是奶酪球的东西,上面裹着坚果粒;几碗蘸酱,有几碗旁边摆着蔬菜,另外几碗旁边放了一碗饼干。我用牙签戳了一片裹有意大利熏火腿的菠萝。我把牙签丢进口袋,把菠萝片拢得更紧凑些,这样就看不出我吃了一片。承办人还没到的时候,我妻子就把酒拿出来放在宽边窗台上了。还有配火柴的蜡烛,随时可以点亮。她对音乐的想法可能是错的—至少第一批人出现的时候,有点音乐挺好—不过何必争论呢?我同意,既然微风习习,我们就不需要开空调了。
没多久,玛丽从楼上下来了。她没穿吊带裙,而是穿了一条我一直都不喜欢的蓝色亚麻裙,手里提着一个行李箱。她没有笑。她的脸突然显得很憔悴。她的头发是湿的,用卡子别到后面。我眨眨眼,无法相信眼前这一幕。
“根本就没有什么晚会,”她说,“我是想让你看看,准备好了饭菜—即使不是你准备的—然后只能等着,那是什么感觉。等呀,等呀。也许这样你就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几乎是我在想“你在开玩笑”的同时,我也立刻有了答案。她不是在开玩笑,但是婚姻问题咨询师—没有哪个咨询师会认同她现在的所作所为。
“你不会这么幼稚吧。”我说。
但是她出了门,沿着走道向外走。飞蛾飞进了屋里。有一只飞过我的嘴边,触到了我的皮肤。“你打算怎么跟福特医生解释?”我问。
她转过身。“你何不请福特医生过来喝杯鸡尾酒?”她说,“还是你觉得真实生活的场景会让他受不了?”
“你要走吗?”我问。但是我已灰心丧气。我筋疲力尽,几乎喘不过气来。我声音很轻,我不确定她是否听见。“你不理我吗?”我叫道。她不回答,我知道她是。她上了车,发动,扬长而去。
有那么一刻,我震惊至极,跌坐在一把门廊椅上,呆呆地望着。街上安静得不同寻常。知了开始高唱。我坐在那里设法平静下来,骑自行车的男孩慢慢地蹬着车往山上爬。邻居的贵宾犬开始吠叫,我听见她用嘘声要它们安静。后来狗吠声就轻了下来。
玛丽在想什么?我不记得上次晚饭迟归是什么时候了。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很多年。
卡特里娜?杜瓦尔经过。“米奇?”她说着抬起手遮在眉毛上方,望着门廊。
“嗯?”我说。
“你这几个星期天拿到报纸了吗?”
“拿到了!”我大声回答。
“我们去海洋城的时候让他们停送了,现在没法再重新开始送,”她说,“我想我本应该请你帮着收报纸的,不过你知道杰克的情况。”杰克是她儿子,稍有点弱智。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取悦杰克,或者她也就这么一说。言下之意,他是一个小暴君。我对他了解很少,只知道他口齿不清,还有就是一次下暴雪,他帮我铲掉车道上的积雪。
“那没事了。”她说着便走开了。
我听到远处的摇滚乐。范德格里夫特家传出很响的笑声。他们家孩子不是病了嘛,是谁这么开心?我眯起眼使劲往房子里看,可是窗户被照得太亮了,看不到里面。又一声尖叫,紧接着又是笑声。我站起来,走到草坪另一头。我敲敲门。莫莉气喘吁吁地来应门。
“你好,”我说,“我知道这个问题有点傻,不过我还是想问问,我妻子今晚有没有邀请你们来喝酒?”
“没有。”她说。她把额前的刘海拂到一边。她女儿踩着滑板从她身后疾驰而过。“小心点!”莫莉喊道。她对我说:“他们明天来给地板重新抛光。她高兴死了,能在屋里玩滑板了。”
“你今晚没给玛丽打过电话?”我问。
“我都一周没见到她人了。没事吧?”她问。
“那她一定是请了别人。”我说。
小女孩又踩着滑板嗖嗖滑过,把滑板一头翘了起来。
“上帝啊,”莫莉用手掩住了嘴说,“迈克尔去杜勒斯接他兄弟了。不会是玛丽问了迈克尔,而他忘了告诉我吧?”
“不,不。”我说,“我敢肯定是我搞错了。”
莫莉一如往常地粲然一笑,不过我看得出来我让她很不安。
回到家里,我把灯调暗了一挡,站在前窗旁,望着天空。今晚没有星星。也许乡间会有,但这儿没有。我看到蜡烛,心想,管他呢。我划亮火柴点起蜡烛。烛台是银质的,装饰华丽,质地厚重,是我姨妈的传家宝,她住在巴尔的摩。蜡烛燃着,我看着窗户,看到了烛焰和我自己的映象。微风吹来,蜡烛结了烛泪,滴落下来,于是我又多看了几秒,便吹灭了。蜡烛冒着烟,但我没有舔手指便掐了烛芯。我又看了一眼空旷的街道,然后坐在椅子上,看着餐桌。
我要让她看看,我心想,她回来的时候我也走了。
然后,我想着要喝上几杯,吃点东西。
但是时间过去了,我没有走,也没有喝酒,碰都没碰桌子上的东西。这时我听到一辆车停了下来。闪烁的车灯引起了我的注意。一辆救护车,我心想—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是她不知怎么的弄伤了自己,救护车不知道什么原因过来了,然后……
我跳了起来。
承办人站在门口,皱着眉头,肩膀微耸。她穿着抹胸上衣配牛仔裙和跑鞋。我身后的屋里一片寂静。我看到她朝我背后外屋灯的方向张望,分明很困惑。
“这只是个玩笑,”我说,“我妻子开的玩笑。”
她皱起眉头。
“没有什么晚会,”我说,“我妻子出走了。”
“你在开玩笑。”承办人说。
我看着她背后的车,车灯在闪。那个男孩不在前座上。“你到这儿来干吗?”我问。
“哦,”她说着垂下眼帘,“事实上我—我想你们可能需要帮忙,我可以来干一会儿。”
我皱起眉头。
“我知道这听起来有点怪,”她说,“不过我刚入这行,想给人留个好印象。”她还是没有看我。“我以前在社区学院总务主任的办公室做事,”她说,“我讨厌那工作。所以我想,要是我做酒席的承办人,有足够多的活儿……”
“好,进来吧。”我说着站到一边。
已经有一阵子了,小虫不停地往屋里飞。
“哦,不了,”她说,“你们有麻烦,我很难过。我只是想……”
“进来喝一杯,”我说,“真的。进来喝一杯吧。”
她看着她的车说:“稍等。”她沿着走道走回车里,关了车灯,锁上车,又沿着走道走了回来。
“我丈夫说我不该插手,”她说,“他说我太用力讨好别人了,如果你让人看出来太急吼吼,就得不到想要的东西。”
“别理他的理论,”我说,“请进来喝一杯吧。”
“我觉得你妻子有点烦躁,”承办人说,“我以为她是因为搞一个这么大型的聚会而紧张,有人帮忙她会心存感激。”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走了进来。
“好。”我说着摊开双手。
她不安地笑了起来。我也笑了。
“红酒?”我说着指指窗台。
“挺好。谢谢你。”她说。
她坐下来,我给她倒了一杯红酒,递给她。
“哦,我其实可以自己来。我是在—”
“坐着别动,”我说,“我作为主人总得招待一下,不是吗?”
我给自己倒了一杯波本威士忌,从冰桶里拿出几块冰,放在杯子里。
“你想讲讲这事儿吗?”承办人问。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说。我用一根手指在杯子里搅着冰块。
“我是从科罗拉多来的,”她说,“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怪,过于保守还是怎么的。”她清了清嗓子。“也许不是,”她说,“我的意思是,很明显,你永远都不会知道—”
“知道别人家里到底有什么事。”我替她把话说完。“现成的例子。”我说着举起酒杯。
“她会回来吗?”承办人问。
“我不知道。”我说。“我们以前当然也吵过架。”我喝了一口波本,“当然,这次不算是吵架,有点像她单方面的胡闹,我猜你会这么说。”
“有点滑稽,”她说,“她告诉你那些人都被邀请了,然后—”
我点点头,打断了她。
“我是说,外人会觉得滑稽。”她说。
我又啜了一口酒。我看着承办人。她是一个瘦削的年轻女人,本人看上去不会对食物有什么特别的兴趣。她其实挺漂亮的,那种清淡的美。
我们沉默着坐了一会儿。我能听到邻居家的尖叫声,我肯定她也听到了。从我坐的位置,我可以看到窗外;萤火虫发出点点短促的微光,从她坐的位置,她只能看到我。她看看我,又看看她的酒杯,再看看我。
“我不是说这对你有多重要,”她说,“但是能看到事情未必是它们表面那个样子,这一点对我有好处。我的意思是,也许这个地方还过得去。我是说,也不见得比其他小城更复杂。也许我有偏见。”她喝了一口酒。“我不是很想离开科罗拉多,”她说,“我在那儿做滑雪教练。跟我一起生活的那个人—他不是我丈夫—我和他本想在这儿开一家餐馆,但没成功。他在这一带有很多朋友,还有他儿子,所以我们来了。他儿子跟他妈妈一起过—我朋友的前妻。我几乎谁也不认识。”
我拿过酒瓶,给她又倒了一杯酒。我喝干最后一滴,晃动冰块,给自己添上酒,把酒瓶放在地板上。
“很抱歉我冒冒失失地搅和了进来。我待在这儿一定让你不自在了。”她说。
“没有,”我说,有一半是真心的,“我见到有人来很高兴。”
她转过身,回头看看。“你觉得你妻子会回来吗?”她问。
“不好说。”我说。
她点点头。“这种情形很奇怪,你知道某个人的一些事,他们却对你一无所知,不是吗?”
“你是什么意思?你刚才跟我讲了科罗拉多,还有你们打算开餐馆。”
“是啊,”她说,“不过那些不是私事。你知道我的意思。”
“那就把私事说来我听听。”
她的脸红了。“噢,我不是那个意思。”
“有什么不行的?”我说,“这个夜晚已经够奇怪的了,不是吗?你跟我说点私事又如何?”
她咬起了手指甲根上的硬皮。她可能比我想象的年轻。她留着一头闪亮的长发。我试着想象她穿着尼龙外衣,站在滑雪场的斜坡上。这让夜晚突然显得更热了。我因此意识到只要再过几个月,我们就都会穿上羽绒服。去年十一月下了场大雪。
“跟我一起生活的那个人是个插画家,”她说,“你可能看到过他的一些东西。他不缺钱,他只是什么都想要。画画,开餐馆。他很贪心,不过他总能想办法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她喝了一口酒。“说这些怪怪的,”她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跟你说我们的事。”然后她不说了,抱歉地笑笑。
我没有安抚她,而是站了起来,在两个盘子里放了些吃的,把其中一个放在我椅子旁边的小桌上,另一个递给她。我又给她倒了一杯酒。
“他在陶瓷厂旁边有一个工作室,”她说,“那栋装有黑色百叶窗的大楼。下午他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带一个野餐篮过去,我们吃午餐,做爱。”
我用拇指和食指把一块饼干掰成两半,吃了。
“不过这不是关键,”她说,“关键问题是,午餐总像一种Wonder面包之类的东西。真的很怪。我切掉面包的硬皮,涂很多蛋黄酱做红肠三明治。或者用Ritz饼干做cheez-whiz芝士酱三明治,或者是花生酱和棉花糖三明治。我们喝Kool-Aid饮料、根汁汽水什么的。有一次我做了热狗,然后切成片,夹在饼干里,再在边上抹上一圈奶酪,就着Dr. Pepper汽水吃。总之,午饭一定得是很难吃的东西。”
“我明白了,”我说,“我猜我明白了。”
“噢,”她说着又垂下了眼帘,“我是说,我猜这很明显,你当然能明白。”
我等着,看她是不是打算让我也吐露一些事情。可她却站了起来,把最后一点酒倒在杯中,背对我站着,看向窗外。
我知道那个陶瓷厂,在小镇比较乱的那一带。那条街上还有一个酒吧。有天晚上,我从酒吧里出来,一个年轻人袭击了我。我记得他骑车冲过来时动作有多快,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尖利的声音,就好像他驾的不是自行车而是辆大汽车。然后他扑到我身上,半打半压,好像我的钱包会从藏着的地方弹出来,就像小丑的头从整蛊魔术盒里弹出来那样。“在我的后袋里。”我说。他随即把手塞进我的口袋,然后在我腰间重击一记。“躺着别动!”他几乎是在耳语,我侧卧着躺在地上,把手盖在脸上,这样,他之后回想起来就不会因为我看清了他的脸而回来找更多麻烦了。我的鼻子在流血。我的钱包里只有大约二十块钱,我把信用卡放家里了。后来,我终于站了起来,试着走动。陶瓷厂里有一盏灯亮着,但是里面没什么动静,我推测里面没人—只是留了一盏灯而已。我把手按在大楼墙上,想站直一点儿。有那么一下,一阵剧痛穿透了我的身体—如此剧烈,我又倒下了。我呼吸了几次,疼痛过去了。透过大玻璃窗,我看到陶瓷做的牧羊人和动物—会放在基督诞生的场景布置里。它们没上釉彩—还没有烧制好—因为全是白色的,大小几乎一样,猴子和东方三博士 看起来非常像。离圣诞节还有一个星期左右,我心想,它们为什么还没完工?时间太紧张了,要是他们再不抓紧上色,就太迟了。“玛丽,玛丽。”我低声说,知道我有麻烦了。然后我努力走动,上了车,回家去见我的妻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