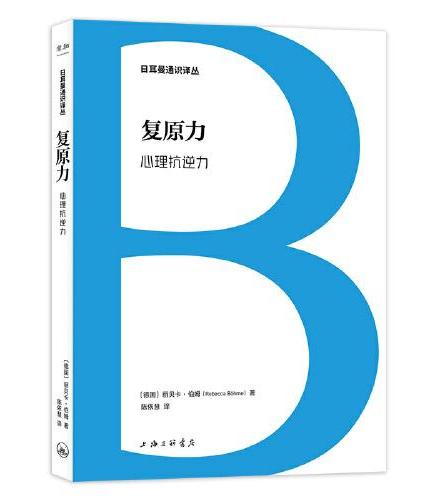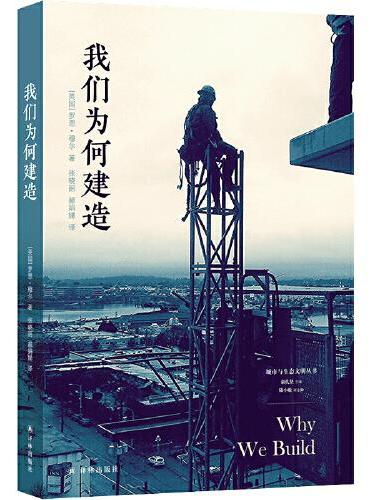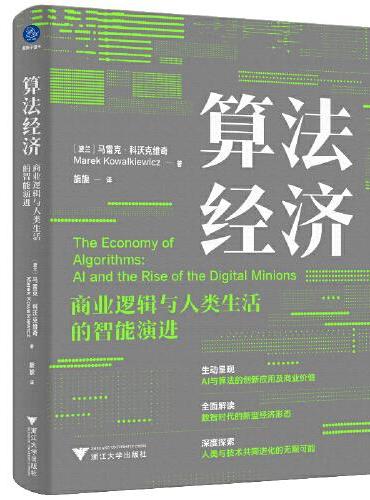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没有一种人生是完美的:百岁老人季羡林的人生智慧(读完季羡林,我再也不内耗了)
》
售價:HK$
5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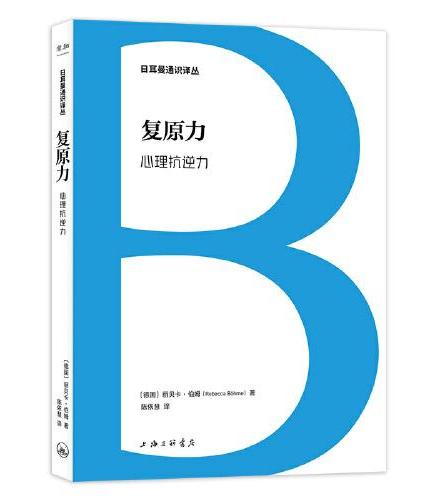
《
日耳曼通识译丛:复原力:心理抗逆力
》
售價:HK$
34.3

《
海外中国研究·未竟之业:近代中国的言行表率
》
售價:HK$
13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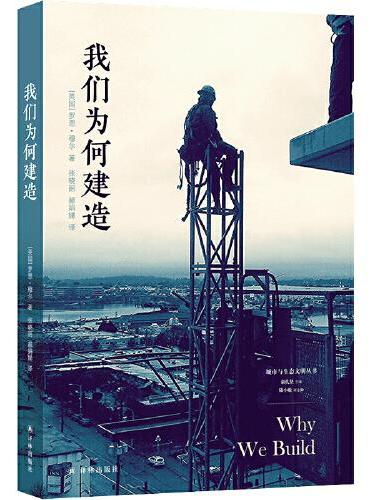
《
我们为何建造(城市与生态文明丛书)
》
售價:HK$
8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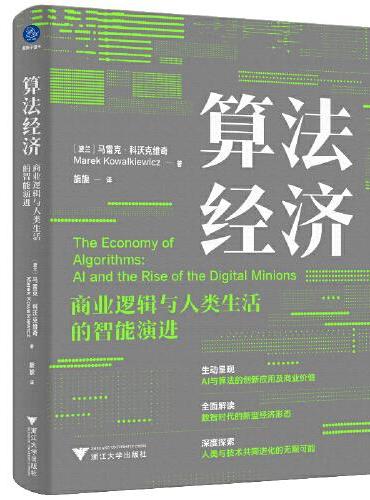
《
算法经济 : 商业逻辑与人类生活的智能演进(生动呈现AI与算法的创新应用与商业价值)
》
售價:HK$
79.4

《
家书中的百年史
》
售價:HK$
79.4

《
偏爱月亮
》
售價:HK$
45.8

《
生物安全与环境
》
售價:HK$
56.4
|
| 編輯推薦: |
★人性之美 思想之美 苦难之美 劳动之美
★张贤亮:新时期文学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生命力最顽强的作家。
★这是一部撕去艺术面纱的书,揭示人性非常态下拥有的丰饶。
★张贤亮说:“我的作品是要告诉人们:那种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再不要重复了,那些摧残心灵的悲剧不要再重演了!”
|
| 內容簡介: |
|
这是一个未被苦难击倒,热爱生命的故事。张贤亮检视当年的日记,以注释的方式,平静地,甚至是幽默地叙述最萧索荒凉的人生经验,丰沛的文字中迸发出对生命的最大热爱,自然而然地为过去四十年中国人的苦难下脚注。他以日记体的形式,将小说艺术推上另一高峰。
|
| 關於作者: |
张贤亮1936年12月生于南京,祖籍江苏盱眙。20世纪50年代初读中学时开始文学创作。1955年自北京移民宁夏,先当农民后任教员。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发表诗歌《大风歌》被划为“右派分子”,在农场“劳动改造”
长达22年。1979年重新执笔创作小说、散文、评论、电影剧本,成为中国当代重要作家。1992年创办宁夏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担任董事长。其代表作有:《灵与肉》、《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我的菩提树》、《习惯死亡》、《青春期》、《一亿六》等。曾三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多次获得全国性文学刊物奖,有多部小说改编为电影电视搬上银幕。作品被译成数十种文字在国外发行。
|
| 內容試閱:
|
9月1日今天算是休息,一早起来就忙忙碌碌,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事,可是院子里总充满着紧张气氛。生活本身贫乏,内容单调,引起思想贫乏症。每天乏味的工作,使人的精神越来越庸俗。何和周一早起来就煮野菜吃,把组员交给他的辣子也煮来吃了。早饭后分瓜,每人一角八分钱。下午集体到卫生所检查身体,不过是量体重身高而已。晚上队长点名谈卫生问题。
试图到会计那里打客饭,未成,还被站长询问半天。
9月2日上午十二农渠间糖萝卜。干劲更低落了,所有人都大吃特吃糖萝卜、葵花子等。郑队长召集开会,大骂“吃青”行为。下午起麻和运糖萝卜。何说:
“管它!不吃白不吃。”也吭哧吭哧大吃糖萝卜。向朱振邦分了一角钱的锯末烟,只有几锅子。晚上学习,斗争刘光富。
9月3日上午十六农晒麻,后到菜地运糖萝卜,全组仍“吃青”。何为了顾全面子,也是怕刘祥如报告,中午不得不发脾气,叫每人交出葵花子。结果这场戏没有演好,下午吃得更厉害了。周和白干脆去偷西瓜了。何气得没办法,睡在田埂上。
9月4日九农渠割绿肥。一早出工就疲塌,何也拖在后面。郑队长大发脾气。全组加班一小时。据刘祥如说城市的供应更紧张,每人每月三包烟,还要领导证明你是吸烟的。今天拿了一个糖萝卜给丁海吉,他很高兴。现在一个糖萝卜也是好的。晚上场长报告“双反”问题,讨论的时候郑队长也讲了话。给了麻维孝半斤粮票打客饭。
注释:
首先要注释的是,八月三十一日与九月一日日记原文上加底点的部分,就是一九七○年这本日记被没收检查人员认为有问题的地方。在这两处文字下用蓝铅笔画了一条波浪,恰似起伏的海涛,使人总不得平静:我至今也不明白这几句话有什么可疑之处,为什么检查人员会特别注意它,他们究竟认为问题在哪里。是不是他们认为那种生活并不是“冷酷”的而是温暖的,不是“庸俗”的而是高尚的,不是“乏味”的而是有趣的呢?我认为是“冷酷”的、
“庸俗”的、
“乏味”的就说明我“思想反动”?……“阶级斗争要天天讲”不仅把同样的人划分成身份绝对不同的两部分,而且使人人的心里都筑起了高墙。人们相互理解本来就十分困难,人为地划分成“阶级阵营”后你就更别想理解别人了;不仅你弄不懂另一“阵营”的人的想法,连据说是与你同一“阵营”的人也不能沟通。高墙上虽然也开了若干个小孔,但那仅供窥探和射击用。
因为我永远也搞不明白哪些文字会受到人们的指责,什么样的句子会被人引申出“反动意义”,所以直到今天我还心存恐惧;今生今世我都要在这蓝色的浪涛上颠簸了。现在还有许多语言的化学家健康地活在我们国家,他们善于从作品的任何一个段落中研究出足够我第三次劳改的分子结构,甚至会添加一些试剂,使我的语言发生“重排反应”,完全变成另外一种化合物。
其实,浮在蓝色波浪上的那几句话只十足地表现了我的天真,表现了我经过七百多天的劳动改造仍然没有进入劳改犯的角色。我仍在要求生活丰富多彩,抱怨生活“内容单调,引起思想贫乏症”,在我心目中,劳改农场好像是所大学校似的。
然而,当时已经全面陷入贫乏的社会却唯独不缺乏“思想”。领导们狂热地探究着每一个人的思想,恨不能用手伸进每个人的脑袋里挖出脑浆来在显微镜下检验一番。每天晚上的小组讨论会、
“生活检讨会”和个人的“思想汇报”、 “……改造总结”等等,都一再强调人们要“暴露思想”。
“好好谈谈,最近你们在想些啥?”领导们经常不辞辛苦地深入到各个号子的炕头上,盘腿一坐,面带微笑,勾引人们倒出脑袋里装的东西。苏效苏啃玉米挨了打,回来后还要他“交代思想”:
“你为啥就舍不得那个玉米,队长叫你放下你还不放?你这是啥思想?”什么思想!你绝不能说是因为饿。饿只是一种感觉而不是思想。
“别人吃的跟你同样的定量,为啥别人就不像你?你这纯粹是故意给社会主义抹黑!”农民不理解叫人挨饿的社会主义,更不懂啃个玉米和社会主义形象有什么联系,只一个劲儿眨巴着小眼睛求饶:“以后我一定多干活,以后我一定多干活!……”而勇敢的知识分子尝试癞蛤蟆、尝试蜥蜴、尝试有毒的蘑菇……则一律是“由于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改造好”!正是他“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支配”才去吃癞蛤蟆、蜥蜴和毒蘑菇的。
你不这样分析,领导的脸上就会马上失去笑容。等着吧,下一个就该轮着你来“交代思想”了。
“看看!这时候还想吃肉呢!”有个知识分子犯人正煮着老鼠被发现了,组长把他被柴火熏得黝黑的缸子端去报告,老政委当即召集犯人开会,举着耗子肉向我们训话。
“知道不?现在毛主席都不吃肉了,他老人家还要跟全国人民一道度过困难哩,这个右派分子倒不自觉!还想方设法找肉来吃。害臊不害臊?大家要好好斗斗他的地主资产阶级享受思想!”
耗子肉被倒掉了,熏得黝黑的缸子也被没收。人们都盯着这个爱吃肉的右派分子。他坐在人群中低着脑袋。我看见他眼里依稀闪着泪花。也不知道是可惜他已经煮熟的耗子肉还是在伟大领袖的感召下觉得惭愧了。
思想暴露出来了,于是就进行“思想排队”。
八月二十九日日记上记的“思想排队”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每个月或两个月进行一次。排在最末尾的当然是思想最坏的人。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麻维孝,这是曾向我宣布自己是“永远也改造不好的人”,却在小组里总是扮演仲裁者的角色。大家在讨论时他很少说话,盘着腿靠在他的铺盖上,捋着他漂亮的三绺胡须。别以为饿着肚子的人对“思想排队”不感兴趣。在“排队”时人们还常常为了一点小事争论不休,连刑事犯此时也不甘落后。是不是每次都排在后面就会受到惩罚?也未必。升级到正式劳改队去的并不是落后分子而是犯了某种严重错误的人;每次都排在前面也不一定能提前“毕业”。但既然除了“思想”之外一切作为“人”的必要条件都丧失了,人人当然只能在“思想”上表现出自己还能称做是一个“人”,而不是牛、马、癞蛤蟆、蜥蜴或其他;只有在这点上人们才取得一点心理安慰,于是就在领导恩赐的这块巴掌大的、名曰“思想”的地面上力争树立起自己作为“人”的尊严。
麻维孝,在思想排队中理应排在最前面,因为他既不“吃青”又不倒换物品,劳动也不落后。可是每次他都谦虚地把自己降到第二位,这样他便取得了排列全组人的思想顺序的资格。小组会即将结束、大家准备拉开铺盖睡觉的时候,组长总要征询他的意见:
“怎么样?老麻,你说呢?”
这时他就会放下捋胡须的手,耷拉下眼皮,郑重其事地说:
“我看嘛,这样吧……”
一、二、三、四……他总会排得很恰当。真是旁观者清!只有吃得饱的人头脑才会这样清楚。他绝对不会让某个表现不好的人每次都排在最后,最后一名经常变化。而组长不管这月的表现好不好却非占第一名不可。他充分地将他关于“善”的哲学付诸实践。果然,没有一个人不服他,不说他好的。
至于我,承他的情,他每次都把我放在中间偏后。据我的记忆,虽然我是小组统计,
“秘书长”,他却没有一次把我放到前面去过。
“你呀!”背后他对我说, “你说说,啥事没有你:
‘吃青’、倒换东西,还有逃跑!劳动又吊儿郎当,干不到别人前头不说,还把好苗当坏苗拔了。就这样,领导还常照顾你,你叫别人咋能服气?你就排在后面吧!”
我咕噜着。我还觉得自己思想挺好呢!
“‘思想好’有啥用?”他不屑地嗤笑我,
“娃娃,活着才是真正的好!先把命保住再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我想,我大概也可算作知识分子中的一种特殊典型:在“思想”上自命不凡,精神的翅膀遨游在现实的“庸俗”世界之上,但在行为方面却顽固地遵循着生存本能的指使,只要有利于活下来的事无所不做。譬如八月三十一日这天所记的方爱华逃跑了一天又回来的事,其实始作俑者不是别人而是我。麻维孝说我逃跑,不仅是指那次长达十五天的逃跑,还要加上在此之前的一次短暂的短跑。因为那次短暂的旅行在劳改队造成的影响,远远大于一些刑事犯翻墙而过,永不回头。自我开了先例,就不断有人只逃跑一天,然后回来写检讨,甚至有人事先把检讨写好再逃跑。方爱华的创造不过在于他写的不是检讨而是一份逃跑原因的说明。这样,逃跑回来后,挨领导臭骂的倒不是他却是组长。
从以上我的注释中读者也可以看出来,劳改农场的管理和整个社会的管理一样,在法律、制度、警卫方面是说不上有什么严格控制力的,但它又绝不是宽松和松懈的。法律、制度、警卫等等方面的不足完全由严密的思想控制弥补了;每个单位都采取家长式的领导,庄园式的人身依附关系附着在上下级的行政关系上,因而使人与人之间有超过血缘关系的紧密度:一个监视一个,谁也别想游离出去。并且,不断的政治运动在每一个人头上经常进行思想梳篦,
“坏思想”要像蚤虱一样遭到清洗。然而,正因为如此,正因为它不是靠枪来管你而是靠你头脑里的思想来管你,如果你有意无意地漠视这种思想管制,要游离出去、要逃跑,却又是很容易的。
还在去年这个时候,劳改队开始大批死人而“巴比伦”还没有死,我已经痛切地感到饥饿的威胁了。一天,我确实有点病,出工时小组的人都走光了我却还躺在炕上。不知怎么,谁也没有注意我,没有叫我,没有催我。鸟儿都飞了,偌大的一片树林寂静无声。我顿时有种茫然的感觉:是去追赶大队还是继续躺着不动?
我抬起头看看四周,只有犯人们乱七八糟的铺盖;阴森的号子在一线灿烂的阳光中更显得阴森。我第一次发现所谓的“家”必须有人在里面活动,哪怕是个流氓小偷在偷东西。空荡荡的号子纯粹是所微型的地狱,呈现出了它全部的丑陋。如果地狱里有臭味的话,那一定是我现在闻着的这种既潮湿又热烘烘的臭味了。我害怕地爬起来,顺手抽出我当做枕头的棉裤走出了大门。
我昏昏沉沉地一直往前走,漫无目的、不自觉地走出了劳改大院,走出了劳改农场的范围,怀里抱着条棉裤走到老乡的田里。
这就是自由;我竟然自由了!没有一个人来阻挡我。虽然路上也碰见好几个劳改农场的干部和工人,还有一个腰带上别着枪的公安人员,但他们根本意料不到一个劳改犯会采取这种公开的方式逃跑——抱着一条棉裤招摇过市,除非是一个疯子!
没有计划,没有预谋,只要把一切束缚你的思想统统抛开便能获得自由!多么简单!但只有极少人能意识到这一点。
自由自在地走到老乡的田里,在清新的空气中头脑稍微清醒了,但首先感觉到的却是饥饿。既然已经自由了,总要利用自由干些什么。
前边不远有座看瓜的草棚,我自由的脚很自然地向有吃的地方走。一个农村老太太坐在草棚里纳鞋底,看见我一点不惊异,还笑眯眯地盯着我怀里的棉裤。劳改农场附近的农民对待犯人,已经像邻居一样熟悉而亲切了。还没等我开口,老太太便问:
“娃娃,来干啥?怀里揣的是个啥?让我看看。”
我把棉裤交给她。向棚里一探头,发觉她果真比犯人还要穷。环顾四周,除了还没有完全成熟的西瓜再没有别的什么可以充饥的东西。老太太挑剔地翻来覆去地看棉裤,将白布里子翻在外面,仔细地检查针线,一面还咕哝着说机器轧的没有手工缝的好。最后,总算通过了鉴定,问我:
“你这条棉裤咋换呢?”
我问她有什么。她的嘴朝田那边一努,说只有瓜。我说瓜还没有熟。她笑道:
“这么大一块田,还没有熟的瓜?我帮你挑。撑不死你!”
老太太稀疏的白发掩不住头发上一块块老人斑,像天空投射在荒原的云影;蓝色的衣衫上补了又补,几乎可以当夹袄穿,我崭新的棉裤摆在她身上更衬托出她的苍老和凄凉。但她爽朗而健谈。
“撑不死你”是本地人表示亲昵的语气,意思是她会拿出很多熟瓜来,多得可以撑破我的肚子。她准备“撑死”我,令我感动得鼻子发酸。瓜就瓜吧,冬天穿的在夏天换吃的,不管能换到什么都是便宜,何况我是不是能活到冬天还很难说。可是我不会挑瓜,我摊开两手说,我分不清哪个瓜是生的哪个瓜是熟的,我只会吃。她微笑着打量我,问我是为什么劳改的。我想,为了一首诗就被劳改,说出来恐怕连这个农村老太太也不相信,我就指了指脑袋,告诉她是那里出了问题。她同情地用嘲笑的口吻说:
“娃娃,头把你害啰!”
是的,
“头把我害了”!后来,每当我又不由自主地动脑筋的时候,我就要想:是不是头又会害我呢?以至于搞得我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只要一运用头脑就心惊胆战。
她果然给我挑了很多熟瓜。她在田里爬来爬去,直起腰时,我看见她汗流满面,边喘气边撩起衣襟擦汗,露出两片干瘪的瘦奶。我赶忙说:“够了够了!我也吃不下那么多,你别摘了,歇一会儿吧。”她却叹了一口气:
“唉!可怜见的!别的啥也没有。瓜,你就放开肚子吃吧!这东西吃不坏人的。”
一大堆滚圆的西瓜终于放在我面前。碧绿碧绿的,个个可爱。可是我在田边吃的话让公社社员看见了会检举她,而我要抱回号子里吃让劳改犯人看见了又会检举我。老太太就从草棚里抽出一条破麻袋,帮我把瓜一个个往里面装。两人一个背一个抱,来回运了好几趟,才把所有的瓜挪到人们不容易看见的树丛里。她拍了拍巴掌,抻了抻衣衫,说:
“好,娃娃,你就在这里消停地吃吧。我走了。”
“消停”是“安静”、
“悠闲”的意思。于是我就“消停”地坐下来开始享受了。
我吃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吃一会儿休息一会儿,有时坐着吃,有时躺着吃,有时边撒尿边吃,从上午一直吃到黄昏,才把几麻袋西瓜吃完。我宁可撑破肚子,也不愿意把瓜剩下。哪怕是撂掉的瓜皮上还有一口,我也看着可惜,又要捡起来再啃。老太太说得对:西瓜吃不坏人。我四周全是西瓜皮和尿水。绿头苍蝇围着我嗡嗡转。我捂着鼓胀的肚子居然丝毫没有不舒服的感觉,我仍然“消停”地躺在树荫下。刚吃的时候还尝不出来西瓜的味道,吃了几个才知道西瓜是甜的,然后再吃,西瓜汁就变成白水一样淡而无味了。现在,休息了很久,瞅着一地青白色的瓜皮,回味那西瓜的红瓤,嘴里再次泛出火一般的甜香。我这时才知道,世界上最美好的事不是我在书上读到过的发现真理,或者是刑事犯们常说的和女人性交,而是——饱!
但是,吃饱了,
“思想”又回来了。肚子的充实和头脑的充实好像是一致的。太阳即将落山,苍蝇像尘埃一样落在地上休息了,蚊子又出来欢唱。蚊子不叮西瓜皮,却一团团地向我劈头盖脸地扑来,我随手向空中一抓就能抓死满手蚊子。再躺在小树丛里我就会像被“照相”的犯人一样被蚊虫叮死。我爬起来,一时却不知到何处去为好。这时“思想”就告诉我应该回劳改队去。我的“思想”通过学习已经达到这样的高度:它从来不会让我认为把我送来劳改是错误的,而只会让我以为我不愿劳改是错误的。
于是,我沿着来的路,像狗似的,每遇到一棵树就朝树下浇一泡尿,一直撒到劳改队。
回“家”后,大队还没有收工,西瓜也还没有完全消化。我又在我的铺盖上躺下了。这时应该干些什么呢?“思想”又教导我还是需要写份检讨。肚子受了西瓜的润泽,我洋洋洒洒地把检讨书写得详细而有文采,几乎每字都可圈可点,不像检讨书倒像一篇游记。待大队回来,我的检讨也写好了。我越过组长,直接把它交给了队长。
队长就站在院子里看。好文章一开头便能吸引人,队长有滋有味地看完了我的检讨书,惊奇地问:
“你狗日的别唬我!一个人一天他妈的哪能吃了几麻袋西瓜?你老实说,你狗日的到底干啥坏事去了?”
幸亏那片小树丛离劳改队不远,队长好奇地拿着手电筒跟着我到了吃西瓜的地点。当他看到凡是电筒光能照射到的地方全是西瓜皮,也不由得笑了起来:
“你狗日的真能!真能!”一脸很佩服我的样子。
我们的领导有时也很可爱,你让他看一些有趣的事,能让他高兴高兴,即使是违犯了纪律他也会饶恕你。
这一天的经历成了我下一次逃跑的演习。我既然没有受到处罚,从我以后,劳改队就经常有犯人只逃跑一天,到附近老乡家里“串个门子”再回来。而老乡们也很乐意接待这种暂时逍遥的犯人:自民间文学也必须为政治服务以来,所有的故事都变成了严肃的报纸社论,但只要有一小块糠菜团子,有的犯人就能把他的罪行讲得天花乱坠,既诙谐又富传奇色彩。老乡们一面饶有趣味地听故事,一面还能换些东西,捞点便宜,何乐而不为?
但是,从此以后,我再不能吃西瓜了,一吃西瓜就胃疼。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