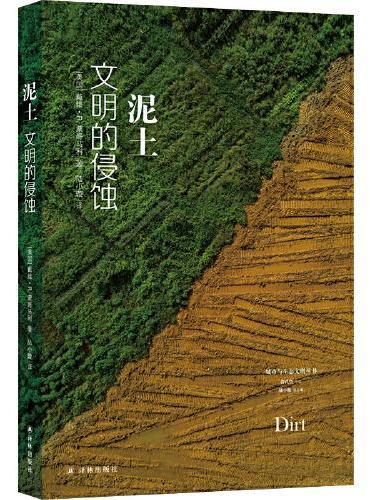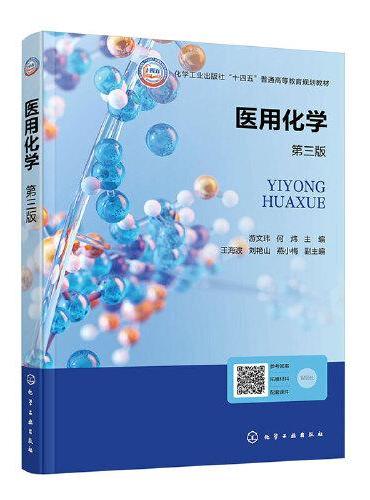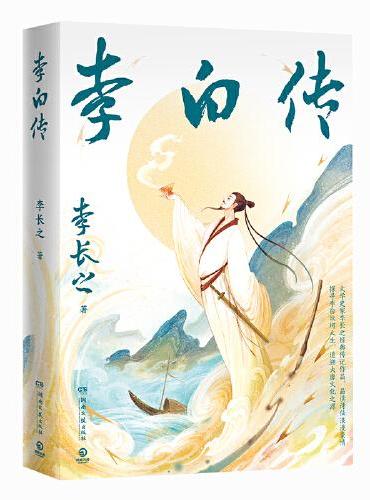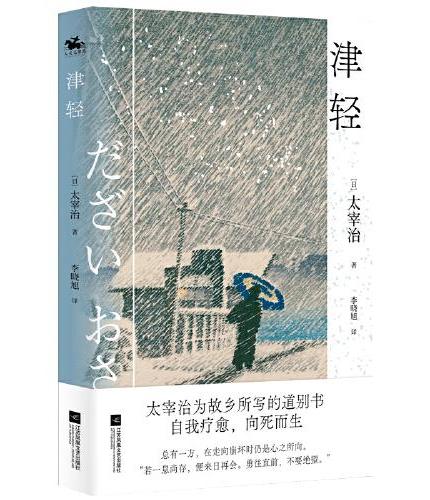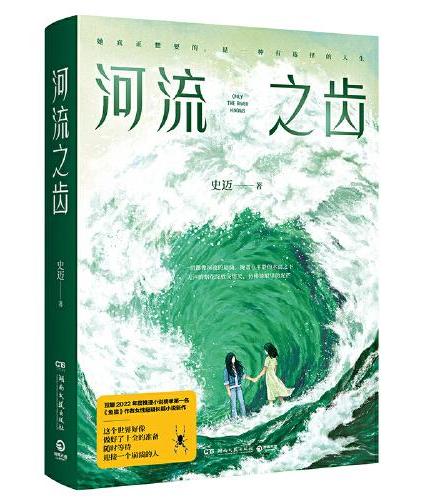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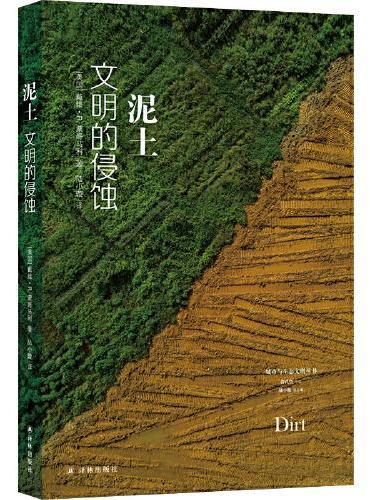
《
泥土:文明的侵蚀(城市与生态文明丛书)
》
售價:HK$
8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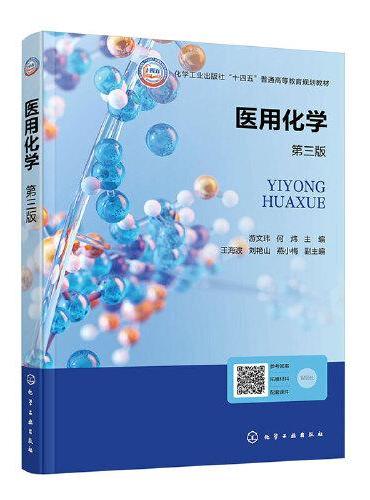
《
医用化学(第三版)
》
售價:HK$
57.3

《
别怕,试一试
》
售價:HK$
67.9

《
人才基因(凝聚30年人才培育经验与智慧)
》
售價:HK$
103.4

《
深度学习详解
》
售價:HK$
11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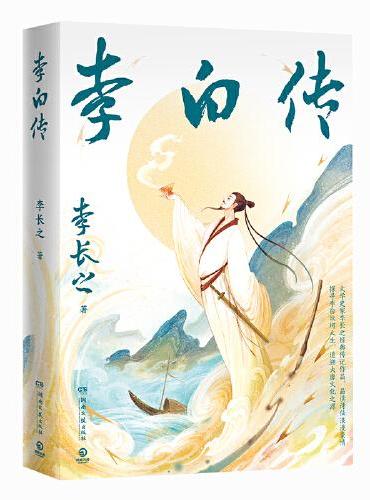
《
李白传(20世纪文史学家李长之经典传记)
》
售價:HK$
4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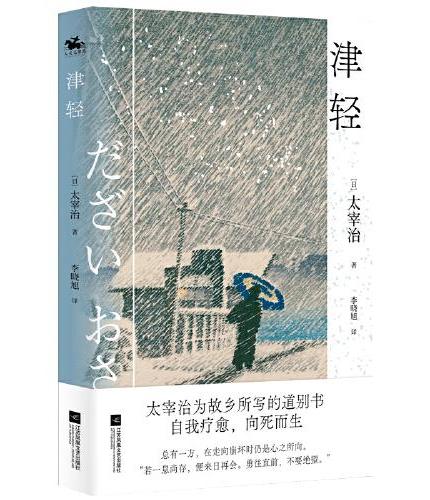
《
津轻:日本无赖派文学代表太宰治自传性随笔集
》
售價:HK$
6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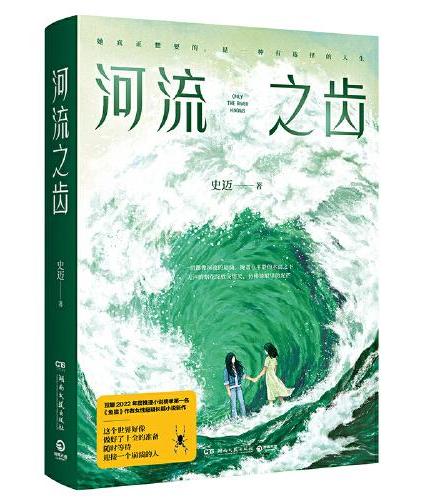
《
河流之齿
》
售價:HK$
59.8
|
| 編輯推薦: |
|
一部完整的两晋政治史读物,葛剑雄、马勇、仇鹿鸣一致推荐。全面揭示晋朝的兴衰与得失。书中围绕两晋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混合周制与秦制的实践、士族政治的偶然与必然、死结现象之于晋朝意味着什么等问题,全面揭示了两晋兴衰背后的深层次治理逻辑与历史因果链。多角度透视晋王朝的困境。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环境等多方面出发,结合人物个案和家族研究,如司马氏篡魏、八王之乱、桓温北伐等政治事件,剖析究竟是哪些死结导致了晋王朝的衰败。视野宽广,指出晋朝承前启后的作用。本书动态地观察了从东汉以来,贯穿两晋,延续到隋唐兴起的长时段的死结现象,并指出晋朝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两次绝无仅有的意义。适合大众阅读的晋朝历史,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作者笔触客观,不偏不倚,叙事细腻,从洛阳的光复和桓温的勃然大怒说起,以简明晓畅的文字勾勒出两晋历史演变的线索,为普通读者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入门指要。穷尽史料,立足史实,论证有理有据。本书立足《晋书》《资治通鉴》《世说新语》等原典,并广泛引用了中外学者最新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诸如晋武帝是少有的仁君、桓温并无篡位安排、孝武帝死于突发疾病等禁得起考究的历史研究结论。正文后附录《晋大事年表》
|
| 內容簡介: |
两晋是黑暗、屈辱、不幸的朝代?晋朝如何突破二世而亡的历史瓶颈期?皇室与士族共治秩序的产生,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
这是一本完整的两晋政治史读物,全面揭示了两晋兴衰背后的深层次治理逻辑与历史因果,多角度透视了晋王朝的困境。书中从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文化环境等多方面出发,结合人物个案和家族研究,剖析了导致晋王朝衰败的死结现象,并关联东汉与三国时代的历史经验,指出北朝、隋唐兴起背后的机理,揭示晋朝在中国历史上两次绝无仅有的价值。本书以简明晓畅的文字勾勒出两晋历史演变的线索,为普通读者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入门指要。
|
| 關於作者: |
|
沈刚,作家,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编辑专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历任上海《萌芽》杂志社编辑、上海《解放日报》编辑,之后创办企业至今。大学时代即发表小说、报告文学作品。小说《别了,十八岁》获“萌芽”文学奖。出版小说集《别了,十八岁》,出版史评著作《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酷爱中国历史的阅读和研究,致力于跨界大历史写作。
|
| 目錄:
|
绪 章 晋王朝何至于此?
第一章 司马懿父子的代魏接力
第一节 系统的死结是怎样形成的?
第二节 司马懿:双面人革命
第三节 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两手策略
第四节 当儒学遭遇玄学
第二章 晋武帝,儒家理想社会的布局
第一节 恢复周制的政治实践
第二节 天下重现大一统
第三节 共治结构的平衡安排
第三章 大一统时代的终结
第一节 杨、贾外戚势力出局
第二节 宗室诸王的混战
第三节 统治集团外部的挑战
第四节 宗室、士族大败局
第四章 建康,共治的新起点
第一节 王马共治与东周模式
第二节 皇权与当权士族的冲突
第三节 共治实践的游戏规则
第四节 渡江名士的选择
第五章 桓温独大的时代
第一节 恢复神州的价值付诸实践
第二节 桓温主导共治的开始
第三节 桓温的两难困局
第四节 江左名士:隐逸或出仕
第六章 苻坚与谢安的解决方案
第一节 混合秦周胡三制的前秦政权
第二节 谢安主导士族联合专政
第三节 淝水之战的胜负与天命所在
第七章 刘裕引领百年变局
第一节 武人势力挑战士族政治
第二节 晋室的实际统治是怎样被终结的? 第三节 刘裕重建集权专制的统治
第四节 首开禅代杀害前朝君主的恶例
余论 历史为何选择北朝?
后记 我写晋朝那些事
参考文献
附录:晋大事年表
十六国一览
|
| 內容試閱:
|
绪论 晋王朝何至于此
洛阳之殇
公元 356 年,晋穆帝永和十二年七月。江陵城外汉江上,晋临贺郡公、荆州刺史、征讨大都督桓温大步登上战船,晋军官兵早已整装待发。随着桓温一声令下,舰队高挂起船帆启航,一时旌旗招展、鼓角齐鸣。舟师沿汉江支流淯水北上,一路未受任何阻击,直奔宛、洛等中原故地。与此同时,东线谯梁水道打通,另一支徐州、豫州所辖晋军,经淮水、泗水进入黄河,迅速向洛阳逼近。
这时,距离晋元帝司马睿在建康重建中央政权,已经过去近四十年。
公元 311 年,晋怀帝永嘉五年六月,成千上万的匈奴兵士、流民攻入洛阳。晋怀帝司马炽仓皇奔出华林园,准备逃往长安,在路上被擒获。来自北境及底层的占领者们,根本无意经营洛阳,大肆劫掠宫庙、官府和巨室,随后又挖掘司马氏陵墓,把金银财宝、年轻妇女
作为战利品。太子宗王、士族官僚及百姓民众三万余人,在大屠杀中遇难。继东汉末年董卓火烧洛阳之后,这座魏晋时代重建的巍峨都城,再度笼罩在熊熊的烈焰中。
早前两个月左右,以督师讨贼名义领军的东海王司马越在项城去世,十余万军民护送其灵柩向东海国转进。匈奴汉国羯族大将石勒率骑兵将其团团围住,无数带火的弓箭疯狂地射向“猎物”。晋军完全丧失抵抗意志,血肉模糊的尸体、伤者混杂堆积,猎手们一面纵火焚杀,一面津津有味地用餐。太尉、士族领袖王衍尽管向石勒乞降,最终仍与大批宗王、公卿和名士一起,被石勒下令推倒土墙埋杀。随后,石勒伏击从洛阳东逃的司马越亲属部将、数十位宗王及众多朝廷官僚,悉数予以杀害。
公元 316 年十月,匈奴汉国首席大将刘曜率部众再度攻陷长安。被拥立为帝的晋愍帝司马邺自缚其身,抬棺下跪出降。晋怀帝、晋愍帝在匈奴军中受尽屈辱,最后依然不免被杀的命运。洛阳陷落前后,晋惠帝皇后羊献容被刘曜纳为妾室,司马越夫人裴妃等遭到抢掠贱卖。
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南北形势发生了巨变。匈奴汉赵政权早被石勒武力取代,石勒及其养子石虎死后,一度强行征服北方大部分地区的后赵政权分崩离析。汉人大将冉闵下达“杀胡令”,造成羯人在内的二十余万各族民众非正常死亡。东晋政权反而在建康站稳脚跟,桓温西攻川蜀,灭亡割据了四十余年的成汉政权,东晋疆域超过三国时期东吴、蜀汉政权的总和。
除了盘踞辽东的鲜卑前燕南下河北、氐人集团西进关中建立前秦,黄河以南地区大小军阀纷纷向建康称臣,东晋政权至少名义上短暂恢复了洛阳等中原旧地。公元 356 年,姚襄羌人集团降晋又叛晋,北归攻击控制洛阳的叛将周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桓温决定兴师北伐。
舰船在河道上平缓前行。长辈回忆、书籍记载中的昔日繁华之地,早已尘封为千里荒野。望着两岸陌生的故土,桓温思绪万千,几乎夜不能寐。次日,桓温带领众僚属登上舰船的平乘楼,眺望中原。《晋书·桓温传》记录,桓温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王夷甫是王衍的字,桓温认为,西晋的沦亡,王衍等士族名士要负主要的责任。
虽然桓温多年来担任军事统帅,但骨子里不失名士本色。桓温军府中聚集了多位士族子弟、文人名士,桓温平时与僚属们保持着随和、平等的交流。桓温话音未落,担任记室的文史名士袁宏立即答道:“国家兴亡自有天命,不一定是他人之过。”
令所有人没想到的是,桓温闻后居然勃然大怒,严厉地驳斥道:“昔日刘表有一头千斤大牛,吃的食物是普通牛的十倍,其负重致远,不如一头病弱的母牛。曹操进入荆州后,立即把它杀了分给军士们享用。”举座皆失色。桓温出于对崇尚务虚清谈的士族名士的强烈否定,以只会吃食而不会干活的大牛为喻,直指占有资源而无所事事者之流。
桓温击溃姚襄羌人集团迫其西逃后,洛阳城中周成率众投降。桓温下令整顿军容,晋军官兵意气风发昂首入城。邙山巍巍,洛水悠悠,尽管洛阳城已不复盛世的神采,但是,这座华夏民族的千年故都,可能永远是南渡士族子弟心目中的精神家园。对于晋室而言,这里静卧着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及晋武帝司马炎、晋惠帝司马衷四代五位皇帝的陵寝,其意义不言而喻。晋武帝完成魏晋禅代后,追尊晋王朝实际奠基人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为帝。追尊祖父司马懿为高祖宣皇帝,伯父司马师为世宗景皇帝,父亲司马昭为太祖文皇帝。
桓温屯军于太极殿旧址前,随后又迁移至金墉城。“谒先帝诸陵,陵被侵毁者皆缮复之,兼置陵令。”(《晋东·恒温传》)东晋朝廷接到洛阳光复的军报,14 岁的晋穆帝司马聃立即穿上细麻布衣,率领文武群臣,至建康太极殿谒拜三日。同时正式派出大臣赴洛阳谒陵,修整五位先帝的皇陵。
不过,朝廷始终没有选出合适的统帅镇守洛阳。不久,桓温班师南归,仅留下数千将士驻扎。洛阳光复前后,桓温多次建议把京师从建康迁回洛阳,一直未获朝廷采纳。无论在当时的晋室朝廷上,还是在后世的历史评论中,桓温经常被认为是假北伐中原之名,行夺位自立之实。九年之后,洛阳再度易手,为前燕鲜卑军人占领。
作为大一统政权崩溃的标志性事件,西晋时期“永嘉之祸”的惨烈程度,远胜过北宋末年的“靖康之耻”;而以正统自居的东晋偏安政权,不仅收复过洛阳故都等中原故土,而且还曾有效管辖多年,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桓温本人是一代士族门阀,为什么他内心对于士族名士的某些特质极其反感?
晋王朝何以兴起又何以衰亡?从洛阳到建康,两晋皇权、士族兴衰的背后,代表了深层次的治理逻辑与历史因果链条。
最黑暗、最屈辱和最不幸的时代?
在中国历史上九个大一统王朝中,晋朝的存在感相对最低。民间对于三家归晋之后的进程知之甚少,反而对于分裂的三国时代津津乐道,江山如画、英雄辈出,一时多少豪杰。曹操、刘备、诸葛亮和孙权等人的名字,在社会上几乎妇孺皆知。这和《三国演义》的充分传播有着直接关系。晋王朝的实际开创者司马懿,小说中是作为诸葛亮的对立面而被描述,所谓死诸葛吓走生仲达,尽管是笑到最后的人,还是被诸葛亮深深压下一头。千年来流传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一语,则是对司马氏家族易代革命持否定态度的明证。
稍有历史知识的人群,对于晋王朝的观感大多较负面。比较常见的评价,即认为晋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屈辱和最不幸的时期之一。
两晋被认为是一个最为黑暗的时代,实际上出于晋朝得国不正的认知。司马氏父子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大量屠杀反对改朝换代的曹魏大臣、名士,皇帝曹髦被当街刺死。司马懿生性残忍,平定辽东公孙渊割据政权时即大开杀戒。《晋书·宣帝传》记载,“诛曹爽之际,支党皆夷及三族,男女无少长,姑姊妹女子之适人者皆杀之,既而竟迁魏鼎云”。
将晋朝称作最为屈辱的朝代,主要是因为当时是北方族群第一次大规模逐鹿中原,北方地区一度仇杀严重。白骨沃野、血流成河,“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发生了把汉族妇女作为“两脚羊”进行残害的极端恶例,造成包括汉人在内的各族民众大量非正常死亡。晋室被迫东迁建康,国家发生持续的内战和动乱。
至少对于崇尚奋斗的群体而言,晋朝可能是一个最为不幸的时代。这一阶段出现了阶级固化和士族专政,整个社会人才的上升通道受到堵塞。一个人地位和身份的提高,主要看他背后的门第名望。国家通过九品中正制等选官制度安排,首先保证士族子弟被品评为上品,直接授予其高级官职。元人刘秉忠有词云,“晋朝人物,王谢风流,冠盖照神州”。东晋时期琅邪王氏、陈郡谢氏等士族门阀,其家族成员遍布朝野、占据要职,其实将国家组织体制高层的治理人才,局限在相当狭窄的范围之内。其他低级士族以及寒门子弟等,仅能成为组织体制中较为次等的角色。
得国不正、国家分裂和士族专政,这些确实部分反映了两晋时期国家治理的现实,但是,这些认识至少并不全面和深入。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父子固然存在残忍好杀的一面,但在改朝换代十六年的准备期中,更多地采取了笼络和收买的方式。
开国皇帝晋武帝司马炎,实际上是帝制时期少有的一位仁君。他高调推崇周制,倡导儒道互补、以孝治国,既向士族名士妥协让步,又积极减轻一般平民的负担;既善待功臣、武将等外朝官僚,又重用宗室、外戚等亲属势力。两晋立国一百五十余年,共产生十余位帝王,他们大多善良、懦弱和短寿。晋朝失去天下,也许和这些帝王无能、控制不了政局有关。暴政肯定不是主要原因之一。
东晋政权偏安江左后,晋明帝司马绍听到王导关于先辈创业时,杀害诸多名士及魏帝曹髦的介绍,不禁掩面,长叹晋祚怎么可能长久。简文帝司马昱善于清谈,临终前口述遗诏,差点将国家私授给权臣桓温,认为晋室只是因为好运而得天下。这些都透露出司马懿的后代们尚未失去天下,先已失去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底气。
晋室东迁后,北方一度处于混乱的状态,固然反映了大一统国家治理的严重挫败,但这并不等于东晋政权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桓温率军灭亡西蜀的成汉,东晋政权实际控制区域超越了前东吴、蜀汉区域总和。晋军多年在黄河以南作战,先后四次恢复旧都洛阳。前秦天王苻坚亲率百万之众南征,谢安以其侄谢玄统领的流民组成的北府兵迎敌,东晋军队不仅在淝水大战中获得大胜,收复大片国土,还北上作战一度攻入河北。
刘裕发起的北伐规模为东晋历次之最。首先刘裕攻灭山东境内的鲜卑族南燕政权,斩杀王公以下数千人,国主慕容超被送到建康处决。他又派军灭亡西蜀的谯蜀政权,之后刘裕指挥大军攻入长安,羌族后秦政权灭亡。刘裕下令杀尽被俘的后秦王公大臣,将后秦国主姚泓押至建康斩首。这一时期东晋政权控制的领土,大致与后世北宋政权接近,创造了大分裂年代南方政权疆域最为辽阔的高光时刻。
两晋时期,士族名士毫无疑问在国家政治运营体系中占据主导的地位,但是,低级士族、寒族子弟并不是说完全没有用武之地。高门士族脱儒入玄,沉溺于务虚空谈,对于实际工作反而不屑一顾,他们更加看重礼仪性、学术性的高位,愿意享受荣誉和清望,这些位置在两晋南朝时期被称为“清官”。反之,一些处理日常繁忙公务、较具风险性的岗位,特别是以军功晋级的武职,在当时被称为“浊官”,多由低级士族、寒族子弟担任。
西晋时期的寒族人士中,大将军邓艾、王濬,分别在攻灭蜀汉、东吴的战役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大臣张华辅佐惠帝司马衷、皇后贾南风夫妻,至少稳定了六七年的政局;东晋时期世家大族的统治日益制度化,仍然有寒族出身的荆州刺史陶侃,平定了“苏峻之乱”;生为低等士族的大将刘裕,最后成为晋朝帝室的终结者。
本部分深入剖析了晋至南北朝时期中国政治系统的死结及其对国家治理的影响。通过四个阶段的分析,揭示了价值理念与政治实践的矛盾,探讨了士族政治、宗室权力斗争等因素如何影响政治稳定与合法性。文章还对比了北朝的改革与南朝的困境,为理解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变迁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编者按
系统死结的四个阶段
秦汉建立大一统政权,为后世中国王朝的基本规模、国家形态和治理体系奠定了范本。魏晋南朝以禅代的方式,把自己作为两汉的直接继承者,其统治者无不以恢复强盛汉朝为己任,然而历经三四百年漫长的探索,始终未能达到目标。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很多,魏晋治理体系的死结本质,即国家倡导的主流意识形态与现实政治的实际操作层面的对立与冲突,至少是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之一。这就对政治系统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构成了重大的挑战。
在儒学居于国家统治思想的君主专制时代,所谓政治系统的合法性,就是要使人们自觉接受最高统治者的皇权受之于天的观念。有效性也是合法性的来源之一,如果新兴的王朝能够安全度过瓶颈期,人们也可能产生认同其天命的习惯。魏晋南朝各代大多得国不正,除两晋经历反复、极勉强地通过瓶颈期以外,其他政权的统治时间均不过两代人五十年左右,其治理体系内在的死结,直接造成其合法性的缺失。
此外,这一时期除西晋政权短暂统一外,天下处于分裂的状态,内部出现士族政治,国家的资源控制与动员能力低下,这些统治有效性的弊端,与系统的死结也存在着较大关系。
并不是说死结决定了两晋的政治发展,而是说在两晋政治发展过程中,治理的死结影响甚至改变了这种发展。如果国家倡导的价值理念,与现实政治中的实践策略相互支撑、融合,即能激发起士民对政权的忠诚与信仰,有助于国家战略目标的实现,但是,两晋大部分时间的治理状态却是相反的情况。具体到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死结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造成的社会撕裂的烈度、广度也各不相同。两晋及其前后的数百年,系统的死结存在于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前后七十余年,自公元 196 年汉献帝建安元年,曹操置献帝于许昌即挟天子而令诸侯,至公元 266 年初,司马炎正式终结曹魏而改国号晋。这一阶段,是国家的价值倡导与现实政治之间尖锐对立的时期,自东汉光武帝刘秀始建立的士民对儒家思想、汉政权和皇帝的三者合一信仰体系彻底崩溃。
其中东汉晚期、曹魏前期,士大夫、民众仍持汉室享有天命的观念,对曹氏父子暴力代汉的合法性严重存疑,这是曹魏政权迅速被颠覆、没有通过瓶颈的重要原因之一;高平陵政变之后,进入了司马氏父子代魏时期,其间发生废帝、弑君等严重挑战儒家价值底线的事件。尽管人们意识到改朝换代已经不可避免,对于统治者不得不表示服从、拥戴,但是,这并不等同于天命层面的认可,相反儒家思想中皇权授之于天的神圣性受到挑战,儒学逐渐失去凝聚人心的价值功能。
第二阶段大约五十年,贯穿整个西晋政权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前半段,死结的对立程度朝着舒缓的方向发展。晋武帝司马炎完成天下统一,通过恢复周制、与宗室士族共治等策略,试图建设晋室的天命合法性。至少在武帝时期及贾后掌权前期,晋政权的统治保持着较高的有效性。不过,士族名士中脱儒入玄的倾向,已经从曹魏时期凤毛麟角的行为,发展为向整个阶层扩散。儒玄两种价值此消彼长,士族官僚先家后国的风气没有转变。晋武帝大量重用宗室诸王,也是基于士民对于晋室的天命缺乏信仰的选择。
八王之乱、永嘉之乱时期,中央政权逐步丧失了统治的有效性。儒法国家中皇权主导的价值,与宗室揽权、士族自保的现实政治形成新的治理死结。统治集团之外的流民群体、少数民族部落揭竿而起,完全否定晋室的合法性。士族名士一边采取随波逐流、明哲保身的态度,一边继续沉溺玄学清淡,以任达、放诞为乐,对于挽救晋政权的危局缺少实际的帮助。
第三阶段接近一百年,自公元 317 年晋元帝建武元年,司马睿在建康重建晋政权,至公元 415 年晋安帝义熙元年,刘裕控制国家运营系统。王导协助晋元帝司马睿,以恢复神州的价值作为晋室重建的合法性来源,把士族联合专政作为有效统治的基础。士族共治要求维护南北士族减免赋役、占有附属人口的经济利益,以及各门户的政治利益,这就削弱了中央集权及国家资源动员能力,而要实现北伐中原的目标,又必须加强集权、提升国家能力,恢复神州的价值号召,与现实政治中“务必清静”、优容士族的操作冲突,构成东晋新时期的死结。
晋元帝发出“免良为奴”的诏令,庾氏兄弟实施“任法裁物”的整顿,司马道子推行“免奴为客”的政策,引发程度不同的动乱,即是触碰了结构性死结的缘故;王导、桓温和谢安等主政者采取尽可能团结、迁就南北士族的政策,保持江南社会的稳定,击溃了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南下,但是,这也可能是桓温、谢安北伐不能成功的原因之一。至少在淝水大战前夕,保卫中华正统的价值,与全面战争动员的现实政治实践之间一度取得短暂的平衡。
第四阶段可能延续整个南朝,其前半段大致为七十年,包括刘裕在东晋掌权的时期,以及刘宋政权时期。刘裕以北伐取得代晋的正当性,但是,他没有为新的王朝树立正常的儒家伦理秩序,刘裕虽恢复了秦汉、曹魏时代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统治策略,却没有重建士民对政权、皇帝和儒家思想三位一体的信仰体系。尽管刘裕、文帝刘义隆名义上倡导儒学的价值,而在实际的政治运作中,完全遵循赤裸裸的暴力至上逻辑。其手段之残忍,远甚于士族共治时期。刘宋政权系统内部的死结对立程度,几乎回到了东汉晚期、曹魏政权前期。
宋武帝刘裕以宗室诸王出镇荆州、京口等要地,与晋武帝司马炎重用宗室的出发点完全相同。晋武帝身后发生八王之乱,宋武帝身后发生子孙相残,本质上都是宗室子弟缺少儒家价值的教育所致。刘裕在禅代前后,野蛮杀害了晋安帝、晋恭帝,之后萧道成建齐代宋,又谋害年仅 13 岁的宋顺帝,对于刘氏宗室大肆杀戮,这些都是价值观不彰、合法性缺失的系统死结对国家治理体系最直接的影响。
士族共治与治理死结
平心而论,晋武帝司马炎是中国帝制历史上一位难得的仁君。如果晋政权在他身后仍能维持统一繁荣的局面,武帝在历史上的评价,至少不会低于汉文帝刘恒,也许可以比肩宋太祖赵匡胤。晋武帝部分恢复周制,实施宗室、士族共治的统治策略,符合两汉以来儒生士大夫的政治追求,体现了他真诚地服膺儒学价值。这也奠定了两晋士族政治的基础。
隋文帝杨坚并无显著军功,仅以外戚及关陇集团二代的身份,花费十个月篡夺北周政权;宋太祖赵匡胤在后周世宗去世仅半年后,即在陈桥驿黄袍加身。这些行为与司马氏祖孙相比,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人们对于隋宋等其他朝代篡位的状况似乎要宽容许多。究其原因,司马氏所处时代较早,除了传说中尧舜禹可能实行过禅让,无论成汤革命、武王伐纣,还是秦汉帝国的统一,都是被包装成替天行道的武装革命。王莽代汉的失败,已经使禅让成为篡位的代名词。曹魏代汉、司马氏代魏的治理体系的底层逻辑中,自开国始即存在着价值导向与现实政治对立的死结,从而造成巨大的合法性先天缺陷。
自西汉武帝时代始,儒生被制度化地引入统治集团,士大夫阶层逐步成长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捍卫者、诠释者,晋武帝司马炎对之让步、笼络,是为了得到士大夫阶层对政权的背书,追求晋室的天命合法性。
西晋时期,士族尚不掌握兵权,还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司马氏统治者本身即为士族中重要成员,晋武帝夺位后,一方面把士族的政治理想付诸实践,即部分地恢复分封的周制,把周人天命观中德治的理念予以落实;另一方面,他也汲取曹魏政权“薄骨肉”而致外臣夺权的教训,大量分封、重用宗室,保证皇权以及司马氏宗室在统治集团中的主导地位。
所以,晋武帝司马炎打开治理死结的努力,取得过阶段性的成效。如果不是他在处理接班人、辅政大臣等重大问题上,过于宽仁放纵、犹豫不决,放弃法家严刑峻法的霸术,混合周制秦制的宗室、士族共治可能会延续下去。帝制时代的历史将因之改写。在印刷术尚不普及、学术掌握在少数经学世家的时代,皇权与文化贵族的共治,也许比秦制的君主绝对专制更能给民众带来幸福感。
由于绝大多数司马氏宗室成员死于“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士族名士在历史大变局中,意外地被推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上。东晋政权以保卫中华正统、恢复神州的价值重建合法性,
这是由王导等南北士族与元帝司马睿共同推动的,成为当权士族主导共治集团的底层逻辑,由此产生新的治理死结。东晋时代死结造成的损害,主要是削弱了国家的资源动员能力,首先集中在影响统治的有效性层面。
相较于西晋皇权主导共治的西周模式,东晋当权门阀主导的君主、士族共治的东周模式,几乎是各派政治势力碰撞、角逐的结果,而非当权者主动的顶层设计。其规则包括一家门阀主导、多家士族联合专政;当权士族需要得到其他门户、名士的认可;荆扬分治、斗而不破的平衡;等等。在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琅邪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和陈郡谢氏等几大门阀发挥了重要作用。士族名士历经虚浮、放达、颓废和血泪,走向了游走于隐逸和出仕之间的黄金时代。
所谓脱儒入玄的思想转变,影响到相当部分士族的行为选择。先家后国、孝而不忠,流连于山水而醉心清谈,对现实的公务漠然,政治效率低下,国家面临危局之际不愿意挺身而出。南渡之后,士族阶层居于共治集团的主导地位,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有所回升,王导等士族领袖身上往往兼具儒玄两种气质。尤其是最富争议的权臣桓温,早期为争取士族群体的认可,曾积极参与名士的清谈活动,主政荆州后高举北伐中原的价值旗帜,抚今追昔,对名士们清谈误国的种种深恶痛绝。
淝水大战的胜利,为东晋政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打下了一剂强心针。不过吊诡的是,孝武帝取得共治集团的主导权后,却触发了宗室、士族势力之间各种矛盾。孝武帝身故不久,即发生大规模的内乱,以刘裕为代表的北府兵中下层武人取得了国家的统治权。尽管刘裕倚仗北伐的战功,使晋宋禅代貌似得到一些合法的理由,但是,刘裕野蛮杀害晋末二帝的行为,实质使刘宋政权自开国起,即笼罩在治理死结的阴影中。随着刘氏宗室自相残杀的加剧,新兴的武人集团取而代之,士族阶层回落至先家后国、为皇权背书的位置。
南朝陷入“强者得立”的政治逻辑
两晋历经西晋、东晋两个阶段,共计一百五十五年;南朝宋齐梁陈四代,共约一百七十年。如果说晋室在抗击北方少数民族的历史阶段,以新的形式取得合法性而获暂时的稳定,晋政权勉强度过了瓶颈的危机,那么南朝各代分别仅有五十年左右的国祚,没有能通过王朝的瓶颈期,始终处在合法性的挑战中。
实际上南朝各代统治者,对于治理体系中暴露出来的弊端,分别作出过一些修补,但从整体而言,这种效果相当有限。南朝相承于两晋,注定无法摆脱治理死结的宿命,其中两汉数百年构建起的儒家价值信仰,从未获得真正意义上的重建。无论是崇尚自然的玄学、追求长生的道家,还是强调轮回的佛经,尽管可以为乱世众生提供精神慰藉,却不适合作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共同遵守的伦理准则。魏晋南朝的情况,与先秦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颇有相似之处。
部分史籍将宋孝武帝刘骏描绘成淫乱暴君。其实孝武帝时期设计过优化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统治策略的系列制度,后成为南朝统治者解决士族、宗室挑战皇权的工具。其中最重要两项制度:以级别低的寒族中书通事舍人控制中枢,排斥士族高官的话语权,形成寒人掌机要的效果;派遣职位低的亲信担任诸王的典签,实际代诸王批阅公文,监视诸王、刺史一举一动,达到典签控州镇的目的。
齐高帝萧道成针对刘宋政权宗室相残,曾告诫太子萧赜,“宋氏若不骨肉相残,他族岂得乘其衰敝”。齐武帝萧赜是南朝诸代极少数依照正常顺序继位的皇帝,曾创造十余年的“永明之治”。齐高帝、齐武帝两代,严格管理宗室诸王,设置典签官越过名义上的刺史处理州政,基本上保全了宗室。
齐武帝去世后,高帝之侄、齐明帝萧鸾篡位成功,他又开始屠杀宗室,齐高帝十九子,齐武帝二十三子,差不多都被他杀光了。明帝之子 15 岁的萧宝卷即位后,相继诛灭六位辅政大臣,齐政权内部发生多起叛乱事件,迅速走上刘宋政权崩溃的老路。
梁武帝萧衍依照刘裕代晋、萧道成代宋模式,通过禅让代齐建梁,随后梁武帝在好友沈约的劝说下,派人杀害了 15 岁的齐和帝。不过,梁武帝认识到儒家王道价值对于治理体系的重要性。尽管诛杀了萧宝融等明帝子孙,但他对高帝、武帝幸存的萧子恪兄弟一脉,仍予以保全善待。梁武帝放手任用宗室子弟,取消宋齐两代执行的典签制度。只要不涉及谋反,即使犯有过错也不惩处,避免骨肉相残而有悖儒家人伦。
《梁书·儒林传》记载,梁武帝在诏书中称,“二汉登贤,莫非经术,服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晋浮荡,儒家沦歇。风节罔树,抑此之由”。为此梁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延揽当时大儒一人一馆,每馆招有数百学生。梁政权正式恢复了国学,规定皇室公卿子弟必须入学。之后陆续设立胄子律博士、集雅馆和士林馆。梁武帝自制四种弦乐器名“通”,又制十二笛辅以钟器,以正国家的礼乐。《北齐书·杜弼传》中记载,东魏实际统治者高欢曾感叹,“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
梁武帝早期曾信奉道教,即位后出于证明统治合法性的需要,大力提倡儒家思想,而对于佛教理念的认可和痴迷,则是他个人学术兴趣以及内心精神的沉淀。梁武帝写下《舍道事佛文》,宣告思想信仰上的重大转变。他和高僧大德保持交游,一起讲经辩理、注释佛经。其中注释《大品经》五十卷,完成后亲往佛寺讲经。梁武帝还示范在家居士受持的菩萨戒,为佛法的弘扬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梁武帝首倡儒家、道家和佛家三教同源,把佛教置于儒道之上,奉佛教为国教和主体,声称孔子和老子为释迦牟尼弟子,这无疑冲击了治理体系中儒家伦理的核心价值地位。
在北魏政权陷入内乱和分裂的过程中,梁武帝没有抓住历史性的机遇,先后三次北伐均无功而返。在梁武帝高度崇佛的鼓动下,南方地区大兴建寺造塔之风。他先后四次宣布出家,高调舍身佛寺,后三次朝臣共以钱四亿万将其赎回。梁武帝还过度优容宗室、士族子弟,为了安排士族职务,不惜一再增置不必要的官位。梁武帝晚年的佞佛行为和宽纵作风,造成君主专制权威下降,严重损耗了国家的人力、财力资源。
侯景发动叛乱后,仅以少量军力、七个月的时间,即摧毁萧梁中央政权。86 岁高龄的梁武帝沦为阶下囚,不久即被饿死。坐镇各地的萧氏宗王忙于兄弟、子侄内争,其中武帝第七子、梁元帝萧绎先后攻灭侄河东王萧誉、兄邵陵王萧伦等人,约请西魏宇文泰,共同讨伐割据益州的武陵王萧纪。梁元帝与宇文泰闹翻后,被岳阳王萧詧引西魏大军攻灭,出降后仍被处死。
陈武帝陈霸先时任萧梁交州刺史,在勤王之师中脱颖而出,先后击败侯景、梁元帝亲信将领王僧辩,抵挡北齐政权的南侵,通过禅让代梁建陈,不久派人把退位的梁敬帝杀死。南陈政权仅存长江以南、江陵以东的地区,但陈氏宗室内部还是充满刀光剑影。陈武帝之侄、文帝陈蒨派人把武帝之子陈昌淹死,文帝之弟、宣帝陈顼把文帝长子陈伯宗废除,从侄子手中抢夺了皇位。宣帝之子、后主陈叔宝遭其弟陈叔陵砍击,侥幸获救后,派兵把陈叔陵杀死,终于登上皇位。
宋武帝刘裕、陈武帝陈霸先得国尚有一定的正当性,宋文帝刘义隆、齐武帝萧赜和梁武帝萧衍前期,都曾提倡儒学、创造治世,但是,只要治理死结不解开,即王朝的天命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围绕着帝位继承的屠杀和血腥,就将持续不断地循环下去。这种类似“强者得立”的权力继承原则,属于北方少数民族的草原争位逻辑。中原王朝自西周政权确立嫡长子继承制,或由皇帝生前指定作为补充,已经相对制度化,这在两汉政治实践中表现
显著,成为皇权“受之于天”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自东汉晚期以来,曹氏、司马氏家族始终无力重建儒家思想、国家政权和皇帝三位一体的忠诚体系,至南朝已发展到禅代中杀害前朝君主,宗室自相残杀、新兴武人集团乘势暴力篡权的循环,皇位继承退化为“强者得立”的北方少数民族早期的治理水准。换言之,南朝政治系统自身不可能打开死结,重塑类似两汉皇权的天命。而且,南朝也无力彻底清除士族政治的弊端,始终存在着国家资源动员能力不足的严重缺陷,至南陈政权后期,其控制的土地、人口已经相当有限。源自秦汉第一帝国的南方政权,不可能重建大一统天下帝国,也逐步失去了汉民族一脉相传的正统意义。
北朝通向了隋唐
后秦政权崩溃后,司马休之等部分东晋流亡者逃往北魏。《资治通鉴·晋纪四十》中记述,“司马休之、司马文思、司马国璠、司马道赐、鲁轨、韩延之、刁雍、王慧龙及桓温之孙道度、道子、族人桓谧、桓璲、陈郡袁式等皆诣魏长孙嵩降”。此外司马懿之弟太常司马馗八世孙司马楚之,曾在刘裕代晋时聚集上万人反抗,投奔北魏得到重用,受封琅邪王、安南大将军,挫败文帝刘义隆的北伐大军。北魏统治者显然把重用幸存的司马氏子弟,作为彰显自身正统的手段之一。
淝水大战之后,源自代国的鲜卑拓跋氏政权重建。北魏政权一边积极从事统一北方的战争,一边不断地通过制度改革,继续探索少数民族统治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道武帝拓跋珪采取离散部落的统治策略改革,以及制定子贵母死最高统治者继承的野蛮规则,完成了北魏国家从部落联盟向专制皇权的过渡。
北魏政权治理体系全面改革,始于孝文帝嫡祖母冯太后。所谓实行官员俸禄制、考课制,其实是要改变北魏政权文武官员早期依靠战争抢掠、搜刮百姓的自肥方式,回归中原王朝正常的国家治理。北魏政权又推出影响深远的均田制,即政府把掌握的大量荒地,分配给失地的农民,收取一定的户调和田租。
根据均田制的规定,男子十五岁以上,授给露田十亩,桑田二十亩,妇人授露田二十亩。露田不得买卖,身死或年满七十归还官府,桑田则为永业,一定条件下可以买卖。奴婢和耕牛参加授田。田地缺乏地区,允许农民迁至他郡。北魏国家实行新的租调制,原先依附、流亡人口大量存在,负担租役的基数较少,一般民众负担较重。新的租调规定以家庭为授田交赋单位,一夫一妻出帛一匹,粟二石,其他人口、耕牛以此类推。《魏书·食货志》中记载,“事施行后,计省昔十有余倍,于是海内安之”。
随即北魏政权推出与均田制配套的三长制,即“五家立邻长,五邻立里长,五里立党长,取乡人强谨者为之”。其实是国家重新介入小型的自治共同体,是秦汉政权时代编户齐民法家方法论的恢复和再现。均田制、租调制和三长制连续改革,使北朝政权获得了南方无法抗衡的资源动员上的优势。
孝文帝拓跋宏亲政后,发起了超越前秦天王苻坚的全面汉化激进政策。孝文帝完全仿照汉族君主的礼教程序,建造太庙和明堂,祭祀华夏先贤舜、禹、周公和孔子,强行实施迁都洛阳的计划。迁洛之后,孝文帝下诏禁止士民穿胡服,命令鲜卑人和其他少数族人全都改穿汉服,官员上朝必须着汉族官员标准朝服。随后宣布禁绝鲜卑语和其他少数族群语言,一律改说汉语,规定迁洛的鲜卑官民,死后葬于河南而不得还葬平城,籍贯全部改为河南郡洛阳县人。
孝文帝曾大会群臣于洛阳光极殿。按照中国传统颁赐官帽朝服,文武百官依礼而立,仿佛穿越回汉魏西晋的时光。孝文帝随后下令,改鲜卑复姓为单音汉姓。以北魏祖先出自黄帝、土德黄色为万物之元的理由,率先将皇族拓跋氏改为元氏。孝文帝仿照魏晋时代士族门第等级的模式,在鲜卑贵族中分姓定族,将军功、官爵作为制定姓族的标准,根据姓族等级高低分别授予不同的官位,和汉人士族的郡姓合为一体,郡姓还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等级。中央政权必须依据门第等级选任官员,形成了北魏政权独特的门阀制度。
孝文帝站在坚持北魏政权相承两汉、魏晋正统的立场,品评汉人士族姓第时,考虑先祖的功绩,并且把魏晋时代士族门第传统全盘接收,完全是出自营造受命于天的合法性需要。这和孝文帝设立太学、国子学和四门小学,始终将儒家经典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其思维方式和心理逻辑一致。
北魏沿袭后赵、前秦等少数民族的统治策略,即以鲜卑民族军功贵族、国人武装支撑起鲜卑民族对于其他多数民族的皇权统治。孝文帝通过汉化文治而改变,重用中原儒士治国,内迁的鲜卑贵族尚适应了奢华的生活,但作为特权阶层的边地鲜卑将士上升的空间被大为抑制。孝文帝去世二十年后,平城以北为抵御柔然设置的六大军镇的鲜卑兵民,爆发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从表面上看,六镇起义,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反汉化的潮流席卷而来。更深一层观察,更多边地少数民族军人进入中原,进一步促进了北方的民族大融合。特别是西魏权臣宇文泰通过鲜卑化的形式,把占人口大多数的汉人纳入国人武装范围。
宇文泰带到关中平叛的鲜卑部众较少,当地多为氐、羌部族以及大量汉族乡兵。宇文泰推行府兵制改革,即模仿鲜卑八部设八大柱国,除宇文泰及宗室元欣以外,其他独孤信、赵贵、李虎、李弼、侯莫陈崇和于谨等六柱国亲自带兵。每位柱国统领两大将军,共十二位大将军、四万八千兵士。宇文泰进一步恢复鲜卑姓氏,本来汉姓者赐以鲜卑姓,之后成为隋室先人的杨忠赐姓普六茹氏,唐室先人李虎赐姓大野氏,凡统率士兵皆以主将的鲜卑姓为自己姓氏。这些措施照顾了鲜卑军团中反汉化的情绪,以鲜卑部落兵制的形式,组成维护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府兵。
宇文泰推出汉族士人苏绰、卢辨依据《周礼》制定的新官制,舍弃魏晋以来官职名号,适当参考秦汉官制,依照先秦时西周政权设立中央组织体制官职。《资治通鉴·梁纪二十二》中叙述,“魏初建六官,以宇文泰为太师、大冢宰、柱国,李弼为太傅、大司徒,赵贵为太保、大宗伯,独孤信为大司马,于谨为大司寇,侯莫陈崇为大司空,其余百官,皆仿《周礼》”其实这并不是简单托古改制,而是从关中古代政治制度中寻找统治的合法性,从儒家思想的源头周礼中,整合关中本位各民族共同的价值认同。
陈寅恪先生认为,宇文泰以鲜卑部落旧制为依归,建立有贵族性质的府兵制,改易府兵将领的郡望和姓氏,并使之与土地结合,是要建立起足以与东魏、梁朝相抗衡的强有力的关陇集团。宇文泰关陇本位政策的另一个表现,是关陇文化本位政策,为了对抗高氏和萧梁,必应别有一个精神上独立的、自成系统的文化政策,以维系关陇地区胡汉诸强的人心,使之成为一家,从思想文化上巩固关陇集团。
至此,形成于西魏、北周的关陇军事贵族集团,已经大致取得了统一天下的资源优势和天命合法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胡汉杂糅、军政合一的体制中,人口、文化享有优势的汉人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奠定了隋唐民族大融合新兴皇权的基础。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盖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承接于两晋、作为秦汉大一统政权残余的南朝,最终被北朝、隋唐帝国整合。
两者相比,魏晋南朝承袭具有强大天命的两汉,通过禅让的名义进行改朝换代,其合法性评价的艰难可想而知。北朝政权实际上源自游牧民族部落,反而没有历史的包袱。其向中原王朝政治系统的靠近、学习和复制,即士族认可其合法性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其统治的有效性,就是其合法性最重要的来源。
虽然隋朝重现天下大一统,依然未能摆脱类似南北朝短命政权的宿命,但是,同出关陇集团的李唐皇权后来居上。唐太宗李世民虽通过“强者得立”的草原规则夺位,却以他个人的君德、贞观之政中民本位的价值,重建了士民对唐政权的忠诚,又被草原各族拥戴为天可汗,成为魏晋以来治理体系死结效应的阶段性终结者。
——选自沈刚《晋朝的死结》,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8月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