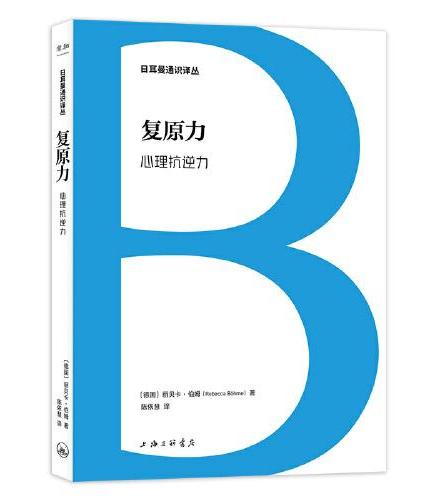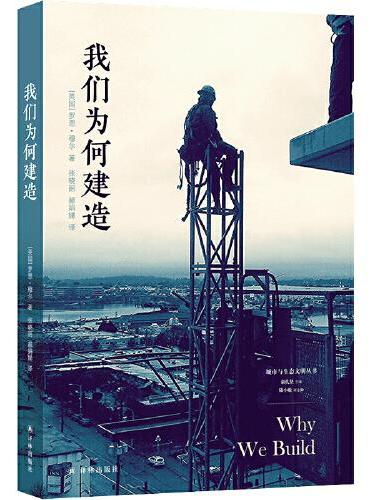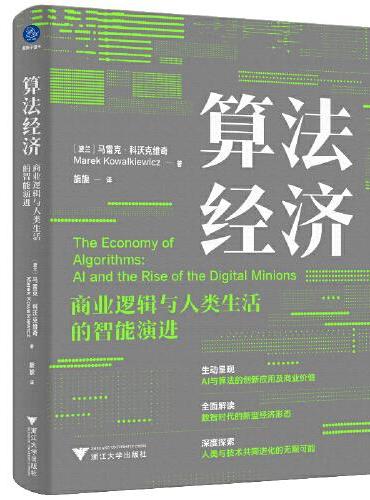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没有一种人生是完美的:百岁老人季羡林的人生智慧(读完季羡林,我再也不内耗了)
》
售價:HK$
5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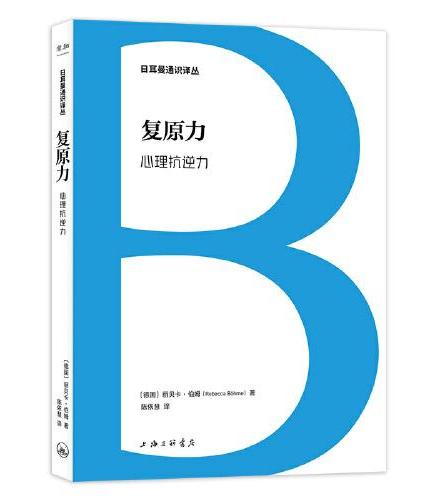
《
日耳曼通识译丛:复原力:心理抗逆力
》
售價:HK$
34.3

《
海外中国研究·未竟之业:近代中国的言行表率
》
售價:HK$
13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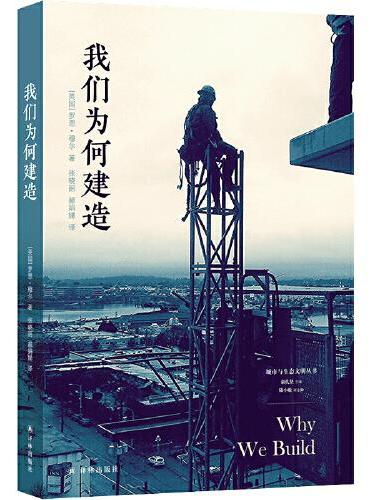
《
我们为何建造(城市与生态文明丛书)
》
售價:HK$
8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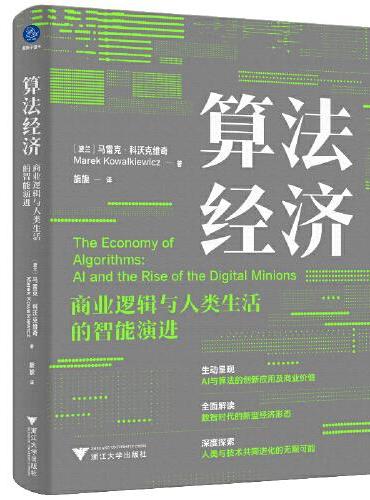
《
算法经济 : 商业逻辑与人类生活的智能演进(生动呈现AI与算法的创新应用与商业价值)
》
售價:HK$
79.4

《
家书中的百年史
》
售價:HK$
79.4

《
偏爱月亮
》
售價:HK$
45.8

《
生物安全与环境
》
售價:HK$
56.4
|
| 內容簡介: |
|
本书是一部长篇都市情感小说。离了婚却没有离家的老何、想离婚却一直没有离婚的老徐、不想离婚却不得不选择离婚的老莫三个人互为多年老友,三人事业发展顺利,可是各自的感情状态却越来越糟糕。于是他们三人相互帮助,终于让三人都得到了各自想要的生活。原以为之后的生活会更加轻松,没想到事与愿违,三人发现原来的生活才是快乐的,是最轻松的生活状态。于是三个人拼命想回到过去,但是均无挽回的可能了。他们三个人开始懂得自己原来很幸福,却不珍惜。之后,老何终于发现前妻一直在默默给予自己温暖,老莫和老徐也认识到了家庭的重要,事已至此,大家都学会了坦然面对生活里发生的变故,三个老朋友开始了新的人生旅程。
|
| 關於作者: |
|
张苏逸,编剧,导演过多部微电影广告,为方中信、陈建斌等明星创作大量广告剧本。出版有长篇小说《锋利无比》《整形术》《亲密的关系》,并创作院线电影《愤怒的牦牛》《全城危急》等剧本作品。
|
| 內容試閱:
|
第一章
一九八三年二三月间,这最为平常的日子,在湫隘村郭身田看来,却真是让人愁肠百结不好过的坎。这天,细蒙蒙的雨丝夹着一些细盐粒般的雪子,正淅淅沥沥地向土地、村庄、森林和小河飘洒着。时节快到惊蛰了吧,雪当然再也不会存留,往往还没有落地,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皖南,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已经过去,但温暖春天的到来还得有些时日。
在这样的天气里,如果没有什么要紧事,村民们宁愿一整天窝在家里不出门。因此,本来就比较小的村庄里比平时少了许多嘈杂,时不时谁家的狗汪汪叫几声。村庄靠山边背阴的地方,冬天残留的积雪和冰溜子正在雨点的敲击下融化,村里的黑泥土小路上漫流着乌黑的泥水。风,依然是寒冷的。空荡荡的村庄里,偶尔走过来一个人,缩着脑袋,用双手捂着两只耳朵,嘴里哈着热气,匆匆而过。这时的农村几乎没有什么生气,更没有一点书里描写的那种山水田园之美的感觉。
在这样的天气和日子里,湫隘村的郭身田一家,可是最没有生机、没有生活味道的,一家人被笼罩在死一般的寂静里。这天早上,郭身田的老婆水莲端了一碗面条走到郭身田的床前,看着蒙头睡得纹丝不动的丈夫,轻轻拍着被头,喊道:“身田啦,起来吃点东西,你睡了两天三夜了,老这么睡着也不中嘛!”郭身田窝在被子里,像一条蚕一样蠕动了一下,没说吃,也没说不吃。这就难了水莲。水莲嫁到身田家快二十年了吧,她对身田的品性、为人都还是了解的。身田是一九六五年的初中毕业生,那年考上高中,因家里孩子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父亲又有病,他只好放弃读高中的机会,回村帮着家里挣工分养家糊口。在湫隘村,身田算得上是“高级知识分子”、文化人,自然很受村人的尊重和抬举。无论村里哪家遇到难事,身田都是有主意的,因为他了解时事政治,通晓乡村事理,遇事能从头到尾分析得透彻。但是,这次身田连睡几天几夜不吭不哈,屁都没放一个,水莲心里知道,身田这回真摊到事了,估计一时半会儿是拿不定主意的。愁啊!水莲知道他的心思,也不好多嘴。她心想,这时最好的办法就是静静地坐在身田床边陪他。
不知过了多久,身田在被窝里拱了拱,发出了一声微弱的声音:“这天,还在下着雨?”“下着哩,雨夹雪子。”水莲回话。又是死一般的沉静。房子里更是寒气袭人,水莲打了一个冷战。“唉!”身田在被窝里滚了一下,叹了口气,露出半张脸来,对水莲说,“我真的不晓得怎么搞了,难死我喽!”水莲说:“身田啊,有什么事能难着你呀?我家老板是有本事的人,难不了你的,我们坐起来好好商量。”身田咧了咧嘴,露出上下两排黄牙,没有接话,也没有坐起来。水莲又说:“身田,你恐怕是在想老巴子的事吧?”身田听了这话,用手把被子头捋一捋,露出整张脸来,眼睛亮了一下,哼哼道:“知我者还是我烧锅的啊。”水莲赶紧趁热打铁接着话头说道:“这些年,我都成你肚子里的蛔虫了,我这么猜呢!”身田又咧咧嘴,那意思是水莲真的知道他的心思,也知道这苦是从哪里生的根发的芽。
身田慢慢地又有几分艰难地坐了起来。水莲赶忙给他披上破棉袄,又给他掖了掖被头,轻轻说:“你坐着,我去给你把面热一热,我们吃点东西再盘算盘算吧。”身田点了点头。
要说郭身田难,也实在是头一回头一等难事摊到他头上了。身田的母亲在上个月过世了。其实母亲过世说来也是平常事,母亲岁数不算多大,害病去世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郭身田在家排行老二,男孩子里头是老大,上头一个姐姐,比他大两岁,下头一个妹妹,比他小两岁,再下头是一个弟弟,最后一个小老巴子。现在事就出在小老巴子身上。
要说这个小老巴子弟弟嘛,真算他命大。话要从那年大姐出嫁说起。那年大姐出嫁不久就有喜讯传回家,说怀上孩子了。喜讯报回家,一家人自然高兴得很,可是母亲同时发现自己也怀孕了。这怎么可能呢?母亲都多大岁数了?开始母亲半信半疑,又不好意思声张。于是有一天,母亲一个人悄悄去邻村找郎中瞧。那郎中把三根指头搭在母亲手腕上移动了一会儿,抬头眯着眼看着母亲说:“郭家婶子,从脉象看,我要恭喜你,你家又要添丁进口啦。”母亲用呆滞的目光看着郎中,说:“当真?”郎中不悦了,说:“哎,郭家婶子啊,我一行医之人何时开过玩笑?”“不不不,”母亲赶忙改口说,“要真是的话,这小伢子来得就不是时候嘛。”郎中就说:“嗳,哪里的话?多子多福嘛。回家好生调养,别苦了你自己,又苦了这小伢子啦。”
母亲回家滴水不喝,粒米不进,一睡就是两天两夜,吓坏了身田的父亲。父亲慌得给她喂水喂饭,见她不张嘴,以为这下自家烧锅的病得厉害了,就要疯急着抬她上公社卫生院。母亲像鼻涕虫一拖好长地摊在床上就是不起,不耐烦地朝父亲嚷嚷:“得绝症啦!没法治的!”父亲找来大女儿、大女婿,二女儿还没有出嫁,身田是男丁中的老大,也明事理了,二弟小一点,没让他参加。父亲和一家人商量为母亲治病——再穷病不能不治。一家人商量来商量去,母亲哇的一声哭了,说:“治个屁呀治,我带上啦!”皖南通常把怀孕说成是带肚子。一家人当时都呆了:“怎么可能呢?”“怎么不可能?”父亲说,“人家外国有五六十岁的女人还怀孩子呢,你们母亲五十不到,怎么就不可能带肚子呢?”一家人从极度恐慌中恢复了平静。二女儿调皮一些,逗母亲说:“妈,好事嘛,你和我姐比赛生小伢子咧,看你们俩哪个过劲。”母亲很是难为情,骂道:“你个鬼小伢子耻笑你老娘。”这一说,把全家人给逗得哄堂大笑。不过话又说回来,在农村,母亲和女儿同时怀孕生孩子的事听说过不少,也不算什么丑事。但真要是轮到哪个头上,哪个都是极其不情愿的,毕竟这在十里八乡也算是件稀罕事,被人当茶余饭后的笑谈一桩,讲起来也够难为情的。
没隔多少时候,糟糕透顶的事发生了:父亲因为害痨病,丢下一家大小人撒手归西,这等于家里的房梁轰然坍塌了。母亲失去丈夫这个家庭顶梁柱后,看着自己渐渐鼓起的肚子,一下陷入了绝境,感觉日子到头了。父亲下葬的那天,母亲到了失控的程度。她哭闹时爆发出空前的体力,在坟地里一会儿跳老高:“冤家啊,你走了干净了,留下我怎么活嘛!”一会儿又倒地四仰八叉,“你个死鬼啊,你干的好事啊!”接着就是打滚放赖,跳啊滚啊地说,“你留个小讨债鬼给我嘛,我哪块能养得活嘛!”谁也拉不住她,那架势,非要跟父亲一道拱到土里才成。
母亲那个绝望啊,眼前就是一堵墙,走不下去了,没办法过去这个坎了。她想啊,肚子里的小鬼不给闹腾得流产掉,生下来怎么活?可这么自己糟蹋自己好几天几夜,肚子也没有瘪下去。后来母亲又想了更狠的办法,定要把肚子里的孩子给流了,万万不能生下来。她在床上用裤腰带死死勒着肚子,要把肚子里的小鬼给闷死掉,让小鬼胎死腹中。可勒着勒着手又松了,不知怎么回事,她心里就有一个声音:“勒死了,勒死了……”就下不去死手了。后来她又一个人在房间里瞎蹦乱跳,用拳头敲打自己的肚脐眼,结果也没有成功。母亲想起父亲,又悲痛,又伤心,格外生自己的气:怎么一下子就给带上了?这么个年纪了,让人笑掉牙啦!母亲那天下了狠心,在一个夜深人静的夜里,提前把家里要做的事都做了,要整理的衣服也整理好,分门别类地放在旧木箱里。她拿来早已磨得锋利的剪刀,坐在床沿上,掀开衣服,露出鼓得山包一样的肚子,把锋利的剪刀对着自己肚子,打算与这个没有出世的小讨债鬼一起走,去找那讨债鬼没见面的父亲。母亲紧闭上眼,狠狠咬着牙,抄起剪刀对着肚子就要狠劲捅下去。当剪刀尖刚触到肚皮时,肚里的小东西忽然动了一下,她的手一顿,剪子咣当一声掉在了地上。母亲再也控制不住了,想想要带着不知男女的讨债鬼一起就这么死去,她撕破了嗓子,拖长的声音像天空中划过的一声响雷:“我的个儿啊……”她伏在床上泪流满面,鼻涕眼睛水顺着面颊流到下巴,又顺着颈子流到山包一样的肚子上。想想这一辈子生儿育女,吃尽苦头,最后竟要以这样的方式离开人间,又想到大女儿都出嫁了,马上要生儿育女,二女儿也不小了,正在张罗找婆家,大儿子身田也正在处着对象,小儿子还在念书。这一件件等着她这当娘的拿大主意的事情在眼前一幕一幕映出,挥之不去。她转而又想,家里本来穷得没人上门,老鼠来家都吃不饱,这要再生下这么个讨债鬼,往后还过什么日子?母亲无力地哭着喊着,哭声里,有感到对不起没见面的小伢子的意思,又有自己劝自己的意思:这又何苦呢?小伢子在肚里已经长成了,是娘身上的肉,与娘心连着心哪。就这样,在那一年,母亲与自己的大女儿身耕前后不差几天,各自生下了孩子。母亲生的是男孩,取名身土。大女儿身耕生的是女孩,取名明好,意思是明天会比今天好。听闻身土出世,村里老人们都说,这孩子天生命硬,长大后不是个人物也是条硬汉。
这样一个遗腹子降临在这个家庭,到底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好歹家里又多一个男丁,长大后成大器倒不指望,只要不成为社会的祸害,日后在生产队孬好也是一户,这样郭家在村子里又多了个户头,你不去欺负别人,那别人也不敢轻易欺负你。农村嘛,哪家门头高、人丁旺,特别是男人多,别人说话行事也是要看看脸色的。这么一想,母亲对这不该来的小鬼倒生出些许欣喜。忧的是,家里多口人,这一日三餐吃喝、春夏秋冬穿衣,都是刚性开支,节省不掉。父亲去世后,家里少了一个整劳力挣工分,收入减半,这时又添丁进口,明摆着日子难挨!
母亲本就是苦班底出生,知道一分钱掰成两半来花,田里一把地里一把,一把屎一把尿地拖着讨债鬼身土抓着日子。母亲善良,为人淳朴,善解人意,在方圆几十里口碑都好,尽管一个女人把持一家大小人度日,但十里八乡的人并没有瞧不起这一家,有的还多多给予关照。日子过得很苦,但也算顺畅。二女儿身勤到了婚嫁年龄就有人上门提亲,不久嫁到城边一户菜农家里,住在县城旁边,做点小生意也方便,家里总也有些零用钱,算是从糠箩掉到米箩了。大儿子身田初中毕业,在生产队算得上是知识分子,脑子也比别人活泛一些,说话办事稳当有条理,社员们都高看他一眼。在农村,这样的年轻男子不怕娶不到老婆。在好心人的撮合下,他与城东圩乡的水莲姑娘结了婚。二儿子身本也念完了初中。这个家庭在母亲的操持下,每个阶段性的任务都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就是在一些父母双全的农村人家,也未必能做到这么顺畅。
话又说到身土。自从先后把大儿子、二女儿的婚事一一办好,帮大儿子盖了三间茅草屋分了家、立了户,把二儿子身本送去学木匠,母亲就一门心思带着身土过日子了。母亲凭自身能力,也只能像养小猪一样,让身土吃山芋,咽洋芋,嚼蔬菜,喝稀粥加面糊糊,饱一餐饿一顿地糊着个嘴,一年到头不到过年过节也很难吃顿荤。自打身土会走路,他就整天跟在娘的身后,在田野,在山地,在菜园,在山林……早上头顶星光,晚上身披月光,一高一矮的身影在山村形成一道游动的剪影,一幅苦苦相依着往前走的农人水墨画。他自己也时常会在地里偷条黄瓜往身上擦擦塞进嘴里,爬到树上摘下不熟的果子就啃了;冬天冻得像个活猴子瑟瑟发抖,鼻涕拖老长;夏天浑身泥巴,只剩两只眼眨巴;吃饭从不洗手,屙了屎抓起土疙瘩蹭蹭屁眼了事。就这,他从小到大没生灾害病,长得敦敦实实。母亲看身土一点点地健康长大,养的过程怪省心,心里油然生起喜滋滋的味儿。母亲还渐渐地发现身土与同龄的孩子有点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他的小脑瓜比人家活泛得多。黑黑的眼珠溜溜转,长长的睫毛一眨巴、小眼角一睃就有个鬼主意,学个什么事上手也快。还有就是他记忆力特别好。他记性好到什么程度,也没有哪个人能拃着手指测量一下,只晓得他只要听见人讲前朝后世的事情,一遍他就记得清清楚楚了。农村里也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只有在农闲时,少许走村串户的民间艺人,如说大鼓书的、唱小戏的到村里说唱,那就是好热闹的事了。特别是那说大鼓书的,村里大人小孩见了像疯了一样,撵在人家屁股后面一遍一遍地听。一场书听下来,别人只是图个热闹,而身土就记住了。说书的人一走,身土拿着小木盆当鼓敲,学着人家一字不落地说唱,比那真正的说书人还像说书人。村里人说,这鬼小伢子,奇人。有年一个说大鼓书的看中了身土的天赋,要收他为徒,纳为义子。身土呢,巴不得跟着师父去走南闯北过快活日子。别小看这说大鼓书的,学好了,那也是一门绝活,到哪里都可以混口饭吃。
身土愿意,家人也动过心。怎么说,这说大鼓书也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活,没点脑瓜子的人是不中的。人家看中了身土,也说明他有这个天赋。一家人商量来商量去,到底还是不愿意。理由之一,说大鼓的本就是居无定所的人,游走乡间,吃百家饭,说得难听些,这就是个要饭的。不行,这等于是把身土小小年纪就送出去讨饭,说出去高低不好听啦。理由之二,身土这小小年纪就走上这么一条路,靠走村串户浪里浪当地混日子,等于从小就不务正业,肯定会把前途毁尽。农民本来就没个前途,但种田种地毕竟是正业,姑娘能看上老实本分的种田种地的人,很少能看上做这么个行当的人。就这样,身土没有去学说大鼓书。教育培养身土这个沉重的担子落在了母亲肩上。如今再怎么吃苦受累,首要的是想方设法让身土去学堂念些书。母亲是个要强的人,也放了狠话:“只要他能念得进去书,就是砸锅卖铁、剐肉卖血,也得让这小伢子念下去!”话是这么说的,母亲有没有砸锅卖铁没看见,是不是真卖了血,有说卖过,有说不肯定。但母亲吃了多少苦,又是如何艰难度日的,这里不说也能想象得到,不说也罢。
身土的不幸降临了:就在前不久母亲病逝了。据说这病早就得上了,没钱治。农村人有了病,一是拖,二是抵,三是扛。命大的,不是绝症,但凡过了这三关还真扛过去了。如果是要紧的病,且是慢性病类,这三关越过越重,最后就是一个“死”字。身土母亲得的据说是腰子(肾)病,最后是拖成了尿毒症死的。
大哥身田从母亲生病直至去世,也尽到了儿子的气力和孝心。母亲在临终前,拉着他的手,有一句没一句地交代:“身田啦,妈舍不得的还是小老巴子,他到底还是太小,不能自立……妈一辈子是个没用的人,你那死鬼大临死了还丢下个身土给我,我也尽力了,今天再也拖不动了。我走后,你是大哥,老巴子还得拖累你,你再难,也要好好把他拖大成人,不行的话,找个愿意收留的人家送了吧……”母亲说着说着,头一歪,眼一闭,手一松,腿一伸,走了。
可怜的母亲命苦啊,活一辈子也没有享过一天清闲。母亲是摔倒在自家菜园子里,被人发现后抬到床上的。一直到闭上眼睛,她的眼泪还挂在两腮未干,裤腿上还沾满了黑土和人畜粪。身田看着可怜的母亲,死时躺在病床上,缩成了一只大老鼠那么点大。她像耗干了全部水分的干树枝,连眼泪也成了挂在橘皮一样的脸上的两道干痕。
身田日子虽苦,但孝心是有的。他要风风光光地把母亲送上山,认认真真让母亲入土为安。他按乡俗从很远的沙滩角村请来了有名的徐山人,中规中矩地给母亲做了三天三夜的斋,想母亲在人间受尽了苦,祝愿母亲到了阴间能做个有福之人。然后请了锣鼓乐队,借了唢呐和音响,吹吹打打,抬着母亲的灵柩热闹轰天地送到了自家自留地里,挖坑,挑土,采青草皮,把母亲的坟捶打捶打,装点得高高大大、新新崭崭。这么一阵累过、忙过、哭过,身田回家一头扎到床上,一睡两天三夜,泪水鼻涕流了再流,眵目糊抹了又生,生了又抹,在被头上擦擦。睡下去的头天,还睡着了一会儿,后头几天就只躺在床上,根本睡不着,心里要想的东西太多了。
身田想啊,自从二弟身本出去跟人学木匠后,母亲带着小老巴身土,虽然有些孤苦伶仃地住在三间茅草屋里,但有母亲,身土就有家。身土今年十四岁了,一直由母亲拉扯着,饱一餐饿一顿,但总还有点日子过着。身土聪明,今年念初中二年级了,明年怎么着初三也是要念下去的。母亲如果健在,这些事身田这个当大哥的自然就少操好多心。如今母亲这么离去了,他当大哥的,看着不成年的老巴弟弟,不能不管!可管,又怎么个管法呢?身田自己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只比身土小一岁,在念初中一年级。三个男孩子,眼看一个接一个长起来,都正值饿狼觅食的年纪,又都是要念书的年纪。他和妻子水莲俩,就像一架破板车,拉着日子一步一步负重爬坡,本来就是一步一滴汗水的,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歇步了。这下再加上这么个老巴弟,你想想这日子怎么过?身田内心当然对母亲的离去感到很难过,更主要的是活着的让他焦虑不安。他反复琢磨着母亲临终前说的“找个愿意收留的人家送了”,话是这么说,可是,哪里有愿意收留身土的人家啊?这愿意收留身土的人家,至少要让身土念完初中吧。另外,这个人家要有个女孩子和身土差不多岁数,有找个男孩入赘为婿的意思,否则谁家愿意收留呢?穷的人家养不起,富的人家看不上。
身田在心里盘算,如果不把身土送走,身土书就念不成了。他自己三个儿子一个接一个地往学校送,你说叫他们兄弟仨哪个不念书,让小叔叔去念,孩子长大后不恨死你这个做大的?若仨人都继续念,再加上身土老弟,四个人念书肯定不成,负担不起。再说啊,就算让身土念完初中,他不过十四五岁,让他独自生活在老屋里,田里地里、山上水中地去讨生活,也太难为他。如果和自己吃住在一起,四个勃勃生长的男子汉,将来要一个一个地帮他们娶妻做屋分户,这是一般人能完得成的任务吗?就他身田的三个儿子,将来长大成人是个什么样子,自己能不能为他们一个个做上房子,娶上媳妇,都是个未知数。
身田越想越难,越想越感到生活没出路。身田在心里想,自己这辈子是没有什么指望了,再苦再难,也要把三个儿子和一个老巴弟弟带大成人,他们中能有个有出息的最好,如果都像自己一样没有什么出息,也要让他们都成上家。尤其是可怜的老巴弟弟,母亲去世后,他的眼神中流露出的是无助,甚至是绝望,整日待在那三间祖上留下来的旧茅草屋里足不出户,一个十四岁的少年,看上去比四十出头的男人还沉默憔悴。身田想,自己如果不尽快有个方案,恐怕这老巴弟弟会抑郁成疾,那时这个家就真倒摊子了。
身田心里的苦楚,妻子水莲自然晓得些。晓得归晓得,也没个主意好拿。所以,水莲安慰着说:“身田啦,有什么就吐出来,别在心里憋坏了。要不请大姐和二妹回来一趟,拿拿主意?”身田说:“是要和她们商量。可好多事是老娘临终前单独对我说的,今朝我拿不出一个主张,就是让她们回来也顶不了用,她们晓得哪个篮子里装的哪个菜啊?”“讲得也是。”水莲嘴里咕哝着。
这一天,身田从自家菜园子回来,叫了水莲说:“你过来一下。”水莲从灶屋里边搓着手边走出来: “有事?”“有呢。”身田说着又朝水莲看了看,“我明朝想出趟门,恐怕后朝才能回。”水莲说:“出门去?中啊,只是想去哪块?身上要揣几个钱啦!”身田说想去一趟梅都何村。“梅都何村?”水莲说,“这个村在哪块?怎么没有听说过?”身田就说:“你哪块晓得这个村啦?我的脑子里都模模糊糊的,那是我奶奶娘家的村,是个有名望的村子,是日子比较好过的村子。奶奶娘家在那块有一个亲戚,按辈我应喊他表姑爷,奶奶在世时我们还走动。小时候我跟奶奶去过。”“哦。”水莲明白了,“那你今朝去他们那块是有什么事吗?” “有的。”身田说,“打算找找表姑爷,去瞧瞧吧,回来再跟你细讲。”
身田出门那天,身土从学校回来问嫂子:“嫂嫂,大哥呢?”水莲说:“你大哥有事出门了。身土有事找你大哥说?”身土说:“没的事,就是我下个学期不念书了,回来帮大哥大嫂讨生活。”水莲说:“巴子你不许瞎想,好歹都听你大哥的。好生吃饭,吃过饭好生写作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