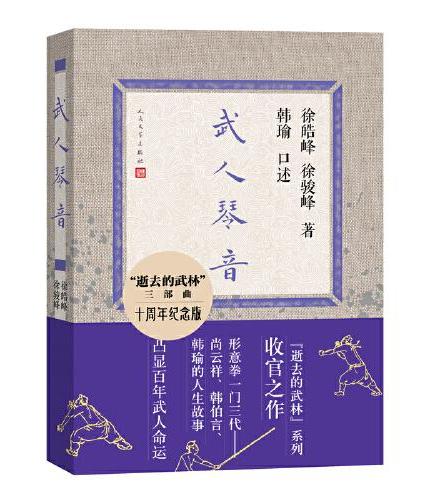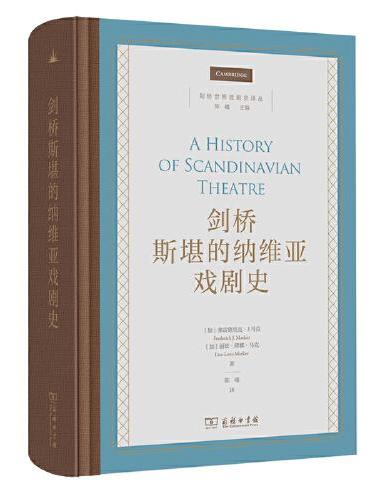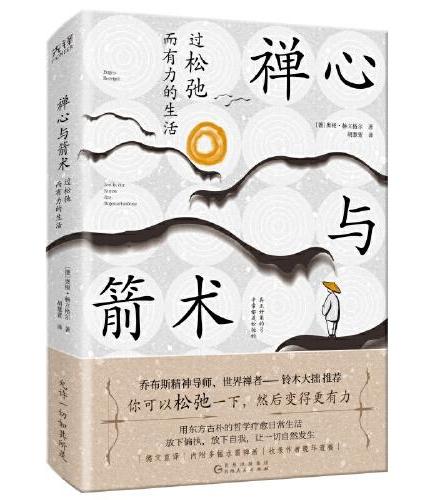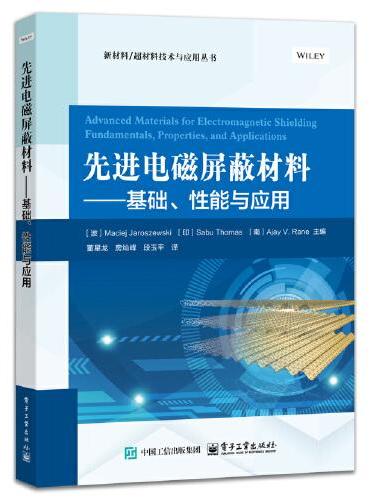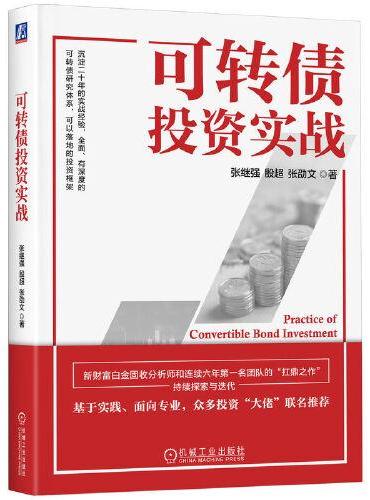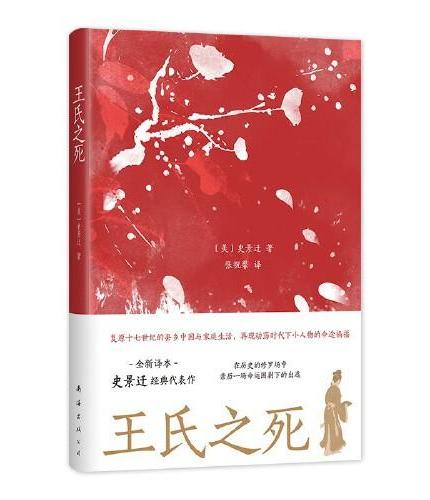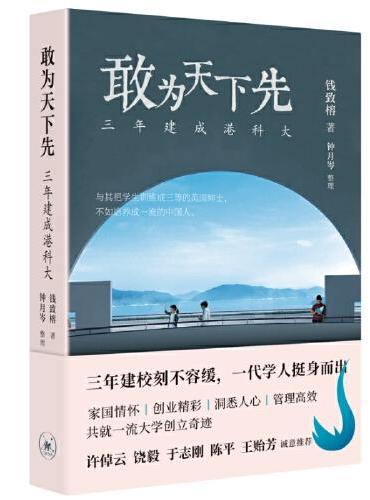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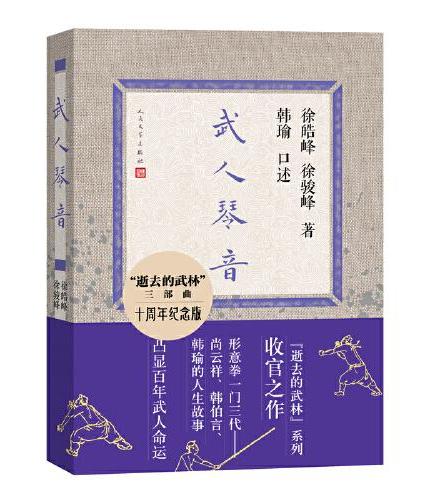
《
武人琴音(十周年纪念版 逝去的武林系列收官之作 形意拳一门三代:尚云祥、韩伯言、韩瑜的人生故事 凸显百年武人命运)
》
售價:HK$
4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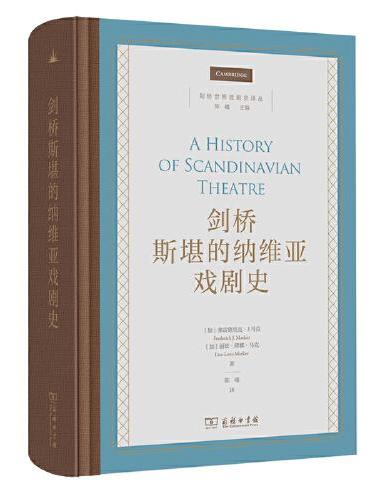
《
剑桥斯堪的纳维亚戏剧史(剑桥世界戏剧史译丛)
》
售價:HK$
15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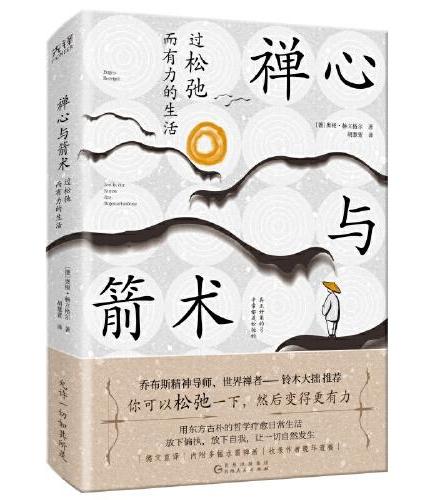
《
禅心与箭术:过松弛而有力的生活(乔布斯精神导师、世界禅者——铃木大拙荐)
》
售價:HK$
6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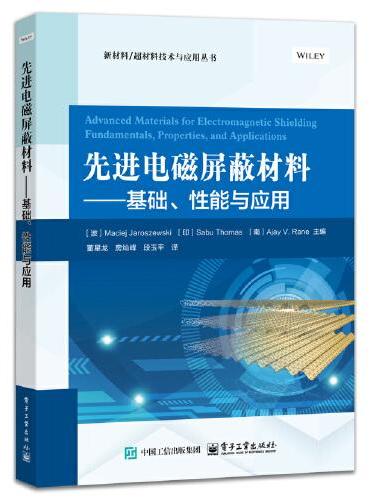
《
先进电磁屏蔽材料——基础、性能与应用
》
售價:HK$
2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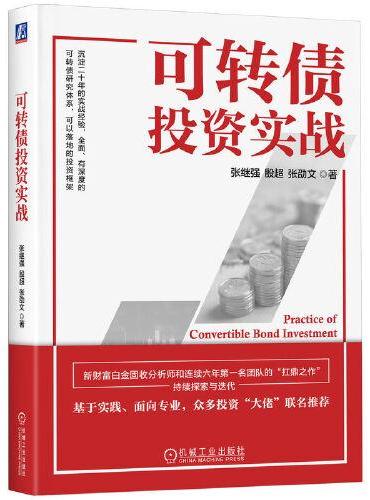
《
可转债投资实战
》
售價:HK$
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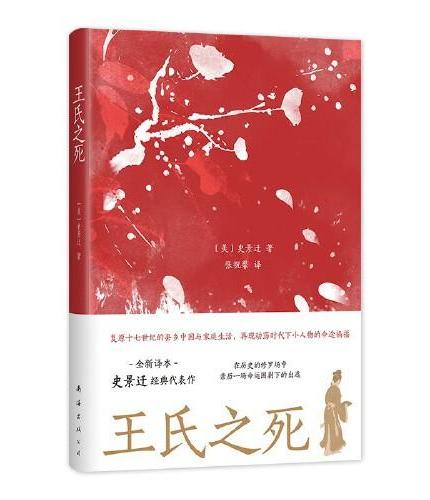
《
王氏之死(新版,史景迁成名作)
》
售價:HK$
5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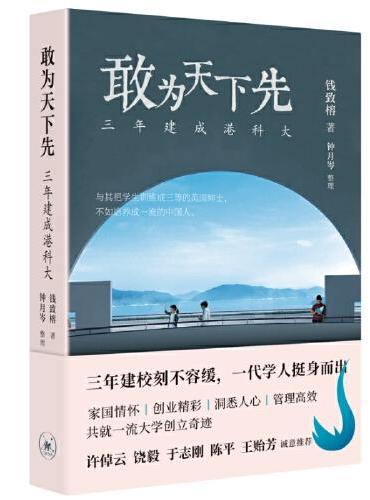
《
敢为天下先:三年建成港科大
》
售價:HK$
77.3

《
长高食谱 让孩子长高个的饮食方案 0-15周岁儿童调理脾胃食谱书籍宝宝辅食书 让孩子爱吃饭 6-9-12岁儿童营养健康食谱书大全 助力孩子身体棒胃口好长得高
》
售價:HK$
47.0
|
| 編輯推薦: |
1、牛津现代欧洲史系列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奠定系列品质格调
本书是牛津出版社现代欧洲史系列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本,在欧美学术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奠定了牛津现代欧洲史系列品牌极高的学术格调,甫一诞生,就被誉为未来多年历史研究标杆作品。
2、作者是业内公认顶尖级学者,学术水平权威
作为众多历史专业奖项的获得者,乔纳森·伊斯雷尔既受到英语世界历史业内的赞美,又受到荷兰本土历史学界的赞同与认可,他对历史脉络的把握与解析,以及对历史事件的复现让作品超越枯燥记录本身,让读者近距离跟随文本,体会时代激情。
3、历史记录广泛全面,展现清晰的时代脉络
作者对于时代特征的把握娴熟而精准,对于一手资料的搜集和分类有超凡的汇总能力,同时对历史有其独到见解。可为对“荷兰共和国(尼德兰联省共和国)”这个国家以及这段历史毫无概念的读者系统性地搭建相关历史知识构架,有助于理解其他相关荷兰史著作。另一方面,也能与欧洲近代崛起的其他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互作信息补充与照应。
4、以学术角度,系统解析荷兰共和国历史
市面上关于荷兰共和国的众多作品中唯一一本以思想史角度出发,全面记录荷兰共和国历史的著作。作者在本书中难
|
| 內容簡介: |
本书是一部全新角度的300年荷兰共和国史,首度全方位解析荷兰共和国从酝酿到衰落的全过程。
全书共分四大部分,分述各时代荷兰地区的发展历程。1477—1588年的共和国奋力摆脱勃艮第的控制,在唤醒自我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的过程中燃起一片宗教改革与大起义狂潮。1588—1647年,处于黄金时代早期的共和国不断寻求抗争西班牙统治的道路,在意识形态上陷入大辩论,在权力的对峙中磨合出宗教宽容政策。1647—1702年,航海贸易的大发展,让八十年战争后的共和国在诸多思想的裹挟下陷入斗争,这种斗争既包含内部意识形态的对抗,也包含共和国与外部英、法间的竞争与厮杀。 1702—1806年,四次英荷战争的摧折,爱国者党运动的席卷,即使有尼德兰新共和国的垂死挣扎,衰落的时代也必然来临。最终,在拿破仑政权下,共和国正式落下帷幕。
全书避免了过去以1649年为界的共和国历史研究角度,将时间追溯到1572年之前以及延伸到取代荷兰共和国的巴达维亚共和国时代,同时将地域从单一的北部地区拓展至南部及德意志诸国辖区。从思想史角度揭露尼德兰南北分裂的真相,是突破传统荷兰史研究角度,颠覆欧洲史陈旧观念的力作。
|
|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乔纳森·伊斯雷尔,本科毕业于剑桥大学,在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在英国多所大学工作三十年,后来被任命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教授,2016年退休。作为沃尔夫森历史奖得主,世界知名启蒙运动历史学家,他与约翰·艾略特爵士和杰弗里·帕克齐名,在学界享受盛誉。他的作品涉及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的欧洲和欧洲殖民史。其研究主要集中在斯宾诺莎、贝勒、狄德罗和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对启蒙运动的影响。
他的著作包括《重商主义时代的欧洲犹太人,1550-1750》(1985);《荷兰共和国:崛起、兴盛与衰落,1477-1806》 (1995);《激进启蒙:哲学和现代性的形成,1650-1750》 (2001);《有争议的启蒙:哲学、现代性和人的解放1670-1752》 (2006);《思想革命:激进启蒙和现代民主的知识起源》(2009)等。
|
| 目錄:
|
第 1 章 导论 1
第一部分创建共和国, 1477—1588 年
第 2 章 迈入近代 9
第 3 章 1470—1520 年:人文主义与宗教改革的缘起 47
第 4 章 1516—1559 年:领土合并 64
第 5 章 1519—1565 年:荷兰宗教改革早期 87
第 6 章 大起义前的社会 125
第 7 章 1549—1566 年:哈布斯堡政权的崩溃 154
第 8 章 1567—1572 年:阿尔瓦公爵的镇压 184
第 9 章 大起义的开始 201
第 10 章 大起义与新国家的诞生 213
第二部分 黄金时代早期,1588—1647 年
第 11 章 1588—1590 年:共和国的巩固 275
第 12 章 1590—1609 年:成为大国 284
第 13 章 共和国的体制 326
第 14 章 荷兰世界贸易霸主地位的肇始 363
第 15 章 大起义之后的社会 388
第 16 章 新教化、天主教化与认信运动 429
第 17 章 身份认同的分化:《十二年停战协定》 476
第 18 章 1607—1616 年:荷兰政治体内部的危机 502
第 19 章 1616—1618 年:奥尔登巴内费尔特政权的倾覆 517
第 20 章 1618—1621 年:反抗辩派的加尔文宗革命 537
第 21 章 1621—1628 年:身陷重围的共和国 571
第 22 章 1629—1647 年:迎来胜利的共和国 605
第 23 章 1590—1648 年:艺术与建筑 654
第 24 章 1572—1650 年:智识生活 678
第三部分 黄金时代晚期,1647—1702 年
第 25 章 1647—1650 年:威廉二世执政期 713
第 26 章 社会 731
第 27 章 1647—1702 年:宗教 765
第 28 章 自由与宽容 813
第 29 章 17 世纪 50 年代:巅峰时期的共和国Ⅰ 839
第 30 章 1659—1672 年:巅峰时期的共和国Ⅱ 884
第 31 章 1672 年:灾难之年 952
第 32 章 1672—1702 年:威廉三世执政期 965
第 33 章 1645—1702 年:艺术与建筑 1031
第 34 章 1650—1700 年:智识生活 1062
第 35 章 殖民帝国 1117
第四部分衰落的时代,1702—1806
第 36 章 1702—1747 年:摄政官治下的共和国 1149
第 37 章 社会 1195
第 38 章 教会 1220
第 39 章 启蒙运动 1244
第 40 章 1747—1751 年:第二次奥伦治革命 1280
第 41 章 蹒跚的共和国与“南部”的新活力 1293
第 42 章 1780—1787 年:爱国者党革命 1316
第 43 章 共和国的落幕 1333
第 44 章 尾声 1344
注 释 1354
参考文献 1479
译后记 1537
|
| 內容試閱:
|
前 言
在这样一个大部头著作的开端,用简短的文字说明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并解释其框架似乎是合宜的。
我的研究目的是将荷兰大起义与黄金时代置于更宽广的背景中,也就是整个近代早期之中。在耕耘这部作品时,我越发确信,只有将荷兰大起义和黄金时代置于宽广的背景中,才能领会它们的意义。这意味着,我们一方面要重返勃艮第时期,另一方面要推进到拿破仑时代。1579—1795 年间,荷兰共和国的官方名称是“联省共和国”,1579年建立的乌得勒支(Utrecht)同盟则是其奠基性联盟。同盟常被视为与过往的决裂,然而如果在14—15世纪的背景下考察,它将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意义。
要完成像本书这样的任务,研究者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论述尼德兰北部与南部之间的关系——前者的大致所在地后来发展成现代的荷兰王国,后者则发展成现代的比利时和卢森堡。回到我刚开始写作的1982年,那时我跟所有同事一样确信,大起义之前低地国家南北之间的分隔没什么重大意义,当时只存在哈布斯堡治下的尼德兰。其下辖的17个省之间尽管存在巨大差异,但或多或少地统一于布鲁塞尔的哈布斯堡宫廷的统治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在南部,北部在许多方面只是南部的附庸,这似乎显而易见。
从这个角度看,这场1572年大起义导致的,因1579—1585年间的一系列事件被巩固的南北分裂,似乎是人为的、非自然的,且并不能在此前的历史中找到根据。历史学家彼得·盖尔(Pieter Geyl)第一个清楚地意识到,大起义之前并不存在与南部相分离的“独特的北部意识”或荷兰民族意识这类东西。在这一点上他无疑是对的。他得出的进一步结论似乎也是正确的,即起义是个意外事件,它没有历史根据,并且毁灭了一个更大的统一体诞生。我认为可以公正地说,一个庞大的尼德兰共同体在16世纪70年代被人为地摧毁,这样的信念随后发展成了稳固的共识。然而,随着研究的推进,我开始相信盖尔的修正派观点只有第一点是正确的:1572年之前的确不存在“荷兰”或特定的北尼德兰身份认同,也没有明确的南尼德兰意识。事实上,我们有理由认为在18世纪末之前,这些东西并未在任何意义上存在。尽管如此,在1572年大起义之前很久,政治、经济和地理的因素就已经让北部和南部成了各自独立的实体。尼德兰的南北二元性事实上已经存在了数个世纪。放在中世纪晚期和16世纪早期的背景下看,1572年事件和南北的最终分裂只是对此的确认,并且也是这种二元性的逻辑结果。
在联省共和国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人们的忠诚和身份认同都是以各省、各城镇,有时候甚至是以当地村庄为基础的,而非与共和国整体相联系。从这一方面来说,逐渐形成的松散的联邦结构与民众的性情、态度十分相适。特别的是,占主导地位的荷兰省与其他省份之间的紧张关系时常是政治事件的中心问题,各省一直竭力保护自己的地方利益,避免被荷兰省统治。这种紧张关系在大起义之前存在了数个世纪,然而在我看来,正是这种紧张让斯海尔德河口和马斯河以北的政治体系得以形成。
然而,如果说南北两地在1572年之前就已是政治和经济上基本独立的地区,且此后也依然如此,那么它们倒也确实发展出了统一的文化。这体现在宗教、思想和艺术方面,很大程度上也体现在语言和文学方面——对说荷兰语的南部省份佛兰德(Flanders)、布拉班特(Brabant)和林堡(Limberg)来说就是这样。在这一方面,大起义确实造成了前所未有且决定性的分裂。北部实行加尔文主义的宗教改革时,天主教的反宗教改革运动在南部取得胜利,大起义由此分裂了曾经一致的文化,以两种相互冲突、敌对的文化取而代之。就这点而言,我们可以说大起义扩大并加深了早已存在于政治和经济生活之中的二元对立。
我的研究主题是荷兰共和国,但我并不希望在时间范围和地理范围上过于局限。我认为,要理解共和国,充分领会它在艺术、科学和精神生活方面,以及商业、航海、社会福利和技术发展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及其重要意义,我们既需要把故事的起源追溯至1572年之前很久,也需要了解取代了荷兰共和国的巴达维亚共和国(1795—1806年),还需要研究比单纯的北尼德兰更广泛的体系。在主要关注北部的同时,我将尝试阐述南北之间的关系,比较双方的异同,于是即便南部受到的关注较少,它也仍是这幅画卷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除此之外,我也主张,在18世纪以前,尼德兰和德意志之间不存在固定不变的边界;尼德兰和相邻的德意志诸国辖区重叠,边境地区纷争不断,最重要的是,二者在宗教和文化上相互影响,这一切都是本书故事中不可或缺、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它们却常常被人忽略。因此,我不仅频繁提及东弗里斯兰(East Friesland)、本特海姆(Bentheim)、林根(Lingen)、明斯特兰(Münsterland)、盖尔登(Geldern)、马克(Mark)和于利希—克莱沃(Jülich-Cleves),而且力图在一定程度上将
这些地区纳入本书的整体视野。
最后,也许应该说明一下,在讨论18世纪的最后几章时,我有意尽量言简意赅。让故事在1780年戛然而止当然不合适——这个时间点正是E. H. 科斯曼(E. H. Kossmann)《低地国家(1780—1940)》(The Low Countries,1780-1940)一书的起始。如果我这样做,就相当于无论故事如何完结,都把读者弃在半路上。但是,像我处理本书其他部分的内容那样详细讨论共和国的最后那些年,似乎既无必要又不可取,因此在本书最后两章,我唯一的目标就是为主体部分展开的主题提供简明扼要的结尾。
第1章
导论
所谓的“荷兰共和国的新世界”给17、18世纪欧洲内外的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无论他们是直接与这个“新世界”接触,还是通过它的航海、贸易或书籍等印刷品间接与之相连。“新世界”持续地吸引着当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外交官、学者、商人、神职人员、士兵、水手和艺术鉴赏家,至今仍在近代西方文明史上拥有重要意义。近代早期的观察者尤其被这里各个领域的创造力和数不胜数的新奇事物震撼。他们来到荷兰,因这里的景象惊奇——海运和商业规模惊人,金融行业和工业技术成熟,城市风景优美、秩序井然、干净整洁,宗教和思想实现了相当程度的宽容,孤儿院和医院运行极佳,教会权力受到节制,军队从属于市政权威,艺术、哲学和科学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当然,外国人在惊奇的同时,也常常表现出批判、不满、鄙视,有时甚至是赤裸裸的敌意。对于外来者而言,共和国治下的荷兰社会有许多特征是畸形和可恶的。荷兰当局准许多元教会并存,人们则有讨论宗教和思想问题的自由,而17世纪末以前,这些事让许多人惊骇。还有一些人不赞同给予妇女、仆人和犹太人等特定群体自由,这些群体在欧洲其他国家一直被限制在卑贱、拘束的生活状态中,在其他欧洲人看来,荷兰给这些群体的自由是过度的。外国贵族倾向于嘲笑荷兰生活和政治中中产阶级的做派,取笑他们不符合恰当的社会等级。17世纪,客渡驳船很少出现在欧洲其他地方,许多乘坐荷兰客渡驳船旅行的外国绅士不安地发现,最普通的荷兰百姓都能随意地与他们交谈,毫不考虑他们的等级,仿佛他们只是随便哪个普通人。1694年,一个德意志人写道:荷兰省女仆的举止和穿着都与她们的女主人十分相似,以至于很难判断谁是主人,谁是仆人。 共和国的官方名称是“联省(the united provinces)”,欧洲人普遍认为这里是神学、知识界和社会混乱的温床,它颠覆了男性与女性、基督徒与异教徒、主人与仆人、贵族与非贵族、士兵与平民此前惯常且恰当的关系,倔强地拒绝给予贵族、士兵乃至丈夫应得的荣誉和地位。同时,对于大多数外国人而言,共和国的政治机构更应该被鄙视而不是赞赏。
因此,外国人想要效仿的事实上从来就不是荷兰共和国“新世界”的全部现实。各个领域都有很多新奇事物,一般而言,他们对采纳其中某种新方法更感兴趣。那些渴望在经济上获得成功的人,学习并借鉴荷兰的商业和金融手段。从16世纪90年代到1740年前后,在这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共和国在世界航海和贸易领域整体上居于首位,也是能想象到的各种货物的中央仓库。这个中央仓库不仅储存了来自全球各地的商品,也汇聚了相关的商品信息、储存和加工商品的技术、对商品进行分类和检验的方法,以及宣传和商业洽谈的方式。17世纪,即便是荷兰商业繁荣的头号劲敌,如路易十四的大臣柯尔柏(Colbert)和英国外交官乔治·唐宁(George Downing,唐宁街的名称由此而来)爵士,都刻苦地仿效荷兰模式,努力引进荷兰技术。与荷兰在世界贸易中的首要地位密不可分的是,共和国在16世纪末到18世纪初也是欧洲的技术领头人,许多外国人关注这里的技术发明,从造船方面的新工艺到改良的水闸、港口起重机、伐木机、织布机、风车、时钟和路灯。这里的外国人甚至包括在1697—1698年和1716—1717年两次到访荷兰省的沙皇彼得大帝。关心农业技术创新的外国人相对较少,但是关注这一领域的人会在荷兰的排水系统、园艺、饲料作物和土壤补给方式等方面发现大量技术革新,它们可以应用到其他地方,并带来利润。18世纪英格兰农业革命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借鉴联省的技术和创新后实现的。另一些人则震惊于荷兰市民生活的秩序井然、高效的福利体系、监狱和刑罚实践以及低得惊人的犯罪率,这些都是荷兰社会的显著特征。军人则对联省进行的军事革命怀着强烈的兴趣,尤其是在1648年之前的岁月里。荷兰军事革命自16世纪90年代开始,由执政莫里斯(Maurits)和弗雷德里克·亨德里克(Frederik Hendrik)推行,其特点是不仅火炮、战略战术、防御工事、围城手段和军事运输方面有所革新,军事纪律和秩序也大大提升。从16世纪80年代到17世纪中叶,尼德兰的北部和南部都是新教欧洲和天主教欧洲的“重要军事学校”;1672年到1713年,低地国家因位于路易十四与欧洲反法联盟大决斗的战略中心,又一次成了欧洲的主要军事实践场所。最后,还有一群倾心于学术和艺术的人,因联省丰富的图书馆资源、科学收藏和出版商以及最重要的思想和宗教自由而络绎不绝地前往荷兰。这些人中有些是近代早期最伟大的哲学家,如笛卡儿(Descartes)、洛克(Locke)和培尔(Bayle)。笛卡儿断言,世上再没有别的国家,“可以让你享受这种完全的自由”。
17和18世纪,外国人认为相比当时欧洲的其他社会,共和国赋予了它的公民、外国居民更多的自由,黄金时代的政治和文化也确实特别强调自由。在荷兰黄金时代最伟大的作家冯德尔(Vondel)创作的众多戏剧中,唯一一部关于荷兰特有主题的作品《巴达维亚兄弟》(Batavische Gebroeders,1663年),便是根据古代巴达维亚人——17世纪的荷兰人将他们视为自己的祖先——从罗马人那里争取自由的斗争改编的。前文那位评论荷兰女仆的德意志作家声称:“这里的居民热爱他们的自由胜过任何东西”。荷兰共和国这种著名的自由基于良心自由。不过,正如英格兰大使威廉·坦普尔(William Temple)爵士在1672年前后所写,它延伸到了更广阔的领域,创造了一种“普遍的自由与安适,它不仅仅局限于良心自由这一点,还扩展到其他能使生活方便、安宁的方方面面,大家各行其是,只关心自己的事情,毫不关心他人的事情”。意大利新教作家格雷戈里奥·莱蒂(Gregorio Leti)曾在意大利、日内瓦和英格兰生活。1683年,他定居阿姆斯特丹。在这里的见闻令他欢欣鼓舞。他在荷兰省感受到的真正的自由与意大利的腐败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他看来,腐化堕落、体制性的专制和对个体尊重的缺失是威尼斯和热那亚共和国的特征。
沉默的威廉(William the Silent,1533—1584年)及其宣传者将自由作为他们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核心正义原则。威廉在1568年发布宣言,解释他为何拿起武器反抗尼德兰的合法统治者:一方面,他提到西班牙国王侵害了各省的自由与特权,在十分有限的意义上使用了“自由”一词;另一方面,他也采用了现代意义上的抽象说法,宣称自己是自由的捍卫者。他强调,人民“过去享有自由”,现在却被西班牙国王打入了“不可容忍的奴隶状态”。大起义之后,相互敌对的各意识形态团体在定义各自的立场时,仍将自由作为核心要素。下述例子颇具代表性:1667年,共和国治下的荷兰省三级会议颁布了它最著名的法案之一,即所谓的《永久法令》(Perpetual Edict,又译作《排除法案》),废除了荷兰省执政一职,他们为此辩护的理由是,这对保护和推进自由而言是必要的。罗梅因·德霍赫(Romeyn de Hooghe)是17世纪末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也是奥伦治的威廉三世(WilliamⅢ of Orange)积极的宣传家。1706年,他出版了一部两卷本的著作来描绘联省,将它称为“世界上已知的国家中”,生活“最自由、最安全的一个”。
不过在黄金时代,许多活跃在共和国里最富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天才却感到失望,他们发现这里著名的自由覆盖的范围事实上并不够广。笛卡儿起初满怀热情,而到17世纪40年代,他开始忧虑自由的局限。斯宾诺莎(Spinoza)一直焦虑不安。作为17世纪荷兰主要的共和派作家之一,埃里克斯·瓦尔滕(Ericus Walten)崇敬自由,痛恨专制,最终却因为渎神的罪名而受到调查,死在海牙的监狱中。德霍赫也不得不从阿姆斯特丹搬到哈勒姆,以避免因传播色情图画而遭受审讯。除此之外,格劳秀斯(Grotius)、埃皮斯科皮厄斯(Episcopius)和其他许多名人也有抱怨的理由。不过,在所有这些人看来,这种相对的自由仍旧是共和国提供的生活便利和有利条件之一——就算不是其中最宝贵的。
在那个时代,共和国真的特别有助于思想、想象力和才华的发展,它提供了许多学术书籍、科学研究收藏、艺术家的素材和神学家的不同观点,其丰富程度是欧洲其他地方难以匹敌的。近代早期,欧洲众多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化人物都诞生在北尼德兰,或将这里视为第二故乡,他们包括伊拉斯谟(Erasmus)、利普修斯(Lipsius)、斯卡利杰尔(Scaliger)、格劳秀斯、伦勃朗(Rembrandt)、冯德尔、笛卡儿、惠更斯(Huygens)、弗美尔(Vermeer)、斯宾诺莎和培尔等。在大师们令人震惊地集中在这片如此狭小的土地上的同时,荷兰在商业、航海、金融以及农业和技术方面处于首要地位,这不是巧合,它们有所关联。此外,如果联省没有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维持着欧洲军事大国的地位,没能在更长的时间里维持着世界主要海上强国的身份,上述成就一个也不能实现,更不能持久。即便在共和国的鼎盛时期,荷兰的人口也不过200万,但正是这个比其主要对手小得多的社会取得了上述所有成就。
一个地区众多领域的创造力和成就同时飞速提升,历史上这样的时刻无疑是罕见的。当这种情况真的出现时,如古典时代的雅典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人们常常惊奇地发现,这种持续的创造力常常限于相当狭小的地理空间内。同时,正是因为这种时刻的稀少和创造力的强劲,这种黄金时代难以用一般的历史标准来评价。展现荷兰黄金时代的全貌是困难的。不可避免,许多问题仍然无法涉及。因此,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另一种做法更具吸引力,即专注于荷兰辉煌成就的这个或那个侧面,如农业或航海,然后将其与欧洲或世界其他地方相关领域的发展进行比较。历史学家确实常常这样做,但考察这一极其丰富的图景的全貌的做法则较少有人选择。这种方法确实更费劲,然而完成这样的壮举是多么有价值!对于每个曾了解过荷兰共和国特定侧面的人而言,通过不懈努力去领会它的全貌有助于加深和丰富他们对特定问题以及整体的认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