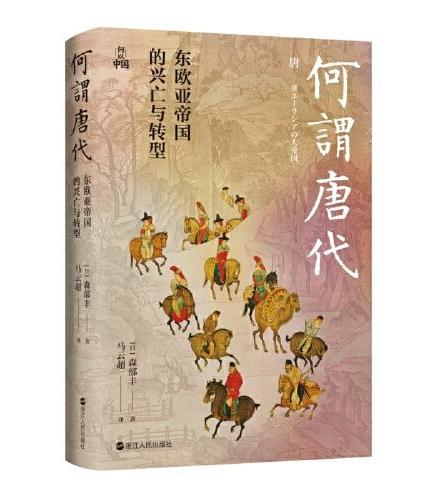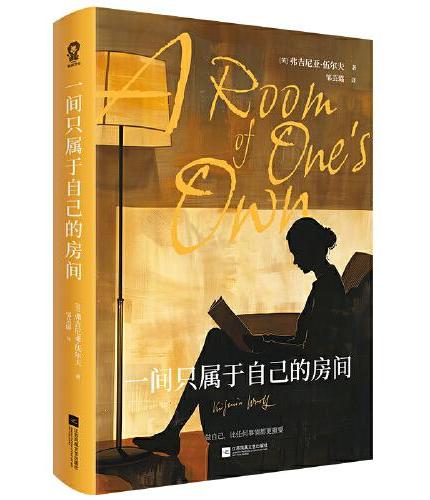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新时代硬道理 广东寻路高质量发展
》
售價:HK$
79.4

《
6S精益管理实战(精装版)
》
售價:HK$
103.3

《
异域回声——晚近海外汉学之文史互动研究
》
售價:HK$
112.7

《
世界文明中的作物迁徙:聚焦亚洲、中东和南美洲被忽视的本土农业文明
》
售價:HK$
102.4

《
无端欢喜
》
售價:HK$
78.2

《
股票大作手操盘术
》
售價:HK$
5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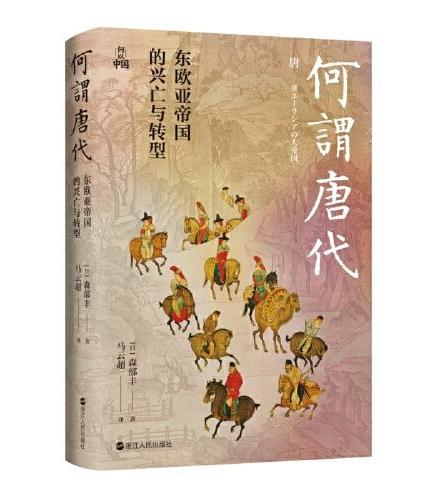
《
何以中国·何谓唐代:东欧亚帝国的兴亡与转型
》
售價:HK$
8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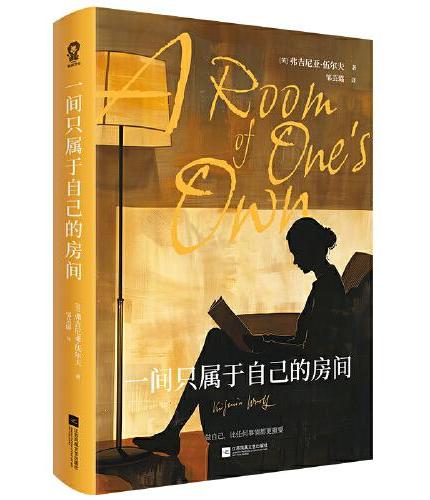
《
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 女性主义先锋伍尔夫代表作 女性精神独立与经济独立的象征,做自己,比任何事都更重要
》
售價:HK$
45.8
|
| 編輯推薦: |
《西线无战事》作者雷马克生前完成的后一部作品,道尽战争阴影中被迫流离失所者的恐惧与悲愁。
逃亡中的人必须依靠偶然事件活下去,偶然事件越不可信,就越使人觉得正常。罗斯在去世当天把他的护照送给了我,我暂时有了新名字,有了未来,成为不幸的逃亡者中“幸运”的那一小撮人。但过往的记忆却始终如幽灵般紧紧追随,等待时机将我击毙。我知道,我需要为这野蛮的、鹰隼般的、让人上气不接下气的自由付出代价。
经典译本,全新呈现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鲍勃·迪伦推崇的大师,茨威格、林语堂、木心盛赞的名家
|
| 內容簡介: |
《天堂里的影子》出版于1971年,雷马克去世半年后,也是他临终前一直在争分夺秒修改完善的一部小说。
小说主人公原是一位德国的新闻记者,纳粹上台后被迫开始四处漂泊。在法兰克福,即将去世的罗伯特·罗斯把自己的护照送给了他。从此他冒名罗斯,靠着这本护照,浪迹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其间进过拘留营,也曾在布鲁塞尔博物馆的地下室里躲藏过两年,终越过比利牛斯山经西班牙到达里斯本。“二战”开始前不久,他乘货轮到达美国——流亡者心中的“天堂”。故事也正是从他到达美国开始写起,在描绘其人生际遇的同时,也勾勒出一幅生活在美国的流亡者的群像。
在被移民局关押六周后,罗斯得到三个月的居留权。他辗转来到纽约,找到了一份古董店助手的工作,接着又受雇于一位卖画的商人。在流亡者聚集的旅馆里,他与持法国护照的俄罗斯时装模特娜塔莎相遇,两人一见钟情。生活看似日渐安稳,但也让罗斯有种说不出的罪恶感,有关过去的记忆一直折磨着他。“二战”结束的消息传来,罗斯决定与爱人和朋友们分别,只身返回欧洲,既是为了报恩,也是为了复仇。他回到布鲁塞尔,寻找当年帮自己藏身的博物馆馆长,但无人知道馆长在被人告发后的遭遇。他回到德国,花了几年的时间寻找家人和凶手,都没有结果,他所遭遇的只有沉默、恐惧和拒绝。
|
| 關於作者: |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Erich Maria Remarque,1898—1970)
德裔美籍小说家。1898年生于德国一个工人家庭,18岁时志愿参加次世界大战并在前线负伤,战后做过教师、记者、编辑等多种工作。1929年,长篇小说《西线无战事》出版,引起轰动,并迅速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使他成为蜚声世界的作家。因为他的反战立场,德国纳粹上台后,将他与托马斯·曼等人的作品公开焚毁。1938年,他被剥夺德国国籍,后流亡美国。1947年,他加入美国国籍,次年返回欧洲并定居瑞士。1970年9月25日,雷马克在瑞士逝世。1991年,雷马克的家乡奥斯纳布吕克设立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和平奖。
雷马克的著作大多带有自传色彩,用词精练,抒情的书写中却透出客观、冷峻的气质,被比作德国的海明威。他一生共著有十五部小说、三个剧本和两部文集,其中《西线无战事》《凯旋门》《伙伴进行曲》《爱与死的年代》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
|
| 內容試閱:
|
序言
近一次战争末期,我是在纽约度过的。我仅会一点英语,是个没有祖国的人,57街的四周成了我的新故乡。我走过了漫长而又艰险的道路,那是所有想避开希特勒政权的人不得不走的苦难之路。这条苦难之路穿过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通往巴黎。它在那里分成两条。一条经里昂到地中海沿岸,另一条经波尔多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西班牙和葡萄牙,到达里斯本港口。
如同许许多多逃离秘密警察的人一样,我也沿着这条路走了过来。然而在我们逃亡所经过的那些国家里,我们的安全仍无保障,因为我们中持有有效证件和签证者寥若晨星。我们要是被宪兵逮住,就会被关起来,判处徒刑或被驱逐。有几个国家未把我们赶到德国边境那边,这无论如何可以说是够人道的。要是我们被逐回德国,必定会被投入集中营并且早已一命呜呼了。
能够携带有效护照的流亡者仅是少数,因此我们几乎是马不停蹄地在逃亡。我们没有证件,在任何地方都不能合法地工作。我们中绝大多数人忍饥挨饿,孤独寂寞,苦不堪言,因此我们就把流亡的道路称为苦难之路。
城镇的邮局和道路两侧的白色围墙旁就是我们逗留的一个个站点。
在邮局里,我们试图获得亲属和朋友留在那里的信件。马路旁的围墙和房屋成了我们的报纸。墙上涂着白色、黑色的符号或文字,我们从中找到了相互间一直在寻觅的、浪迹天涯者的留言、住址、警告、暗示,仿佛听到他们在一个普遍冷漠无情的时代对着天空呼喊。随后而来的是一个非人道的时期—战争时期。在战争中,秘密警察、民兵以及宪兵一道干着卑鄙的勾当,追捕我们这些不幸的人。
1
几个月前,我搭乘一艘货轮从里斯本来到美国。当时我只会一点点英语,我就像一个半聋半哑的人从别的星球上被流放到这儿。那当然是别的星球,因为欧洲在打仗。
此外,我的证件也有问题。虽然我奇迹般地搞到了有效的美国签证,持这签证入了境,但是护照上写的不是我的姓名,而是别人的姓名。移民当局对此产生了怀疑,把我关押在埃利斯岛。六个星期后,他们才准许我居留三个月。在这期间我必须设法搞到去别的国家的入境许可证。我在欧洲时已经有过此类经历。几年来,我待在欧洲一个地方从未超过一个月,我是待一天换一个地方。作为德国的流亡者,我从1933年起已被正式宣告死亡。如今有三个月时间我无须再逃亡,这简直是个令人难以理解的梦。
很久以来,用别人的名字、持死人的护照生存,我已经觉得这不值得大惊小怪了;相反,我觉得这很合适。我在法兰克福继承了这本护照。那位在死的那天把它送给我的人姓罗斯,于是我同样也叫罗伯特·罗斯。我几乎把我的真姓忘了。如果能保住生命,那么许多事情都可以忘记。
我在埃利斯岛遇到一个土耳其人,他在十年前曾到过美国。我不知道如今人们为何不让他入境,我也不去问他是什么原因。我曾多次看到过一些人被驱逐,其原因是表格中所提出的问题他们都回答不出来。这个土耳其人把一个俄罗斯人的地址给了我,那俄罗斯人住在纽约。土耳其人是早几年认识他的,当然不知道他是否还在世。尽管如此,我一被释放,就立即前去找他。我这么做是理所当然的,多年来我就这样生活。逃亡中的人必须依靠偶然事件活下去,偶然事件越是不可信,就越是使人觉得正常。这就是今日的童话,它们虽然不能令人振奋,但其结局却往往令人惊喜地比先前预料的要好。
那个俄罗斯人在百老汇附近一家低档的小旅馆里干活。他叫梅利科夫,说德语,并且立即接待了我。作为一个老流亡者,他一眼看出我缺少的是住处和工作。住处还容易解决,可以在他房间里再放一张床。可我持旅游签证是不许工作的,我必须搞到另一种签证:一个有限额号码的入境签证。我只好打黑工。我在欧洲时曾干过,而我觉得打不打黑工并不碍事。我身边还有些钱。
“您想过您可以靠什么生活吗?”梅利科夫问我。
“我在法国后是靠给商人推销假画和假古玩生活的。”
“您懂得鉴别画的真伪吗?”
“懂得不多,但有一些实际经验。”
“您在哪里学到的?”
“我在布鲁塞尔博物馆里待了两年。”
“被雇用吗?”梅利科夫惊异地问。
“躲藏。”我回答。
“躲避德国人吗?”
“躲避占领了比利时的德国人。”
“您躲了两年?”梅利科夫说,“而他们没有发现您?”
“没有发现我,但发现了藏我的人。”
梅利科夫凝视着我:“您逃脱了?”
“是的。”
“关于那个人您还听到过什么吗?”
“通常发生的事,他们把他投入了集中营。”
“他是德国人吗?”
“他是比利时人,博物馆馆长。”
梅利科夫点点头。“这么长时间怎么会没有人发现您?”他随即问道,“难道没有人参观博物馆吗?”
“有人来。白天我待在地下室的一个储藏室里。晚上馆长来,带给我食物,给我开门,让我过夜。我待在博物馆里,可我不能走出地下室。当然我不能开灯。”
“其他职员知道吗?”
“不知道。储藏室没有窗。有人来储藏室,我就得屏住呼吸。让我担惊受怕的是在不该打喷嚏的时候打喷嚏。”
“有人因此而发现您吗?”
“没有。有人注意到馆长晚上不是待在博物馆里,就是再回博物馆一次。”
“明白了,”梅利科夫说道,“那时您能读书看报吗?”
“只有在夏天和有月光的夜里。”
“您在夜里可以在博物馆里到处走来走去,观看画儿吗?”
“只要可以看的都看了。”
梅利科夫微微一笑。“我从俄国逃出来时,在芬兰边境上,有一次就在木屋的木材堆下躺了六天。当我出来时,我觉得躺的时间要长得多,好像至少有十四天。但是当时我年轻,年轻人总觉得时间过得慢。您肚子饿吗?”他突然补问一句。
“是的,”我说,“而且非常饿。”
“这一点我也想到了。一个人被释放时总是觉得饿。我们到药店里去吃饭。”
“到药店里去?”
“确切地说,到一家杂货店去。这是这个国家很有特色的一种店。人们在那里可以买到阿司匹林,也可以就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