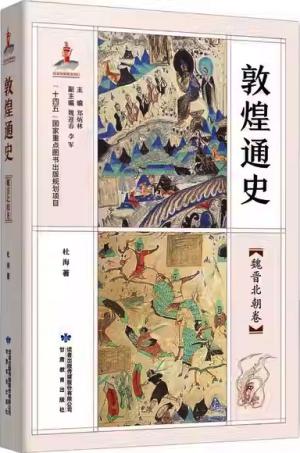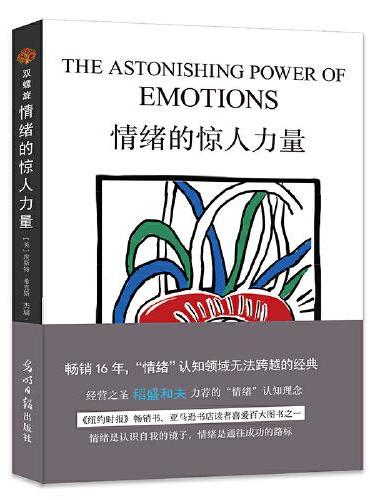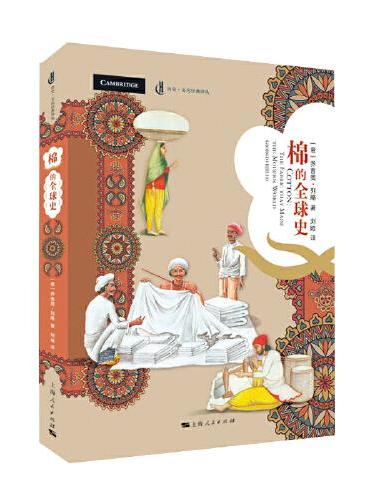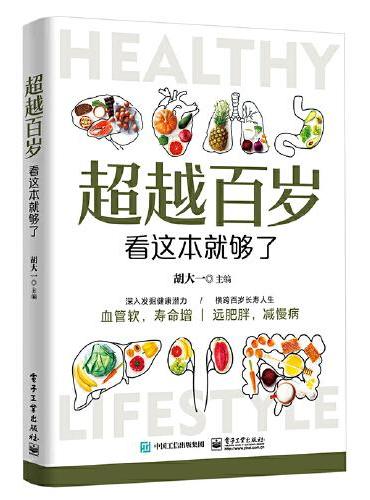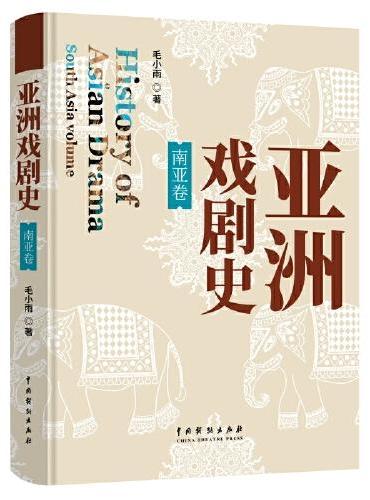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樊树志作品:重写明晚史系列(全6册 崇祯传+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明史十二讲+图文中国史+万历传+国史十六讲修订版)
》
售價:HK$
498.0

《
真谛全集(共6册)
》
售價:HK$
115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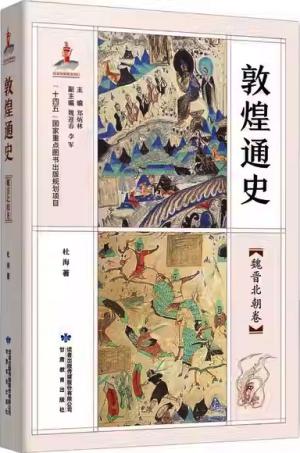
《
敦煌通史:魏晋北朝卷
》
售價:HK$
162.3

《
唯美手编16:知性优雅的编织
》
售價:HK$
5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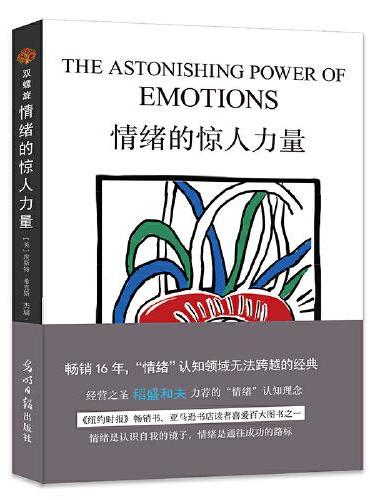
《
情绪的惊人力量:跟随内心的指引,掌控情绪,做心想事成的自己
》
售價:HK$
5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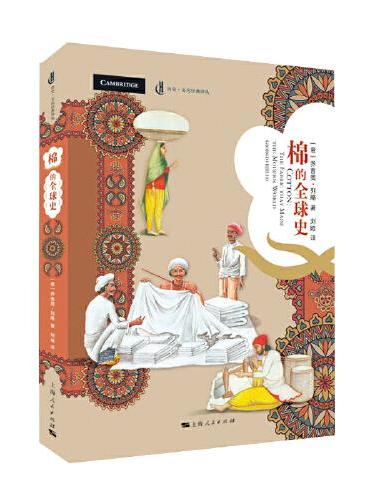
《
棉的全球史(历史·文化经典译丛)
》
售價:HK$
1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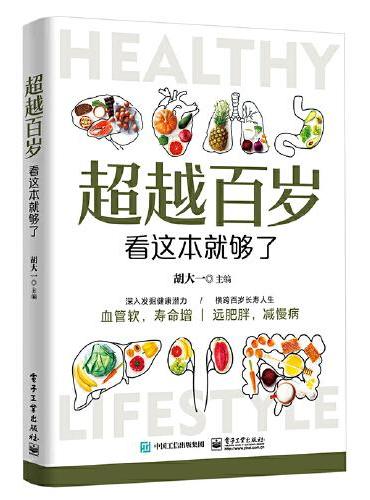
《
超越百岁看这本就够了
》
售價:HK$
5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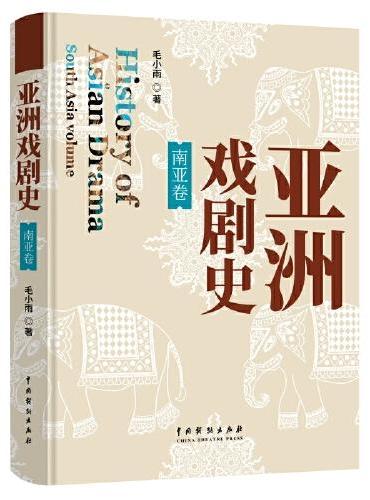
《
亚洲戏剧史·南亚卷
》
售價:HK$
147.2
|
| 內容簡介: |
|
本书作者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国际组织,将其视为一种官僚机构,把它们当作具有独立实体地位的行为体,从而对它们的性质、行为偏好、能力、特征和权威性等进行全面、细致的考察,并试图构建一种研究国际组织的方法,让人们正确地认识国际组织,并恰当地运作国际组织。本书重新解释了国际组织的三个活动领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利用其专业知识和权力对成员国经济的渗透;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在重新界定难民定义和对遣返的决定上所发挥的作用;联合国安理会对卢旺达种族屠杀的不干预决定。
|
| 關於作者: |
迈克尔·巴尼特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校级教授(University Professor),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关系理论、国际组织和中东政治。主要著作有《中东地区的国家安全与对外政策》《为世界定规则》《见证种族灭绝:联合国和卢旺达》等。
玛莎·芬尼莫尔 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校级教授,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组织、全球治理和国际事务中的伦理,主要著作有《干涉的目的》《为世界定规则》《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等。
译者简介
薄燕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环境与国际关系、国际组织和全球治理。主要著作有《国际谈判与国内政治:美国与<京都议定书>谈判的实例》(2007年)、《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中美欧三边关系》(2012年)、《中国与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变迁》(合著,2017年)。
|
| 目錄:
|
前言/I第一章官僚化的世界政治/1
理解国际组织的行为/4
案例设计/11第二章作为官僚机构的国际组织/22
官僚机构/23
国际组织的权威和自主性/26
国际组织的权力/36
国际组织的病症/42
组织的变迁/50第三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专业知识与权力/6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任务、结构与自主性/67
专业知识与波拉克模型(Polak model)的建立/70
构建健康经济/76
目标扩散与组织性功能障碍/83
专业知识、量化与权力/86第四章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如何界定难民和
自愿遣返/102
国际难民机制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的缘起/105
遣返文化/123
罗兴雅人的“自愿”遣返/135
结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的权力与病态/149第五章种族屠杀与联合国的维和文化/165
早期/168
冷战之后/171
卢旺达/179
维和与公正的意识形态/196第六章扩展中的全球官僚机构的合法性/208
组织的演变和扩展/210
合法的全球治理和不民主的自由主义/218缩略语表/230
参考文献/231
译后记/259
|
| 內容試閱:
|
前言
这本书源自我们两个人始于1994年的一系列谈话。当时,巴尼特(Barnett)正在联合国工作,而芬尼莫尔(Finnemore)正在世界银行做研究。我们经常碰面并且交换观点。这样的对话几乎总是以幽默的质询结束,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接受的研究生教育没有向我们呈现国际组织的真实面目。这些俏皮话实际上表达了我们真正的挫败感,即我们看到了国际组织的真实情况,但是学术文献很少讨论这些问题。
我们的情况反映了当时美国的学术状况。我们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接受的研究生教育。当时冷战塑造了国际政治,并且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的新现实主义主导了国际关系理论。我们母校的院系并没有开设有关国际组织的课程。这反映了一门学科对这些国际组织失去了兴趣。20世纪80年代的国际关系成为研究国家和国家行为的学问。我们所有的理论都是关于国家的理论。其他的行为体,如国际组织,被看成是国家行动的副产品,而这也只是在它们确实得到了关照的情况下。
然而,更令人惊讶的是,对国际治理感兴趣的学者也忽视了对国际组织的研究。到20世纪70年代晚期,关于国际组织的研究随着有关相互依赖和国际机制文献的出现而黯然失色。这些国际治理的研究者表明:国际生活远比大国现实主义的政治丰富得多,而持久的国际合作在国际制度的扶持之下是可能实现的。这些洞见具有重要和持久的意义,但是学者们是在一种国家主义的框架内表达他们的观点的。这种框架是从那些不屑于把国际组织作为独立行为体的新现实主义者那里借来的。这些学者对规范国家行动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感兴趣。国际组织被当成机制的组成部分,并且只是其他行为体——主要是国家——借以展开行动的舞台。它们并不能凭借自身的权利而成为行为体,也没有独立的实体地位。对这些学者来说,有趣的理论问题是国家为什么能够合作建立国际组织。至于说这些国际组织建立之后做了些什么,以及它们的行为是否符合国家的预期,显然没有激起学者们的好奇心。新现实主义者和机制研究者对此均不感兴趣,从而使得国际组织成为一个“大呵欠”(great yawn)——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沮丧地如是说。
为了理解国际组织如何运作,我们转向运用组织理论而不是国际政治理论。我们在这方面并非先行者。许多国际关系学者已经运用组织的微观经济学理论来解释一般意义上的国际合作,也偶尔分析国际组织。依据这种观点,国际组织是改善信息不完全和降低较高的交易费用的解决方案。然而,这些方法至少有两个严重的缺陷:一个是理论上的,一个是规范性方面的。在理论上,这些方法更适合解释为什么组织会存在而不是它们在建立后做了些什么。它们没有提供国际组织的实质性偏好、能力或者特征。为了解释国际组织的行为,我们需要运用不同的工具。我们在社会学中找到了。社会学家发展了关于组织和官僚机构的丰富的理论体系。他们认为,官僚机构是特殊的社会形式。它们自身内在的逻辑导致了特定的行为趋向。我们把这些洞见运用到国际领域。这种方法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它提供了一种基础,凭此可以把国际组织作为具有独立实体地位的行为体,并且能够对它们的性质和行为倾向理论化。我们发现,“官僚机构的逻辑”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论断。这事关国际组织自主性的来源、国际组织权力的本质和影响、国际组织失败的原因以及它们演化和扩展的方式。通过把国际组织作为社会的产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它们的权威、权力、目标和行为。
这种方法也有助于我们解决一些规范性的问题。大部分学术研究方法把国际组织当作一件好东西。这是一种有利于国际组织的规范偏见。国际组织帮助国家进行合作。它们帮助人们颠覆暴虐的政府。它们传播好的规范。它们表达了一种进步和启蒙的精神。这种对国际组织美好方面的强调不仅仅是一种选择性的偏见,也反映了理论上的支配权。国际组织的微观经济学理论和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理论几乎总是把国际组织塑造成一个积极的角色。在这些微观经济学理论内,没有一个国际组织的存在不是服务于带有价值观的目标。因为根据这些理论,国家会放弃任何不履行这些目标的组织。在自由主义的理论内,国际组织不仅被作为合作的促成者,而且被看作进步的传输者,同时也是成功民主的化身和自由价值——包括人权、民主和法治——的提供者。
然而,如果我们从以下的前提出发,即国际组织是官僚机构并且据此行事,我们就会产生不同的预期。我们看到的情形是,国际组织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成为良好的公仆,也会造成不受欢迎和弄巧成拙的后果。确实,国际层面上对官僚机构的欢迎是非同寻常的。官僚机构在社会生活中通常会遭到嘲笑——它们因为其文牍主义、行动愚钝和反应冷淡而臭名昭著。我们的方法能够确定国际组织一系列或好或坏的行为。
国际官僚机构是把双刃剑,并且这种特征在我们的头脑中有重要的历史对应物。当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明确地叙述他那创造性的关于官僚结构和其成为“铁笼”可能性的观点时,他在国家层面上努力解决的问题同样在国际层面上激起了我们的兴趣。官僚机构于19世纪晚期在普鲁士国家扩散的方式与现今国际层面上正式组织的扩展方式非常类似。他的问题与我们的问题是类似的。他想知道这为什么会发生以及它对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含义是什么。韦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来自他对以下问题的分析,即官僚机构作为一种社会形式到底是什么,它们如何受到西方文化的支撑以及它们在现代世界中做了什么。我们也是如此。
在本书中,我们试图建构一种研究国际组织的方法。我们并不是先行者,但是我们在该领域的同行并不多。虽然对于国际组织的研究兴趣出现了重要的复兴,但是很少有实证研究深入到这些组织的内部去看个究竟。在很多方面,我们认为自己进行研究的过程并非不同于有关国家的研究过程。多元和阶级的国家观点把国家看作是一种消极的结构,并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主导学术界。统治阶级在其中实施统治或者社会利益相互竞争,很类似于现实主义者和机制学者对待国际组织的方式。这些观点没有能够通过任何有意义的方式考察国家本身。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开始,一种有关国家相对自主性的非同寻常的文献发展起来。从很多方面看,我们写作的时机与研究国际组织的学者们所处的时机类似。学者们现在才开始认真地对待这些组织的内部运行,并且询问如何系统地分析它们的难题。
我们花费了很长时间才到达这一步。我们从1994年开始交换观点并且在1997年首次写出了我们的观点。那个观点成为我们在《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上发表的一篇论文的基础。我们当时知道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并且幸运地从以下的基金会获得经费,它们是麦克阿瑟基金会(the MacArthur Foundation)、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the Smith Richardson Foundation)、美国和平研究所(the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威斯康星大学校友研究基金会(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Alumni Research Foundation)以及乔治·华盛顿大学促进基金会(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Facilitating Fund)。尽管我们希望在经费用完之前完成任务,但我们的雄心却使得这笔钱几年内就耗尽了。我们感谢这些基金会不仅是因为它们最初的支持,还因为它们的耐心。
在过去几年里,我们累积了对很多人的感激,而写完这本书的真正乐趣之一在于向很多提供批评和支持的人表示感谢。他们是霍华德·阿德尔曼(Howard Adelman)、伊曼纽尔·阿德勒(Emanuel Adler)、汤姆·卡拉(Tom Callaghy)、杰夫·克里斯普(Jeff Crisp)、迈克尔·多伊尔(Michael Doyle)、雷蒙德·杜瓦尔(Raymond Duvall)、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彼得·埃文斯(Peter Evans)、奥菲欧·菲奥里托斯(Orfeo Fioretos)、盖伊·古德温吉尔(Guy GoodwinGill)、埃里卡·古尔德(Erica Gould)、乔玛丽·格里斯格雷伯(JoMarie Griesgraber)、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吉尔·洛希尔(Gil Loescher)、克里斯·麦金托什(Chris Mackintosh)、阿济兹·艾利·莫汉姆德(Aziz Ali Mohammed)、安迪·莫拉维希克(Andy Moravcsik)、克雷格·墨菲(Craig Murphy)、路易斯·波利(Louis Pauly)、乔恩·佩弗豪斯(Jon Pevehouse)、雅克·波拉克(Jacques Polack)、马克·波尔拉克(Mark Pollack)、邓肯·斯奈德(Duncan Snidal)、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巴里·斯坦(Barry Stein)、迈克尔·蒂尔尼(Michael Tierney)、埃里克·沃特恩(Erik Voeten)、凯特·韦弗(Kate Weaver)、斯蒂弗·韦伯(Steve Weber)、汤姆·韦斯(Tom Weiss)、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格瑞·伍兹(Ngaire Woods)以及康乃尔大学出版社的一位匿名评审人。他们都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建议。特别的感谢要献给杰夫·勒格罗(Jeff Legro)。他两次阅读了书稿,并且给了我们极其宝贵的反馈和修改意见。我们分别在很多地方对具体的案例和主要的观点作过讲演。这些地方包括:欧洲大学研究所、芝加哥大学、科罗拉多大学、明尼苏达大学、多伦多大学、华盛顿大学、耶鲁大学、杜克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马里兰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众多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也就该领域中所发生的活动提供了重要的信息。我们感谢他们并且尊重他们保密的要求。大概最重要的是,我们深深感激我们所研究的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他们经常慷慨地安排时间,并且耐心地回答我们的很多问题。
当然,还要感谢罗杰·海登(Roger Haydon)。他又一次做了我们要求一位编辑能够做的所有事情——并且更多。我们清楚地记得当他知道我们要共同写一本书时的反应:他大笑起来。为了掩饰失态,他说他只是不能想象风格如此不同的两个学者如何合作写一本书。我们现在意识到他是一位激励别人的大师:我们不能放弃,因为我们拒绝承认他说的是正确的。我们诚挚地感谢出版社的罗杰·路易斯·罗宾斯(Roger Louise E.Robbins)。她也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如果她也是作者之一的话,这本书会写得更好。
我们深切的债务是私人方面的。我们的配偶和孩子们与这本书的关系超出了他们的愿望。他们对于无休止的电话的耐心使得本书得以问世。他们要求我们在写书之外应该做点别的事情,这使得我们能够保持正常。
迈克尔·巴尼特(Michael Barnett)把这本书献给朱迪思(Judith)和马丁·沙姆佩因(Martin Shampaine)。他们是一个女婿能够拥有的最好的岳父母。玛莎·芬尼莫尔(Martha Finnemore)把这本书献给她的家庭,正如同她所有的著作一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