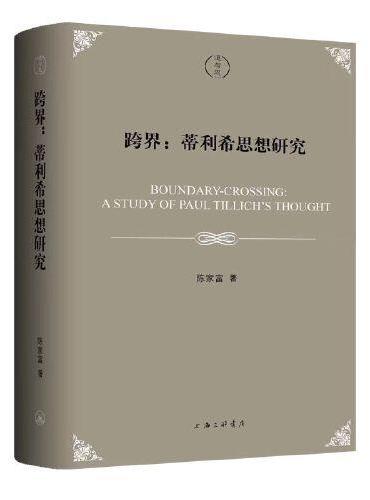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养育女孩 : 官方升级版
》
售價:HK$
5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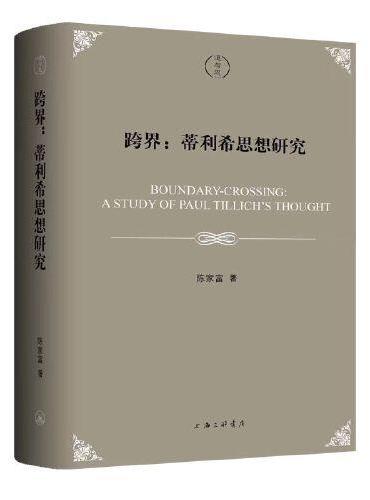
《
跨界:蒂利希思想研究
》
售價:HK$
109.8

《
千万别喝南瓜汤(遵守规则绘本)
》
售價:HK$
44.7

《
大模型启示录
》
售價:HK$
112.0

《
东法西渐:19世纪前西方对中国法的记述与评价
》
售價:HK$
201.6

《
养育男孩:官方升级版
》
售價:HK$
50.4

《
小原流花道技法教程
》
售價:HK$
109.8

《
少女映像室 唯美人像摄影从入门到实战
》
售價:HK$
110.9
|
| 編輯推薦: |
四个平淡无奇的“小人物”,谱写以色列情报历史的离奇开篇
四个从长相到能力都并不出众的青年,无意中组成了犹太国家的第一个国外情报小组;他们所属的“阿拉伯分部”虽然极少得到历史学家的关注,却是以色列建国初期仅有的获取有效情报的途径之一。他们构成的组织,后来孕育了举世闻名的情报机构——“摩萨德”。
游走在两个世界的“边缘人”,犹太复国运动的一个精妙隐喻
四个间谍有着复杂的身份,他们是出生在阿拉伯国家、成长于中东社会底层的“米兹拉希犹太人”——阿拉伯人眼中的仇敌、以色列人眼中的异类,被称作“变得像阿拉伯人的人”,游走在两个世界的边缘。他们的双重身份也是这个国家的隐喻,“每个国家都有明面上的故事,也都有隐秘的自我”。
打破以色列历史叙事的西方中心主义神话,探寻今日社会矛盾的伏笔
“像阿拉伯人的人”已经成为历史,但犹太人之间的内部纷争却延续至今,从未停止,而矛盾的根源,自以色列人寻求建国时起,就已埋下。被排斥在历史叙事边缘的帕尔马赫“黑人分部”成员,既是摩萨德崛起的基石,也是了解以色列动荡灵魂的窗口。
|
| 內容簡介: |
以色列的摩萨德,是与美国中情局、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和英国军情六处齐名的世界四大情报机构之一。书中的四位间谍,正是摩萨德的前身“黎明”组织的成员。
间谍故事的主角,似乎往往都是能改变历史进程的传奇人物。但这四位间谍却从未经历过那样的巅峰时刻。他们生于阿拉伯人与犹太人混居的贫穷社区,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却因为外貌无异而成功潜伏于阿拉伯人之间,成为了以色列的第一批间谍。但在回到以色列后,他们却也同样因为“像阿拉伯人”而被排斥到历史叙事的边缘。
通过大量口述、笔录、回忆录和档案,作者提笔揭开了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中被掩盖的一角,露出滚滚而来的洪流之下,历史中最真实的人。
|
| 關於作者: |
[以]马蒂·弗里德曼 著 曾记 译
马蒂·弗里德曼(Matti Friedman):著名以色列裔记者、作家,曾任美联社记者和《纽约时报》专栏撰稿人。其作品《无国之谍:以色列建国之际的秘密特工》《南瓜花:士兵的故事》《阿勒颇抄本》曾获萨米罗尔犹太文学奖、加拿大国家犹太图书奖和索菲·布罗迪勋章等荣誉。
曾记:博士,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副教授,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已出版《无泪而泣——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的“特别工作队”》等译著及专著多部,在《翻译季刊》(Translation Quarterly)、《外语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东方翻译》、《边疆与周边问题研究》、Israel Affairs、China and the World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多篇。
|
| 目錄:
|
译者的话
本书中的四名间谍
前言
第一部分? 海法
1.侦察员
2.营地
3.修车行
4.观察者(1)
5.猛虎
6.以撒
7.“椋鸟行动”
8.“雪松”
9.观察者(2)
第二部分? 贝鲁特
10.基姆
11.难得的机会
12.以色列的沦陷
13.“三个月亮”报刊亭
14.地中海赌场
15.希特勒的游艇
16.破坏者
17.绞刑架
18.犹太国家
19.情人乔吉特
20.“红发”博凯
21.归家
后记
资料来源
致谢
|
| 內容試閱:
|
后 记
在特拉维夫,我坐在一条长凳上,盯着一间报刊亭。我已经看了一个小时了,尽管这间报刊亭没什么神秘的,只有一个小房间大小,搭了一顶条纹雨篷,一面墙上贴着卖彩票的海报。我在长凳上坐下时,刚过七点钟,报刊亭还关着门,但不久就开了。先是几分钟的忙碌,一切有条不紊。一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老妇人打开了门锁,接着一名穿着黑色 T 恤的中年男子摆出了几把椅子,一个穿蓝裙子的女人则在里面忙着些什么。椅子放这儿,桌子放那儿,再摆上烟灰缸。三人穿插交错,虽没有交谈,却配合默契,各司其职。
中年男子摆出了一货架薯片。一面墙上的金属窗板向上打开,透过窗户可以看到老妇人的上半身和报刊亭的内部——一台放着软饮料的冰箱,一个售卖比克(BIC)打火机和棒棒糖的柜台。城里别处的报刊亭会卖卡布奇诺和无麸质松饼给网站设计人员,但这里不会。这个报刊亭开在小学旁边,平平无奇。即便连人带亭子被整个抬起,飞到东边落在约旦的安曼,或飞到南边落到埃及的亚历山大,又或者飞到西面落在希腊的某个岛上,都不会引起注意,生意照做,不受影响。
一名警察慢悠悠地经过,向老太太打了个招呼,脚步没停。一个小女孩背着大大的粉红色书包,踮起脚尖,买了一包粉红色的口香糖。一位出租车司机买了包L&Ms香烟,和亭子里的女人很熟络,毫无客套,显然多年来他已经从这儿买过很多这样的香烟了。这是夏末一个平常的日子,地中海东岸的人们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大海掩藏在建筑物背后,却不时用一阵微咸的海风送来问候。在世界的这片角落,现在正是出门的好时候,阳光明亮而不刺眼,离热起来还有几小时。我向老太太要了杯黑咖啡。她不认识我,但还是用带着阿拉伯口音的希伯来语亲切地叫我“亲爱的”,然后转身进了里间,过了一会儿端着一个纸杯出来。我则继续观察着。我来到这里,是为了要想象一下那间在贝鲁特的报刊亭,它和我之间隔着敌对的边界,隔着七十年的动荡岁月。像这间报刊亭一样,它坐落在一条安静的街道上,紧挨着一所学校。大海,同一片大海,也在不远处,能闻到它的味道。我想象着 1948 年夏末那个早晨,职员和工人们经过紧闭的报刊亭,走向马车、汽车和市中心的有轨电车汇成的喧嚣。几名学生从这里路过,走向“三个月亮”学校。
报刊亭里传来“咔嗒”一声,窗户撑起来了。两个年轻人从柜台后往外看。两人忙碌着,时而并排,时而交错,轻松自如,非常默契。他俩都留着小胡子,其中一人戴着眼镜。我有一张照片,照片中他俩对着镜头咧嘴笑着,头发向后梳,领子没扣上,看上去既会说笑又能战斗。如果问他俩叫什么名字,戴眼镜的人会说他叫作阿卜杜勒·卡里姆,另一个会说他叫易卜拉欣。一辆奥兹莫比尔汽车停在路边,另一个年轻人出现了。像前两人那样,他肤色黝黑,留着小胡子,但从他踏上人行道的那一刻起,就能感觉到他更加趾高气扬。他声音洪亮,是个冒险家。他大步走向柜台边,那两人和他握手,亲吻他的脸颊。这位就是贾米尔。第四个人走了过来,他就是尤瑟夫。他似乎比其他人更有派头,带点知识分子的气质。别被他们放松的姿态骗了,他们已有五位朋友丢了性命,命运仍然没有放过他们。他们凭着偷听到的谈话、报纸上的字句以及晾衣绳传来的滴答声,竭力去了解周围发生的事情,推测接下来的动向,但一切都还笼罩在迷雾中。他们躲在报刊亭里,仿佛那是一艘救生艇,是方圆数公里内唯一的依靠。此刻我坐在眼前这座报刊亭旁,却仿佛在看着他们那间报刊亭。就算他们中间有哪个人走了过来,似乎也不奇怪。
从报刊亭驱车往前开一小段路,就来到一栋普通公寓大楼。入口处写着卡塔什、鲁宾斯坦、亚历山德罗夫、卡马赫吉和其他人的名字,名字的主人从别处来到这里,变成了别的人。一个门铃按钮旁边写着以撒为自己选择的姓氏。从选择这个姓氏开始,他便掌控着自己的命运。一部电话亭大小的电梯把我带到七楼,他就在门口,个子不高,留着小胡子,戴着眼镜。他就是以撒·索山,或者扎基·沙索,或者阿卜杜勒·卡里姆。
以撒的职业生涯涉及以色列情报机构的多个部门。有一段时间,他负责偷渡路线,帮助犹太人逃离叙利亚,其中一条路线是从他的家乡阿勒颇经贝鲁特登上近海的一艘船,然后抵达海法港。他参照英国皇家特别空勤团建立了一支突击队伍,用于敌后作战。在这支队伍里早期的士兵当中,有一首阿拉伯语歌很是流行,歌名叫作《穆萨·宰因》(Musa Zein),一问一答,很有感染力,这首歌就是以撒在海滩上训练士兵跑步时教给他们的。以撒小时候家在犹太区,附近街道上有穆斯林的婚礼游行,他就是从那里听到这首歌的。
我还认识另一名老间谍,他曾经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安全屋见到过以撒。以撒正在询问另一名间谍。当时以色列刚建国不久。那名被询问的间谍还是个学员,此时才刚知道情报人员并非电影里看到的那样。以撒既不咄咄逼人,也非温文尔雅。他言语温和,娓娓道来,俨然是个没有高中文凭的心理学家,一个自学成才的学者,洞悉人性,熟知中东的事情。
以撒的第一任妻子亚法因病早逝,后来他娶了拉结,是他在阿勒颇认识的几兄弟的妹妹。婚后他俩还住在以前的公寓楼里,幸福地生活了许多年。他有一双儿女,女儿在特拉维夫,儿子在纽约,还有个弹钢琴的孙子。1950年春天的那个夜晚,他乘船回国的时候,完全想象不到今天的日子。途中他既没憧憬未来,也没回顾过往,只是趴在栏杆上吐了一路。
天亮时分,他们到了海法。水手们抛下缆绳,发动机“啪”一声熄了火。以撒和同伴分别后独自一人待在码头上。没有英雄的欢迎仪式,甚至根本没有人来迎接他,只有一张职员住宿券,找不到更好的地方的话,可以在军队招待所凑合一晚。他以为帕尔马赫会有人来找他,听他讲故事,但帕尔马赫已经不复存在了。两年前他混在难民中乘车离开,现在又回到了这座城市——但又不是原来的城市,原来的房子中全是陌生的面孔。他回到了战火纷飞时离开的国家,但又不是原来的国家,是他从未来过的地方。他还是他,但同时又变成了另一个人。
在我们为了写这本书进行最后一次谈话的时候,以撒已经 93岁了。他告诉我,他发现自己在想念母亲。他的语气很惊讶,仿佛从没有过这样的事。他母亲的名字叫玛扎尔。以撒 7 岁时,她死于分娩,葬在过去的阿勒颇,葬在另一个世界,在那里,20 世纪的历史尚未滚滚而来,把一切搅得粉碎。
他不记得母亲长什么样了,这让他很烦恼。有时她的样子似乎触手可及,然后又从脑海里溜走了。她没有留下照片。如果铆足劲儿回想,以撒可以看到她的轮廓,就好像正仰望着她,光线从她背后照下来,也许正是阿勒颇的阳光。也许她正要把他抱进怀里。
他的母亲又瘦又高,戴着一个黄金的小吊坠。但他看不清她的面容,也听不见她的声音。以撒想知道母亲是怎么叫自己的,是和其他人一样,还是有什么特别的昵称——只有她才会叫的那种。母亲是怎么叫他的?他想知道,但已经不记得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