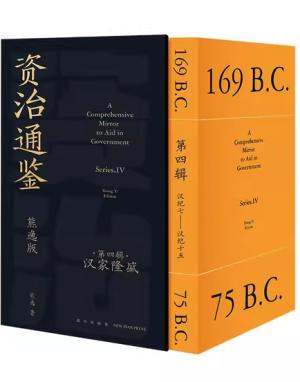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战胜人格障碍
》
售價:HK$
66.7

《
逃不开的科技创新战争
》
售價:HK$
103.3

《
漫画三国一百年
》
售價:HK$
55.2

《
希腊文明3000年(古希腊的科学精神,成就了现代科学之源)
》
售價:HK$
82.8

《
粤行丛录(岭南史料笔记丛刊)
》
售價:HK$
80.2

《
岁月待人归:徐悲鸿自述人生艺术
》
售價:HK$
61.4

《
女人的中国医疗史:汉唐之间的健康照顾与性别
》
售價:HK$
10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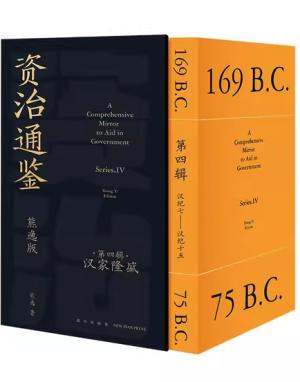
《
资治通鉴熊逸版:第四辑
》
售價:HK$
470.8
|
| 編輯推薦: |
|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历史观的集中体现。
|
| 內容簡介: |
|
1931年,卡尔·贝克尔就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发表演讲《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这个命题是其历史观的生动写照,由此引发了众多历史学家及史学爱好者的关注和讨论。本书是由贝克尔的学生汇编的贝克尔的历史学与政治学文集,共收录论文十六篇。除这篇演讲之外,还包括贝克尔对诸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学家的论述和评论,如:1776年精神、自由主义、美国边疆;雨果、狄德罗、罗兰夫人;亨利·亚当斯、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等等。每篇文章都见解独到,文字精妙老辣。
|
| 關於作者: |
卡尔 · 贝克尔(Carl Lotus Becker,1873--1945), 美国历史学家,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1931年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曾受教于哈斯金斯、特纳、鲁滨逊等知名史家,后长期执教康奈尔大学。著有《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革命的前夜》《合众国:一场民主试验》《论<独立宣言>:政治思想史研究》等。
马万利,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西方思想史、美国史的教学、译介与研究。
|
| 目錄:
|
卡尔·贝克尔的生平与学术(代译序) / 1
前 言 / 1
上篇 1776 年精神 / 3
论堪萨斯 / 4
布赖斯勋爵与现代民主 / 30
1776 年精神 / 51
现代利维坦 / 84
自由主义—一个过路站 / 93
论言论自由 / 102
中篇 历史与历史学家 / 115
历史学家的标签 / 116
亨利·亚当斯的教育 / 128
再论亨利·亚当斯 / 149
威尔斯与“新史学” / 156
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 / 177
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 / 218
下篇 解读 / 241
朱丽叶·德鲁埃与维克多·雨果 / 242
狄德罗的悖论 / 248
约翰·杰伊与彼得·范肖克 / 270
罗兰夫人的回忆录与信件 / 284
附 录
卡尔·贝克尔的主要著述及相关文献 / 312
译后记 / 333
|
| 內容試閱:
|
很久以前,我就学会了语句压缩,即如何将一小段话压缩成最短的几个词。我不确定,今天我还能不能做得到;但是,早年的那些训练自有它的用处,因为它使我懂得,要理解一个事物的基本属性,最好是能够剥去它所有外在的、不相关的附加物,也就是说,将它最大程度地简化。现在,带着些许忧虑,带着真诚的歉意,我要将这种方法,用于考察历史学这一主题。
首先,我要解释,当我使用“历史学”一词时,我指的是历史知识。无疑,在漫长的过去,出现过各种各样的事件,不论我们是否了解它们,它们都构成了某种终极意义上的历史。不管怎么讲,这些事件有很多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我们甚至不知道它们发生过;还有很多事件我们知道得并不完整;甚至还有少数事件,我们自以为知道了,但从不能绝对地确定。这都是因为,我们不能还原它们,不能直接地观察或者检验它们。事件本身一旦发生,作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事件就已消失;因此,在处理这个事件时,我们能够观察或者检验的唯一的客观现实就是时间所留下的某些物质线索—通常是书面文献。对于过往事件的这些线索、这些文献,我们应该感到满足,因为它们是我们所能拥有的全部。从它们之中,我们推断那是什么事件,我们断定那个事件如何如何,认为那就是事实。我们不说,“林肯被谋杀”;我们说,“林肯过去被谋杀,这在现在是一个事实”。事件是发生过,但不再发生了。我们一直坚持、必将坚持的,只是关于事件就是那样的事实断言;直到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的断言是错误的或者不充分的。那么,让我们承认,有两种历史:曾经一次性发生过的真实的事件系列,以及我们推断并记住的观念系列。第一种历史是绝对的、不可改变的—不管我们怎么说、怎么做,它就是它;第二种历史是相对的,总是随着知识的增长或精炼而改变。这两种历史或多或少地相互对应,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这种对应尽可能地准确。但是,真实的事件序列只能凭借我们所推断和记忆的观念系列而存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得不将历史等同于历史知识的原因。出于各种现实的目的,就我们而言,就当前而言,历史就是我们所知道的那样。
我打算压缩到最简化的程度的,就是这种意义上的历史。为做到这一点,我需要找到一个简洁的定义。我曾读到这样一句话,“历史就是关于过去发生的事件的知识”。这是个简洁的定义,但是还不够简洁。它里面有三个词还需要进一步考察。第一个词是“知识”。知识是一个令人敬畏的词。我总把知识想作某种收藏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或者《神学大全》里的东西,某种很难掌握的东西,某种无论如何我不具备的东西。这个定义一下子就剥夺了我作为历史学家的头衔,我不喜欢,因此我要问,什么是知识的关键所在?对了,那就是记忆(我是指广义上的记忆,指关于被推断的事件的记忆以及被考察的事件的记忆)。其他的因素也很重要,但是记忆是最根本的因素;因为没有记忆就没有知识。这样,我们的定义就变为:“历史就是关于过去发生的事件的记忆。”但是,“事件”这个词又暗指某些宏大的事物,比如,攻占巴士底狱、美西战争。一切发生过的事情未必都能宏大得成为一个事件。当我驾车行驶在伊萨卡岛那些曲里拐弯的街道上,这就是一个事件—有人做了事;如果交警用喇叭叫我靠边停车,这也是一个事件—有人说了话;如果我心里暗骂交警不该这样做,这也是一个事件—有人在思考。的确,人们所做、所说、所想的任何事情,都是一个事件,不论它看上去重要,或者不重要。但是,由于我们说话时一般都会思考,至少带有最起码的思考;由于正如心理学家告诉我们的,我们思考时不可能不说话,或者至少不可能不带有喉部的预先振动,我们就有理由将思想这个事件与说话这个事件合并到一句话里,这样,我们的定义又变成:“历史就是关于过去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的记忆。”但是,“过去”这个词既让人误解,又显得多余。它让人误解,因为当“过去”这个词被与“历史”这个词同时使用时,似乎指的是遥远的过去,而历史则止于我们出生之前。它显得多余,因为毕竟,一切所说的话、所做的事一旦被说出来、被做出来,就成为过去。因此,我省略这个词,这样我们的定义又变成:“历史就是关于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的记忆。”这才是将历史简化到最低程度的定义,但它包含了理解历史实际上是什么所需要的一切基本要素。
如果历史的本质就是关于所说的话和所做的事的记忆,那么很明显,每一个正常的人,张三、李四,都多少知道点历史。当然,说破这一点会让人不快,我们会尽可能避而不谈。我们摆出够专业的样子,说一般人哪里知道历史,这时我们的言外之意就是,他没能获得高级学位。而那些头脑简单的人,比如大学生等,在被按照知识的学术门类招收进来时,认为自己不懂历史,因为自己从来没有在以前的学校里上过历史课,或者从来没有读过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无疑,学术规则有它的用处,但是,要想理解历史,将其简化到最低程度,必须剥去的,正是这样一种表面的附加物。你、我、张三、李四都一样,都记得那些说过的话、做过的事,并且只要清醒着,就一定会记得。设想一下,张三早上一觉醒来,记不起说过的话、做过的事;那么,他真的就是灵魂出窍了。这种事有可能发生,人有可能突然忘记全部的历史知识。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事不会发生。一般情况下,当张三早上一觉醒来,他的记忆伸展到过去的国度、遥远的国度,自己倾心经营的那个小世界也即刻变得鲜活起来;他的记忆把那些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按往昔的样子拉到一起,并使之与他当前的观念,与明日将要说的话、将要做的事协调一致。没有这种历史知识,没有这种关于所说的话、所做的事的记忆,他的今日将变得盲目,他的明日也将没有意义。
既然我们是在最简洁的意义上谈论历史,我们应该说,这个张三还不是一个历史学教授,而只是一个没有额外历史知识的普通公民。由于没有什么演讲要准备,早上一觉醒来时,他关于所说的话、所做的事的记忆大概不会使他想到某些与李曼·冯·桑德斯的代表团或者《伪伊西多尔教令集》相关的事情;它只会使他意识到他昨天在办公室所说的话、所做的事的场景,意识到一个意义非凡的事件:通用汽车公司的股票跌了3个点;意识到上午10点安排了一个会议,意识到自己约好下午去打九洞高尔夫,或者意识到其他具有这类意义的历史事件。张三所知道的历史远不止这些;但是在他醒来的那一刻,这些就足够了—关于所说的话、所做的事的记忆,发挥着历史的作用,在早晨7点半,以其最简洁的方式,有效地调度着张三在自己经营的那个小世界里忙碌着。
或许,这些到最后还不够奏效,因为大家都知道,单纯的记忆是靠不住的。有可能,张三在喝咖啡时,不太容易意识到他现在回忆不起来的那些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我们都知道,并且感到很遗憾,这时候他没能记住历史事件,他只是记得有一个事件发生过,我们应该记得,但他却想不起来了。这种情况太常见了。这就是张三的难题,一些历史僵硬地、无生气地躺在史料堆里,不能对张三起任何作用,因为他的记忆拒绝将它们带入鲜活的意识。那么,张三该怎么做?他做的是任何历史学家都会做的事情:他要走进史料,搞点历史研究。从自己那个小小的“个人资料室”(我指的是他外套里的口袋)里,掏出一个本子—或许是《手稿》,第35册,翻到第23页,他读到:“12月29日,付史密斯先生的煤钱,20吨,1017.20元。”立刻,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在张三的脑子里鲜活起来。他脑子里映出这样一幅图画:自己去年夏天向史密斯先生订购过20吨煤,史密斯先生的货车开到自己的家门口,那些昂贵的煤从地窖窗口滑进去,扬起一片灰尘。这些历史事件,虽然不如《伪伊西多尔教令集》的伪造重大,但是对张三来说仍是有意义的:虽然它不是一个自己当时亲眼目睹的事件,但是,通过人为的记忆延伸,他能够对这个事件形成一个清晰的印象,因为他对手稿做了一点研究,那些手稿就保存在他的“个人资料室”里。
张三脑子里映出的那幅史密斯的货车把煤拉到自己家门口的景象,就是一幅关于过去所说的话、所做的事的图画。但是,这幅图画并非是孤立的,它并非一个好古之人自娱自乐的纯粹想象,相反,它与一幅关于将来要说的话、要做的事的画面相连;这样,整个一天,在张三脑子里,与那幅关于史密斯煤车的画面相连,时不时闪现这样一幅画面:自己下午4点要到史密斯的办公室付钱。到了4点,张三来到史密斯的办公室。“我要付煤钱,”他说。史密斯感到疑惑不解,他找出一本账册(或者一个档案盒),也对自己的“个人资料室”研究了一番,说道:“你不欠我钱,张三。你是来这里订购过煤,但是我这里当时没有你要的那种煤,所以你转到布朗那里去订购了。是布朗给你运了煤,你欠他的钱。”于是,张三来到布朗的办公室。布朗也拿出一本账册,也对自己的“个人资料室”研究了一番,结果,不错,史密斯是对的。于是张三付了钱,到晚上,他从乡村俱乐部回家后,又对另一堆文件做了一番研究,结果,的确,他找到了一张布朗的账单,上面清楚地标记着:20吨壁炉煤,1017.20元。到此,问题算是研究清楚了。张三心满意得,他找到了自己身上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的解释。
当听到有人说自己是一个历史学家,张三一定很诧异。然而很明显,他完成了历史研究所包含的所有基本过程,难道不是吗?人们要想做一件事情(这里要做的事碰巧不是发表演讲或者写一本书,而是付账;这对他、对我们造成误导,使他、使我们不知道他究竟在做什么),第一步就是回忆起那些说过的话、做过的事。事实证明,单凭记忆是不够的,他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查阅某些文件,以便找到必要的、还不知道的事实。不幸的是,结果发现,不同的文件记录是相互冲突的,这样,就必须对文本予以甄别和比较,以便消除误会。做完了这一切之后,张三打算做最后一步—通过记忆的延伸,在脑子里构造一幅画面,我们希望,这是一幅最终的画面,它有选择地包含了一系列事件:他向史密斯订购煤,史密斯又把订单转给布朗,布朗把煤送到他家。根据这个画面,张三就能付账了,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的。如果张三做这番研究,为的是写一本书,而不是为付账,那么就没有人会否认他是一个历史学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