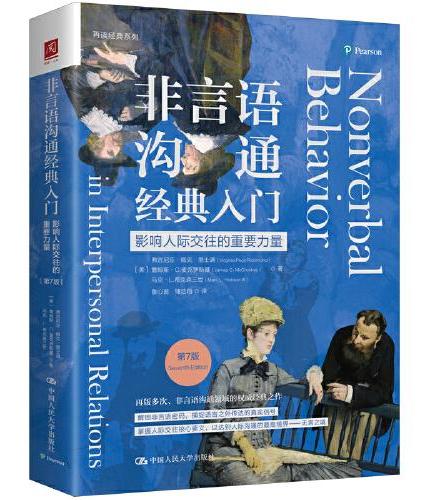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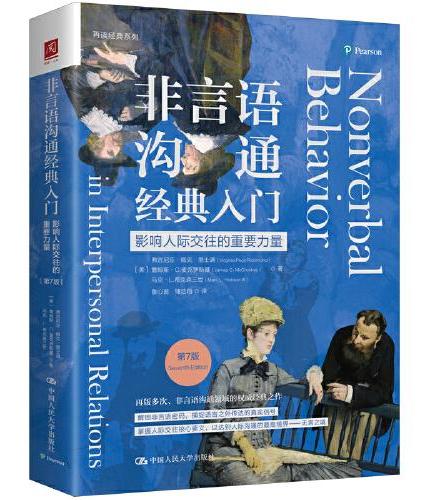
《
非言语沟通经典入门:影响人际交往的重要力量(第7版)
》
售價:HK$
123.1

《
山西寺观艺术壁画精编卷
》
售價:HK$
1680.0

《
中国摄影 中式摄影的独特魅力
》
售價:HK$
1097.6

《
山西寺观艺术彩塑精编卷
》
售價:HK$
1680.0

《
积极心理学
》
售價:HK$
55.8

《
自由,不是放纵
》
售價:HK$
54.9

《
甲骨文丛书·消逝的光明:欧洲国际史,1919—1933年(套装全2册)
》
售價:HK$
277.8

《
剑桥日本戏剧史(剑桥世界戏剧史译丛)
》
售價:HK$
201.6
|
| 編輯推薦: |
★ 职业光环背后,是鲜活的个人。
在外人眼中,心外科医生是神秘且强悍的人物,他与死神争夺生命控制权,是容不得同事犯错的严厉“大boss”,在医院里横着走了一辈子。但其实,他也曾内向瑟缩,也曾因自己的操作粗心坑惨队友,会因抢救稚童、老友的失败而心如刀绞;也要为了突发的抢救而忍痛抛下过生日的女儿、生产的妻子,甚至还会在自己接受小小的窥镜治疗时提心吊胆。他也和普通人一样有喜怒哀乐,有得意和悔恨,有长处和弱点……有危急关头的挺身而出和当仁不让的坚决意志。历史就是由这样一个个的人创造的。
★ 医学进步黄金时代的画卷。
自50年代心内直视手术出现以来,心外科经历了飞速发展:体外循环、人工辅助装置、各种高难度术式纷纷涌现,这背后则有众多医学天才群峰耸峙。作者于60年代进入医学院,在学习和执业的过程中,师从本托尔、罗斯等杰出前辈(皆有以自己命名的术式),更受教于成功应用体外循环第yi人柯克林、人工心脏移植第yi人库利。作者自己亦推动改进体外循环抗感染技术,将罗斯的瓣膜术式首次用于婴儿,用成人心脏辅助装置帮助儿童恢复、研发硅橡胶气管等,为心胸外科做出开创性贡献。透过本书,读者能看到,在那个对丙肝、
|
| 內容簡介: |
心外科医生,有着开胸换血、起死回生的神秘力量,但也是活生生的人,也经受着所有人都有的核心情绪——大部分时候。
一次诡异的运动事故,冥冥中将韦斯塔比塑造成了全球领军级的心外科医生之一。“我从打蔫的紫罗兰,变成了无拘无束、胆大自负的混蛋。我变得对压力免疫,成了习惯性的冒险者,始终渴求着刺激,像一块磁铁似的,把高风险病例吸到身边,并陶醉在和死神的竞赛之中。”
而又一个寒冷冬日,孩子的拯救和降生,“帮我改变了对生命的看法,也将我塑造成了一个更优秀的外科医生——我变成了比过去好得多的人,也重又明白了爱能带来欢腾、喜悦。”
透过韦斯塔比的心路剖白和自我反思,读者将看到一场场生命的冒险,一次次爱的悲欢,以及现代心外科那扣人心弦的全部故事——“它们正是在我这一生中渐渐铺陈开的,能够参与其中,我很自豪”。
|
| 關於作者: |
斯蒂芬·韦斯塔比(1948— ),心脏手术专家及人工心脏专家,生物工程博士,从医已逾半世纪,手术生涯约四十年。曾任牛津约翰·拉德克利夫医院心外科主任医师多年。现为Celixir公司医学总顾问、皇家布朗普顿医院基金会心外科主任医师、斯旺西大学生物医学工程教授。参与过近12000台手术,其中多有惊险、开创性术式。发表专业论文300余篇,编撰专业书籍十余种,屡获国内外奖项,如英国医学会主席奖、美国心脏学会心脏医学先锋奖、得州心脏研究所Ray C.Fish科学成就奖等。
译者简介
高天羽,笔名“红猪”,长期任《环球科学》杂志与果壳网翻译,出版译作数十种,如《遥远地球之歌》《世界为何存在》《恶的科学》《神经的逻辑》《脑子不会好好睡》《打开一颗心》等。
李清晨(审读),黑龙江人,小儿心胸外科医生,科普作家,著有《心外传奇》,纪录片《手术两百年》联合编剧。
|
| 目錄:
|
推荐序
前 言 1
序 章 5
章 家 庭 21
第二章 悲 伤 45
第三章 风 险 69
第四章 傲 慢 85
第五章 完 美 101
第六章 欢 腾 119
第七章 险 境 145
第八章 压 力 169
第九章 希 望 191
第十章 韧 性 215
第十一章 惨 痛 241
第十二章 恐 惧 259
致 谢 295
术语解释 299
译名对照表 307
|
| 內容試閱:
|
第二章 悲伤
晚上11点50分。侧面刷着“东英吉利卫生局”的救护车闪着蓝灯,终于到了。急救人员掀开后车门,早已过了当值时间的露西沿斜坡走了上来。我一看就知道是她。她带着一沓病历走向急诊部入口,好似电影《卡萨布兰卡》里的场景一般。那一瞬间,我心想,她可真美。
“您就是教授吧?”她说,“诺顿太太跟我讲过您。我是在剑桥受的培训,他们现在还会谈到您。”我心想肯定不是什么好话。
推车载着斯蒂夫受损的大脑和身体来到我们面前。我们六个月前还见过面,在医学院同学会上。他发表了一席风趣的讲话,庆祝在座各位都还活着,虽然他自己已经接受了一次心内直视手术。我当时还在下面开玩笑说,要是手术来找我做,结果可就不一定了。现在他被送来了牛津,情况危急,而他的家人仍在M25公路上。我们预想的重逢可不是这样的。我牵起他的左手,他随即牢牢抓住了我。他这一侧身体还能动弹。我们和露西排成一列,穿过急诊部,沿走廊直接进了手术室。我草草看了一眼CT片 :他的情况确实要命。
要先有同意书,我们才能做手术,但他现在孤身一人,我也不想把话说得太直接,只告诉他我会修复他的夹层,运气好的话,他的中风也能好。他艰难地告诉我,自己想在麻醉之前再看一眼希拉里和孩子们。露西有希拉里的号码,我打了过去。他们zui快也要45分钟才能赶到。时间每多过一分,神经系统恢复的可能性就少一分,而我们已经浪费了好多个小时。我向斯蒂夫保证,绝不会让他死,他用左手钩划了知情同意书,我也在下面签了自己的名字,戴夫·皮戈特随即注射了一剂保护大脑的巴比妥酸盐,送他去了没有知觉的世界。
我们已经把亲切交谈减到了zui少。外科手术必须不带感情,zui好连病人的名字都别知道。这不是什么大问题 :斯蒂夫已经说不出话,我也不可能向他讲述真实的风险—不做手术,他必死无疑。他也是医生,明白状况。在zui后的清醒时刻,我没必要给他徒增焦虑了。
我在咖啡间里坐定,直到他像百合花一样苍白的身体被涂上棕色碘伏,盖上手术巾。我不想看到他松垮的躯体。我更想记住他曾经的样子 :那副在冬日下午大步走进球场的健美体魄,涌动着肾上腺素,等不及要上场冲撞一番。我们那时如影随形,现在却扮演着截然不同的角色。斯蒂夫坐在诊室里,和病人们亲切地聊天,分发药片,实在是像样的医生。而值此深夜,我则在等着操刀手术,用摇摆锯锯开他的胸腔——还是在度过了充满失望、争执和痛苦的漫长一天之后。不过比赛一旦开始,肾上腺素就会驱散疲倦,让我忘记时间。
经过上一次手术,斯蒂夫的胸骨内面和心脏正面之间已经没有了心包和胸腺。扩张的主动脉薄如蝉翼,紧贴在胸骨下方。这种情况下,用摇摆锯再次开胸极其危险。为了降低致命大出血的风险,我暴露了他腿部的主要动脉和静脉,把它们连上心肺机。这样万一骨锯撕开心脏或主动脉,我还可以立刻切换到心肺转流,拿掉循环系统的压力,再抽干出血点的血。这一招多数时候都能奏效,但有时也会失败。心外科手术要真这么容易,那人人都能做了。
给斯蒂夫开刀就像为一座维多利亚时代的老房子更换管道。主管线都坏了,那些从锅炉连出来的管道也都得换掉——它们已经锈到不行,随时会崩碎。而我在作业时,绝不能任由热水在里面流动。我必须做和“鱼刺女士”一样的处理 :给他的脑部降温,把全身的血液都抽到心肺机里去。戴夫在他的头皮上连了脑电图电极线,监测他的脑波。随着体温下降,斯蒂夫的脑波渐渐消失,但他的脑波在中风后就已经不正常了。阿米尔沿着上次手术留下的疤痕切开皮肤,用电刀烧穿覆盖在骨骼上的脂肪,再用钢丝剪剪断上次的不锈钢骨缝线,将它们抽出。每次开胸骨我都要亲自上阵。想要摇摆锯切的深度恰到好处,需要精准的判断。你必须细细地感受它锯穿胸骨的一瞬,然后及时抽回,因为胸骨内面可能已经和右心室的肌肉粘在一起了。
出现夹层的主动脉呈现出吓人的深紫色,仿佛一只惊惶愤怒的茄子。透过薄薄的外膜,我可以看到下面的血液湍流。戴夫往食管里放了一只超声探头,位置就在心脏后方。探头显示主动脉壁的初始裂口位于冠状动脉的起点上方约1厘米处。冠状动脉是主动脉的关键分支,负责为心肌本身供血。我的任务是换掉撕裂的部分,将血流引回它的天然归宿,借此让斯蒂夫阻塞的脑动脉和肾动脉恢复供血。他那只损坏的肾脏肯定能恢复,但受伤的大脑就不太可能了。它已经太久没有得到血液和氧气,虽说巴比妥酸盐和降温或许能帮上点忙。
我吩咐灌注师布莱恩开始转流,给他降温到18摄氏度。把活人全身的血液都抽干可是件奇事。能干出这种事的,只有吸血鬼,和少数能给先天性心脏缺陷和各处的动脉瘤做手术的心外科医生。我是治这两种病的行家,把病人抽空是家常便饭。我曾在罗马尼亚的德古拉城堡做过一场关于“宰人”[宰牲即需要放净血液]的搞笑演讲,感觉自己仿佛回了老家。德古拉伯爵和我有很多共同点。
我在和时间赛跑时通常很放松,哪怕病人脑内已无血流。我不会站在那里思忖神经细胞的死亡,也不会匆忙下手。半夜一点半,我让布莱恩停止转流、开始抽血,这24小时里我是第二次下这样的命令了。斯蒂夫把那一腔加了抗凝剂的冷却血液抽进贮血器,这些血在被重新泵入体内前,会像一壶黑加仑汁一样存着。我切开抽空血液的撕裂主动脉,直到能看清那些通向头部和手臂的重要分支的内部。
第yi步是用组织凝胶重新黏合剥离的血管膜。我可是全世界首批使用这种胶水的外科医生,我经手的病人有很高的存活率,这种胶功不可没。然后,带着强迫症似的谨慎,我缝了一段移植血管上去,并在下面垫了几条特氟龙垫片,以防缝线割伤脆弱的组织。每个病人的性命都仰赖我的大脑皮层和指尖的连接,主动脉夹层的病人尤其如此。阿米尔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每一个动作,想学到我技术中的所有细微之处,这也是他乐意过来加夜班的原因。阿米尔总有一天能成事。
在没有血流的情况下,修补主动脉并装入移植血管用了34分钟。对正常大脑而言,这仍然在安全时限内,不过斯蒂夫的大脑已经不正常了。我们小心翼翼地将血液重新注入血管树,从头端的血管中排出空气。刚连回心肺机,针孔就开始渗血。出血要在逆转抗凝后才能止住—为防止血液在体外循环回路的异物表面上形成血栓,我们使用了抗凝剂。完成这样一台手术要记住许多细致步骤,但整个流程都刻在我的神经回路中,即便在凌晨时分,我也能不假思索地完成每一步。
现在该加热血液,恢复正常体温了。当温暖的血液流经冠状动脉,斯蒂夫的心肌又活了回来,它先是扭了几扭—我们管这个叫室颤,接着就自发除颤,开始缓慢而慵懒地收缩起来。随着体温越升越高,心脏收缩得也越来越快。很快,脑电图上重新出现了脑波。戴夫认为情况似乎已经有了一点好转。
这种复苏过程我们以前只见过一次。当时我们是在努力抢救几个孩子,他们坠入了冰层,溺亡在冰冻的池塘中。像这种情况,只在加拿大有过几例罕见的幸存案例。牛津的创伤科医生逼着我们加热那几具没有生命的躯体,zui后我们成功救活了心、肺、肝、肾,但孩子们的脑已经受了致命伤。我们先是给了他们的父母以希望,而后又夺走了它。
凌晨3点,我把手术台交给了阿米尔。复温要持续30分钟,而此时我得知希拉里和其他几名访客已经等在重症监护家属室。从好的方面说,他们的到来打破了我们和护理团队的僵局,现在我至少知道有一张床位在等他。我走到家属室门口,他们一下子都站了起来。这倒不是出于尊敬,只是条件反射。这里的人又可以开一场医学院同学会了——斯蒂夫的人缘就是这么好。在场的人中,斯坦是肿瘤学教授,约翰是麻醉主任医师,彼得是全科医师。他们都是来支持希拉里和孩子们的。
根本来不及打招呼,我先说了他们想听的消息:斯蒂夫情况不错,我已经补好主动脉,并给大脑恢复了供血。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这简单的一句话就让他们放下了悬着的心,解开了心里的疙瘩。只要有消息,无论好坏,总能消解对未知的极大恐惧。当他们站在这里,在深夜中远离家乡,他们的老伙计却扮演着另一重角色。这时的我不再是那个来自斯肯索普的酒鬼傻小子了。
拥抱、亲吻和安慰的话随之而来,然后是那个常见的要求:“我们现在能看看他吗?”我只好解释说斯蒂夫还在手术台上,胸腔仍然大敞着,身体正在心肺机上复温,人还没完全脱离危险,但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我补充说,可能要再过两个小时,我们才能控制出血,关闭胸腔。说完这句我就走了,打算去向护士长道歉,因为我冷不丁塞给他们这么个病人。但我发现护士的人手其实是够的——上一个从导管室送来的心脏病发作患者左心室破裂,救不了了。轰鸣的传送带继续迎来送往。
我疲倦地溜达回手术室,和两名麻醉医师一起坐在斯蒂夫的床头。阿米尔很开心能继续主持手术。斯蒂夫的体温已经回升到37摄氏度,心脏虽说还是空的,但看它的样子已经不再愤怒了。我要布莱恩在里面留一点血,这样万一有残留的空气也都可以射进移植血管。我听见斯蒂夫的人工主动脉瓣发出了令人安心的嘀嗒声,借着心脏后面的超声探头,我们能看见小气泡快速通过主动脉瓣,就像一场暴风雪。不用我提,阿米尔已经把排气针安插到位。气泡间歇性地冒出,zui后完全停止。我们现在可以关心肺机了。我要戴夫开始往他的肺部通气,很快就听见布莱恩说“停止转流”。阿米尔和代班主治医像两个足球比赛观众似的站在一边,看着我在凳子上发号施令。我在监视屏上仔细查看心脏和主动脉的内部图像,他们俩则从外面观察。
“怎么样,”我问阿米尔,“有出血吗?”
“看上去非常好。只是移植管周围有点渗血。没有大问题。”
“那么你接下来要怎么做?”
没有回答。他太累了。
“注射鱼精蛋白。”我吩咐戴夫。鱼精蛋白是从鲑鱼的精液中提取的,能够逆转肝素的抗凝作用,肝素则来自牛的内脏。所以我这门高贵的专业,是托了牛鱼之福,在凌晨的这个时候想到这一点,真是发人深省。
阿米尔在心脏周围轻轻塞满纱布块,好让渗出的血液凝在上面。接着他开始放置胸腔引流器,再用不锈钢丝关胸。墙上的挂钟显示着4点30分。戴夫翻阅着一本摩托车杂志,布莱恩问我他能不能撤掉机器,为早晨的手术做好设置,然后就回家。有些人真是没耐力。阿伊琳和她的巡回护士也都蔫了。我建议她们在输入血液和凝血因子时轮流休息一下。终于,手术室里注入了一丝宁静。任务完成!
手术楼后面是一片停车场,停车场后面是老海丁顿墓地,两者间只隔了一道由未修剪的女贞和小松柏组成的薄薄树篱。我在夜色中走了出去,经过那辆始终没有开往剑桥的奔驰车,它的副驾位子上还藏着要送给杰玛的生日礼物。我信步穿过那座华丽的金属栅栏门,爬上一片俯瞰剑桥郡乡间的小山坡。我来到一个女婴的坟墓旁,在草地上安静地平躺下来,仰望夜空。那块墓碑上写着“幼年早逝”的字样。她是 20 年前在我手里走的,这件事我一直不曾忘记。要是还活着,她也该到杰玛这个年纪了。然而上帝却给了她一颗扭曲纠结的心,我没有治好。所以情绪低落时,我常会来和她坐坐,只为提醒自己,我不是战无不胜的。今天真是艰难的一天。还是应该说是昨天?
清晨6点。阳光突破了地平线,麻雀开始啾鸣。汽车的头灯在下面的牛津环路上快速闪过,载着早早起床的伦敦通勤者和在考利(Cowley)汽车厂上夜班的人。苏应该已经在来办公室的路上了,于是我慢吞吞地走回 5 号手术室,现在里面空荡荡的,只有阿伊琳一个人。她正在擦洗地上的血液和尿液,为上午的手术清单做着准备。斯蒂夫已经被送到 ICU,在他那个大家庭的簇拥之下,情况很稳定。
阿米尔兴冲冲地说 :“精彩的一例!真高兴你打给了我。”
那个代班主治医已经不见人影。大概是捡财宝去了。
我看上去很糟,闻起来也很糟。于是我去更衣室冲了个澡,换了一身干净的蓝色手术服。这个仪式标志着昨天的结束和今天的开始。我走进办公室,先给苏泡了茶,然后就着我自己的茶水服了一剂利他林。牛津的学生们会用这种兴奋剂来集中注意力、提高考试成绩,我也会在累坏的时候用它提神,或是在倒时差的时候配合褪黑素使用。当然了,这都是为病人着想。
早上七点半,我加入了 ICU 的查房队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