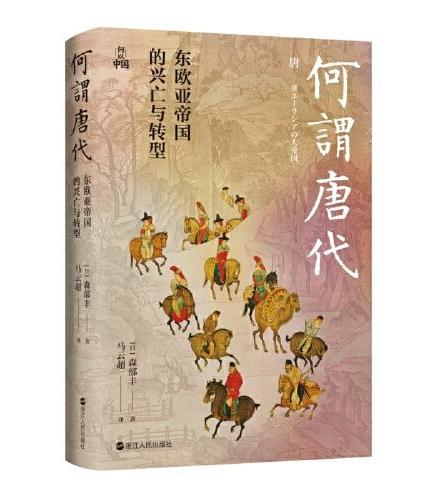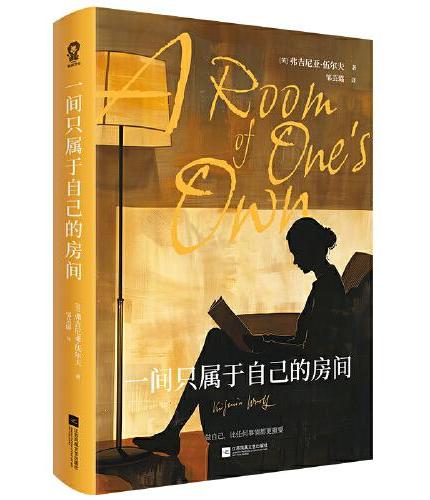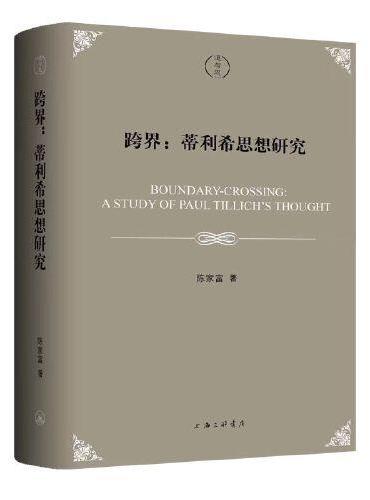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无端欢喜
》
售價:HK$
76.2

《
股票大作手操盘术
》
售價:HK$
5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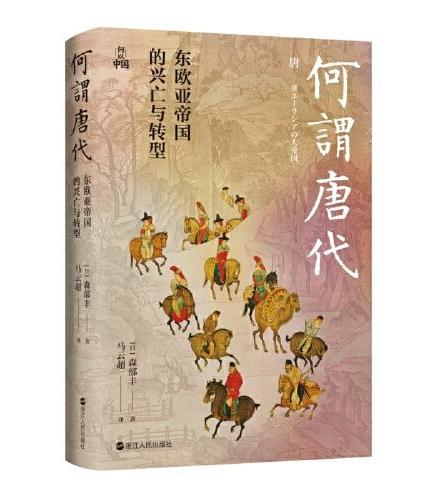
《
何以中国·何谓唐代:东欧亚帝国的兴亡与转型
》
售價:HK$
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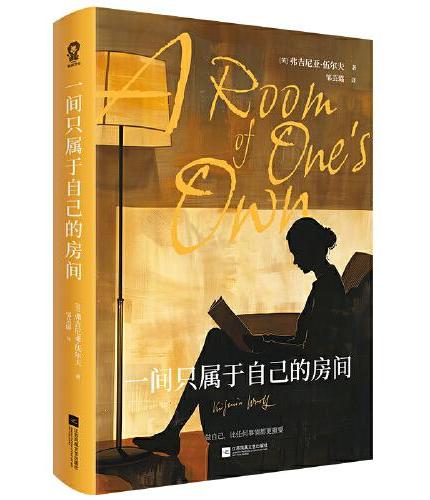
《
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 女性主义先锋伍尔夫代表作 女性精神独立与经济独立的象征,做自己,比任何事都更重要
》
售價:HK$
44.6

《
泉舆日志 幻想世界宝石生物图鉴
》
售價:HK$
134.2

《
养育女孩 : 官方升级版
》
售價:HK$
50.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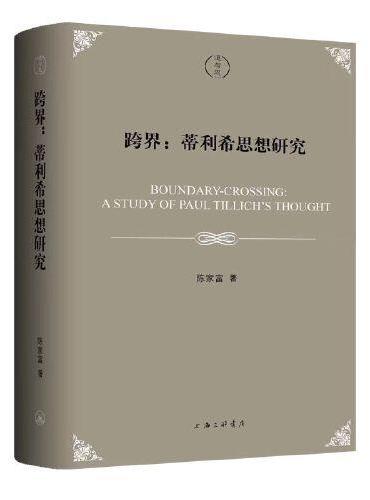
《
跨界:蒂利希思想研究
》
售價:HK$
109.8

《
千万别喝南瓜汤(遵守规则绘本)
》
售價:HK$
44.7
|
| 編輯推薦: |
颠覆传统的新式奇幻,现实主义的写作风格打破传统,引领幻界新风潮。
乔·阿克罗比的成名巨作!出版即横扫欧美市场广受赞誉。
《律法》系列入围2008年康普顿库克奖、2010星空幻想奖 、2010 幻想文学大奖决赛。
被英国奇幻图书书评百大奇幻。
该系列GOODREADS累计40多万好评。
|
| 內容簡介: |
卷一:
这是一个魔法正在消失的时代,
这是一个英雄不再、腐败滋生的世界。
强大的蛮族战士、自恋的青涩贵族、残缺的审问官和怨毒的女战士,
神通广大的大法师将他们召集到一起。
命运的罗盘缓缓转动,
谁将获得救赎?
谁能打破枷锁?
卷二:
为拯救王国,审问官临危受命,孤身前往南方主持大局;
为对抗强敌,法师组建的非主流队伍万里迢迢远赴海外,
寻找救世良方。
然而既往的恩怨并未结束……
在世界的边缘,
在荒芜的诅咒之城,
盘踞着过去的阴影……
卷三:
国王驾崩,群龙无首,
强敌压境,步步紧逼。
然而冥冥中自有天意,
法师与他精心挑选的队伍终于触及到终极奥义。
这一次,
律法将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
这一次,
离打开分割人魔两界的大门仅剩咫尺……
|
| 關於作者: |
作者简介:
乔·阿克罗比,英国著名当代奇幻作家,新史诗奇幻流派领军人物,曾为电影剪辑师。他以“律法”三部曲成名,其作品着重于将高度现实主义的人物描绘和高度戏剧化的情节转折相结合,在欧美幻想文坛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该系列入围2008年康普顿库克奖、2010星空幻想奖 、2010 幻想文学大奖决赛。并被英国奇幻图书书评百大奇幻,迄今已被翻译为数十国语言。其《破碎之海》系列也摘得2015轨迹奖。随后更是佳作连连,律法独立续作《英雄》《冷宴》等也收获了超高口碑。
译者简介:
屈 畅,“冰与火之歌”系列译者,致力于创办国内为优秀的大部头奇幻书籍品牌“史诗图书”,《巨龙的颂歌—— 世界奇幻文学史》作者。
赵 琳,“冰与火之歌”系列译者。就职于史诗图书。
|
| 內容試閱:
|
卷一:
罗根来不及穿鞋。
他跌跌撞撞穿行于林间,踏过黏滑的湿地、污泥和潮湿的松针,胸脯因急促的呼吸而剧烈起伏,血液在脑中嗵嗵乱撞。他打了个趔趄,四仰八叉摔倒在地,手中战斧差点劈开自己的胸膛。他躺在那儿喘粗气,望着影影绰绰的森林。
他很确定狗子片刻前还跟他一起,现在却全无踪影。其他人也不知下落,他和他的手下被冲得七零八落。他本应回去和他们会合,无奈到处都是山卡1。他感觉到它们在林间穿梭,鼻子里充满它们的气息。左边隐约传来打斗的呐喊,罗根慢慢从地上起身,努力不发声。只听“噼啪”一声响,树枝清脆断裂,他迅速回头。
一支长矛向他刺来,恶狠狠地来势汹汹。执矛的正是个山卡。
“见鬼。”罗根咒道。他扑向一旁,脚下一滑,摔了个嘴啃泥。他在污泥中扑打翻滚,心想自己的背随时可能被一矛刺穿。他慌乱爬起,惊魂未定、气喘吁吁。当他看到矛尖再次刺来,赶紧一个急闪,连跌带滑躲到大树干后。等他探头,扁头一声低吼,又是一刺,他立刻闪向树干另一边—之前只是虚晃,扁头果然中计。罗根用尽全身力气大吼,绕过树干跳出去挥斧砍下。随着“咔吱”的骨骼碎裂声,斧刃深嵌入山卡的脑壳。罗根向来幸运,他觉得自己的幸运也该到头了。
扁头站在那,眨眼瞪他,然后开始左右摇晃,鲜血沿脸颊滴落,终岩石般砰然倒地,在罗根脚下不停抽搐。它倒地之势几乎将罗根手中战斧带飞,罗根竭力握住斧柄,而山卡死握着长矛,矛尖就像打麦的连枷一样在空中挥舞。
“啊呀!”矛尖划过胳膊,罗根大叫一声。同时他感到一片阴影笼罩在脸上。另一个扁头。该死,另一个大家伙。敌人已欺身向前,双臂抓向他,而他的战斧尚未拔出,闪躲也来不及。罗根张大了嘴,却说不出一个字。命在旦夕,你能说什么呢?
他们撞在一起,倒在湿地上,在淤泥、荆棘和断枝间翻滚,咆哮着挥拳撕打。罗根的头重重地撞到树根,耳朵嗡嗡作响。他随身带了把刀,却想不起放在哪里了。他们就这样翻滚着,翻滚着,一路滚下山坡,周围天旋地转。罗根一边使劲摇头,驱除脑中的眩晕,一边死命勒住扁头的脖子。他们一路滚落,似乎永无止境。
在悬崖边安营扎寨本是个好点子,因为谁都没法摸上绝壁;但当罗根的肚子触到悬崖边,这个好点子失去了所有说服力。他双手胡乱抓向湿地,却只抓到松软泥土和褐色松针,不论手指怎样用力,却什么都抓不牢。他开始坠落,不禁呜咽起来。
双手终于抓住了什么。是一条从峡谷边缘探出的树根。现在他在空中晃来晃去,大口喘气,但死死抓着树根。
“哈哈!”他放声大笑,“哈哈!”他还活着。两个扁头就想结果九指罗根?他试图拽自己上去,但没成功。脚太沉。他朝下望。
河谷很深,两边都是陡峭石壁。树木从岩石缝中生出,枝叶朝四面八方扩展,伸向空空的天际。河水在下潺潺流过,水势激猛,与参差的黑色岩岸激起白色水沫。这些足够险恶了,但真正的麻烦近在咫尺—他没有摆脱那个体型巨大的山卡,对方肮脏的双手死死箍住他的左脚踝,身体在空中来回微荡。
“见鬼!”罗根咒道。麻烦大了。他曾多次遇险,但总能活到为胜利高歌的一刻,可当下处境是糟糕的,令他不由得反省人生。现在看来,那是多么痛苦、无趣的一生啊,他这一生没让任何人过得更好,他这一生充斥着暴力与伤痛,还夹杂着一些失望和困苦。他双手发麻,前臂犹如火烧,而大块头扁头非但看起来一时半会不会自行掉入河谷,反倒拽着他的腿往上挪。
它停下来,抬头盯着罗根。
换做是罗根抓着山卡的脚踝,他极可能想:“我的命全靠手里这条腿了,好不要贸然行动。”人类会选择自保,但罗根很清楚山卡不会这么想。果不其然,只见它张开大口,深深咬入他小腿。
“啊呀呀呀!”罗根闷哼一声,随即放声号叫,赤裸的脚跟使劲砸山卡的头,很快砸出一道血淋淋的伤口,却止不住它撕咬。他蹬得越厉害,抓在滑腻树根上的双手就越往下滑。手里树根所剩不多,看样子随时可能折断。他努力不去想双手和前臂的疼痛,不去想小腿里扁头的牙齿。他就要掉下去了,能选择的是掉在岩岸边的石堆里,还是掉入奔腾的水流中。
他顶多只有这两个选择。
与其担惊受怕,不如放手一搏,罗根的父亲常这样说。于是他用能活动的右脚紧抵岩壁,深吸一口气,用尽仅存的力量荡出去。他感到小腿里的牙齿松开了,接着是紧握脚踝的双手,一瞬间,他如释重负。
然后他开始下坠,势如流星,河谷两旁的岩壁飞掠而过—褐岩、青苔和小堆积雪都在翻滚。
罗根缓慢地在空中翻身,四肢乱舞,吓得喊不出声。疾风抽打着双眼,撕扯着衣服,堵住了呼吸。他看到大个山卡撞上旁边岩壁,弹开滚落,粉身碎骨,必死无疑。真是喜闻乐见,但他的满足感一闪即逝。
流水迎面扑来,像狂奔的公牛冲向他,挤出肺里空气,驱赶脑海中的意识,将他吞入冰冷的黑暗……
卷二:
该死的雾。它涌进眼睛,让你只能看清前方几跨1;它涌进耳朵,让你啥都听不见—听见也辨不清方向;它涌进鼻子,让你只闻到潮气、湿气。该死的雾,探子的天敌。
他们几天前渡过白河,离开北方进入安格兰。一路上狗子都很紧张。侦察陌生的土地,时刻担心卷入战团,这压根儿非他们本意。所有人都紧张。除了三树,他们都没离开过北方。寡言或许例外,他从不说自己去过哪儿。
他们路过几个被烧毁的农场,途经一座杳无人烟的村子,联合王国的房屋又大又方。他们看到马和人的足迹,不少足迹,却没见人。狗子知道贝斯奥德离得不远,正派人四处扫荡,烧光杀光抢光—大肆破坏。贝斯奥德的探子也无处不在,倘若狗子或他们中其他哪个被抓,便只有死路一条,而且会被慢慢折磨死。千刀万剐,脑袋插矛上等等,狗子心知肚明。
若被联合王国抓住呢?多半也是死吧。毕竟双方在打仗,打仗的人脑子不好使,狗子不觉得他们会浪费时间分辨北方人的好坏。总而言之,他们性命岌岌可危,这足以让他们紧张了,何况他本是个容易紧张的家伙。
现在的雾更是雪上加霜。
雾中缓步潜行让他口渴,于是他穿过茂密灌木,往水声传来的方向走。到河边,狗子跪下双手掬水喝。这里落满腐烂树叶,十分湿滑,但区区湿滑顾不得了,反正他脏透了。一阵风从树林外吹来,浓雾倏忽聚拢,继而散开,让狗子看到了他。
他躺在狗子前头,双腿泡在河里,上身在岸上。他们四目相对,都吓得愣住了,直至狗子看到他背后露出一截长棍子—一根折断的长矛—才意识到:他死了。
狗子往水里吐口唾沫,缓缓逼近,同时环视四周,以防有人从背后偷袭。这是个二十多岁的男人,黄发,灰唇上残留着棕色血迹。尸体身着被水泡涨的加垫夹克,这一般是穿在链甲下的。看来是个战士,可能掉了队,迷了路然后被杀。肯定是联合王国人,但外貌和狗子及其他北方人也没什么不同,并且现在人死了,死人看起来都差不多。
“大平衡者。”狗子心情复杂地轻声道。这是山民对死神的叫法。死神面前,众生平等。无论有无外号、南方北方,他终都会逮住你,一视同仁。
水里的人看来没死几天,凶手可能还在附近,这才是狗子担心的。迷雾中充满声音,可能有上百亲锐埋伏着等他们,也可能只是河水潺潺。狗子抛下河边尸体,潜回树林,矮身躲过灰雾中出现的一条条树枝。
他差点被一具树叶半埋的尸体绊倒,此人手臂大张,仰面朝天。另一具尸体侧面中了两箭,脸栽在泥里,双膝下跪,屁股撅天。狗子早知死没有尊严可言,他加快脚步,想尽早与其他人会合报告,尽早远离尸体。
结果他看到更多尸体,简直要受不了了。他从来受不了尸体。人变尸体很简单,他知道一千种方法,而无论哪种都没有后悔药吃。前一秒那人还充满希望、思想和梦想,有朋友、家庭与归宿,下一秒就入土了。狗子想起受过的伤、参加过的战争和搏斗,不禁感叹还活着真幸运。傻瓜的幸运。他担心自己的运气是不是到了头。
他快跑起来了,在浓雾里像个浑小子一样乱撞。不再沉心静气,不再嗅探,不再倾听。他是有外号的人,几乎踏遍北方每寸土地,原不该如此莽撞,但人总有例外情况。
他从没见过眼前这番景象。
他身侧被狠撞了一下,摔个狗啃屎。他想爬起来,却立刻被踢倒。他试图还击,但袭击他的杂种力大无比,不等他动手,又把他仰面朝天踢翻在地。他只能咒骂自己粗心大意,咒骂自己,这些尸体还有这片雾。一只手钳住他脖子,快要捏碎气管。
“嗨啊。”他呻吟着抓挠那只手,心知在劫难逃,所有的愿望即将化为尘土。大平衡者终于还是逮住他了……
对方的手指停住了。
“狗子?”有人在他耳边问,“是你?”
“嗨啊。”
那只手松了,狗子使劲吸了口气,感觉自己被拉着外套拽起来。“我操,狗子!差点儿弄死你!”他听出声音了。好吧,狗日的黑旋风。狗子为差点被他掐死而生气,又为还活着傻开心。真是个傻瓜。他听到黑旋风笑话他。笑得真他妈难听,像乌鸦叫:“你没事?”
“你好热情。”狗子一边使劲儿喘气,一边哑着嗓子说。
“算你小子走运,我本想下重手咧。重手咧。我当你是贝斯奥德的探子,我以为你走远了,在山谷对面。”
“你看到了,我没去。”他轻声说,“其他人呢?”
“在操蛋的雾飘不到的山头上,那里看得远。”
狗子冲来路点头。“那边有尸体,很多尸体。”
“很多尸体?”黑旋风问,好像狗子不明白很多尸体是个什么概念,“哈!”
“没错,是很多,而且我估计死的都是联合王国人。似乎打了一仗。”
黑旋风又哈哈大笑:“打了一仗?你估计?”狗子不确定他什么意思。
卷三:
“好个寒夜!”狗子高声说,“都快夏天了!”
三人齐齐看向他。近的是个老头,一头灰发,面容沧桑。他身后是个左臂齐肘断掉的年轻人。后是个半大孩子,站在码头边,郁郁地望着漆黑的大海。
狗子夸张地一瘸一拐走过去,拖着条腿,装作痛得龇牙咧嘴的样子。他摇摇晃晃走到高杆灯笼下—警钟就在杆子上—朝三人扬起手里的瓶子。
老头笑着把矛立在墙根。“水边总这么冷。”他搓着手迎上来,“幸好你带了暖身子的,呃?”
“是啊。幸好幸好。”狗子起开瓶塞,晃晃瓶子,拎出个杯子,倒了点酒。
“不用客气,呃,兄弟?”
“那当然。”狗子又倒了杯酒。独臂男为拿杯子,不得不放下长矛。男孩后才过来,警惕地把狗子打量了个遍。
老头用手肘顶他:“小子,你老妈会管你喝酒啊?”
“谁怕她?”他故意放粗嗓子,凶巴巴地反问。
狗子递过杯子。“照我说,你有力气提矛杀敌,就该有胆子举杯痛饮。”
“那当然!”他恶狠狠地从狗子手里抢过杯子,但烈酒下肚仍让他不禁打战。狗子想起自己次喝酒,难受到不行,只觉天旋地转,于是笑了。男孩却以为他在嘲笑自己。“你到底是谁?”
老头啧了一声:“别管这孩子。他还小,以为装出一副粗鲁模样才让人看得起。”
“没啥。”狗子说着给自己倒了杯酒,把瓶子放在石头上。他利用这片刻余暇仔细思考将说出口的话,确保不出错。“我叫克里格。”他认识一个叫克里格的人,那人死于山间的争斗。他对那人没啥好感,不知是怎么联想到的。算了,眼下哪个名字都差不多。他一拍大腿。“这腿在杜别克挨了一下子,没好利索,没法赶路啊。头儿看我这样上不了前线,就送我过来,和你们一起发呆咯。”他一偏头,只见月光下的海面水纹荡漾、波光粼粼,宛如活物。“倒也好。老实讲,老子全身都是疤咧。”至少后一句绝非虚言。
“我理解。”独臂在狗子眼前晃了晃断肢,“外面咋样?”
“还那样。联合王国人干坐在自己的要塞外面,挤破头想进去,而我们在河对岸以逸待劳。相持好多个星期了。”
“我听说有些小子跑到联合王国那头去了。听说老三树也现了身,还死在战场上。”
“他可是我们这儿的大人物,三树鲁德。”老头说,“大人物啊。”
“可不是。”狗子点点头,“可不是。”
“听说狗子接了班。”独臂说。
“真的?”
“据说是真的。那个下流坯,生得牛高马大,叫他狗子是因为他咬掉过女人的奶头。”
狗子眨眨眼:“是吗?哎,我没见过他。”
“我听说血九指也来了。”男孩压低声音,双目圆瞪,活像见了鬼。
另两人嗤之以鼻。“血九指早死啦,小子,那个操蛋的魔鬼死了才好。”独臂打了个激灵,“妈的,净说些触霉头的话!”
“都说了只是听说。”
老头又灌口酒,舔舔嘴唇。“爱咋咋地。反正联合王国人夺回要塞就会厌倦北方,然后漂洋过海滚回家,一切又恢复正常。不管咋说,不会有谁来乌发斯。”
“是啊,”独臂欢快地说,“谁也不会来这儿。”
“那我们干吗来这儿看守?”男孩抱怨。
老头翻个白眼,仿佛已无数次听过这个问题,又无数次给出相同答案,“因为这是我们的任务,小子。”
“任务就是任务,必须完成。”狗子想起罗根说过这个,三树也说过。现在两人都去了,都入了土,但道理没变。“不论是无聊的任务、危险的任务,还是肮脏的任务。哪怕是你不想做的任务。”见鬼,他又尿急,一碰上这种时候就想撒尿。
“是这个理。”老头盯着杯子笑了,“身不由己啊。”
“没错。可惜了,你是个不错的头儿。”狗子把手伸到后面,好像在挠屁股。
“可惜?”男孩迷惑不解,“什么意—”
话音未落,黑旋风已出现在他身后,割开了他的脖子。
寡言的脏手几乎同时钳住独臂的嘴,血淋淋的刀尖从独臂的斗篷中穿出。狗子纵身一跃,朝老头肋下快速捅了三刀。老头气噎一声,身形晃动,双眼大睁,手里还拎着酒杯,张大的嘴无力地流出涎水,接着便倒下了。
男孩拼尽全力爬出一小段路,一只手捂着脖子想止血,另一只手伸向挂警钟的杆子。他挺有胆气,狗子心想,喉咙都被割开了,还想着报警。但男孩没爬出一跨远,黑旋风便重重一脚跺在他脖子上,彻底结果了他。
男孩颈骨的断裂声让狗子一阵恶寒。他不该落得这等下场,真的不应该,但战争便是如此,太多人无谓地死去。无论如何,任务就是任务,他们三个毫发无伤地做到了,还能有更好的结果吗?只是他嘴里一阵苦涩。他从不觉得这是个轻松活儿,而现在比以往更难受,因为他成了头儿。
奇特之处在于,在别人的命令下动手杀人要容易得多。
杀人不是个轻松活儿,不比想象—当然,除非你名叫黑旋风。这混蛋杀人跟撒尿一样轻松,是个无可挑剔的行家里手。狗子看他弯腰从独臂软绵绵的尸体上扯下斗篷,披到肩头,然后漫不经心、像扔垃圾一样把尸体翻进海里。
“你有两只手。”已披上老头斗篷的寡言说。
黑旋风瞅了他一眼:“你想表达什么?老子当然不会为了装得像就自废一条胳膊,白痴!”
“他的意思是可以藏起来。”狗子看着黑旋风用脏兮兮的手指擦擦一只杯子,倒了酒一饮而尽。“这种时候你喝得下?”狗子边扒男孩沾血的斗篷边问。
黑旋风耸耸肩,又倒一杯。“浪费可耻呗。何况就像你说的,好个寒夜。”他狡黠一笑,“操,他奶奶的你可真能扯,狗子。叫克里格。”他夸张地晃荡两步。“这腿在杜别克挨了一下子!咋想出来的?”他扬手拍拍寡言的肩膀,“妙极了,对吧?有个形容词儿叫啥来着?那词儿叫啥来着?”
“以假乱真。”寡言说。
黑旋风眼睛一亮。“以假乱真。没错,狗子,你这个以假乱真的杂种。我敢说,你就说自己是‘无帽人’斯凯林他们都会信。睁眼说瞎话!还一本正经!”
狗子笑不出来。两具尸体倒在石头上,他都没敢仔细看一眼,暗自惦记男孩少了衣服会不会冷。这想法够蠢的,毕竟男孩就在一跨外,淹没在自己的血泊中。
“别废话了。”他嘀咕,“快把他们处理掉,然后去门边守着。说不定有人过来。”
“行啊,头儿,行啊,你说啥都行。”黑旋风把两具尸体推入水中,拽下警钟的舌头,使劲扔进大海。
“可惜。”寡言说。
“啥?”
“可惜这口钟。”
黑旋风冲他眨眼:“可惜这口钟,天啊!你咋突然多话了?不过你知道吗,我更喜欢之前的你。可惜这口钟?疯了吗小子?”
寡言耸肩:“南方人来了说不定需要。”
“那他奶奶的就跳水去捡,很难吗?”黑旋风抓起独臂的矛,大摇大摆地走向敞开的大门,一只手缩进抢来的斗篷,嘴里喃喃自语。“可惜这口钟……他奶奶的死者在上……”
狗子边舒活脚趾边摘下灯笼,面朝大海举起来,再用斗篷盖住。他又举了两次才将灯笼挑回杆上。摇曳的小火苗承载着所有希望,它是宁静的大海边能看见的光源。
他在原地久久等待,等着整件事搞砸,等着镇里喧闹起来,六十名亲锐涌出大门,干掉他们这三个来找死的人。他越想越憋不住尿,然而什么也没发生。万籁俱寂,只听见空心的钟碰撞杆子,冰冷的浪涛拍打石头和木材。一切正如计划。
艘船自黑暗中悄然滑出,船头的摆子咧嘴而笑,身后是紧紧挤在一起的二十名亲锐。他们谨慎万分地划桨,苍白的面孔神情专注,咬紧牙关以保证安静,但每一次木头或金属的碰撞声,仍会让狗子心头一颤。
船靠近后,摆子及其手下挂了几袋稻草在船边,消减木板撞击石头的动静。一切都按照一周前的计划进行。狗子和寡言抓住扔来的绳子稳住船,再将绳子绑紧。狗子抬头看了眼静静靠在大门旁墙上的黑旋风,后者轻轻摇头,表示镇里没异动。这时摆子已悄无声息上了岸,在黑暗中蹲身靠近。
“干得好,头儿。”他满脸笑容地轻声道,“干净利落。”
“待会儿有时间庆祝,现在先把其他船安顿好。”
“行啊。”更多的船驶出黑暗,带来更多亲锐、更多稻草。摆子的手下稳住船,把人拉上岸。近几周有许多北方人来投诚,什么样的都有,的共同点是不满贝斯奥德的新做派。水边很快聚起好大一群人,若非亲眼所见,狗子绝不敢信。
他们按计划分成几队,每队有自己的头儿和任务。有些家伙熟悉乌发斯,狗子早先让他们在泥地里画出草图,并让所有人仔细看过,做到心里有数,这是三树的风格。想起黑旋风当时的怨言,他不禁莞尔,现在看来都值得。他蹲在门边,目睹众人鱼贯而入,每队都井井有条、无声无息。
打头阵的是巴图鲁,带着十二名亲锐。“很好,霹雳头,”狗子说,“你负责主门。”
“行啊。”巴图鲁点头。
“你的活儿是重中之重,一定要安静。”
“安静,行啊。”
“好运,大巴。”
“用不着。”大个子说着带人匆匆消失在漆黑夜色中。
“红帽子,你负责井边的塔和塔边的墙。”
“好的。”
“摆子,你和你的手下在市镇广场把风。”
“放心吧头儿,猫头鹰都没我们看得紧。”
他们一个接一个进门,踏入黑乎乎的街道,跟微风吹拂海面、海浪拍打巉岩一样沉静。狗子给每队分派任务,拍着肩膀将他们送走,后轮到黑旋风,他带着一队凶神恶煞的手下。
“黑旋风,你负责镇长大厅。照说好的,周围架上木头,但别点火,听见没?别乱杀人,还没到时候。”
“还没到时候,好吧。”
“还有,黑旋风。”他转过身,“别招惹女人。”
“你把我想成啥了?”黑旋风的牙齿在黑暗中闪过一道寒光,“牲口吗?”
终于安排完毕,只剩他、寡言及其他数人守望水面。“嗯。”寡言缓缓点头,这算是很高的称赞了。
狗子指指杆子。“把钟弄下来?”他说,“看来会用得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