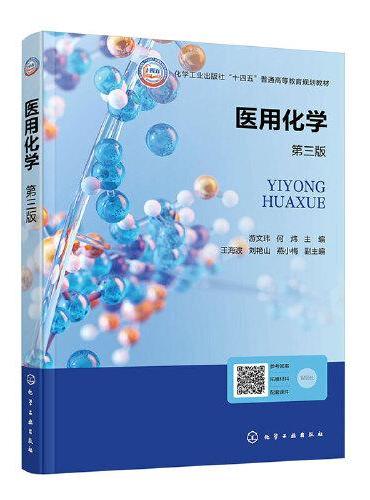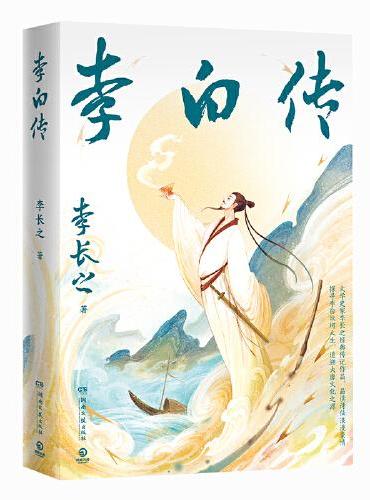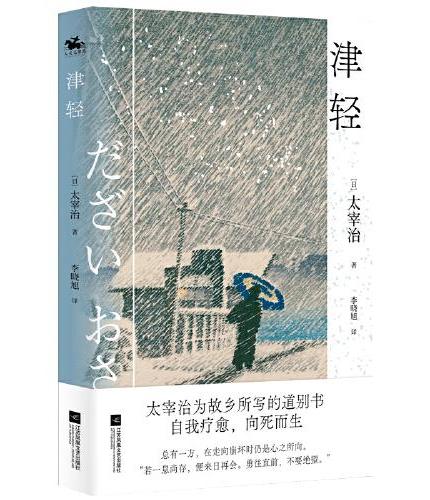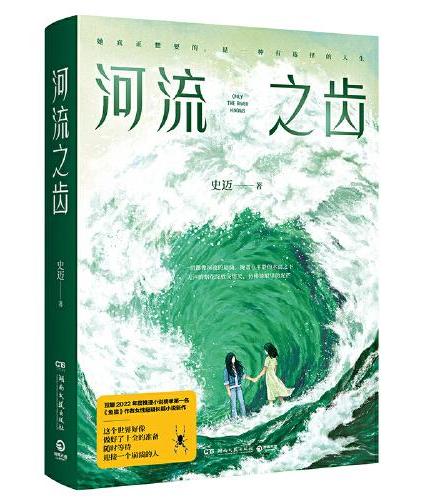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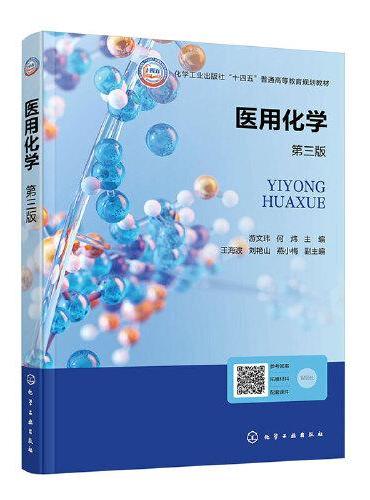
《
医用化学(第三版)
》
售價:HK$
57.3

《
别怕,试一试
》
售價:HK$
67.9

《
人才基因(凝聚30年人才培育经验与智慧)
》
售價:HK$
103.4

《
深度学习详解
》
售價:HK$
114.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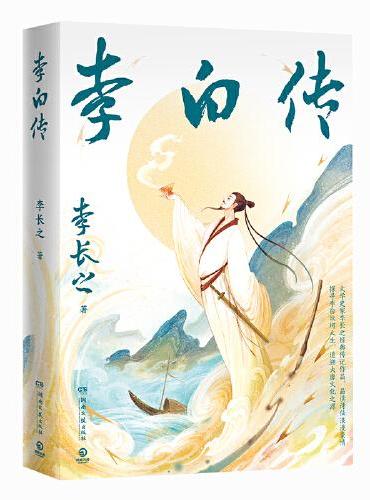
《
李白传(20世纪文史学家李长之经典传记)
》
售價:HK$
4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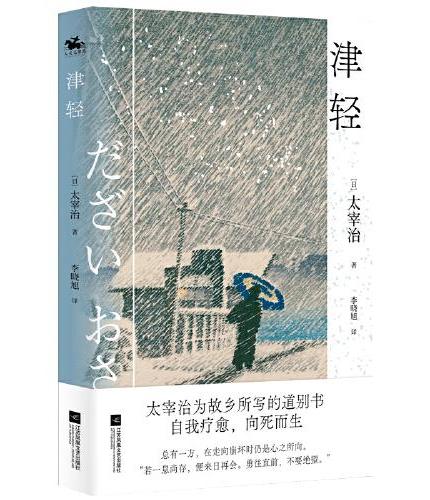
《
津轻:日本无赖派文学代表太宰治自传性随笔集
》
售價:HK$
6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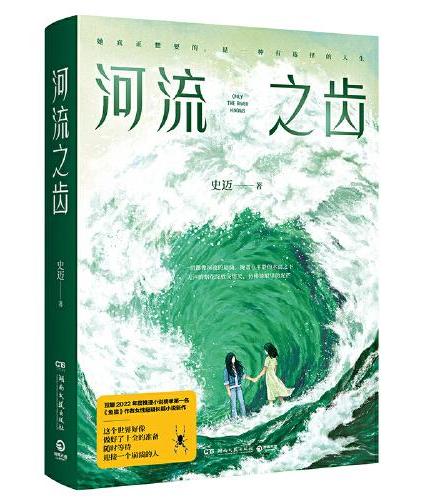
《
河流之齿
》
售價:HK$
59.8

《
新经济史革命:计量学派与新制度学派
》
售價:HK$
89.7
|
| 編輯推薦: |
关于地域思想史的研究,力图打通常州今文学派产生的外部背景和内在思想脉络。
探讨思想由何而来,因何而变。
|
| 內容簡介: |
|
在儒学发展史上,常州今文经学是值得重视却又少有研究的一派。作者对常州今文学派产生、兴盛的“内在理路”和“外部环境”做了互动的分析,认为18世纪的今文运动深深植根于区域性的社会活动之中。这本书实际是在深入探讨“思想”从何而来,又因何而变。它是一部打通“思想史”与“社会史”的力作。
|
| 關於作者: |
|
艾尔曼,1946年出生,宾夕法尼亚大学博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专长研究中国思想文化史与日本文明史等。
|
| 目錄:
|
中国文化史的新方向:一些有待讨论的意见
——代中文版序 / 1
序论 / 1
章中华帝国晚期江南地区的学派与宗族制度 / 1
节学术流派 / 2
第二节宗族与学派 / 4
第三节中华帝国晚期的宗族 / 9
第四节宗族与国家 / 16
第二章常州庄、刘两族 / 28
节庄氏家族的出现 / 28
第二节庄氏家族的崛起 / 31
第三节庄氏家族与明清易代 / 34
第四节科举及第的世家 / 37
第五节庄、刘两族的亲属关系 / 41
第三章经世之学与常州今文学派 / 52
节唐顺之与常州经世之学 / 53
第二节庄起元与晚明庄氏遗产 / 59
第三节庄存与的经世学和举业建树 / 63
第四节学术官僚庄存与 / 68
第五节庄存与与和 / 74
第四章经学传统的重建 / 84
节常州汉学 / 84
第二节常州易学 / 90
第三节庄存与与汉学 / 95
第四节庄存与的易学 / 97
第五章庄存与与公羊学 / 104
节《春秋》的功用 / 105
第二节明清之际的《春秋》研究 / 111
第三节庄存与与《春秋》 / 121
第六章从庄述祖到宋翔凤 / 135
节庄述祖 / 135
第二节庄有可 / 140
第三节庄绶甲 / 143
第四节宋翔凤 / 146
第七章刘逢禄与今文经学 / 156
节刘逢禄的仕途经历 / 156
第二节刘逢禄与汉学 / 159
第三节刘逢禄与今文经学研究 / 161
第四节刘逢禄的《论语》学 / 170
第五节刘逢禄与《左传》 / 177
第六节刘逢禄论何休 / 181
第八章法家与今文经学 / 188
节律与礼 / 188
第二节律与《春秋》 / 190
第三节《春秋》与案例 / 191
第四节经学、法律和新儒家 / 194
第五节今文经学的现实对策 / 197
第九章政治、语言和今文遗产 / 202
节政治危机与乾嘉易代 / 203
第二节语言的政治 / 213
第三节经世之学、变革与东林遗风的复兴 / 219
第四节政治学的语言 / 224
结论 / 236
附表
一明代常州庄氏家族主要支系表 / 240
二明代庄氏家族第二房主要支系表 / 241
三明清之际庄氏家族第二房谱系表 / 242
四清代庄氏家族第二房主要支系表 / 243
五明代常州刘氏家族一房、二房主要支系表 / 243
六清代常州刘氏家族主要支系表 / 244
参考书目 / 246
|
| 內容試閱:
|
中国文化史的新方向:一些有待讨论的意见
——代中文版序
18世纪晚期,清朝的儒家学者章学诚宣称“《六经》皆史也”。从汉代到清朝的两千年来,这些儒家经典一直被奉为“圣经”,再加上《四书》,共同构成了儒家教育的基础。此外,科举考试也把对这套儒家典籍的精通作为担任官员的知识条件。不过,到了章学诚的时代,这些经典正在失去原有的支配性地位,其势虽缓却已无可挽回。相对地,历史研究的势力逐渐形成气候。章学诚的登高一呼,代表着中国学术界演变过程的一个重要转捩点。到了20世纪,史学与哲学已经无可逆转地取代了经书,成为现代中国学术的支配性框架。
如果章学诚活在200年后的今日,他或许会说:“廿五史皆文也。”在我看来,20世纪晚期的世界学术也正面临一个转折点,在宽广的意义上,这次转变对我们所了解的历史研究构成了严重威胁。当今有许多批评史学家的人,认为后现代文学批评乃是未来的潮流。他们质疑历史的权威与真实性,例如他们会说“史学家和小说家无从分辨”,或者“事实是不可知的”,或者“小说家编造谎言以便陈述真实,史学家制造事实以便说谎”。换句话说,后现代主义者企图将史学化解为文学,正如同200年前章学诚将经典转化为史学一样。史学家辩称史学是以客观科学为根基的一门学科,跟小说家与作家所创造的小说和故事本质上不同。后现代的评论者则根本否认有所谓的客观的历史研究,反而将小说和史学一并归入人类主观创制的文学世界。
这类后现代主张无疑地过于夸张,但是史学家也不能因此不假思索地不理会这些批评。至少,史学家必须承认在历史写作里有非常类似小说的成分存在,当今全世界的初级和高等教育历史课本的“国史”里,弥漫的国族主义式的说法,即为一例。举一端而言,历史事件与人物的阐述,和“叙事风格”就十分相似,结果史学家的心态(例如中国的“褒贬”传统)和疑旨(problematique)很难跟小说家的“设局”和“角色刻画”的技巧有所区分。如果史学家连后现代对史学正中要害的批判都无法接受,那么独立于“国史”之外的历史学的未来发展不免遭受伤害,当代的史学研究难免走上一条漫无方向的政治道路,就像两个世纪以前的经学一样。此外,或许是理所当然,文字就不免成为支配性但多元的人类表达形式。
在某些政治条件下,诸如台湾到20世纪80年代止对言论自由的压制,史学家从事研究工作时必须屈从他们所处的政治环境。在这种环境里,他们不能自由取用图书馆与研究机构里具争议性的一手材料,学术界对有关1911年民国革命以来的中国现代史里的任何敏感题材,也多所顾忌。例如在20世纪60、70年代,台湾几乎没有学者敢冒险进入禁忌的领域研究民国史。那些胆敢抗议的人,也都付出了职业上的沉重代价。因此,面临这种历史写作上的明显限制,许多有才华的20世纪作者都转向文学,以之作为抒发感受的工具。在台湾,1947年以来的“台湾史的事实”,直到近都潜藏在台湾文学而非学院期刊或学术著作里。相同地,大陆作家是在小说和故事里,而非在官方的历史叙事里,成功地呈现了20世纪60年代的“红卫兵恐怖”。有些积极进取的史学家,则设法从明清小说与短篇文学作品里挖掘文化讯息,他们已经发掘出丰富的“小说虚构”矿脉,呈现了传统中国医药、科举考试,以及宗教在民俗文化里扮演的日常文化角色,适足以补充在官方史籍、政府公报、家谱或国家档案里找到的说法。
那么史学家应该做什么?这当然没有简单的答案,对那些仍然活在严厉惩处异议的政权下的人而言,尤其是如此。但是限度,那些身处较自由的学术环境中的人,比如说今天台湾的史学家,应该为自己的学科提出一套辩解,既考虑到后现代的威胁,同时又得体地维护史学的任务,使它与文学的工作有别,但不与文学疏隔。否则,落伍的史学家会渐渐发现他们的学生投向文学,视之为解开历史事件“实情”的工具。仅仅替这种转变贴上“时尚”的标签并不足以成事,因为史学这个领域其实已经陷入自己的虚矫夸言里,却又无法在新环境里再造自身。儒家经学在20世纪的没落,应该会让我们警觉到当一个学门失去了生命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命运。
历史学家在今天所面对的抉择,格外丰富而且复杂。随着西方后现代时代的来临,我们的前辈所执守的旧方法论,日益显得不合时宜。但是许多困扰我们前辈的方法论问题,并没有因为史学界必须处理的当代世界有所变化而解决。曼海姆在他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Ideology and Utopia)里,曾经力陈社会学化约论的危险。虽然他务求将知识现象联接到它们在社会形构中的位置,曼海姆和他的追随者还是对社会的阶级分析过于执着。到后,对他们而言,意识形态 永远是占支配地位的社会阶级的掌中物。曼海姆的方法论过度决定(overdetermined)了思想的社会起源,却没有在社会形构中,替个人的自主性留下足够的空间。
同样,目的论(teleology)依旧是当代历史里,西方“现代主义”的主要遗产。不论是在观念史或是在社会经济史家所提出的典型“现代化叙事”(modernization narrative)里,两种史学家都以今度古,“现代”(the present)一变,度量的准绳也随之而变。在比较早的“现代”里,中国显然落后且弱于西方诸国时,儒家被揪出来为落后负责。如今中国的“现代”和它的“过去”大不相同了,儒家的形象也从待罪的被告转变为促进现代性的功臣。在很多方面,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现代”来衡量什么样的“过去”(the past);测度的过程端视一开始选择用什么样的“现代”量尺而定。
现代化本身并不是问题所在。太平天国平定之后,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正式展开,此后史学家在所有的层面上——从思想以迄经济——都必须将现代化过程纳为分析对象。可是,一旦对中国历史上国家与社会构造里尚不见现代化的时代运用现代化模型所提供的概念架构,问题就产生了。换言之,将适用于分析1860年以后中国历史现象的框架,用在更早的时期,乃是一种年代错置。后,我们会以目的论式的论证收场,将历史现象化约为它们从来不是的东西——迈向现代化过程的“步骤”或“障碍”。这种依据“现代化”的量尺,对中国的过去所做的“正面”或“负面”解读,曾经是近好几个世代史学家的研究典范。这种过度强调“现代”(所谓的“现代性”)是“过去”准绳的偏颇之论,其中所包含的反历史偏见,已经被后现代论者成功地揭发了。现代化依然是近代中国史的重要探究对象,但是它已经不再是评价前现代中国的整体框架了。
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洲结构主义一直势力鼎盛,特别是在法国;其中重要的遗产,或许正是功能论。在当今的西方文化史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知识考古学”和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再生产”两种取向,被广泛用来描述与分析精英在社会与政治生活里,维持其对财富、权力和声望的支配时所运用的文化霸权形式。福柯的论点是现代欧洲的国家及其精英的“霸权”,为了将人民控制与圈制在新崛起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经济之下,组构了监狱和医院。布尔迪厄的“再生产”模型,则明确取代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以“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lty)作为评估一个社会的社会动态的主要标准的做法。涂尔干(Durkheim)对于教育在社会固有的“分工之再生产”里的角色,曾经进行先驱性的分析;布尔迪厄则更进一步,赋予关于政治和社会支配之文化形式的研究新的生命,在上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这些课题原本是以经济决定论来分析的。
然而,当代历史社会学里新功能论分析的振兴,给史学家带来了许多问题。对于文化现象做功能论的描述,就像先前结构主义的经验一样,不能妥当地处理作用者(agent)的意向和这些意向付诸实践后所产生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后果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福柯看来,对于欧洲史上监狱和医院改革在制度方面的结果,所有牵涉在改革过程中的作用者都有责任,即使他们的个人意向跟历史后果千差万别。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追随福柯,认为西方所有研究亚洲的学者,从马可?波罗(Marco Polo)到费正清(John Fairbank),都必须对正当化了的19—20世纪帝国主义在亚洲行径的“东方论”(Orientalism)的产生负责。但是那些学者的真正意图,对功能方面的后果却毫无意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