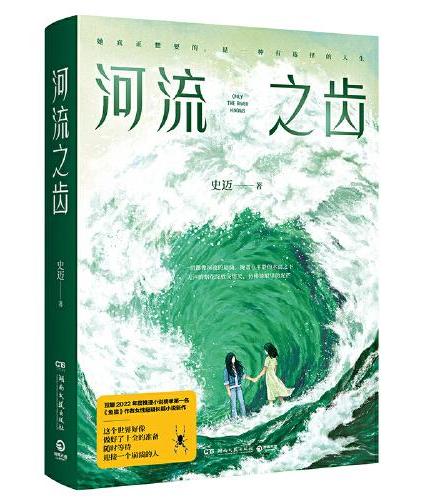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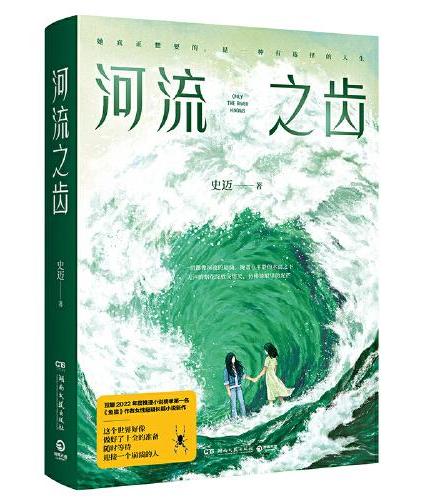
《
河流之齿
》
售價:HK$
59.8

《
新经济史革命:计量学派与新制度学派
》
售價:HK$
89.7

《
盗墓笔记之秦岭神树4
》
售價:HK$
57.3

《
战胜人格障碍
》
售價:HK$
66.7

《
逃不开的科技创新战争
》
售價:HK$
103.3

《
漫画三国一百年
》
售價:HK$
55.2

《
希腊文明3000年(古希腊的科学精神,成就了现代科学之源)
》
售價:HK$
82.8

《
粤行丛录(岭南史料笔记丛刊)
》
售價:HK$
80.2
|
| 編輯推薦: |
假如你有幸在巴黎度过青年时代,那么,在此后的生涯中,无论走到哪里,巴黎都会在你心中。因为,巴黎是一个流动的圣节。
——海明威
在任何一个时代,历史学领域的杰作都是少之又少的。泽尔丁的《法兰西浪漫史》就属于这类杰作。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堪称学术研究的里程碑。
——《时代周刊》
这本书读起来像本小说……一幅幅光彩夺目的画像, 一个个新颖独特的洞见,和一系列令人着迷又让人紧张的分析。 ……一个新的法兰西形象呼之欲出。
——《快报》杂志
|
| 內容簡介: |
本书刻画了1848—1945年法国社会色彩斑斓的风貌。作者对法国风云激荡时期不同阶层人物的野心与情感的细腻描述既令人惊奇,又引人深思。
尽管时空相隔,我们在今天阅读它依然会有丰盛的收获。除了展现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段重要历史,它还会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掩卷之时检视我们心底隐藏的卑微与梦想出人头地的雄心壮志,也让我们思考除了维持家庭生活的和谐表象,我们需要给出什么样的真正意义上的欣赏、爱和感激。
|
| 關於作者: |
[英]西奥多·泽尔丁(Theodore Zeldin)
英国人,牛津大学教授,历史类图书重大奖项“沃尔夫奖”获得者。
对法国近现代史素有研究,也许是因为旁观者清,泽尔丁对法国社会也有着精辟独到的见解。他不仅是个出色的学者,也是个很有才情的作家。凭借观察入微的写作本领和细致诙谐的笔触,他收获了“当代巴尔扎克”的美誉。
|
| 目錄:
|
第一章 装腔作势的资产阶级 003
第二章 医生 015
第三章 公证人 035
第四章 富人 045
第五章 实业家 055
第六章 银行家 069
第七章 普通人的野心 079
第八章 公务员 103
第九章 农民 121
第十章 工人 183
第十一章 婚姻与道德 263
第十二章 儿童 289
第十三章 女性 315
注释 335
|
| 內容試閱:
|
《法兰西浪漫史》可以用欣赏系列小说的方式来进行阅读,这种系列小说的每一部都从不同的角度讲述了一个家庭或者社区的故事。本系列中的每一章、每一卷都可以独立阅读,它们各自都有出人意料的内容,因为我的本意是展示一个和人们想象中不同的法国;它们各自都有英雄与反英雄的人物群体,因为我认为法国不是由一个人、一个阶级或一套既定的规则主宰的。然而,从总体来看,书中描绘法国的诸多不同侧面的目的是让读者重新不带偏见地审视法国,审视这个国家的人与众不同的习性嗜好、装腔作势的特有姿态,以及该国所经历的种种苦痛。作为一个国家,法国的这些特质经常触怒它的邻国,即使它已经赢得了它们的钦佩,甚至是喜爱之情。
这部历史著作与小说的相似之处不止于此,因为我试图将历史学家的关注点与小说作家的关注点结合起来。历史学家通常主要关注公众生活、争论性话题和社会运动,所以就把私生活和个人情感的领域留给了小说作家。因为我认为人类的行为是混乱和模糊的,没办法只把它简单呈现为对荣耀、正义和自由的追求,而且我认为根本不可能对人类的动机做出任何证明,所以我所写的不是一个由因果关系串联的、一般性的国家故事。相反,我从独立的个体出发,试图展现该个体所受到的来自内外的种种压力。我把他的压力、困扰归纳为六个方面:野心、爱、冲突、骄傲、品位和焦虑。
本书讨论的是前两个问题。对野心的研究—对希望与嫉妒,欲望与挫折,傲慢、贪婪与模仿的研究—使得我们把被认为是社会诸多弊病的罪魁祸首的阶级斗争置于显微镜之下。我关注的是人们对自己的感觉,而不是想当然地认为他们的行为主要由个人经济状况决定。我研究了金钱、安全、名誉、权力、幸福、娱乐各自的致命吸引力,它们将一个国家隐秘地划分为不同的阶层。我试图深入了解人们在职业、人生方向、对成功的理解及如何取得成功这些方面所做的不同选择的意义,我还试图展现法国人是如何从竞争中遭受折磨并受到鼓舞的,他们也因为疯狂而犯了许多错误。
爱是另一种我们需要研究的导致变化的革命力量。人们通常认为成年男性的活动会决定历史的进程,而关于这一群体如何应对女性和儿童的挑战,历史上却鲜有记载。男人并不完全是通过家庭来统治社会的,因为家庭生活是基本规范这一理论只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正如我即将展示的那样。在男性统治的世界中,女性在某些方面确实处于严重劣势,但女性也有自己的世界,她们拥有一种不同的权力。同样,儿童也发展出了他们特有的对家庭和学校的抵抗形式。我们研究爱就是为了展现:法律法规是多么无力;任何叛逆即使是悄无声息地秘密进行的,也可以结出硕果;外表的尊重和体面是如何掩盖内里的紧张和混乱的。
我在这本书中使用的写作方法是在法国人周围竖起许多面镜子,以便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审视他们;这一系列的其他几卷书则将这些主题延伸到了他们的个性深处。为了让读者适应我提供的千变万化的视野,他们必须愿意暂时忘却他们的历史知识,就像他们在看印象派或立体派的画作时必须忘却对传统画作的审美一样。我希望阅读这本书不仅能让读者改变他们对法国人和法国历史的态度,更重要的是,能让他们重新发现自我。
引
言
一项民意调查显示,法国人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其实,所有国家的人—正如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同样的民意调查所显示的那样—都认为自己很聪明,但法国的确是最看重智力的国家,因为富有智慧是法国人最欣赏的优点。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研究法国人尊崇智力的形象,评估智力、理性及思想在法国人生活中的地位,解释法国的知识分子为何会受到如此高的推崇,并探讨这种现象产生的结果。我希望这会有助于阐明这一时期的法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我认为,知识分子在法国历史中扮演的角色需要受到格外关注,并作为研究的基础,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穿越令人困扰的、漫长的、充满冲突的法国历史的迷雾。因为知识分子不仅在这些历史冲突中起了主导作用,还对这些冲突进行了阐释说明和分类归纳,从而影响了后人对历史上这些冲突的看法。是知识分子制定了他们声称对国家造成了分裂的重要议题,也是他们定义了那些关乎成败的原则。他们的观点成为公认的真理,以至于这些观点会主导事件的形成,因为新出现的争议正好在他们定义好的范畴之内。他们赋予了历史学家一个理论框架,让后者可以很方便地把过去的事件记录下来,但这个框架并不一定是唯一可以被使用的框架。我们需要更仔细地研究框架发生变化的原因,而且无论如何都要给其他观点留出空间。
对法国近代史的阐释通常有两种方式。传统的方式是把它表现为革命和反革命之间展开斗争的画卷。从这一方式来看,法国在政治、宗教和意识形态上都处于根本的分裂状态,社会动荡、暴力丛生和无休止的论战是其表现形式。另一种阐释历史的方式是把这些斗争看作社会分裂的表面现象,其目的是揭露虽然民主取得了胜利,但权力却集中在资产阶级内部,甚至只集中在资产阶级的一小部分人手中,集中在几百个家庭中的事实。资产阶级的胜利被认为是革命的成果,而随后的历史是资产阶级巩固其地位和人民群众试图推翻其统治的历史。这两种解释历史的方式都强调了把法国人分为不同阶层的因素。第一种解释研究的是原理—这个国家产生的不同政治理念对解释发生的事件至关重要。第二种解释揭示的是,经济特权的不平等及其社会弊端展现了革命的不完全性,并表明从革命原则到革命实践道阻且长。我们诚然可以以当事人的口吻描述发生的历史,但党派和个人偏见是否扭曲了他们的观点,他们的党派内部是否如领导人声称的那样存在不同政见,那些改革者在咒骂过去时是否也在某些方面墨守成规,社会阶层之间的敌意是否真的像某些时候表现的那样绝对,这些问题都值得一问。法国人的共同信仰、态度和价值观往往跨越意识形态和阶级,难以被翔实描述,因为在政治纷争的混乱中,这些很少被提及。但如果要正确地看待这些分歧,评估其局限和重要性,则需要考虑这些未被明言的假设。我们不仅要知道法国人为了什么而争吵,而且要知道争吵在他们的生活中处于何等地位,这对我们的理解是很有帮助的。家庭就是一个无可争议的社会组织的例子,是某些典型的具有法国特色的行为的根本来源。与此同时,紧张的家庭关系可能会像政治分歧一样造成分裂。这是一个几乎无人涉足过的主题,也是亟待产生新见解的领域。我本人在这方面的贡献只是试探性的和探索性的,对法国社会的固有特征做进一步研究似乎还有更大的空间,这类研究对改善法国历史研究的不均衡状态很有意义,因为一直以来都是社会事件、变革、发展、各种运动和风潮等更受人关注。1
我并不是说我要去定义法国人永恒不变的灵魂、思想或性格,但这是很多人都热衷于谈论的事情,我也会试图探讨他们为什么相信这样一种永恒的存在。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值得研究,然而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摆脱民族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仍然在不知不觉中主导着许多著作:我们不应该仅仅因为法国大革命的宣称,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法国在1848—1945年这一时期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法国历史往往是从统治者的视角出发,围绕着其对自身权力的关注来被讲述的。事实上,这一时期的法国社会由许多生活形态各异的群体组成。我试图描述其中一些问题、野心、争斗和挫折,它们构成了这本书的重要部分。
确实有一种强大的社会运动试图掌控和统一不同阶层,这就产生了斗争,而这场斗争在很多方面都比广为人知的关于君主制和共和制的争论更为彻底。众所周知,中央集权在革命中幸存了下来,但对它的抵制也幸存了下来,这种抵制远比人们意识到的更为强烈。这场斗争不仅是政治上的斗争,而且是智力的、文化的和社会的斗争。要想了解一个国家,人们不仅需要研究这个国家的事件,还要研究与这个国家相关的神话的传播及民众对国家的态度的变化。神话的创造者—知识分子—和政治家一样值得特别关注。
如今的作者习惯在一本历史书的开头先为其不足之处道歉。这不是谦虚,也不仅仅是约定俗成的惯例:历史写作者常常处于艰难的、不确定的状态。在过去,历史在人文科学中有很高的地位。当时的革命青年也常常满腔热情地去听历史讲座—这些讲座有时是民族运动的里程碑。历史学习曾经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后来却不再如此。尽管仍然有人致力于将历史培养成“通识教育”学科,但历史学科紧跟哲学脚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智力练习,甚至只是一种娱乐消遣—当其通俗易懂、可读性强时。社会科学承担了历史学科提供广泛概括和普遍解释的任务。总的来说,历史学家不再声称他们可以传授四海皆准的伟大真理,也不宣称他们即将发现这些真理。即使是那些勇于研究新途径或挖掘新资源的活跃的小团体,也不再有如此奢望。
这种情形也许是历史研究不断野心勃勃地扩展其研究对象范围的必然结果,生活中没有哪一个方面是历史学者不想加以研究的。扩大历史研究范围的趋向并不新鲜:伏尔泰、麦考莱和米什莱反对把历史研究的重点都放在国王和议会上。但直到现在,这貌似仍然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改革运动,实现目标的艰难由此可见一斑。文献资源的不足阻碍学术前进的步伐,而新的研究兴趣点又把研究的视野拉得更远。人类丰富多彩的活动很难被压缩在一卷书中,也没有人能够独立理解其全部内容。一个写通史的人几乎不可能奢望他的作品能实现自己的初心。
现在的历史学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矛盾的是,人们反而更难全面了解过去了。现在有待阅读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如果要写一部1848—1945年的法国通史,就需要熟悉那些年出版的书。我估计大约有100万本这种类型的书(平均每年会出现约1万本新书)。如果一个人每天读一本书,那么10年下来,他只能读完
3 650本,而且读的不过是随机抽取的样本。当然期刊和报纸也少不了,1865年至少有2 000种,1938年有近8 000种,20世纪50年代有15 000种。还有些手稿材料,这些材料散布于国家的、省级的、教会的、商业的和私人的档案馆中,尽管备受时间摧残,其体积仍然庞大。除了这个时代的产物,我们还需要阅读现代历史学家所写的关于这一时期的著作。法国历史年鉴列出了9 246本/篇仅在1970年这一年出版/发表的书和文章。1969年的统计显示,1789年以来,法国的大学共有1 380篇关于历史研究的博士论文,其中有640篇是关于法国的,更不用说数量比这多得多的硕士论文,抑或是其他国家的大学正在进行的有关法国历史的研究了。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其学术产出正呈现惊人的增长态势。1945年之后的20年里,美国的大学授予的历史博士学位数量增加了四倍。然而,没有一位历史学家可以仅局限于阅读同时代或本国的书籍,他们也不能忽视同根系的其他学科—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文学等—的研究及这些研究的参考书目。如果这些参考书是用不同语言写成的,那阅读的任务就更让人望而生畏了。所以,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觉得自己已经足够胜任撰写一部通史的工作。2
现在的研究正在以一种日益深入的方式进行,但研究的范围越来越窄。这种专业化在历史学科的不同分支之间已经造成了沟通上的障碍。例如,经济史和历史人口学中的新兴科研方法在某些方面用的是数学的知识,这就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训练方式。这种详细的研究和这些新兴的方法往往可以带来非常有原创力的结果,但问题是把这种研究结果有效传播出去非常困难。更糟的是,历史研究不是循序渐进地直线进行的,而且它的目标不明确,它不像医学研究那样可以把治疗某种特定的疾病作为明确的目标。每一代人的研究兴趣点都会转移,宏伟的研究计划也会慢慢搁浅。历史学科中的新发现、新成果被收入教科书的速度很慢,而且通常都会被人想方设法归于传统框架之中,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旧有知识体系。对个人而言,要在一段广阔复杂的历史中获得独立的视角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尽管很多旧有的历史观点已经被专家证明是错误的,但它们仍然顽强地存在着。
以上即是历史学家们,包括我,在书前写致歉词的部分原因。但在我看来,这些困难还有它们的另一面。如今的历史研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充满活力、更具独创性和技巧性。面对大量新材料,我们需要的不是一蹶不振的绝望心态,而是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这种新方法显然不同于过去历史学家期待把所有可能用到的书都搬到自己图书馆的时期所用的方法。阿克顿勋爵在谈到法国大革命时说道:“几年后,一切秘密都会变得众所周知。”他错了。现在看来,历史是一门永远不会发掘全部真相的学科。我们把历史建设成一门科学的尝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我们最好可以取其精华,而不必让19世纪的理想成为我们的桎梏。不管怎样,自然科学家已经放弃了19世纪的理想中所包含的关于方法论的幻想。历史可以继续向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学习,但自称是当前最流行的某个学科分支并不会提高其威望。
历史学科有自己的吸引力和优点,它可以把不利情形变为有利条件。在一个专业化程度日益提高的时代,历史仍然是最自由的学科,尽管其学科内部存在一些困难。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它能研究的内容;它不产生最终的答案,但它允许学生自己探索;它给学生提供最充分的空间,以使每个人都能以自己的方式去探寻真相。阿克顿勋爵主编的《剑桥近代史》的撰稿者曾被要求确保读者不知晓他们分别撰写了哪些内容,这在当时是可以接受的,因为那时人们认为真相在等待人们去发现和总结,而如今已经不同了。历史学家承认,不管他们多么谨慎,他们对事实的选择和使用都会受到他们自己个性的影响。他们从历史中所看到的,必然会部分地受他们独特的眼光、他们所受的教育和教养以及他们个人的兴趣和偏见影响。除了某些数字统计,很少会出现两个人在同一段历史中所看、所得、所感完全相同的情况。历史是一门要求人们在欣赏人物和事件时充分利用自己的个性、想象力和同情心的学科,压抑自己个性的、麻木的研究者是无法完成历史研究的任务的。历史专业能力很容易就能获得,但历史学家需要从更广泛的人生经验和更广博的人类品质中受益,他们很难像有些科学家那样在20多岁时就达到事业巅峰。历史学家的目标之一就是尽可能扩大他们与世界的接触面,无论这种接触是以多么间接的方式进行的。
历史研究是一种个人经验,其中的主观因素非常值得重视,尤其是在其他许多学科研究变得越来越技术性的时候。承认历史学家是戴着有色眼镜看待问题的—他们对事件原因的很多主观性阐释只是因为这种阐释对他们自己来说是连贯而真实的—并不是在承认错误,而是表明每位历史学家都可以在作品中表达自我。当然,历史学家对细节的掌控越小心翼翼,他们就越有可能令人信服。但是,因为历史学家使用文学体裁作为他们的媒介,他们不仅有机会证明某个观点,还有机会唤起一个时代的氛围—用当代人还未曾看到的意义和特征来重建一个时代。所有的年轻人都急于与时俱进,急于相信某种历史流派—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或统计学的—才是正确的。跟他们不同,我相信历史研究所采用的丰富多变的研究方法才是该学科真正的力量源泉,也会是让其发扬光大的真正原因。
但我不认为历史只是为了给人提供乐趣或为了满足古文物爱好者的好奇心而被设计出来的,它不仅仅是艺术或八卦消息。它也不是一种奢侈品,而是每一代人对自己的时代不断进行的重新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于什么值得保留、什么需要舍弃这一持续论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看来,与当今大众关注的热点脱节,并不是“学术性”历史写作的必要前提。相反,我认为历史学家可以更清晰地思考当下社会的理想、习惯和制度,因为在这些理想、习惯和制度中,总是藏着历史的影子。
因此,我没有按时间顺序来撰写历史—有几部按此框架写作的著作在这方面做得已经相当好了。我的方法是分析性的,也就是说,我会试着理顺法国社会不同的构成元素和不同的生活方面,并对它们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独立的研究。我希望历史学家对法国所做的传统性概括会因为我的这种撰写方式变得生动起来,从而才有可能使人们看到这些概括是如何被创造的,是由谁创造的,其含义是什么,以及概括中隐藏了什么。我的重点是去理解法国人的价值观、野心与抱负、人际关系及影响他们思维模式的因素,这种特殊的阐述方法意味着我会遗漏很多方面,但我对我的书从不以全面自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