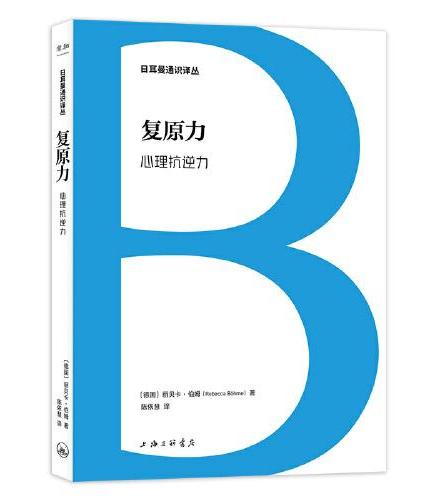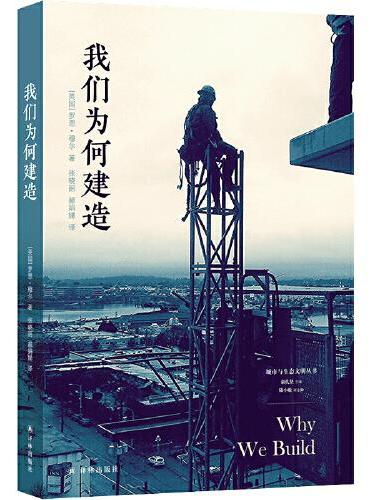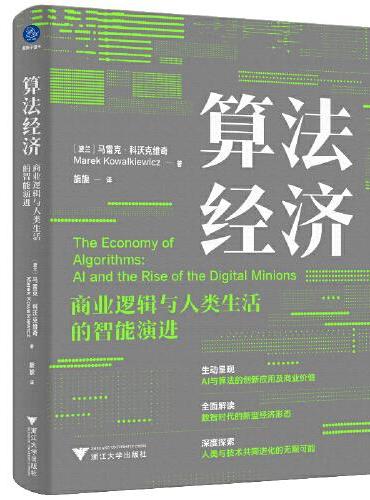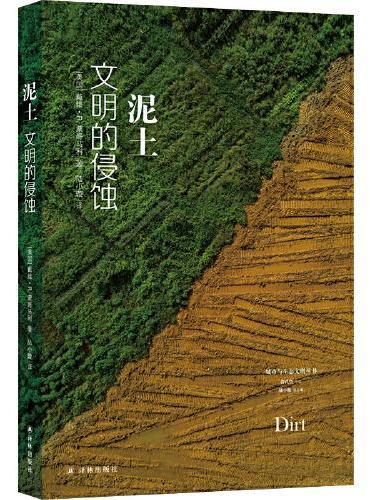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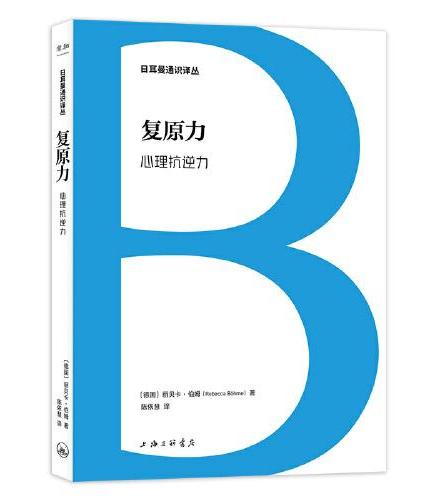
《
日耳曼通识译丛:复原力:心理抗逆力
》
售價:HK$
34.3

《
海外中国研究·未竟之业:近代中国的言行表率
》
售價:HK$
13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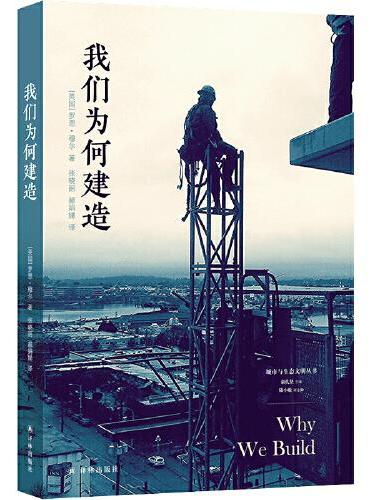
《
我们为何建造(城市与生态文明丛书)
》
售價:HK$
8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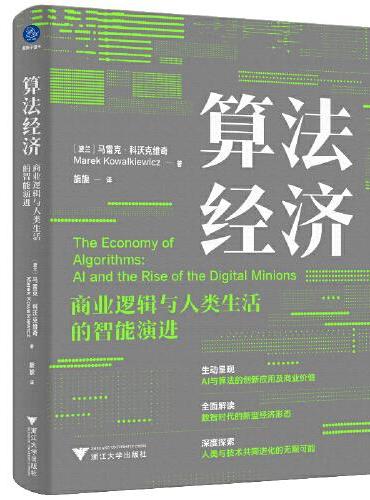
《
算法经济 : 商业逻辑与人类生活的智能演进(生动呈现AI与算法的创新应用与商业价值)
》
售價:HK$
79.4

《
家书中的百年史
》
售價:HK$
79.4

《
偏爱月亮
》
售價:HK$
45.8

《
生物安全与环境
》
售價:HK$
5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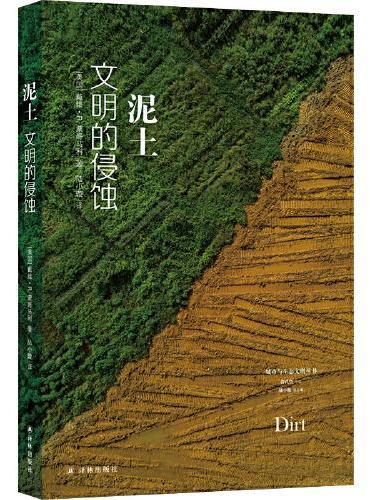
《
泥土:文明的侵蚀(城市与生态文明丛书)
》
售價:HK$
84.0
|
| 編輯推薦: |
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
穆时英,《上海的狐步舞》(1934)
我们确实都是恶魔手中的牵线木偶。
夏尔波德莱尔
毒品、堕落和风月场等主题总是很受欢迎法兰奇以充沛的精力和热情讲述了这一切。
加里克瑞斯特(Gary Krist),《纽约时报》
节奏快而情节奇除悬疑怪谈之外,作者还生动地描绘了日军占领前夕的上海对喜好*阴暗罪案故事的读者来说,这个没有英雄的卡萨布兰卡正合口味。
《科克斯书评》
叙事生动而又考据严谨,为读者展示了某个俗丽野蛮的国际化大都市最终泯灭于暴力的过程。
《金融时报》
它读起来更像是本冒险小说,而非经年累月的学术研究造就的详尽论文。你从一开始就会被它吊起胃口。老实说,我已不记得上次遇到如此引人入胜且读起来津津有味的非虚构作品是什么时候了。我一头扎到水下,读完半本书后才想起浮出来透口气。
罪案元素网站(Criminal Element)献给A.V.W
保罗法兰奇的《恶魔之城》仿佛一部黑色犯罪电影,将怀旧之情发挥得淋漓尽致,讲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关于上海的流亡者和罪犯的那段既光鲜又肮脏的历史。
《纽约杂志》
本书对东方巴黎的腐化、美丽和疯狂的捕捉
|
| 內容簡介: |
日本侵华时期的上海,罪恶深渊中的两个男人在围城之中,演绎了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
在耽于享乐的上海,维也纳人乔法伦得以积累资本并逐渐获得赫赫声名。他是歌舞表演之王,他的名字在臭名昭著的歹土夜总会法伦之家的霓虹灯招牌上不断闪耀。美国逃犯杰克拉莱带着被酸液腐蚀的指尖,以老虎机之王的身份,在上海闯出一片天。衣冠楚楚的乔与幸运的杰克犹如两颗殒石在空中轰然相撞,随后又在狂乱的挣扎中携手合作,抱团熬过这座城市彻底沦陷前的*后一段日子。
保罗法兰奇还原了旧日上海歹土外侨的生活,还原了那里的种种罪恶,生动再现了这座城市长期以来被人忽视的一段历史。
|
| 關於作者: |
保罗法兰奇(Paul French),哈生于伦敦,求学于伦敦和格拉斯哥,曾在上海工作、生活多年,出版过多部传播甚广的分析、评论中国的专著。其代表作《午夜北平》是爱伦坡奖最佳罪案实录奖项(Edgar Awardfor Best Fact Crime)和英国犯罪小说作家协会的非虚构类金匕首奖CWA Gold Dagger for Non-Fiction 得主。
译者简介
兰莹,先后就读于外交学院英语系、中国人民大学美术学院。现为公务员,从事对外文化艺术交流工作。业余从事文学、历史、美术领域的翻译,译有《午夜北平》等四本书。
|
| 目錄:
|
前言引言
序幕 恶魔的最后一舞
第一部分 崛起之路
第二部分 乱世之王
第三部分 身份成谜
尾声 陷落的城市
后记
上海新旧地名对照表致谢
免费在线读序幕 恶魔的最后一舞(节选)
1941年2月15日
上海歹土,大西路,法伦夜总会
上海已经今非昔比了她一再听到别人如是说。这句话如此频繁地出现,已成为公认的观点。人们在外滩附近举办的依然浮华的鸡尾酒会上这样说,在法租界优雅依旧的公寓和别墅里的宴会中也这样说自1937年8月那个血色星期六以来,上海就不再是曾经的上海了。
她对这种看法并不赞成。这并不是说战争、轰炸和日本人没有改变上海,而是说这种改变并非全都是负面的。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使人们对金子的需求迅速飙升,她的父亲,一位金条交易商因祸得福,现在赚到了比之前更多的钱。日本人将外国租界团团围住,确实造成了一定的不便:进出港的船舶减少,民航服务名存实亡。许多生活中的赏心乐事也消失了,生活在受保护的孤岛可能会有些无聊,但这些都可以克服。
爱丽丝戴西西蒙斯(Alice Daisy Simmons)刚满二十八岁。她出生于上海,未婚,是自称上海人的外侨之一,也是她父亲公司的合伙人。对她来说,孤岛上的生活激动人心。她的衣柜里塞满了定制礼服和西伯利亚皮草。从她位于法租界的顶层公寓看出去,这座城市入夜时灯火闪耀,好似一只珠宝盒。他们都知道战火几乎已烧遍中国内陆;战时陪都重庆在夜晚会遭到轰炸;没人敢于螳臂当车,拦住渴望征服全中国的日本军队的去路。但在这里,在上海的外国租界里,霓虹灯仍然在闪烁,计程车司机仍然你推我搡地揽客,夜总会一如既往地宾客盈门。
其他外侨女孩已经搭船离开上海,有的南下去了香港,有的远走至澳大利亚,但她留了下来。她的父亲对上海有信心,认为日本人会在此留一片特殊区域来为他们自己创造利润,因此他们不会来侵扰租界,而是会用栅栏把它围好,让上海继续做它一直在做的事:赚钱。她也相信这一点。
于是,她留在孤岛,随后发现在这处被围住的避难所里,仍有经济实力住在此地的那些人继续沉迷于享乐;而与此同时,这世界的其他地方已战火连天。这就是1941年的上海。她也是它的一部分。序幕 恶魔的最后一舞(节选)
1941年2月15日
上海歹土,大西路,法伦夜总会
上海已经今非昔比了她一再听到别人如是说。这句话如此频繁地出现,已成为公认的观点。人们在外滩附近举办的依然浮华的鸡尾酒会上这样说,在法租界优雅依旧的公寓和别墅里的宴会中也这样说自1937年8月那个血色星期六以来,上海就不再是曾经的上海了。
她对这种看法并不赞成。这并不是说战争、轰炸和日本人没有改变上海,而是说这种改变并非全都是负面的。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使人们对金子的需求迅速飙升,她的父亲,一位金条交易商因祸得福,现在赚到了比之前更多的钱。日本人将外国租界团团围住,确实造成了一定的不便:进出港的船舶减少,民航服务名存实亡。许多生活中的赏心乐事也消失了,生活在受保护的孤岛可能会有些无聊,但这些都可以克服。
爱丽丝戴西西蒙斯(Alice Daisy Simmons)刚满二十八岁。她出生于上海,未婚,是自称上海人的外侨之一,也是她父亲公司的合伙人。对她来说,孤岛上的生活激动人心。她的衣柜里塞满了定制礼服和西伯利亚皮草。从她位于法租界的顶层公寓看出去,这座城市入夜时灯火闪耀,好似一只珠宝盒。他们都知道战火几乎已烧遍中国内陆;战时陪都重庆在夜晚会遭到轰炸;没人敢于螳臂当车,拦住渴望征服全中国的日本军队的去路。但在这里,在上海的外国租界里,霓虹灯仍然在闪烁,计程车司机仍然你推我搡地揽客,夜总会一如既往地宾客盈门。
其他外侨女孩已经搭船离开上海,有的南下去了香港,有的远走至澳大利亚,但她留了下来。她的父亲对上海有信心,认为日本人会在此留一片特殊区域来为他们自己创造利润,因此他们不会来侵扰租界,而是会用栅栏把它围好,让上海继续做它一直在做的事:赚钱。她也相信这一点。
于是,她留在孤岛,随后发现在这处被围住的避难所里,仍有经济实力住在此地的那些人继续沉迷于享乐;而与此同时,这世界的其他地方已战火连天。这就是1941年的上海。她也是它的一部分。
在2月的某个寒天里,时近午夜,爱丽丝到达位于大西路的法伦夜总会。这是她最喜欢的夜总会,恐怕也是远东地区最大的夜总会。这地方迷住了她。日本人入侵沪西后,允许歹土的卡巴莱歌舞厅、赌场、毒窟和妓院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中迅速发展,它们拥挤地排列在街头巷尾和林荫大道上。于是,她开始找借口避开闷热会客室里的晚会、无聊的午餐间闲聊和法租界里的咖啡厅。她发现法伦夜总会就在霓虹灯下,就在所谓的上流社会之外。这座三层楼高的赌场里充斥着轮盘赌、十一点和铮琮作响的骰子。
在这里,人人都认识她、尊敬她。其他宾客和她同样兴奋。看门的那位年轻的奥地利流亡者让两扇大门在她面前敞开,夸张地鞠着躬,将她引进来,还厚着脸皮冲她挤眉弄眼。门口的安保负责人沃尔特伦塞(Walter Lunzer)是维也纳人,长得虎背熊腰,但很有魅力。他帮爱丽丝脱下皮草,一位衣帽间的女侍已经送上一只衣架。他打了个手势,示意爱丽丝往吧台走。法伦先生,这处俱乐部的金主,上海战时夜生活的首席导师,已经在那里了,他从立在角落的冰桶里拿出香槟,为她倒满一杯。这只冰桶永远是满的,以备衣冠楚楚的乔向他最喜爱的老主顾敬酒。乔吻了她的双颊,举起手中的香槟杯。他们碰杯。他在她耳畔悄声低语,与此同时乐队正在舞池搅起暴风疾雨。她没太听清他的话,但她点头微笑。和绅士乔在一起时总是能听到恭维话。
爱丽丝穿过食客和跳舞的人群,不屑理睬他们的问候和邀舞。这些留在上海的家伙算是很幸运了他们还吃得起牛排,喝得起香槟。虽然这个群体的人数不断减少,但最擅长聚会和赌博的人都来了法伦夜总会。她拾级而上,去楼上的赌场,走向轮盘赌台。她的同道中人每夜都聚在那里。爱丽丝喜欢轮盘赌,这游戏的输赢纯靠机遇。只有那些相信高赔率,而且钱包鼓得足以支撑整晚赌博的人才会得到回报。令人惊讶的是,在上海这样一个没人敢打赌说自己能比别人活更久的城市,竟然会有这么多人对轮盘赌台顶礼膜拜。然而,赌桌边挤满了人,没有空凳子了,但她知道他们总是能给她找个位子的。
她通常在晚上来这儿,先跟赌场经理杰克拉莱,也就是绅士乔的搭档聊会儿天。乔是个温和的人,有着中欧人的高雅,而杰克这个率直的美国佬也自有其粗野的魅力。但今晚,她知道杰克不会在这里,她听说杰克和法院有点麻烦,正敛迹蛰伏。有些人认为他已经不告而别,其他人则说他正潜藏于虹口的小东京。如果警方(或者说上海仅存的执法机构)执意要把他投入监狱的话,他就不会再出现了。
她停下脚步,和几个朋友碰杯,祝大家今晚有好手气。这些人也爱在法伦夜总会的轮盘赌台边消磨夜晚。然后她向赌台走去,决定去看看今晚好运之神是否会护佑自己。杰克的副手、暂代赌场经理艾伯特罗森鲍姆(Albert Rosenbaum)看见了爱丽丝,向她眨眨眼。他拍了拍一位衣着华丽的华人的肩膀,在后者耳旁低语。那花花公子一直在下低注,赌的还是等额赔率,因此和庄家堪堪打平。他拒绝了荷官继续下注的提议,决定今晚到此为止。罗森鲍姆在此人面前放了几个筹码,作为让出位子的补偿,后者把那堆筹码装进了口袋。罗森鲍姆向爱丽丝打了个手势,请她坐到那个空位上,然后在她面前的桌子上放了一堆筹码。她见到罗森鲍姆在他的小本子上记下数额。一位好的赌场经理总是会保证口袋里有钱的常客面前随时都有筹码。
爱丽丝把最后一滴香槟酒饮尽,向乔点了点头。后者正走出酒吧,走上楼梯,要和罗森鲍姆一起去顶楼的私人办公室。
突然,她听到楼下传来枪声和尖叫声。她知道发生了什么。这里是歹土,绝望的持枪歹徒曾洗劫其他夜总会和赌场。她看到旁边台子上的赌徒手忙脚乱地钻到桌底。随后又传来更多尖叫、大喊和玻璃碎裂的声音。枪声再次响起,这次是在赌场所在的楼层。一盏灯被击成碎片;还有一枪打中了轮盘赌台对面的墙,打得木屑横飞。她听到从楼梯传来的沉重脚步声,于是转过身来。爱丽丝看到了手里拿着枪的杰克拉莱,十分惊讶。他的德国保镖施密特(Schmidt)挥舞着一支毛瑟枪。人群四散,想逃下楼梯。杰克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因为警察正在抓他,他是上海的头号通缉犯。他向她咧嘴微笑,露出断掉的牙齿。她曾经如此熟悉这个笑容。他看起来局促不安,随后转开视线。杰克和施密特把枪口指向天花板开了火。赌场员工伏身寻找掩体。杰克瞬间又把目光转向她。她觉得后背有强烈的烧灼感传来,然后倒在了地板上。
|
| 內容試閱:
|
序幕 恶魔的后一舞(节选)
1941年2月15日
上海“歹土”,大西路,法伦夜总会
“上海已经今非昔比了……”她一再听到别人如是说。这句话如此频繁地出现,已成为公认的观点。人们在外滩附近举办的依然浮华的鸡尾酒会上这样说,在法租界优雅依旧的公寓和别墅里的宴会中也这样说……自1937年8月那个“血色星期六”以来,上海就不再是曾经的上海了。
她对这种看法并不赞成。这并不是说战争、轰炸和日本人没有改变上海,而是说这种改变并非全都是负面的。通货膨胀和社会动荡使人们对金子的需求迅速飙升,她的父亲,一位金条交易商因祸得福,现在赚到了比之前更多的钱。日本人将外国租界团团围住,确实造成了一定的不便:进出港的船舶减少,民航服务名存实亡。许多生活中的赏心乐事也消失了,生活在受保护的“孤岛”可能会有些无聊,但这些都可以克服。
爱丽丝·戴西·西蒙斯(Alice Daisy Simmons)刚满二十八岁。她出生于上海,未婚,是自称上海人的外侨之一,也是她父亲公司的合伙人。对她来说,“孤岛”上的生活激动人心。她的衣柜里塞满了定制礼服和西伯利亚皮草。从她位于法租界的顶层公寓看出去,这座城市入夜时灯火闪耀,好似一只珠宝盒。他们都知道战火几乎已烧遍中国内陆;战时陪都重庆在夜晚会遭到轰炸;没人敢于螳臂当车,拦住渴望征服全中国的日本军队的去路。但在这里,在上海的外国租界里,霓虹灯仍然在闪烁,计程车司机仍然你推我搡地揽客,夜总会一如既往地宾客盈门。
其他外侨女孩已经搭船离开上海,有的南下去了香港,有的远走至澳大利亚,但她留了下来。她的父亲对上海有信心,认为日本人会在此留一片特殊区域来为他们自己创造利润,因此他们不会来侵扰租界,而是会用栅栏把它围好,让上海继续做它一直在做的事:赚钱。她也相信这一点。
于是,她留在“孤岛”,随后发现在这处被围住的避难所里,仍有经济实力住在此地的那些人继续沉迷于享乐;而与此同时,这世界的其他地方已战火连天。这就是1941年的上海。她也是它的一部分。
在2月的某个寒天里,时近午夜,爱丽丝到达位于大西路的法伦夜总会。这是她喜欢的夜总会,恐怕也是远东地区的夜总会。这地方迷住了她。日本人入侵沪西后,允许“歹土”的卡巴莱歌舞厅、赌场、毒窟和妓院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中迅速发展,它们拥挤地排列在街头巷尾和林荫大道上。于是,她开始找借口避开闷热会客室里的晚会、无聊的午餐间闲聊和法租界里的咖啡厅。她发现法伦夜总会就在霓虹灯下,就在所谓的“上流社会”之外。这座三层楼高的赌场里充斥着轮盘赌、十一点和铮琮作响的骰子。
在这里,人人都认识她、尊敬她。其他宾客和她同样兴奋。看门的那位年轻的奥地利流亡者让两扇大门在她面前敞开,夸张地鞠着躬,将她引进来,还厚着脸皮冲她挤眉弄眼。门口的安保负责人沃尔特·伦塞(Walter Lunzer)是维也纳人,长得虎背熊腰,但很有魅力。他帮爱丽丝脱下皮草,一位衣帽间的女侍已经送上一只衣架。他打了个手势,示意爱丽丝往吧台走。法伦先生,这处俱乐部的金主,上海战时夜生活的首席导师,已经在那里了,他从立在角落的冰桶里拿出香槟,为她倒满一杯。这只冰桶永远是满的,以备“衣冠楚楚的乔”向他喜爱的老主顾敬酒。乔吻了她的双颊,举起手中的香槟杯。他们碰杯。他在她耳畔悄声低语,与此同时乐队正在舞池搅起暴风疾雨。她没太听清他的话,但她点头微笑。和“绅士乔”在一起时总是能听到恭维话。
爱丽丝穿过食客和跳舞的人群,不屑理睬他们的问候和邀舞。这些留在上海的家伙算是很幸运了——他们还吃得起牛排,喝得起香槟。虽然这个群体的人数不断减少,但擅长聚会和赌博的人都来了法伦夜总会。她拾级而上,去楼上的赌场,走向轮盘赌台。她的“同道中人”每夜都聚在那里。爱丽丝喜欢轮盘赌,这游戏的输赢纯靠机遇。只有那些相信高赔率,而且钱包鼓得足以支撑整晚赌博的人才会得到回报。令人惊讶的是,在上海这样一个没人敢打赌说自己能比别人活更久的城市,竟然会有这么多人对轮盘赌台顶礼膜拜。然而,赌桌边挤满了人,没有空凳子了,但她知道他们总是能给她找个位子的。
她通常在晚上来这儿,先跟赌场经理杰克·拉莱,也就是“绅士乔”的搭档聊会儿天。乔是个温和的人,有着中欧人的高雅,而杰克这个率直的美国佬也自有其粗野的魅力。但今晚,她知道杰克不会在这里,她听说杰克和法院有点麻烦,正敛迹蛰伏。有些人认为他已经不告而别,其他人则说他正潜藏于虹口的“小东京”。如果警方(或者说上海仅存的执法机构)执意要把他投入监狱的话,他就不会再出现了。
她停下脚步,和几个朋友碰杯,祝大家今晚有好手气。这些人也爱在法伦夜总会的轮盘赌台边消磨夜晚。然后她向赌台走去,决定去看看今晚好运之神是否会护佑自己。杰克的副手、暂代赌场经理艾伯特·罗森鲍姆(Albert Rosenbaum)看见了爱丽丝,向她眨眨眼。他拍了拍一位衣着华丽的华人的肩膀,在后者耳旁低语。那花花公子一直在下低注,赌的还是等额赔率,因此和庄家堪堪打平。他拒绝了荷官继续下注的提议,决定今晚到此为止。罗森鲍姆在此人面前放了几个筹码,作为让出位子的补偿,后者把那堆筹码装进了口袋。罗森鲍姆向爱丽丝打了个手势,请她坐到那个空位上,然后在她面前的桌子上放了一堆筹码。她见到罗森鲍姆在他的小本子上记下数额。一位好的赌场经理总是会保证口袋里有钱的常客面前随时都有筹码。
爱丽丝把后一滴香槟酒饮尽,向乔点了点头。后者正走出酒吧,走上楼梯,要和罗森鲍姆一起去顶楼的私人办公室。
突然,她听到楼下传来枪声和尖叫声。她知道发生了什么。这里是“歹土”,绝望的持枪歹徒曾洗劫其他夜总会和赌场。她看到旁边台子上的赌徒手忙脚乱地钻到桌底。随后又传来更多尖叫、大喊和玻璃碎裂的声音。枪声再次响起,这次是在赌场所在的楼层。一盏灯被击成碎片;还有一枪打中了轮盘赌台对面的墙,打得木屑横飞。她听到从楼梯传来的沉重脚步声,于是转过身来。爱丽丝看到了手里拿着枪的杰克·拉莱,十分惊讶。他的德国保镖施密特(Schmidt)挥舞着一支毛瑟枪。人群四散,想逃下楼梯。杰克不应该出现在这里,因为警察正在抓他,他是上海的头号通缉犯。他向她咧嘴微笑,露出断掉的牙齿。她曾经如此熟悉这个笑容。他看起来局促不安,随后转开视线。杰克和施密特把枪口指向天花板开了火。赌场员工伏身寻找掩体。杰克瞬间又把目光转向她。她觉得后背有强烈的烧灼感传来,然后倒在了地板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