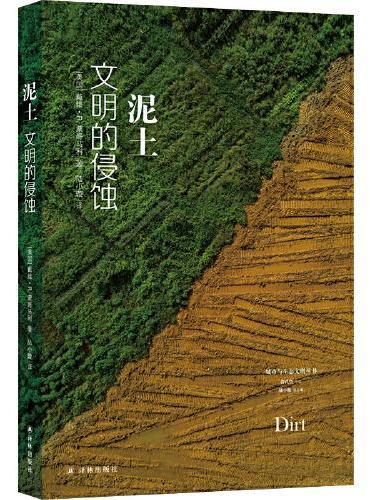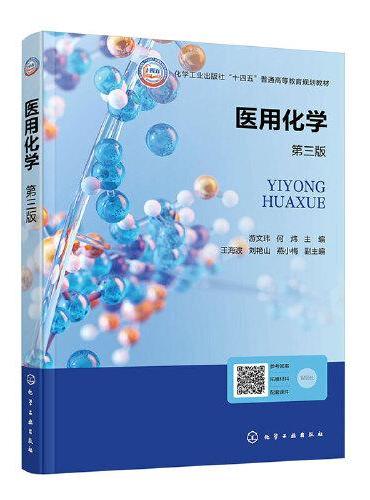|
他的头脑已成了传奇南方朔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九日, 上午十时, 当代最杰出作家之一的卡尔维诺, 因为脑溢血而逝世, 享年仅六十二岁。卡尔维诺的逝世, 使他成为近代文学的一则传奇。而他的传奇里最主要的乃是那些总是不断创造惊奇的脑细胞。将卡尔维诺的作品引进美国, 并与之成为挚友的美国作家维达尔Gore Vidal, 后来在追念文章里如此写道: 第一次脑内出血后, 曾进行了一次长达好几个小时的手术, 他从昏迷中醒来。……当时, 那位脑神经外科医师对他的病情十分乐观。他告诉新闻界, 从未看过一个人的脑内构造像卡尔维诺那么纤细复杂。……他说他也是卡尔维诺的读者, 还曾经为了他的书和子女们辩论。这一颗使他觉得扑朔迷离的头脑, 就为了它的稀罕, 他也必须让它继续活下来。卡尔维诺的头脑是近代文学最大的传奇, 这或许正是他的文学生涯仿佛高峰连绵, 永远看不见尽头的原因。他的文学风格很少在一个地方停驻, 每次都带给人们不可思议的惊喜。他的文学跨越了写实和奇幻的传统边界, 将小说拉高到了语言哲学、符号学和人类学的层次。而后期的《看不见的城市》, 以及他活着时所出版的最后一本独白小说《帕洛马尔》, 更将文学提到形而上学并驾齐驱的高度。卡尔维诺的不可思议, 乃是他几乎开创出直到如今的全部新叙述形式和话题。他的想象奔驰在大到宇宙生成, 小到波浪及砂粒的观察之间。他的《烟云》是文学探讨环境的最先驱作品; 他以文学探讨记忆、欲望和感觉, 也都是先河实验。当然更不能忘了他在诸如《如果冬夜, 一个旅人》, 以及短篇作品《基督山伯爵》等里对后设小说所作的开创了。卡尔维诺的脑细胞纤细复杂, 不可揣度。他是近代文学最大的研究发展部, 不断在为文学的知觉范围、文体的类型, 甚至语言文字本身, 进行着新边界的探索。而六十二岁即告逝世, 无疑是太早了一些, 如果他继续活着, 不知道他还会创造出多少的惊奇。但也正因他一直看着未来, 因而疏忽了过去, 当他猝逝, 后来的人遂看不到一本差堪安慰的传记。我们只能在他的作品里想象, 而不能借着传记和他接近。其实, 卡尔维诺并非全无传记, 多年以来, 我就始终将《帕洛马尔》视为他的心灵传记。这本独白式的小说里, 帕洛马尔是卡尔维诺自己。它叙述他观察事物的方法, 观察后的联想, 最后则将这两者连结并拉高到理念的层次。心灵的独白和自我诘问, 他留下了许多让人得以理解他的轨迹。但心灵传记终究还不是传记。然而, 这个缺憾却在卡尔维诺逝世之后逐渐补齐。他逝世之后, 他那位高雅多才、娇小、满头红发的妻子齐姬塔不断整理遗著, 不但将尚未集辑的残篇先后出版, 更将具有自传、传记、访谈性质的文章汇整。于是, 遂有了《圣乔凡尼之路》和《巴黎隐士》这两本具有传记性质的专书。前者是卡尔维诺的早年回忆, 而《巴黎隐士》则是他大半生的成长痕迹。尽管这些仍然不是自传或传记, 但它毕竟已填补了那一片空白。由他的作品, 以及这些有传记义涵的生命记录, 我们已经可以更加靠近卡尔维诺了。《巴黎隐士》由十九篇或长或短的文章辑成, 题材有日记、回忆短文、访谈、短评等。尽管体例不统一, 但毫无疑问的, 乃是其中都充斥着卡尔维诺生命历程的内容。由卡尔维诺的妻子所写的前言, 我们可以知道其中有十二篇早在卡尔维诺生前就已存放在自己列为“自传”的档案里。对于这些留存的资料, 他计划怎么处理, 我们并无法知悉。他可能根据这些重写一本自传, 也可能只是增补剪辑。但这样的工作在卡尔维诺逝世后已永不可能, 我们只好自己跳进这些生命痕迹的海洋里与他共泳, 并以他的作品来和这些资料参照, 重编出我们自己心目中的他的自传。《巴黎隐士》由三个主要阶段的文章组成。第一个阶段包括了他青少年时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下, 经过参与地下抗德, 加入意大利共产党, 以及后来退出共产党的记录与省思。第二阶段则是一九五九至一九六零年间他首次访问美国时所写的信札式日记。第三阶段则是后来他多次接受访问的记录。这三个阶段的记录对理解他的生平及文学都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他早年参与政治的那些经验和反省, 显示出他不受拘束以及非政治化的天性。他后来在《帕洛马尔》里有这样的一段话, 可以拿来参证: 在一个每个人都抢着发表意见和要做出判断的时代与国度, 帕洛马尔养成了一种习惯, 每逢想要提出什么主张时, 就先咬舌头三次。当他咬过舌头后仍觉得对自己的主张能够信服, 他才说出来。……能够提出正确的见解, 并不是什么特别了不起的事。就统计上的意义而言, 当各种疯狂、混乱和庸俗的观念袭上心来, 不可避免的也会伴随着某些精彩、甚至还是天才的想法。但他会有这种情形, 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在别人身上。一个对政治事务会有这种看法的人, 其实已是对政治最有洞识的人, 而有了洞识, 也就必然走到了政治的上方, 而不可能继续在政治中淌流荡漾。卡尔维诺的这种态度不但显示在作品和评论里, 也同样显示在许多次的访谈中。他是那种众生平等, 端视万事万物, 并能出入自得的人。也正因这样的廓然心境, 他遂能很细致的去观察和解读, 并赋予事物各种多角度的意义。他一九五九至六零年间第一次到美国, 行程上的所见所思, 尽管信手拈来, 但吉光片羽, 多见犀利的锋芒, 卡尔维诺的确是那么的不同, 所以始能不同的站在当代作家群里而那么的头角峥嵘。卡尔维诺的文学创作固然是一家之言, 但他的各种文论与评论也都斐然可观。他早年的《文学之用论文集》, 以及逝世后结集的《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都是例证。不过, 卡尔维诺是文学家, 一切的讨论最后终究要落实到他的作品和创作世界中。在《巴黎隐士》里, 他一九七八年接受意大利中生代杰出作家朱迪契的访问; 一九八五年接受意大利文论家玛丽亚?寇尔提的访问, 这两篇访谈录都是一流的问话, 一流的答复。尤其是他答复朱迪契的那篇最有文学上的参考价值。朱迪契Daniele Del Giudice今年五十岁, 他小了卡尔维诺整整两个世代, 已被认为是卡尔维诺的文学继承者, 因而他的访问最能掌握住卡尔维诺文学作品的核心。其中有一段答复很可以作为理解卡尔维诺的基本参考点: ……而追求和谐的欲望来自对内心挣扎的认知。不过偶然事件的和谐幻象是自欺欺人, 所以要到其他层面寻找。就这样我走向了宇宙。但这个宇宙是不存在的, 纵使就科学角度而言。那只是无关个人意识, 超越所有人类本位主义排他性, 期望达到非拟人观点的一个境域。在这升空过程中, 我既无惊惶失措的快感, 也未曾冥思。反倒兴起一股对宇宙万物的使命感。我们是以亚原子或前银河系为比例的星系中的一环: 我深信不移的是, 承先启后是我们行动和思想的责任。我希望由那些片段的组合, 亦即我的作品, 感受到的是这个。对于卡尔维诺的文学, 我曾对它的分期和时代背景等因素作过扼要的论列。对于这一部分, 在此不拟重复。不过, 所有的分期都是一种为了记忆的方便而作的权宜设计, 而在分期里, 真实的卡尔维诺仍是那一个不变的实体, 只是可能换上不同的衣服。也正因此, 尽管卡尔维诺的文学, 从他《通向蜘蛛巢的小路》里那个在蜘蛛洞口张望的小孤儿开始, 虽然历经寓言、法国新小说、博尔赫斯的魔幻隐喻, 一直到“后现代”与“后结构”, 它只有很少的时候有点玩兴过浓, 但绝大多数的时间里, 他那种表面轻盈的文学里, 所承载的其实是另外一种更大的重量。他后期的文学早已与渲染式的叙述诀别, 而成为一种文学低限主义表现形态下的自我诘问与辩难。那是一种“独我主义”Solipsism式的重新开始, 他要透过这样的质问, 借着否定和扬弃而寻找《帕洛马尔》里不断出现的那个“合一”The One。他从早期开始, 就有好多故事到最后都让主角去面对大海或草地。他们的背后是一片被解构掉的荒芜, 而前面则是未可知的憧憬。这是一种强烈的对比和矛盾, 而人在两者之间, 很有一种天地悠悠, 谓我何求的孤绝况味。卡尔维诺的文学有好多个不同层次的阅读, 它的叙述方法仿佛万花筒般的瑰丽。它观察事务或意义, 都会将它正读与反读并施, 解开它的归属位置, 而后重新放在一个与它相对立或相反的关系里, 让虚假因此而被抛出, 使意义从此而成为一种等待。卡尔维诺毕生的文学事业, 即是在于不断的抛出, 世界因而变得更加空旷, 但空旷的虚, 却又是好大的沉重。每当展读卡尔维诺的作品, 在尝尽它智巧、锋利、通达、豁然的况味后, 我最后总是会在恍惚的太息中掩卷, 油然而生古今混同的苍茫之感, 并觉得自己似乎也变成了那个静观万务的巴黎隐士卡尔维诺。卡尔维诺的著作里, 我最喜欢的是那本《帕洛马尔》, 一方面因为那是他的心灵独白与冥思, 也是他活着时所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在他赠书给至交时题曰: “这是我对自然的最后思考。”这本薄薄的小书, 封面是对比的两个人, 一个是伽利略, 另一人则是隔着屏风而沉睡或者在冥想的女士。封面的这种对比似乎很有暗指的意义, 科学家根据观察而测度世界, 而小说家则用想象来描述及捕捉真实。他把自己提到与伽利略等高的地位。而卡尔维诺也以他自己来证明了这种可能性。因此, 让我们来喜欢卡尔维诺! 前 言 此书中收录了卡尔维诺已经发表、散见各书的十二篇文章, 未发表的一篇《美国日记》, 还有一篇在意大利未发表过、瑞士卢卡诺区限量出版的《巴黎隐士》。一九八五年八月, 距出发去哈佛大学一个月, 卡尔维诺既累又烦。他本想在去美国前结束手边正在准备的六篇演讲稿, 但未能如愿。他也许会修改、调整、“剪贴”, 继而一切, 几乎一切如旧。他毫无进展。我当时想, 可能的解决办法是说服他转移注意力, 把精神集中到他众多计划中的一个。对我的问题: “你为什么不干脆丢开演讲去把《圣乔凡尼之路》写完呢?”他说: “因为那是我的传记, 而我的传记还没有……”话没说完。他是要说“还没结束”抑或想的是“那还不是我完整的自传”?多年后我偶然发现一个文件夹, 标题是“自传作品”, 包括他的弟子已做好初版说明的一系列文章。所以说, 是有另外一个, 与《圣乔凡尼之路》书中所勾勒的完全不同的自传计划。不能说不可能, 但很难猜出卡尔维诺想以什么方式呈现这些按时间先后排列的文章。毫无疑问谈的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 其意图是要阐明他在政治、文学、存在上的选择, 让大家知道这些选择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以及何时发生。何时格外重要: 在《青年政治家回忆录, 一九六零至一九六二年》的作者注中, 卡尔维诺写道: “关于我所表达的信念第二篇, 如同这本合集的任何一篇文章, 只是我对事物当时——仅止当时——看法的见证。”卡尔维诺为此书所准备的材料只到一九八零年十二月。按作者意愿, 十四篇文章中三篇以时间为序刊出两个版本。我加入了最后五篇, 因为那些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传作品, 也因为我觉得其余作品会因之更完备。将这些文章摆在一起,我发现其中几篇缺少那种自传作品应有的直接性。当然不纯是为了这个原因,我想到要把《美国日记一九五九至一九六零年》收进来,是因为那次旅行在他一生中的重要性, 卡尔维诺于不同场合都曾提到或写过。尽管如此, 他仍然决定不出版由这次旅行写就的《一个乐天派在美国》, 虽然当时已在二校。对此临阵反悔, 在他一九八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写给卢卡?巴拉内利Luca Baranelli的信中有所解释: “……我决定不出版该书, 因为校对时重看, 我觉得就文学作品而言太过小品, 就新闻报道而言缺乏新意。我做得对吗?天知道! 当时倘若出版, 这本书毕竟是对那个时代, 我的某一段心路历程的一个记录……”反之,《美国日记》不过是他定期寄给埃伊纳乌迪Einaudi出版社朋友达尼埃莱?彭克罗利Daniele Ponchiroli的一组信札, 这些信也是为出版社所有工作人员, 甚至像卡尔维诺所言的, 任何一个想知道他的美国印象及经验的人所写的。作为自传资料——而非文学作品——我认为这是绝对必不可少的; 作为自画像, 最发自内心也最直接的文字。 所以, 这本书的价值可以是: 将读者与作者之间关系拉得更近, 透过这些文章深入这层关系。卡尔维诺认为:“重要的是我们之为我们, 深化我们与世界、与他人的关系, 这个关系可以是关系之所以存在的爱加上转换的意志力之总和。”埃斯特尔?卡尔维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