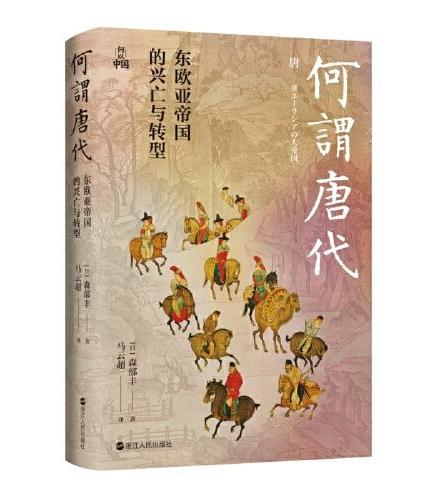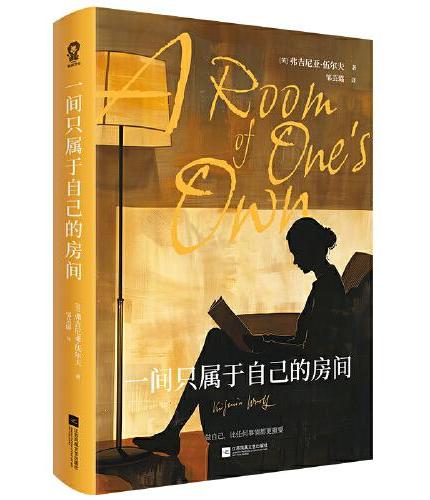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新时代硬道理 广东寻路高质量发展
》
售價:HK$
77.3

《
6S精益管理实战(精装版)
》
售價:HK$
100.6

《
异域回声——晚近海外汉学之文史互动研究
》
售價:HK$
109.8

《
世界文明中的作物迁徙:聚焦亚洲、中东和南美洲被忽视的本土农业文明
》
售價:HK$
99.7

《
无端欢喜
》
售價:HK$
76.2

《
股票大作手操盘术
》
售價:HK$
5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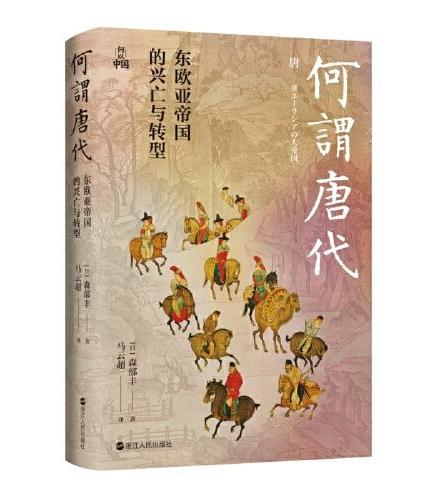
《
何以中国·何谓唐代:东欧亚帝国的兴亡与转型
》
售價:HK$
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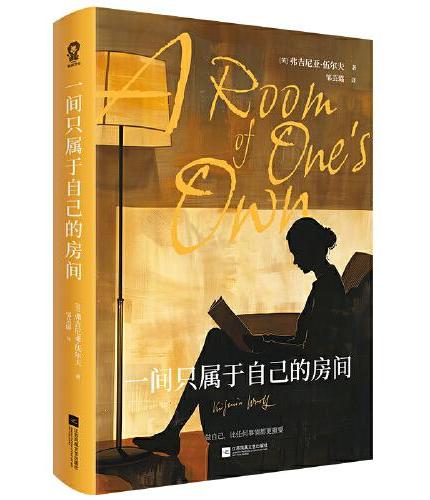
《
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 女性主义先锋伍尔夫代表作 女性精神独立与经济独立的象征,做自己,比任何事都更重要
》
售價:HK$
44.6
|
| 編輯推薦: |
★作者杨慎,记诵之博、著述之富,后人推为明代首位。
★杨慎《词品》一出,当时学人竞起而仿效,欲附骥尾。
★王大厚先生笺证《词品》,逐一核校原书,标明出处。
|
| 內容簡介: |
《升庵词品笺证》,六卷,拾遗一卷,附录四卷,明杨慎撰,王大厚笺证。底本为明嘉靖三十三年周逊序刻六卷本,校以嘉靖三十年珥江书屋本、万历四十五年杨有仁《升庵外集》本、万历年间陈继儒序刻本、天启七年安徽歙县程好之刻本、清嘉庆十四年李鼎元重校印李调元《函海》本。另参校了明刻四卷本二种、清刻节略本一种。笺证则核正引文,标明出处,于升庵此书多所补苴。
杨慎原书凡十馀万字,其论词篇幅之大,涉猎之广,辨析之精,世所罕匹。整理者王大厚全面梳理杨氏所征引各书,尽可能找出其原始出处。
|
| 關於作者: |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新都(今属四川成都)人。正德辛未(1511)进士榜首,授翰林院修撰。嘉靖三年,以谏大礼,谪戍滇中。
王大厚,巴蜀书社编审。著有《升庵诗话新笺证》(套装上中下册),为中华书局《中国文学研究典籍丛刊》之一种。
|
| 內容試閱:
|
楊慎(一四八八一五五九),字用修,升庵其號也,四川新都人。楊氏世代士宦,自父祖及叔伯子姪,一門七進士。祖楊春,精研《易》學,慎自幼秉承祖學,得其所傳。父廷和,懷經濟之才,負公輔之望。正德初劉謹用事,八黨干政,閣臣李東陽援廷和入閣以相抗,卒誅劉謹。正德七年,晋内閣首輔。時奸佞江彬等人導帝荒政出遊,廷和頗以持重,乂安中外。及帝崩,廷和主政三十七日,誅江彬、錢甯,革冒濫,裁工役,恩倖得官者大半斥去,正德蠹政,釐抉且盡。史稱其誅大奸,决大策,扶危定傾,功在社稷。然廷和新政,多不便於權豪貴倖,尤其爲失職者所恨。及世宗入嗣,詔議其父興獻王祀禮,新進及佞倖皆傾力附之。廷和堅執國典,主考孝宗,每抗旨執奏,封還御批。世宗大恨之,益鋭意尊親,主考興獻。因引張璁、桂萼,屏除閣臣,重用宦豎。凡正邪相争之事,皆以議禮出之。廷和不得已,嘉靖三年,上疏辭歸。於是張璁用事,大禮議成。按世宗在位四十年,於明乃升平盛世。史稱嘉靖初善政,張璁之功也。然廷和執政雖止三十七日,黜弊政,革冗員,興利除害,朝政一新。張璁繼之,不過規隨而已。蓋廷和於議禮,執意過偏,復恃擁立之功,視天子若出己門,致引世宗之恨,新政難施,甚而貽禍子孫,其可悲也乎!
升庵少年穎悟,以才情震播鄉里。武宗正德二年,鄉試第一,六年殿試狀元,授翰林院編修。世宗即位,爲經筵講官,預修《武宗實録》,秉筆直書,備具董狐之才。嘉靖三年,以議大禮,上言直諫,忤世宗,下詔獄,再受廷杖,死而復蘇,謫戍雲南永昌衛(今雲南保山)。從此僻居邊疆三十五年,嘉靖三十八年,卒於戍所,年七十二。
升庵以《黄葉詩》受知李東陽,出其門下。登第後入翰林,於秘閣書無所不讀。嘗語人曰:資性不足恃,日新德業,當自學問中來。謫戍之後,更肆力於學。其自序《丹鉛别録》,嘗云:自束髮以來,手所鈔録,帙成逾百,卷計越千。足見其淹博融通,聰明穎悟之外,實自用功勤學中來也。其平生著述四百餘種,廣涉經、史、百家、天文、地理、金石、博物、文獻考據、詩文詞賦以及音韻、文字之學。凡宇宙名物之廣,經史百家之奥,下至稗官小説之微,醫卜技能、草木蟲魚之細,靡不究心多識,闡其理,博其趣,而訂其訛謬焉。其爲學,治經不專限一藝,傳疏不墨守一家,小學之業,自古音古訓,以至篆籀銘刻,俗語雜字;諸子之書,自儒學道術,而旁及天文醫技,書畫博物。史則兼重雜載裔族,文獻金石,水經山圖,民俗方志;文則遍及詩賦詞曲,輯詩採謡,評文論藝。網羅百家,窮搜逸典,抉隱探微,針肓發墨,學者從風,日趨新變。《明史》本傳謂:明世記誦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爲第一。實非虚誇之言。
升庵究心詞學,尤極其力。任良幹序《詞林萬選》,嘗云升庵太史公家藏有唐宋五百家詞,雖曰誇飾,然亦足見其蒐集之功。平生編著《詞林萬選》、《百琲明珠》、《草堂詩餘補遺》、《古今詞英》、《詞苑增奇》、《填詞選格》、《填詞玉屑》、《詩餘輯要》諸書,並校點批評《花間集》、《草堂詩餘》。更著《詞品》一書,專論詞學。所作《升庵長短句》正、續編各三卷,存詞三百四十餘首,穠麗富贍,情致婉孌,尤以小令當行擅場,譽爲一代詞宗。今箋證《詞品》既竟,因擇其有裨詞學研究者數事,約略述之。
一
推尊詞體。自古文體有尊卑之别,詩尊而詞卑。蓋詩言志,詞則爲詩之餘,所言私情曲意,皆詩之不能道者也。雖文章豪放之士鮮不寄意于此,但隨後却往往自掃其跡,曰謔浪遊戲而已,不敢自毁其譽。若柳永混跡烟花,專事於詞者,終爲士林所棄。今檢《全宋詞》録作者一千三百餘人,較《全宋詩》作者近萬,人數相差六七倍之巨。殆詩文辭賦,古人以爲名山事業,而作爲小詞,乃伶工賤役之事,士大夫初不屑爲。即便一時興到之作,亦往往棄之不惜,存之則别刻,不入本集。而樂工歌伎所作,率皆淫辭濫調,文理欠通,可傳者少,亡佚者多。下至於元,儒士處娼優、乞丐之間,無可進身,皆躭玩北曲,氣格鄙俚以近俗。歷元至明,朝廷以程、朱理學治天下,頒《五經》、《四書》、《性理大全》,禁性絶欲,規定八股明經取士。士子皓首窮經,競趨時文,以求進身。文章之士,噤若寒蝉。中葉以後,文壇七子復以古相尚,倡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填詞於不朽之業,最爲小乘,纖言麗語,大雅是病。而於時傳奇方興,南風正熾,士夫禀心房之精,從婉孌之習者,風靡如一。至是詞學益衰,幾至於絶。當此之時,升庵疾起而力振之,作《詞品》六卷附《拾遺》一卷,凡三百二十餘則,彙集衆説,考流别、明正變、品評作品,欲示人以填詞之方,扶危濟傾,以救詞弊。因於《詞品序》首提詩詞同工而異曲,共源而分派之説。强調詩、詞共源,將詞之地位,與詩並行。既曰詩詞同源,填詞亦可上追風雅,繼武樂府,所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然詩之情曰暢志,詞之情曰縱欲,二者所司不同,功用各異,故曰分派而異曲。詞雖貴綺艷,不近曲禮,惟其能遣興抒懷、娱情怡性,曲盡人情之常,故偶然作之,亦無傷於大雅也。因舉勳德重望、剛方端嚴之士,若韓琦、范仲淹等,亦曾偶作綺艷小詞以遣興,復謂廣平之賦《梅花》,司馬公亦有艷辭,亦何傷於清介!更引朱熹《雲谷寄友絶句》日暮天寒無酒飲,不須空唤莫愁來之句,指出晦翁於宴席,未嘗不用妓。道學壁壘深嚴,而師儒老宿如朱子亦難忘情,何况世俗,於是詞可作而不必諱矣。
明初文坛,以臺閣相高,填詞意竟言終,殊少真趣;道學之士,復以談學論道入詞,酸腐庸陋,讀之欲嘔。而世俗日偷,尚淫綺而斥莊雅,取法不高,詞風益卑。其時前代詞集盡佚,惟《草堂詩餘》行世,填詞者奉以爲圭臬,不辨良莠,徒事摹擬。升庵患之,乃於《詞品》中予《草堂詩餘》多加批評,指斥流弊,褒揚是非,明其得失,補其闕遺,意欲爲填詞者引航導路。明天順間詞人馬洪,以詞名東南,自序其《花影集》云:花影者,月下燈前,無中生有。以爲假則真,謂爲實猶涉虚也。升庵嘉其以情爲實,以境爲虚,虚實之間,意味無窮。因舉其梅花《江城引》,以爲清氣逸發,瑩無塵想;復舉其題許東溟小景《昭君怨》,以爲言有盡而意無窮,方是作者,可謂推崇備至。《詞品》録其作品多至十六首,全書所録唐、宋詞人詞作,無出其右者。蓋馬洪詞出《草堂》而取法其上,升庵欲以爲範,指示時人也。
《詞品》一出,當時學人皆起而效尤。或引而據之,或辯而難之,皆欲附其驥尾,以求一逞。一時蔚然,遂成大觀。其時舊本《草堂詩餘》,按時令節序分篇,不便取用。有顧從敬取以重編,類分以體調長短,得《類編草堂詩餘》五卷。升庵因取以批點,畀與《詞品》並而行之。自後是書大行,有明以來,翻刻改編不下數十餘種。而多取效升庵,增補評騭,繕而完之。明末清初詞學大興,升庵扶正糾偏、發矇震聵之功,不可没焉。
二
探究源流,以明詞史。宋王灼以爲:蓋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至唐稍盛,今則繁聲淫奏,殆不可數。古歌變爲古樂府,古樂府變今曲子,其本一也。後世風俗益不及古,故相懸耳。而世之士大夫,亦多不知歌詞之變。提出樂府詞曲嬗變之説。升庵於此,亦嘗論之:漢代之音可以則,魏代之音可以誦,江左之音可以觀。雖則流例參差、散偶昈分,音節尺度粲如也。有唐諸子效法於斯,取材於斯,昧者顧或尊唐而卑六代,是以枝笑幹,從潘非淵也,而可乎哉!因有《選詩外編》、《五言律祖》、《絶句衍義》以及《千里面譚》之輯,以見唐人聲詩,出於六朝樂府。二人所見,可謂略同。
升庵又引王僧虔《古今樂録》:諸曲調皆有辭有聲,而大曲又有艷、有趨、有亂。辭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類也。艷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亦猶吴聲、西曲,前有和後有送也。解之云:艷在曲之前,與吴聲之和,若今之引子;趨與亂在曲之後,與吴聲之送,若今之尾聲。羊吾夷、伊那何,皆辭之餘音嫋嫋,有聲無字,雖借字作譜而無義,若今之哩囉嗹、唵唵吽也。以爲知此可以讀古樂府矣。宋沈括嘗云:詩之外又有和聲,則所謂曲也。古樂府皆有聲有詞,連屬書之,如曰賀賀賀、何何何之類,皆和聲也。今管絃之中,纏聲亦其遺法也。唐人乃以詞填入曲中,不復用和聲。朱熹亦云: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泛聲。後来人怕失了那泛聲,逐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二人所謂古樂府之和聲、泛聲,即升庵所説之辭之餘音嫋嫋,有聲無字,雖借字作譜而無義也。足見升庵於聲詩、曲詞嬗變之跡,已自得明晰之見。因云:唐人絶句多作樂府歌,而七言絶句隨名變腔。如《水調歌頭》、《春鶯轉》、《胡渭州》、《小秦王》、《三臺》、《清平調》、《陽關》、《雨淋鈴》,皆是七言絶句而異其名。其腔調不可考矣。唐人絶句即是詞調,但隨聲轉腔,以别宫商。如《陽關》、《伊州》、《水調》皆是。指出七言絶句入樂,樂人多易其原題以就樂府之調名。同一七言絶句,可入任一樂調歌之,隨所入樂調之不同而隨聲轉腔,以别宫商。由是推知,同一詞調,歌者歌聲婉轉,轉折不同,則聲情各異。記譜者於轉折處添字注音,後之填詞者於注音處添加實字,則詞體生焉。故《詞品》又引《苕溪漁隱叢話》以證之,云:唐初歌詞,多是五言詩或七言詩,初無長短句。中葉以後至五代,漸變成長短句。及本朝,則盡爲此體。
然升庵填詞之溯源尚不止於此,更提出填詞起於唐人,而六朝已濫觴,倡言填詞必泝六朝,亦昔人窮探黄河源之意之説。即音樂而論,詞樂爲燕樂,此今人所共識。而六朝音樂乃爲清商樂,故人或以升庵填詞必泝六朝之説爲非。然清商與燕樂,豈可絶然劃分!《樂府詩集近代曲辭序》云:其著令者十部:一曰讌樂,二曰清商,三曰西涼,四曰天竺,五曰高麗,六曰龜兹,七曰安國,八曰疎勒,九曰高昌,十曰康國,而總謂之燕樂。聲辭繁雜,不可勝紀。凡燕樂諸曲,始於武德、貞觀,盛於開元、天寶。則知清商實已包含於燕樂之中。《唐六典》云:凡有大燕會,設十部之伎於庭,以備華夷。十部共奏,不過昭示大國雍熙,夷部諸樂,備數而已。故鄭樵言十部之樂,其實皆主於清商。果然如此,則隋唐詞樂與六朝清商,實是一脈相承。如是而言,升庵之議,有何不可?升庵嘗論六朝梁、陳《選》詩云:詳其旨趣,究其體裁,世代相沿,風流日下,填括音節,漸成律體。蓋緣情綺靡之説勝,而温柔敦厚之意荒矣。大雅君子,宜無所取。然以藝論之,杜陵詩宗也,固已賞夫人之清新俊逸,而戒後生之指點流傳。乃知六代之作,其旨趣雖不足以影響大雅,而其體裁,實景雲、垂拱之先驅,天寶、開元之濫觴也,獨可少此乎哉!即填詞而論之,詞與六朝樂府緣情綺靡之情韻正同,堪可借鏡,此實升庵强調填詞必泝六朝之最終目的。升庵論詩主情,其《詩話》論之詳矣,而此説正其理論主張之擴展延伸。
唐宋詞調,多爲俗曲小唱。據今人統計,宋詞作者以南人爲多。南人所習用,自當以南方俗樂爲主。南方鴃舌之音,更適南口,故宋詞中每有以南音入韻者。升庵於此亦有所見,其填詞用韻宜諧俗、張仲宗、林外諸條已言之矣。然明人大多不明南北詞曲之辨,升庵於此亦不甚了了。故其《詞品》往往兼取詞曲而論之,作長短句,亦時取曲譜而填之。其時南詞北曲並行,填詞作曲,混雜不分。有識之士痛詞之入曲,欲嚴詞、曲之别,實則欲明其雅、俗之辨。升庵持論,亦乎如此。以爲詞用閩音,乃是鴃舌之病,豈可以爲法。極稱元人周德清著《中原音韻》,一以中原之音爲正,偉矣!嘗云:近世北曲,雖皆鄭衛之音,然猶古者總章、北里之韻,梨園、教坊之調,是可證也。近日多尚海鹽南曲,士夫禀心房之精,從婉孌之習者,風靡如一。甚者北士亦移而躭之,更數十年,北曲亦失傳矣。此雖言北曲,實則於詞調亡佚之由,已自在不言之中矣。然其發見宋詞多用南音,提出填詞用韻宜諧俗之論,實大輅之椎輪也。於後人進一步探討詞之南方特質,頗具發軔之效。
升庵非不知樂者,其説詞亦多從樂調入。其論轉、慢之爲曲名,填詞之借腔别詠等等之類,皆具卓識。若其論慢字爲樂曲名云:慢字爲樂曲名。陳後山詩:吴吟未至慢,楚語不假些。任淵注云:慢謂南朝慢體,如徐、庾之作。余謂此解是也,但未原其始。《樂記》云:宫、商、角、徵、羽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又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宋詞有《聲聲慢》、《石州慢》、《惜餘春慢》、《木蘭花慢》、《拜星月慢》、《瀟湘逢故人慢》,皆雜比成調,古謂之嘖曲。嘖與賾同,雜亂也。琴曲有名散,元曲有名犯。又曲終入破,義亦如此。凡此皆剖析委曲,見解新穎,爲治詞史者所樂道。
樂府宫調下轄曲子若干,其調或喜或悲,各寫名牌,以便樂部揀選,是爲曲名。填詞者選調填詞,須知曲調之喜怒哀樂,方可依調而填之。若詞意與曲調不諧,則難以感動人心。故沈括有云:唐人填曲多詠其曲名,所以哀樂與聲尚相諧會,今人則不復知其聲矣。哀聲而歌樂詞,樂聲而歌怨詞,故語雖切而不能感動人情,由聲與意不相諧故也。宋人王灼《碧鷄漫志》嘗取樂曲二十餘首,考論調名之源。其時詞調未失,其論尚可及於音譜樂調之變。而當升庵之世,詞樂早亡,考訂詞調所出,已自不能。惟有據詞意推其詞名原義,或可進而探知其調之喜樂哀怨。故升庵於此,頗致意焉。嘗云:唐詞多緣題所賦,《臨江仙》則言水仙,《女冠子》則述道情,《河瀆神》則詠祠廟,《巫山一段雲》則狀巫峽。如此詞題曰《醉公子》,即詠公子醉也。爾後漸變,與題遠矣。他如《搗練子》,即詠搗練、《人月圓》,即詠元宵、《乾荷葉》,即詠乾荷葉等皆是。實則詞調創始之初,因事立題,是所必然,除沿用舊曲若《伊州》、《水調》者,類皆如此。惟是後世所賦漸多,離題漸遠,初始難索矣。然辨識詞名之始,此自是一途。
詞人創調製曲,肇錫以佳名,是所願也。摘取前人名言佳句以飾其作,自是首選之義。正德間都穆作《南濠詩話》,即明此理,嘗云:昔人詞調,其命名多取古詩中語。後四十年,升庵亦提出詞名多取詩句之説,正所謂英雄所見略同也。因例舉之云:《蝶戀花》則取梁簡文帝翻階蛺蝶戀花情,《滿庭芳》則取吴融滿庭芳草易黄昏,《點絳唇》則取江淹白雪凝瓊貌,明珠點絳唇,《鷓鴣天》則取鄭嵎春遊鷄鹿塞,家在鷓鴣天,《惜餘春》則取太白賦語,《浣溪沙》則取少陵詩意,《青玉案》則取《四愁詩》語。《西江月》,衛萬詩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裏人之句也。《瀟湘逢故人》,柳渾詩句也。《粉蝶兒》,毛澤民詞粉蝶兒共花同活句也。升庵以考證之法解析詞名,雖不無穿鑿附會、勉强臆測之處,要其新穎别致,思至情切,自非博洽廣識之士,不能出此。胡應麟於升庵調名緣起之説,辨駁尤多,然雖反復辨難,皆不過駁正糾偏而已,終不能證唐詞多緣題所賦、詞名多取詩句立論之非。胡氏因更立樂府所重,在調不在題之論,云:余謂樂府之題,即詞曲之名也;其聲調,即詞曲音節也。今不按《醉公子》之腔,而但詠公子之醉;不按《河瀆神》之腔,而但賦河瀆之神,可以爲二曲乎?考宋人填詞絶唱,如流水孤村、曉風殘月等篇,皆與詞名了不關涉。而王晋卿《人月圓》、謝無逸《漁家傲》,殊碌碌無聞。則樂府所重,在調不在題,斷可見矣。詞具音樂屬性,聲腔韻律乃首要之義,以謂樂府所重,在調不在題,誠不爲過。然製詞創調須聲意相諧,因事立題,亦是必然,故詞名與曲意何得無關?升庵考訂詞名,其意正在追索曲意。胡氏取後世填詞所賦予詞名了不關涉之例,以證升庵考辨詞名源起爲枉費徒勞,實乃巧言佞説,强詞奪理也。後清人毛先舒頗承升庵之説,起而力駁胡氏之議,並從而衍之,有《填詞名解》之作。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