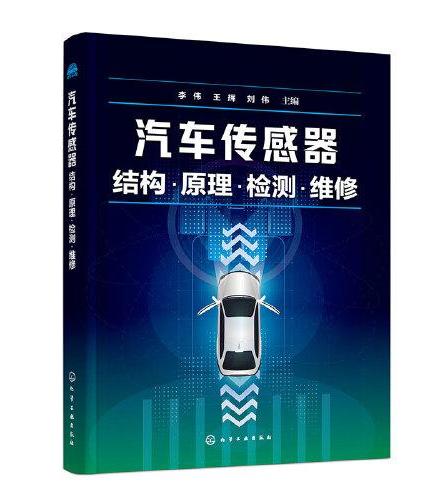序:比深情更可贵的是俯身的瞬间邹滢颖
我看过农人最美的笑容。江南的田地,七八亩连在一起就十分可观了。最热的七月底,那七八亩水稻成熟了,金黄一片,密密扎扎、沉甸甸、能与三伏时的阳光争一下光芒,让一手打造出这一切的人站在稻子前面,像个得胜的将军。风吹稻田,吹干了农民身上流不完的汗,远处的田野一望无际。这样的景象,我也亲眼见过。但随着城市的扩张,土地荒芜,村庄凋敝,那个一步一步离开农田、离开故乡的农民,成为渐渐消失的乡村的最后一笔。我只能感叹不知道还能做什么,直到华诚出现。
华诚刚来杭报副刊的时候,交给我一本简历,我一看惊了,那不是简历,是一本厚厚的书,里面全是他的作品。从衢州到杭州,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做个更好的写字的人;但是没几年,他已经不满足于文字的深耕,重新把目光投向了故乡,田园将芜胡不归?他回去种田了,一亩三分地,天光云影共徘徊。我看过他的一张照片,站在成熟的稻田中,汗湿衣襟,那张照片让我又一次感到了吹过稻田的风。他把父亲的水稻田打造成了一个IP知识产权。
谁都知道干农活苦,从小干惯农活的华诚不会不懂这个。农忙时,男人凌晨三点多出工,妇女孩子四五点时也在田间了,赶在最毒的太阳到来前抢种抢收。最难受的是下午三四点,什么虫子都出来了,叮得你发毛。但是在他的笔下,清晨的露珠、稻田里的声音,都是可以观察和聆听的,写得又美又硬,像谷粒,扎着了你也无所谓。你所忽略的美好故土,他用自己的劳作打造了两个,一个在大地上,一个在文字里;一个可以收获,一个用于收藏。
父亲的水稻田不仅团结了他家三代人及村里农民,还帮助华诚找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他们互称稻友,一起种田一起出书。我有时觉得草木光阴里可以保留更多寂静的劳作,像五十岚大介的《小森林》,像高仲健一的《山是山水是水》,在劳作中,你拥有抚平伤口的能力,保留更完整的自己,但那是很老派的想法,何况华诚看上去并没有什么伤口需要抚平,他一直是平稳温暖、给人信赖的小哥哥模样。
因为一块水稻田,帮助了一个人脱粒、去腻,不至品在岁月忽晚中徒留空叹。对渐渐消逝的故土发出喟叹,那还仅仅停留在动心的境界,远远抵不上俯身的瞬间,那是动身的境地。深情与俯身隔了一段长长的修行,而劳作是唯一抵达的办法。那是只有在稻田中吹过风的人才能明白的。
自序
劳作的意义
故乡不只是用来怀念的
孩子们成群结队满村子乱跑的情景不见了。
哪怕是周末,村庄也是静悄悄的。
没有摇着拨浪鼓卖小玩意儿的货担郎,没有走村串户的木匠、箍桶匠与赶公猪的人,没有抬着嫁妆吹吹打打的长长队伍,也没有人穿着蓑衣赶着牛从细雨中走来。
村庄寂静得可疑。显而易见,我们的村庄正在发生着深深的变化。房子变得高大,道路变得平坦。新农村建设使得村庄变得新起来,但是这仍无法阻止村庄里的人越来越少的趋势。
这就是现在的村庄,每一次回到我的村庄里去,我都觉得眼前景象可疑。
同样可疑的还有春节村庄一下子热闹起来,到处都是衣着光鲜、面容陌生的返乡人。
明明都是这个村庄的村民,但是大多数时候他们都会消失,像一滴水消失在大海中。
我在浙西衙州常山县天马街道一个叫作五联村的地方长大。
每天上学要从广阔的田野间穿过,闻着稻花和油菜花的芳香,农忙时和父母一样挽起裤脚下田,一个暑假下来整个人晒得黝黑。
当我因为插秧、割稻而腰酸背痛、苦不堪言之时,父母的告诫就在耳边响起:你看,如果不好好读书,就只有一辈子种田。
好啊,那就咬牙,努力读书。
十六岁,我终于离开村庄,考上了省城的学校,后来又留在了城市工作,从此不用当农民。
后来,每一次回到村庄,我都发现村庄在变得陌生。
我们以前读书,看到古诗里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牧童遥指杏花村,朝耕及露下,暮耕连月出,觉得这是中国的农村,江南的农村。
现在,这样的情景已经没有了。
村民们离开祖祖辈辈熟悉的土地,转向陌生的城市和工厂谋生。土地似乎一夜之间被他们抛弃。可是如果死守土地,洒下无数汗水换回的收获,根本不足以维持基本生活。
农民是自卑的,我的父亲当了一辈子农民,从来没有为自己是个农民而感到骄傲过。他和别人一样挥汗如雨,他能种出很好吃的水稻与青菜,但是他从来没有为此而自豪。
他们是被时代的列车抛弃的群体。这个社会不需要他们当农民了。但是,我们的村庄真的就应该变成这样吗?中国传统乡村延续数千年的生活方式,就要这样消逝了吗?
每一滴汗水,理应配得上那份骄傲
谁的故乡不在沦陷?但除了感叹,还应该做点儿什么。哪怕力量微小,改变不了世界,或许可以改变身边一点点。
乡村也不只是用来怀念的,需要大家一起去建设。
从二○一四年开始,我发起了父亲的水稻田活动,重新回到乡下老家,与父亲一起种一片水稻田。同时,我也用文字和图片来记录水稻的耕作与生长,记录一个村庄的变化。
因为下田,我和父亲之间的共同话题多了起来,我开始慢慢懂得父亲。
父亲高中毕业,有点文化,当过几十年农村电工。他一辈子都没离开过土地。他和我母亲一起,在土地上艰辛劳作,先后把三个子女送进学校,送进了城市。
十多年前,我就希望父母跟着我们一起到城市生活。我觉得土地没有那么重要,如果父母为了生活过得更好,完全可以和我们一样离开土地,进入城市。但他们不习惯,也不愿意。我也不理解,为此我们还发生过争论在我看来,家里那点田地,扔了不足惜。父亲却看得比什么都重。
当我重新回到稻田,重新洒下汗水劳作,重新耕耘与收获的时候,我与土地之间那种断裂的联系终于又重新建立起来了。
一同建立起来的,还有我对父亲的理解。同时,我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也在慢慢地发生改变。我不再认为城市是更好的生活地点,我也不再认为从事其他任何职业比当农民更值得骄傲。
农民和村庄,在这个喧嚣的时代是被掩盖、被遮蔽的。农民的劳作价值是被忽视的,被极大低估了。
如果我不为当农民的父亲以及更多的农民父亲们说话,还有谁能为他们说话?
因为父亲的水稻田这个乡村实验项目,许许多多的城市人来到我们家的水稻田。
春天,大家挽起裤脚下田,一起插秧;秋天,大家扛出沉重的打稻机,一起用镰刀割稻。
这些活儿不要说孩子们.就是很多成年人都没有体验过。只有直接接触土地,才会深刻感受到劳作的辛苦、粮食的得之不易。
我们的孩子,还能认识粮食吗?
种田在这个时代似乎是一件有些可笑的事,尤其是单家独户的小农种田,愈加显得不合时宜,种田注定是要亏本的。
这是一项笨拙的劳动。其实很多手工活计也都是如此,都是笨拙的劳动。
一个绣娘可能要花两三年才能绣完一件作品;一个篾匠终其一生也做不了多少竹篮;一个农民,一辈子又能插多少秧呢?
这些笨拙的劳动者,最可惜的,不是他们做不了多大的事,而是即便一辈子都在做这件事,却仍然被时代所抛弃。
时代像列火车跑得太快,笨拙的人跑丢了鞋,仍然赶不上它。
但,这恰恰是我来做父亲的水稻田这件事的初衷所在。
从春到秋,我想记录下水稻耕种的过程,我想体会父辈在劳作中的艰辛与汗水。我想把这样的劳作与耕种,传递给我们的孩子,以及城市里的人们。
二O一六年,我那本关于稻田的书《下田:写给城市的稻米书》,由三联生活书店出版。
那本书是我写给父亲和村庄的,更是写给城市,写给孩子的。
或许再过十年,当这些年老的农民也不得不离开土地的时候,我们的水稻田都会荒芜,长满野草。
因为没有一个年轻人能真正继承父辈们的种田手艺。
城市里的孩子,他们双脚接触不到真正的土地。传统的中国农耕文化正在快速地消失,即使是农村的孩子,他们也不会种田了。
时代终究会朝前发展,而劳作的意义永恒。
当我蹲在稻田中间,注视一株水稻的花时;当我趴在野草中,观察一只纤弱的豆娘起起落落时;当我在稻禾中间汗落如雨,或当我品尝着自己劳作所获的大米时我发现,生活本来如此简单而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