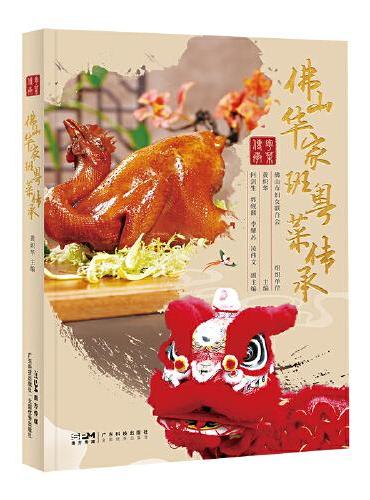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甲骨文丛书·中华早期帝国:秦汉史的重估
》
售價:HK$
300.2

《
欲望与家庭小说
》
售價:HK$
98.6

《
惜华年(全两册)
》
售價:HK$
70.3

《
甲骨文丛书·古代中国的军事文化
》
售價:HK$
99.7

《
中国王朝内争实录(套装全4册):从未见过的王朝内争编著史
》
售價:HK$
244.2

《
半导体纳米器件:物理、技术和应用
》
售價:HK$
177.0

《
创客精选项目设计与制作 第2版 刘笑笑 颜志勇 严国陶
》
售價:HK$
6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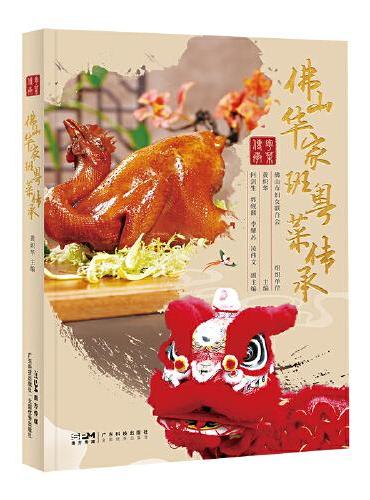
《
佛山华家班粤菜传承 华家班59位大厨 102道粤菜 图文并茂 菜式制作视频 粤菜故事技法 佛山传统文化 广东科技
》
售價:HK$
221.8
|
| 編輯推薦: |
● 《再见,宝贝》是钱德勒本人*满意的作品。
● 本书出版于1940年,是作者第二部以私家侦探马洛为主角的小说,三次改编为电影,另有舞台剧和广播剧版本。
● 那是一个金发女郎。一个足以让主教一脚把彩色玻璃窗踹个洞的金发女郎。
|
| 內容簡介: |
本书出版于1940年,是作者第二部以私家侦探马洛为主角的小说,三次改编为电影,另有舞台剧和广播剧版本。
马洛遭逢了凶悍的对手。正当他准备从一件平凡的案子中抽身时,却发现自己在正确的时间来到了错误的地点:面前是一具被打断脖子的尸体。在马洛查明真相的过程中,一伙珠宝窃贼逐渐现身,另外几桩命案等待着他,而驼鹿马洛伊深爱的女孩维尔玛如同幽灵般难以捉摸,美艳,又似乎随时能置人于死地。
|
| 關於作者: |
|
钱德勒是世界小说史上最伟大的名字之一。他是艾略特、加谬、钱锺书、村上春树等文学大师最崇拜的小说家。被称为文学大师崇拜的大师。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位被写入经典文学史册的侦探小说大师。他的作品被收录到《美国文库一》中。他共创作了七部长篇小说和20部左右的短篇。钱德勒被誉为硬汉派侦探小说的灵魂,代表着硬汉派书写哲学的最高水平。他是美国推理家协会(MWA)票选150年侦探小说创作史上最优秀作家的第一名,他塑造的侦探菲利普马洛被评为最有魅力的男人。在四十年代好莱坞男演员以能扮演菲利普马洛为荣,其中以亨弗莱 鲍嘉扮演的马洛最为成功。钱德勒是电影史上最伟大的编剧,他为好莱坞缔造了激动人心的黑色电影。他与比利怀尔德合作的《双重赔偿》被称为黑色电影的教科书。自1942年到1947年,他的4部小说6次被搬上银幕,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福克纳都只能给他当助手,与他合作过的大牌导演有希区柯克、比利怀尔德、罗伯特艾特曼等。似乎至今没有一个作家享有好莱坞如此的厚爱。
|
| 內容試閱:
|
中央大道上有几个种族混杂的街区,这些地方还没有完全被黑人所占据,此处就是其中之一。我刚刚从一家店面大小只有三把椅子的理发店里出来;某家代理行认为一个名叫德米特里阿莱蒂斯的代班理发师就在那里工作。这是笔小生意。他的老婆说,她愿意付一小笔钱,只要能让他回家。
我一直没能找到他,可阿莱蒂斯太太也一直没有付我钱。
那天很暖和,此时已经接近三月底了,我站在理发店外,抬头看着一块伸在外面的霓虹灯广告牌,那属于二楼一家叫弗洛里安的餐厅兼赌场。一个男人也在抬头看着那广告牌。他仰望着那些落满灰尘的窗户,脸上现出一种凝固的狂喜神色,就好像是一个匈牙利移民第一眼看到自由女神像一般。他是个大个子,但身高不超过六英尺五英寸,肩宽也不超过一辆啤酒货车。他离我大概有十英尺远。他的胳膊松弛地垂在身体两侧,一支被遗忘的雪茄在他粗大的手指后面冒着烟。
纤瘦安静的黑人在街上来来往往,不时驻目向他投去匆匆的一瞥。这个男人值得细看。他头戴一顶起毛的博尔萨利诺帽,身着一件粗陋的灰色运动夹克,上面挂着白色的高尔夫球充作纽扣;他的行头还包括一件褐衬衫,一条黄领带,一条打褶的灰色法拉绒便裤和一双短吻鳄皮鞋,脚趾处绽开了白色的大洞。从他的外套贴胸口袋里,一条演出用的手帕钻了出来,垂在外面,颜色是与他的领带一样的亮黄色。他的帽檐上还别着几根五颜六色的羽毛,但这真的已经没有必要了。中央大道绝非这世上衣着最低调的地方,可即便是在这里,他看上去也招摇得像是一只大狼蛛落在了白蛋糕上。
他的肤色苍白,胡子也该刮一刮了。他的这把胡子永远都该刮。他长着蜷曲的黑发,眉毛长得都快碰到那只宽鼻子了。对于这样一个大块头的男人来说,他的耳朵却细小匀称,眼睛中闪着泪珠般的光芒灰眼睛似乎经常给人这种感觉。他的站姿像尊雕像,过了许久,他露出了一丝微笑。
他慢慢地穿过人行道,走到那扇双开式弹簧门跟前,紧闭的门后就是通往二楼的楼梯。他一把把门推开,朝街道的左右两边投去面无表情的冷冷一瞥,然后走了进去。要是他只是个小个子,而且穿得较为低调的话,那我可能会以为他打算持枪抢劫呢。但这样的衣服,这样的帽子,这样的块头绝不可能。
弹簧门向外摆了回来,然后渐渐不动了。可就在它完全停下之前,门又突然间猛地被朝外撞开了。某个东西飞过人行道,落在了阴沟里,刚好掉在两辆停在路边的汽车中间。那东西手膝着地,发出一声尖利的叫声,就像一只被逼进角落的老鼠。它慢慢地爬了起来,找回了一顶帽子,然后跨回到人行道上。那是个瘦骨嶙峋、肩膀窄窄的棕肤年轻人,穿着件淡紫色的套装,上面别着一支康乃馨。它长着一头光溜溜的黑发。它张开嘴,叫唤了一阵子。路人们茫然地盯着它。随后它重新快快活活地戴好帽子,悄无声息地走到墙边上,迈着外八字的步子顺着沿街的一排房屋默默地走开了。
沉寂。人流如旧。我走到那扇双开门边上,站在门前。两片门板现在已经一动不动了。这不关我的事。于是我把门推开,朝里面张望。
黑暗中伸出一只手来,手掌大得可以让我坐在上面。那只手一把抓住我的一只肩膀,几乎把它捏得粉碎。然后这只手把我从门里拖了进来,轻轻松松地将我提上了一级台阶。一张巨大的脸孔正盯着我看。一个低沉的声音对我开了口,语调很平静:
进来抽烟的,是吧?我也是,伙计。
屋里面很暗,很安静。头顶上隐隐传来人声,可楼梯上只有我们两个人。这大个子一脸严肃地盯着我,继续用那只手摧残着我的肩膀。
一个黑人,他说。我刚刚把他扔出去了。你看到我把他扔出去了?
他松开了我的肩膀。骨头好像还没碎,但整只胳膊都麻了。
这本来就是那种地方,我边说边揉着肩膀。你还能指望怎么样?
别这么说,伙计。那大个子轻轻地发出咕噜噜的喉音,就像是四只老虎刚刚用完餐。维尔玛以前在这里工作。小维尔玛。
他再度伸手去抓我的肩膀。我想要躲闪,可他的动作快得就像只猫。他又一次开始用那些钢铁般的手指折磨我的肌肉。
没错,他继续说。小维尔玛。我已经有八年没有见到她了。你说这是家黑人店?
我用低哑的声音说了声是。
他又把我向上提了两级台阶。我奋力地挣脱开来,试图获得一点周旋的空间。我没带枪。寻找德米特里阿莱蒂斯似乎不需要枪。但我怀疑就算有枪也没什么用。这大个子说不定会一把将它从我手里夺走,然后塞进嘴里。
你上楼自己看看吧,我努力不让自己的声音透露出身体所承受的剧痛。
他再次放开了我。他用那双灰眼睛看着我,眼神中流露出某种哀伤。我现在感觉很好,他说。我可不想让什么人来烦我。你跟我一起上楼吧,也许我们可以喝上两杯。
他们不会招待你的。我跟你说了,这是家黑人店。
我已经有八年没见到维尔玛了,他用他那低沉悲伤的嗓音说着。从我说再见起到现在,已经有八年了。她有六年没给我写信了。可她一定有她的理由。她以前在这里工作。她很可爱。你跟我上楼去,咋样?
好,我大声喊道。我跟你走。只是别扛着我。让我自己走。我很健康。我完全是个成年人了。我可以自己上厕所,自己料理一切。只是请你别扛着我。
小维尔玛以前在这里工作,他轻声说着。他根本没听我说话。
我们朝楼上走去。他允许我自己走路。我的肩膀生疼,脖子后面全湿了。
2
又有一扇弹簧门挡在了楼梯顶端,不知紧闭的门后面究竟有什么。大个子用两根拇指轻轻地把门推开,随后我们进了房间。这是一间狭长的屋子,不太干净,不太明亮,也不太欢乐。
角落里,一道光锥下,一群黑人围在一张双骰儿赌桌边唱着歌,聊着天。紧挨着右手边那面墙的是一个吧台。房间里剩余的地方差不多摆满了一张张小圆桌。屋里有几个顾客,男男女女,全都是黑人。
赌桌边的歌声顿时停了下来,桌前的亮光也忽的一下灭了。一阵突然的沉寂,沉重得就像一条进水的船。一双双眼睛望着我们,栗色的眼睛,嵌在一张张肤色从暗灰到深黑的脸孔上。一颗颗脑袋慢慢地转向我们,脑袋上的眼睛在一片属于异族的、怪异的死寂中闪着光,瞪视着。
一个脖颈粗实的黑人正靠在吧台的一端,他的衬衫袖筒上缠着粉色的吊袖带,宽阔的后背上背着粉白两色的吊裤带。此人浑身上下都写着两个字:保镖。他慢慢地把那只抬着的脚放下,然后慢慢地扭头盯着我们,一边把两脚缓缓张开,伸出一条宽大的舌头舔了舔嘴唇。他长着一张几乎报废的脸,看上去好像被人用各种物品轮番砸过一遍,就差掘土机的铲斗了。它曾被人划上疤痕,被砸扁,再碾粗,脸上的口子有的一格一格,有的一条一条。这是一张无需再有恐惧的脸。它已然经受了所有你可以想象得到的摧残。
他的一头短发皱巴巴的,发色中带着一抹灰。一只耳朵缺了耳垂。
这黑人生得肩宽体阔。他两腿粗壮,看上去有一点罗圈,这在黑人当中可不太常见。他又舔了舔嘴唇,露出一个微笑,然后身子动了起来。他以一种放松的、拳击手式的半蹲姿势朝我们走了过来。大个子一言不发地等着他。
这个胳膊上缠着粉色吊袖带的黑人伸出一只巨大的棕色手掌贴在大个子的胸膛前。这手虽大,可这样看起来却显得像根大头针。大个子一动不动。保镖挤出一个温和的微笑。
白人不能进,伙计。这是给有色人种的。对不起。
大个子转动着那双小小的、哀伤的灰眼睛,往房间里四下张望着。他的脸颊微微泛红。臭擦鞋的,他压低了嗓子,愤怒地说了一句。然后他又提高了音量。维尔玛在哪儿?他问那保镖。
保镖没有放肆地大笑。他端详着大个子的衣服他的褐衬衫和黄领带、他粗陋的灰外套,还有上面的白色高尔夫球。他微微地转动着那颗厚实的脑袋,从各个角度审视着这一切。他又低头看了看那双短吻鳄皮鞋,轻轻地笑出声来,像是被逗乐了。我有一点为他感到难过。这时他又轻声地开了口。
维尔玛你说?这里没有维尔玛,伙计。没有婊子,没有马子,什么都没有。这里是饭馆儿,伙计,这里是饭馆儿。
维尔玛以前在这儿工作的,大个子说。他的语调像是在做梦,就好像他正独自一人在树林里采着野紫罗兰。我掏出手帕,又擦了擦脖子后面的汗。
保镖突然放声大笑。没错,他边说边飞快地扭头瞅了一眼身后的人群。维尔玛以前在这儿工作。可维尔玛现在不在这儿工作了。她退休了。呵呵......呵呵。
麻烦把你那只该死的手从我衬衫上拿开,大个子说。
保镖皱了皱眉。他可不习惯听别人这么跟他说话。他把手从衬衫上拿开,握成了拳头,它的大小和颜色都像极了一只巨大的茄子。他得考虑他的饭碗、他好勇斗狠的名声,还有他的公众信誉。这些问题他考虑了一秒钟,然后犯下了一个错误。他又狠又快地挥了一记拳,胳膊肘猛的向外一抽,拳头落在了大个子的下巴一侧。房间里四下传出一阵轻轻的喘气声。
这可是结结实实的一拳。大个子肩膀一垂,身子紧跟着晃了一下。这一拳力道十足,挥出此拳的这个人平时一定没少练过。大个子的脑袋只歪了不到一英寸。他没有试图招架。他承受了这一击,微微抖了抖身子,喉咙里轻轻地哼了一声,然后一把抓住了保镖的喉咙。
保镖想要用膝盖顶他的裆部。大个子让他在半空中转了个身,他那双花里胡哨的鞋一下子在粗糙的油地毡上滑脱了。他把保镖的身体向后一弯,腾出右手去抓他的腰带。那腰带就像绑肉绳一样一下子断了。大个子伸出一只巨大的手掌,直直抵住保镖的脊柱,然后奋力一推。他直接把保镖扔到房间那头去了,这家伙在空中转着圈,左摇右摆,两手乱舞。三个人跳起身来躲开他。保镖翻身倒地时带翻了一张桌子,接着狠狠地砸在了踢脚板上,声音响得你在丹佛都能听得见。他两腿抽搐了一下,然后就躺倒不动了。
有些家伙,大个子开口道,总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该狠。他朝我扭过头来。对了,他说。你跟我喝一杯吧。
我们走到吧台前。那些顾客或单身一身或三三两两,全都成了一言不发的影子,他们无声地从地板上漂过,又无声地从楼梯尽头的那扇门里飘了出去。无声如草地上的黑影。他们甚至都没有让弹簧门摇摆。
我们在吧台上倚着身子。酸威士忌,大个子说。你的自己点。
酸威士忌,我说。
于是我们拿到了酸威士忌。
大个子顺着又厚又矮的玻璃杯壁面无表情地把酸威士忌舔下肚去。他严肃地盯着酒吧招待这是个愁眉苦脸的瘦小黑人,穿着一件白外套,脚痛般地动来动去的。
你知道维尔玛在哪儿吗?
维尔玛,是吗?酒保哼哼唧唧地说。我最近没在这块儿瞅见她。最近没见着,没有,先生。
你来这儿多久了?
让我瞧瞧,酒保放下毛巾,额头上现出一条条皱纹,然后扳起了手指头。大概十个月吧,我猜。大概一年。大概
到底是多久,大个子说。
酒保两眼瞪得像铜铃,喉结上上下下地扑腾着,像只没头的母鸡。
你们这笼子变成黑人夜店有多久啦?大个子粗声盘问道。
谁说是?
大个子的的手捏成了拳头,手中那只装着酸威士忌的玻璃杯几乎顿时消失在了无形之中。
五年吧,我说。至于这个叫维尔玛的白人姑娘,这家伙肯定什么也不知道。这里没人知道。
大个子看我的眼神就好像我刚刚从蛋里孵出来一样。那杯酸威士忌好像没有让他高兴起来。
混蛋,谁让你来插一脚的?他问我。
我挤出一个微笑,一个大大的、温暖的、友好的微笑。我就是那个跟你一起进来的家伙。想起来了吗?
他咧嘴回了我一个笑容,一个干巴巴的笑,只见白牙,没有意义。酸威士忌,他吩咐酒保。把你裤裆里的跳蚤抖干净。上快点儿。
酒保迈着小碎步子跑前跑后,骨碌碌地翻着白眼。我背靠吧台,抬眼看着房间。屋里现在空了,只剩下了酒保、大个子和我自己,当然还有那个一头撞在墙上的保镖。那保镖开始动弹了。他慢慢地挪着身子,像是忍着剧痛、十分吃力的样子。他沿着踢脚板不声不响地爬着,像缺了一只翅膀的苍蝇。他挪到了桌子后头,精疲力竭的样子就像一个人突然之间苍老了、幻灭了。我看着他挪动身子。酒保这时又拿来了两杯酸威士忌。我朝吧台转过身子。大个子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那个在地上爬行的保镖,然后就不再留意他了。
这夜店里现在什么都没有留下了,他抱怨道。以前这儿有一个小舞台,有乐队,还有一个个漂亮的小房间,男人可以进去找些乐子。维尔玛在这儿唱过歌。她是个红头发。媚得就像蕾丝内裤。我们那时都要结婚了,结果他们陷害了我。
我喝下了第二杯酸威士忌。这场冒险已经快让我受够了。怎么陷害的?我问道。
你以为我这八年都上哪儿去了?
捉蝴蝶。
他用一根粗得像香蕉的食指戳着自己的胸膛。蹲在牢里呐。我叫马洛伊。他们叫我驼鹿马洛伊,因为我个儿大。大本德银行劫案。四万大洋。我一个人干的。厉不厉害?
你现在打算把钱花掉对吧?
他狠狠瞪了我一眼。这时我们身后传来一阵声响。那保镖站起身来了,左摇右晃地走了几步,伸手握住赌桌后面一扇黑门的把手。他打开门,几乎是摔进去的。门哐的一声关上了,然后咔哒一声上了锁。
那是什么地方?驼鹿马洛伊厉声问道。
酒保的眼珠在脑壳里飘忽不定,然后才费力地定睛望着那扇门,保镖刚刚跌跌撞撞地从那里钻了进去。
那那是蒙哥马利先生的办公室,先生。他是老板。他的办公室就在那后面。
他说不定知道,大个子说。他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他最好不要也跟我说笑话。已经碰着两个这样的人了。
他慢悠悠地穿过房间,步履轻快,心中没有一丝顾虑。他巨人般的后背遮住了那扇门。门锁着。他拉住门摇了摇,一块门板飞到了一边。他走了进去,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一阵沉默。我看着酒保。酒保看着我。他的眼神若有所思。他擦了擦柜台,叹了口气,右臂撑在台面上趴了下来。
我伸手越过柜台,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这只胳膊又瘦又脆。我捏着它,对他微笑。
你那底下藏着什么东西,伙计?
他舔了舔嘴唇,抵着我的胳膊,一言不发。一抹灰色爬上了他那张发亮的脸膛。
这是个狠角儿,我说。而且他很容易发飙。他喝了酒就这样。他正在找一个他以前认识的姑娘。这地方以前是家白人店。懂了没有?
酒保舔了舔嘴唇。
他离开这里好久了,我接着说。八年了。他好像没有意识到八年究竟有多久,但我估计在他看来那就是一辈子。他觉得这儿的人应该知道他的姑娘在哪里。懂了没有?
酒保慢吞吞地说:我以为你跟他是一伙儿的。
我身不由己啊。他在楼下问了我一个问题,然后就把我拖上来了。我以前从没有见过他。但我可不想让人给扔到房子的那头去。你那底下藏着什么?
我弄了一把锯短的猎枪,酒保说。
啧啧,那是违法的,我低声说。听着,你跟我是一伙儿的。还有别的吗?
我还弄了一把左轮,酒保说。在雪茄盒里。放开我的胳膊。
很好,我说。你可以走开了。悠着点儿,侧着身走。现在不是开大炮的时候。
你算老几,酒保冷笑着,用他疲倦的身体顶着我的胳膊。你算
他突然打住了。他的眼珠在滴溜溜得转。他的脑袋猛地一抖。
屋后传来一声直直的闷响,声音就来自赌桌旁边那扇紧闭的门后面。也许那只是摔门的声音。但我觉得不像。酒保也觉得不像。
他此刻呆若木鸡,嘴角流着口水。我竖起耳朵听着。再没有别的动静了。于是我猛地朝柜台的那头扑去。我已经听得太久了。
屋后的那扇门砰地一声开了,驼鹿马洛伊一个箭步冲出门来,动作流畅又凶猛,接着又突然刹住了,双脚就像在地上生了根一样,脸上浮现出一个咧开大嘴的苍白笑容。
一支柯尔特点四五手枪攥在他手里,就像把玩具枪。
谁都不许摸裤子,他懒洋洋地说。把手老老实实地放在吧台上。
酒保和我都把手放了下来。
驼鹿马洛伊迅速地将房间扫视了一遍。他那紧绷的笑容就像是钉在脸上似的。他移动脚步,无声地穿过房间。他看上去确实像是能单枪匹马抢劫银行哪怕是穿成这样。
马洛伊走到了吧台前。站起来,黑鬼,他轻声说。酒保把两手高高地举在半空中。大个子走到我背后,仔仔细细地用左手把我身上摸了个遍。他火辣辣的气息喷在我的脖子上然后挪开了。
蒙哥马利先生也不知道维尔玛在哪儿,他说。他想要用这个告诉我。他用结实的大手拍着那支枪。我慢慢地转过身来看着他。没错,他说,你会了解我的。你不会忘了我的,伙计。我只要你告诉那些小子们:不要乱来。他扭了扭枪。好啦,拜拜了,你们两个小阿飞。我得去赶电车了。
他开始朝楼梯的顶端走去。
你还没付酒钱呢,我说。
他停住了,认认真真地看着我。
也许你那里有两个钱,他说,但我不想捏得太狠了。
他继续往前走,穿过了那扇弹簧门,随后远传来了他走下楼梯的脚步声。
酒保俯下身子。我一跃而起,绕到了柜台的后面,一把将他挤开。一支枪管被锯短的猎枪躺在吧台下的一层架子上,枪上盖着毛巾。猎枪旁边是一只雪茄盒,里面是一把点三八口径自动手枪。我将两把枪全都拿在了手里。酒保向后退去,抵着吧台后面的那排玻璃酒架。
我转身绕过吧台的一头,穿过房间,来到赌桌后面那扇洞开的房门前。门后是一条走道,呈L型,几乎没有照明。保镖烂泥般地趴在走道的地板上,不省人事,手里握着一把刀。我俯下身,把刀拽了出来,从后楼梯上扔了下去。保镖喘着粗气,他的手软弱无力。
我跨过他的身体,打开了一扇用剥落的黑漆刷着办公室字样的房门。
一张有划痕的小书桌紧挨着一扇用木板封了一半的窗户。一个男人的躯干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椅子的靠背很高,刚好抵着这个男人的后颈。他的脑袋沿着椅子的靠背向后折叠,角度大得刚好让他的鼻子指着那扇钉着木板的窗户1。它就这么折着,像是一块手帕,或是一块装着铰链的板子。
此人右手边的一只书桌抽屉开着。抽屉里面是一张报纸,中间有一片油污。那支枪一定就是从这里来的。这么做在他当时看来似乎是一个好主意,但蒙哥马利先生的脑袋目前所出的位置证明,这是一个馊主意。
桌上有部电话。我把那只锯短的猎枪放下,走过去把门锁上,这才打电话报警。这样让我感觉安全些,而且蒙哥马利先生似乎也不在意。
等到巡逻车里的小子们咚咚咚地奔上楼梯的时候,保镖和酒保都已经不见了,这地方只有我一个人了。
中央大道上有几个种族混杂的街区,这些地方还没有完全被黑人所占据,此处就是其中之一。我刚刚从一家店面大小只有三把椅子的理发店里出来;某家代理行认为一个名叫德米特里阿莱蒂斯的代班理发师就在那里工作。这是笔小生意。他的老婆说,她愿意付一小笔钱,只要能让他回家。
我一直没能找到他,可阿莱蒂斯太太也一直没有付我钱。
那天很暖和,此时已经接近三月底了,我站在理发店外,抬头看着一块伸在外面的霓虹灯广告牌,那属于二楼一家叫弗洛里安的餐厅兼赌场。一个男人也在抬头看着那广告牌。他仰望着那些落满灰尘的窗户,脸上现出一种凝固的狂喜神色,就好像是一个匈牙利移民第一眼看到自由女神像一般。他是个大个子,但身高不超过六英尺五英寸,肩宽也不超过一辆啤酒货车。他离我大概有十英尺远。他的胳膊松弛地垂在身体两侧,一支被遗忘的雪茄在他粗大的手指后面冒着烟。
纤瘦安静的黑人在街上来来往往,不时驻目向他投去匆匆的一瞥。这个男人值得细看。他头戴一顶起毛的博尔萨利诺帽,身着一件粗陋的灰色运动夹克,上面挂着白色的高尔夫球充作纽扣;他的行头还包括一件褐衬衫,一条黄领带,一条打褶的灰色法拉绒便裤和一双短吻鳄皮鞋,脚趾处绽开了白色的大洞。从他的外套贴胸口袋里,一条演出用的手帕钻了出来,垂在外面,颜色是与他的领带一样的亮黄色。他的帽檐上还别着几根五颜六色的羽毛,但这真的已经没有必要了。中央大道绝非这世上衣着最低调的地方,可即便是在这里,他看上去也招摇得像是一只大狼蛛落在了白蛋糕上。
他的肤色苍白,胡子也该刮一刮了。他的这把胡子永远都该刮。他长着蜷曲的黑发,眉毛长得都快碰到那只宽鼻子了。对于这样一个大块头的男人来说,他的耳朵却细小匀称,眼睛中闪着泪珠般的光芒灰眼睛似乎经常给人这种感觉。他的站姿像尊雕像,过了许久,他露出了一丝微笑。
他慢慢地穿过人行道,走到那扇双开式弹簧门跟前,紧闭的门后就是通往二楼的楼梯。他一把把门推开,朝街道的左右两边投去面无表情的冷冷一瞥,然后走了进去。要是他只是个小个子,而且穿得较为低调的话,那我可能会以为他打算持枪抢劫呢。但这样的衣服,这样的帽子,这样的块头绝不可能。
弹簧门向外摆了回来,然后渐渐不动了。可就在它完全停下之前,门又突然间猛地被朝外撞开了。某个东西飞过人行道,落在了阴沟里,刚好掉在两辆停在路边的汽车中间。那东西手膝着地,发出一声尖利的叫声,就像一只被逼进角落的老鼠。它慢慢地爬了起来,找回了一顶帽子,然后跨回到人行道上。那是个瘦骨嶙峋、肩膀窄窄的棕肤年轻人,穿着件淡紫色的套装,上面别着一支康乃馨。它长着一头光溜溜的黑发。它张开嘴,叫唤了一阵子。路人们茫然地盯着它。随后它重新快快活活地戴好帽子,悄无声息地走到墙边上,迈着外八字的步子顺着沿街的一排房屋默默地走开了。
沉寂。人流如旧。我走到那扇双开门边上,站在门前。两片门板现在已经一动不动了。这不关我的事。于是我把门推开,朝里面张望。
黑暗中伸出一只手来,手掌大得可以让我坐在上面。那只手一把抓住我的一只肩膀,几乎把它捏得粉碎。然后这只手把我从门里拖了进来,轻轻松松地将我提上了一级台阶。一张巨大的脸孔正盯着我看。一个低沉的声音对我开了口,语调很平静:
进来抽烟的,是吧?我也是,伙计。
屋里面很暗,很安静。头顶上隐隐传来人声,可楼梯上只有我们两个人。这大个子一脸严肃地盯着我,继续用那只手摧残着我的肩膀。
一个黑人,他说。我刚刚把他扔出去了。你看到我把他扔出去了?
他松开了我的肩膀。骨头好像还没碎,但整只胳膊都麻了。
这本来就是那种地方,我边说边揉着肩膀。你还能指望怎么样?
别这么说,伙计。那大个子轻轻地发出咕噜噜的喉音,就像是四只老虎刚刚用完餐。维尔玛以前在这里工作。小维尔玛。
他再度伸手去抓我的肩膀。我想要躲闪,可他的动作快得就像只猫。他又一次开始用那些钢铁般的手指折磨我的肌肉。
没错,他继续说。小维尔玛。我已经有八年没有见到她了。你说这是家黑人店?
我用低哑的声音说了声是。
他又把我向上提了两级台阶。我奋力地挣脱开来,试图获得一点周旋的空间。我没带枪。寻找德米特里阿莱蒂斯似乎不需要枪。但我怀疑就算有枪也没什么用。这大个子说不定会一把将它从我手里夺走,然后塞进嘴里。
你上楼自己看看吧,我努力不让自己的声音透露出身体所承受的剧痛。
他再次放开了我。他用那双灰眼睛看着我,眼神中流露出某种哀伤。我现在感觉很好,他说。我可不想让什么人来烦我。你跟我一起上楼吧,也许我们可以喝上两杯。
他们不会招待你的。我跟你说了,这是家黑人店。
我已经有八年没见到维尔玛了,他用他那低沉悲伤的嗓音说着。从我说再见起到现在,已经有八年了。她有六年没给我写信了。可她一定有她的理由。她以前在这里工作。她很可爱。你跟我上楼去,咋样?
好,我大声喊道。我跟你走。只是别扛着我。让我自己走。我很健康。我完全是个成年人了。我可以自己上厕所,自己料理一切。只是请你别扛着我。
小维尔玛以前在这里工作,他轻声说着。他根本没听我说话。
我们朝楼上走去。他允许我自己走路。我的肩膀生疼,脖子后面全湿了。
2
又有一扇弹簧门挡在了楼梯顶端,不知紧闭的门后面究竟有什么。大个子用两根拇指轻轻地把门推开,随后我们进了房间。这是一间狭长的屋子,不太干净,不太明亮,也不太欢乐。
角落里,一道光锥下,一群黑人围在一张双骰儿赌桌边唱着歌,聊着天。紧挨着右手边那面墙的是一个吧台。房间里剩余的地方差不多摆满了一张张小圆桌。屋里有几个顾客,男男女女,全都是黑人。
赌桌边的歌声顿时停了下来,桌前的亮光也忽的一下灭了。一阵突然的沉寂,沉重得就像一条进水的船。一双双眼睛望着我们,栗色的眼睛,嵌在一张张肤色从暗灰到深黑的脸孔上。一颗颗脑袋慢慢地转向我们,脑袋上的眼睛在一片属于异族的、怪异的死寂中闪着光,瞪视着。
一个脖颈粗实的黑人正靠在吧台的一端,他的衬衫袖筒上缠着粉色的吊袖带,宽阔的后背上背着粉白两色的吊裤带。此人浑身上下都写着两个字:保镖。他慢慢地把那只抬着的脚放下,然后慢慢地扭头盯着我们,一边把两脚缓缓张开,伸出一条宽大的舌头舔了舔嘴唇。他长着一张几乎报废的脸,看上去好像被人用各种物品轮番砸过一遍,就差掘土机的铲斗了。它曾被人划上疤痕,被砸扁,再碾粗,脸上的口子有的一格一格,有的一条一条。这是一张无需再有恐惧的脸。它已然经受了所有你可以想象得到的摧残。
他的一头短发皱巴巴的,发色中带着一抹灰。一只耳朵缺了耳垂。
这黑人生得肩宽体阔。他两腿粗壮,看上去有一点罗圈,这在黑人当中可不太常见。他又舔了舔嘴唇,露出一个微笑,然后身子动了起来。他以一种放松的、拳击手式的半蹲姿势朝我们走了过来。大个子一言不发地等着他。
这个胳膊上缠着粉色吊袖带的黑人伸出一只巨大的棕色手掌贴在大个子的胸膛前。这手虽大,可这样看起来却显得像根大头针。大个子一动不动。保镖挤出一个温和的微笑。
白人不能进,伙计。这是给有色人种的。对不起。
大个子转动着那双小小的、哀伤的灰眼睛,往房间里四下张望着。他的脸颊微微泛红。臭擦鞋的,他压低了嗓子,愤怒地说了一句。然后他又提高了音量。维尔玛在哪儿?他问那保镖。
保镖没有放肆地大笑。他端详着大个子的衣服他的褐衬衫和黄领带、他粗陋的灰外套,还有上面的白色高尔夫球。他微微地转动着那颗厚实的脑袋,从各个角度审视着这一切。他又低头看了看那双短吻鳄皮鞋,轻轻地笑出声来,像是被逗乐了。我有一点为他感到难过。这时他又轻声地开了口。
维尔玛你说?这里没有维尔玛,伙计。没有婊子,没有马子,什么都没有。这里是饭馆儿,伙计,这里是饭馆儿。
维尔玛以前在这儿工作的,大个子说。他的语调像是在做梦,就好像他正独自一人在树林里采着野紫罗兰。我掏出手帕,又擦了擦脖子后面的汗。
保镖突然放声大笑。没错,他边说边飞快地扭头瞅了一眼身后的人群。维尔玛以前在这儿工作。可维尔玛现在不在这儿工作了。她退休了。呵呵......呵呵。
麻烦把你那只该死的手从我衬衫上拿开,大个子说。
保镖皱了皱眉。他可不习惯听别人这么跟他说话。他把手从衬衫上拿开,握成了拳头,它的大小和颜色都像极了一只巨大的茄子。他得考虑他的饭碗、他好勇斗狠的名声,还有他的公众信誉。这些问题他考虑了一秒钟,然后犯下了一个错误。他又狠又快地挥了一记拳,胳膊肘猛的向外一抽,拳头落在了大个子的下巴一侧。房间里四下传出一阵轻轻的喘气声。
这可是结结实实的一拳。大个子肩膀一垂,身子紧跟着晃了一下。这一拳力道十足,挥出此拳的这个人平时一定没少练过。大个子的脑袋只歪了不到一英寸。他没有试图招架。他承受了这一击,微微抖了抖身子,喉咙里轻轻地哼了一声,然后一把抓住了保镖的喉咙。
保镖想要用膝盖顶他的裆部。大个子让他在半空中转了个身,他那双花里胡哨的鞋一下子在粗糙的油地毡上滑脱了。他把保镖的身体向后一弯,腾出右手去抓他的腰带。那腰带就像绑肉绳一样一下子断了。大个子伸出一只巨大的手掌,直直抵住保镖的脊柱,然后奋力一推。他直接把保镖扔到房间那头去了,这家伙在空中转着圈,左摇右摆,两手乱舞。三个人跳起身来躲开他。保镖翻身倒地时带翻了一张桌子,接着狠狠地砸在了踢脚板上,声音响得你在丹佛都能听得见。他两腿抽搐了一下,然后就躺倒不动了。
有些家伙,大个子开口道,总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该狠。他朝我扭过头来。对了,他说。你跟我喝一杯吧。
我们走到吧台前。那些顾客或单身一身或三三两两,全都成了一言不发的影子,他们无声地从地板上漂过,又无声地从楼梯尽头的那扇门里飘了出去。无声如草地上的黑影。他们甚至都没有让弹簧门摇摆。
我们在吧台上倚着身子。酸威士忌,大个子说。你的自己点。
酸威士忌,我说。
于是我们拿到了酸威士忌。
大个子顺着又厚又矮的玻璃杯壁面无表情地把酸威士忌舔下肚去。他严肃地盯着酒吧招待这是个愁眉苦脸的瘦小黑人,穿着一件白外套,脚痛般地动来动去的。
你知道维尔玛在哪儿吗?
维尔玛,是吗?酒保哼哼唧唧地说。我最近没在这块儿瞅见她。最近没见着,没有,先生。
你来这儿多久了?
让我瞧瞧,酒保放下毛巾,额头上现出一条条皱纹,然后扳起了手指头。大概十个月吧,我猜。大概一年。大概
到底是多久,大个子说。
酒保两眼瞪得像铜铃,喉结上上下下地扑腾着,像只没头的母鸡。
你们这笼子变成黑人夜店有多久啦?大个子粗声盘问道。
谁说是?
大个子的的手捏成了拳头,手中那只装着酸威士忌的玻璃杯几乎顿时消失在了无形之中。
五年吧,我说。至于这个叫维尔玛的白人姑娘,这家伙肯定什么也不知道。这里没人知道。
大个子看我的眼神就好像我刚刚从蛋里孵出来一样。那杯酸威士忌好像没有让他高兴起来。
混蛋,谁让你来插一脚的?他问我。
我挤出一个微笑,一个大大的、温暖的、友好的微笑。我就是那个跟你一起进来的家伙。想起来了吗?
他咧嘴回了我一个笑容,一个干巴巴的笑,只见白牙,没有意义。酸威士忌,他吩咐酒保。把你裤裆里的跳蚤抖干净。上快点儿。
酒保迈着小碎步子跑前跑后,骨碌碌地翻着白眼。我背靠吧台,抬眼看着房间。屋里现在空了,只剩下了酒保、大个子和我自己,当然还有那个一头撞在墙上的保镖。那保镖开始动弹了。他慢慢地挪着身子,像是忍着剧痛、十分吃力的样子。他沿着踢脚板不声不响地爬着,像缺了一只翅膀的苍蝇。他挪到了桌子后头,精疲力竭的样子就像一个人突然之间苍老了、幻灭了。我看着他挪动身子。酒保这时又拿来了两杯酸威士忌。我朝吧台转过身子。大个子漫不经心地瞥了一眼那个在地上爬行的保镖,然后就不再留意他了。
这夜店里现在什么都没有留下了,他抱怨道。以前这儿有一个小舞台,有乐队,还有一个个漂亮的小房间,男人可以进去找些乐子。维尔玛在这儿唱过歌。她是个红头发。媚得就像蕾丝内裤。我们那时都要结婚了,结果他们陷害了我。
我喝下了第二杯酸威士忌。这场冒险已经快让我受够了。怎么陷害的?我问道。
你以为我这八年都上哪儿去了?
捉蝴蝶。
他用一根粗得像香蕉的食指戳着自己的胸膛。蹲在牢里呐。我叫马洛伊。他们叫我驼鹿马洛伊,因为我个儿大。大本德银行劫案。四万大洋。我一个人干的。厉不厉害?
你现在打算把钱花掉对吧?
他狠狠瞪了我一眼。这时我们身后传来一阵声响。那保镖站起身来了,左摇右晃地走了几步,伸手握住赌桌后面一扇黑门的把手。他打开门,几乎是摔进去的。门哐的一声关上了,然后咔哒一声上了锁。
那是什么地方?驼鹿马洛伊厉声问道。
酒保的眼珠在脑壳里飘忽不定,然后才费力地定睛望着那扇门,保镖刚刚跌跌撞撞地从那里钻了进去。
那那是蒙哥马利先生的办公室,先生。他是老板。他的办公室就在那后面。
他说不定知道,大个子说。他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他最好不要也跟我说笑话。已经碰着两个这样的人了。
他慢悠悠地穿过房间,步履轻快,心中没有一丝顾虑。他巨人般的后背遮住了那扇门。门锁着。他拉住门摇了摇,一块门板飞到了一边。他走了进去,门在他身后关上了。
一阵沉默。我看着酒保。酒保看着我。他的眼神若有所思。他擦了擦柜台,叹了口气,右臂撑在台面上趴了下来。
我伸手越过柜台,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这只胳膊又瘦又脆。我捏着它,对他微笑。
你那底下藏着什么东西,伙计?
他舔了舔嘴唇,抵着我的胳膊,一言不发。一抹灰色爬上了他那张发亮的脸膛。
这是个狠角儿,我说。而且他很容易发飙。他喝了酒就这样。他正在找一个他以前认识的姑娘。这地方以前是家白人店。懂了没有?
酒保舔了舔嘴唇。
他离开这里好久了,我接着说。八年了。他好像没有意识到八年究竟有多久,但我估计在他看来那就是一辈子。他觉得这儿的人应该知道他的姑娘在哪里。懂了没有?
酒保慢吞吞地说:我以为你跟他是一伙儿的。
我身不由己啊。他在楼下问了我一个问题,然后就把我拖上来了。我以前从没有见过他。但我可不想让人给扔到房子的那头去。你那底下藏着什么?
我弄了一把锯短的猎枪,酒保说。
啧啧,那是违法的,我低声说。听着,你跟我是一伙儿的。还有别的吗?
我还弄了一把左轮,酒保说。在雪茄盒里。放开我的胳膊。
很好,我说。你可以走开了。悠着点儿,侧着身走。现在不是开大炮的时候。
你算老几,酒保冷笑着,用他疲倦的身体顶着我的胳膊。你算
他突然打住了。他的眼珠在滴溜溜得转。他的脑袋猛地一抖。
屋后传来一声直直的闷响,声音就来自赌桌旁边那扇紧闭的门后面。也许那只是摔门的声音。但我觉得不像。酒保也觉得不像。
他此刻呆若木鸡,嘴角流着口水。我竖起耳朵听着。再没有别的动静了。于是我猛地朝柜台的那头扑去。我已经听得太久了。
屋后的那扇门砰地一声开了,驼鹿马洛伊一个箭步冲出门来,动作流畅又凶猛,接着又突然刹住了,双脚就像在地上生了根一样,脸上浮现出一个咧开大嘴的苍白笑容。
一支柯尔特点四五手枪攥在他手里,就像把玩具枪。
谁都不许摸裤子,他懒洋洋地说。把手老老实实地放在吧台上。
酒保和我都把手放了下来。
驼鹿马洛伊迅速地将房间扫视了一遍。他那紧绷的笑容就像是钉在脸上似的。他移动脚步,无声地穿过房间。他看上去确实像是能单枪匹马抢劫银行哪怕是穿成这样。
马洛伊走到了吧台前。站起来,黑鬼,他轻声说。酒保把两手高高地举在半空中。大个子走到我背后,仔仔细细地用左手把我身上摸了个遍。他火辣辣的气息喷在我的脖子上然后挪开了。
蒙哥马利先生也不知道维尔玛在哪儿,他说。他想要用这个告诉我。他用结实的大手拍着那支枪。我慢慢地转过身来看着他。没错,他说,你会了解我的。你不会忘了我的,伙计。我只要你告诉那些小子们:不要乱来。他扭了扭枪。好啦,拜拜了,你们两个小阿飞。我得去赶电车了。
他开始朝楼梯的顶端走去。
你还没付酒钱呢,我说。
他停住了,认认真真地看着我。
也许你那里有两个钱,他说,但我不想捏得太狠了。
他继续往前走,穿过了那扇弹簧门,随后远传来了他走下楼梯的脚步声。
酒保俯下身子。我一跃而起,绕到了柜台的后面,一把将他挤开。一支枪管被锯短的猎枪躺在吧台下的一层架子上,枪上盖着毛巾。猎枪旁边是一只雪茄盒,里面是一把点三八口径自动手枪。我将两把枪全都拿在了手里。酒保向后退去,抵着吧台后面的那排玻璃酒架。
我转身绕过吧台的一头,穿过房间,来到赌桌后面那扇洞开的房门前。门后是一条走道,呈L型,几乎没有照明。保镖烂泥般地趴在走道的地板上,不省人事,手里握着一把刀。我俯下身,把刀拽了出来,从后楼梯上扔了下去。保镖喘着粗气,他的手软弱无力。
我跨过他的身体,打开了一扇用剥落的黑漆刷着办公室字样的房门。
一张有划痕的小书桌紧挨着一扇用木板封了一半的窗户。一个男人的躯干直挺挺地坐在椅子上。椅子的靠背很高,刚好抵着这个男人的后颈。他的脑袋沿着椅子的靠背向后折叠,角度大得刚好让他的鼻子指着那扇钉着木板的窗户1。它就这么折着,像是一块手帕,或是一块装着铰链的板子。
此人右手边的一只书桌抽屉开着。抽屉里面是一张报纸,中间有一片油污。那支枪一定就是从这里来的。这么做在他当时看来似乎是一个好主意,但蒙哥马利先生的脑袋目前所出的位置证明,这是一个馊主意。
桌上有部电话。我把那只锯短的猎枪放下,走过去把门锁上,这才打电话报警。这样让我感觉安全些,而且蒙哥马利先生似乎也不在意。
等到巡逻车里的小子们咚咚咚地奔上楼梯的时候,保镖和酒保都已经不见了,这地方只有我一个人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