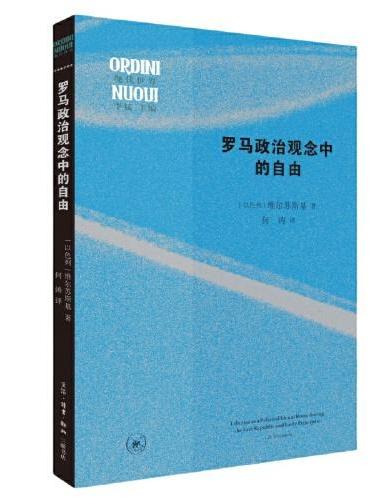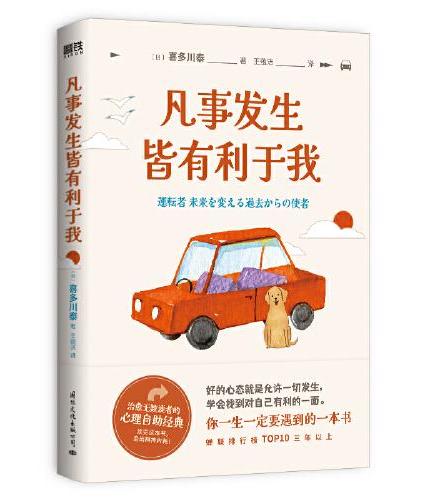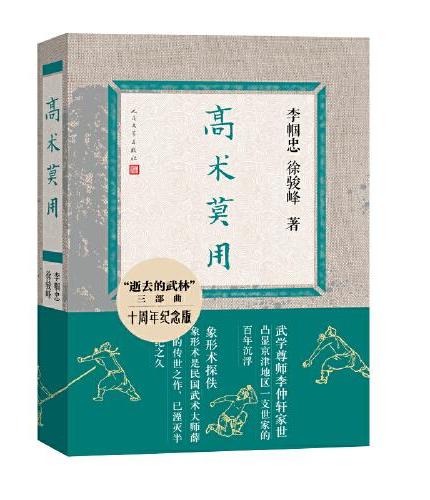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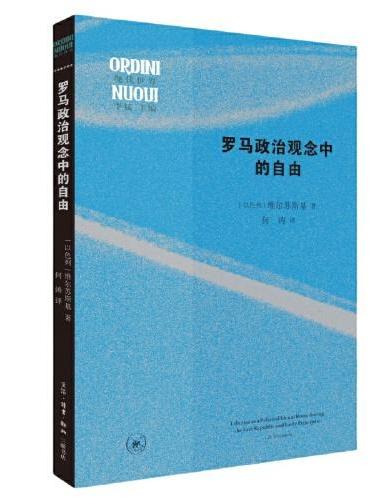
《
罗马政治观念中的自由
》
售價:HK$
50.4

《
中国王朝内争实录:宠位厮杀
》
售價:HK$
6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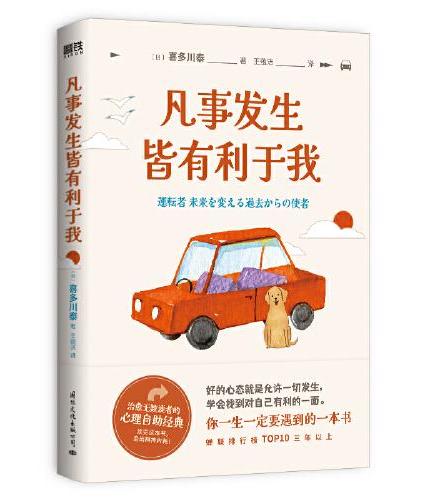
《
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这是一本读了之后会让人运气变好的书”治愈无数读者的心理自助经典)
》
售價:HK$
44.6

《
未来特工局
》
售價:HK$
5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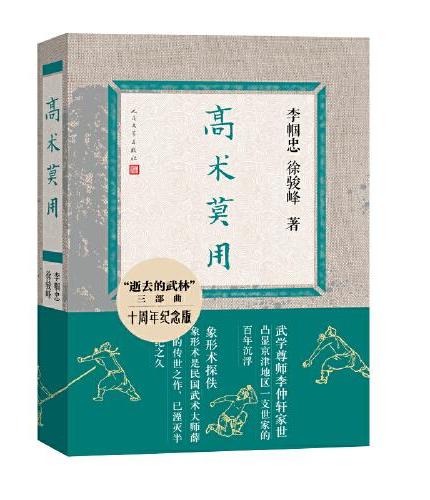
《
高术莫用(十周年纪念版 逝去的武林续篇 薛颠传世之作 武学尊师李仲轩家世 凸显京津地区一支世家的百年沉浮)
》
售價:HK$
54.9

《
英国简史(刘金源教授作品)
》
售價:HK$
98.6

《
便宜货:廉价商品与美国消费社会的形成
》
售價:HK$
77.3

《
读书是一辈子的事(2024年新版)
》
售價:HK$
77.3
|
| 內容簡介: |
吕留良(16291683)是清初著名的理学家、出版家、诗人。字庄生,又字用晦,号晚村,别号耻斋老人、南阳布衣,浙江省崇德县(今桐乡市)人。一生从事朱子理学的研究与传播,然与当时其他讲理学者不同,不以语录、讲章行世,而以时文评选著称。
明清之际推尊朱学的学者极多,吕留良认为只有朱子之学才是孔孟正学,不合朱子者都是异学,都需要辟之,除了王学,还有佛学,以及陈亮之类的事功之学。吕氏的理学思想与学术观点,大都保存在其文集(书信、序跋等)与时文评点中。其时文评语,后经其弟子汇辑成《四书讲义》出版;而文集后虽有刻本,但也大都不全。作为易代之际的理学家,吕氏多关注出处、辞受、君臣、朋友之道,重节义、反功利,此即朱子理学之精髓,更是孔孟儒家之真谛,戴名世《九科大题文序》说:吾读吕氏之书,而叹其维挽风气,力砥狂澜,其功有不可没也。而二十馀年以来,家诵程朱之书,人知伪体之辨,实自吕氏倡之。 可见吕氏著作之风行海内,且起到了推尊朱学,维挽士风的作用。所以说,吕留良的著作,对清初朱子学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乾隆一朝,曾将吕留良的著作全面禁毁,以致流传极稀。所以对吕留良著作的整理,就显得极为重要。不仅有助于推动吕留良研究的全面深入展开,对清初理学的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都极有裨益。吕留良(16291683)是清初著名的理学家、出版家、诗人。字庄生,又字用晦,号晚村,别号耻斋老人、南阳布衣,浙江省崇德县(今桐乡市)人。一生从事朱子理学的研究与传播,然与当时其他讲理学者不同,不以语录、讲章行世,而以时文评选著称。
明清之际推尊朱学的学者极多,吕留良认为只有朱子之学才是孔孟正学,不合朱子者都是异学,都需要辟之,除了王学,还有佛学,以及陈亮之类的事功之学。吕氏的理学思想与学术观点,大都保存在其文集(书信、序跋等)与时文评点中。其时文评语,后经其弟子汇辑成《四书讲义》出版;而文集后虽有刻本,但也大都不全。作为易代之际的理学家,吕氏多关注出处、辞受、君臣、朋友之道,重节义、反功利,此即朱子理学之精髓,更是孔孟儒家之真谛,戴名世《九科大题文序》说:吾读吕氏之书,而叹其维挽风气,力砥狂澜,其功有不可没也。而二十馀年以来,家诵程朱之书,人知伪体之辨,实自吕氏倡之。 可见吕氏著作之风行海内,且起到了推尊朱学,维挽士风的作用。所以说,吕留良的著作,对清初朱子学的提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由于乾隆一朝,曾将吕留良的著作全面禁毁,以致流传极稀。所以对吕留良著作的整理,就显得极为重要。不仅有助于推动吕留良研究的全面深入展开,对清初理学的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的研究都极有裨益。
本次整理,以康熙二十五年吕氏天盖楼刻本为底本进行点校,并将讲义内容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逐条对应,不仅有助于阅读,而且也便于对比考察吕留良朱学诠释的成就。
|
| 關於作者: |
吕留良(1629-1683),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思想家、诗人和时文评论家、出版家。又名光轮,一作光纶,字庄生,一字用晦,号晚村,别号耻翁、南阳布衣、吕医山人等,暮年为僧,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浙江崇德县(今浙江省桐乡市崇福镇)人。顺治十年应试为诸生,后隐居不出。康熙间拒应满清的鸿博之征,后削发为僧。死后,雍正十年被剖棺戮尸,子孙及门人等或戮尸,或斩首,或流徙为奴,罹难之酷烈,为清代文字狱之首。吕留良著述多毁,今有俞国林汇集为《吕留良全集》十册行世。
俞国林,浙江省桐乡市大麻镇人。2001年7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为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主任。曾主持国家新闻广电出版总局指导的《学术著作出版规范》之古籍整理出版规范的制定,成为新闻出版的行业标准(CYT 124-2015)。先后荣获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十佳编辑、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青年岗位能手,首届北洋传媒中国好编辑学术类第二名,《新京报》2015年度致敬编辑等称号。《光明日报》2016年2月23日第9版以《如何做一位学者型编辑》为题,做专题报道。编撰有《天盖遗民:吕留良传》、《吕留良诗笺释》(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吕留良全集》(大清史文献丛刊项目)、《顾颉刚旧藏签名本图录》等。
|
| 目錄:
|
序 一
整理凡例 二一
弁言 一
四书讲义卷一 大学一
经一章 一
四书讲义卷二 大学二
传首章至传七章
四书讲义卷三 大学三
传八章至传十章
四书讲义卷四 论语一
学而篇 凡十六章
四书讲义卷五 论语二
为政篇 凡二十四章
四书讲义卷六 论语三
八佾篇 凡二十六章
四书讲义卷七 论语四
里仁篇 凡二十六章
四书讲义卷八 论语五
公冶篇 凡二十七章
四书讲义卷九 论语六
雍也篇 凡二十八章
四书讲义卷十 论语七
述而篇 凡三十七章
四书讲义卷十一 论语八
泰伯篇 凡二十一章
四书讲义卷十二 论语九
子罕篇 凡三十章
四书讲义卷十三 论语十
乡党篇 凡十七节
四书讲义卷十四 论语十一
先进篇 凡二十五章
四书讲义卷十五 论语十二
颜渊篇 凡二十四章
四书讲义卷十六 论语十三
子路篇 凡三十章
四书讲义卷十七 论语十四
宪问篇 凡四十七章
四书讲义卷十八 论语十五
卫灵公篇 凡四十一章
四书讲义卷十九 论语十六
季氏篇 凡十四章
四书讲义卷二十 论语十七
阳货篇 凡二十六章
四书讲义卷二十一 论语十八
微子篇 凡十一章
四书讲义卷二十二 论语十九
子张篇 凡二十五章
四书讲义卷二十三 论语二十
尧曰篇 凡三章
四书讲义卷二十四 中庸一
第一章至第十一章
四书讲义卷二十五 中庸二
第十二章至第十六章
四书讲义卷二十六 中庸三
第十七章至第十九章
四书讲义卷二十七 中庸四
第二十章
四书讲义卷二十八 中庸五
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六章
四书讲义卷二十九 中庸六
第二十七章至第三十三章
四书讲义卷三十 孟子一
梁惠王上 凡七章
四书讲义卷三十一 孟子二
梁惠王下 凡十六章
四书讲义卷三十二 孟子三
公孙丑上 凡九章
四书讲义卷三十三 孟子四
公孙丑下 凡十四章
四书讲义卷三十四 孟子五
滕文公上 凡五章
四书讲义卷三十五 孟子六
滕文公下 凡十章
四书讲义卷三十六 孟子七
离娄上 凡二十八章
四书讲义卷三十七 孟子八
离娄下 凡三十三章
四书讲义卷三十八 孟子九
万章上 凡九章
四书讲义卷三十九 孟子十
万章下 凡九章
四书讲义卷四十 孟子十一
告子上 凡二十章
四书讲义卷四十一 孟子十二
告子下 凡十六章
四书讲义卷四十二 孟子十三
尽心上 凡四十六章
四书讲义卷四十三 孟子十四
尽心下 凡三十八章
附録一
附録二
|
| 內容試閱:
|
四书讲义序
张天杰
吕留良(16291683)字庄生,又名光轮,字用晦,号晚村,别号耻斋老人、南阳布衣,暮年为僧,名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浙江崇德县(康熙元年改名石门县,今属桐乡市崇福镇)人。吕留良是明末清初著名的诗人,同时又是著名的理学家、时文评选家、刊行程朱遗书著称的出版家,后三者则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其相关成果之一便是《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以下简称《四书讲义》)。此外,吕留良还着有《何求老人残稿》、《吕晚村先生文集》等,今有俞国林兄汇编为《吕留良全集》十册。
一
吕留良的本生祖吕熯,明嘉靖时的江西淮府仪宾、尚南城郡主,后为侍养父母而与郡主一同回籍。本生父吕元学,万历二十八年(1600)举人,后谒选为繁昌知县,兴利除弊,有循吏之称。吕元学育有五子:大良、茂良、愿良、瞿良和留良。其中吕茂良,官刑部郎;吕愿良,官维扬司李。吕元学卒后四月,侧室杨孺人生下吕留良。吕留良诞生之后,其母无力照料,便将他交给三兄愿良夫妇抚育。吕留良三岁时,三嫂又病故,又过继给堂伯父吕元启。不久之后嗣父、嗣母,以及本生母相继过世,故而吕留良的少年时代几乎都是在不间断的服丧之中度过的,不可不谓孤苦凄凉。当时的吕家,还是一个深受明朝恩泽的官宦世家、文化世家,故而少年失怙的吕留良,还是得以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并表现得聪慧超群。
吕留良十六岁时,明亡清兴,不得不面临艰难的出处抉择。起先,吕留良散金结客、毁家纾难,曾与其友孙爽、侄吕宣忠等人参与过太湖义军的抗清斗争,失败之后吕宣忠被杀,吕留良于悲痛之中逃逸他乡。后来,因为害怕仇家陷害,羽翼未丰的吕留良于顺治十年被迫易名应试为诸生。其子吕葆中在《行略》中说:癸巳始出就试,为邑诸生,每试辄冠军,声誉籍甚。由此可知吕留良虽不汲汲于功名,却在举业上有着非凡的才能,而后从事时文评选而成名也就不足为怪了。直到康熙五年方才决意摒弃科考,被革去秀才,这在当时也是惊人之举,吕葆中《行略》说:一郡大骇,亲知莫不奔问旁皇。此时写有著名的《耦耕诗》表达其隐居不出、终老乡野的志向,其一曰:
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雅集图中衣帽改,党人碑里姓名非。苟全始信谈何易,饿死今知事最微。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
然而清廷却并未轻易放过吕留良,康熙十七年(1678)有博学鸿儒之征,浙江当局首荐吕留良,他誓死拒荐;康熙十九年又有山林隐逸之征,吕留良闻知消息当即吐血满地,无奈只得在病榻之上削去头发,披上袈裟,后隐居于吴兴妙山的风雨庵。
即便如此,生前在节义之间的挣扎结束了,死后却依旧难以免除是非。雍正十年,受到曾静案的牵连,吕留良被剖棺戮尸,甚至连累子孙以及门人,或被戮尸,或被斩首,或被流徙为奴,罹难之惨烈,可谓清代文字狱之首。
以上之所以稍稍详述吕留良生平,是因为其遗民心态之曲折,与其学术思想之发展息息相关。
二
吕留良一生从事朱学,然与当时其他讲理学者不同,不以语录、讲章行世,而以时文评选著称,《四书讲义》便是其时文评选之中发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相关义理的精华。
时文,也即八股文、四书文,又称经义、制义、时艺等。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第一场,就是以八股文的形式考试学子,且以《四书》中的句子命题,故而对于《四书》以及朱学是否有着正确的理解,也是科举成败的关键。当然,这样的评判标准,是建立在学风、士风端正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生逢明清之际的乱世,学风、士风皆难免乖戾,这在结社、选文上表现尤其突出。吕留良在《东皋遗选序》中说:
自万历中,卿大夫以门户声气为事,天下化之。士争为社,而以复社为东林之宗子,咸以其社属焉。自江淮讫于浙,一大渊薮也。凡社必选刻文字,以为囮媒。自周钟、张溥、吴应箕、杨廷枢、钱禧、周立勋、陈子龙、徐孚远之属,皆以选文行天下。选与社,例相为表里。
当时的复社、应社、几社,以及吕留良之兄吕愿良集合浙省十余郡文士所举的澄社,吕留良之友孙爽、侄吕宣忠所举的征书社,也都有选文之举。而举征书社之时,年仅十三岁的吕留良就有参与。
吕留良两度从事时文评选,并成为与艾南英、陈子龙等齐名的时文名家。其前期的时文评选时间较短,顺治十二年至十八年,应陆文霦之邀而开始时文评选,主要由于出处节义而内心苦闷彷徨,故藉以填补其心;康熙五年被革去秀才之后,再度从事时文评选,直到康熙十二年,一方面是因为放弃诸生后治生之需要,如在《与董方白书》中就说选文行世,非仆本怀,缘年来多费,按此粗给,遂不能遽已。另一方面是因为寄托议论、讲明义理之需要,《与施愚山书》说:某跧伏荒塍,日趋弇固,偶于时艺,寄发狂言,如病者之呻吟,亦其痛痒中自出之声,而赏音者以为有当于歌讴。吕留良便在家中开设了天盖楼书局,自己刊刻发行所评选的时文选本,摆脱了书商约定评选时限、篇幅等约束,不只是收入的增加,而是真正实现改革时文,并藉此弘扬朱子理学了。
关于吕留良为什么致力于时文评选,还需要说明三点。其一,吕留良对于晚明士人的结社、选文之风并不满意,认为是以门户声气为事,在《东皋遗选序》中就说:于是郡邑必有数社,每社又必有异同,细如丝发之不可理。磨牙吮血,至使兄弟姻戚不复相顾。士风之坏,除了结社还有评选时文,吕留良在《答赵湛卿书》中说:盖选手二字,某所深耻而痛恨者,不幸其行迹如之。尝谓近世人品文章,皆为选手所坏。他本人亲自从事选业十多年,故深知其中的弊病,确实当时选手多有龌龊肺肠,以至于坏了人品文章,吕留良之所以以选手为耻而又坚持评选,就是为了矫正不良之风。
其二,吕留良对八股取士并不认同,但也不认为问题出在八股上。他在《戊戌房书序》中说:自科目以八股取士,而人不知所读何书。探其数卷枕秘之籍,不过一科贵人之业。科举考试以八股文的考试为重,导致许多考生的枕边秘籍只有时文评选的册子了。不过究其病根,却并不在八股取士上头。吕留良接着说:然以为科目之弊专由八股,则又不然。夫科目之弊,由其安于庸腐,而侥幸苟且之心生。文气日漓,人才日替,陈陈相因,无所救止。应该说他看得还是很准的,科举的弊病根源在于人心,也就是侥幸苟且之心,再养成庸腐之习,故愚以为欲兴科目,必重革庸腐之习而后可。吕留良之所以投入于时文十多年,就是希望用好的时文,来驱逐恶的时文。事实上,时文也有好文字,比如吕留良曾将自己所作时文汇集为《惭书》,为此书作序的黄周星说:若如用晦所作,雄奇瑰丽,诡势瑰声,拔地倚天,云垂海立。读者以为诗赋可,以为制策可,以为经史子集诸大家皆无不可。何物帖括,有此奇观,真咄咄怪事哉!使世间习此技者皆如用晦,则八股何必不日星丽而岳渎尊也?因此,吕留良以时文名家的身份来做时文评选,也就能顺理成章了。
其三,吕留良更为在意的是,通过讲章、时文反对俗学、异学。什么是俗学、异学?吕留良《四书讲义》卷一说:除却俗学、异学,即是大学之道。俗学者,今之讲章、时文也;异学者,今之阳儒阴释以讲学者是也。也就是说当时广泛流传的时文、讲章都是俗学,主要由村师所授;晚明以来的讲学先生多半受到阳明心学的影响,将佛、道等异学杂入儒学之中,他们所讲都是异学。对此问题,吕留良还在《答叶静远书》中有说明:病在小时上学,即为村师所误。授以鄙悖之讲章,则以为章句传注之说不过如此;导以猥陋之时文,则以为发挥理解与文字法度之妙不过如此。凡所为先儒之精义与古人之实学,初未有知,亦未尝下火煅水磨之功。俗学与异学导致士人以为章句、传注之说不过如此,以为发挥理解与文字法度之妙不过如此,因此不对先儒之精义与古人之实学下火煅水磨之功,还自以为已有所,结果就是离正道越来越远了。所以,吕留良要用时文评选来重新讲明章句、传注,讲明先儒之精义与古人之实学,以及八股文的文字法度,把被俗学、异学搞得乌烟瘴气的讲章、时文风气端正过来。
此外,还需要再补充一点,端正士人之心也只有时文最为有效。吴尔尧《天盖楼大题偶评序》中曾引吕留良的话:读书未必能穷理,然而望穷理必于读书也。秀才未必能读书,然而望读书必于秀才也。识字未必能秀才,然而望秀才必于识字也。舍此识字秀才读书者而安望耶?在吕留良看来,直接针对士人,也即识字秀才,改变士风、学风的唯一办法就是通过人人都离不了的时文,以最为优秀的评选来作引导,从而端正人心,维挽世道。吕留良以时文反时文,因而着成一系列著名的时文选本,以及后人汇编的《四书讲义》等书,整整影响了有清一代。诚如对吕留良评述最为全面而实在的钱穆先生在《吕晚村学述》中所说:在彼之意,实欲拔赵帜,立汉帜,借讲章之途径,正儒学之趋向。
对于时文,吕留良也有矛盾的心态,在《与吴玉章第二书》中说:取圣贤之书,虚心玩味,先通其文义而渐求其理之所归,不必作时文。有所见,即作古文论说亦得,或作讲义、或作书牍亦得。他认为读书有得,与其写八股时文,不如写古文或讲义、书牍,也就是说作时文不见得真有必要了。
三
吕留良时文评选的著作主要有《天盖楼偶评》、《天盖楼制艺合刻》、《十二科小题观略》、《十二科程墨观略》、《唐荆川先生传稿》、《归振川先生全稿》、《陈大樽先生全稿》、《钱吉士先生全稿》、《黄陶庵先生全稿》、《黄葵阳先生全稿》、《江西五家稿》、《质亡集》等。后来则有吕留良的弟子,将这些时文选本之中的吕氏评语摘出,并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顺序加以重新组合,重要的版本有以下三种:周在延编《天盖楼四书语录》四十六卷,清康熙二十三年金陵玉堂刻本;陈鏦编《吕晚村先生四书讲义》四十三卷,清康熙二十五年天盖楼刻本;车鼎丰编《吕子评语》正编四十二卷附严鸿逵记《亲炙录》八十九条《吕子评语余编》八卷附《亲炙录》六条,清康熙五十五年顾麟趾刻本。上述三书,体例大略相当,编次最全则为《吕子评语》,其正编发明书义,内容与语录、讲义大致相当,其余编论文章作法,为此书独有,然此书最晚出,而十二年后曾吕文案发,车鼎丰兄弟以刊刻逆书与严鸿逵等往来获罪拟斩,故此书流传最少。因此,在康熙后期以及雍正初年,流传最广则是《四书讲义》,故而后世学者研究吕留良对《四书》的诠释,对于孔孟以及程朱等义理的阐发,特别是其朱学思想的主旨,还是通过《四书讲义》一书。下面就以此书为主,并辅之文集,来探讨一下吕留良的《四书》诠释以及朱学思想。
关于吕留良是否笃信朱学,学界多有不同说法,其中影响颇大的则是全祖望在《小山堂祁氏遗书记》之中的说法:初南雷黄公讲学于石门,其时用晦父子俱北面执经。已而以三千金求购澹生堂书,南雷亦以束修之入参与。交乃既毕,用晦之使者,中途窃南雷所取卫湜《礼记集说》、王偁《东都事略》以去,则用晦所授意也。南雷大怒,絶其通门之籍,用晦亦遂反而操戈,而妄自托于建安之徒,力攻新建。全祖望的说法影响极大,比如章太炎《书吕用晦事》就说吕氏之学本非朱学,以太冲主王学,欲借朱学与竞。且不说吕留良是否有与黄宗羲竞争之意,但看其学术发展脉络,即可知其于朱学必然自幼精通。如其在《复王山史书》中说:某荒村腐子也,平生无所师承,惟幼读经书,即笃信朱子细注,因朱子之注,而信程张诸儒,因朱子程张而信孔孟。吕留良自幼熟读朱子《四书章句集注》,并认为由朱子可至二程、张载,再至孔子、孟子,也就是说笃信朱学为儒门正宗。再者,吕留良少年时代就钻研时文,而时文成败在于是否对《四书》之精义、实学有所精通,故由此亦可知其必然笃信朱学。康熙初年,也就是黄宗羲到吕家处馆之时,吕留良在《与张履祥》的信中说平生言距阳明,却正坐阳明之病,也就是说与当时的大多士人一样,他也受过王学影响,但并不能说放弃了朱学的立场,也正因为有点朱、王调和之心态才会与黄宗羲交往,然在康熙五年之后则渐渐放弃调和,转而推尊朱学,故而与早就转向朱学的张履祥多方联系。康熙八年,张履祥到吕家处馆之后,吕留良的朱学自然也就更为精进了。
明清之际推尊朱学的学者极多,而吕留良并非简单的尊朱辟王,其本意并不在王学,而只在于朱学。吕留良《答吴晴岩书》说:凡天下辨理道、阐絶学,而有一不合朱子者,则不惜辞而辟之者,盖不独一王学也,王学其尤著者尔。吕留良认为只有朱子之学才是孔孟正学,不合朱子者都是异学,都需要辟之,除了王学,还有佛学,还有陈亮之类的事功之学,如《四书讲义》卷十六说:学术义利之分不可不辨,亦即朱子与龙川力辟之旨也。吕留良认为,儒门正学唯由朱学而上,方可讲求。最为完整的一段论述在《复高汇旃书》中:
金溪之谬,得朱子之辞辟,是非已定,特后人未之读而思耳。若姚江良知之言,窃佛氏机锋作用之绪余,乘吾道无人,任其惑乱;夷考其生平,恣肆阴谲,不可究诘,比之子静之八字着脚,又不可同年而语矣。而所谓朱子之徒,如仲平、幼清,辱身枉己,而犹哆然以道自任,天下不以为非。此道不明,使德祐以迄洪武,其间诸儒失足不少。故姚江之罪,烈于金溪,而紫阳之学,自吴、许以下已失其传,不足为法。今日辟邪,当先正姚江之非,而欲正姚江之非,当真得紫阳之是。《论语》富与贵章,先儒谓必先取舍明而后存养密。今示学者,似当从出处去就、辞受交接处,画定界限,札定脚跟,而后讲致知、主敬工夫,乃足破良知之黠术,穷陆派之狐禅。盖缘德祐以后,天地一变,亘古所未经,先儒不曾讲究到此,时中之义,别须严辨,方好下手入德耳。
吕留良指出,宋代陆九渊(金溪)流于佛禅而非儒门正学,经过朱子的严词辟陆,是非得以分辨,到了晚明时代的王阳明(姚江)则更流于佛禅,且多权诈,故而危害比陆九渊更甚。所以要辟邪,当纠正王学之非;而要纠正王学之非,则又要先得朱学之是。吕留良还指出,自从宋末德祐年间以来,诸如元代的许衡(平仲)、吴澄(幼清)等人,也是徒有尊朱之名,未得朱学之真,因为他们在元代的异族统治之下辱身枉己;而朱学之真则是必先取舍明而后存养密,也就是当从出处去就、辞受交接处,画定界限,札定脚跟,而后讲致知、主敬工夫。在吕留良看来,这一道理朱子等先儒也未曾十分讲究,因为他们未曾经历类似德祐以后那种天地亘古未有的变化,而吕留良本人则经历明清鼎革的变化,对于出处之中的节义有着更为深刻的认识。
在《四书讲义》之中,也多有阐发先讲明出处、辞受而后方可讲明致知、主敬的观念,这方才是吕留良朱学的根本所在。他所认为的朱学的真精神,就在立身行己之道,也即重节义、反功利。钱穆先生的《吕晚村学述》也说:讲理学正当从出处去就、辞受交接处画定界限,札定脚跟,而岂理气心性之空言,所能辨诚伪、判是非?此一主张,乃畅发于其《四书讲义》中。亦可谓当晚村之世,惟如晚村,乃始得为善述朱学也。《四书讲义》卷三十五说:
近来多讲朱子之学,于立身行己,未必得朱子之真。其忧有甚焉者,开堂说法,未开口时,先已不是,又何论其讲义、语录哉!故今日学人,当于立身行己上,定个根脚。
卷三十八则说:
圣贤于出处去就、辞受取予上,不肯苟且通融一分,不是他不识权变,只为经天纬地事业,都在这些子上做,毫厘差不得耳。
能够做到大圣大贤的人,都是在出处、辞受上必有坚持,经天纬地事业也都从细微小事上做起,所以立身行己,毫厘差不得。《四书讲义》卷七中也说:
人必取舍明而后可以言存养。吾见讲学宗师,谈心论性,诃诋古人。至其趋膻营利,丧身失脚,有不可对妻子者,吾不知其所讲者何事也。
吕留良讲《四书》、讲朱学,其出发点都是节义之道,所以认为将心性说得高妙没有益处,更何况空谈心性而自身节义无一可取,或趋于功利而丧身失脚。吕留良并不是说谈心说性,以及讲求存养工夫本身有误,而是说学问也有一个先后之分,也即节义最为重要,先讲求立身行己的工夫,然后才是存养工夫;也只有先讲明立身行己,方才能够不趋附于功利以至丧身失脚。
再看吕留良所论夷夏之防,其实也就是从节义之道出发的,指出必须讲明节义,反对功利。《四书讲义》卷十七子贡曰管仲章说:
圣人此章,义旨甚大。君臣之义,域中第一事,人伦之至大。若此节一失,虽有勋业作为,无足以赎其罪者。若谓能救时成功,即可不论君臣之节,则是计功谋利,可不必正谊明道。开此方便法门,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谁不以救时成功为言者,将万世君臣之祸,自圣人此章始矣。看微管仲句,一部《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为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论节义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
前人对此章关注极多,唯有钱穆先生强调吕留良讲《春秋》大义为域中第一事者,其立足点是在节义,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盖夷夏之防,定于节义,而摇于功名。人惟功名之是见,则夷夏之防终隳。人惟节义之是守,而夷夏之防可立。钱穆先生的诠释当是符合吕氏原意的。在吕留良看来,夷夏之防固然当守,此本不必多言,然而需要讲明的则是如何守其防,唯有先明节义而已;至于夷夏之防与君臣之义的选择,也就在于节义的大小,而不在于功名的大小。吕留良还说:若将尊王另分在僭窃上说,此功不足赎忘君雠之义也。圣人论管仲,只许其功,并未尝有一言及于纠、白之是非也。此处也是吕氏不同于朱子之处,朱子还在辨析公子纠与小白谁大谁小以及君雠之义,而吕留良则指出,不必论及公子纠、小白的是非,更不必论及功名,只要讲明管仲所作所为的节义之大小。至于朱子等先儒为什么在此问题上会有纠结,吕留良关于此章的评语原本还说:要之,此一段道理,先儒不曾经历讲究,固难晓然耳!此段保留在《吕子评语》卷十七,而《四书讲义》则没有收录,然而却可从此看出吕留良对于《春秋》大义的思考,也是与其经历明清鼎革之变,在节义上有新的体证相关的。吕留良还说:此章孔门论出处事功节义之道,甚精甚大,后世苟且失节之徒,反欲援此以求免,可谓不识死活矣。也就是说,此章真正需要辨析的就是节义与功名之别,节义大小必须辨析,而功名无论大小都要服从于节义,如不重节义而重功名,就会被失节之徒给误用了。
再看《四书讲义》所论君臣、封建与井田,也是在辨析节义与功利。卷六说:人知父子是天性,不知君臣亦是天性,不是假合。卷三十七中说:
君臣以义合,合则为君臣,不合则可去,与朋友之伦同道,非父子兄弟比也。不合亦不必到嫌隙疾恶,但志不同,道不行,便可去,去即是君臣之礼,非君臣之变也。只为后世封建废为郡县,天下统于一君,遂但有进退而无去就。嬴秦无道,创为尊君卑臣之礼,上下相隔悬絶,并进退亦制于君而无所逃,而千古君臣之义为之一变,但以权法相制,而君子行义之道几亡矣。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此章孔门论出处事功节义之道,甚精甚大。子贡以君臣之义言,已到至处,无可置辨,夫子谓义更有大于此者,此春秋之旨,圣贤皆以天道辨断,不是夫子宽恕论人,曲为出脱也。后世苟且失节之徒,反欲援此以求免,可谓不识死活矣。无论若辈,即王魏事功,安得据管仲之例乎!
圣人此章,义旨甚大。君臣之义,域中第一事,人伦之至大,此节一失,虽有勋业作为,无足以赎其罪者。若谓能救时成功,即可不论君臣之节,则是计功谋利,可不必正谊明道,开此方便法门,乱臣贼子,接迹于后世,谁不以救时成功为言者,将万世君臣之祸,自圣人此章始矣。看「微管仲」句,一部春秋大义,尤有大于君臣之伦,为域中第一事者,故管仲可以不死耳,原是论节义之大小,不是重功名也。惟误看此义,故温公以篡弑之魏当正统,亦谓曹操有救时之功,遂以荀彧比管仲、苏氏又以冯道儗之,此义不明,大乱之道矣。
管仲之功,非犹夫霸佐之功也;齐桓之霸,非犹夫各盟主之霸也。故余谓注中「尊周室」二句,只作一句看,方与白文意合,若将尊王另分在僭窃上说,此功不足赎忘君事雠之义也。然先辈都如此说,亦不止一人之疏。要之此一段道理,先儒不曾经历讲究,固难晓然耳。
圣人论管仲,只许其功,并未尝有一言及于纠白之是非也,故程子曰:「管仲不死,观其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乃知其仁。若无此,则贪生惜死,虽匹夫匹妇之谅亦无也。」朱子曰:「仲之意未必不出于求生,然其时义尚有可生之道,未至于害仁耳。」又曰:「召忽之功无足称,而其死不为过,仲之不死亦未尝害义,而其功有足褒耳,固非予仲之生而贬忽之死也。」此三条最分明。所谓匹夫匹妇之谅,亦以其后之功较之,则此一死直小谅耳,故下个「岂若」字,谓其不死又过于死也,非指当时原不可死,死即匹夫匹妇之谅也。论者于此旨未彻,多欲曲为不死出脱,即程子兄弟之说,愚犹以为多此一节,然其义犹正大;今有云,「为傅从亡,与委贽之臣不同」,又云,「是僖公公家之臣,非公子之臣,故原可不死」,则尤为害理!如此,则王珪、魏徵,高祖尚在,亦君臣未定,高祖改命太宗为太子,即王、魏知有唐而已,又何以有罪律之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