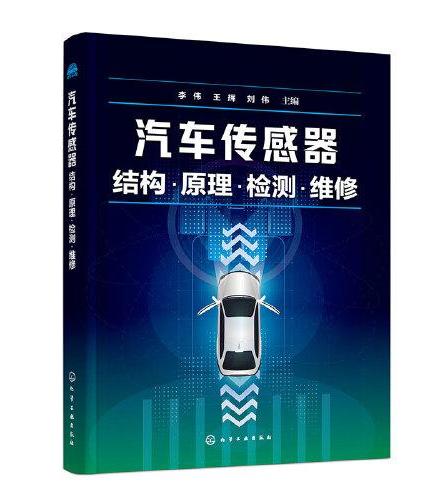新書推薦:

《
中国高等艺术院校精品教材大系:材料的时尚表达??服装创意设计
》
售價:HK$
76.2

《
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
》
售價:HK$
143.4

《
国家豁免法的域外借鉴与实践建议
》
售價:HK$
188.2

《
大单元教学设计20讲
》
售價:HK$
76.2

《
儿童自我关怀练习册:做自己最好的朋友
》
售價:HK$
69.4

《
高敏感女性的力量(意大利心理学家FSP博士重磅力作。高敏感是优势,更是力量)
》
售價:HK$
62.7

《
元好问与他的时代(中华学术译丛)
》
售價:HK$
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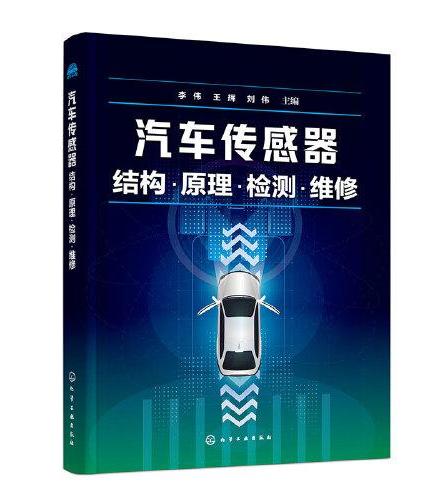
《
汽车传感器结构·原理·检测·维修
》
售價:HK$
109.8
|
| 內容簡介: |
|
本书篇幅不大,但令人耳目一新:阿克曼直截了当地说别了,孟德斯鸠( Good-bye, Montesquieu),他打破美国行之已久的三权分立教条,尝试建构一种新分权的模式,这对读者来说恐怕有一定的震撼效果。作者特别强调,自由民主的宪政价值并非是一元的,它至少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民主正当性、职能专业化与基本权利保障。作者明确的反对总统制,因为它在一定意义上与共和自治的核心精神背道而驰,甚至会带来对法治的严重挑战。不过,作者也并不迷恋美式总统制的反面,也即威斯敏斯特式的议会制。作者以当代德国、加拿大、南非、印度等国家的经验为基础,提出了有限议会制及一个半议院的方案。除了立法、行政、司法分支外,在政府组织中还可能包括其他分支,如廉政的分支(独立的监察机构)、规制的分支、民主的分支(选举委员会)、分配正义的分支;他们并非传统的三权中的任何一权,我们不能仅仅因为这一事实而否定其在现代权力分立中的地位。总之,在作者看来,权力分立是一个好主意,但是没有理由认为那些经典作者已经将分权制设计得尽善尽美。我们礼赞孟德斯鸠与麦迪逊的最佳方式,就是探寻新的的宪政模式,哪怕这会以改变我们熟悉的三位一体配置为代价。
|
| 關於作者: |
|
布鲁斯阿克曼,美国当代宪法学家与政治理论家,1943年出生于纽约市,先后毕业于哈佛大学(1964年)和耶鲁法学院(1967年),曾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耶鲁法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自1987年始担任耶鲁大学斯特林法学与政治学讲座教授。阿克曼教授在政治理论、美国宪政与比较宪法领域内均有卓越的原创学术贡献。他的代表作品《我们人民》多卷本被认为是过去半个世纪在整个宪法理论领域内所进行的最重要的工程,2010年因《美利坚共和国的衰落》的出版而入选《外交政策》评选的全球百大思想家。译者聂鑫,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法律史、比较宪法等。先后在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获得法学学士、硕士与博士学位;曾赴(台湾地区)政治大学、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台湾地区)中研院等处游学。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法学研究》、《中国法学》等刊物发表论文约30篇;独著专著《中国近代国会制度的变迁》、文集《中西之间》、教材《中国法制史讲义》。
|
| 目錄:
|
Ⅰ总译序
引言Ⅰ民主正当性
A反对总统制
1分权主义者的回应
2超越威斯敏斯特传统
3个人崇拜
B有限议会制
1找回人民
2用法院来制衡
3从理论到实践
C一个半议院的方案
1选举产生的联邦参议院
2由地方使节组成的议院
3非联邦制下的国会两院制
Ⅱ职能专业化
A智识上的挑战
1美国
2欧洲
B两个中庸的方案
1廉政的分支
2规制的分支
C冲突的分权主义
D从理论到实践
1政治化专业主义的代价
2从宏观到微观
E分权主义与法治
Ⅲ基本权利
A民主的分支
B保障基本权利
1放任自由主义
2积极自由主义:分配正义的分支
Ⅳ新分权的架构别了,孟德斯鸠(代结语)译后记
|
| 內容試閱:
|
一布鲁斯阿克曼,现为耶鲁大学斯特林法学与政治学讲座教授。在学界出道之初,阿克曼主攻法经济学和政治理论,这一阶段为期约十年,直至阿克曼在1980年出版里程碑式的重要作品《自由国家内的社会正义》。进入20世纪80年代,阿克曼开始了一个关键的研究转向。一方面,他从未停止关于政治理论和公共政策的著述,从1999年至2004年先后出版了他写作计划中的美国公民三部曲,继续着他在规范性政治理论和民主理论领域内的探索;另一方面,自他在1983年于耶鲁法学院以《发现宪法》为题发表斯托尔斯讲座,1985年在《哈佛法律评论》上发表经典论文《超越卡罗琳产品案》,阿克曼即已开始将主要的学术精力转向美国宪政史的研究。30年过后,阿克曼的作品早已在美国宪政研究中建立了一个无法绕开的学术传统,树立起一座难以逾越的学术丰碑。而本文集就主要收录了他在美国宪政史研究中的代表作品。阿克曼的研究转向,让他投身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宪法理论共和主义复兴的浪潮。在这一学术运动中,他和更年长一些的哈佛的弗兰克迈克尔曼、更年轻一些的芝加哥大学的凯斯桑斯坦,共同成为共和主义复兴中的三驾理论马车。而在耶鲁法学院内,阿克曼接下了由亚历山大比克尔所开创的耶鲁宪法学的旗帜,成为耶鲁学派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内的标杆人物。在比克尔和罗伯特卡沃先后在1974年和1986年英年早逝后,阿克曼在耶鲁学派中的承前作用已无需多言,而他对后学的启发更是功德无量,现在可以说,他在《我们人民》多卷本中所开创的新学术传统,已经塑造了耶鲁学派宪法分析的基本框架。正因此,阿克曼在1987年由哥伦比亚大学重返耶鲁大学任教,在44岁时即得以晋升耶鲁的最高教职斯特林讲席教授,且在法学院和政治学系内双聘。就我阅读范围所及,这一记录虽然不是前无古人,新政期间由罗斯福任命至最高法院的道格拉斯,在任教耶鲁法学院时,校方曾因防止他会被奔赴芝大的哈钦斯校长挖角,年仅34岁就受聘斯特林教席的职位。但在法学院早已吸纳研究型大学的学术评价体制的今天,阿克曼所创下的记录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应当是后无来者的。在阿克曼的美国宪政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当属《我们人民》多卷本。关于这一写作计划,桑斯坦曾在《新共和》中称其是美国宪法思想在过去半个世纪内的最重要贡献之一,二战后论述美国宪法的最杰出作品之一;列文森教授也称《我们人民》是过去半个世纪在整个宪法理论领域内所进行的最重要的工程。当然,阿克曼的理论历来也不乏其不满者,但即便是保守派的学者批判阿克曼,在法律评论内的文章题目还是我甚至比布鲁斯阿克曼更聪明。阿克曼的学术生涯目前远未到盖棺论定的时刻,实际上,我们在未来数年还可期待阿克曼学术产出的第三波。先是《我们人民》的写作计划已由三卷扩展至四卷,新的第三卷《民权革命》基于他2007年在哈佛法学院霍姆斯讲座《活宪法》,书稿很快即可送交出版社;而第四卷《解释》目前也正在写作过程中。此外,阿克曼还在电邮中告知他的新计划,一本是在政治理论领域内的《活在时间中》,另一本则是更美国宪法一点的《代际间斗争》。作为阿克曼作品中译的组织者,我期待着早日读到阿克曼的新作,也期待着可以尽早将它们作为阿克曼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译介给中文读者。二为什么要(重)译阿克曼;或者换位思考,读者至少是那些希望理解美国宪法的读者为什么要读阿克曼?在下文中,我不是以研究者的身份回到美国宪法理论的脉络内去重述阿克曼的理论要点,也不是要为阿克曼理论体系内那些被误用的概念做正本清源式的解释。换言之,下文并不是阿克曼理论in a nutshell,而是我在阅读阿克曼的基础上,重新理解美国宪政的历史后形成的一些基本看法,就此而言它更像英文中所说的buyers guide。阿克曼的理论追求是要重新讲述美国宪政史。在《我们人民》多卷本写作的开篇,作者上来就开宗明义:美国是一个世界强国,但它是否有能力去理解它自己?时至今日,它是否还满足于作为智识上的殖民地,借用欧洲的概念来破译自己民族身份的意义?从一开始,这就是阿克曼用来拷问自己并追问美国法律人的问题。在阿克曼看来,美国宪政叙事的问题在于宪法理论的欧洲化:美国在两百多年的宪政历程中早已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但理论家却只会用源自欧洲的理论去表述美国的经验。正因此,阿克曼的宪法理论工作,就是要实现美国宪法理论的向内转向,要通过从洛克到林肯和从卢梭到罗斯福的转向去重新发现美国宪法。在美国这个从不乏体制自信的公法输出国,阿克曼倡导的是理论自觉,他要重新讲述美国宪政及其本土资源。在重新发现美国宪法的理论之旅中,阿克曼的出发点是二元民主,在此基础上建构出他的一整套论述。根据阿克曼的讲述,二元民主其实并不复杂:美国宪政内设了两种政治决策的过程,第一种是人民得以出场的宪法政治,处身于激情被压制的危机之中,美国人民可以动员起来,启动宪法改革的公共审议,在深思熟虑后给出高级法意义上的决断。第二种是日常的常规政治,它们发生在两次宪政时刻之间,在常规政治中,人民回归他们的私人生活,而授权他们选出来的代理人去进行政治议题的民主审议。二元民主作为一种宪政模式,是相对于英国模式的一元民主和德国基本法模式的权利本位主义而言的。二元民主之所以成为美国宪政的基本组织原则,并非只是因为二元民主是一种更好的政体设计,主要原因在于它是美国建国者所规定并且在其宪政发展中不断实践和调适的高级法。而且二元民主区分了人民的意志和政治家的意志,人民的意志作为高级法,必定表现为人民在历史某一时刻在政治舞台上的现身说法。这就决定了阿克曼需要回到历史的深处去发现美国宪法,宪法历史包含着解码我们政治现实含义的有价值线索。也正是因此,阿克曼以及共和主义学派的历史转向,从一开始就不是要去重现那种在那儿等待被发现的事实真相,而是要从美国宪政史的政治斗争中去发现美国实在的高级法。这就是历史的政治学了。事实上,就在阿克曼在1983年的斯托尔斯讲座中第一次阐释其二元民主理论时,保守派的原旨主义运动已经是暗流涌动。两年后,里根的司法部长更是自觉地提出作为一种政治纲领的原旨解释论。阿克曼也是一位原旨主义者,只是他并非桑斯坦所称的身披法袍的极端分子,也没有布伦南所说的伪装成谦逊的傲慢做派,但这并不能否认关键问题在于争夺对历史的解释权,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美国如何去讲述两百年的宪政史。诚如桑斯坦所言:美国宪法是建立在有关权威的理念之上,而不是有关善好或正当的理念上。阿克曼的二元民主论不是没有背后的政治追求。进步和保守两派的左右互搏主要围绕着罗斯福新政的宪法正当性。在保守派的原旨主义论述中,罗斯福新政放逐了建国者留下的放任自由的宪法秩序(理查德爱普斯坦曾著书《进步主义者是如何篡改宪法的》),因此要对原初宪法忠诚,就要倒拨宪法的时钟,清算罗斯福新政、沃伦法院和民权革命的遗产;但阿克曼所要证成的则是,罗斯福新政是一次成功的宪法政治,人民的出场留下了作为高级法的不成文宪法,反而里根革命是一次失败的宪法时刻。这位出生于裁缝家庭,没有新政后普及的公立教育怎能上哈佛和耶鲁的宪法学家,实际上是在新右翼保守主义那里争夺对美国史的阐释权,在保守派回潮时守护新政不成文宪制的正当性。曾有学者在《哈佛法律评论》批判阿克曼的转向,认为阿克曼的原旨主义显示出美国自由主义的悲哀现状,因为自由派已经无法在实体上去说服美国人民去接受新政自由主义,而只能祭出一种甚至不成文的祖宗成法。但这种批评显然未能理解理论家的良苦用心,因此也未能理解为什么要通过反思过去两个世纪历史发展的进程去发现美国宪法。这样说意味着我们应当回归有关宪法与历史的关系论述。宪政就其本意而言不可能是一种活在当下的政治:尤利西斯的自缚不可能是用左手绑缚右手或右手绑缚左手,而是政治共同体内前代人对当代人与后代人的承诺和约束。至于这种代际承诺是否正当,会不会造成死人之手的统治,这是另当别论的问题。正是在阿克曼夫子自道的一篇文章中,他清楚地指出,美国宪法并非根源于政治哲学的seminar,没有可以作为逻辑起点的自然状态或者原初情境,而是形塑于每一代人的政治斗争。合众国本身是一个经由革命、制宪所建构的共同体,宪法是这个共同体的最高纲领,在这种宪制体内,革命先贤、建国之父与制宪诸君是三位一体的。同样,根据阿克曼的宪法类型学,美国宪法代表着革命胜利后的新开始,区别于德国基本法作为政治崩溃后的新开始与欧盟的从条约到宪法的模式。而在新开始类型的宪法中,原旨解释有着天生的正当性。正因此,即便原旨解释方法在学理上早已是千疮百孔,背后隐藏的政治动机也已是路人皆知,但原旨解释在美国就是一种政治正确的主义:如今,我们都是原旨主义者了。但原旨主义也是一个口号,各自表述。对于美国的原初建国者,阿克曼既没有像保守主义者那样去唱红,也没有像上一代进步学者比尔德或第一位黑人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那般去打黑。阿克曼没有将原旨解释奉为新教条:1787年的制宪者是伟人,但不是超人。在阿克曼看来,原教旨的原旨主义认为宪法的全部含义都起源于并且固定在建国那一刻,这实际上否定了宪法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美国宪政的时间性并不是指它在开始时也就结束了,而是指美国宪法是一种代际间的对话,这或许是巴尔金教授在新著中所说的活原旨主义。活原旨主义意味着:一方面,在任何一个经由革命而制宪并建国的国家内,历史中隐藏着宪法的规范,忘记历史就意味着对宪法的背叛,割裂历史就意味着对宪政连续性的人为隔断;另一方面,历史虽然不可能还原为事实真相,但法学家在转向历史时也不能去做森林里的狐狸,宪政不是谈出来的,宪政史也不可能只是坐而论道,只有对历史忠诚,才能培育时下常说的宪法爱国主义。从阿克曼出发,我们在面对美国宪政史时可以得出下述五个命题。第一,美国宪政史可以写成一部美国史。美国是一个通过制宪建国的国家。宪法在先,而美国在后,United States是通过宪法才united起来的。这意味着美国是一个宪法共同体,就此而言,美国宪法史也就可以写成一部美国史,理解美国宪法也就是在理解美国本身。对比中国,这一命题可以得到更好的理解:无论是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文明秩序,还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中国的政治根基都不是也不应是成文宪法。中国宪法史不可能讲成上下五千年,不可能覆盖中国这个政治文化共同体的全部时空。但美国的可能性就系于它的宪法。阿克曼曾经说过:我们的宪法叙事将我们构成一个民族。在《我们人民奠基》中,阿克曼曾设想过如下的场景:如果合众国如二战后的德国那样分疆裂土,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宪法,那么或许不需太长时间,新英格兰的人民会认为他们更像北方的加拿大人,而不是生活在西南地区的前同胞们。因为宪法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我们就可以知道美国宪法不只是法院视角内的司法化宪法,不只是法院用以化解政治冲突的司法学说和技艺,美国宪法并不能只讲述最高法院自己的故事,并不限于最高法院设定的剧场。在《我们人民奠基》中,阿克曼将基本分析单元由法院转向他所说的宪法政体,这是他迈出的一小步,但对我们来说却是重新理解美国宪政的一大步。第二,美国只有一部宪政史。美国只有一部宪法:1787年的费城宪法,两百年来经历27次文本修正,至今仍是美国的高级法和根本法,美国宪法的超稳定说也由此而来。当然,美国宪法一路走来不是没有生与死的考验,最紧迫的是让宪政传统断而未裂的南北战争,此外还有大大小小的危机。但美国只有一个政治纪元,只有一种政治时间,无论其政治身份在危机时刻经历何种结构性的再造,还都是发生在1787年宪法设定的框架内。阿克曼有一句话说得好:法国自1789年经历了五个共和,而我们只生活在一个共和国内。我们现在说奥巴马是美国第44任总统,这是从华盛顿而不是林肯或罗斯福起算的。美国宪政的连续性给学者提出了一个挑战,即如何形成我们关于美国宪政的总体史观,如何把握美国宪政实践的总体韵律,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美国只有一部宪法史,这一命题不仅是理论设计的要求,更是美国宪政自身实践所提出的命令。任何关于美国宪政的法学理论,即便是那些仅处理宪政史某一片段或局部的研究,都必须具有总体性的视角,至少应隐含有在理论上自洽的总体史观,否则由此形成的研究结果很可能是盲人摸象。从宪法学的视角去切入美国宪政研究,既要看到树木,更要看到森林,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第三,美国1937年后的现代宪法根源于建国、重建和新政这三次大转型。美国宪政的连续性并不意味着它是按部就班的、循例守法的、或自生自发的,美国宪政实践的复杂就在于它的连续性孕育于不断自我革新的能力中,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问题的关键是要到哪里去发现这种变化。根据阿克曼的宪法理论,这种延续性再造主要不是法院的创造性宪法解释,也不是27条宪法修正案,美国人今天生活在罗斯福新政所形成的宪法秩序内,而这个自1937年后统治美国的现代宪法根源于建国、重建和新政三次宪政转型。阿克曼在《我们人民转型》内就专书处理了这三次宪政转型。翻译总是会造成或多或少的意义耗损,回到英文原文Founding,Reconstruction和New Deal,我们应能更好地把握其中的结构性再造和国家体制转型的含义。而宪法时刻在二元民主结构内的提出,也意味着美国宪政发展并不是均质的。阿克曼曾指出:现代美国人并不认为我们历史中的每一年都对今天的宪法有同样的贡献。而且,美国宪政史的时间并不是自然意义上的时间,不是距离我们越近的时间就越有宪法相关性,是否相关取决于人民有没有出场现身说法。反求诸己有助于我们设身处地去把握这一命题,每个中国人想必都能理解1949或1978在中国宪政史中的意义,美国人同样如此。这一命题如果成立,也向国内的美国宪法研究者提出了历史转向的要求。长久以来,我们抱着接轨的心态而追求走在宪政理论的前沿,拱手将我们自己的研究议程交给哈佛法律评论;而网络和数据通讯技术的跃进也让今天的研究者可以足不出户,就能捕捉到位于美国宪政发展轨迹的末梢。但是,如果阿克曼的研究对我们的方法论有何启示的话,那就是要去重新发现美国宪政的deep past,这些遥远过去包含着美国宪政的真正教义。宪政作为治国安邦的道理,并不是隐含在最高法院的宪法解释中,而且总体上看,越近世的大法官其实越近视,越陷入了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化困境。我们有必要从九人转向1780年代建国联邦党人,1860年代的重建共和党人,1930年代的新政民主党人。事实上,我们学美国宪法这么多年,猛回头却发现法学院内的研究者其实并不熟悉林肯,大都是些心灵鸡汤的叙述或人云亦云的流俗意见而已。第四,美国宪政转型的模式表现为人民主权的革命。美国是个守法的民族,美国宪法是美国的公民宗教和根基圣典,但美国宪政发展最隐蔽的原动力却不在自由法治,而是介于纯粹守法和无法暴力之间的人性尺度上的革命。在《我们人民转型》中,阿克曼曾提出一个吊诡的判断:违反法律并不必然意味着非法,这实际上表达出二元民主论的基础命题,即美国宪法的根基是人民主权。宪法政治可以区分为两个轨道,第一个轨道是法治主义的模式,就是根据由美国宪法第五条所内设的修宪程序去提出并且批准宪法修正案,第二个轨道则是人民主权的模式,用阿玛的话说就是重返费城去制宪:宪法政治本身就表示它要结束一个旧时代,开启一个新秩序,至少在逻辑上不必严守旧体制遗留下的规则去规训新政治主体在动员后的意志表达。事实上,法治模式无法解释美国三次宪制转型:费城宪法的制定过程违反了1781年的《邦联条款》;内战修正案之所以能得到四分之三多数州的批准,是因为重建国会剥夺了南方脱离州的代表权,是在枪杆子下的同意;罗斯福新政则根本没有去启动修宪程序,美国现代宪法的根基在很大程度上是不成文的。但在二元民主的框架内,违法不意味着非法,更不是对正当性的否定。实际上,人民在动员起来后经过深思熟虑所给出的理性判断,这本身才是美国宪法的根基。阿克曼在近期的霍姆斯讲座中指出,美国1787年宪法所设定的是一种联邦主义的修宪程序,要求以我们州为单位的批准,罗斯福曾在炉边谈话时指出:即便35个州内的全美95%的人口都支持修宪,但13个州内的5%的选民即可以阻止修正案的批准,就此而论,既然美国至少在内战后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裂的民族国家,这一新政治身份就与原初的修宪程序形成一种根本性的断裂,正因为此,美国在内战后尤其是20世纪内的主要宪政表达都是绕开宪法第五条的。
总译序ⅩⅢ
宪法研究者经常将宪政想象为政治的理性化或多元(利益)化,但至少美国宪政的经验可以表明,宪政的存续不仅需要文功,有时候更需要武卫。如果回到汉密尔顿在美国宪政经典《联邦党人文集》开篇提出的问题,美国宪法作为一种实践,两百年来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慎思和选择,还取决于强力与偶然。或者更准确地说,汉密尔顿的问题一开始就是错的:这两组在理论上看起来势同水火的范畴,在实践中经常却是水乳交融。如果理论家继续坚持法治主义的解释模式,所要付出的代价就是丢失建国、重建和新政的正当性,这无异于否定了美国的治国之本,是对历史的篡改。再有一次这样的成功,我们必将一败涂地。第五,现代宪法解释的本质是代际综合。二元民主的宪制要求内置一种守护机制,因为人民仅仅是在激情被压制的危机时刻才会出场,而在政治热情消退,人民退回私人生活后,宪法设计必须保证日常政治的决策者不会违反甚至改变由革命一代人规定的高级法,否则,借用马歇尔在马伯里诉麦迪逊中的判词,成文宪法就是人民的荒谬企图,用以限制就其本质而言不可限制的一种权力。司法审查就是这样的守护机制:二元民主宪制内的宪法解释是要向后看的,要代表已经回归私人生活的人民去监督常规政治内的代表,司法审查在这时虽然反对此时此地的多数,但在历时性的维度内却成为民主自治不可或缺的环节。更重要的是,由于美国的宪政转型并不是全盘否定或从头再来式的彻底革命,不是在一张白纸上画最美的图画,1937年后的现代宪法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代际间的对话,因此宪法解释的本质是要综合不同宪政秩序的多元传统。也因此,如何在宪法解释中通三统,如何在司法审查中完成代际综合,统合起建国、重建和新政的三种传统,是美国最高法院在现代宪政秩序内所要面对的解释难题。
ⅩⅣ别了,孟德斯鸠
迄今为止,阿克曼只是在《我们人民》第一卷解释的可能性一章内初步阐释了代际综合的解释方法,但即便简短的啼声初试就已经一鸣惊人,有学者曾将这有限篇幅内的概要称为阿克曼最重要的贡献。例如阿克曼曾在此处为1905年的洛克纳诉纽约州翻案,这个判断之所以在现代宪法学内声名狼藉,不是因为它在判决之初就是个错误,而是因为它被罗斯福新政所修改了,而且这次修宪的主旨就是永远不再洛克纳,就是要从放任自由的宪政秩序转变为现代积极国家。而在目前正在写作中的第四卷《解释》内,代际综合的问题将得到全景式的阐释,我相信这会成为对美国司法审查历史的一次重述。三现代社会的学术从来不可能是一个人的事业,而必定是一种集体的工程。本套文集之所以可能,现在想来也是各种因素在偶然间的一次交汇,但最不可或缺的还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在本文集酝酿全过程中一以贯之的大力支持,
总译序ⅩⅤ
尤其要感谢刘海光、彭江、顾金龙、张翀、张阳诸位编辑老师热情、负责、专业的工作。感谢布鲁斯阿克曼教授,对于阿克曼教授的学术研究,我作为一位宪法理论的后学历来抱有最高程度的敬意,也很幸运,在2009至2010学年度,我有机会跟随他研习美国宪法和政治理论,对于我的这个翻译计划,阿克曼教授给予了一个学者所能给出的全部支持,大到原著的版权联系,小到原著封面用图的版权联络,都承蒙他在其中的牵线搭桥。还要感谢加盟本套文集的四位译者汪庆华、江照信、黄陀和阎天。他们不计学术翻译所能量化出的回报,而在繁忙的教学、科研和求学过程中承担起繁重的翻译工作,能邀请到他们实在是我作为组织者的最大幸运。最后还要感谢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北京大学法治研究中心以及这里的诸位师长和学友,在这个友爱的学术共同体中,我收获了首先安居、然后乐业的幸福。正如审慎以及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断从来都是美国宪政决策者的美德,简约以及在有理有据基础上的旗帜鲜明也是学者的美德。有了阿克曼教授写在前面的中译本序言,我原本是不需要写这么多的,只是希望我在前面抒发的之我见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进入本套文集的阅读。在全球秩序进入中美国的时刻,希望本套文集的出版有助于我们去理解美国宪政以及美国本身,也让我们有理由去认真对待自己的宪政过去、现在与未来。
ⅩⅥ别了,孟德斯鸠
田雷2013年4月于重庆大学文字斋
对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在今日之实践提出质疑,是为传统政治理论的重大挑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