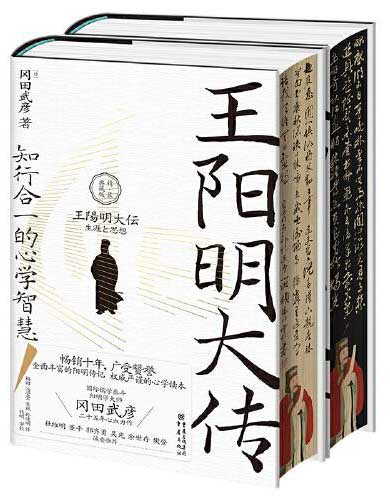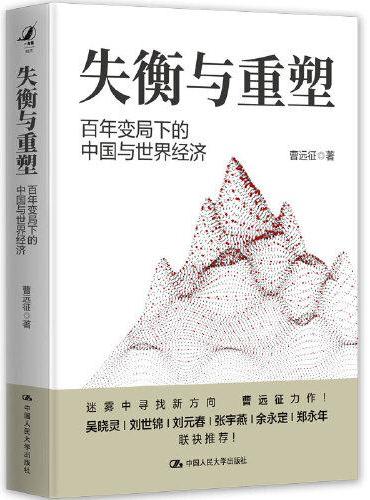新書推薦: 《
重写晚明史(全5册 精装)
》 售價:HK$
781.8
《
汉末晋初之际政治研究
》 售價:HK$
132.2
《
强者破局:资治通鉴成事之道
》 售價:HK$
80.6
《
鸣沙丛书·鼎革:南北议和与清帝退位
》 售價:HK$
121.0
《
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兼论宗教哲学(英国观念论名著译丛)
》 售價:HK$
60.5
《
突破不可能:用特工思维提升领导力
》 售價:HK$
77.3
《
王阳明大传:知行合一的心学智慧(精装典藏版)
》 售價:HK$
221.8
《
失衡与重塑——百年变局下的中国与世界经济
》 售價:HK$
132.2
編輯推薦:
【50年来海外清史研究的扛鼎之作,突破费正清学派理论模式】美国首屈一指的清史大家罗威廉新作首次出版,海外清史研究扛鼎之作。罗威廉为当今美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汉学家,也是西方学界研究清史的*人,他在国内出版的《红雨》《汉口》等作品在读者心目中已成经典佳作。罗威廉教授以其毕生治清史的深厚功力为基础,综合了国际及中国清史学界数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大力突破费正清学派的理论模式,不再强调中国朝代更迭、道统延续,代表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海外清史研究的新成就!
內容簡介:
《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是哈佛中国史丛书的末卷。本书抛弃了清朝无能保守及中国近代史起于西力入侵的传统观点,将清朝视为一个克服种种挑战、成就斐然而必须完整视之的重要断代,以深入展现中国近代历史自身演变的特质。作者罗威廉教授是驰名国际的清史专家,他同时融合了新清史、社会史、内亚史、东亚史以及比较世界历史的眼光,对于清代历史各重要阶段的起源、发展及特性,做出了完整而深刻的诠释。本书堪称数十年来海外清史研究最重要的通俗佳作。
關於作者:
罗威廉(William T. Rowe),1947年生,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汉学家之一。他同时也是《晚期中华帝国》(Late Imperial China)杂志主编、《近代中国》(Modern China)和《城市史杂志》(Journal of Urban History)编委。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东亚的社会经济和城市史。著有哈佛中国史丛书第6卷《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以及《红雨:一个中国县城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共同体(17961895)》等。
目錄
推荐序葛兆光
內容試閱
【中文版总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