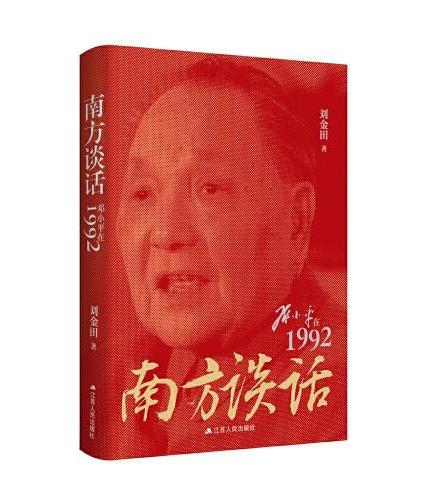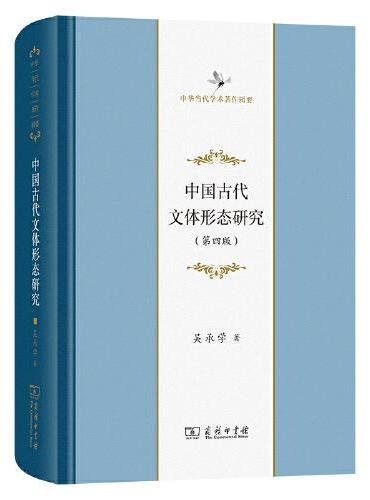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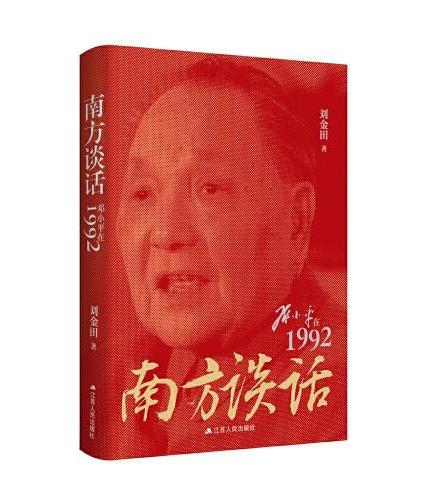
《
南方谈话:邓小平在1992
》
售價:HK$
80.6

《
纷纭万端 : 近代中国的思想与社会
》
售價:HK$
1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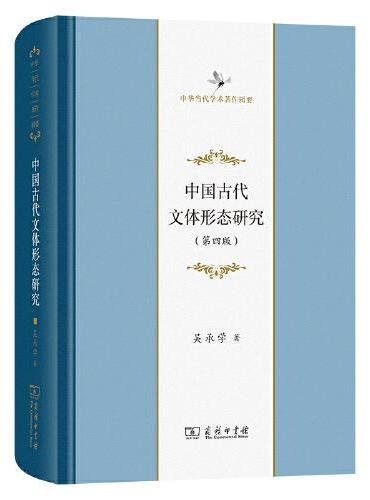
《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第四版)(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
售價:HK$
168.0

《
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大学问
》
售價:HK$
99.7

《
甲骨文丛书·波斯的中古时代(1040-1797年)
》
售價:HK$
88.5

《
以爱为名的支配
》
售價:HK$
62.7

《
台风天(大吴作品,每一种生活都有被看见的意义)
》
售價:HK$
53.8

《
打好你手里的牌(斯多葛主义+现代认知疗法,提升当代人的心理韧性!)
》
售價:HK$
66.1
|
| 編輯推薦: |
■ 本书是一部感动全球的治愈之书,更是震撼灵魂、深入骨髓的救赎之作。
本书讲述了一位小女孩从绝望到对人生充满希望的温情故事。当全世界都否定她、嘲笑她、伤害她;唯有一个人,相信她、帮助她、拯救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遭遇艰难时刻。也都会在艰难时刻拥有他人的支援和恩泽。那么在你人生*艰难时刻,谁又是你生命里的光?
■ 本书法国超高人气作家,*销量之王马萨霍托*受欢迎作品。
本书作者希里尔马萨霍托出生于1975年。2006年,正当泡着热水澡上网时,他脑中突然闪现一个句子:上帝是我哥们儿,于是他迅速投身写作行列。《寻找光的小女孩》是他自己*满意的一部作品,阐释了绝望中的希望,能带给万千读者无穷的精神力量。以下是法国各大媒体对他及这部作品的评论:
● 希里尔马撒霍托在诙谐的故事情节下,触及许多生命的大问题。他的上帝让人感到窝心,文笔则十分流畅,而略带挖苦的对话及口语化的文风,让此书相当容易阅读。
《费加洛报》
● 本书用深入却简明易懂的方式,让我们有机会去思考何谓自由、何谓受苦、何谓爱。
Elle(《ELLE世界时装之苑》)
● 完美出击的处女作!希里尔马萨霍托以大众文学作家黑马之姿
|
| 內容簡介: |
战争过后,世界一片荒芜。
羸弱的孩子们躲到暗无天日的地底下,吃垃圾为生。所有人都以为生活只能是这样:残酷、痛苦、欺凌唯有她,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女孩,始终坚信这世上会有爱与美好,这便是她心中的那片光,亦是她活下去的希望。
小女孩要亲自找到光,不管付出怎样的代价。
一天,她饱受凌虐,奄奄一息地躺在废墟里,等待死亡降临。这时,一位老先生出现在她面前。他冒着生命危险将小女孩藏在黑漆漆的屋子里,悉心照料她,并借由家里的食物、摆设和照片,一一向她叙说战争来临前人们曾拥有的美好生活,竟和小女孩心中的光无比吻合。而渐渐恢复健康小女孩亦为心如死灰的老先生带来活着的乐趣和希望
面对黑暗的再次袭来,小女孩对美好世界的执念与希望,又能否改变二人的未来?
|
| 關於作者: |
希里尔马萨霍托(Cyril Massarotto)
生于1975年,现居法国,曾任乐团填词人。2006年创作处女作《上帝是我麻吉》,轰动法国书市,他也一举成为法国销量最高的作家之一。
《寻找光的小女孩》是他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一问世便登上电商好书榜,320万粉丝感动落泪,1800万读者五星推荐。
|
| 目錄:
|
恐惧
光儿
安心和填饱肚子
单词和名字
还有那痛恨我们的大雨
梦境
战后的清单
爱、希望与认命
清理过的房子
最美妙的声音
希望
爷爷
孤注一掷
外面
致幸存者
正常的生活
生日
死者
警报
光芒乍现
结束
尾声
|
| 內容試閱:
|
1 恐惧
脏兮兮的小小身躯,蜷躺在废物堆中。我透过窗板的缝隙,观察了那尸体好几分钟,乃至于好几个钟头我已经没有时间概念了。就在尸体那只裸露的脚旁边,垃圾动了一下,我起先以为是老鼠,或是一阵我没听到的风这些年,我的听力愈来愈差。我拿起眼镜,戴到鼻头上。天色渐渐昏暗,但我再度看到有动静:尸体的另一条腿,也就是穿着脏鞋子的那条腿,在废物堆中移动了。我的心揪了起来。那孩子露出来了脸,还露出一头沾着血块的长发。是个小丫头。
一个活生生的小丫头。或至少,她还没死。
我静静等待。
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这座城市已经死了那么久,她怎么有办法一路来到这里,来到市中心?难道她漫无目的地爬行,最后才来到距离我家几公尺的这里?我很害怕:说不定是那种人故意把她丢在这里,说不定他们在暮色中虎视眈眈,等着毫无防御能力的我自己出来,那么,他们一定会杀了我。
她呻吟了一声,仿佛一道闪电划过心头我幻想她是我的小莉莎,伤痕累累躺在那里,只能靠我去救她。我的心肝莉莎,我的宝贝莉莎呀。我决定把恐惧抛到脑后,悄悄打开大门的三道锁和两条闩。然后我深深吸了一口气,从仅可容身的狭窄门缝钻到外面来。
我在屋外才走了两步路,恐惧便袭上心头:我和那小女孩的距离只有约莫十五公尺,脑海里却浮现最惨绝人寰的画面包括我自己看过的画面,还有最初,仍有无线电广播时,听人讲过的画面。我仿佛能想见自己受尽他们极尽所能的凌虐,在他们手上断送此生。我加快脚步,好像甚至还跑了起来。
好不容易来到她身旁,我弯下身子想抱起她,忽然感觉自己的腰闪到了。
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自己会就这么蹲着,手上抱着小女孩瘦弱的身躯,一直卡在这里。于是我聚集全身的力气,猛一用力,把她从废物堆中抽离出来。我腰杆子瞬间痛得锥心刺骨,痛楚来得又急又快,叫人难以忍受,逼迫我发出一声沉重又惊心动魄的号叫,连我自己听了都吓一跳,那简直就是个垂死老骨头的哀号。
直到耳边听到一声奇怪叫声,小女孩才睁开眼睛。几秒钟前,把她捧起来的那双手,确实把她从黑暗深渊中拉出来,但直到这一声叫喊,她才真正恢复意识。起先,她不明白自己所看到的:天色暗了,她的头轻微摆动着,然而她明明很确定自己没有移动的力气。接着,画面逐渐清晰:有一个肩膀、一个脖子,和一个头,但角度是由下往上看。这三样东西都特别特别大。一阵惊恐从心底蹿起,她赶紧闭上眼睛再重新睁大,发现自己此刻是倚贴着一片胸膛,上方有一把如错综复杂的荆棘般浓密的大胡子,是某个人或某个东西正一面把她抱在怀里,一面喘着大气。这种野兽般的喘息,把小女孩吓坏了。她开始隐约猜出发生了什么事。
她感觉到停了三四次,宛如在登阶梯,又听到一只脚踢开一扇嘎吱作响的门,接着整个大身躯转过来以反方向前进,门喀啦一声关上。她似乎来到一间屋子,但四周依然一片黑暗:没有火,也没有灯。小女孩感觉自己全身血液仿佛凝结,因为她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了:这里是妖怪巨人的家。
妖怪巨人把她轻轻放在某种柔软又舒服的东西上,再回去把门上锁。她成了俘虏。他像头野兽,依然喘着大气。小女孩从来没见过妖怪巨人,但底下的某些小孩曾或近或远、或多或少见过他。某天早上,在地面上,他曾试图擒抓他们其中一人,那小男孩差点就被抓走了,他吓得魂不附体,接连好几个星期不肯再出来。妖怪巨人家的四周是禁区,但有些人说自己清晨天亮时曾试着靠近过:他们看到院子里并排放了好几具人骨骷髅。
初次发现妖怪巨人的踪影,是许多年前,战乱刚起的时候。年纪最大的三个孩子,早上睡觉前,经常会说起这个高大魁梧的老人的事。他头发很长,大胡子乱糟糟的。某天夜里,他们看到他大咧咧走在马路中央光是这一点就令人啧啧称奇:这表示妖怪巨人不怕那种人,因为他居然连躲都不躲手上捧着一个全身血淋淋的小女孩的遗体。他们偷偷尾随他,亲眼看到妖怪巨人不时停下来,发出几声号叫,把脸埋进遗体,吮饮她的血。很小的时候,这传说让她心里有点毛毛的,但如今,她心想与其落入暴虐残酷的那种人手中,或许还不如被这个老妖怪巨人带走。她深知,那种人对所有的人都会做出很恐怖的事情,对小女孩更是心狠手辣:如果遇到小女孩,他们会慢慢玩弄。每当大孩子们讲起这类事情,她总会捂住耳朵,光是看他们的手势,似乎就看到了许多件一个小女孩原本不该知道的事情。
奇怪的是,因为太害怕那种人,她现在反而比较不那么害怕妖怪巨人。小女孩心情平静地期盼自己的血可以很快被喝光,她就能迅速死去,不用受太多苦。
当然,如果能够选择,她还是宁可活着,但她实在太虚弱了,根本不可能逃走或以任何方式抵抗。她很认命,原本打算逆来顺受,忽然内心深处有个小齿轮转动了。这个小构造,带动另一个构造,它又再带动别的构造这一连串奇特的机制运转下,孕育出一个微妙的东西:希望。
也说不上来为什么,但小女孩开始暗自期盼妖怪巨人不是坏人。她很纳闷自己为什么有这种想法,后来才发现,是因为她从自己所躺的沙发上,闻到一股美妙的花香:一个妖怪巨人的家里居然这么好闻,未免太奇怪了。再说,从来就没有谁是好闻的,从来没有,说不定只有她除外,但只好闻过几个钟头,而且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小女孩以前经常在漫漫长夜里,被逼着外出搜刮东西。某次,她在一栋大楼的瓦砾堆中,找到一支装着黄色液体的小管瓶,打开塑胶盖子后,她头一次闻到一股很神奇的味道,想必是天堂的气味吧也就是她父母亲如今所在的地方的气味。她把这项发现告诉其他孩子,有个十三岁的大孩子教他们这东西叫香水,以前,妈妈们用来擦在头发和耳后,让自己闻起来香香的。小女孩把整瓶液体倒在自己头发上,一整天闻起来都很浓郁且很香,后来到了晚上气味就消失了,她一直不明白为什么。
她把头稍微侧偏,想更仔细地闻一闻抱枕上的气味。刹那间,她回想起妖怪巨人把她抱在怀里时,她也曾从他的胡子闻到过相同的奇妙气味。一个妖怪巨人绝对不会闻起来这么香,她很确定。如果她的直觉是对的呢?如果这妖怪巨人,其实只是个身材高大、披头散发且有着一脸杂乱大胡子的老人呢?
妖怪巨人回到她身旁,站着端详了她一会儿,随即又离去。她看不到他,但每一秒都知道他正在做什么:先是远去的脚步声,水从细长瓶颈流出来断断续续而闷稳的声音,然后是回来的脚步声、在近处点起打火机的擦石声,以及油芯燃烧起来所发出的典型而让人安心的声音。
小女孩最爱的东西,莫过于光亮,连某些孩子找到带回来的食物或玩具都比不上。漆黑会令她紧张,然而她明明已经不小了她感觉自己已经十岁,或快要十岁了。在底下,和她同龄的女孩早就什么都不怕了,但她没办法。虽然她的记忆里只有底下,和底下几乎无所不在的黑暗,但她很怕黑。所以她每次出来搜刮物品,绝大多数的时间都用来寻找能照明的东西,而不是寻找食物。她因此被毒打了不知多少回,最后一次,就是昨夜的那次。
一块湿润的布料放在小女孩额头上,把她吓了一跳。
别怕你好烫,得让你退烧才行。
他的声音很奇特,很粗又低沉,她从来没听过这样的声音。她很错愕,再度感到恐惧袭卷而来。
只好把我仅剩的药给你了
然而,声音不只低沉,也很温柔且温暖。就像香水一样。
等他坐到她身旁,油灯照亮了他,小女孩终于看清他的长相了。
是个老人。
妖怪巨人果然是个老人。她从来没见过真正的老人。当然,他们经常会发现很多年长者的照片和图片,她知道老人是什么模样就像她也知道那种人是什么模样一样。但现在居然亲眼见到一位老人家,还这么近距离感觉真的很奇怪。底下年纪最大的孩子伍拉狄米,也才不过十九岁而已至少他是这么说的,因为十八岁的那几个人怀疑他为了当老大而撒谎。她唯一看过的大人,是个已经死掉的人:是个那种人,他自己一个人闯得太深了,大孩子们对他下手可一点也没留情。
这个老人和其他人都不一样,和伍拉狄米、那种人和图片上的老人等等都不一样,但他不是什么妖怪。他确实很高大,不像孩子们传说中的那么巨大,但还是很高大。而且,他看起来很强壮,并不是因为他很肥胖,或特别有肌肉,而是他散发出一种浓浓的力量感。他的手臂和肩膀就像老树的枝干般厚实而粗壮。
老人的模样就是这样,像某夜小女孩见过的烧焦的大树。那一夜的满月很明亮,宛如海蓝色的太阳。那是她少数几次去这座城市的另一头,那边的一切早已死绝了。
老人的脸看起来也像烧焦了。他的褐色皮肤宛如旱季大地般皴裂,好几道深深的沟痕交错着,尤其在额头上和眼睛四周。那浓密的胡子,小女孩原本以为是灰色的,其实已经几近白色,遮住了他整个下半张脸。他宛如刷子般的长眉毛,颜色也很淡,不过仍较偏向灰色。头发所剩无多,鼻子既尖又厚,令小女孩印象深刻。鼻子很抢眼,又高又长的耳朵也是。
说到底,是真的:这老人长得很像个妖怪巨人。
他把一只手伸到小女孩的脖子下面,轻柔地把她的头托起来,再用另一只手把两颗胶囊放进她嘴里,喂她喝了几口出奇清净的水。
你饿吗?她好想马上点头,以便充分表达这份已经折磨了她好几天的饥饿感其实根本是长久以来都挥之不去的感受。然而她实在太虚弱,动作缓慢沉重无比,她很担心老人不明白她的意思。所以她努力想坐起来,结果眼前的小黑影愈来愈密布,直到变成一片漆黑。
那可憐的小丫头累坏了。她连回答我的力气都没有,直接头倒在我手心里睡着了。她浮肿的脸颜色泛黄,某些地方还青一块紫一块。我尽量小心翼翼地用一个抱枕取代我的手,然后拿了一条我平常用来盖腿的格子毛毯覆盖在她虚弱的身体上。我很后悔没先拿厚棉被垫着沙发,再让小丫头躺上去,因为污垢和血渍一定会弄脏我的抱枕。
一直到睡觉前,我都因此闷闷不乐。
爬上楼时,我的背再度疼痛起来。也难怪了,这是意料中的事呀!随着年纪愈来愈大,我学到的教训愈来愈多,其中包括这一课:过了一定的年纪后,每次花力气,哪怕只是一下子,就注定要带来顽固持久的痛楚。
在这太漫长的一生当中,我记得很多事情我的第一台脚踏车、儿子的诞生;一切由它开始也由它结束的那个雨天、我的莉莎的死。可是,在这一切的记忆当中,有一道光芒特别照亮了某个特殊的日子:我成了个老头子的那一天。
那一天爬楼梯时,我比平常都觉得更艰辛吃力,只好把两只脚都放在每一阶上。判决已无可逆转,事实摆在眼前:今后我就是个老人。以前,奇数阶梯由右脚负责,左脚负责偶数阶梯。然而,自从这沉痛的一天以后:第一阶,右脚,再左脚;第二阶,右脚,再左脚;如此类推,直到最顶。依照世界的定律,只要老了,凡事都要花双倍的时间,行动的速度会减半,可是如果每爬一阶梯还必须两只脚都放,那么爬楼梯就必须花去四倍的时间。仔细想想,真不公平:大好人生摆在眼前时,做起事来,神速无比;来日无多时,却只能用慢动作,看着仅存的时光溜走。
要是早知道,我一定会当个懒惰的年轻人,或许就能省下一些体力,留着攀爬每晚上床睡觉前所需先登上的这喜马拉雅山般的楼梯。该死的背,根本是个连站都快站不住的该死臭皮囊。
躺下来会比较好,好一点点而已。我躺在床上,想来想去都是同一些问题:该拿小女孩怎么办?她是什么人?是否值得为她消耗我的药品,和使自己身陷险境?而且重点是,她怎么有办法出现在这里?我已经四年多没见过也没听过任何活人了。上一次,也是个孩子,那次是个小男孩。我是最近一次出去时遇见他的,那天晚上,迫于必须,我鼓起勇气出去寻找电池我的库存用尽了。尽管多年来已没有任何频道发出讯号,我每天早上仍会努力把整个波段仔细搜索一遍。我把搜寻范围集中在这一带豪宅最多的地方,那是较往南方的一条路段北方,早已尽是废墟或灰烬。我满载而归,天色才正要转明,我心满意足但战战兢兢,就在到了我家巷口的时候,我迎面遇上一个瘦巴巴的小男孩,他正费力掀开一个地下水沟的孔盖。我很意外,愣在原地,但那男孩一见到我便开始大呼小叫。我想安抚他,向他伸出手,他却尖叫得更厉害,立刻跳进废水道,匆匆关上盖子。他似乎吓坏了,想必他误把我当成那种人吧。我走到孔盖旁,听到他的尖叫声在废水道的长廊里回荡,其他一些幼童也惊慌失措,跟着喊叫起来。我这才发现那底下不是只有那个小男孩而已。我赶紧回家,生怕小男孩的叫声会暴露我的踪迹。脱离险境后,我忍不住纳闷,为什么我从来没想过要像他们一样,去地底下生活。但我发现我宁可死,也不愿如老鼠般苟活在那么不堪的烂泥坑里。
活在地底下的那些人,应该有好几十人,甚至上百人吧。那些孩子八成形成了某种社群,一群小野人集结在一起,相信那小丫头也是他们的一份子,不然以她区区九、十岁的年纪,不可能靠独自的力量存活那么久。她年纪居然这么小,是很不可思议的,战乱爆发时,她应该才不过两岁吧。
某方面来说,这让我安心:假如她是从某个地方来的,她就能回某个地方去。等她能站起来,我就立刻把她送回给她的同伴。
天呀,我好累。
2 光儿
我醒来时胆战心惊,因为听到大雨打在我家窗户上。打从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滂沱大雨便成了我最惧怕的一件事。对雨也许不如对那种人那么恐惧,然而只要任何丝毫的降雨,便足以令我心惊胆跳。就像每次只要一下雨,回忆的画面便不请自来,将我淹没;就像每次我泪水满溢眼眶,又回想起自己躲在那个大型垃圾桶里,无力又懦弱地观看俨然是世界末日的那个无尽雨天。
但这些画面即我从店里出来,怀里抱着一大堆姜饼人的画面忽然被楼下传来的一声呻吟驱散。小女孩喃喃呓语,她好像在叫我:
汪
她的这一声立刻把我拉回现实,让我意识到她出声可能惹来的危险,所以我赶紧起床。我从楼梯上方低头往下,压低声音对她说:
来了!嘘!
汪
我怕她没听到,稍微拉高音量,但特别留意别变成喊叫:
我来了!别再出声,不然会被听到!
幸好她没再说话,静静等我,让我松了一口气。到了沙发旁,我看到她双眼在黑暗中闪闪发亮。她手指着关着的窗板,对我轻声说:
光
唉,我从来不开窗板的,不然万一被那种人看见反正现在是晚上呀!
光。
要不要我来点油灯?
光,光,光!
好啦,好啦,拜托你小声一点!喏,亮了这样行了吗?
她点点头表示行了。
你不希望我们被发现,对不对?
她摇摇头表示不希望。
如果是这样,我拜托你别再嚷嚷。起码我发现你吃的药发挥作用了!你饿了吧?
她点点头表示对。
咦,你会说话吗?
她摇摇头表示不会。
可是你刚才明明喊了好多次光,你会说话呀!
光
你是故意的吗?
难道你真的不会说话?
她摇摇头表示不会。
你只会说光?
她点点头表示对。
居然有这种事居然给我碰上只会说一个字的丫头!我该拿你怎么办?至少得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呀!
喂,努力一下嘛,你总有个名字吧!
你倒是说话呀!随便说什么都好!
光光?
好啦,那就这么办吧,我们就叫你光儿。
小女孩很高兴:老人替她取了个名字呢。几乎像个真的名字了。在底下,孩子们从来没想过要帮她取名字;每个人都有名字,唯独她没有。然而,有个大孩子某天曾说,多年前,曾经有人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根据他的说法,当初是小女孩年约十五岁的姐姐带她来底下的,姐姐把小女孩的名字告诉了一个男孩,但那个男孩后来和姐姐一起返回地面上,从此再也没回来。大孩子又说,想也知道,姐姐和那男生在上面遇害了。到头来没有任何人知道这该死的名字。小女孩从来就不相信这个说法,因为她从来不记得自己有过任何姐姐或妹妹,也不记得自己有过什么名字。孩子每次要叫她,就喊喂 哎或弹弹手指。他们也常叫她哑巴。
然而她并不是哑巴,她会说一个字:光。她知道为什么自己能说这个字,因为长久以来,光亮就是她最殷切渴望的东西。但她从来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只说得出这个字。然而,她很清楚自己的发音咬字能力没有问题。最好的证明是,在底下的时候,她曾经在睡觉时说梦话。起初几次,其他孩子把她叫醒,鼓励她再多说说看,但不论她怎么努力,还是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光这个字,别人就渐渐对她失去了兴趣,并替她取了另一个绰号疯女。她讨厌死它了。
因为她明明不疯,这一点她很确定。再说,她其实能说话,甚至很能说话,只不过是在自己心里说。她会编故事给自己听。她像个字句话语的风车磨坊,只不过还没有风吹动这风车罢了。要是真有那一天她经常幻想自己突然开窍的那一天,自己一定会一口气把曾经嘲笑过她的人通通滔滔不绝回呛得目瞪口呆。啊,等到她开窍的那一天,那些笨蛋一定会傻眼!等着瞧吧,他们通通等着瞧
可是没了。
他们什么也瞧不着。永远不会有那一天了。
现在,她再也不是他们那一伙的,再也不是了。因为那些孩子不但把她打得半死至少他们一定以为她死了居然还把她的躯体丢弃到妖怪巨人这里来,不惜大费周章,把她拖来这个自从知道有妖怪出没后就被列为禁区的地方。
从这一刻起,她意识到自己没有退路,以后的生活再也不同了。她不知道这样是福还是祸,不知道自己到底该害怕,还是反而该安心。她很快就发现自己什么也不知道了,她已完全不知所措。她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假如我回去底下,其他孩子会不会排挤我,又把我丢弃在妖怪巨人家的门口?然后又问了另一个问题:不然,我能不能跟这老人待在一起?以及第三个问题:万一他也把我赶出去,我该去哪里?结果问题愈来愈繁多,她感觉到自己开始发抖,呼吸变得急促,仿佛有人把她往后拉扯,仿佛她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瘫软跌倒了
后来,她才知道这种可怕的感觉是怎么一回事:是不确定感。以前在底下,尽管每天都要面对饥饿、恐惧、羞辱和愤怒,但每天的生活很规律,她从来不用担心明天会如何。在底下,白天就躲起来睡觉,晚上则出去寻觅食物或以她而言,寻找能发光的东西,其他一概不必多管。可是在这里,她似乎再也没有任何可依据的准则了。
她发现自己只知道一件事:从今以后,她名叫光儿。
于是,她的呼吸趋缓了,双手不再颤抖,一股温暖的感觉包覆了她。
她有名字了。
她有身份了。
她是光儿。
我把灯凑到她脸旁。盖着厚厚的棉被睡了二十个小时,加上药品的辅助,让她元气大振。她消肿了许多,甚至看起来气色不错。小孩子嘛。
虽然她皮肤某些地方仍有淤青,我终于能看清她的五官,看清楚她真正的长相。干掉的泥巴块下的长发,似乎是浅色的。她的眼眸又大又蓝,颜骨立体俏丽,小小的下巴有一点尖尖的。鼻子很小巧,鼻尖翘得很低调,使她的容貌有那么一点像猫科动物。是的,没错:小丫头有着一张猫咪般的漂亮小脸蛋。
光儿呀,你想吃什么?
好看来我需要点时间适应了算了,我替你决定吧。我们先来喝个好汤!
看她一脸茫然的样子,我发现她不知道汤是什么东西,至少她听不懂这个字。我去厨房,点燃小煤气炉,把锅子放到蓝色火焰上,再把一整罐七种菜泥的蔬菜罐头汤倒进锅子。我有很多种选择,说不定多达六七种不同的料理方式,但我不想把口味弄得太复杂,或把组合弄得太花哨,毕竟她在味觉上一定还是个新手。这七种蔬菜相当合适。
我拿着新婚时那套餐具里的木头旧汤匙搅拌浓稠的汤头时,雨势变本加厉了。我再度不寒而栗,于是闭上双眼,集中注意力想别的事情,但根本是白费力气,我心知肚明。一如外头闪电划破天际,我内心同样被回忆撕扯。一切又浮现我脑海。那个雨天。
莉莎的姜饼人。
那种人。
我,躲在垃圾堆里。
所有的人呀,他们发出的声音呀
老人把汤端来时,汤碗里冒出的热气,令光儿很惊奇。她用双手捧着碗,那触感太温暖、太舒服,她忍不住泛起笑容。她吹了吹袅袅而上的热气,一面纳闷到底该用吃的还是该用喝的。她满怀感激望着老人。
她发现他眼角有泪水颤抖着。汤碗的热度如一股暖流传遍她整只手臂,又如一阵美妙的波动布满她的身体,让她全身逐渐放松。
很明显地,她的恐惧已烟消云散。
她不太清楚这种感觉究竟从何而来,也未追问为什么煮汤竟能让这么老的男人热泪盈眶。或许她永远也不会知道答案,可是,不知为何,有一件事她非常笃定:她永远也不想和老人分离。
3 安心和填饱肚子
光儿一整天都在吃东西。所吃下的这些东西,她一个也不认得,但她记住了每个东西的名字她非常喜欢学习新单词,等到她能开口说话的那一天,就能派上用场了:橄榄、油渍沙丁鱼、红豆以及玉米。关于最后一项,她怀疑很久以前,小时候的某天,她曾经从某户人家的地下储藏室带了一罐这种玉米回去。但她不确定到底是不是相同的东西,再说当时,根本就不准她吃。真可惜,吃起来很甜,很美味。
说到底,她这一辈子,其实品尝过的味道寥寥无几。他们找到的罐头,大多被大孩子们分掉了,年纪小的孩子只吃得到剩下的一点水果罐头而已。除了菇菌以外,她几乎没吃过什么别的东西。下水道里有很多菇菌。在她小时候,必须去很远的地方摘采,要在地道里愈走愈远才采得到,但某天有个大孩子发现,只要是他们排泄粪便的地方,菇菌便长得特别茂盛。于是,在点子王迪多的一声令下,他们大小号都必须去遍布各处的地道的某些特定地方,并洒上他事先发配的一些菇菌碎屑。过一段时间,菇菌便大量冒出来。菇菌不够吃的话,老鼠也是很美味的,但必须生火烤熟它们才行,可是火烟恐怕会害他们被上面的人发现。
吃完玉米后,光儿表示她还想再吃,但老人说必须省着点吃,因为不知道战争会持续多久,还说她已经在短短几个钟头内吃掉三天的分量了。她假装无奈地接受,其实也知道自己已经不饿了。
让肚子慢慢消化,很舒服地静静休息了一会儿后,老人对小女孩说:
来,我有东西要给你看。
她紧跟着他,从厨房的一头来到另一头。他挪走一张地毯,把地上的一个活动门板掀开,提了一盏灯凑过来。
跟我来,你看了就知道。
他们小心翼翼走下一条短短的楼梯,老人伸直手臂,把手上提的灯尽量向前,照耀地下室的最里面。
她不禁目瞪口呆。
是食物,堆得像小山一般高的食物。不论是她面前、上方、地上、架子上,或纸箱里,到处都有百百千千个罐头。她甚至没想过世上竟然可以有这么多食物。
你看吧,我们的存粮足够,但要节制。依照我的计算,如果考量各种罐头不同的容量,一天平均吃三到五罐的话,这里差不多够吃三年。或许你以为这样很多,但我一开始的存量是现在的三倍!
光儿敞开双臂,双手一摊,皱起眉头。
想不想知道我怎么弄来这些的?
她奋力点头。
当然是我自己扛回来的呀!我不敢出去,但别无选择,我总得要喂饱我的小莉莎这附近有三家店铺和一间加油站,我推着推车出去,几个晚上就解决了。噢,要是我再多跑几趟,一定能搬更多回来,可是某天晚上,我差点撞见那种人。我以为马路上都没人了,但我把推车推上人行道时,不小心翻覆了,金属罐头掉在地上,发出好大的声响,于是我听到某人喊叫的声音,还有其他人的喊叫声和朝我的方向跑来的脚步声,甚至有一声枪响。我顺利逃回来这里,但至少整整两个晚上睡不着觉,你想也知道呀从那之后,我只再出去过两次而已。我最怕的就是引起他们的注意,怕他们来到这里,发现我的莉莎反正,我已经累积了足够的食粮,够我们爷孙俩捱好几年。
光儿一面聆听老人说话,一面忍不住直盯着罐头看。她感到非常幸福,因为发现左方有一整箱红色和白色的蜡烛,就像她以前找到过的那种蜡烛一样。
你知道吗,一般都以为罐头只能保存两三年,到保存期限为止。你知道保存期限是什么意思吗?嗯,看来不知道,总之,就是保存日期的意思,通常用很小的字印在表面。其实才不是那样!保久罐头可以保存一百年都不会坏,所以才叫做保久罐头呀!甚至可以超过一百年,很不可思议,对不对?这就让我想起以前,我和凯特琳呀,我们只要一看到罐头过期,就通通扔掉,有时甚至快要到期的也扔,以防万一嘛!真浪费因为呀,是这样的,相信我,某些食物多摆几年反而更美味,这里有些罐头是我从一爆发战乱就吃到现在的,已经八年多喽,而且愈来愈好吃呢!至于饮料,可就差多了,我带回来的瓶装饮料并没有撑多久。这些年来,我轮流使用六十几个瓶子,只要下雨,就盛接雨水,再用后面的煤气桶把雨水煮沸,用蜡把瓶口封住,便大功告成。我最害怕的就是没有煤气可用,但其实有这么多桶库存,再撑个十几年也没问题。煤气可是很方便的。
这个地方让她有一种很不真实的感觉。这里一切的一切,都是她短短一辈子以来,苦苦寻找且梦寐以求的,甚至还超乎她的想象。光亮和食物,正是她在底下最大的痛苦根源,尤其是食物。
最近这阵子,菇菌和老鼠已不够填肚子了,有三个年龄分别为十一、十四和十五岁的女孩生产了,还有一个怀孕了,她们食量大增,每个人只好加倍努力去找食物回来养活大家。光儿仍一意孤行,坚持只找电池或蜡烛。尽管大孩子们多次修理她,并下了最后通牒,她出去寻找整整七个钟头后,带回来的仍只有区区三根火柴和一小片擦火板。她还记得开头的几拳,先打肚子,再打脸;然后,就什么也不记得了。
她好不容易恢复意识,挣扎着爬了几十公尺,又再度昏厥过去。隔天夜里,她似乎从关着的窗板之问,隐约看到透出微光。她用尽余力,往光源靠过去,但未能如愿。她试图横越一堆垃圾时,全身顿时瘫软无力,当下,她以为自己要死了。这一切,都是为了光亮,和为了食物。
但现在,这些通通抛到脑后了。她有得吃,也有得照明了。而且她有他。
光儿一面沉浸在这座宝藏山所带来的满足喜悦中,一面牵起老人的手。他的手指又细又长,实在一点也不像什么妖怪巨人。
于是小女孩把手紧紧握住。他们便这样,默默待了许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