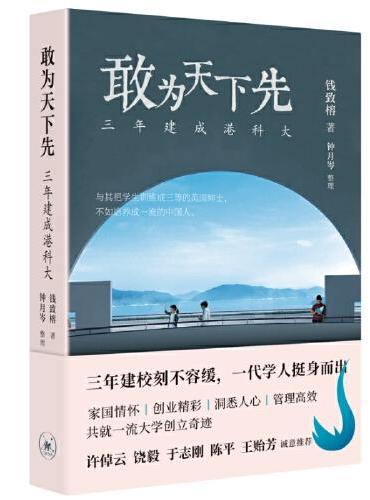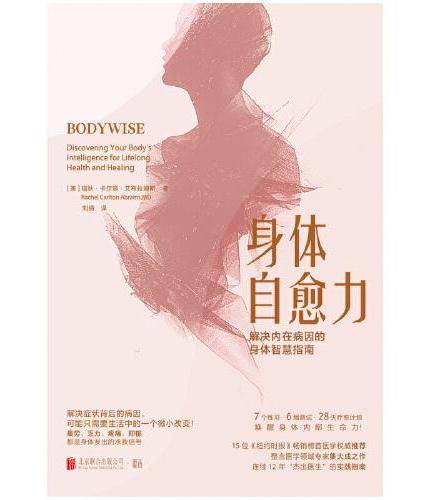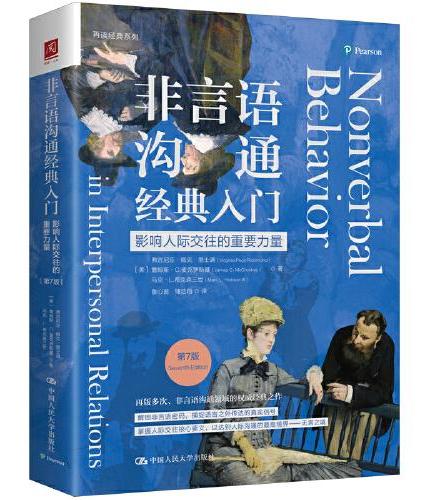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在近半个世纪中,中国大陆的散文进入了工农兵代言人的时代。诚然,它有前后期之分,可以70年代中期文革结束为前后期区分的标志,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是后工农兵代言人时代。
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这是树立权威的时代。战争是权威,党派是权威,枪杆子是权威,权力是权威。当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以后,整个中国处在国共对立的你死我活的战争状态中。阶级斗争以战争的形式出现,战争主宰了一切。散文家在这场你死我活的对抗中必须做出选择。其实在之前,这一选择就已经严峻地摆在面前,40年代初,发生在延安的文艺整风,就是要求散文家做出新的选择。
当时代车轮刚刚驶入40年代,毛泽东就已意识到文化的重要。他在1940年1月延安创刊的《中国文化》上发表了长篇论文《新民主主义论》,用大量的篇幅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认识和立场,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尽管这种立场表述是纲要性质的蓝图描绘,但有一点是具体的、清晰的,而且是毫不动摇的,就是新文化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里的无产阶级领导是非常落实的、具体的,其含义应是管理、指挥、服从。毛泽东坚持的是两条:一条是党指挥枪,另一条是党指挥文化。文化必须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文化必须服从党派和权力的权威,必须服从意识形态的权威,散文绝不能例外。
但这一切并没有引起当时延安作家的足够重视。从延安作家队伍的结构来看,大部分是从国统区和沦陷区投奔而来的,跟随武装部队从江西经历二万五千里长征来的极少,这一结构决定了他们对延安的认识心态上的差异。作为当时共产党的军事人员和领导者来说,他们是九死一生,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最后终于在延安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延安是命根子,他们已无路可走。而且延安处在日军和国民党围困之中,在战时特定环境下,延安是一个封闭的社会。再从权力管理系统来看,从中央到地方,体系非常严密,形成一种国中之国的割据局面。这种割据,决定了延安的共产党领导人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并理所当然地要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审视延安发生的一切,以确保政权的巩固。延安的安全和稳定高于一切。对于从国统区和沦陷区投奔而来的大批作家来说,他们的心态不同。他们是满怀激情,为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来到延安,他们把延安视为理想的王国和完美的圣地。作家们又非常敏感,他们在延安的现实生活中看到了另一面,那就是等级制度、干部庸俗的心态以及享乐主义等等。作家们把理想和完美视为高于一切,这样冲突就不可避免。王实味在《政治家艺术家》中就用文学的手法描述了这两种不同心态的冲突:有些以政治家自傲的人,望到艺术家便嘴角浮漾着冷讽的微笑;另有些人以艺术家自高的人,提到政治家也要耸耸肩膀。其实,客观反映总都有些真理,最好是彼此都把对方当作是镜子照一照自己。不要忘记:彼此同是带着肮脏黑暗的旧中国的儿女呀! 倘若冲突双方仅仅是冷讽的微笑和耸耸肩膀,事情就简单多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其严重和残酷远比人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在近半个世纪里酿造了许多冤案。而发生在40年代初批判王实味的这场冲突,竟成为20世纪中国散文史上的一个沉重话题。
冲突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
事情的缘起是在1942年春天,当时丁玲主编的《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了王实味、萧军、丁玲、艾青和罗烽等的杂文。王实味19061947,河南潢川人。1922年入北京大学,同时从事文学创作和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抗战前夕去延安,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员。他在1942年3月13日、23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杂文《野百合花》,在1942年3月17日《谷雨》上发表了杂文《政治家艺术家》。萧军19081987,辽宁义县人。早年就读于东北陆军讲武堂,曾在东北宪兵教练处任少尉军事及武术助教。九一八事变后,拟组织抗日义勇军,失败后逃赴哈尔滨,在哈尔滨与萧红出版短篇小说合集《跋涉》。1933年他和萧红逃到上海。他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由鲁迅亲自撰序推荐出版,声名大振。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到武汉参加《七月》刊物编辑工作。次年去延安,后辗转到四川,从事工人业余文艺教学工作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40年再赴延安,主编《文艺日报》。他在1942年4月8日《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杂文《论同志之爱与耐》。丁玲19041986,湖南临澧人。1921年到上海入平民学校,次年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读了一年左右到北京。1927年发表处女作《梦珂》,接着发表《莎菲女士的日记》等,影响颇大。1936年逃离南京到达延安,曾任中央红军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1941年主编《解放日报》文艺副刊。1942年3月9日在《解放日报》副刊《文艺》第98期上发表杂文《三八节有感》。艾青19101996,浙江金华人。早年曾赴巴黎习画,后来开始写诗,1936年出版的诗集《大堰河》奠定了他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1941年辗转到了延安,一度任教于鲁迅艺术学院,主编诗刊。1942年3月11日,他在《解放日报》副刊《文艺》第100期上发表了杂文《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19091991,辽宁沈阳人。1928年毕业于哈尔滨呼海铁路练习所。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在杨靖宇领导下担任哈尔滨东区区委宣委,创办《文艺》《夜哨》周刊。抗战爆发后去武汉,参与编辑半月刊《哨岗》。武汉沦陷后他去了重庆,继续从事革命文学活动。1941年赴延安,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主席。1942年3月12日在《解放日报》副刊《文艺》第101期上发表了杂文《还是杂文的时代》。
这批性质相似的杂文在同一期间出现,显示了这样五个共同特点:第一,这批杂文作家都是抗战前后从国统区和沦陷区进入延安的,在到达延安之前,他们已有了较大的文名和声望,不是一般作家。第二,这批杂文都发表在延安最权威的刊物《解放日报》上,影响很大。第三,时间集中,都发表在1942年春天。第四,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延安现实中的阴暗面进行揭露和批判。第五,在文体上均是杂文,对问题的揭露和批判是以直截了当、一针见血的方式呈现的。它们成了第一批公开发表的批评延安的意见书。散文的文体特征,决定了它在这场冲突中充当了出头鸟的角色。
这批杂文集中揭露和批判了延安的阴暗面和黑暗面,揭露是无情的。以《野百合花》为例,它的要害是野。野在于它认为延安有黑暗,有些人在那儿间接助长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尤其对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在这一点上,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也做了同样的揭露。另外,《野百合花》还对延安缺乏爱,对一些干部只顾自身享乐,只顾自己的一点利益等庸俗丑陋现象也提出了批判。艾青、萧军、罗烽等的杂文也基本上是对这些现象进行揭露和批判的,尤其是罗烽提出的还是杂文的时代成了这批杂文的理论依据和口号、旗帜。
如果客观来看这些揭露和批判,应该是可以容忍和允许的。但问题在于,它们的集中出现,在延安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人还把王实味捧为延安的鲁迅。由于延安的政权和体制,是从江西根据地延续而来,是以军事手段建立起来的,战争环境中凭借军事手段建立起来的政权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从江西到延安,从来没有任何人包括作家对这一权威发动批判和挑战,而且这种权威在战时环境中保持高度警惕。罗烽在《还是杂文的时代》中说道,延安是政治警觉性表现的最高的地方。因此,对延安政权的阴暗面的揭露和批判,尤其是它在群众中引起的轰动效应,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注意。后来在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对这一局面曾做了这样的评价:1942年,王实味在延安挂帅,他出墙报,引得南门外各地的人都去看。他是总司令,我们打了败仗。我们承认打了败仗,于是好好整风。文学问题一下就转化成政治问题。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从5月27日开始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对王实味、丁玲、萧军、艾青、罗烽等进行批判,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用政治手段,动用权力来解决文学问题,开创了把文学问题和政治问题混为一谈的先河。批判者成了被批判者,成了敌人。丁玲做了自我批判。王实味最后以反党五人集团和托派问题被捕,并于1947年被错误地处决。
这里特别要提一提,在对王实味等人的批判上,运用了群众批判的手段,它不同程度地动员广大群众参加,以会议的形式展开。如对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的批判,当时中央研究院开始以座谈会形式进行批判。座谈会从1942年5月27日开始,到6月11日结束,共开了十六天,其间开了十四次大会。当时会议参加者对6月8日的座谈会做了这样的记述:从早晨七点起,就不断地像潮水一样涌来了一千多个旁听者,他们来自七十几个机关学校在内。一千多个人对一个人批判,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场景!鲁迅曾说:牺牲为群众祈福,祀了神道后,群众就分了他的肉,散胙。不幸,鲁迅的话成了王实味等的谶语,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大陆文坛上对作家和作品时常运用群众批判的手段。当群众在一种权威体制运作下变成一种专制、一种暴力时,它就可能成为一种可怕的力量。王实味等在群众批判下,完全失去了语言的感觉,因为群众批判重复着战斗的刺激的语言,形成一种声势、一种压迫、一种结论。王实味们终于败下阵来。
《野百合花》等杂文的出现,使毛泽东等人认识到,除了政治权威、军事权威以外,还要建立文化权威,而且建立文化权威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中的无产阶级领导的蓝图开始了全面具体的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