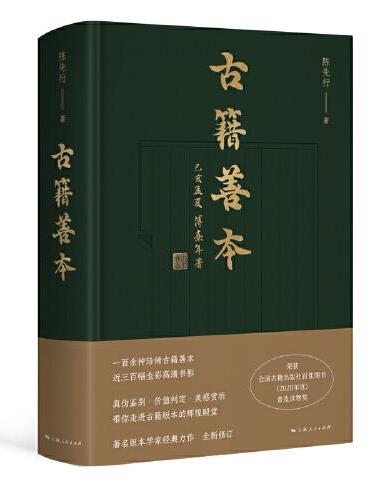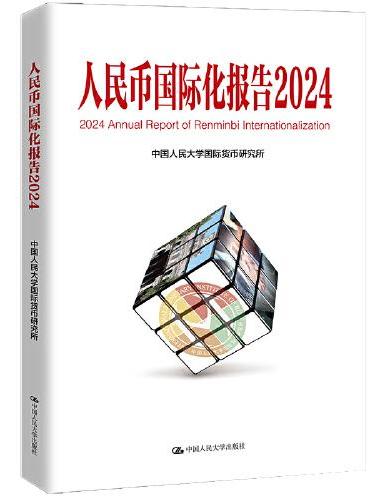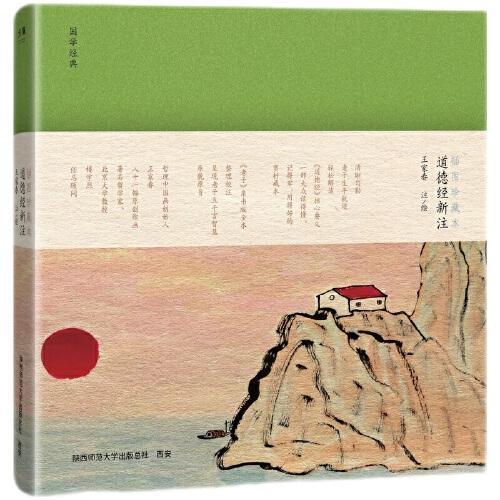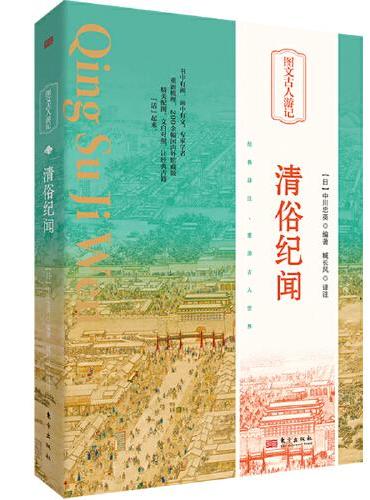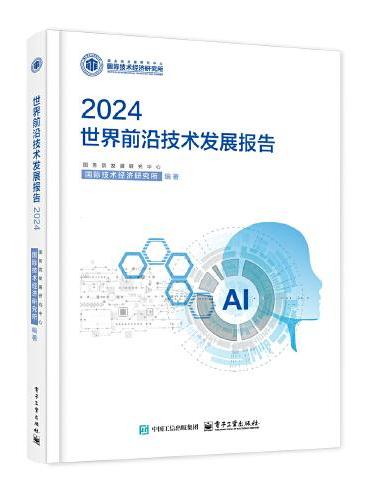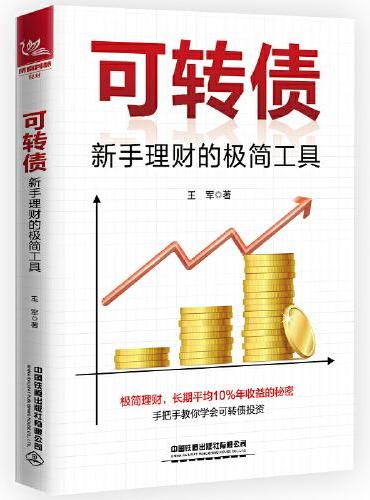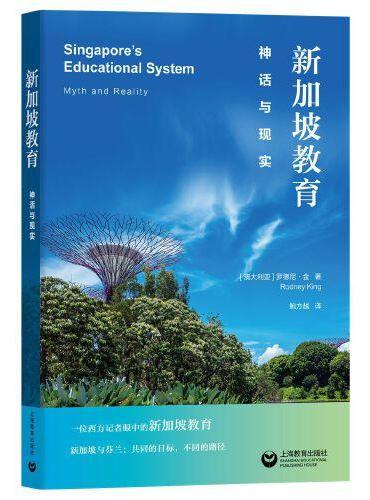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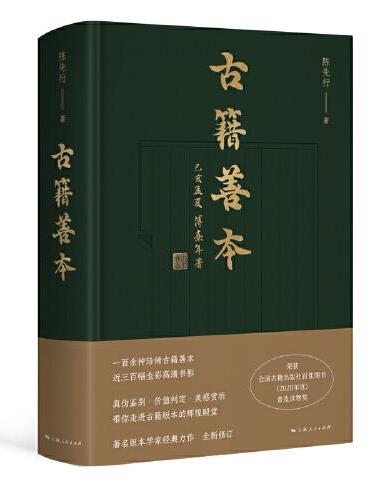
《
古籍善本
》
售價:HK$
53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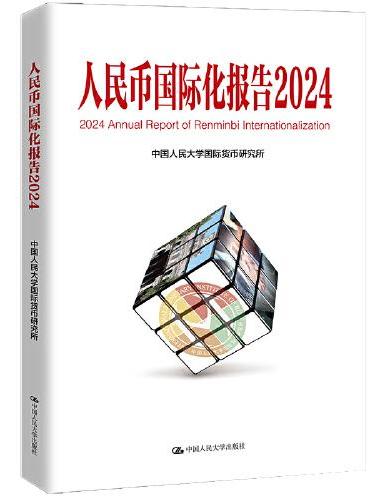
《
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4:可持续全球供应链体系与国际货币金融变革
》
售價:HK$
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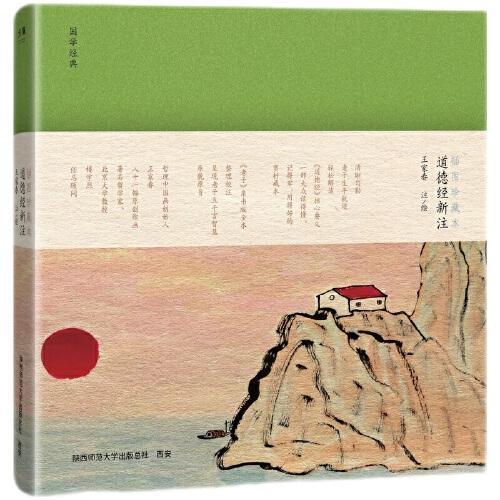
《
道德经新注 81幅作者亲绘哲理中国画,图文解读道德经
》
售價:HK$
14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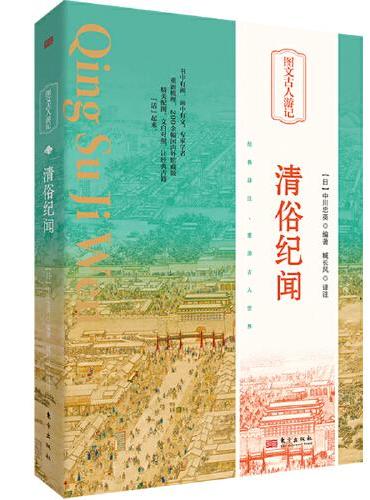
《
清俗纪闻
》
售價:HK$
98.6

《
镜中的星期天
》
售價:HK$
7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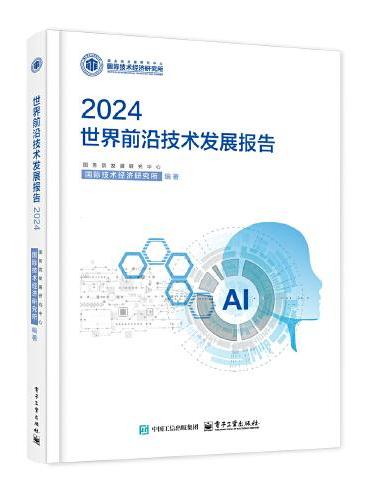
《
世界前沿技术发展报告2024
》
售價:HK$
18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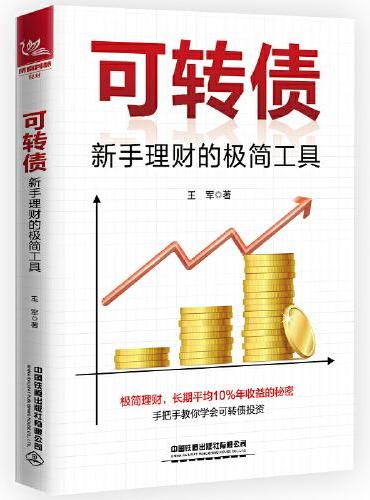
《
可转债——新手理财的极简工具
》
售價:HK$
6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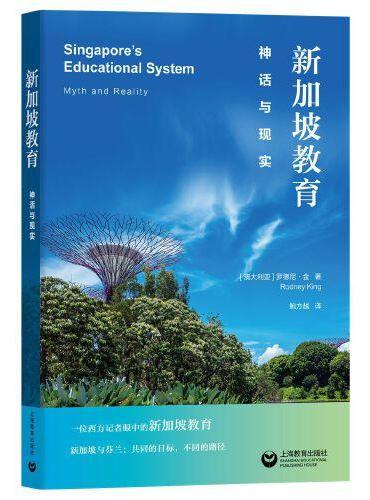
《
新加坡教育:神话与现实
》
售價:HK$
96.3
|
| 編輯推薦: |
☆还未出版便售出全球20余国版权,梦工厂抢先买下电影拍摄权
☆《银河护卫队》知名编剧尼克尔帕尔曼亲自操刀剧本改编。
☆作者弗朗西斯卡海格好莱坞五大经纪公司之一联合人才经纪公司 United Talent Agency签约作家,知名诗人,曾获英国霍桑登文学奖奖学金。
☆比《饥饿游戏》更沉痛,比《移动迷宫》更惊惶,奇幻与科幻二者完美结合的反乌托邦科幻佳作。
☆全美好评如潮,口碑远超《饥饿游戏》、《分歧者》、《暮光之城》等超级IP作品。
☆挣脱即毁灭,你我之间的命运,就是同生共死。面对亲密的仇敌,如何割舍掉令人痛心的牵系,到底要怎样,才能冲破致命的桎梏?
☆这世界于你至美,于我至苦。本是同根生,奈何却相煎?
|
| 內容簡介: |
《烈火的召唤》是海格的奇幻小说处女作,以一对双胞胎之间的致命关联为主线,讲述了同生共死命运下的敌对阵营,试图重建末日后的世界以及为自由而斗争的故事。作者以高度丰满的叙事架构和诗意的语言,构建了一个黑暗与希望交织的世界,引领读者跟随着勇敢的主人公一路冒险,破除桎梏,拯救他们所爱。作品充满了迷人的复杂性,情节变幻莫测,隐秘而深刻的故事氛围贯穿始终,十分引人入胜。
该系列的第二部《人骨地图》目前已创作完成,预计于2016年5月出版。
|
| 關於作者: |
|
弗朗西斯卡海格(Francesca Haig),作家,诗人。墨尔本大学博士毕业,主要研究领域是灾难文学,现任英国切斯特大学高级讲师,好莱坞知名经纪公司UTA签约作家。她曾在澳大利亚与英国的文学刊物上发表多篇诗作,并于2006年出版首部个人诗集《生命之水》,2010年获英国霍桑登(Hawthornden)奖学金。
|
| 目錄:
|
第一篇 监禁
1. 被捕
2. 失落的记忆
3.野心家与毒药
4.告别
5.定居地
第二篇 醒觉
6. 困兽
7. 计谋
8. 水缸密室
9. 黑暗深处
10.艰难的挣脱
11.偷马贼
12.喘息之舞
13.伪装
14.新霍巴特
15.掉头
16.火
17.岛
第三篇 使命
18.不速之客
19.幻象
20.抽丝剥茧
21.靶心
22.血色将至
23.最后的守卫
24.恶梦
25.阿尔法女孩
26.必要的同行
27.沉睡的废墟
28.无路可退
29.温德姆
30.同类的较量
31.共殒
32.扎克
33.西方
|
| 內容試閱:
|
摘录一:
1.被捕
我一直以为他们会在夜里来抓我,而事实上,当六个男人骑着马出现在平原上时,正是白天里最热的时候。彼时正是农作物收获的季节,定居地的人们都早出晚归,日夜劳作。对这块欧米茄人获准居住的贫瘠土地来说,好收成几乎很难出现。上一季的暴雨将深埋地下还没发芽的种子冲得七零八落,结果根菜长得都很小,或者干脆什么都没长。有一整块地的马铃薯都往下长了,躲在肮脏的地表之下五英尺深处,长得瘦小干枯,我们最终还是把它们刨了出来。有个男孩在挖马铃薯的时候淹死了,水坑虽然只有几码深,但土墙塌了,因此他再也没能爬起来。我想过离开这个鬼地方,但所有的山谷都被雨水灌满了,而且在这样一个人人忍饥挨饿的季节,没有地方会欢迎陌生人的。
没法子,我只能留下来,熬过这悲惨的一年。人们在议论大旱灾时期的故事,当时连续三年庄稼歉收。虽然当年我还是个小孩子,我仍然记得饿死的牛群曝尸在尘土飞扬的田野里,尸骨嶙峋。但那是十几年前的事了,这次不会像大旱灾时期那么糟糕,我们如此互相安慰,仿佛这样说多了就会成真一样。接下来的春天,我们细心呵护着地里的麦苗。早熟作物长得都很壮,那一年我们从地里挖出来的又长又胀的胡萝卜,给年轻的半大孩子们带来了不少欢乐。从我自己那块小小的地里,我收获了满满一袋大蒜。我把它抱到集市上去,像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样。整个春天,我看着公共地里的小麦长得又高又壮。在我的小屋后面,一片薰衣草整日被蜜蜂环绕,而在屋子里,食物堆满了架子。
他们来的时候,正是收获期间。我一开始就感觉到了。老实说,我有不祥的预感已经好几个月了。但现在我能清晰地感觉到,突然警醒起来,这种感觉我没法向任何人解释清楚,除非他也是个先知。如果非要描述的话,就像感到某些东西在发生变化,比如云层掠过太阳,或者风突然改变方向。我站直身子,手里握着镰刀,往南望去。当呼喊声从定居地的另一端远远传来的时候,我已经在逃跑了。随着叫喊声越来越大,六个骑马的男人疾驰而来,当他们进入人们的视野时,其他人也开始四散奔逃--阿尔法人袭击欧米茄人的定居地,强抢财物的事并不少见。不过,我知道他们为何而来。我也清楚现在逃跑没有什么意义。妈妈警告过我,但当我注意到时,六个月已经过去了,一切都太晚了。虽然我已经穿过围栏,冲到了布满圆石的定居地边缘,我心里很清楚,他们还是会追上我的。
他们几乎没有减速,就抓住了我。在我奔跑的时候,一个男人直接把我抱起来,带起了我脚底的泥土。他一拳打在我手腕上,我手一松,镰刀掉在地上。接着,他把我脸朝下扔在马鞍前,当我挣扎乱踢时,似乎都踢在马身上,结果马跑得更快了。随着马背不停颠簸,我的肋骨上下撞击,五脏六腑似乎都要颠出来,那感觉比之前挨的一拳难受多了。一只有力的手按着我的背,当这个男人身体前倾催促马向前冲时,我能感觉到他的身体压在我身上。我睁开眼但很快又闭上了,马蹄扬尘,皮鞭飞舞,土地在眼前呼啸而过,这种颠倒错乱的视野可没什么好看。
当我们逐渐慢下来时,我才敢再次睁开眼睛。一把尖刀抵在我的背上,我能清楚地感觉到。
"我们收到的命令是不能杀你," 这个男人说道,"打晕了也不行,你的孪生哥哥是这么吩咐的。但除此之外,如果你要给我们找麻烦,我们可不会手软。我会先切掉你一根手指,办这点事甚至都不用下马,这一点你最好相信。听明白了吗,卡珊德拉?"
我想说"是",结果一口气喘不过来,只咕噜了一声。
马队继续前进。我继续在马背上头下脚上颠簸不休,忍不住吐了两次,第二次吐在男人的皮靴上。注意到这一点,我不免有些得意。男人停下马,一边咒骂不休,一边扶直我的身子,用一根绳索把我捆得结结实实,两条胳膊绑在两侧不能动弹。坐在他的身前,我的血液开始回流到身体里,头脑顿时清醒不少。绳子在我胳膊上勒出印来,但至少让我稳当了不少。男人在后面紧紧抓着绳子的一头,就这样我们一直骑行到傍晚,夜色像套索一样滑落地平线,我们稍作停留,下马吃饭。有个男人给了我片面包,但我没什么胃口,只从水瓶里啜饮了几口温水,有股发霉的味道。接着我又被提起来,这次坐在另一个男人前面,他的一蓬黑胡须扎得我后脖颈生疼。他用布袋套住我的头,但在黑暗中,其实没有多大区别。
早在马蹄声渐渐变响,提醒我们已经踏上砂石修砌的道路之前,我就感觉到了远方的城市气息。透过罩在头上的麻袋布,我开始看到闪烁的光线,感觉到周围的人群,比集市日的黑文市场人还要多,我猜可能有几千人。路开始变得陡峭起来,马队速度减慢,马蹄踏在鹅卵石上哒哒作响。后来我们停下了,我几乎是被扔给另一个人,他拖着我磕磕绊绊走了几分钟,不时停下来开门。每次我们继续往前走时,我都听到门在身后关闭上锁的声音。每次门闩滑回原位的吱轧声就像重重的一击,打在我的心头。
终于,我被推倒在什么柔软的东西上面。我听到身后有金属的摩擦声,那是一把刀出鞘的声音。我还没来得及哭出声,绑在身上的绳索已经被割断,掉落在地。一双手在我脖子上摸索,接着麻袋被人从我头顶扯下来,粗糙的麻布擦伤了我的鼻子。我发现自己在一张低矮的床上,房间非常小。一间没有窗户的牢房。帮我松绑的男人已经出去,回身把金属门锁上了。
我瘫在床上,品尝着嘴里泥巴和呕吐物混合的味道,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一半为我自己,另一半是为了孪生哥哥,他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摘录二:
2.失落的记忆
第二天一早,和往常一样,我从烈火的梦中惊醒。
数月之后,每次从此类噩梦中醒来时,我都忍不住对自己身处牢房禁锢之中心怀感激。小小的房间里光线灰暗,四壁依旧牢不可破,与梦中无边无际狂野残酷的大爆炸景象形成鲜明对比。
关于大爆炸的故事并无书面记载,也没有图画流传于世。当它的印记随处可见时,把它写下来或画下来又有什么意义呢?即使到现在,距离那场毁灭一切的爆炸已经过去四百多年了,从每个破碎的悬崖、烧焦的平原和灰烬堵塞的河流里,仍能看到它的痕迹。它无处不在,已经成为地球能够呈现的唯一故事,别人又为何要费心记录它呢?这段历史已经写在灰烬和尸骨中。大爆炸之前,人们曾谈论着关于烈火的种种,关于世界的末日。后来,烈火终于给出了这场空前绝后的启示。
在大爆炸中幸存下来的大多数人都变成了聋子和瞎子。其他幸存者则往往发现自己已孤身一人,如果他们要讲故事,聆听者只有空气。即使有些人还有同伴,从来没人能准确形容爆炸发生的时刻:天空变了颜色,巨大的声响终结了一切。当幸存者试图描述这段记忆时,就和我一样陷入词穷的困境,只记得那一刻的巨响。
大爆炸震碎了关于时间的观念。在一瞬间,它将历史无可挽回地分成了爆炸前和爆炸后。如今已经过去数百年,大爆炸的幸存者早已不在人世,人证全无,只有像我这样的先知,能够在睡醒之前惊鸿一瞥,或在眨眼的瞬间突然看见耀眼的火光,地平线像纸片一样熊熊燃烧。
关于大爆炸的故事,只在吟游诗人之间传唱。当我年纪还小时,每年秋天经过我们村庄的吟游诗人会歌唱,大意是海洋尽头的其他国度派来天降大火和致命的辐射,以及随后漫长的寒冬。当时我只有八九岁,有一次在黑文市场,扎克和我听到一个灰白头发的老吟游诗人唱着同样的调子,但歌词不尽相同。关于漫长寒冬的副歌部分是一致的,但她没提到其他国家。她唱的每一节都是关于那场大火,描绘它如何吞噬了世间万物。
当我拉着父亲的手问他这件事时,他耸耸肩说,这首歌有很多版本,但那又有什么不同呢?就算以前在海洋那头有别的大陆,现在也已不复存在了,至少所有水手都这么说。关于方外之地和海洋对面国度的传闻不时出现,但也仅是传闻而已,并不比欧米茄自由岛的传言更可信,据说在那座岛上,欧米茄人免于阿尔法人的压迫,过着自由的生活。如果被人听到讨论这类事情,会招来当众鞭打,或者被绑在树干上等死,就像我们曾经在黑文外面看到的欧米茄人,被钉在太阳底下暴晒,直到他的舌头长满鳞片,像从嘴里钻出来的蓝色蜥蜴。两个无聊的议会士兵在旁边看守,不时踢他两脚,以确保他还活着。
不要再问问题,父亲如此警告我,不要问爆炸之前,不要问方外之地,也别问欧米茄自由岛。爆炸之前的人们问了太多问题,做了太多探索,瞧瞧他们得到的是什么?这就是现在的世界,或者说是我们所知的全部世界,北面、西面和南面被大海阻隔,东面是死亡之地。探究大爆炸来自何处已毫无意义,重要的是它发生了。这些都已年代久远,和大爆炸毁灭的史前世界一样不为人知,从此之后只有传言和废墟流传下来。
在牢房的头几个月,我还被准许偶尔放放风。每过几个礼拜,我和其他一些被囚禁的欧米茄人,在众多守卫的监视下,三人一组被带到城墙上稍事活动,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守卫的看管很严,不仅把我们彼此分开,还将我们远离能俯瞰下方城市的城墙垛口。第一次放风,我就学会了不与其他囚徒接近,更别提说话了。当守卫们押送我们从牢房出来时,其中一个家伙抱怨灰白头发、单腿跳行的囚徒走得太慢。"如果你没拿走我的拐杖,我兴许能走快点。"那名女囚徒如此说道。守卫们没回话,女囚徒转头看了我一眼。她的表情算不上是微笑,但却是我进入看护室以来看到的第一丝暖意。抵达城墙后,我试图挨近她说句悄悄话,结果在离她还有十英尺远时,守卫已经把我用力按在墙上,我的肩胛骨撞上石头,附近的皮肤立刻青紫一片。他们把我押回牢房,其中一个冲我吐了口唾沫。"不许跟别人说话,"他说,"瞅一眼也不行,你听见了吗?"我的双手被别在身后,没办法擦掉他吐在我脸上的口水,那玩意儿热烘烘的,让人反胃。自此之后,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女囚徒。
一个多月之后我第三次被带上城墙,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放风。我站在门旁,眯着双眼适应烈日照在打磨的石头上反射的光芒。两个守卫站在我右边窃窃私语。左边20英尺之外,另一名守卫靠在城墙上,盯着一个欧米茄男人看。这个男人在看护室待的时间应该比我长,我如此揣摩。他的皮肤之前肯定是黑色,如今变成了暗灰色。他一直不安地晃动着双手,还有他不停动嘴唇的样子,就像嘴唇安错了牙床一样。从放风开始一直到结束,他都在同一段石墙之间拖着扭曲的右腿来回走动,尽管在上面禁止互相交谈,我仍能不时听到他的喃喃低语,好像正在数数:两百四十七。两百四十八。
大家都知道,很多先知最后都疯了,多年被幻觉侵袭,最终让他们失去理智。幻觉里都是火焰,而我们就像灯芯。这个男人不是先知,但我并不奇怪,任何人在看护室里关上足够长的时间,最终都会疯掉。而我一边要对抗自己的幻觉,同时还要面对牢房冰冷无情的四壁,我又能坚持多久呢?一年或者两年之内,我思量着,我可能变成那个数自己脚步的人,仿佛数字的纯洁能给一个凌乱的头脑带来某种秩序。
在我和测步数的男人之间有另一个囚徒,是个比我大几岁的女人,黑头发,笑脸盈盈,只有一只胳膊。我们俩一起被带到城墙上,这是第二次。我尽量走到守卫能够允许的城墙边缘,一边注视着砂岩筑成的墙垛口外围,一边想方设法试图跟她说话或者传递信号。我离城墙边还不够近,没法完整看到在这座位于山坡顶的堡垒之下,城市是如何的铺开。地平线被城墙挡住了,我只能看到远处灰色的山丘。
突然我意识到数数声停了。当我转身想看看发生了什么时,那个欧米茄男人已经冲向那个女人,用双手紧紧掐住她的脖子。女人只有一只手臂,没办法奋力反抗,也没能及时叫出声来。我还在数码远之外时,守卫已经冲了过去,只用了几秒钟就把男人从她身旁拉开,但已然太迟了。
我闭上眼不忍看她的尸体:脸朝下倒在石板上,脑袋偏向一侧,角度非常奇特。但对先知来说,紧闭的眼睛阻挡不了什么。在我颤抖的脑海里,我看到女人死去那一刻发生的另一件事:就在这座堡垒里,一百英尺的上方,一杯葡萄酒洒落在地,血红色在大理石地板上摊开。一个穿丝绒上衣的男人向后倒去,腿脚挣扎了片刻后便气绝身亡,他的双手最终掐在自己的脖子上。
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去过城墙上。有时我觉得自己听见那个发疯的欧米茄男人在一边怒吼一边捶打牢房的墙壁,但那只是沉闷的击打声,是一种午夜的悸动。我从来都不清楚是真的听到了那声音,还是仅仅感觉到了它。
在我的牢房里,几乎从来没有黑夜。一只玻璃球悬挂在天花板上,它一直亮着,发出苍白的光和轻轻的咝咝声,那声音如此低微,有时我怀疑它只是我自己耳朵里的嗡鸣而已。最初几天,我提心吊胆地注视着它,等着它燃烧殆尽,将我留在彻底的黑暗中。但它并不是蜡烛,更不是油灯。它发出的光与众不同:冰冷而稳定。每过几周,它那毫无生气的亮光才会中断一次,彼时它会先闪上几秒,然后完全熄灭,将我留在无形的黑暗世界中。但每次黑暗的持续时间都不超过两分钟。光会伴随着几番闪烁再度亮起,就像是什么人从睡梦中醒来,接着履行看守的职责。我于是开始逐渐企盼这些间歇的故障,因为它是刺眼而无休止的亮光唯一的中断时刻。
这一定就是电,我如此推测。我听过关于电的故事:它像一种魔法,是大爆炸之前的时代大多数技术的关键要素。但无论它曾多么辉煌,现在都应该不复存在了。在大爆炸中遗留下来的机器,也都在之后的肃清运动中都被捣毁了,幸存下来的人们摧毁了所有技术的产物,他们认为正是这些技术将整个世界变成了灰烬。所有爆炸前的残余之物都是禁忌,以机器为甚。戒律来自于恐惧,所以打破戒律将要遭受的惩罚也是最残酷的。危险牢牢印刻在我们烧焦的世界表面,也印刻在欧米茄人扭曲的身体上。对此我们无须多余的提醒。
然而,现在这里有一件机器,是电力的一部分,正悬挂在牢房的天花板上。它并不像人们私下议论的那样恐怖,也没有多么强大。它不是武器,不是炸弹,也不是离开马匹还能开动的车。这只是一个玻璃灯泡,和我的拳头一般大小,在牢房顶上发着光。我情不自禁地盯着它看。它的中心部位极其明亮,无比洁白,就像大爆炸的火光都被积攒在里面。我盯着它看了太长时间,以至于我闭上眼睛,它明亮的形状仍蚀刻在我眼前的黑暗中。我既着迷又害怕,最初几天在灯光下畏缩发抖,仿佛它要爆炸一般。
令我恐惧的不单单是这光亮本身,而是目睹它意味着什么--这是对戒律的亵渎,一想到这点我就不寒而栗。如果议会打破戒律的消息传出去,人们会掀起另一轮肃清运动。大爆炸带来的噩梦,仍然如此真实,如此深入骨髓,他们绝对无法容忍造成这一切的机器继续存在。因此,我深刻了解到,电灯对我而言意味着无期徒刑:既然我已见过它,他们肯定不会放我出去了。
我无比怀念天空的色彩,比其他任何感觉都要强烈。天花板下有个窄小的通风口,从其他地方引来新鲜空气,但从没有一丝阳光照进来。我只能通过每天两次的进食来计算过了多少日子,每次他们都把盛着饭的托盘从门缝底塞进来。最后一次城墙放风过去数月之后,我仍能在脑海里回想起天空的概念,但已经忘了它确切的样子。我记起大爆炸之后漫长寒冬的样子,当时空气中弥漫着厚厚的烟尘,人们在很多年之后还是无法见到天空。据说在那个时期出生的人,有的到死都没见过天空的样子。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相信天空的存在,在脑海中想象天空的模样对他们而言是否成为一种信仰,就像现在的我一样。
计算我在牢里待了多少天,成为我保持时间观念的唯一方法,而随着总数的增加,它对我而言也成为一种折磨。我并不是在倒数距离出狱还有多少时间,因为那是绝无希望的,只是随着天数不断攀升,同样增加的还有焦虑和不安,就像漂浮在黑暗禁闭的无形世界中。
城墙放风被叫停之后,剩下的唯一定期事件就是每过两个星期,神甫前来审问我关于幻觉的事。她告诉我,别的欧米茄人可见不到任何人。想到神甫的模样,我不知道是该羡慕还是同情他们。
据说双生儿是在大爆炸之后的第二和第三世代才开始出现的。凛冬期并没有双生儿--事实上几乎没有婴孩出生,更别说有人能幸存。很多年间出生的都是残缺的肢体,或者无法辨认形状的死婴。极少数人存活下来,其中的更小一部分能够繁育后代,那时人类看起来真的要灭亡了。
当人类试图从满目疮痍中艰难复苏之时,双生儿的出现,毫无疑问地受到热切的欢呼。有了这么多婴儿,正常存活的比率也非常高。双胞胎总是一男一女出现,其中的一个堪称完美,不仅发育正常,而且健壮活泼。但很快,一种致命的对称性变得愈发明显:每个完美婴儿出现的代价就是他或她的孪生兄弟姐妹,他们天生带着缺陷:残疾,肢体萎缩,畸形有的瞎了一只眼,有的多了一只,有的甚至生来就无法睁开双眼。这些人被称作欧米茄,他们是阿尔法的阴暗面。阿尔法人称欧米茄人是异种,说他们是从母体里排出的毒瘤。大爆炸对人类造成的毒害无法排除,因此便附着在欧米茄人身上。他们承担了异变的后果,从而使阿尔法人得以解脱。
然而,事实并不尽然如此。双生儿之间的区别虽然看上去十分明显,但他们的内在关联则没那么容易辨认。不过,事实每次都无可置疑地证明着这种关联的存在。就算没人能理解个中缘由,结果也并没有什么不同。一开始,人们以为这是巧合,但逐渐地,大量尸体作为铁证推翻了人们的怀疑。双生儿同年同月同日出生,也在同一时刻死去。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离得多远,其中一个死亡时,另一个也会立刻离世。
极端的痛楚,或者严重的疾病,也会影响到他们彼此。其中一个高烧时,不管另一个在哪儿,都会马上体热如火;一个昏迷时,另一个也会失去知觉。微小的伤病似乎传递不了效果,但当一人受重伤时,另一人会因剧烈的疼痛感而尖叫出声。
后来人们发现欧米茄人不能生育,还曾指望过一段时间他们会自然灭绝。人们认为这只是暂时的顽疾,是大爆炸过后的暂时情况。但自此之后每一代人均是如此:双生儿,一个阿尔法,一个欧米茄。只有阿尔法人能传宗接代,但他们生下的每个正常孩子都伴随着一个孪生的欧米茄。
当扎克和我作为完美的一双儿女出生时,父母亲肯定数了又数:四肢健全,十根手指,十根脚趾,全都完好无缺。他们必然无法相信,因为没人能逃离阿尔法和欧米茄的命运。从来没有。欧米茄的缺陷在一段时间之后才显现出来,这种事时有耳闻:一条腿没有跟着另一条同步生长,在婴儿期没有注意到的耳聋,一条手臂发育不良,孱弱不堪。但到处都有这样的传言,据说有很少的欧米茄人从未展现出生理的缺陷:有个男孩一直看起来很正常,直到有一天他尖叫着从屋里跑出来,几分钟之后,房梁突然塌了;有个女孩抱着牧羊狗哭泣,一周之后,邻村一辆马车将这只狗撞死了。这些欧米茄人的突变是看不到的,他们被称为先知。先知非常少见,几千人里才会出现一个。有个先知每月都去下游人口众多的黑文镇赶集,大家都认识他。尽管欧米茄人不允许出现在阿尔法人的集市上,但多年来他获得了接纳,藏在货摊后面,前面摆放着板条箱和成堆的变质蔬菜。我第一次去集市时他已经老了,但还在做他的生意,为农民预测下一季的天气,或者告诉商人的女儿她将会与谁结婚,以换取一个铜币。他一向行为古怪,嘴里不停地念念有词,似乎是什么永无休止的咒语。父亲带着扎克和我走过他面前时,这位老先知大喊起来:"烈火!永恒的烈火!"旁边的摊贩毫无反应,很明显,这种事他们已司空见惯。这是大多数先知的命运:大爆炸在他们脑海里烙下印痕,他们被迫与之共生。
我不记得何时才发现自己的与众不同,但当时我已足够大,知道要将这种事隐藏起来。早些年,我和父母一样毫不在意:哪个小孩从噩梦中醒来不会哭喊尖叫?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我的梦是不一样的:关于大爆炸的梦总是惊人的一致;头一天我梦到一场风暴将至,第二天晚上又梦到风暴降临;我梦到村庄的四十来间石头房子,环绕着中间一口石头砌成的绿井,这些细节和场景远远超出我对村子的认知。我知道的只是这个浅浅的山谷,房屋和木头建成的谷仓聚集在一起,离河边一百英尺远,地势足够高以免洪水侵袭,每个冬天洪水都会给田间带来肥沃的淤泥。而我的梦里满是不熟悉的风景和陌生的脸庞:足有我家小屋十倍高的堡垒,房梁低矮,地面用粗砂铺就;城市的街道比河还要宽,人群熙来攘往。
当我年纪足够大,开始怀疑这一切时,我也知道了扎克每晚都安然入睡,自然醒来。在我们共用的小床上,我教会自己安静地躺着,平息狂乱的呼吸声。当幻象尤其是大爆炸炫目的火光在白天出现时,我学会了不叫喊出声。父亲第一次带我们去下游的黑文镇时,我认出拥挤的集市广场曾在我梦中出现,但当我看到扎克犹豫不前,抓住父亲的手时,我模仿了他慌乱的眼神。
因此,父母亲一直在等待。和所有父母一样,他们只为我俩做了一张床,等着在我们被区分开并且断奶之后,将其中一人送走。一直到三岁,我们仍然无法分辨,于是父亲为我们做了一对大点的床。尽管我们家的邻居米克的木工手艺在山谷里名闻遐迩,这次父亲并没有找他帮忙。他独自一人躲在厨房窗外,在有围墙的小院里偷偷做了这两张床。之后几年间,每次我那张腿脚不齐的小床嘎吱作响时,我都会记起父亲第一次拖着这两张床进屋时的表情,他把两张床尽量分开,直到几面窄墙能容忍的极限为止。
父亲和母亲从此很少跟我们说话。那正是大旱灾时期,每样东西都要定量供应,在我看来,连言语也开始变得匮乏。在山谷里,以往每个冬天低处的田地都会被洪水淹没,而如今河水变成不起眼的涓涓细流,两岸的河床像古老的陶器的皲裂表面一样。我们这个一向宽裕的村子也没什么余粮。头两年收成都很差,第三年滴雨未下,庄稼全都枯死了,我们只能靠往年的积蓄维持生活。干瘪的田地被尘土侵蚀,不少家畜都死掉了,这年景就算有钱也买不到饲料。遥远的东方传来人们饿死的故事。议会派人到各个村庄巡逻,防范欧米茄人突袭劫掠。那年夏天,他们绕着黑文镇和其他阿尔法人的大型城镇建起了围墙。那些年我见过的唯一一群欧米茄人,去往收容所途中时经过我们的村子。可是他们看起来又瘦又累,无法对任何人造成威胁。
旱灾结束之后,议会的巡逻仍然延续下来。父亲和母亲也没有放松警惕。我和扎克之间最细微的不同都被抓来认真解析。当我们都染上冬热病时,我偷听到父母在长篇累牍地讨论是谁先生病的。那时我已经六岁或者七岁。透过卧室的地板,我听到父亲的声音从下面的厨房传来,他坚持认为我头天晚上看起来脸有点红,十小时之后扎克和我醒来时,都已经烧得非常厉害。
也就是在那时我才意识到,父亲对我们的谨慎是出于怀疑,而非是因为惯常的粗暴脾气;母亲一贯的关照中除了母爱,还有些别的复杂感情。扎克曾经整天跟在父亲屁股后面,无论是去水井,还是去田里或者谷仓。随着我们年纪渐长,父亲在我们面前变得易怒而警觉,他开始把跟在后面的扎克赶跑,冲他大吼大叫让他回家里去。然而扎克一有机会,仍然会找借口跟在父亲身后。如果父亲在上游的灌木丛里捡树枝,扎克会拉着我跑到那儿采蘑菇。如果父亲在地里收玉米,扎克会突然热心起来,跑去修理通往旁边牧场的栅栏门。他会保持一段安全距离,但一直尾随着父亲,就像一个错位的影子。
晚上当父亲和母亲在议论我们时,我会紧紧闭上双眼,好像这样就能把透过地板传来的谈话声挡住一般。我能听到扎克在对面墙边的床上轻轻动弹,呼吸声不紧也不慢。我不知道他究竟是睡着了,还是在假装而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