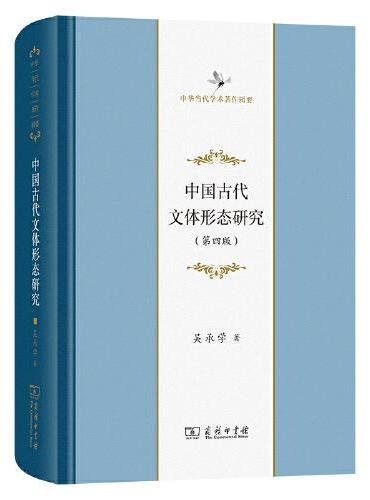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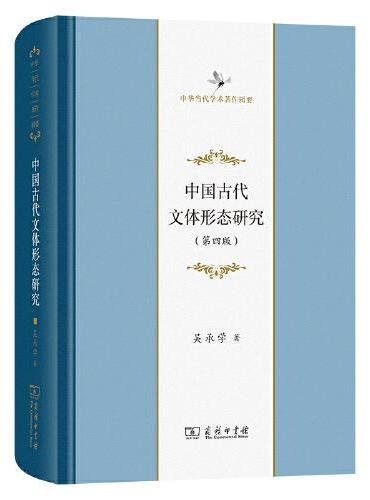
《
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第四版)(中华当代学术著作辑要)
》
售價:HK$
168.0

《
朋党之争与北宋政治·大学问
》
售價:HK$
99.7

《
甲骨文丛书·波斯的中古时代(1040-1797年)
》
售價:HK$
88.5

《
以爱为名的支配
》
售價:HK$
62.7

《
台风天(大吴作品,每一种生活都有被看见的意义)
》
售價:HK$
53.8

《
打好你手里的牌(斯多葛主义+现代认知疗法,提升当代人的心理韧性!)
》
售價:HK$
66.1

《
新时代硬道理 广东寻路高质量发展
》
售價:HK$
77.3

《
6S精益管理实战(精装版)
》
售價:HK$
100.6
|
| 編輯推薦: |
作者是一位奇人:历经清朝、民国、新中国,作品曾被私人收购、焚毁,成为民间禁书史上奇观。
本书是一本奇书:首部翔实记录旗人命运的长篇京味小说,一段民国版“茶花女”的爱情奇遇。
本书记载的是一部奇史:书里真切细腻地再现了百年前老北京的社会风貌,还有一个理想主义者想要改变中国的心路历程。
正如本书编者陈均所言:这本书写的是世相(社会小说),但探寻的依然是从古至今的知识分子之寄托:这个社会为何会堕落,而且还将堕落下去?理想的社会到底在哪里?
|
| 內容簡介: |
满族青年宁伯雍留学日本六年,回国后遇上辛亥革命,听说老同学在前门外经营《大华日报》,便去求职,成为记者。
从京郊到城里后,宁伯雍看到了一个日益变化的北京城。他在龙泉寺认识了梆子小花旦白牡丹,并与沛上逸民等人组织团体捧白牡丹。从此白牡丹渐渐走红,后被维二爷独占,厌弃宁伯雍等人。宁伯雍又认识了妓女秀卿。秀卿对高官富商冷眼冷语,对宁伯雍却另眼相待,两人渐生情愫。秀卿不幸患病,临死前将母亲和弟弟托付给宁伯雍……
|
| 關於作者: |
穆儒丐:中国现代史上最早的白话小说家之一和享誉一时的剧评家。1884年(也有一说为1883年)生于北京西郊香山的旗人家庭。1905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11年回国。1916年至沈阳。1945年返回北京,先后从事秘书、教师、报纸编辑等职业。1953年被聘为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1961年2月15日逝世。著有数量众多的小说、随笔、戏曲评论和岔曲作品,但因其特殊的经历,被后人所忽略。
陈均: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编订朱英诞、穆儒丐、顾随等作家的作品及京昆史料文献多种。出版有专著《中国新诗批评观念之建构》、《京都聆曲录》及诗集《亮光集》、小说《亨亨的奇妙旅程》等。
|
| 目錄:
|
第一章 021
第二章 040
第三章 069
第四章 084
第五章 107
第六章 130
第七章 153
第八章 164
第九章 176
第十章 194
第十一章 206
第十二章 220
第十三章 237
第十四章 252
第十五章 278
原书序跋 283
|
| 內容試閱:
|
民国元年三月,在由西山向青龙桥[青龙桥:位于今颐和园北宫门外,为明清以来由西山通往海淀的交通要道。1900年,八国联军入京时,慈禧太后即经由此桥出京,仓皇逃往山西。]的道上,有一个青年,骑着一头驴,年纪约有二十八九岁,他在驴背上,态度至为闲雅,不住地向北山看那仲春的景色。在他所骑的驴前面,另有一头驴,驮着他的行李。驴后面跟着两个村童,手内替他提着小皮包,一边叱着驴,一边还玩耍。青年也不管他们,只顾看他的山景。
这时约有午前十点余点,前两天的春雨,把道路洒得十分洁润,一点尘土也扬不起。那山上草木,被雨沾润,都发了向荣的精神,一阵阵放来清香,使人加倍地爽快。那道路两旁的田间,麦苗已然长起来了,碧生生的一望无边,好似铺了极大的绿色地衣,把田地都掩盖住。驴子所经过的地方,时时有成双成对的喜鹊,由麦田里飞起来,鸣噪不已地飞到别的田地里去。赶驴的小童,见了这些喜鹊飞鸣,便由路上拾起石子,追击它们为戏。
那山麓间的农村,也有用秫秸围作墙院的,也有用天然石筑成短垣的,院子里面都栽着小枣、山桃、苦杏等树。那桃、杏树已然开了花,红白相间,笼罩着他们的茅屋,衬着展然欲笑的春山,便是王石谷[
王石谷,即王翚(1632─1717),常熟人,被称作“清初画圣”,与王鉴、王时敏、王原祁合称山水画家“四王”。
]所画的《杏林归牧图》,也无此风致。
如今利用这青年在路上行着,且叙叙他的家世。这青年,姓宁名和字伯雍,上有父母,下有兄弟,世居这西山麓下,虽无多余财产,却世世守着几本破书。伯雍幼时,由小学而中学而高等,受了几年良好教育,陶铸的品行学问[ 指造就出很好的品行学问。
],很有出人头地的地方,因为公家有考送留学生之举,他却考中,便送到东洋学了几年法政。如今他才卒业归国,没有半年工夫,便赶上革命的动乱,他无心问世,便在山林里,奉着他的父母隐居起来。伯雍为人,并不是不喜改革,不过他所持的主义,是和平稳健的。他视改革人心、增长国民道德,比胡乱革命要紧得多,所以革命军一起,他就很抱悲观。他以为今后的政局,不但没个好结果,人的行为心术,从此更加堕落了,所以他甘心隐居,不问世事。这时他的父母,见他已然老大不小,便把头五六年给他定的媳妇娶了过来。且喜这位娘子,倒也贤慧,能够体贴丈夫意思,上事翁姑,下和兄弟,家庭之间,总算幸福不浅。这时有近畿一旅军队,营长等中上级的军官,都和伯雍有乡谊,而且还有许多同学的,知他在家赋闲,便聘他来掌书记。
伯雍因为在家白闲着,终归是闲不起,没法子只得受了人家聘书。好在做幕的勾当,名义上还清高一点。当下禀明父母,择个日子,到军营里给人家做书记去了。他以为这些军官,除了同乡就是同学,自然容易处的。谁知这些老爷大人们,在军营里染了满身骄傲脾气,动不动以阶级压人。伯雍初到营时,多少还受点礼遇,过了二十天一个月的,也就不拿伯雍当事。有时大家一起闲谈,还指桑说槐的,把书呆子贬得一文不值。他们说念书好一点的,总要带一贴[ 一贴:量词,一张一块。
]酸狂样子,看不起人,照伯雍这样纯厚端庄的,也太少了。可是如今看不起人的穷酸,要想当个司书生,都没人要。当初被他们看不起的人,如今倒大马长刀,当了营长、团长,还有当旅长的,这不上天睁开眼睛,无形中惩治他们一下子吗?说到这里,许多老爷大人总要哈哈大笑,并且有的说:“这些穷酸也不能办什么大事!他们的材料,自能当个司书生,不致饿死,也够他们享受的了!”
伯雍听了这些话,自然有些不愿意。虽然目下念书的不值钱,也不应当这样作践。何况当初都是村学房圣人龛下一同长起来的,便是如今所业不同,有幸不幸之分,也不可因为自己地位一时比人家强,便这样肆口奚落,未免使人太难堪了。从此伯雍不愿在军营里做那会使笔的奴隶。有一天,他给营长留下一张辞呈,卷了铺盖,竟自回家去了。次日营长回营,知道伯雍已然辞了差使,还打发副官到伯雍家里挽留一次。伯雍婉言谢绝说:“贱质不惯于军营生活,诸君抬爱,异日再补报吧!”副官无法,回复营长另聘高明去了。
这是还没改民国那一两个月内的事。转过年来,便是民国元年,伯雍依然在家赋闲。假如他有相当的不动产,丁[ 丁:遭逢。
]此大革特革时代,他一定不会出来的。在山里头侍奉父母,闭户读书,老老实实当一辈子山农,也就够了。无奈他房无一间,地无半亩,仰事俯畜,不能不另谋生计,长此家居,终非了局。可巧这时有同窗友人,在前门外开了一家报馆,定名《大华日报》。两个经理,正经理白歆仁[ 白歆仁:为穆儒丐友人乌泽声在小说中的化名,详情另述。
],副经理常守文,都是新被选的众院议员,一个加入国民党,一个加入进步党,当初他们都是很有志气的青年,如今荣膺民国代表,在议会里很占一部分势力,由党部支了一笔补助费,开张了这家报馆。伯雍听说他们的报销路还不坏,打算在他们报馆里卖文为生,或者充任一员编辑亦可。于是他给歆仁去了一封信,说明所以。歆仁素日很知道伯雍的笔墨有两下子,假如得他来帮忙,于报纸声价不无小补。而且伯雍为人狷介,最不爱提钱字,较比他人,容易打发,一举两得,有何不可?何况他来求我,我没去邀他,日后的薪金大小,他不能与我争执了。主意拿定,便给伯雍去了一封信说:“你命令我的事,已然和同人说好了,请你赶快到馆,襄助一切。”伯雍见字,收拾进城。前面所述,正是他雇了驴子,进城上报馆的那一天。
伯雍一边催促着驴,一边看那山村景色,不知不觉,已然到了万寿山[ 万寿山:燕山余脉,颐和园内,昆明湖前。
]。他由驴上下来,付了驴钱,招呼了一辆车,言明雇到新街口,二十五枚铜元。到了新街口,他多给拉车的五枚,说:“我多着一件行李,这五枚给你打酒喝吧!”拉车的道声谢,接了钱,用条破手巾,不住擦他脸上的汗。伯雍在一旁看着,老大不忍,暗道:“小二十里路,给他三十铜子,还很高兴。可见出汗赚钱,过于不易了。”这时伯雍方要再呼一车,到宣武门外去。那拉车的见伯雍还要出城,又知他肯多花钱,便说:“先生!不必另雇车了,我送你去就完了。”伯雍说:“你已然出了一身汗,跑了二十来里路,再到南城恐怕你的力气来不及。”这时那车夫已然把汗擦干,喘息定了,连说:“行行!三四十里算什么,我就怕不挣钱!道路多跑,倒不在乎。先生,你上车吧!”伯雍说:“你既然愿意去,我仍坐你车去吧,省得费事。”当下告诉他什么地名。伯雍方要上车,这时在街心上,早拥来许多辆车,一个个你一言我一语,都说:“先生别坐他的车了,他已然跑不动了。”这个拉车的见大众车夫抢他买卖,便大声说道:“谁跑不动!有敢跟我赛赛的么?”还是伯雍排解了几句,别的拉车的才散了。当下上了车,那车夫拉起来便跑。伯雍说:“你倒不必快跑,我最不喜欢拉车的赌气赛跑,你只管自由着走便了。”车夫见说,果然把脚步放慢了些。此时伯雍在车上问那车夫道:“你姓什么?”车夫道:“我姓德。”伯雍道:“你大概是个固赛呢亚拉玛[ 固赛呢亚拉玛:旗人。此为满语汉译之词。
]。”车夫说:“可不是,现在咱们不行了。我叫德三,当初在善扑营[
善扑营:清代禁卫军之一。“善”即“擅”之意。擅长相扑的人编为军营,即善扑营。清亡后,善扑营解散,扑户们无以为生,或设馆教授摔跤,或设场卖药,或拉人力车,或卖苦力,或流浪街头。
]里吃一份饷,摔了几年跤,新街口一带,谁不知跛脚德三!”伯雍说:“原先西城有个攀腿禄[ 攀腿禄:清末善扑营扑户名单中有“搬腿禄”。
],你认识么?”德三说:“怎不认得!我们都在当街庙摔过跤,如今只落得拉车了,惭愧得很。”伯雍说:“你家里都有什么人?”德三说:“有母亲,有妻子,孩子都小,不能挣钱。我今年四十多岁,卖苦力气养活他们。”伯雍说:“以汗赚钱,是世界头等好汉,有什么可耻!挣钱孝母,养活妻子,自要[ 自要:只要。
]不辱家门,什么职业都可以做。从前的事,也就不必想了。”德三说:“还敢想从前!想起从前,教人一日也不得活!好在我们一个当小兵儿的,无责可负,连庆王爷还觍着脸活着呢。”这时德三已然把脚步放快,他们二人已无暇谈话。伯雍抬头看时,已然到了西四牌楼。只见当街牌楼,焦炭一般,兀自倒在地下,两面铺户,烧了不少,至今还没修复起来。这正是正月十二那天,三镇兵士焚掠北京的遗迹。
伯雍看了这些烧残的废址,他很害怕地起了一种感想:“这北京城自从明末甲申那年,遭了流贼李自成一个特别的蹂躏,三百来年,还没见有照李自成那样悍匪,把北京打破了,坐几天老子皇帝。便是洪杨那样厉害,也没打入北京。不过狡猾的外洋鬼子,乘着中国有内乱,把北京打破了两次,未久也就复原了。北京究竟还是北京。如今却不然了,烧北京打北京的,也不是流贼,也不是外寇,他们却比流贼外寇还厉害!那就是中国的陆军,当过北洋大臣、军机大臣,如今推倒清室,忝为民国元首,项城袁世凯的亲兵。项城先生是北洋派的领袖,国家陆军多半与他有关系。如今他的兵,在他脚底下,居然敢大肆焚掠,流贼一般的饱载而去。此例一开,北京还有个幸免吗?哎呀!目下不过是民国元年,大概二年上就好了,二年不好再等三年,三年不好,再等四年。四年不好,再等五年。五年不好,再等六年。六年不好,再等七年、八年、九年……若仍见不出一个新兴国家样子,那也就算完了。”伯雍一边感想着,一边替未来的北京发愁。他总想北京的运命,一天不如一天。他终疑北京是个祸患的症结,未来惨象比眼前的烧迹废址,还要害怕得多。他终以北京是不可居的,还是在西山寻个无人所在,韬晦起来,较着平安。但是他房无一间,地无半亩,仰事俯畜,都得现抓。为饥所驱,遂把伯雍一个志行高洁、有意山林的青年,仿佛用鞭子赶到猪圈里去。他明知道一入北京,人也得坏,身子也得坏,耳目所接,一定不如涧边清风、山间明月,但是无论怎样与志相违,终是不能不到北京城里去,他的境遇也就很可怜了。
伯雍在车上不住感想,车夫德三在马路上不住飞跑。少时已出了宣武门,进了西茶仓胡同,伯雍才把他的思潮打住。又走了半里多路,进了一条僻巷,早见一个如意门,两边青灰墙上,写着老大白字:大华日报社。伯雍教车站住,下了车,教车夫把行李搬到门洞内,然后递给德三一张五吊钱的票儿,德三千恩万谢去了。伯雍来到门房,只见有三四名馆役,正在炕上躺着睡觉。伯雍叫了几声“借光”,才有一个由炕上爬起来,蒙眬着眼睛,懒恹恹地问伯雍说:“你是做什么的?”伯雍当时取出一张名片说:“烦劳通禀白先生一声,就说鄙人求见。”那馆役此时仍是懒洋洋的,仿佛再睡一会儿才好呢,所以他很愿意来客赶紧就去了,他好再睡。只听他打着呵欠说道:“你要见总理么?总理没在报馆。”说罢似仍然要去睡觉。伯雍见这馆役的神气,待理不理的,知他为睡魔所困,想是昨夜不曾睡觉,也不嗔怪于他,只得把自己来历说了一番,并不是寻常拜访,特来到社做编辑的。那馆役见说,少微[ 少微:稍微。
]把精神一振,说:“你先生在此等一等,我去回一回账房的经理。”当下他拿了伯雍的名片进去了。不多时出来,和伯雍说:“请进去吧。”伯雍随他进去,走入一个木板屏门里面,却是坐西五间正房,南北各有两间厢房,院子没有一把掌[ 把掌:巴掌。
]大,被四面房屋欺得连太阳光也得不着。馆役把伯雍让到南厢房里,里面也有几件木器,最重要的是一个铁柜,证明此处是报社的“财政部”。随墙放着一张木床,上面放着烟具。早有一个极瘦的人,由床上站起来,向伯雍一拱手,做出笑脸来说:“伯雍先生请坐请坐,我常听我们总理提你先生,兄弟很是久仰的,头几天总理跟我们说,已然把你先生约来帮忙。好极了!活该我们的报纸应该发达!”这时伯雍一边还礼,一边问那瘦人说:“阁下贵姓?”那人说:“贱姓吕,草字子仙。”伯雍说:“久仰久仰。”于是二人就木床上对面坐下,彼此周旋几句。吕子仙烟瘾未足,仍旧躺下吸烟。吸了两口,问伯雍说:“伯雍兄于此怎么样?”伯雍说:“倒是喜爱,还没尝试过。”子仙说:“不吃甚好。兄弟一生事业,便为这东西给耽误了。假若我不吃烟,内阁总理也敢去做。”伯雍说:“现在阔人,谁不吃烟?皆因吃烟才能做总理。照我们不吃烟的,也无非给人家卖卖胳膊[ 卖卖胳膊:靠体力劳动为生。
]。自目下看起来,究竟是没出息的人,吃大烟才能表示有做阔事的资格。”吕子仙见说,不禁大笑说:“伯雍你这样一个人,还会说笑话。如此看来,我这烟倒得足吸一气。”他又连吸了五六口,精神比从前大了些儿。伯雍细看他时,虽然瘦得不成样儿,眼睛里却含着机警的神气。歆仁既然用他当账房经理,想必是歆仁的心腹,可以无疑了。
此时外面已有午后四五点钟,伯雍一个山居的人,起得绝早,自然早晚饭也早些。他此时因为行了三十多里路,虽然骑驴坐车,未免有些劳乏,肚子里尤觉饥饿,可是报馆里静悄悄的,一点声息也没有,厨房里也不见有什么动静。吕子仙把烟吃完,才叫馆役打水,漱口净面,原来他才起床不大会儿。伯雍无法,初来乍到,也不能便要饭吃,只得向吕子仙说:“兄弟下榻地方,想是预备出来了?”子仙道:“头几天便预备好了。”说着叫来一个馆役,把伯雍带到寝室,却是那五间上房,南套间里。伯雍到了套间一看,沿窗放着一张书案,案面上蒙的绿呢,已然看不出本色,一块黑、一块黄、一块红的,还有一圈一圈的茶污。那纸烟的烧迹,比马蜂窝还密。案头沿墙去处,放着一个书架,尘土积得有一钱多厚。挨着后檐墙,两条长凳,架着一张藤织床面。他的行李,已被馆役堆在床屉上头。此外别无陈设。惟有那墙上,因为潮湿,把糊纸霉得都变了颜色,一块一块的霉湿阴晕,蔽满了四壁,隐隐现现的,好似郭河阳[
郭河阳:即郭熙,北宋著名山水画家,有《早春图》《窠石平远图》《幽谷图》等传世,其画山石多用卷云或鬼脸皴。
]云山的蓝本。
伯雍一见这屋子,也就明白他后来的运命了。他没法子,把行李打开,向馆役要了一把掸子,把案子和书架打扫打扫,把自己带来的几本破书,放在书架上,然后把铺盖就床上叠起来。他略微休息休息,又到外屋去看一看。外头四间,却隔成两间。堂屋临窗,也是一个大书案,上面放着文具,它那墨污的程度,比套间那张还厉害。挨着西墙,放着一张榆木擦漆的方桌,一边放一把旧式大椅。此外有许多报夹子,架着那些交换报。伯雍暗道:“这间一定是编辑部了。”那北屋屋门上,挂着一张青布帘,下面犄角不知被什么烧去半边。上面的污垢,与书案上的绿呢面,可称双绝。此时伯雍知道屋里必然无人,因为过于寂静了,他遂把门帘揭起,到这屋里一看。两张床上,都放着油污的寝具,大概是底下人的。他一想:“不能,底下人自有下房,这里明明是上房,怎能住底下人呢?一定是编辑先生卧榻了。”这屋窗前,也一样放一张书案,文具倒很齐备。伯雍把各屋参观已毕,他的感想,也不知是喜是伤。
只见他点点头,仍回到自己屋中。他此时饿极了,听一听厨房那里还没信,也没人来问他开饭不开饭。他暗想道:“大概饭时还早,别教老肚埋怨我了,应当吃点什么才对。”想罢,取出二十枚铜子,喊了两声“来人”,却不见有人答应。他不由暗想道:“我叫‘来人’,他们或者不愿意,叫他们一声‘馆役’试一试。”也不见答应。伯雍无法,又叫一声伙家,就短叫大哥、先生了,却仍不见有人答应,气得伯雍无法,暗道:“他们真会欺负人。我新来的人,就不配使令你们么?我自己有腿,会外头去吃饭。”当下要出去吃饭。只听厢房里吕子仙喊了一声“来人”,遂听门房那边四五个人一齐答应了一群:“是。”随着就听有一个人,连忙跑过去。只听吕子仙和那人嚷道:“你们都干什么来着?上屋叫半天人,怎么一个答应的也没有,快过去问问什么事!”没一会儿,果见一个馆役,到伯雍屋里问说:“先生有什么事吗?”伯雍本来有着气,要出去吃饭,如今见一个馆役跑了过来,当时把气减了许多。及见那馆役问说:“有什么事吗?”只得把那二十枚铜子交给那馆役,说:“求你到外头给我烙一斤饼,买一吊钱酱肘子来。”那馆役见说,接钱去了。此时伯雍倒不禁好笑起来,暗道:“这些馆役,怎这样不知自爱?我叫了半天,却一个答应的没有。账房经理不过哼了一声,五六个人,一齐答应。不用说他们心里就知有总理、经理,把别的先生自然看不到眼里。小人常态,大抵如此,姑且不必与他计较。等日后手内富裕,给他们几个零钱花,也就不能呼应不灵了。”
正自想着,那馆役已然把饼烙来,伯雍趁热,卷了酱肘子,饱餐一顿。因为他饿极了,在乡下时,哪里这晚[ 这晚:这么晚。
]吃过饭?他吃完了,电灯早来了,俗语说得好:吃饼,离不开井[ 北京土语,意为饼吃多了口渴。
]。他此时已然不敢教馆役替他泡茶,生恐碰钉子。幸亏他还明白,仍跑到吕子仙屋中。子仙一见他,便说:“你自己买饭吃做什么?咱们馆里有的是厨子,饿了自管分付[ 分付:吩咐。
]他。”伯雍说:“为我一个人,也没有开饭的道理。再说饭时未到,不可破例,此时我倒很渴的了。大哥!你教他们给弄壶水来喝。”子仙说:“那容易。”只听他沉着声音叫声“来人”,门房那边又“嗡”的一声,有五六个人答应起来,比司令官的命令还有效呢。随即有个年青的馆役,年约十八九岁,面皮挺俏皮的,跑过来问有什么事。子仙说:“你去给泡壶茶来,拿好叶子。”那馆役见说,由一张抽屉柜内取出两罐茶叶,问用哪个。子仙说:“糊涂!拿一包给总理喝的。”那个馆役又由别的抽屉内,取了一包茶叶,拿了茶壶去了。少时,把茶泡来,给伯雍和子仙,每人斟了一碗,却站在一旁。这时子仙又躺在床上,弄他的大烟。伯雍乏了,也躺在对面,因问子仙说:“馆里什么时候办事?怎么这时候编辑部里还冷清清的?”子仙说:“每日吃完晚饭才办事呢。这时候稿子也不能来,所以他们吃了早饭,便都出去瞎跑,有听戏的,也有看朋友的,待一会儿,就热闹了。串门子的也都晚上来,完了事,还可出去逛逛胡同,打八圈麻将什么的。你如今入了报馆很好,究竟比你老在乡下强得多。”伯雍一听,便有些害怕,暗道:“晚间办事,已然是没益处了。办完事,还打麻将逛窑子,那一夜还有睡觉的时候么?”
他正自寻思着,早听院中有了脚步声音,也有不等进屋子,便喊叫开饭的。一阵说笑,都奔上屋去了。此时子仙因向伯雍说:“你去看看去,他们都回来了。”伯雍道:“兄弟与他们诸位还没会过面,求老兄给介绍一下子,我们好同手办事。”子仙说:“好,我同你过去。”当下吕子仙同着伯雍到了上屋的编辑部,先和二位住馆的编辑先生见了面。一位姓张名瑶,字子玖,直隶人。一位姓王名桐,字凤兮,京兆人。这二位都是三十上下的岁数,子玖先生还是前清的一位孝廉公,他们都彼此交换了名片。另有二位少年,一位是韦少卿,一位是讹若士。若士是江苏人,生得和女孩子一样。少卿倒是北京人,很有文名的,不过有些怪僻性质,人人都说他狂傲。他们二人,都在《民德报》当编辑,在这边也帮忙,所以先到这边来发稿子,完了再回那边去。少年人如此用功,也是很可佩服的了。
吕子仙一一替伯雍介绍完了,仍回自己屋中去了。此时他们几人初次对面,自然要说些久仰的话。虽然彼此闻名,当然不必拘泥,这时也不得不略事谦抑。可是十句话过来,他们便大讲特讲起来。张子玖此时得意扬扬地说他方才在茶室里挑了一个姑娘:“别提多好啦!头是头,脚是脚,才十八岁。明天一定要去住局[ 住局:嫖客在妓院里过夜。
],皆因她待我太好了!头一天招呼,竟会有这样的劲儿。”伯雍见子玖差不多有四十来岁了,身上的衣服,脸上的气色,在窑子里,似乎得不了什么待遇。他为什么这样入迷呢?或者他特别有此嗜好。这时只见韦少卿指着张子玖说:“老张,你大概又提起你那窑案了。我一听这事我脑袋就疼!窑子里哪有有情的人?再说你逛窑子,也不讲什么品题,自要肯留髡[ 留髡:原意为留客,此处指嫖宿。
]的。在你就算遇了神仙,你不过恣行肉欲,在我们跟前卖弄什么,我们不爱听。”这时讹若士方在据案大书,把十几张宣纸信笺,已然用秃笔给抹得不成模样。听了韦少卿奚落张子玖,他便把笔一投,鼓掌大笑起来。完了又附和着少卿说:“老张逛窑子,跟猪八戒玩老雕一样,什么人玩什么鸟![ 歇后语。指一个人的爱好体现了他自己的性格与修养。
]”此时张子玖脸上有些红了,可是假做笑容,和他们辩道:“我天天逛窑子,也不是去言情,不过大爷玩乐,聊以解忧。我比不起你们,你们都是宝哥哥林妹妹一流人物,不妨彼此言情,我跟谁言去呢?只可到二等茶室里去物色知音。”旁边王凤兮怕他们越说越深,只得从旁取笑说:“算啦!算啦!子玖如不弃嫌,我当你的宝哥哥如何?”大家不禁大笑起来。这时只见进来一个馆役问说开饭不开,凤兮说:“快开吧!早就饿了。”馆役见说,遂把外屋那张方桌放在当地,安了五个座位。伯雍已然吃过饭,只得陪他们坐一坐,凑个热闹。大家吃完饭,便去预备发稿。伯雍头一天到馆,也不知做什么功课,只在旁边看他们做活。只见他们把通信社的稿子,往一块粘了粘,用朱笔乱抹一气,不够的,便拿了剪子,向交换报上去寻。不大工夫,新闻电报都算有了,交给馆役往印刷所送。他们腾下手来,又作论说时评,还要来两首诗。伯雍在旁边看着,却很惊讶的,这样忙忙乱乱的,胡抓一气,居然也能出两大张报,却是不易了。伯雍正自参观编辑事务,只见进来一个馆役,向他说:“总理来了,请您过去呢。”伯雍见说,随那馆役去了。原来这报馆却是两个院子,由厢房旁边一个小夹道,便可以通过那边。那边也另有大门,因为欲图两院的联络,所以生辟了这一条小径,为是方便,可是总理过这边来的时候很少,都是由这边往那边叫人,所以这边的情状,总理很难赏下贵目的。
白歆仁每天到议院里去出席,散了会,还到党部去办公,最后才到报馆来。每天头一段紧要新闻,虽然关系国家大事,可是在总理看去,却是关系报馆的生死,也是他一身升沉之所系,所以等闲不肯交给编辑去做,总是他自己捉笔。他每天除了做第一条要闻,还要审查别的稿子,生恐有不谨慎的地方,所以他很觉得劳累。此刻他才由党部里来,知道伯雍到了,旧日老同学,当然要请过来一叙。
伯雍随那馆役进了夹道,忽的豁然开朗,只见五间厅房,前廊后厦,每根柱顶都装一盏电灯,照得院中十分明亮。各种花木的盆桶,已被花儿匠摆设停妥。东西各有三间厢房,也都带廊子。南面临街,却是连大门共五间草房。院内格式,虽然不是什么伟大的局势,却很整齐洁净。那五间厅房,都安着整扇大璃玻[ 璃玻:玻璃。
]。屋内电灯辉煌,满壁书画,已然凭着灯光看见了。这时那馆役把伯雍引到当院,自回去了。只见另有一个四十来岁的差役,气度很是不凡的样子,站在厅堂门前,预备肃客[ 肃客:迎进客人。
]打帘子。伯雍暗道:“派头真不小哇!这里与那边一墙之隔,居然是两个世界。”一边心思,已上台阶。那差役已把帘子揭起,伯雍躬身进去,只见四间一通连,只另隔一个套间。这大厅之内,壁上挂的,案上放的,架上架的,可谓满目琳琅。只那桌椅一项,极时髦和中国黑木的,共有四堂,恍然到了木器铺。伯雍正欲看看室内陈设,只听歆仁在套间内嗽了一声说:“伯雍来了!请屋里来。”此时那差役已然把那湖色绣花软帘揭起,伯雍到屋里一看,只见歆仁在一张钢丝床上仰卧着呢。见伯雍进来了,他才扎挣着起来,直咬牙皱眉的。他二人见了面,彼此对鞠一躬,然后逊伯雍在一把软椅上坐了,他却坐在他那把办公用的转心椅子上。差役献上茶,自出外屋去了。歆仁因向伯雍说:“老同学,咱们有些日子没见了,怎么有些日子,简直又换了一个朝代。革命以前,你往哪里去了?我们也不知你的住址,大家都很念叨你。我们在去年八九月里,很替皇室奔走了许多日,打算仍然贯彻我们君主立宪的主张,无奈大势已去,我们只得乘风使舵,不得不与南中首义的人联络。目下经我介绍,入了进步党的很多。守文[ 守文:暗指穆儒丐友人恒钧。
]却做了国民党支部部长。当初次选举时,我们哪里不找你!只是找不到。你若在城里,也能弄到一名议员。不然我和蒙古王公说一说[ 乌泽声出身蒙古八旗,故有此语。
],什么蒙古议员、西藏议员,也能得一个。如今却被别人占了去。你的为人,过于因循,在政治方面,未免过于不注意,以后却很难了。在党里没有功,谁肯给你买议员。别忙,我先介绍你入党,然后我再向党魁替你说项。”伯雍说:“那倒不必。兄弟到如今,对于政党是抱一种怀疑,不愿人说我在哪一党。况且政变以来,我终日在山窟窿里住着,把性质养得益发疏懒。我的志愿,不过在社会上卖卖胳膊,聊博升斗,孝养老亲,也就够了。飞黄的事,我已不想。”歆仁听了,微微一笑,说:“你要替前清守节吗?你不过是个洋举人,还够不上遗老资格。”伯雍说:“不管够不够。我的性质,只是不愿意做官。我自己知道,便是勉得一官,也弄不到好处。既然弄不好,何必一定去弄?所以我只愿在社会上做事,较比做官仿佛自由一点。我所以给你写信,也是这个意思。论理,我向你们大家告个帮,也能够我活一年半载的,但是究竟没有自己挣的吃着舒服。我如今不过欲赖笔尖,卖几个钱,求你原谅这点微忱,给我相当的报酬便了。”歆仁听了,连连摇头说:“可惜!你在同人里面,很是有出息的。不想你弄成这么一种性质!你若老这样,恐怕你将来要穷死。”伯雍说:“那也无法。假如社会上不要我这样的人,我不死怎的。”歆仁听到这里,似乎有点不愿意再和伯雍说话。只见他连连打呵欠,伸懒腰,不住地说:“好乏好乏!今天可累坏了!”
伯雍见歆仁有些困怠,便说:“我看你有些劳倦,你歇一歇吧。”歆仁说:“我真得睡一觉!今天在议会里,为了许多议案,累得筋疲力尽,完了又到党部办公,真是苦事。但也无法,回头还得编新闻。他们我谁也不敢靠,一不留神,就出毛病。有一天头段新闻我没管,总统府竟给圈出来,传谕注意。若不是有人维持,不但报馆禁不起,连我也老大不便。如今你来了,好极啦!你得多替我帮忙。我们的报,固然唯党魁之马首是瞻。对于老袁,一句话也别得罪。他不久要当中国大皇帝了。现在已有一群人想着那么办,不过不便明说,将来由宣传入手,先说共和不便于中国,然后再往帝制上做。这种风气,我已揣摩出来了。我们不可不先事预备,所以我求你替我帮忙,多多注意。将来免不了大买报馆,我们的报,不要落第才好。”伯雍说:“这事难极了。我新来乍到,怎能统御别人?你不要把难题往我身上加。你是总理,责任还是你负。你就给我一个责任,不与别人冲突才好。不过我不能坏你的事便了。要紧的东西,还是你自己办,较为稳健。”歆仁说:“也是。没法子,我还得累。有必要时,你得替我帮忙。目下咱们的报,文艺部太不好,明天你就替我办文艺部,与别人一点冲突没有。你看如何?”伯雍说:“那好极了。我就替你办办。别的不行,文艺部或者能多干两天。”
这时歆仁又打了两个呵欠。伯雍说:“你歇歇吧!我到外屋看看你的书画。”歆仁说:“好!回头见吧。”伯雍来到外屋,由头看去,虽无唐宋人的真迹,由四王吴恽,直到戴文节,以及成刘翁铁的墨宝,挂满了四壁。今人如吴昌硕、林琴南的东西,也都有几幅。案上的古玩,也有几件出奇的。伯雍看完这些东西,又想起方才他那间寝室和编辑部的污秽,暗道:“人是平等的吗?平等不过是一句哑谜,不知冤死多少人了。智者、黠者、悍者、猾者,都能猜得破,说是假的。不过他们不肯说破,还拿着去冤人。人们一天不明白,还以为平等是真的,便一天一天地受人家的欺弄。他们要做不平等事,必得先说人家不平等,等到他们把人推倒,他们的不平等,比人家还厉害。不过口里还说是为平等、争自由便了。其实他们所说的话,还是愿意人家服从他们。不然,他们既为平等,何必自己要当总统,要当总长,要揽政权。怎见得就是你们配呢?这不是明明不做平等的事么?可是他们早早若说平等是假的,人也就不猜这哑谜了。他们由哪里如愿以偿呢?”
伯雍由后院过来,天已不早了,只见编辑部里黑洞洞,一点声音也没有了,惟有吕子仙那房里,一灯荧然,大概还在那里喷云吐雾。他以为别的先生完了事,都睡觉了,不便惊动,便到子仙屋里,果见子仙在床上吃烟呢。他见伯雍进来,由床上欠欠身说:“在这里歇歇吧。”伯雍便躺在他对面。子仙说:“你见着总理了。”伯雍说:“见着了。”子仙说:“你们是老同学,他将来一定优待你,你只跟着他忍着,他不久要当总长了。他当了总长,咱们都能阔。咱们的报馆,原不为赚钱,现在的经济,也无力扩张,可是咱们总理手眼很大,凡是跟他做事的,将来都有个位置。所以我劝你极力帮他忙,先别求眼前的便宜,如同[ 如同:至于。
]薪水什么的,可以不必跟他争多论少。再说你们是同学,原说不到这上头,有钱没钱,不是一样。说回来了,这报馆跟你自己的一样。”子仙说一句,伯雍答应一句,实则伯雍也无心听他的话,知道他的话,都是替歆仁在那里做宣传。他等子仙吸完一口烟,才问他说:“编辑部都完事了吗?”子仙说:“都完了,就等总理头条新闻了。他们利用这点时候,又出去逛窑子去了。只有韦少卿和讹若士,天天这边完了事,便回他们《民德报》去,已然走了半天。”伯雍说:“天气大概不早?”子仙说:“早呢!也就十二点钟。”伯雍说:“若在家里,我早睡了。好在今天没我的事,我睡觉去了。”说着辞了子仙,到他自己寝室,暗中摸索,把电灯捻亮,把铺盖放好,宽衣睡下了。他一个山居的人,平日早睡早起,鼻子里所闻的都是新鲜空气,哪里这晚睡过觉?哪里住过这样霉湿屋子?若不是他这一天的劳累,他真不能睡好。在伯雍为人,向持达观,人情世故,没有他不明白的,没有他没看透的,所以他尚能随遇而安。他看着世上那些形形色色,不是可笑,就是可怜,尤且[ 尤且:尤其。
]对于方才子仙那些话,他以为可笑极了。至于歆仁的状态,他更以为可怜。据伯雍的意思,总不愿歆仁做一个滑头政客,如今自己既有相当力量,应当尽全副精神,经营报务,在社会上广求后援,成为言论界一个有名人物,何必利用报纸的空名,一心专想买收,做一二人的走狗,也未免过于没出息了!他竟在政界上揣摩风气,迎合意旨,将来究竟怎样呢?倒替他怪发愁的了。伯雍一边想着,耳边只听外屋壁钟,嗒嗒地响,忽地交了一下。他惊道:“真不早了!”于是他打断思潮,渐渐入了黑甜乡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