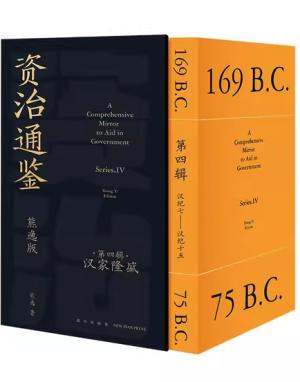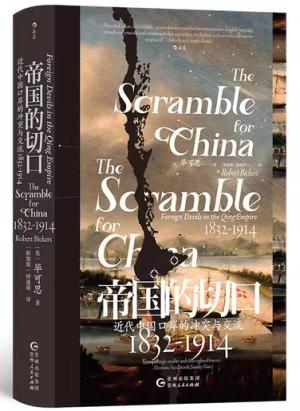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希腊文明3000年(古希腊的科学精神,成就了现代科学之源)
》
售價:HK$
82.8

《
粤行丛录(岭南史料笔记丛刊)
》
售價:HK$
80.2

《
岁月待人归:徐悲鸿自述人生艺术
》
售價:HK$
59.8

《
女人的中国医疗史:汉唐之间的健康照顾与性别
》
售價:HK$
10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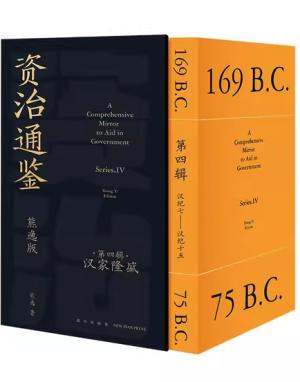
《
资治通鉴熊逸版:第四辑
》
售價:HK$
458.9

《
中国近现代名家精品——项维仁:工笔侍女作品精选
》
售價:HK$
66.1

《
宋瑞驻村日记(2012-2022)
》
售價:HK$
1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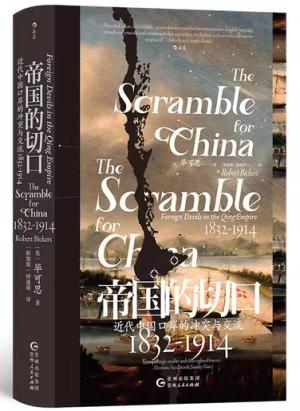
《
汗青堂丛书138·帝国的切口:近代中国口岸的冲突与交流(1832-1914)
》
售價:HK$
124.2
|
| 編輯推薦: |
|
《安娜·卡列尼娜》一部社会百科全书式的文学经典,大文豪托尔斯泰的代表作。小说中追求爱情与自由,并为自己的追求付出了生命代价的女主人公安娜,被评为*有魅力的女性形象之一。一百多年以来,安娜不断活跃在戏剧舞台、影视荧幕上,深受世界各国读者和观众的喜爱。小说通过两条线索进行,与安娜这一条线索并行的是列文这一条线索。在列文的身上,有托尔斯泰的影子。列文是贵族地主,他看到当时的社会矛盾与社会变革,进行了积极不懈的探索,力图从困境中突围。小说心理描写细腻入微,堪称经典。著名翻译家力冈先生倾力翻译,用词精准优美,忠实原著,同时符合中文表达习惯,传世译本,值得收藏。
|
| 內容簡介: |
|
安娜是美丽优雅温柔聪慧的贵族少妇,伏伦斯基是英俊潇洒聪明多金的高贵武官。他们相遇在莫斯科火车站,他对她一见倾心,疯狂热烈地追求她。他们陷入不伦之恋中不能自拔。安娜最终卧轨自杀,为爱情和自由献出了生命。文学史上不乏为爱情和自由奉献所有的动人女性形象,但安娜这朵娇艳脱俗的玫瑰无疑是最经典的,也是最深入人心的。如果只是讲述一段简单的不被世俗接受的爱情故事,这部作品不会被誉为社会百科全书式的杰作。与安娜这一条线索同时进行的是列文,作为贵族地主,他在面对当时农村剑拔弩张的矛盾危机时,进行了不懈改革与探索,志在解决当时的社会矛盾。从莫斯科到外省乡村,150多个鲜活的人物,不动声色的矛盾冲突力透纸背,生动再现当时的社会矛盾。
|
| 關於作者: |
|
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出生于俄国贵族家庭,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后回到农庄,致力于农民教育,从事创作。他是俄国著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思想家,19世纪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世界杰出文豪之一。他的作品涉及文学、哲学、美学、政治、宗教等领域,对世界文学具有重要影响。他的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宁娜》《复活》等,戏剧《黑暗的势力》和一些短篇小说及文学评论。
|
| 目錄:
|
一 001
二 039
三 072
四 096
五 125
六 151
七 176
八 202
作者年表 211
|
| 內容試閱:
|
幸福的家庭每每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苦情。奥布朗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套。妻子发现丈夫和以前的法籍女家庭教师有私情,就向丈夫声明,不能再跟他一起过下去了。在口角之后第三天,司捷潘阿尔卡迪奇奥布朗斯基公爵(社交界都叫他的小名司基瓦)在惯常的时间早晨八点钟醒来,不是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在自己的书房里,在上等山羊皮沙发上。依照他九年来的老习惯,不等起床就朝他在卧室里挂晨衣的地方伸过手去。这时他才猛然想起自己为什么不睡在卧室里,而睡在书房里,于是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皱起眉头。“是啊!她不肯原谅,也不可能原谅。而且最糟糕的是,一切都是我的过错。”他想道。
“唉,唉,唉!”他回想起这次口角中最使他难堪的场面,灰心绝望地叹起气来。奥布朗斯基是一个以诚对己的人。他不能欺骗自己,不能让自己相信他已经悔恨自己的行为。他这个三十四岁的风流美男子,不再爱一个只比他小一岁,已经是五个活着、两个死去的孩子母亲的妻子。这一点他并不后悔,后悔的只是没有想到更好的办法把妻子瞒住。“以后自会有办法的。”奥布朗斯基对自己说过这话,站起身来,穿上晨衣,来到窗前。他拉开窗帘,使劲按了按铃。贴身老仆马特维听到铃声,立即走了进来,手里拿着长衣、靴子和一封电报。奥布朗斯基拆开电报,把电报看了一遍,他的脸顿时放起光来。
“马特维,我妹妹安娜阿尔卡迪耶芙娜明天要到了。”“谢天谢地。”马特维说这话,表示他和东家一样理解这次来访的意义,就是说,奥布朗斯基的好妹妹安娜阿尔卡迪耶芙娜这一来,会促使他们夫妻和好起来。“给她收拾楼上的房间吗?”马特维问道。“你去禀报达丽雅亚历山大罗芙娜,她会吩咐的。”“是,老爷。”
当马特维回到房里来的时候,奥布朗斯基已经梳洗完毕,准备穿衣服。“达丽雅亚历山大罗芙娜吩咐我传话,说她要走了。说让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好啦。”马特维说。奥布朗斯基没有作声,他的脸上出现了有点儿可怜的笑。“啊?马特维?”他摇着头说。“没事儿,老爷,会雨过天晴的。”马特维说。“好吧,给我穿衣服。”他对马特维说着,很果断地脱下晨衣。奥布朗斯基尽管生活放荡,官衔不高,年纪较轻,却在莫斯科一个机关里担任着体面而薪俸优厚的主官职位。这个职位他是通过妹妹安娜的丈夫阿历克赛亚历山大罗维奇卡列宁的关系谋得的。卡列宁在一个部里担任要职,莫斯科这个机关就隶属于他那个部。不过,即使卡列宁不给他的内兄谋得这个职位,奥布朗斯基也可以通过许许多多其他人士,谋得这个职位或者其他类似的职位,可以得到六千卢布的年俸。这笔进项他是非常需要的,因为尽管他的妻子有大宗财产,他的家业却已经败落了。
半个莫斯科和半个彼得堡都是奥布朗斯基的亲戚和朋友。他生来就在新旧显要人物的圈子里。因此,地位、租金、租赁权等等人世间福利的分配者都是他的朋友。奥布朗斯基要弄到一个肥缺,也就不需要费多大力气了。需要的只是不亢、不嫉、不争、不怨,而他生性随和,一向就是这样的。奥布朗斯基担任这个职务已是第三年,不仅得到同僚、下属、上司和一切跟他打过交道的人喜欢,而且也得到他们的尊敬。这天奥布朗斯基来到自己的官府里,走进他的小办公室,跟同事们握过手,便坐了下来。
他说了几句笑话,说得恰到好处,便收住话头,开始办公。还不到两点钟,办公厅的大玻璃门忽然开了,一个体格强壮、肩膀宽阔、下巴上留着鬈曲胡子的人走了进来。“原来是你呀!列文,难得难得!”奥布朗斯基打量着来到跟前的列文,带着亲热的笑容说。列文和奥布朗斯基几乎同庚,列文是他少年时代的伙伴和好友。尽管他们性格不同,志趣迥异,他们的友情却是深厚的,“你怎么不嫌脏,到这种鬼窝儿里来找我啦?”奥布朗斯基说过,握了握手,“来了很久了吗?”“我刚到,就想来看看你。”列文一面回答,一面朝周围打量着。“哦,对了,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奥布朗斯基说,“这是我的两位同事:菲里浦伊凡内奇尼基丁,米哈伊尔斯坦尼斯拉维奇格里曼维奇。”然后转身对着列文,“这位是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地方自治会议员,自治会的新派人物,畜牧学家,猎手,我的好朋友,谢永盖伊凡诺维奇柯兹尼雪夫的弟弟。”
“我有幸认识令兄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格里涅维奇说着,伸过他那指甲老长的瘦长的手。列文皱起眉头,冷冷地握了握手,立刻转过身和奥布朗斯基说话:虽然他非常尊敬已成为全俄闻名作家的异父同母哥哥,可是,当别人不是把他当作康斯坦丁列文,而是当作有名的柯兹尼雪夫的弟弟的时候,也还是无法忍受。“不,我已经不是自治会议员了。我跟所有的人都吵过,再也不参加会议了。”他对奥布朗斯基说:“太快啦!”奥布朗斯基微微笑着说。“是怎么一回事儿?因为什么?”
“说来话长,以后再说吧。”列文说,“咱们在什么地方再见见面呢?因为我非常非常需要和你谈谈呀。”“哦,好吧,咱们就一起吃晚饭。”“吃晚饭?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不过有两句话要说说、问问,以后再细谈。”“那你现在就说说这两句话,到吃饭的时候再细谈。”
“谢尔巴茨基一家人怎么样?一切还都是老样子吗?”他说。奥布朗斯基早就知道列文爱上了他的姨妹吉娣,听了这话微微笑了笑,眼睛里放射出快活的光彩。“是这样,没有什么变化,不过可惜你这么久没有来。”“怎么啦?”列文惊愕地问。“没什么,”奥布朗斯基回答说,“咱们以后再谈吧。这样吧,你要是想见到他们,今天四点到五点,他们肯定在动物园。吉娣在那儿溜冰。你就上那儿去吧,我回头去找你,咱们一块儿到什么地方去吃晚饭。”“好极了,那就再见吧。”当奥布朗斯基问列文究竟为何事而来的时候,列文红了脸,并且为了
脸红生自己的气,因为他不能回答他说:“我是来向你姨妹求婚的。”虽然他就是为这事来的。
列文家和谢尔巴茨基家都是莫斯科的贵族世家,一向关系密切,交谊深厚。列文的母亲去世较早,他已经不记得自己的母亲了。正是在谢尔巴茨基家里,他第一次感受到有教养的名门望族的家庭生活气氛。在他的心目中,这一家人,尤其是姑娘们,仿佛个个都罩着一道神秘的、诗意的帷幕,他不仅看不到他们的任何缺陷,而且认为罩在这道诗意的帷幕之下的,是最高尚的感情和完美无瑕的品性。他这个出身望族、称得上富有的三十二岁男子,向谢尔巴茨基家小姐求婚,似乎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他完全可能立刻被当作理想的佳婿。可是列文已经堕入情网,因此他觉得吉娣在各方面都极其完美,是超凡脱俗的天仙,而他自己是卑微低下的庸夫,让别人和她自己认为他配得上她,那是无法想象的事。
列文为了要见到吉娣,几乎每天在交际场上和她见面,就这样在莫斯科过了两个月,忽然断定这是不可能的事,便到乡下去了。列文之所以断定这是不可能的,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她家的人眼里是一个没有出息的、跟美貌迷人的吉娣不般配的女婿,吉娣也不会爱他的。但是,一个人在乡下待了两个月之后,他认识到,这恋情已经不是少年时代经历过的那种恋情,这恋情使他片刻不得安宁;他认识到,她会不会做他的妻子这个问题不解决,他就活不下去;他认识到,他的灰心绝望只是出于他的臆测,没有任何根据表明他会遭到拒绝。于是他现在抱着坚定的决心来求婚,如果答应的话,就结婚。要不然……他还无法想象,如果遭到拒绝,他会怎么样。下午四点钟,列文揣着一颗怦怦跳动的心在动物园门口下了车,顺着小径向山上溜冰场走去,他料定可以在那里找到她,因为在门口看到了谢尔巴茨基家的轿式马车。他顺着小径往溜冰场走,一路上自言自语:“不要翻腾,要镇定。你翻腾什么?你怎么啦?安静点儿,傻东西!”他对自己的心说。
他越是拼命要自己镇定,越是紧张得气都喘不上来。他又走了几步,面前就出现了溜冰场,他立刻就在溜冰的人群中找到了她。她站在溜冰场那一头,她的服装和姿势似乎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列文在人群中找她,就像在荨麻丛中找玫瑰花一样容易。一切都因她而大放异彩。她是使周围一切绽开笑靥的微笑。吉娣的堂弟尼古拉一看见列文,就冲他叫了起来:“嘿,全俄第一名溜冰高手!来了很久了吗?快穿上冰鞋!”“我没有冰鞋呀。”列文一面回答,一面因为在她面前这样大胆和放肆心中暗暗吃惊,同时片刻不离地注视着她,虽然眼睛没有看她。她在拐弯的地方很不灵活地摆动了一下她那裹在长靴里的秀足,显然很胆怯地朝他溜过来,眼睛看着她已经认出来的列文,朝他笑着,同时也笑自己的胆怯。
“您来这儿很久了吗?”她说着,向他伸过一只手来。“我吗?没多久,我昨天……我是说今天……才到的。”列文因为激动,一下子没有听明白她问的话,就回答说:“我想来看看您。”他说过这话,立刻想起他是为什么来找她的,发起窘来,脸红了。“我还不知道您会溜冰,而且溜得这样好。”“您的称赞是很难得的。这里―直有人在说,您是了不起的溜冰高手呢。我真想看看您溜冰。您就穿上冰鞋,咱们一块儿来溜吧。”“我这就去穿。”他说。于是他就去穿冰鞋。
列文心想:“是的,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幸福!一块儿,咱们一块儿来溜吧,她说的呢。我现在就对她说说吗?可是我很怕开口,就因为我现在很幸福,至少是有幸福的希望……那怎么办呢?……不过应该说呀!应该说,就是应该说!决不能优柔寡断!”列文胆怯地来到她跟前,但是她的微笑又使他镇定下来。她把一只手伸给他,他们就肩并肩地溜起来,渐渐加快了速度,溜得越快,她把他的手握得越紧。“要是跟您在一起,我早就学会了。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相信您。”她对他说。“在您依靠着我的时候,我也就相信自己了。”他说。可是他立刻就因为说出这话觉得害怕,脸也红了。果然,他一说出这话,她脸上的亲切表情顿时消失,好像太阳躲进乌云里。列文看出他所熟悉的她这种表示深思的脸部变化。她那光溜溜的额头上出现了皱纹。“您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吧?不过,我没有权利这样问。”他连忙说。
“为什么呀?……没有,我什么不愉快的事也没有。”她冷冷地回答,并且立刻又补充说,“您这次来,要住很久吗?”“我不知道。这取决于您呀。”他说,但立刻就觉得害怕了。不知是她没听见这话,还是她不愿意听,反正她好像打了一个趔趄,就匆匆地从他身边溜走了,朝妇女换鞋的小屋溜去。“我的上帝,我做了什么呀!我的上帝呀!帮助我、教导我吧。”列文祷告说,同时觉得很需要剧烈地运动一下,就奔跑起来,左旋右转,在冰上兜起圈子。“他这人真好,真可爱。”这时候吉娣从小屋里出来,带着亲切而无声的微笑,像看着好哥哥一样看着他,心里想道。“难道我有什么错儿吗?难道我做了什么坏事吗?人家说我卖弄风情。我知道我爱的不是他;但我跟他在一起总觉得很快活,而且他又是这么好的一个人。不过,他为什么说这种话呀?……”她想道。列文看到吉娣要走,又看到来接她的母亲站在台阶上,就停下来,沉思了一会儿。他脱下冰鞋,在动物园门口追上了她们母女。
“很高兴看到您。我们还像往常一样,星期四接待客人。我们很高兴接待您。”公爵夫人淡淡地说。这种冷淡的态度使吉娣觉得难受,于是她忍不住要弥补一下母亲的冷淡。她转过头来,笑盈盈地说:“再见!”这时奥布朗斯基高高兴兴朝动物园里走来。可是他一走到岳母面前,岳母问起陶丽的健康状况,他回答时就流露出一脸忧愁和负疚的神气。他闷闷不乐地小声和岳母说了一会儿话,这才挺起胸膛,挽住列文的胳膊。“怎么样,咱们走吧?”两个朋友一路上都没有说话。列文在寻思吉娣脸上的表情变化意味着什么。他一会儿认为是大有希望的,一会儿又悲观失望。
奥布朗斯基一路上想的是晚餐的菜单。列文跟着奥布朗斯基一起走进饭店的时候,他不由得发现奥布朗斯基脸上和整个身上有一股特别的神气,似乎是一股压抑着的喜洋洋的神气。“请到这边来,大人。”一个鞑靼老头说。他拿着餐巾和菜单站在奥布朗斯基面前,听候吩咐。“那么,伙计,就给我们来三十个牡蛎,一个蔬菜汤,再来个浓汁比目鱼,再来个……煎牛排;注意,要好的。哦,再来只腌鸡,怎么样?还有水果罐头。咱们喝什么酒?”奥布朗斯基说。“随便,不过要少一点儿,就香槟吧。”列文说。
过了五分钟,老侍者端着一盘带珠母色贝壳的打开来的牡蛎,用手指头夹着一瓶酒,像飞一样走了进来。奥布朗斯基揉搓了一下浆硬的餐巾,塞到背心领口里,舒舒服服地摆开两臂,吃起牡蛎。列文也在吃牡蛎,虽然他觉得面包夹干酪更有味道,不过他很欣赏奥布朗斯基那种狼吞虎咽的神气。“你不怎么喜欢牡蛎吧?”奥布朗斯基一面说,一面把自己杯子里的酒喝干,“还是你有什么心事?嗯?怎么样,今天晚上你到我们那儿,就是说,到谢尔巴茨基家去吗?”他意味深长地闪动眼睛说:“是的,我一定去,”列文回答说,“尽管我觉得公爵夫人的邀请并不热情。”“瞧你!瞎说什么呀?这是她的气派,贵夫人气派嘛。”奥布朗斯基说,
“哦,你究竟为什么事到莫斯科来的?”“你能猜到吗?”列文一面回答,一面用他那在深处闪着亮光的眼睛盯着奥布朗斯基。“我能猜到,不过这事儿我不能先开口。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来,我猜得对不对。”奥布朗斯基带着微妙的笑容看着列文说。“不过你是不是弄错了?你知道咱们说的是什么事儿吗?”列文用眼睛紧紧盯着对方说,“你以为这事儿可能吗?”
“我以为可能。为什么不可能?任何姑娘遇到求婚,都认为是光彩的事。”“是的,任何姑娘都是这样,不过她不是这样。你要明白,这对于我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看在上帝面上,你把话全说出来吧。”“我对你说的,就是我心里想的。”奥布朗斯基笑着说。“不过我还要对你说说:我妻子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人……”奥布朗斯基想起自己和妻子的事,叹了一口气,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又说下去,“她有先见之明,看人看得很透。不但如此,她还知道今后会怎样,尤其是在婚姻方面。她不仅很喜欢你,她还说,吉娣一定会做你的妻子。”
列文一听到这话,顿时笑逐颜开。“她这样说哩!”列文叫起来,“我一向都在说,她,你的妻子,简直太好了。这就够了,这事儿谈够了。”他说着,站了起来。“好吧,不过你坐下呀。还有一点我应该对你说说。你认识伏伦斯基吗?”奥布朗斯基问列文。“不,我不认识。你问这干什么?”“你要认识认识伏伦斯基,因为他是你的情敌之一。”“伏伦斯基是什么人?”列文说着,脸色变了,出现了懊恼和不快活的神气。“伏伦斯基是基里尔伊凡诺维奇伏伦斯基伯爵的一个儿子,是彼得堡花花公子的一个活标本。他非常有钱,长相又漂亮,交游很广,是一个侍从武官,同时又是一个非常招人喜欢的、和善的小伙子。我到这儿以后还了解到,他很有教养,又很聪明;这是一个很有前程的人。”列文皱起眉头,没有作声。“哦,你走后不久他就来到这儿,据我看来,他爱吉娣爱得神魂颠倒,而且,你也明白,她母亲……”
列文身子靠到椅背上,一张脸都白了。“不管怎样,我劝你尽快把问题解决,今天不必谈,”奥布朗斯基说,“明天早晨你就去正正经经地求婚,上帝会保佑你的……”“你不是一直想到我那儿去打猎吗?到春天就来吧。”列文说。现在他心里十分后悔,觉得真不该和奥布朗斯基谈这件事。有关彼得堡的一名什么军官跟他竞争的话以及奥布朗斯基的推测和劝告,玷污了他的一腔特殊的感情。奥布朗斯基微微笑了笑。他理解列文此刻的心情。“我有时间一定去。”他说。
鞑靼老侍者送来账单,列文应摊十四卢布,要是在别的时候,他这个乡下人肯定会吓一跳,可是现在他毫不在意,付了账,便回家去换衣服,要去谢尔巴茨基家,他的命运就要在那里决定。谢尔巴茨基公爵家的吉娣小姐芳龄十八岁。她是这一年冬天才在交际界抛头露面。她在交际界博得的赞赏超过她的两个姐姐,也超过公爵夫人的预料。不仅出入莫斯科舞场的年轻人几乎个个迷上了吉娣,而且在第一个冬天就出现了两个郑重其事的求婚者:列文以及他走后立即出现的伏伦斯基伯爵。
列文在冬初的出现,他的频繁来访和他对吉娣很明显的爱慕,使吉娣父母第一次郑重其事地谈她的婚事,并且发生了争吵。公爵看中了列文,说列文配吉娣再好不过了。公爵夫人却说吉娣还太年轻,说列文还没有什么真心实意的表示,说吉娣对他没有什么情意;可是她没有说出主要的理由,那就是她盼望女儿有个更好的夫婿,她不喜欢列文。等到伏伦斯基上场,她就更认为自己完全说对了,认为吉娣一定会找到一个不单是好的、而且是令她荣耀的夫婿。伏伦斯基处处符合吉娣母亲的心意。他非常富有,非常聪明,门第高贵,既然是侍从武官,自会有锦绣前程,又是一个俊美的男子。她认为再也不能有更好的了。伏伦斯基在舞会上明明白白地向吉娣献殷勤,跟她跳舞,经常来她们家,可见他的真心实意是无可怀疑的。可是,尽管如此,母亲在整整一个冬天里一直是忐忑不安,忧心忡忡。她现在怕的是,伏伦斯基对她的女儿不过只是献献殷勤罢了。她看出来,女儿已经爱上了他。今天,列文的出现使她增添了新的忧虑。她怕列文这一来,会把这件眼看就要定下来的婚事破坏了。在吃过晚饭到晚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