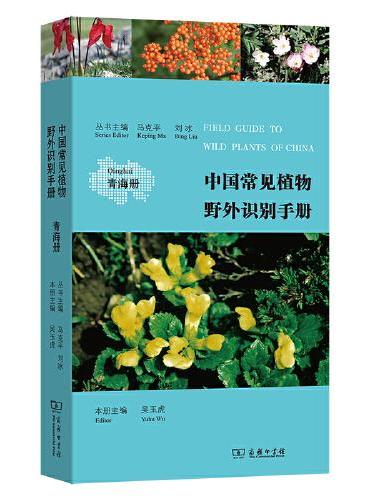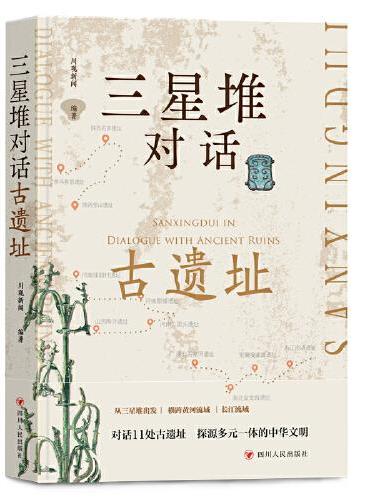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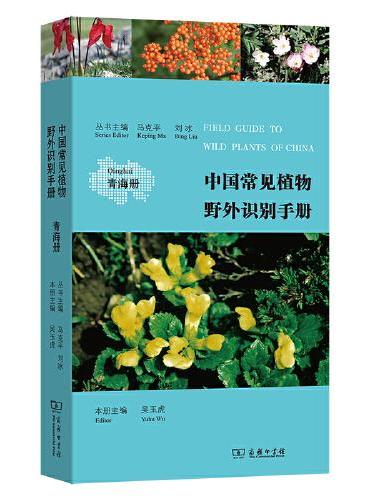
《
中国常见植物野外识别手册:青海册
》
售價:HK$
7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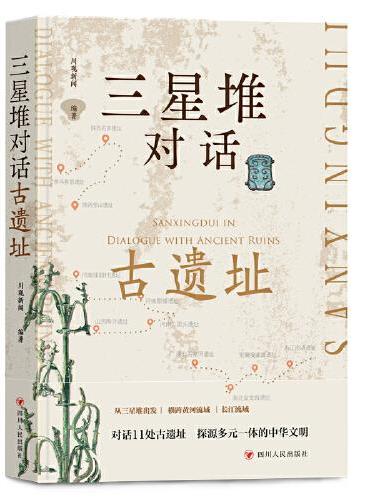
《
三星堆对话古遗址(从三星堆出发,横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对话11处古遗址,探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
售價:HK$
87.4

《
迷人的化学(迷人的科学丛书)
》
售價:HK$
143.4

《
宋代冠服图志(详尽展示宋代各类冠服 精美插图 考据严谨 细节丰富)
》
售價:HK$
87.4

《
形似神异:什么是中日传统政治文化的结构性差异
》
售價:HK$
55.8

《
养育不好惹的小孩
》
售價:HK$
77.3

《
加加美高浩的手部绘画技法 II
》
售價:HK$
89.4

《
卡特里娜(“同一颗星球”丛书)
》
售價:HK$
87.4
|
| 內容簡介: |
本书收录的《大先生》是以鲁迅为原型创作的话剧。这是第一次将鲁迅形象搬上话剧舞台的尝试。
李静所写的鲁迅,不是预期之中的历史叙事,也没有示人以耳熟能详的“斗士和导师”面目,而是从鲁迅的临终时刻写起,用意识流结构贯穿起他生前逝后最痛苦、最困惑的心结——那是一个历史夹缝中备受煎熬的形象。
李静的“自白”向我们讲述了她艰难的创作过程,有利于读者鉴别面对历史和现实的诚实。
李静与陈丹青和赵立新的深入访谈,有利于读者理解鲁迅这个让中国人永远爱、永远痛、永远绕不过去的复杂形象。
|
| 關於作者: |
李静,文学评论家,剧作家。北京日报副刊编辑。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
以评论王小波、莫言、木心等作家获得2011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评论家奖;以剧本《大先生》获老舍文学奖优秀戏剧剧本奖。
已出版《捕风记》《必须冒犯观众》等作品。
|
| 目錄:
|
大先生——无场次非历史剧
自白
我为什么这样写鲁迅?
鲁迅,戏剧创作的“百慕大三角”
一个戏剧菜鸟的“鲁迅”编造史
写作的灵魂想象力
爱的信誓
该怎么谈你呢,先生?
看,这个人
致 X.D.
致 L.
《非攻》的动词及其他
李静、陈丹青、赵立新三人谈
《大先生》,大先生及其他
残稿
盛宴
起殇
兄弟
血绳
知己
后记
|
| 內容試閱:
|
自白:我为什么这样写鲁迅?
我声称要写话剧《鲁迅》至少三四年了,一直干打雷不下雨。朋友们渐渐把它当作了一件可以原谅的事,安慰我说:“没关系,鲁迅从死掉那天起就有人要写他,不是一直没人写出来吗?你不是唯一的倒霉蛋。”其实不是的。萧红在鲁迅先生逝世五年后就创作了默剧《民族魂鲁迅》,日本剧作家井上厦在 20世纪 90年代也写出了诙谐风趣的《上海月亮》。只能说,1949年之后的中国剧作家还没有足够幸运的时机和灵感,来自由地呈现这位天才而复杂的作家。2012年 2月,我不敢相信摩挲了三年的话剧剧本《鲁迅》,真的在我手中完成了。
朋友们看完,有激动赞赏的,有不以为然的,更多的是有些惊讶:“你为什么这样写他呢?”的确,我的《鲁迅》不是预期之中的历史剧,也没有示人以耳熟能详的“斗士和导师”面目,而是从鲁迅的临终时刻写起,用意识流结构贯穿起他生前逝后最痛苦、最困惑的心结——那是一个历史夹缝中备受煎熬的形象,我试图让他成为一面破碎的镜子,同时照照我们的历史和现在。他逝后的事怎么出现在意识里呢?是呀,这个技巧我想了很久,此处就卖个关子吧。
鲁迅先生的伴侣许广平有篇回忆文章《最后的一天》,作于1936年 11月 5日,落款注明“先生死后的二星期又四天”,里头写到一个细节:10月 19日零时——那时距先生辞世只有五个多小时了——许先生给他揩手汗,“他就紧握我的手,而且好几次如此。陪在旁边,他就说:‘时候不早了,你也可以睡了。’我说:‘我不瞌睡。’为了使他满意,我就对面斜靠在床脚上。好几次,他抬起头来看我,我也照样看他。有时我还陪笑的告诉他病似乎轻松些了。但他不说什么又躺下了。也许这时他有什么预感吗?他没有说。我是没有想到问。后来连揩手汗时,他紧握我的手,我也没有勇气回握他了。我怕刺激他难过,我装做不知道。轻轻的放松他的手,给他盖好棉被。后来回想:我不知道,应不应该也紧握他的手,甚至紧紧的拥抱住他,在死神的手里把我的敬爱的人夺回来。如今是迟了!死神奏凯歌了。我那追不回来的后悔呀。”
这段话如同一个伤口,使我在构思过程中不时感到疼痛。这个人的勇毅和脆弱,炽烈和敏感,沉默和爆发,克制和缠绵……时刻对立共存在他矛盾的天性中,直到最后一息,仍彼此纠缠欲说还休。在那生死交界的时刻,爱人未能给他默契的回握和陪伴。
他孤单地踏上了无法回归的旅程。我不知许广平先生如何挨过那些心碎自责的日子。我只知,我的《鲁迅》必须从临终这一刻开始——它是一口沸腾的深井,吸引我跳进去。
跳进去之后,最要紧的是选择——让哪些场景进入主人公的意识中?意识流的好处是自由,坏处是容易飞散,飞散不好,观众就会打哈欠——这一点,戏剧着实和小说不同。彼得·布鲁克(PeterBrook)早就警告过:“戏剧这种形式是多么脆弱而难以维系,因为这小小的生命火花得点燃舞台上的每一分每一秒。”对剧作者来说,点燃火花的实验室在其自心。在浩如烟海的鲁迅著作和相关回忆录中,我生平第一次以偷窥癖的嗅觉和冷血,搜寻他的痛苦、纠结、迷误和软肋,从中提炼我需要的火花。我要写的不是领袖敕封的“圣人”——所谓“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和“空前的民族英雄”,也不是大众追捧的“凡人”——所谓最有人情味的“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师长”。不。我要写的是一个复杂而本真的心灵。他的伟大和限度,创痛和呼告,我不想辜负。
鲁迅的平生,有三大伤心——早年不幸的婚姻,中年兄弟失和,晚年与全心扶助的左翼力量闹得不愉快。他的身后,则留下了一个谜团,这谜团他若地下有知,一定更其痛苦——他虽一生致力于反抗专制强权、帮助弱者追求自由,若干年后却被弱者拥戴出来的最高领袖把他当作自己囚禁自由的盟友。《鲁迅全集》是“文革”时期唯一公开出版的伟人全集(连革命导师们都只能出选集),一个通过注释和各种回忆录而改造包装出来的横眉冷对、痛打落水狗的“棍子”形象,使伤痕累累的人们唯一想要对他做的,就是厌倦和逃离。时至今日,关于“为何鲁迅能被权力利用”的问题,在中国学术界依然争论不休。
我决定以我的方式,在剧作中触及这一切。并非因为这些事件是鲁迅人生中最有争议、最赚眼球的内容,而是因为,它们最能显现他贯穿一生的精神逻辑。这个逻辑,既是鲁迅精神复杂性的成因,也是作为戏剧主人公的他,精神戏剧性之核心所在。这个逻辑是什么呢?
说来话长,归结起来便是“爱与自由的悖论”。这里的“爱”,不是爱情,而是牺牲之爱,舍我之爱,类似十字架上的耶稣之爱。不同的是:耶稣为彼岸的天国而牺牲,鲁迅为地上的天国而舍我——他太爱那些无依的灵魂,放不下弱者的眼泪,他希望自己加入的战斗能给他们现世的超度和安慰。因此,“眼泪”是这部剧作的核心词。但先生的经验和理性尚未认识到:凡以“地上天国”之名建造的,莫不是人间地狱;在这过程中,崇高的牺牲者托举起来的不是众生的自由,而是“人神”的僭越。但他自由的天性却已预感到这种危险,因此他最终的选择是:左右开弓的独自“横站”。
从私人生活到公共生活,鲁迅一生都往来奔突于律令般的“爱”
和天性的“自由”之间,以自我牺牲始,以逃离桎梏终——直到
生命的尽头。这个孤独伟大的悲剧人物,他的悲剧性永远属于现在进行时,其烈度不因时代变迁而稍减。望着他寂寥的背影,我感到如果再不走近他,就永远走不近他了。对他的负心已久,我只想以我的《鲁迅》,稍稍减轻自己的亏欠。
2013年 1月
鲁迅,戏剧创作的“百慕大三角”
自 2009年初我接受导演的约稿,到 2012年 2月完成,话剧剧本《鲁迅》经历了三年多的孕育期。2013年 1月,《天涯》杂志打破从不刊发剧作的惯例,将其全文发表,此事在文本阶段才告结束。
有人问:你为什么花这么长时间写一部不到三万字的《鲁迅》呢?想了下,时间长当然是因为自己思致愚钝、准备不足,而这么长时间却没放弃,则是为了对鲁迅的爱与好奇,为了他与今日之“我”的相通——他当年反对的事物,至今依然是我们获得幸福的最大障碍——这样一个灵魂,用三年时间寻找一个呼应他的方式,在我是值得的。还有一个不想放弃的原因,便是它的难度。早有前辈警告过:“鲁迅题材可是个百慕大三角啊,搞创作的没有不在他这儿翻船的,你要小心!”果真如此吗?那更要一试。在我的“船”出发之前,翻检了一下先行者的航线,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果然是表面风光无限,海底暗礁重重!
电影演员赵丹 1980年临终时发表过一篇文章《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里面有一段牢骚:“像拍摄《鲁迅》这样的影片吧,我从 1960年试镜头以来,胡髭留了又剃,剃了又留,历时 20年了,像咱们这样大的国家,三五部风格不同、取材时代和角度不同的《鲁迅》也该拍得出来,如今,竟然连‘楼梯响’也微弱了。”其实,他的付出可不只是“胡髭留了又剃”,自从周恩来 1960年拍板决定做传记故事片《鲁迅传》上下集,他请缨出演并获准之后,就开始常年模仿鲁迅的生活习惯——比如抽烟抽到根,用小酒盅喝绍兴黄酒,用鲁迅爱用的那种“金不换”毛笔写字,家里的写字台上摆放着鲁迅当年使用的那种墨盒、八行红格纸、浆糊、竹条、瓦片之类,并学着像鲁迅那样亲手装订图书和画册、补裱残旧古书……疯魔若此,只为了形神兼备地饰演他挚爱的鲁迅先生。
也难怪赵丹如此投入,单看当时的主创阵容,就足以亮瞎所有的眼睛:陈白尘、叶以群、柯灵、杜宣等集体编剧,陈白尘执笔,于伶任历史顾问,陈鲤庭执导,赵丹饰鲁迅,于蓝饰许广平,孙道临饰瞿秋白,蓝马饰李大钊,于是之饰范爱农,石羽饰胡适,谢添饰阿Q……此外,还有沈雁冰、周建人、许广平、杨之华、巴金、周扬、夏衍、邵荃麟、阳翰笙、陈荒煤等组成的庞大顾问团。如此群星灿烂,《鲁迅传》自然万众瞩目,还没等剧本停妥,友好国家就来订购影片拷贝了。
但结果是:这部本来计划 1961年献给建党 40周年的电影,最后没有拍成,只有层层审核、屡次修改的《鲁迅传》(上部)文学剧本留存于世(剧本修改后的第三稿发表于 1961年《人民文学》第 1—2期,又多次修改后,1963年 3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了单行本)——不但主人公鲁迅面目全非,艺术上也烙下“两结合”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 的印记,这是“政治挂帅”的必然结果。
正如学者李新宇在《1961:周扬与难产的电影 》和学者谌旭彬在《电影〈鲁迅传〉流产始末》两篇文章中所揭示的:《鲁迅传》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艺作品,而是一个意识形态“形象工程”。在剧本创作开始前,周恩来即已定调:要塑造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鲁迅,要以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鲁迅的评价为纲。剧本为了突出党的领导和鲁迅的“高大形象”,只好虚构史实,遮蔽细节:比如第一次约鲁迅给《新青年》写稿的不是钱玄同,而成了李大钊;即使多次有鲁迅北平家中的场景,也坚决不让他的妻子朱安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出场,以免他们给伟人“抹黑”;鲁迅南下厦门不是为了爱情,而是因为听从李大钊“到南方看看革命形势”的号召;鉴于陈独秀的“历史错误”,他不能出现在影片中,但他的儿子陈延年是个没有污点的烈士,因此便被安排在广州引导鲁迅投身革命——尽管没有任何资料证明他和鲁迅见过面——他不失时机地掏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赠与先生,后者读完则表示灵魂深受震撼……
即使这样意识形态化的鲁迅形象,也不能获得领导人的一致通过。由于鲁迅晚年在上海与若干“左联”领导发生过公开的冲突,而这些人在新中国的文艺界又身居高位,那么如何在影片中叙述鲁迅和他们,就成了一个问题。(这一问题至今创作者也不能全无顾忌。)据学者李新宇推测,这是《鲁迅传》流产最重要的原因。但这也只是一个推测。一个浩大工程不了了之而无任何交代,是“人治”体制的一大特色。
1980年,旧梦不死的赵丹找到陈白尘,希望他修改当年的剧本,被陈先生拒绝,称“曾经沧海难为水”——他已没有力量抹掉涂在鲁迅先生脸上的金粉,恢复他的本来面目了。读到这份资料,我忍不住想:所谓“鲁迅被权力利用”,也只能做到有限的断章取义;鲁迅形象在彼时之不可呈现,已在在表明他与他的“利用者”之间,隔着无可跨越的天堑。
2005年,由刘志钊编剧、丁荫楠导演、濮存昕主演的电影《鲁迅》上演,这是第一部以鲁迅为主人公的影片。它以鲁迅的最后三年为素材,融合各种生活片段和作品意象,力求表现他“金刚怒目,菩萨低眉”的性格。
戏剧舞台则一直不乏改编自鲁迅小说的作品,如梅阡的《咸亨酒店》、林兆华的《故事新编》和李建军的《狂人日记》等。但以鲁迅为有机主人公的戏剧,新中国一直付诸阙如。反倒是1940年,曾有萧红创作的默剧《民族魂鲁迅》上演,该剧选择鲁迅少年、青年、中年、晚年的几个片段加以动作铺排,最后归于“伟大的民族魂”主题,体现了当时的时代色彩。到了 21世纪初,导演张广天借鉴活报剧形式作话剧《鲁迅先生》,将先生的言行口号化,用以义愤填膺地批判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戕害。
这个中国人耳熟能详、叙述最多的人物形象,为何却一直不能在银幕和舞台上被完整而真实地呈现?除了非常时期的历史原因之外,更重要的缘故是:无论电影还是戏剧,都面临一个难题——鲁迅精神世界的强烈和复杂,难以外化于他的人生经历中;以写实手法表现鲁迅,总有捉襟见肘、貌合神离之憾。
窥看了前人的探索和牺牲,我在创作话剧《鲁迅》时,便避实就虚地营造了一个恍惚迷离、生死交界的空间,以此呈现鲁迅先生波涛汹涌的内在世界。但是究竟呈现得怎么样,会不会同样葬身于百慕大三角,实难自知,一切交由读者、观众和时间去裁判罢。
2013年2月3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