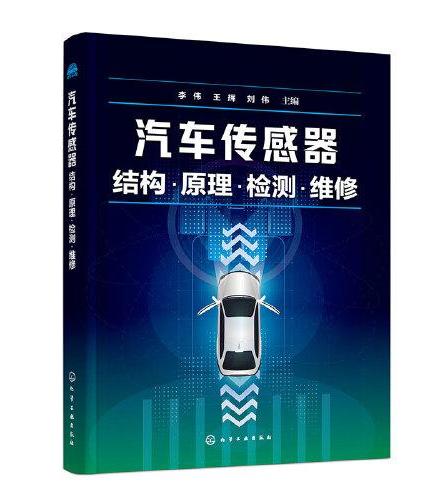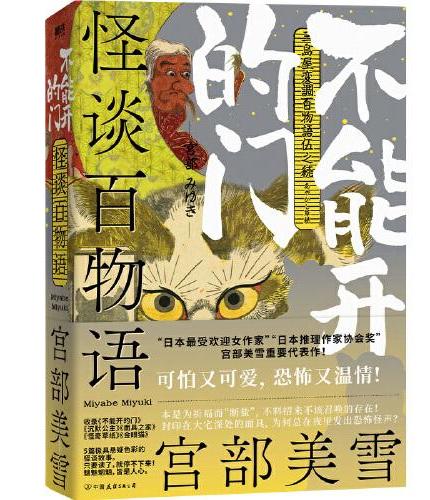新書推薦:

《
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
》
售價:HK$
147.2

《
国家豁免法的域外借鉴与实践建议
》
售價:HK$
188.2

《
大单元教学设计20讲
》
售價:HK$
78.2

《
儿童自我关怀练习册:做自己最好的朋友
》
售價:HK$
71.3

《
高敏感女性的力量(意大利心理学家FSP博士重磅力作。高敏感是优势,更是力量)
》
售價:HK$
62.7

《
元好问与他的时代(中华学术译丛)
》
售價:HK$
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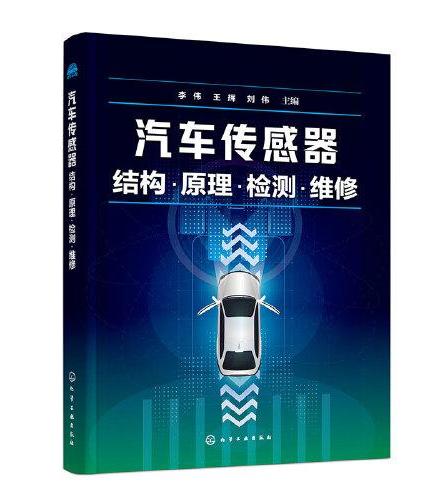
《
汽车传感器结构·原理·检测·维修
》
售價:HK$
1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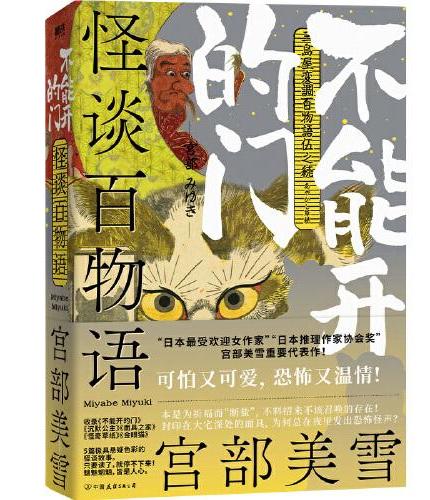
《
怪谈百物语:不能开的门(“日本文学史上的奇迹”宫部美雪重要代表作!日本妖怪物语集大成之作,系列累销突破200万册!)
》
售價:HK$
66.7
|
| 編輯推薦: |
《观念之色:中国传统色彩研究》:深入探究中国传统色彩观念背后的成因。
《观念之色:中国传统色彩研究》是国内学界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传统色彩的学术著作,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和创新性。
|
| 內容簡介: |
中国传统色彩运用的核心是“观念”,体现为极为明确的政治、伦理、文化目的性。中国传统色彩观念是一种目的性设计,由此形成了一种独立的色彩系统观念,具体呈现在诗歌、文学、绘画、生活器用的色彩表现上,中国传统色彩也因此获得了独立于西方色彩体系之外的身份存在。
《观念之色:中国传统色彩研究》为中国传统色彩的专题研究,重点研究中国传统色彩系统观念的自然演化、目的性设计,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传统色彩运用、观念演化过程中的色彩事件。通过从中国历代史料及出土文物、古代图像出发,寻求一种有关“中国传统色彩系统观念的文化想象”,并由此探讨中国传统色彩系统观念的可能成因及建构机制。本书试图梳理出一个中国传统色彩系统观念的基础成因,因此在所涉及的时段选择上,从基础生成的先秦出发,经由秦汉、两晋南北朝至中国传统文化最终成型的唐、宋时期。
|
| 關於作者: |
陈彦青,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学博士,现任职于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主要从事视觉符号学、色彩学研究及现当代艺术批评。
主要科研成果为:2012年,主持研究汕头大学文科科研基金课题“中国传统色彩暨间色系统研究(唐、宋年间)”。2013年,《〈中华古今注〉记秦始皇“三品绿袍”之误》发表于《装饰》第二期;《中国传统色彩系统的观念设计及其历史叙事》发表于《南艺学报·美术与设计》第二期。2013年,《中国色彩系统观念建构一种:间色的转换》发表于《新美术》第四期,并被《人大复印报刊资料·造型艺术》第六期全文转发。2013年,出版《中国现代艺术与设计学术思想丛书·乔十光》(主编)。
|
| 目錄:
|
目录
序 杭间
第一章 引 言
一、中国传统色彩系统观念的存在
二、中国传统色彩系统观念的成因及其目的性建构
三、色彩观念调控下的时代色相
四、必须重新审视中国传统色彩中“传统”的问题
第二章 中国色彩系统最初生成(先秦时段)的表现
一、不清晰但存在的“前色彩系统”
二、五方位与五色观
三、从历时“玄黄”到共时“五色”
四、中华色彩系统基础建构之初成
五、“五德终始说”统摄的色彩世代及政治、伦理建构
六、先秦(战国)时期色彩运用:色相及色彩词
第三章 秦、两汉(兼论新莽、三国)色彩系统建构及表现
一、秦朝的色尚选择及色彩表现
二、“赤—黑—黄—赤”:反复的西汉色尚
三、被忽略的新莽与东汉的必然选择
四、色彩禁色的初现和色彩等级(东汉)的表现
五、东汉时期的色彩运用:色相及色彩词
第四章 两晋南北朝色彩系统表现
一、晋朝的王朝色彩选择及“金行服赤”之疑
二、南朝宋、齐、梁、陈的色尚选择
三、北朝的行次、色尚选择与问题
四、南朝色彩系统的等级表现及色彩事件
五、北魏制度改革下的色彩等级表现
六、北周色彩等级表现
七、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色彩运用:色相及色彩词
第五章 隋唐、五代色彩系统建构及色彩表现
一、隋唐色彩象征的选择、色彩建构
二、等级色彩观念的新建构——品官服色
三、释、道色彩的世俗化及文化影响
四、从文化意蕴而来的色彩感觉细化
五、唐朝“焕烂求备”的生活色彩
六、隋唐、五代时段色彩运用:色相及色彩词
第六章 两宋兼涉辽、西夏、金的色彩系统表现
一、宋、辽、金的王朝象征色彩选择及其相互关系
二、宋朝色彩系统下的政治伦理结构及等级制度(兼论辽、金色彩等级)
三、间色“紫”的尴尬
四、两宋年间士人阶层政治、生活态度的转变
五、两宋时段生活色彩的各种表现
六、两宋兼涉辽、西夏、金时段色彩运用:色相及色彩词
第七章 作为生活色彩系统关键的间色表现
一、间色的身份转换
二、中国色彩的文化意蕴及其展开层面
三、小结
第八章 结 语
一、基本色彩观念背后的思想史典型体现
二、色彩系统建构的基本模式:特定条件下的身份转换
三、色彩意蕴的阐发:色彩禁僭现象之外间色发展的结果
四、水墨:另一个精神色彩系统的存在
五、结语之结语
参考书目
后 记
|
| 內容試閱:
|
在有关中国传统色彩研究的广博范围内,本书的重点落在了中国传统色彩系统观念的自然演化、目的性设计,以及与此相关的中国传统色彩运用、观念演化过程中的色彩事件上。通过从中国历代史料及出土文物、古代图像出发,寻求一种有关中国传统色彩系统观念的文化想象,并由此探讨中国传统色彩系统观念的可能成因及构建机制。由于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梳理出一个中国传统色彩系统观念的基础成因,因此在所涉及的时段选择上,从基础生成的先秦出发,经由秦汉、两晋南北朝,至中国传统文化最终成型的唐、宋。
之所以选择唐、宋作为一个结点,主要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生长、成熟,到唐、宋时期可说基本成型。正如傅斯年先生在1918年的《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所说:“就统绪相承以为言,则唐宋为一贯;就风气异同以立论,则唐宋有殊别。然唐宋之间,既有相接不能相隔之势,斯唯有取而合之。” 傅先生所言,正是多数史家所采用的做法和观点。而《剑桥中国隋唐史》所举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的观点,也认为“唐代和宋初代表着中国‘中世’的终结和‘近世’中国的开始” ,而这一过渡期间的历史,无疑具有无法拆分的一贯性。
一、中国传统色彩系统观念的存在
(一)中国传统色彩系统观念研究的基本意义
对于中国设计史研究而言,我们的关注重点大多落在现当代这一与我们所处时代密切相关的时段,而对于中国一直生长着的,从文明开端就未曾间断的传统设计观念,却有所忽略,这其中就包括了对中国传统色彩系统的研究。
我们在当代设计的色彩运用中,其实已经从某种意义上被动地忘却了自己的历史和传统。而我们在试图重拾传统之时,却又不知如何下手。因为,我们大多已经把中国传统色彩当成了历史的存在,表现为一种进行自我割裂的状态。这其中的关键在于,我们理解中的中国色彩已经被多数人认为是某种历史的碎片,或者说是一种曾经的视觉化的色相存在,而非一种观念。但中国传统色彩最重要的存在意义,又恰恰是“观念”。在很多时候,这种“观念”的存在有着强烈的目的性设计,并表现为很多色彩事件的产生。它是一种关于社会建构的认识表现,也体现在充满了文化意蕴表达的多层解读中。
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如中国一般,在历史与文化、政治、经济生活中受到“色彩”观念的深刻影响。不论是朝代更替、等级制度、生活与经济生产,似乎都被笼罩在以“五德终始说”为主导所支配的“五方正色”之中,而论及中国传统的色彩观念时,“五方正色”也似乎被“必然”地作为论述的重点和不多的选择。但实际上,与“五方正色”相伴而存在、互为主体也同样重要的“间色”系统,却少被提及或被一言带过,严重失衡。而在中国传统色彩系统的建构机制中,正色和间色的身份实际上并不是稳固的,在有限制的条件下,两者可转换。
正是在这种认知的状况之下,对中国传统色彩的认识难以避免地走向割裂和失真,失去了其试图置入的“真实生活”。《礼记·玉藻》中言“衣正色,裳间色” ,可见“间色”系统至少在春秋战国年间就已经被应用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了,此后在历朝历代的各种典章制度及经典文论里也多有论及。单《红楼梦》一书中出现的颜色词,就多达一百五十五种 。而通过笔者的梳理和研究,传统色彩甚至多达三百多个色相 。若“五方正色”的五个颜色真的在历史中基本保持其不变的色相的话,那这间色的数量实在是蔚为壮观,正如《孙子·势篇》所言:“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 那么,只记住这五个如结构般岿然不动的“青、赤、黄、白、黑”,而忽视“不可胜观”的间色系统,对于我们试图还原一个传统的色彩文化及其鲜活的历史存在,是不可能获得一个更为贴近的“真实”的。若“五方正色”如语言的结构般稳固不变,那么,间色的应用其实正如语言中语境各异的“词”的替入,而“意义”的产生,也在于此。
对于中国传统色彩系统应用的研究,并以此寻找一个以“正色—间色”为核心的饱满的中国传统色彩系统,虽艰巨但却是必要的。其意义在于,重新还原和认识中国传统的色彩观念,寻求一种生活的真实,并期望以此能对当下中国的色彩观念、文化认同提供一种认识“自我”、“过去”与“现在”的观照。
(二)色彩学研究的基本格局
色彩研究的格局基本上分为四大类别,即原理性色彩研究、应用性的色彩研究、思想性的色彩研究及概论性的色彩研究。
对原理性色彩研究的了解是每个色彩研究者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它是色彩研究课题是否能够真正深入的关键,将在某些层面上对本书的写作起到原理支持和基础理论准备。在原理性色彩研究上,早期的色彩学家多为此事。现代意义上的色彩学的建立,很大部分是从牛顿的光学实验开始,而属于中国色彩本身的研究,要延后很多年,但并不能因此说中国人对于色彩的研究是一种空白,只不过在中国历史中,关于色彩问题的关注采取的是另外一种方式,一种完全有别于西方从牛顿肇始的现代色彩学式的思考。
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关注光学现象,比如墨子的光学八条 ,但此后并未有更大发展。中国先民在此时期已经对自然繁复多变的色彩进行了有目的性的提纯,比如对于五方正色和间色的描述及现实生活的应用,并且形成了稳固的一套色彩应用系统。这些关于色彩的描述虽无专论,却散见于历朝历代的各种文献之中,形成了一种独特而强大的色彩观念,较早的有关色彩系统“正色—间色”的描述在中国早期最重要的典籍《十三经》里,可谓无处不在。比起西方,中国人对于色彩的态度更为明确也更实用,它直接影响了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也无时无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真实生活。
而对色彩的变化,战国军事家孙武在《孙子·势篇》中便已经看到了色彩混合搭配的无穷可能:“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 虽然他的目的并不在谈论色彩而在兵事,但这种看待色彩的方式其实正是中国色彩在它几千年的历史中主要承担的角色。真正可以算是谈论色彩原理的较早记载,我们可以在唐朝陆羽的《茶经》里看到:“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清代早期的博明在《西斋偶得》“五色”条中就阐明了三对色彩的“自然之对”:“五色相宣之理,以相反而相成,如白之与黑,朱之与绿,黄之与蓝,乃天地间自然之对,待深则俱深,浅则俱浅,相杂而间色生矣。”并进而发现,“今试注目于白,久之目光为白所眩,则转目而成黑晕,注朱则成绿晕,注黄则成蓝晕。错而愈彰,黼黻文章之所由成” 。比起同时代西方物理学家牛顿对色彩的认识,其实是更为深刻的。
在西方色彩学中,早期的牛顿走的正是一条所谓的“科学”色彩研究之路,但他从光学入手的色彩研究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西方美学家的猛烈抨击,其中以德国文豪歌德为最重要的代表。从此开始,西方色彩学研究便走了两条看似互不待见的路,一条是以牛顿为开始的光学色彩研究之路,另一条路则是以稍晚于牛顿的英国人哈里斯在1766年出版的《色彩的自然系统》所基于的色彩自然的真实体验研究 。
与西方色彩学相比,中国基于西方色彩体系的当代色彩学研究起步较晚,虽然也出现了部分相关研究,但由于游移于西方色彩体系的强大话语和对中国传统色彩体系的狐疑之中,故而在应用性的色彩研究上较少创建,还在摸索之中,反而是在色彩的思想性研究上着力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有姜澄清《中国色彩论》、牛克诚《色彩的中国绘画》 、彭德《中华五色》 、王文娟《墨韵色章——中国画色彩的美学探源》、李应强《中国服装色彩史论》、曾启雄《中国失落的色彩》 、杨建吾《中国民间色彩民俗》 等。这些学者为中国传统色彩研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总的来说,这些关于色彩的研究大多以史带论,对于色彩美学思想史的描述有着各种充分的描述。
当代有关古代色彩技术研究的文献极少,这其中曾启雄的《中国失落的色彩》可以说是较为丰富的了,但如果是作为专论的话,基本是没有的。有关中国古代色彩技术的描述大多散落在其他文献及专著中,重要的主要文献有:吴淑生、田自秉先生的《中国染织史》、赵丰的《中国丝绸通史》、黄能馥先生的《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历代织绣珍品研究》、郑巨欣的《中国传统纺织品印花研究》等。《中国丝绸通史》是其中比较系统阐述中国古代染色发展脉络的一部著作。
与此同时,也有学者在努力实践着色彩学的社会运用,并试图将其渗入一个更为广泛的跨学科的领域里。 此外,还有相当多的中国色彩研究学者从局部入手,进行传统色彩学的研究,也获得了较为重要的成果。 在色彩的思想性研究上,另一个重要方向是关于色彩语义学的研究 。而概论性的色彩研究在四个研究类别中可说是数量最多的,不一而足 。
二、中国传统色彩系统观念的成因及其目的性建构
(一)色彩观形成的最初脉络
自然界的色彩千变万化,无法胜数,但在先人的视觉体验里却是慢慢形成某种认识和观念的,我们现在所能感觉到的色彩,已经是数千年来各种文化、认识、观念下的产物了。
综合各种史料、出土文物的发现及相关研究成果的分析,中国古代早期色彩观念的认识、色彩的使用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其色彩观念的生长推论如下:1.浑然一色——2.二色初分(阴阳、黑白、纯杂)——3.三色观(黑、白、赤)——4.四色观(黑、白、赤、黄)——5.五色观(黑、白、赤、黄、青)——6.玄色统辖下的五色系统(玄黄——黑、白、赤、黄、青)及间色系统的产生。它们的生成和演化有着一个自然生长以至目的性建构的过程。
(二)另一种中国思想史:从“相克”革命到“相生”禅让的“五德终始说”的色彩观念转换
以五行说为根本的“五德终始说” 的建构其存在基础,是华夏先民带有目的性的一种建构。但后人一谈阴阳五行,大多将造用者视为战国年间的驺衍。
驺衍的理论结构严密,从其当下上推黄帝直至天地未生之时,建构了一个涵括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理想世界。更重要的是,这个理想世界是可以从逻辑上来进行推论预测的,目的就在于“用”。而且,其清晰的关系建构让这一说法变得可用。这也就难怪,从“五德终始说”出发的五色观可以在中华文明中盛行不敝。
中国传统色彩在现实生活世界中的运用及表现,在先秦获得了一个较为自由的生长阶段,到战国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中华文化色彩系统,我们称之为“前色彩系统”。其定义的要点在于,这一色彩系统更大程度上是自发的,其中虽也有人的意志存在,但并非是一种强烈的、目的性明确的、有意识的人为建构,更多的是一种自然生长的形成。
与色彩系统的建构息息相关的“三统五德”观念虽肇始于先秦,但其被利用却是到了下一个大时段才真正开始,这一时段涵括秦朝、西汉、新莽、东汉和三国,色彩和其他各种文化要素一起成为了统治阶层建构社会权力结构、政治、伦理观念的关键。在这一中华文化性格真正建立的大时段中,结束了西汉王朝的新莽政权虽然仅存在短短的十五年,但王莽的改制及其苦心经营的汉王朝的禅让,却对此后的中国历史发展模式影响巨大。因此,虽然新莽在历史中很少被作为一个王朝被提及,但在关于中华文化、政治观念建构,特别是色彩系统建构的讨论中,却显得十分重要,值得专文讨论。
从秦朝开始,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对自己王朝的“色尚”非常重视,并将其看成是王朝正统性表现的象征之一。但采取何种色彩,又依据何来,却有多种考量和选择。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汉取代秦朝之后,在“色尚”上便出现了数次反复;而王莽的改制及“色尚”选择背后,又充满了各种目的,甚至设计;东汉开国,制度虽有新创,但对新莽一套又多有继承,其象征色彩的选择是对西汉的一种间接认定,或者说,在我们对西汉“色尚”究竟如何尚存疑问时,东汉的“色尚”选择让这一疑问的答案渐趋明朗。故而对于这一大时段“色尚”变化的认识,可以让我们较为清晰地窥见中华文化、政治观念建构,特别是色彩系统建构的生成过程。
从秦用水德到东汉确定火德,中国古代王朝对于王朝象征的主要取用方式历经了从“五德相克”到“五德相生”的思维模式转化。西汉年间,关于“德”、“色”取用的游移不定深刻地体现了这一大时代的思想转化。“五德终始说”和“五色”观念作为影响了中国历史数千年的文化思维模式之一,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和方向。相生和相克背后是看待世间万物基本规律的不同选择,也表明了这一文化主体的精神内核所在。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此后的社会制度、道德伦理建构,并影响这一文化体的文化思维模式和国民文化性格,进而影响更为具体的身体性的体验,比如视觉,比如更为具体的视觉中的色彩体验。
(三)中华色彩系统的基本构成:正色与间色
中国传统色彩系统的最根本构成是中华五色与间色,即“五方正色:青、赤、黄、白、黑”及以各色调配合成的间色。正色是色彩系统的构成主体,或曰结构、骨架,但并非中华色彩之全部。中华五色与间色形成了一种相互作用、互为主体的关系。
1.被置入生活系统的视觉存在
中国传统色彩系统被置入的,应该是一个大生活系统。色彩系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生活系统的一种体现,以视觉表达的形式出现。而生活系统直接面对的,即是一种“生活”的“真实”或“现实”。生活系统中的“生活”以一种观念上的真实——视觉上的中华五色及间色表现出来,而其中,间色则成为现实生活丰富多彩更为主要的表现。从“丰富多彩”一词中,我们也许可以看到,生活中的人们内心对于视觉世界的某种期待,而这种期待,也并不仅仅在于多彩的色彩世界吧。
2.正色与间色的基本构成关系
那么,作为大生活系统主要构成关系之一的色彩的生活系统又有怎样的基本构成呢?首先需明确的是,“生活系统”的最基本构成,即“个体—整体”的基本关系。“个体—整体”的维系和运转是生活系统最基本的运作。整体与个体形成了无法拆解的关系体。整体也许更多地以结构的形式出现,它遵循着某个更高的规约,而个体更多地体现了其既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又保有自己精神存在的个性。作为五种色相,五正色本身以一种个体的方式存在,并潜入到色彩的生活系统之中。正色观念就像是一个统摄系统的整体,而间色则更多地体现为面貌各异的个体。个体在某种层面是服从于整体的,间色的存在既依赖于正色,又体现出差异变幻的倾向;当其需被归类时,则又自动归队在五色系统的色系之中。在《礼记·玉藻》中,正色与间色的关系被表达得非常清楚,并明确了其运用的关系:“衣正色,裳间色。非列采不入公门。振絺綌不入公门,表裘不入公门。 ”
在其进一步的解释里,展现了五正色和五间色的色彩系统。五正色分别为“青、赤、黄、白、黑”,而五间色则为“绿、红、碧、紫、駵黄”,皆是正色相配而成。然而,五间色呈现出其强烈的存在。可以说,这十个分别占据方位的“正色”和“间色”,便是中华色彩系统最基本的构成。
3.更大个体的存在:凌驾于“五正色”之上的强大“杂色”(间色)
有时,某些个体会因为其异样的强大而影响了整体的运行,这种影响在中国传统色彩中体现为“玄、纁、紫”等色的存在。如果从色相来说,它们无疑应被纳入间色之中。
《周礼·考工记》中“六入为玄” ,若以正色必纯的标准,玄分明便是杂色,应处于间色系统之中。但是,它们在色彩历史中又堂而皇之地在某些特定时段里被等同为正色的一员,其地位远远超越了五正色中的某些色彩。特别是作为象“天”的玄色,更是远在五色系统真正形成之前便已在先民的色彩运用中占据了至高的地位。《礼记正义·玉藻》正义曰:“玄是天色,故为正,纁是地色,赤黄之杂,故为间色。 ”
“黑”因其纯而为正,玄色六入而近于黑,但它毕竟还是不纯之色。但因其象“天色”,“天”为最难测的一种威权象征的存在,也因此,在明确“青、赤、黄、白、黑”为五正色的同时,也将“玄”色以正典的形式纳入“正色系统”之中。甚至,这玄色更像是一种俯视“五方正色”的更高的色彩存在,是一种统摄之色。若将这各种色彩的构成以立体视之,则“五方正色”处于中间平面上,而“玄”及“冥”却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了。玄为杂色,象天;纁为杂色,象地,其指向可被视为一种更大的空间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实在,可以容身万物。正色于人间各处一方,是有指向的方位,为虚的存在,然而却为纯色,其中的深刻含义,实待深析。紫色也为杂色,却又在大多历史时段成为人间最贵之色。从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作为杂色的这几种颜色,其所承载的意义及象征,更多是以“整体性”的面貌出现,是一种各色皆在的“大”杂色,更涵括了作为“五方正色”的“青、赤、黄、白、黑”。
这种强大的个体对整体的影响改变了整体的结构。玄、紫二色改变了五色的结构,以至于“青、赤、黄、白、黑、玄、紫”的色彩结构在中华传统色彩的历史上长时间地占据着主导地位。
(四)间色系统的产生
那么,间色系统是如何产生的?它与正色系统的出现又有什么关系?从中国传统色彩系统的产生来看,它经历了一个从最初的复杂到简单,又从简单到复杂的过程。
何谓“最初的复杂”?我们必须回到色彩应用之前的世界。当先民最初决定选择应用某个颜色时,他眼前的世界呈现的是何种色彩状况呢?他直接面对的,将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自然系统呈现出来的变幻莫测的色彩。而若从后来中国色彩系统的定义来看,当时的这些色彩无疑更近似于间色。因此,我们若出于描述的方便考虑,需要对这种“最初的复杂”加以命名的话,“前间色系统”也许是较为适用的。此时的先民对于色彩的应用,无疑与“思想”没有多少关系,其决定性的因素,是身体性的本能反应,或如对天地变幻、草木枯荣的感受,又或如对锦翼翠羽的欣赏,等等,莫不如是。
从万千自然色彩中被提纯应用的五正色之最初,除了视觉感受,也有材料便于运用的因素。在视觉上,五色中“青、赤、黄”三色正是现代西方色彩理论中的三颜色,而“黑、白”二色虽未被西方色彩理论归为色相,但被作为色彩明度的两极。 可见在色彩的身体感受上,人类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只不过归类各有差异。这是五种最为本质与纯正的中国色彩,是思想单纯的先民身体感受最强烈的色彩感觉。
从最初的复杂到简单,色彩的应用经历了一个选择的过程。这几种被选择出来广泛使用的色彩,在生活世界的现实应用中又慢慢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变成了某种社会的秩序。“五色”与“五行”、“五方”等构成了社会伦理的运行机制,意义也从原来的简单再变为复杂。这种重生的复杂,与原初的复杂性已经完全不同。原初的复杂是色相变化的复杂,是自然界呈现给先民的视觉现象;自然界的这种呈现是主动的,先民只是被动接受而已。而重生的复杂却表现为思想,即简单的五色“青、赤、黄、白、黑”被人为地赋予异于色彩本身的、与人类社会活动相关的更多的意义与象征。正是由于与社会活动的密切相关,作为一种配置,间色系统随之而生,成为社会秩序的必要成分。
这种随着“主—从”、“正—间”而产生的社会伦理性结构并非间色产生的全部原因。当五种简单色相被按照方位、季节、相生、相克和等级严密地嵌入时,极具稳定性的色彩结构便产生了。
然而,因其系统的稳定,难以避免地在现实生活应用中呈现出简单和寡味。而身体的感受在本能上,寻求丰富和新鲜感的身体需求又是难以压制的,因此,从简单的五种色相转向复杂的色相追求,也变成一种必然,比如间色。而对以间色为代表的复杂色相的追求,往往又在某种程度上冲击着作为正色的五色的地位。因此,才有了孔子的“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夺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才有了历朝历代对色彩的专用和禁用的反复强调。
就间色而言,因其依附于正色而生的现实,以及作为色彩系统子系统的存在,必然具有自身的运行规律,并表现为某些行为及痕迹。作为间色系统本身,它难以计数的色彩之间也存在着各自的关系,并一如正色般表现为某种等级关系。只不过,对于间色系统而言,它们的这种关系又是相对随意而多变的,表现出灵动活泼的一面。
相对正色而言,间色本身一开始就被认定为“卑贱”之色。虽然这种“卑贱”的形容更多地来自规定者的认定,但不可否认的是,认定间色为低下、卑贱者的规则的制定者,是承认间色的有效存在的。间色甚至被大量使用在重要的场合,只不过,对于它们的使用基于某种使用原则。《礼记·玉藻》中“衣‘正’裳‘间’”的说法是最为权威的说明。
从历代《舆服志》中的各式车、服的颜色使用来看,间色的应用无处不在。而对于这些应用在历代礼制中的间色,我们是否可以将其认定为间色系统中最上面的一个等级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如果我们的判断是基于五色系统的应用逻辑的话。与最高层次的五方正色相互配合应用于最高级别的皇家礼制中的间色,其重要性是明显的。而且,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些重要的间色在皇家或臣工的常服中,有时并不以搭配正色的角色出现,有时它们甚至就是常服的主体颜色。
间色系统另一个更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其常常成为历代民间的时代流行色。而这一点似乎成为时代的一种现象,特别是在几个文化、经济繁盛的时代,表现得更为强烈。这种现象最后往往会引起朝廷的关注,并因此引发了关乎礼制与纲常的相关讨论。
由于在所谓的正色运用上轻易不敢僭越,而间色的规约又不太严格,为色彩应用提供了相当的灵活性。并且由于间色本身的多变,在理论上也与流行的短时效性相近,因此,间色成为历代民间的流行色也就是必然了。
而除了宫闱间的常服和燕居之服为民间的流行色提供了一定的仿效外,民间流行色的间色应用的另一个重要源头则来自与间色身份相符的青楼之类的“卑贱之地”。大胆变化与推陈出新的色彩运用,也多由此处而出,甚至可以说,“卑贱之地”正是以间色系统为主导的流行色的主要策源地。
(五)正色和间色的身份转换及不同等级色彩系统的叠用
正色和间色的使用在中国传统里其实并非一成不变的身份认定,它们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系统建构的结构观念,即一个事物的运转并非个体的自存在,而是各种结构关系相互配合运行的结果。正色和间色在实际运用中,是有机制转换的,整个中国传统色彩系统其实是由各个等级不同的系统组成,形成了一种历时和共时性的关系。
《考工记》里谈五色并涉玄黄搭配,其实已经涉及了另外一个问题,这里面,隐藏着古人在思考、建构五色系统时非常缜密的系统观念。而其关键就在于“玄”所承载意义的改变。天和地是在先民思维中最容易,或许也是最早形成的对世界的认识,那么在文化色彩观念中开始将色相有意识地进行附和时,天玄和地黄便成为了一对稳固的色彩搭配,成为了等级最高的一对色彩搭配,在五方五色之上。
五色是一个系统,是与人直接相关的方位系统,与生活直接相关。而“玄”的加入,则是色彩系统的进一步升级。天玄作为一种更高的存在,是威权、神秘、未知、过去、未来的象征,而五色则指代着现在。加入“玄”之后的六色概念,其实可以看成是“玄黄”系统,在这个系统下面,“黄”的指代已经涵括了五色。所以,在中华古代色彩观念中,存在着不同层面的色彩系统,玄黄系统是最高等级,象征人神关系,是一种历时性的关系;五色系统是次一等级,是生活世界的系统。虽然五色五方也都附丽神明,但所指代之事,皆从生活中来,或事有大小之别而已,从这一意义看,五色系统无疑是共时性的。
在这种身份转换机制下,作为生活色彩最高代表的“紫衣红裳”在南朝宋明帝时期的出现,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色彩事件,“紫、红”作为间色的身份在这里被转换成一种正色的现实存在。与此同时,在生活色彩被体认的同时,等级色彩也越发严苛。这体现为历史上各种色彩禁僭的现象上,其中更以“借紫”现象的泛滥为代表。而作为等级色彩最为典型表现的品官服色制度,也在隋、唐被确认了下来。从品官服色的等级色彩设计方面看,等级色彩的观念先行表现得十分强烈,完全是一种观念设计的结果而非自然生长。而品官服色也在历史进程中被根据需要不断地进行着目的性的调整。
三、色彩观念调控下的时代色相
“色彩生活系统”在“大生活系统”中充当的其实是一种个体的身份,这一“大个体”呈现出变化的面貌,在历史各个时段表现不一。不管是“青、赤、黄、白、黑”,还是“青、赤、黄、白、黑、玄、紫”,它总会因在各个时段应用的变化而呈现出某种总体的色相。某种成分会在这一总体色相中占据主角地位,体现在时代里的表现便是“夏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 等现象。但是,时代的总体色相并不仅仅呈现为以朝代“色尚”呈现的色彩,时代颜色的整体意象综合了生活系统的各大关系,已远远地超越了“色彩的生活系统”。
(一)时代色相的主要构成因素
那么,在各个不同时期里中国的生活色彩体现为时代的颜色时,又是如何被构成的呢?这些呈现出来的色相里包含了色彩的不同层面,并被纳入某种相互交涉的关系之间。其中最为主要的因素有五个:
第一为“被规约的色彩”。这一行为的过程正是 “有意识”作用的结果。
第二为“身体自发性色彩”。它在更多的时候被归结为身体性的“无意识”行为。
第三为“文化意蕴阐发的色彩”。这更多地体现为时代的精神状况,是“有意识”的一种过程。
第四为“技术性色彩”。这是一种被技术“制约”的因素,而各个时代的时尚流行,有时则因为技术问题被放大,新的色彩的出现、对难以轻易生产的颜色的追求等,莫不如此。洪迈在《夷坚志》乙卷十五“诸般染铺”中所传达出来的,正是当时民间对于“技术性”的向往。
第五为技术性的色彩往往被纳入一种生产关系之中,与其相对并行的是另外一个重要因素,为“色彩经济”。在经济关系运行中,经济利益驱使下的色彩呈现,如《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五》 中所述春秋时齐国从上到下对于“紫色”的态度表现,也是无法忽略的。而在《荀子·王制篇》里,紫色之应用于衣服上,已是理所当然了。
(二)时代色相五种构成因素的相互交涉
以上五种构成因素的相互交涉与作用具体表现为几类:
第一,有意识的“被规约的色彩”对无意识的“身体自发性色彩”的作用。有意识的规约在规约者那里被放大,而在被规约者这里则慢慢地演化成一种潜在的意识,然后又作用、影响着身体对于色彩的感觉,比如“白色”意识的形成。从纯净之色慢慢地被规约为一种“凶丧”之色,并成为自发的身体性感受。
第二,有意识的“被规约的色彩”对有意识的“文化意蕴阐发的色彩”也同样发生着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说,“文化意蕴”的产生是依附于“规约”的,它并无完全自发的成分,这也是其“有意识”的原因。“被规约的色彩”因为自身稳定的结构性存在才让“意蕴”得以散发出来,并形成一种难以言明却又分明存在的文化体味和表达,是一种结构的溢出。
第三,有意识的“被规约的色彩”作用的另一个因素,则是“技术性的色彩”。这二者之间本身的内在构成极为相像,只不过,“被规约的色彩”更多的是一种主动结果,而“技术性色彩”则相对被动。此种主动与被动正是其关系运行之所在。“被规约的色彩”总是主动地把技术性生产出来的新色彩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而正如 “香色”、“柳黄”、“明黄”、“姜黄”之类的颜色,在它们被技术性地生产出来之后,被动地被纳入到“黄”色系之中,并又在此后成为另一类“被规约的色彩”。 自东汉开始,历代对色彩多有禁用,而所禁者即为规约。
第四,“身体性自发色彩”与“文化意蕴阐发的色彩”之间也同样发生着相互关系。文化意蕴的阐发在某种程度上即是对身体性色彩的不自主的表达,比如对各种环境色的直接身体反应的描述与发挥,而这种描述对象重点的观照,更多地恰恰不是五方正色,而是间色。比如在历代诗词和笔记之中的“天水碧”与“太师青”、“雨过天青”、“流黄素”、“猩猩血”,等等。这些充满了文化意蕴的色彩于后人而言,已经远远超出色彩的范畴,并被多层面的演绎,身体性的自发已经完全归宿于文化意韵之中了。
在这些关系之间,系统的运行并不会如上面所分析的那般被拆分成若干对简单关系,而是一种多方渗透、作用的过程。当然,在某些特定时段中,其中的某些因素会略微彰显,以一种更具主导性的姿态展现。但是,这种主导性的持续是短暂的,它总是被轻易地重新纳入整体的系统运行之中。
这种各要素的整体运行体现了中国传统色彩现象的复杂化。但正是这种复杂化的存在,才展示了中国传统色彩真正“意义”所在。这种“意义”所呈现的是一个整体,而产生“意义”的,正是“被规约的色彩”之外色彩呈现的变幻不定,即间色的运行。中国各个时代生活的整体色彩意象及其意义,因为间色系统的存在和运行而产生。
(三)外来者的色彩及融入
中国传统色彩应用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并非一成不变,总有一些改变在发生,但这种变动却是极微弱的。不同的时代,总是有某些来自异域的色彩以某种形式进入中国的传统色彩系统,而它们,往往成为某一时段的流行,比如胡服及佛教色彩的进入。很多胡服所采用的色彩被直接定义为间色,宋朝周密《癸辛杂识》中就有“胡服间色”一说。
而以佛教为代表的外来文化的进入所带来的新色彩的运用, 则使得中国传统色彩中的某些色彩的意义被添加,其源与中华五色系统本不近同,但由于文化的渗透及同化的作用,其色彩观念也在时代的进程中进行着自我微调。
四、必须重新审视中国传统色彩中“传统”的问题
由此而言,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关于中国传统色彩中“传统”的问题。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应用色彩,处于实际应用的现实之中。正如当下的中国色彩应用之现实。若从表面现象来看,西方的色彩体系和色彩认知无疑在当下的现实应用中占据了主导。那么,它是否已经完全取代了中国传统色彩系统了呢?答案是否定的。
中国传统色彩体系的产生及其基于的认知根本,最主要的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只要这种文化精神依然存在,根植于其之上的中华色彩便必然会顽强地生存着。当然,必须承认的一个现实是,当下的中国民众对于色彩的身体性体验已大大超出前代。而中国的传统色彩应用也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精神体现,更多地潜藏在精神维度里,并只是在某些时段适时地出现。虽然在大多数时间里,它呈现出一种隐匿的状态,但又常常让人觉得无处不在。
而西方的色彩体系也自有其根植的土壤,它们之于中国现代色彩的应用,更多的是在表象之上。似乎就像唐宋间的外来文化那般,但又分明不似唐宋年间只是五色系统的一种依附,倒像是有取而代之的企图,表现出一种强势的介入。然而,这种介入所必需的精神土壤至少在此时看来,与其色彩应用并不同步,它在某些方面改变着中国民众对于色彩的认知,但远未至取代之势。
正如中国传统色彩在当下应用中无奈的现实一般,间色系统所呈现的生活色彩,一到它触及社会结构、伦理底线之时,便会有某种力量将其纳入那个稳固的五色系统之中。就像在消化、转化、运用“胡服”及“佛教”色彩一样,西方色彩理念之于中国色彩应用,也处在相似的过程中,它也许会因为某一时段的强势让当时的传统色彩认知发生某些改变,但是,只要浸染中华文化的中华民众依然保有其最根本的思维模式及基本道德判断,就将不会产生偏离的结果,而是一种更适合于当下生活系统的、更为丰富、更具开放性,同时又保持身份与自尊的当代传统。古代也好,现代也罢,我们是不能以色相在简单运用中的变化(即表象)来轻易命名所谓的“新”传统,看色彩的眼睛的背后是观念,而观念总归要回到它精神的居所。
我们的讨论必须重新回到近代之前。因为,近代、现代、当代正处在一个延续的进程中,连接着未来。此时,我们无法给出一种判断式的结果,只能暂存不论。
当我们重新回到中国古代社会,去探寻古人看待色彩的眼睛及其背后的观念时,会发现色彩的观念其实并没有唯一性。从大的层面来分,有两者,一个来自士林、统治阶层,而另一个则来自民间。它们的观念的出发根本截然不同,一个将色彩当成媒介,指向庞大的社会结构系统运行,另一个则将色彩更多地指向身体性的感受。
中国色彩观念是复杂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基于整体的结构和系统,孤立的色彩运用是极为少见的。从色彩系统的成因和变化、转换来看,它已经不仅仅只是中国设计史上的重要一环,它甚至可以被看成是另一种中国思想史。设计史的研究视野本来就是开阔的,关于“用”的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身体性的“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