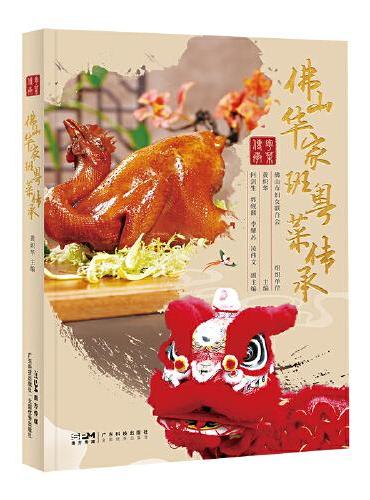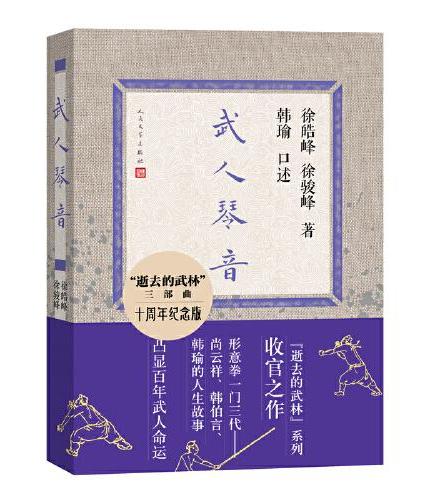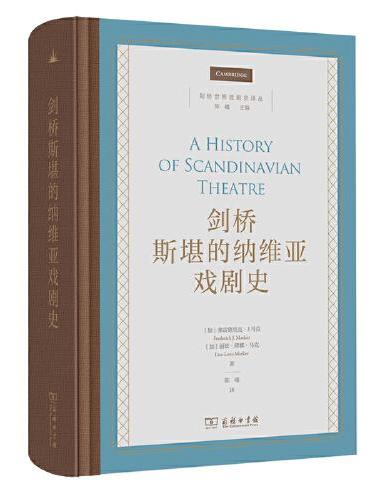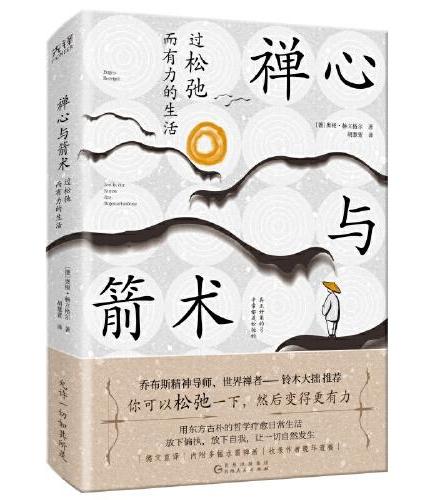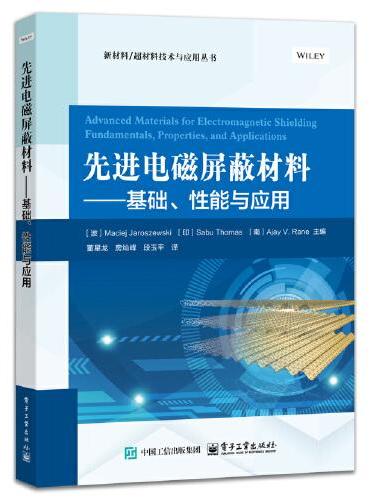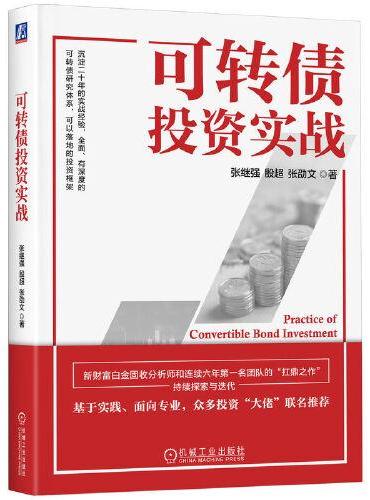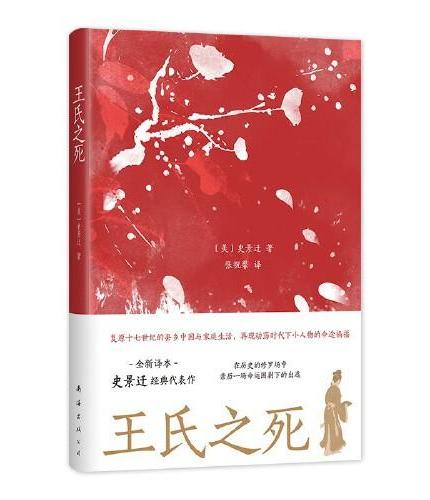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创客精选项目设计与制作 第2版 刘笑笑 颜志勇 严国陶
》
售價:HK$
6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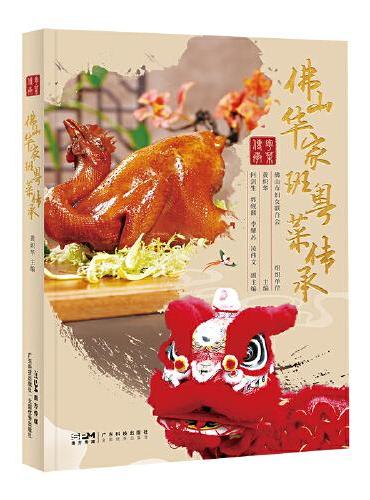
《
佛山华家班粤菜传承 华家班59位大厨 102道粤菜 图文并茂 菜式制作视频 粤菜故事技法 佛山传统文化 广东科技
》
售價:HK$
2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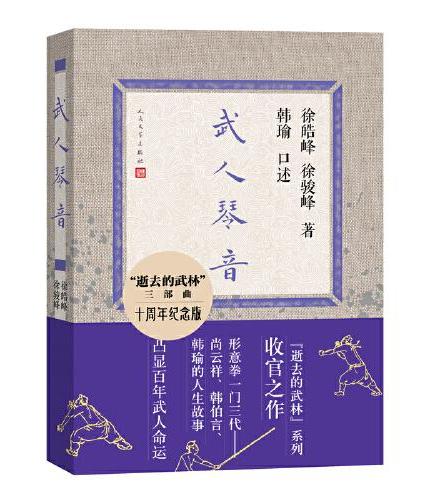
《
武人琴音(十周年纪念版 逝去的武林系列收官之作 形意拳一门三代:尚云祥、韩伯言、韩瑜的人生故事 凸显百年武人命运)
》
售價:HK$
4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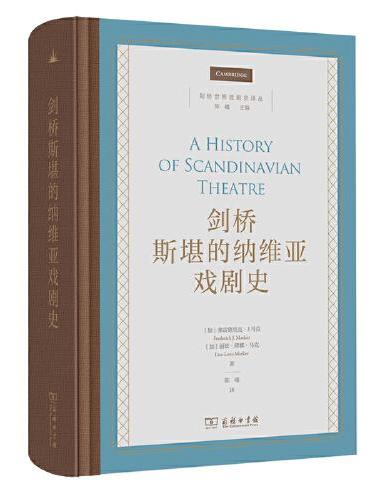
《
剑桥斯堪的纳维亚戏剧史(剑桥世界戏剧史译丛)
》
售價:HK$
15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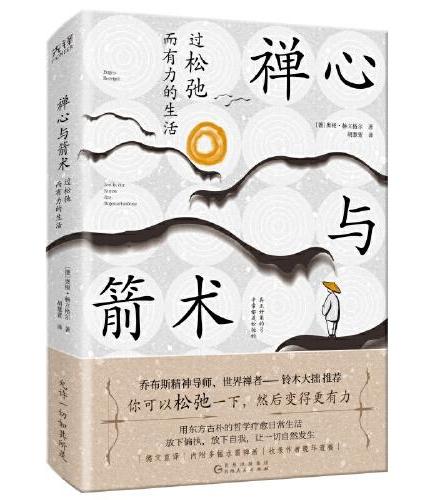
《
禅心与箭术:过松弛而有力的生活(乔布斯精神导师、世界禅者——铃木大拙荐)
》
售價:HK$
6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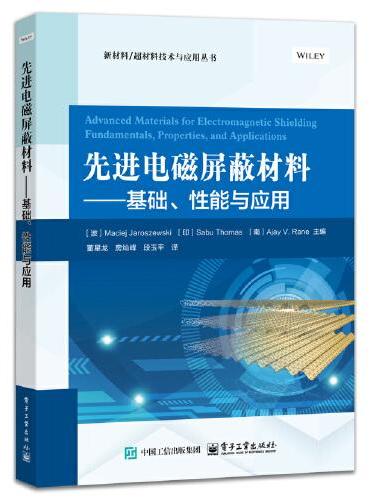
《
先进电磁屏蔽材料——基础、性能与应用
》
售價:HK$
22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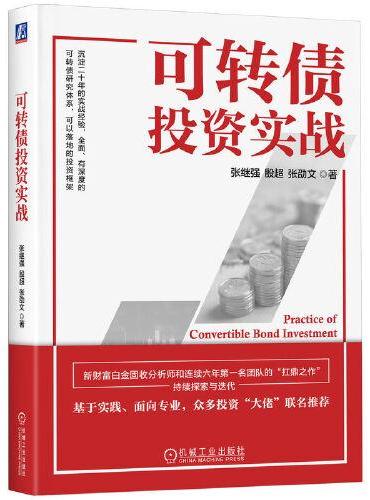
《
可转债投资实战
》
售價:HK$
9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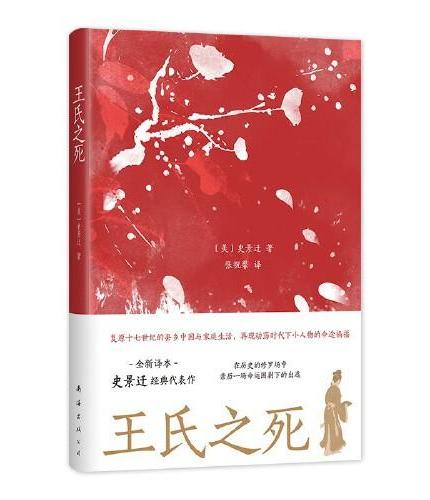
《
王氏之死(新版,史景迁成名作)
》
售價:HK$
54.9
|
| 編輯推薦: |
江山为聘,天地为媒。
腹黑高冷闷骚男vs医术无双痞子女。
入错房,嫁对郎,乾纲独断一双人!
千万里江山,百十里红妆,不敌三生三世相许,三日诉情长。
一个个令人意外的高潮转折,一段段令人飙泪的白首天涯。
他们的一日,曾比一生更长。
他们的三日,曾是三生三世。
2015年感动万千读者的最美禁忌之恋,令无数读者洒泪疯推的历史言情悬爱巨作!
如果不是为了一个人,谁肯枯守一座城。
他们一起经历了那寒风凛冽的芦花飞絮,一起经历了亲密接触的大狱,一起经历了大水中的棺材板,一起经历了杀人无形的繁华岸,一起经历了战场上的千军万马,一起经历了大漠里的执手天涯……
终于,赵十九回归了,这一次的王者归来,他要将江山付做那十里红妆,苍穹为媒,只为他宿命中的新娘,倾世笑颜。
回首此一番,面临十分险,走了九曲路,背着八仙局,破了七星阵,身在六月里,心系五月花,月下四静谧,血战三千里,只求双影曳,一点为红妆。终是踏破天行路,剑指江山誓红颜!
2015年感动万千读者的最美禁忌之恋,令无数读者洒泪疯推的历史言情悬爱巨作!
|
| 內容簡介: |
他与她在清凌河相会。
他与她在卢龙塞喝酒。
她为他在漠北的苍穹之下,破冰取鱼。
他为她在大雪的极寒天气,打貂做衣。
他说:“阿七长大了,要换新鞋了。”
可一个男人最无助的时候,竟是他贵为王爷,拥兵千万,却不能为她做一双合脚的鞋。若一定要拥有至高的权力才能给心爱的女人幸福。
那么,他肯。
他说:“我要给你一个婚礼,以天下之重。”
秣马厉兵,胜利在望,可阴山地底皇陵的爱情考验,却为他们带来了一场灭顶之灾。
……
情爱路,向来远。英雄血,总是痴!
权谋争霸、庙堂杀机、地宫宝藏、九宫八卦,
他与她,从京师到漠北,到漠北回京师,一步一脚印,一步一红妆。
|
| 關於作者: |
|
姒锦,潇湘书院金牌大神,行文从不拘泥于传统的言情套路,善于以独特的笔锋讲述不一样的故事,“阴谋与爱情并重,欢笑与泪水齐飞”,有“女海岩”之美誉。《名门盛婚》和《步步惊婚》出版上市热销,《且把年华赠天下》(原名《御宠医妃》)第一部上市一周全渠道断货,引阅读狂潮,长期占据各项榜单第一。作者言:人世孤独,遇情遇爱不难,难的是遇心。姒锦笔下的故事,都是遇上“心”的故事。
|
| 目錄:
|
目录
第一章 以毒攻毒
第二章 生米与熟饭的妖娆
第三章 初体验
第四章 一个温柔了岁月,一个惊艳了时光
第五章 卿卿我我,意浓浓
第六章 上善若水,大爱无言
第七章 上阵不离夫妻兵
第八章 蓬头垢面,也美冠天下!
第九章 因为在意,所以残忍。
第十章 阴山之危!
第十一章 翻手云,覆手雨
第十二章 为爱执念
第十三章 三日三生三世
第十四章 长歌扼腕
第十五章 顺手栽赃
第十六章 素手一翻,风云反转
第十七章 清算
第十八章 人一入戏,必有惊变
|
| 內容試閱:
|
正文
第一章 以毒攻毒
那人仍是不出声,就在接近床边时,突然,他一个跃身扑过来,扣紧夏初七的手腕,仿若黑暗中也可视物。哐当一声,她手上的匕首已落地。不等她挣扎,他突地将她紧紧抱在怀里,一张带了夜露的冰凉面孔压下来贴在她的脸上,浓重的呼吸间,是他磁性的低笑。
“小奴儿,想爷了?”
夏初七胸口气得一阵发抖。
“赵十九,我得罪你祖宗了?可吓死我了。”
夏初七说话向来彪悍。但一句“祖宗”吼出去,半晌没有听见赵樽回答,她愣了一下。她原是习惯了开玩笑,在后世这样骂一句,没人会说什么,可想想赵十九这家伙是一个迂腐的古人,“祖宗”是拿来供奉的,不是拿来骂的,她不由得有点心虚。
“喂?”
仰着头,她嘻嘻一笑,正准备向他道个歉,却见他支起身子,轻哼一声,“有辱斯文。”
夏初七松了一口气,伸手勾住他的脖子,压着声线笑问:“骂人是吧?晋王殿下贪慕女色,夜闯深闺,强压人妻,道德败坏,与我相比,究竟哪一个更加有辱斯文呢?”
赵樽不回答,手臂一紧,死死勒住她的腰,低下头,在她受不住痒的吃吃笑声里,寻到她软软的唇,狠劲儿地啃。她先是咯咯直笑,可在他力道极大的亲吻里,吸着他身上若有似无的轻幽香味儿,几天来的想念一刹那悉数入脑,于是小小挣扎了一下,便反手抱紧了他。
以唇相接。
黑暗模糊了人的视线。
可黑暗却让人的触觉与心思更为敏锐。
两个人都没有说话,只默默地吻着,没有什么花哨的动作,也没有传说中天雷勾动地火的猛烈,就那么拥抱,亲吻,津沫相渡,耳鬓厮磨。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拉着她侧躺过来,将她纳入怀里,长吁了一口气,轻声问她。
“阿七还没回答爷的话。”
脑子都被亲懵了,夏初七还记得什么。
“哪一句?”
他低下头,亲了一下她的额。
“这几日,可有想爷?”
想吗?不想他才怪了。
但女人,最是喜欢口是心非。
夏初七懒洋洋地窝在他怀里,慵懒地靠着他,手指头一下下有节奏地在他喉结上画着圈地玩耍,由着指下那一处坚硬顺着她的手指滑来滑去。她玩得兴起,拿指甲轻轻刮着它,轻笑一声。
“您要带了银子,我便想您。您若没带银子,我才懒得想您。”
赵樽手臂一紧,使劲敲她一下。
“不知羞的……”
在她吃痛的嘶声里,他抚上她的脸,掌心的温度烫得惊人。
“分明是有人耐不住深闺寂寞,约了本王来共叙旧情、同享敦伦的,难不成是爷记错了?”
“敦伦”这个词夏初七以前不懂,新近才学会的。这不是要大婚了么,那从来没有生过孩儿的诚国公夫人,便亲自言传身教了她许多“敦伦”之事,她这才晓得,“敦伦”这个听上去刻板、神圣、严肃的词,竟然是指夫妻房事。
先前她就有些想笑,如今听赵樽说来,又想到诚国公夫人那张脸,不由得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使劲儿在他胸口处霍霍着,叽叽出声,像一只偷到了油的小老鼠。
“好好好,我孤单,你寂寞,我们两个都难熬,行了吧?那爷,反正大婚的日子近了,今夜正逢月朗星稀,天气甚好,虽说没有红鸾照,没有花烛烧,也没有合欢帐,但我将就一下也是可以的……”
她捻调掐词地学着时下女子的忸怩劲儿,还没把这段台词念完,自个儿已经笑得趴在他怀里了,可他却没有笑,只在黑暗里静静地看着她,似乎根本就没有当她在玩笑,忽地一个翻身压过来,脑袋蹭在她的颈窝里,低低地说了一句。
“好,爷也将就一下。”
拍了一下他紧实的背,夏初七“去”了一声。
“行了别闹了,一会儿闹得有人难受了,我可是不管的。好吧,看在你今晚上翻墙越户也辛苦了的分上,我特地给你做了好吃的,就放在桌上。自己去尝尝味道,可有精进?”
她想把话扯开,赵樽却是不允。
“阿七不将就了?”
“……不将就。”
“那你戏耍了爷,要怎样补偿爷?”
开个玩笑也要补偿啊?夏初七抬头看过去,借着窗外的月色,见他棱角分明如精工雕琢的脸上,一双浅眯的眸子,平添了几分氤氲之气,声音不由得也柔了几分。
“您想要我怎么补偿呢?”
赵樽没有说话,鼻尖贴上她的鼻尖。
慢慢地,他的手指抚上她的唇,意有所指地嗯了一声。
“阿七得主动点。”
夏初七哑然,双颊顿时像被火烧了一般,耳朵尖似乎都快要着火了。几乎是下意识地,她张口就咬住他不安分的手指,直到他嘶了一声才放开。
“还敢不敢胡说八道?”
赵樽情绪不明地冷哼一声。
“不乐意就算了!狠心咬人,该当何罪?”
听着他不怒不愤却略带一点儿委屈的声音,夏初七突然心疼他了。想想他一个大男人,活了二十多岁都没尝过女人的滋味儿,确实也惨。做了一番深刻的思想斗争,她心里挣扎来挣扎去,跃跃欲试的好奇心占了上风,最终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你先吃东西。这个事,一会儿,一会儿再说。”
赵樽定定地盯着她,唇角微微一扬,随即起身去点了烛火,坐在桌案边上,揭开那个檀木食盒的盖子。等他看见里头那七块方方正正的玫瑰糕时,目光稍稍深了一下。
“怎么样,有没有感觉很惊喜?”夏初七懒洋洋地倚在榻上问。
赵樽转过头去,看着她在烛火下洋洋得意的小样子,眉头皱了一皱,“起来伺候爷吃。”
夏初七侧躺着,单手撑着脑袋,眼睛眨了一下,“有没有搞错?吃东西还要人伺候,你要不要我帮你张嘴呀?”
“倒水!就你那臭手艺,爷怕噎着。”
知道这人向来没什么好话,夏初七习惯了也就不当回事。伸了个懒腰,她笑着去拎了灶火上温着的水,给他倒了一杯放在桌上,打着哈欠坐在他身边。
“倒水一次,十两。”
“爷刚亲了你一回,抵销了。”
“不对,如今我身价不同了,郡主了,您得加价,二十两。”
赵樽雍容高华地咬了一口玫瑰糕,淡淡地瞄她一眼,有些感慨,“二十两?二十两可以买两个媳妇儿了。”
夏初七低笑一声,随手捋了捋披散的长发,托着腮看他吃东西,表情很是欢愉,语气却是不屑,“行啊,没问题。赶紧吃完走人,带着你的银子,去多买几个媳妇儿回府里,少来招惹我。”
“说真的?”赵樽扬眉。
“自然是真的!谁稀罕你,多少好男人排着队等我!”
“那爷可真走了?”
他作势要起身,夏初七气得直拍他。
“你敢!”
手挥出去,被他顺势捉住,握在掌中。
她抽手,他却不放,只饶有兴趣地看着她细白柔嫩的小手,唇角带出一抹促狭的浅笑。那只手上是一排修剪得整齐的圆润指甲,指甲泛着晶莹剔透的粉润光泽,令人爱不释手。
“爷的阿七,什么时候也长得娇滴滴的了?”
娇滴滴?夏初七汗毛都竖了起来。
“赵十九,你敢再肉麻一点儿吗?”
赵樽黑眸一眯,显然不太明白“肉麻”是什么意思,不过大抵也习惯了她嘴里时常冒出一些不太容易理解的词,只默了一下,便专注地看着她,眼波流转间,慢慢牵起她的手,凑到唇上吻了一下。
“味道不错。”
夏初七面上一红,“夸人,还是夸糕?”
赵樽眉头一皱,放开她的手,拈起一块糕来。
“糕比人,胜一筹。”
夏初七暗暗磨牙,“谢了!既然糕这么好吃,您可得全给我吃完。我辛辛苦苦做的,不多不少,正好七个,要是不吃完,看我往后还给不给你做!”
其实她早发现赵樽不爱吃甜点,可他却面色不变,只瞄她一眼,“罢了罢了,阿七如此记仇,爷便说实话了:玫瑰糕好吃,却不如阿七好吃。谁知美人意,销魂别有香?”
夏初七不是一个脸皮薄的姑娘,往常不仅说过比这更加没脸没皮的话,也听过各种各样的荤段子,眼睛都不眨。可人就是这么奇怪,要是她不在意赵樽,跟他说什么都无所谓,正是因为在意,这个男人被她放在了心里,哪怕是一句很正经的话,也能被她听出“余韵”来。
面颊一红,她斜睨过去。
“流氓!”
赵樽唇角微牵,露出一抹若有似无的笑意。
“小流氓。”
窗内红烛轻燃,窗外芭蕉影稀。
两个人坐在一处,吃着糕点,几日未见,自然有诉不完衷肠,闪闪躲躲的语气里都是那种说不知如何说,不说又觉得心里闹得慌的初恋情怀,还有便是深夜独处时,那剪不断理还乱的朦胧窘迫。
夏初七的心怦怦跳着,拈起一块玫瑰糕往他嘴里送去。也不知他是有意还是无意,一口将她的手指吃下去,还吮了一下。
从手指到心的距离有多远她不知道,只知道这动作赵樽做出来,实在太要命,就那么一下,她的身子便热了,“讨厌!”
赵樽眸子微暗,声音喑哑,“傻瓜!”
两个人说来说去,嘴里就没有半句好话,一个“讨厌”,一个“傻瓜”。可恋人之间的感情就是那么微妙,“讨厌”吃着糕点,总是看向“傻瓜”,“傻瓜”端着茶水,生怕“讨厌”噎着,又是拍背,又是递水,那脉脉温情。“讨厌”不像是真讨厌,“傻瓜”也不像是真傻瓜,“讨厌”刚毅俊朗,“傻瓜”娇俏可人,一来一去,你瞅我瞄,这情景看得窗台上鸟笼里的小鸟心神荡啊荡啊,嘴里不停地发出咕咕声。
窗外的月光都醉了。
屋子里静悄悄的,此时无声胜有声。
“阿七……”
吃了玫瑰糕,漱完口,赵樽终于想到了他应得的补偿,“爷吃饱了,可以了?”
他的声线极是醇厚,夏初七听入耳里,眼睫毛狠狠地一眨,只觉得心窝里像在涨潮,后浪扑向前浪,一浪高过一浪,一张脸憋了个粉腻腻如那白玉染红。
像要上战场一般,她终于下定决心,轻嗯一声,瞄向不远处的罗绡软榻。
“榻上去呗?”
赵樽唇角不着痕迹地跳了一下,“阿七是说……?”
“去不去?”夏初七又臊又不安。
赵樽眉梢一跳,不再多言,脱靴上榻。
看着他,看着他,夏初七口中的唾沫越来越多,咽了又咽,咽了又咽,方才无奈地羞赧开口,“先说好,这个事,我,我也没有做过……”
“嗯?”赵樽定定地看着她。
“嗯什么嗯?”
夏初七轻轻咬着下唇,不好意思地瞄他,心里很不平静,欲说还休,欲言又止,带了一点不明不白的尴尬,鼻尖上添了一层细细密密的汗,再一次,她重申,“我要做得不好,你别瞎叫唤!”
赵樽眸底噙笑,唔了一声,表示明白了。
夏初七犹豫了一下,“不行。你,你先闭上眼睛。”
赵樽深深地看了她一眼,果真闭上了眼睛。
见他老实了,夏初七的胆子也大了,她低下头,审视了一下他紧闭的双眼,确定他没有偷瞄,方才放下心来,压抑住狂乱的心跳,手指慢吞吞地搭上他领口的盘扣。一颗,又一颗,再一颗……颤着手解开盘扣,磨蹭了一会儿,手指慢慢滑向他腰间的玉带,松开,又往下……
“阿七……”赵樽猛地睁开眼,抓住她的手,眸底除了欢喜,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促狭笑意,“你这是要做什么?”
夏初七的脸蛋已然烧得通红。
“明知故问!不是你要我补偿你的?”
赵樽眸子微闪,一本正经地望着她。
“爷只是要亲个嘴,阿七你都想到什么了?”
夏初七双眼圆瞪,张开的唇再也合不上。
她敢保证,要是那把匕首还在手上,她一定立马捅死他。赵十九简直就是人间祸害,贼到极点,故意引导她胡思乱想,然后哄得她心甘情愿地应了,却又在最后关头戏耍她,让她丢脸,弄得她好像很喜欢那啥一样。
心脏怦怦怦如在敲鼓。
夏初七咬着下唇,瞪着他,一字一顿。
“赵十九,你,真,贱!”
赵樽大袖微拂,捏了捏她的鼻头,声音哑了。
“傻瓜,爷怎么舍得那样待你?过来,躺好。”
“还躺什么躺?”
夏初七憋了一团火没处发泄,恶狠狠地拍开他的爪子,赌气转过身去,不再搭他的话,却感觉腰上一紧。他勒紧她,往榻上一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把她压在下头。一时间,榻上流苏沙沙直响,榻前的珠帘哗啦声声,她挣扎了几下,恼羞成怒了。
“赵樽你个混蛋,你还想做什么?玫瑰糕也吃了,玩笑也开完了,你还不赶紧留下银子,回你的晋王府去,那里有的是小娘等着你回去睡!”
赵樽扬了一下眉,低笑,“爷就乐意睡你。”
夏初七气恼得不行,不情不愿地挣扎着,却被他束缚了双手,等指尖上的凉意被他干燥的大手温暖了,她的气也就下来了。
“算了,老子懒得理你!”
赵樽松了一口气,一只手揽了她的腰,把她贴在身前,唇角泛出一抹笑意,“不生气了?阿七,你若是真想得慌,爷自然也不介意……”
想得慌?他全家都想得慌!夏初七恶狠狠地瞪着他,觉得祖宗的脸都被她丢尽了。
“去去去,这辈子你都别想了。”
赵樽黑眸一暗,看着她,没了声音。
夏初七急吼吼地骂完,也没了声音。
屋子里一片静谧,除了呼吸,什么也没有。
四目相对,暧昧的气息在二人间流转。
他的双手不由自主地握紧,再握紧,紧得不能再紧,让她觉得再紧一下自己就被他给勒死了,他却再也没有动弹,石化一般僵硬了好久,那一双手又慢慢地松开,松开,再松开,直到他高大的身子咚的一声,翻倒在她的身侧,平躺下来,半晌不说话。
夏初七大口呼吸着,紧张之极。
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走路。
她当然晓得他怎么回事,知道他也很想。
“初哥初妹”在一起,又是在这样的时代,那尴尬,实在难以启齿。夏初七到底是一个后世来的人,她明白,这样夜闯姑娘的房间并且做出这样离谱的事,对赵樽来说已经是逾矩了,与她仅仅只是羞涩不同,他的心里不知有多挣扎。
“怎么闷着了?”她低低一笑。
身边传来他带着喘息的低叹,“离成亲也就一月而已。”
像是对她说的,又像是自言自语,他闷闷的声音乐得夏初七噗的一声笑了。她瞄他一眼,故意伸手过去,碰了他一下。可只一碰,便察觉到他的身子绷得紧紧的。
“晚上还回去吗?”为了不显尴尬,她咳了一声,换了个话题。可话一出口,她就发现,这个话题一样尴尬。
赵樽黑眸炯炯,突然张开手臂,“阿七,来爷怀里。”
“好。”夏初七乐呵呵地滚过去,任由他抱了,将头枕在他的肩膀上。他暗暗叹了一口气,“不回了。”
心里怪异地一暖,夏初七嗯了一声,身子靠他更近。
“外头那些事,你都处理好了?”
赵樽静默了一刻,一只手轻拍着她,语气淡淡地回应,“军心不定,民心则不安;民心不安,社稷则不稳。兵变的事情虽是解决了,可京军主官调动却在所难免。”
夏初七自己就是军人出身,自是明白个中意思。在一个窝子里待久了,就跟里面的人混熟了,人熟了,感情就深了。当兵的人,大多只听顶头上司的话,军事将领频繁调度,兵与将就会不熟,不熟则不会生变,这个道理,古今通用。
“头痛吗?”她没有问太多,只用手在他腰上捏了捏。
轻嗯一声,赵樽把她拉近,下巴搁到她的头顶,“阿七,今年六月,最迟八月,我们便可北上了。”
四月初七大婚,六月北上,真是一个美妙的计划。北平府,想到那个地方,夏初七心里也感到很温暖,几百年之后,她就出生在一个历史上叫做“北平府”的地方。
默了片刻,她微微侧了一下身子,抬手顺了一下他的头发,又收回手,双手来回搓动,等手指头搓热了,方才重新在他的太阳穴上慢慢揉起来,“爷,这些日子,我得找找我表姐,有好些事,我得办。”
赵樽轻唔了声,闭着眼享受她手指的按压。
“阿七,有一件事,爷也得告诉你。”
“什么事呀,这么严肃?”
赵樽拉下她的手握在手中,语气凉凉,“大牛的家眷从青州府过来出了事,他的未婚妻死了。这事是锦宫的人干的……那锦宫当家的,已然伏法。”
“什么?”
心里讶异万分,夏初七几乎是下意识地坐起身来。
“你说,袁大哥他……死了?”
赵樽拉她躺下来,拍拍她的背,“是。”
一个“是”字,代表了一个生命的终结,也让夏初七将整件事情串联了起来。
那日,她去锦绣楼见虎子时,虎子说,袁大哥接了一单大买卖,领着兄弟们出了京师。当时她根本就没有当一回事,可竟有这么巧,袁形接的“大买卖”竟然是去伏击陈大牛的家眷,还杀了他未过门的媳妇儿。
到底是谁花钱,要买陈大牛未婚媳妇儿的命?
狠狠地闭了一下眼睛,她的心脏一阵狂乱跳动,“不瞒你说,先前我去打探表姐的消息时,知晓她曾经与袁形接触过,我怕这件事也与她有关。爷,你那里可有她的消息?”
“都是男人,没有妇人。”
微微一怔,夏初七嘴里一阵涩意,“爷,我认识袁形。他这个人很江湖气,为人也仗义,还曾帮过我。他带的锦宫,虽说是捞黑的,吃的也是偏门饭,可他说过不会与朝廷作对,更不可能去抢劫定安侯的家眷……”
“阿七!”赵樽不等她说完便喝道,语气严肃了不少,“往后,不要再与那些人打交道。”
夏初七看着他,迟疑了良久,方问:“我的那些事,你都知道?”
赵樽轻嗯一声,面上情绪不明。
夏初七抬头,“你……不怪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