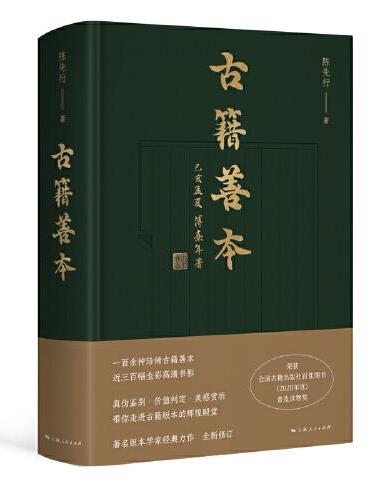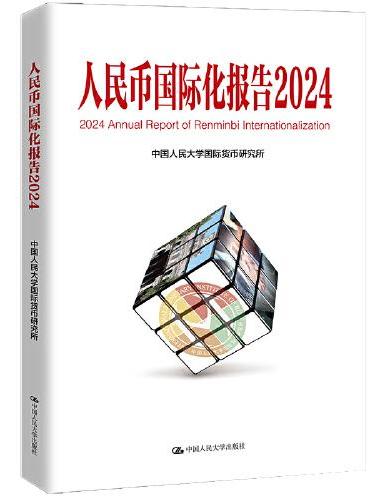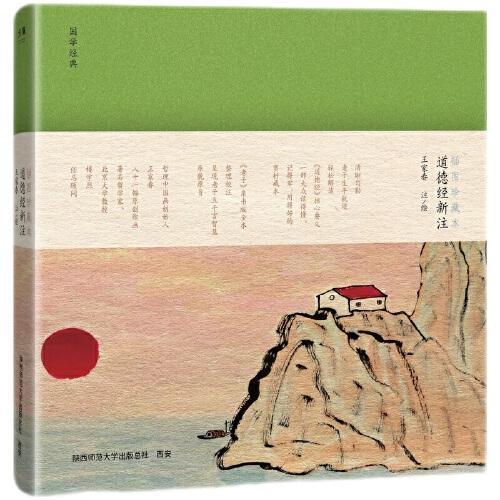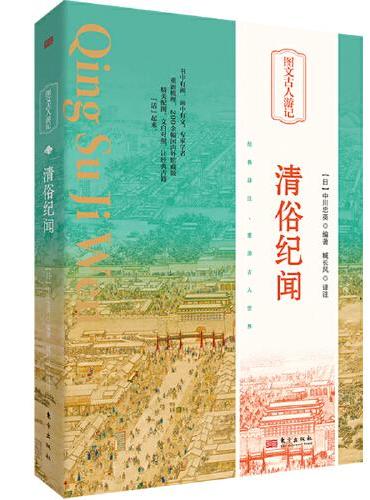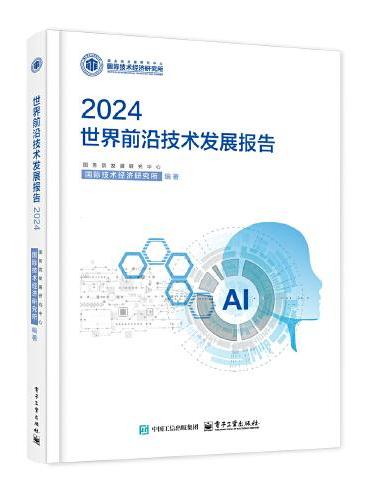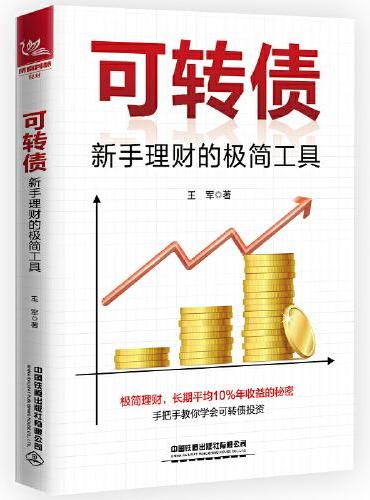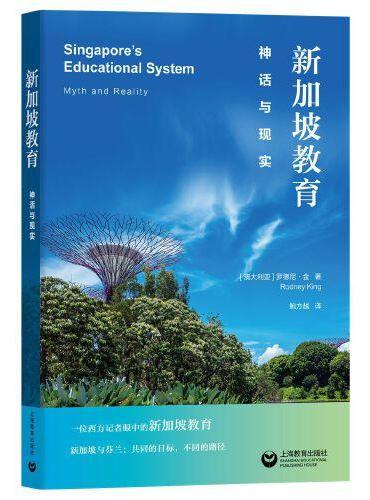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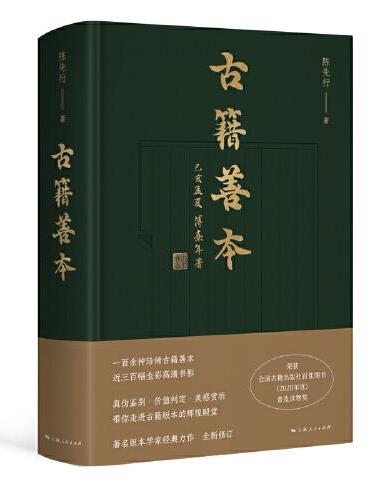
《
古籍善本
》
售價:HK$
53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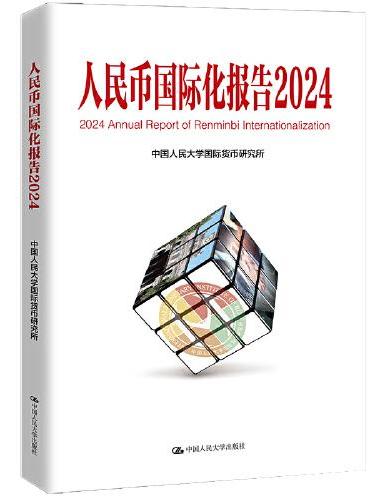
《
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4:可持续全球供应链体系与国际货币金融变革
》
售價:HK$
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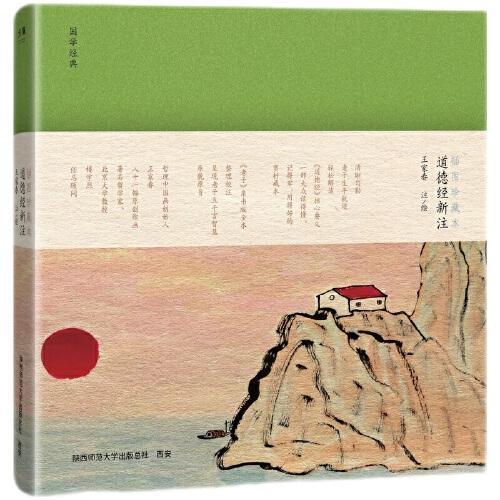
《
道德经新注 81幅作者亲绘哲理中国画,图文解读道德经
》
售價:HK$
14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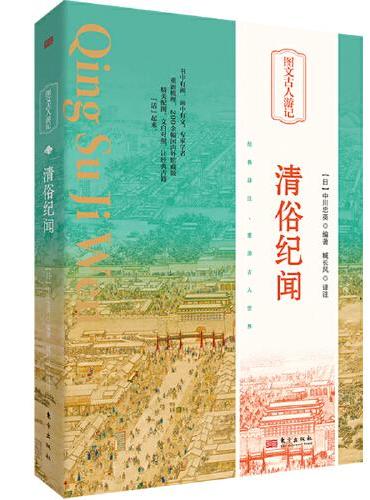
《
清俗纪闻
》
售價:HK$
98.6

《
镜中的星期天
》
售價:HK$
7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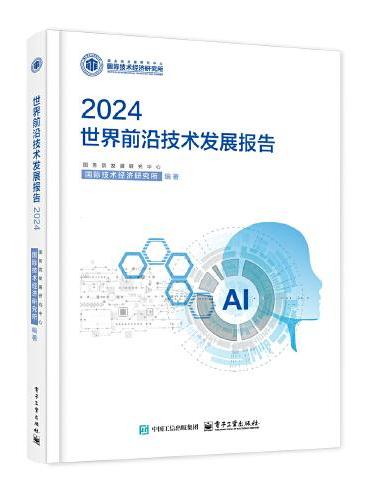
《
世界前沿技术发展报告2024
》
售價:HK$
18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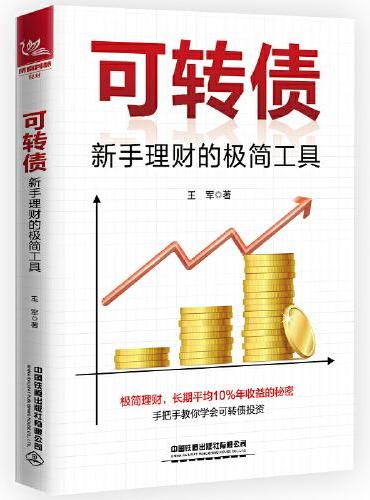
《
可转债——新手理财的极简工具
》
售價:HK$
6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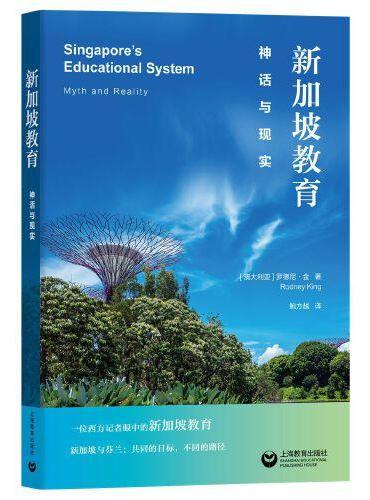
《
新加坡教育:神话与现实
》
售價:HK$
96.3
|
| 編輯推薦: |
|
《英格兰,英格兰》是巴恩斯的历史幻想名作,被认为是他最有趣的一部长篇小说。他的这个荒诞可笑的故事告诉我们:英格兰就是一座主题公园,里面的每样东西都不是真品,而是复制品,甚至每个国家都是这样一座公园。这大大违背我们的信仰啊!但巴恩斯说,你之所以相信它们,是因为你打心里喜欢复制品甚于真品。一部将要毁你历史观的神奇小说。
|
| 內容簡介: |
商人杰克爵士在一座岛上建了个“英格兰精华”主题乐园,乐园中英格兰历史传统的各种元素都有逼真模仿。这个英格兰的复制品居然非常成功,游客们趋之若鹜,甚至喜欢它胜过“原版”的英格兰。
玛莎参与这个虚构历史的项目,在同历史一样真假难辨的童年记忆中搜寻着离家出走的父亲。
|
| 關於作者: |
朱利安巴恩斯(1946— ),英国当代著名作家。父母皆为法语教师,哥哥在牛津大学教授哲学,妻子帕特凯伐纳是著名的文学经纪人。巴恩斯毕业于牛津大学,曾参与《牛津英语辞典》的编纂工作,做过多年的文学编辑和评论家。
“聪明”是巴恩斯作品的一贯标识。八十年代他以突破性之作《福楼拜的鹦鹉》入围布克奖决选,跻身英国文坛一流作家之列。此后,获各大文学奖项无数,三进布克奖决选,并于2011年凭借《终结的感觉》赢得大奖,同年获大卫柯恩英国文学终身成就奖。
巴恩斯也深得法国读者的好感,他是唯一一位同时获得法国梅第奇奖和费米娜奖的作家,并先后荣获法国文化部颁发的文学艺术骑士、军官、司令勋章,堪称在法国最受欢迎的英国作家之一。
|
| 目錄:
|
1 英格兰
2 英格兰,英格兰
3 安吉利亚
|
| 內容試閱:
|
英格兰
“你的第一段记忆是什么?”有人问。
“我不记得。”她回答。
虽然还有人会怀疑这是她的聪明之处,但多数人都会觉得这只是个玩笑。不过她就是这么想的。
“我知道你的意思,”同情者会打个圆场,轻描淡写地说一句,“第一段记忆之后总有一段又一段的记忆,你不可能再回到最初。”
可是不对:这也不是她的意思。你的第一段记忆不同于你的第一件乳罩之类的东西,也不同于你的第一个朋友、你的初吻、第一次性交、第一次婚姻、第一个孩子、你双亲中某一位的先一步离世,或者那种突然产生的直面生活的绝望境地的感觉——所有的这些都不同于你的第一段记忆。它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抓得住的东西,那时间可以年复一年慢吞吞而滑稽地以奇妙的细节装点——比如一阵轻雾、一片雷雨云、一顶冠冕——但绝不能抹除的东西。记忆的定义不是个物件;它……就是一段记忆。一段现在的记忆,忆及早些时间的一段记忆;早些时间的记忆又忆及更早的一段记忆……如是回溯。于是人们清晰地记得一张脸、一副让他们弹跳的膝盖、一片春天的草地;一只狗,一位老奶奶,耳朵毛被咬湿分绺的毛绒绒的动物;他们记得一辆童车,在童车里看到的景象,从童车里跌下来,头撞到了一只倒扣着的花盆,那是他们的哥哥用来垫脚看看新来了什么样的人(当然,许多年以后,他们也开始怀疑,会不会是他们的哥哥一时气急了,把他们从睡眠中揪起来并把他们的头撞在花盆上……)。这一切他们都记得清楚明白,不容置疑。但是不管这是不是别人的讲述,是不是温馨的想象,也不管它是不是出于用爱打动倾听者心灵而有意设计的美好愿望——不管它的来源和意图到底是什么,反正她不相信。玛莎·柯克伦还要活很久。在她的一生中,她是不会碰到在她看来不是谎言的第一段记忆的。
所以,她也说过谎。
她说,她的第一段记忆是坐在厨房的地板上,地板上铺着松软的拉菲草垫,就是上面有很多洞洞的那种,她会用一只勺子穿过洞眼,把它撑大,然后揪着拍打——没人会责备她,因为她妈妈在后面自顾自地唱着歌——她妈妈做饭的时候总喜欢唱些老歌,不是那些她平常喜欢听的歌,甚至于直到今天,当玛莎打开收音机,听到诸如《你最棒》,或者《我们都会在河边相会》,或者《日日夜夜》的时候,她都会突然闻到荨麻汤和煎洋葱的味道,这事儿不够奇怪吗?——嗯,那首也是,《爱情是一件最奇怪的事》,每次歌声响起都意味着一下子给她切开的淌着汁液的橙子——而在地板上,在垫子上散铺着她的英格兰政区拼图板,妈妈已经决定要帮她把周围的一圈以及海洋拼接好,于是在她面前就留下了这样一个这个国家的框架,这片形状有趣的拉菲草垫,有点像一位肥胖的老太太伸着腿坐在沙滩上,她伸出去的腿就是康沃尔郡,当然,她那个时候还没有想到这些,也不知道这块拼图板是什么颜色,你也知道孩子们拼图时的样子,他们只是随意抓起一块硬往缺口里塞,所以她可能拿起来的是兰开夏郡的那块,然后把它当作康沃尔郡了。
是的,就是这样,这就是她的第一段记忆,她的第一个非常巧妙而又不失纯真地编造出来的谎言。总会有人在孩提时代有过同样的拼图板,有过轻松的比赛。比如他们会先拼出哪一个郡——通常都会是康沃尔郡,有时候也会是汉普郡,因为汉普郡有怀特岛郡与之相连,伸向大海,你很容易就能够拼接成功。在康沃尔郡或者汉普郡之后就有可能是东英吉利亚,因为有诺福克郡和萨福克郡并肩蹲坐其上,就像一对兄妹,或者像一对肥胖的夫妻躺在一起,彼此相拥,或者还可以把它们当作一个胡桃的两半。接着就是肯特郡,竖起手指,或是扬起鼻子,冲着大陆发出警告——当心,对面的外国佬;牛津郡在和白金汉郡耍勺子,拍扁了伯克郡;诺丁汉郡和德比郡就像两只并排而立的萝卜或是松果;卡迪根郡拥有如海狮般平滑的曲线。他们会记得那些在周边的面积大而形状清楚的郡,大个儿的拼好后,还剩中间那些乱七八糟奇形怪状的小郡,让你不知道如何下手,根本不记得斯塔福德郡应该在哪儿。然后他们就会努力去回忆每一片的颜色,此时每一片的颜色显得非常重要,就像名称一样重要。现在,过了这么久,康沃尔是紫红色的吗?约克郡是黄色,诺丁汉郡是褐色的吗?或者诺福克郡是黄色的——要不就是她的姊妹萨福克郡?如此种种的记忆,即使错了,也是那么的真切。
不过她觉得这些未经加工的记忆也许是真的:她从地板上走到了餐桌边,那些拼图板她拼起来更快更有序,也更诚实了——她不会再把萨默塞特郡强行放到肯特郡的位置了——而且她通常会沿着海岸线开始拼图——康沃尔郡、德文郡、萨默塞特郡、蒙茅斯郡、格拉摩根郡、卡马森郡、彭布罗克郡(因为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正好是肥胖老妇人的肚子)——这样一直转回到德文郡,然后再填上别的郡,把那些乱糟糟的英格兰中部地区留到最后,她便即将大功告成,可总有一块拼图板会丢。莱切斯特郡,德比郡,诺丁汉郡,沃里克郡,斯塔福德郡——通常总是它们中的某一个会找不到——每当这个时候,看着面前的那个不完整的世界,一股悲伤、挫败和失望的情绪就会笼罩着她,直到父亲在某个最不可能的地方将那一块找出来。每当这个时刻,父亲总会出现在她近旁。斯塔福德郡在他的裤子口袋里干什么?怎么会跑到那儿去了?她看见它跳了吗?她觉得是猫把它放那儿的吗?而她会一直微笑着冲他摇头说不,因为斯塔福德郡已经找到,她的拼图,她的英格兰,还有她的内心又都变得完整了。
这是一段真实的记忆,可是玛莎仍然心存疑惑;它是真实的,但是并非未经提炼加工。她知道这件事发生过,因为它发生过好几次;可是在最后整合这段记忆的时候,每一次特别的标志性细节都没有了踪迹——而她现在只好去弥补这些细节,比如她的父亲在下雨天出门去,回来后把那块湿漉漉的斯塔福德郡拼图板给她的时候,或者当她父亲将莱切斯特郡的一角掀起来的时候的那些细节。童年的记忆就是那些你醒来后仍然记得的梦境。你梦了一整夜,或者很长时间,一夜之中最关键的那几个时段,而当醒来后,你能记住的就只是遭到遗弃,或者被人背叛,或者深陷困境,或者置身于一片冰冷的旷野;有时连这些记忆都没有,只有这一事件激起的一波渐趋平淡的情感涟漪。
这是不相信的另一个理由。如果不是一件事的记忆,而是一段有关记忆的记忆的记忆,像平行排列的镜阵,那么你的大脑现时告诉你的彼时发生的事情就会带有两者之间发生事情的印记。这就像一个国家的历史记忆一样:过去永远不是简单的过去,而是能够让当下心安理得地存在的依据。个人的情况也是这样,只不过其过程显然没有这样直截了当。那些生活中充满了失落的人们会记住一段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呢,还是会记住某一件让他们觉得现在的失落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呢?那些对生活心满意足的人们会记住先前的满足呢,还是某个面对厄运力挽狂澜的时刻呢?在人的外表和内在之间总会侵入一些宣传的因素,一些贩卖或者营销的因素。
也是一种持续的自欺欺人。因为即使你意识到了所有这一切,抓住了记忆系统中的不纯和漏洞,你,或者你的某个部分,还是会相信那个天真可信的东西——是的,那个东西——即你所谓的记忆。上大学的时候,玛莎和一位西班牙姑娘克里斯蒂娜成了好朋友。她们两个国家共同的历史,或者至少是最具争议的部分,都已经是几个世纪以前的事了;可是即便如此,当克里斯蒂娜开玩笑说“弗朗西斯·德雷克当过海盗”的时候,她还是会说,不,他不是,因为她知道他是英格兰的一位英雄、男爵、将军,所以他是一位绅士。当克里斯蒂娜再次更加严肃地说“他是个海盗”的时候,玛莎认为那是失败者为了遮羞而编造的谎言。后来,玛莎在大英百科全书上查找德雷克的资料,“海盗”这个词倒是从未出现,却频繁见到“抢劫”“掠夺”这样的词,玛莎非常理解,在某个人这里只被当作“劫掠者”的人在另一个人那里则完全可能是海盗。不过不管怎么说,弗朗西斯·德雷克在她心里仍然是英雄,她查到的资料对这一点丝毫没有影响。
后来当她回首这些往事的时候,看到的是那些她并不相信的、清晰的、冠冕堂皇的记忆。还有比农产品展销会那天的记忆更清晰更丰富的吗?那天,湛蓝的天空上飘浮着云朵。她的父母亲握着她的手腕,把她高高地荡到空中,她落地的时候脚下松软的草就像蹦床一样。洁白的大帐篷,门廊处彩带飘摆,和牧师们的住处一样坚固结实。后面是起伏的山峦。山上绒毛蓬乱的动物漫不经心地看着山下展览场内的那些精心饲养的系着笼头缰绳的亲戚们。随着气温升高,从啤酒帐篷后面的入口处飘出阵阵气味。等待上简便厕所的队伍,气味也差不多。挂在维耶拉法兰绒格子衬衫扣子上的硬纸标牌。梳理着山羊光滑绒毛的的男人们,从小马背上滑落下来而眼含泪水的孩子们,还有远处修补损坏了的篱笆的敏捷身影。圣约翰医院的救护车驾驶员们等着有人晕倒,等着有人从保险索上摔下来,等着有人心脏病发作;等着出事儿。
可是什么事儿也没有,反正那天没有,她记得那天没有。那本目录她保存了好几十年,其中大部分奇怪的诗行她都能记诵。地方农业部门和园艺协会的奖品一览表。虽然只有不过三四十页,但是对于她却不仅仅是一本红色封面的小册子:还是一本图画书,虽然只有文字,一本年历,一本草本名录,一件神奇的工具包,一本速记手册。
三根胡萝卜—长
三根胡萝卜—短
三根芜青—普通品种
五颗土豆—长
五颗土豆—圆
六颗蚕豆
六颗红花菜豆
九颗矮菜豆
六根葱,大又红
六根葱,小又红
六根葱,大又白
六根葱,小又白
各种蔬菜。六个不同的种类。如果有花椰菜的话,一定会连着茎梗展出。
装着各种蔬菜的托盘。托盘也许会盖着,不过只有装欧芹的那个盖着。
二十穗小麦
二十穗大麦
装在西红柿盒子里的追播草场的草皮
装在西红柿盒子里的永久性草场的草皮
有繁殖计划的山羊一定得用缰绳牵着,而且与那些无繁殖计划的山羊时刻保持两码的距离。
所有进场的山羊必须是母羊。
进场的164和165类的山羊要带一只小羊。
小羊是指刚出生到十二个月大的羔羊。
果子酱坛子
软果酱坛子
柠檬奶酪坛子
水果冻坛子
腌洋葱坛子
沙拉酱坛子
产奶的弗里斯安奶牛
弗里斯安小奶牛
产奶的弗里斯安小母牛
不足两颗臼齿的弗里斯安小母牛
经过检疫的牛都要用缰绳牵着,而且时刻与那些没有经过检疫的牛保持三码的距离。
有些词玛莎也不认识,也只懂得很少一部分说明内容,但是目录上有些东西让她觉得很满意——条理清晰,详尽周全。
大丽花三枝,装饰用,8英寸——装在三个花瓶
大丽花三枝,装饰用,6英寸—8英寸——装在一个花瓶
大丽花四枝,装饰用,3英寸—6英寸——装在一个花瓶
大丽花五枝,小花球
大丽花五枝,绒球形,直径小于2英寸
大丽花四枝,仙人掌形,4英寸—6英寸——装在一个花瓶
大丽花三枝,仙人掌形,6英寸—8英寸——装在一个花瓶
大丽花三枝,仙人掌形,8英寸以上——装在三个花瓶
简直就是一个大丽花的世界。应有尽有。
父母亲有力的手臂将她荡到空中。她走在他们俩之间的木板栈道上,头顶上是帆布帐篷,空气炎热,散发着青草的气息,她看着自己的小册子,像个创造者一样坚定权威。她觉得,那些摆放在他们面前的物品在她给它们命名分类之前好像并不真正存在一样。
“这些是什么呢,大小姐?”
“二,七,噢,五只烹饪苹果。”
“差不多。有五只。不知道它们属于什么品种。”
玛莎又看了看那本小册子。“普通品种。”
“就算是吧。普通品种的烹饪苹果。我们得在商店里找到它们。”他装得非常严肃,不过她的妈妈已经笑出了声,还用手梳理着玛莎的头发,其实那根本没有必要。
他们看到绵羊被夹在汗流浃背、二头肌发达的男人们的腿间,在嗡嗡飞转的剪刀声中,它们被脱去了身上的羊毛;铁笼子里装着焦躁的兔子,又大又干净,像假的似的;还有家畜的队列,骑马的盛装竞赛,猎犬的赛跑。炎热的大帐篷里面有油脂果脯蛋糕、奶油酥、葡萄干馅饼和薄煎饼;苏格兰煎蛋切分得像一块块菊石;一码长的欧防风和胡萝卜,像锥子一样,尾部细得像蜡烛芯;溜光的洋葱的茎秆被揪在一起,系成一对一对的;鸡蛋五个一堆,旁边有一个打开了,倒在碟子里,供人鉴别优劣;甜菜根切开了,展示其内部树一样的环纹。
不过在她的脑海里不断闪现的是阿·琼斯的豆子——后来过了很久很久,还是萦绕不散。一等奖的,他们就给红牌;二等奖的,蓝牌;优胜者,白牌。豆类的所有红牌都给了阿·琼斯先生。九颗普通品种的红花菜豆,九颗圆圆的蔓菜豆,九颗扁胖的刀豆,六颗蚕豆,六颗青蚕豆。他还赢得九荚豌豆和三根短胡萝卜的竞赛,不过这些她不怎么感兴趣。因为阿·琼斯先生还会让豆子展现出神奇。他把豆子放在一块一块的黑色丝绒布上。
“看上去像个珠宝橱窗,呃,可爱吧?”她的爸爸说,“哪位要一对耳环?”他把手伸向阿·琼斯先生的九颗圆圆的刀豆,她妈妈咯咯地笑着,而玛莎说“不要”,声音很大。
“哦,那么,好吧,大小姐。”
即使他不是故意的,也不应该那么做。那可不好玩。阿·琼斯先生可以让一颗豆子看上去完美无瑕。它的颜色,它的比例,它的光亮润滑。九颗豆子更是美丽无比。
上学的时候,他们唱过歌谣。他们四个人一组肩并肩坐着,穿着绿色制服,像豆荚里的豆子。八条腿圆,八条腿短,八条腿长长,八条腿寻常。
玛莎·柯克伦搞错了,每天早晨都会以宗教歌谣开始。接下来是枯燥乏味的乘法表,和愚蠢的诗词歌谣。比乘法表和诗词歌谣更难背、更令人激动的是历史歌谣。他们会在学校晨会上不合时宜地被要求即席背诵。宗教歌谣会在急促的呢喃中完成;但是到了历史歌谣的时候,身材肥胖、仿佛已经老态龙钟的梅森小姐像一位神灵附体的女祭司一样,带领他们虔诚歌咏,指引着这些福音传播者们,保持整齐的节奏。
公元前55(啪啪)罗马入侵
1066(啪啪)海斯汀斯之战
1215(啪啪)英国大宪章
1512(啪啪)亨利八世(啪—啪—)护教誓死(啪—啪—)
她喜欢最后一句:合仄押韵,易记易背。1854年呀(啪啪)克里米亚战呐(啪啪)——他们总是喜欢这样吟唱,也不管梅森一再纠正他们,要他们不要添词加字。就这样,一路唱下来,直到——
1940(啪啪)不列颠战争
1973(啪啪)罗马协定
梅森小姐会带领他们沿着历史的长河顺流而下,然后又逆流而上,从罗马到罗马,回到起点。就这样,她将他们激发起来,让他们的头脑变得灵活敏捷。然后她会给他们讲骑士精神和英雄故事,讲瘟疫和灾荒,独裁和民主的故事;讲皇家宫廷的金碧辉煌和严谨谦卑的个人主义的高尚美德;讲圣乔治的故事,他是英格兰以及阿拉贡和葡萄牙的守护神,也是热那亚和威尼斯的护国公;讲弗朗西斯·德雷克勋爵和他的英雄壮举;讲波阿狄西亚以及维多利亚女王;讲当地的一位乡绅,他参加过十字军,现在直挺挺地躺在他妻子旁边,在乡村教堂的墓地里长眠。他们听着,倍加全神贯注,因为只要梅森小姐高兴了,就会用更多的歌谣来结束一堂课,可是这一次不同。还会有些表现日期的动作;各种变化,各种即兴的表演和恶作剧;词语也是躲闪腾跃,但全都要合仄押韵。伊丽莎白和维多利亚(啪啪啪啪),他们就会回应1558和1837(啪啪啪啪)。或者(啪啪)魁北克的伍尔夫(啪),他们就得回以(啪啪)1759(啪啪)。或者她不再示意他们说“火药阴谋”(啪啪),而是一下子改成了“奎多·福克斯被活捉”(啪啪),而他们还要找到那个节奏说1605(啪啪)。她带领着他们纵横跨越两千年,让历史变得不再是机械进程,而是一系列生动而又富有竞争性的时刻,就像摆放在黑色绒布上的豆粒。很久以后,当她生活中所有要发生的事情都发生过了的时候,玛莎·柯克伦仍然是一看到书中的一个日期或者一个名字,头脑里就会听到梅森小姐拍手回应的声音。老尼尔森可怜,不在人世,1805年塑像,特拉法加广场。爱德华八世失国,1936年没了王位。
杰西卡·詹姆斯是她的朋友,一个基督徒,上历史课的时候坐在她的身后。杰西卡·詹姆斯,这个虚伪背信的家伙,在晨会上坐在她的前面。玛莎是个聪明的姑娘,因此不是个信徒。早晨祷告的时候,她一直紧紧地闭着眼睛,做着不一样的祈祷:
紫花苜蓿在德文郡放屁,
噗隆一声好似打雷。
他们的大棚来了。
你的泔水残渣也来了
来到巴斯,在塞文河的近旁。
给我们吧,就在今天,给我们三明治抹酱,
给我们公共汽车票,
因为我们要给向我们要票的人,
不要把我们领进佩恩车站,
黄油抹猪肝,还有象鼻虫。
因为这就是你的大棚,还有鲜花和故事,
永永远远是我们。
她还在琢磨着一两句需要改进的地方。她不觉得这首诗有什么冒渎神灵之处,除了关于放屁的那一句有一点儿。她觉得这里面有几句还特别优美:有关大棚和鲜花的寥寥数语总能够令她想到九颗圆蔓菜豆,这一点,如果上帝真的存在的话,他也一定会表示赞同的。但是,杰西卡·詹姆斯揭发了她。不是揭发,她做了件比这聪明得多的事情:让玛莎自己揭发了自己。一天早晨,在杰西卡的指挥下,周围所有的人都一下子鸦雀无声,可以清楚地听到玛莎一个人的声音,她正全神贯注地强调着三明治抹酱、猪肝以及象鼻虫的重大意义,等睁开双眼,看到了扭转过来的肩膀,腆着的小胸脯,还有和他们班坐在一起的梅森小姐投过来的威严目光。
在这一学期剩下的日子里,她都被安排站在一边,带领整个学校的人祈祷,被迫每句话都要字正腔圆,而且还要装得热情饱满,至信至诚。过了一阵子,她发觉她做这件事情很在行,就像一位蒙受了圣恩的罪犯在向陪审团保证他的罪孽已经被洗刷干净,而他们会仁慈地认为可以将他释放了。梅森小姐越是疑惑不解,她就越是觉得乐趣无穷。
人们开始把她带到一旁。他们会问她,反差如此巨大是什么意思。他们会告诉她说这样做是聪明过了头。他们会忠告她,玛莎,玩世不恭可不是好的品行。他们希望她不要不懂规矩。他们有意无意地暗示她,玛莎的家庭跟其他的家庭不一样,当然还要克服重重困难,性格也要去逐步培养。
她并不理解什么是性格培养。它一定是你具有的某样东西,或者一旦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会改变的东西,就像她的母亲最近变得越来越刻薄,越来越暴躁。你怎么可能自己培养自己的性格呢?她望着乡村的院墙,试图找到某种类比:一块块石头,粘着泥巴,然后是一排棱角分明的燧石,表明你已经是成年人,你已经确立了你的性格。这毫无意义。玛莎的照片显示她在冲这个世界皱眉头,撇着嘴,眉头锁得紧紧的。这表示她对这个世界的不认可吗?表明她的不讨人喜欢的个性,或只是人家曾告诉她妈妈(在她小时候),拍照时一定要让阳光从右肩上照过来?
无论如何,培养性格不是她那个时候的首要任务。农产品展销会后,过了三天——这是一段真实的,未经加工的记忆,她对此确信无疑,她对此几乎确信——玛莎坐在厨房餐桌旁;她记得她妈妈在做饭,但是没有唱歌——没有,她肯定没有,她已经到了记忆固化为事实的年龄——她妈妈在做饭,而且没有唱歌,这是事实,玛莎做完了她的拼图,这是事实,拼图上有一个诺丁汉郡图块大小的洞,从中可以看到餐桌的纹理,这是事实,她爸爸不在周围,这是事实,她爸爸把诺丁汉郡放在他的口袋里了,这是事实,她抬头张望,这是事实,泪滴从她妈妈的脸颊滑落到了汤里,这是事实。
依托这种孩童的逻辑,她知道不应相信妈妈的解释。面对这样的不可理喻和泪水,她甚至有些微的优越感。对于玛莎来说,这一切简直太简单了。爸爸离开去找诺丁汉郡图块了。他以为他把它放在口袋里了,但是找的时候却没有。这就是为什么他不再对她笑脸相迎,还叱责猫咪。他知道他不能让她失望,所以他就去找那一块,只不过花的时间比他想象的要长得多。反正他会回来,一切又都会完好如初。
后来——后来来得太快了——一种异样的感觉进入了她的生活,一种她还没有恰当的词语去描述的感觉。一个突然的、合理的、合仄押韵的理由。(啪—啪—)为什么爸爸要出走。是她弄丢了那个图块,是她弄丢了诺丁汉郡,放在某个她想不起来的地方,或者也许放在了某个窃贼会光顾并盗走的地方,所以她的父亲,那个爱她,那个说过他爱她,而且永远都不想看到她失望,永远都不想让他的大小姐把嘴嘟成那样的父亲就离家出走,去找那块拼图,而且即使书籍和故事传说可作参考,那也会花很长很长的时间。她父亲也许会好多年回不来,那个时候他也许已经是满脸胡须,并且已经花白,他看上去会显得——他们怎么说来着?——面容憔悴,营养不良。而这一切都是她的错,因为她的粗心或者愚蠢,是她造成了她爸爸的消失和她妈妈的痛苦,所以她千万不能再粗心和愚蠢了,因为这种事容易反复。
在厨房那边的走廊里,她发现了一片橡树叶。她爸爸进来的时候,脚上总是会带着叶子。他说这是因为他太急于赶回来看到玛莎了。妈咪常常会生气地告诉他不要油嘴滑舌,而且玛莎也完全可以等到他把脚擦拭干净。玛莎自己呢,因为害怕引发类似的责备,总是很仔细地擦干净鞋子,每次这么做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感觉。现在,她的手掌上托着这枚橡树叶。扇贝一样的边缘使得它看上去像一块拼图板,甚至有一瞬间,她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这是一个信号,或者一个巧合,还是其他什么:如果她保留好这片叶子,作为时时想起爸爸的信物,那么他就会保存好诺丁汉郡图块,然后回来。她没有告诉她妈妈,而是把那片树叶夹进了从农展会上带回来的小红本里。
至于杰西卡·詹姆斯,朋友、叛徒,恶自有报,玛莎相信这一点。她不是基督徒,宽恕是别人践行的美德。杰西卡·詹姆斯,贼眉鼠眼,一脸伪善,声音像晨祷一样单调乏味,杰西卡·詹姆斯,她的父亲永远也不会消失,杰西卡·詹姆斯开始和一个腼腆的高个儿男生约会,那位男生一双红红的手潮湿柔软,看不清关节轮廓。玛莎很快就忘了他的名字,但是一直记得他的那双手。玛莎要是再年长一些的话,肯定会觉得,能够做出的最冷酷的事情就是让杰西卡·詹姆斯和她的那位就会傻笑的追求者继续促膝亲昵,自以为是,直到有一天他们沿着走廊走过十字军墓地,他裤脚边跟着一条狗,一起走向他们余生的夕阳。
玛莎其实还没有那么世故。但是,凯特·贝拉米,朋友、阴谋家,故意透露给那个男生说如果他正在考虑换一个更好的女朋友的话,玛莎也许会有兴趣和他约会。玛莎已经发现,她几乎可以令任何一位男生对她心生倾慕,只要她不喜欢他。现在有各种计划必须展开商讨。她可以直接抢走那个男生,和他一起招摇炫耀一段时间,让杰西卡·詹姆斯在全校面前丢脸。或者,他们也许可以安排一场小小的哑剧表演:凯特带着杰西卡·詹姆斯装着漫不经心地出去散步,然后“偶然”来到一个地方,一只肥胖的猪手握着温软乳房的景象会撕碎她那一本正经的小心灵。
玛莎还是决定实行最为残酷的报复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她并不需要去做什么事情。凯特·贝拉米,声音天真单纯,但却心机深重,她说服那个男生相信玛莎也许真的爱上他了——从开始认识他的那天起——但是她在爱情以及一切与爱情相关的问题上很严肃,而他得义无反顾地公开地与那位虔诚小姐一刀两断,然后才可以有机会。经过几天艰难的思考和欲望的煎熬,那个男生照做了,杰西卡·詹姆斯也果然流下了令他们感到满意的泪水。好多天过去了,到处都可以看到玛莎欢笑的样子,可是却没有任何信息传来。男生焦躁地找到她的同伙,而她却跟他装傻,说他一定误会了:玛莎·柯克伦和他出去约会?这怎么可能。男生极其愤怒,感到蒙受了羞辱,他在放学后拦住玛莎;她嘲笑了他的自以为是,想入非非。他会没事的;男生都这样。至于杰西卡·詹姆斯,她一直都沉浸在那样的痛苦之中,这让玛莎很高兴,直到她离开学校。
又是几个冬去春来,玛莎慢慢地清楚地意识到诺丁汉郡图块和她的父亲都不会回来了。她仍然相信他们都会回来,只要她妈妈还哭哭啼啼,还使用高架子上面的一个瓶子,还非常非常紧地抱着她,告诉她所有的男人都是要么很坏要么很弱,有的是既坏又弱。这样的场合玛莎也会哭,仿佛她们共同的泪水可以把她的爸爸带回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