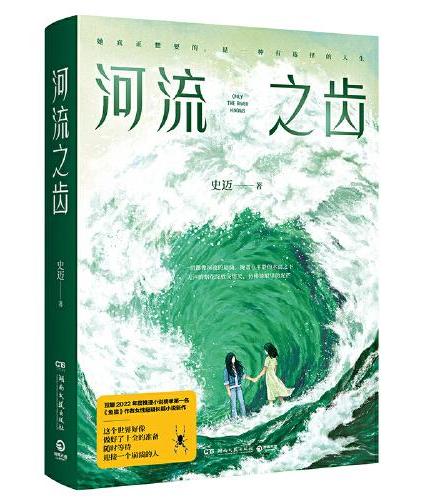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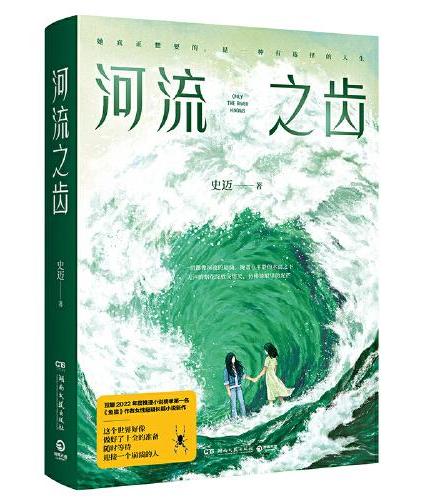
《
河流之齿
》
售價:HK$
59.8

《
新经济史革命:计量学派与新制度学派
》
售價:HK$
89.7

《
盗墓笔记之秦岭神树4
》
售價:HK$
57.3

《
战胜人格障碍
》
售價:HK$
66.7

《
逃不开的科技创新战争
》
售價:HK$
103.3

《
漫画三国一百年
》
售價:HK$
55.2

《
希腊文明3000年(古希腊的科学精神,成就了现代科学之源)
》
售價:HK$
82.8

《
粤行丛录(岭南史料笔记丛刊)
》
售價:HK$
80.2
|
| 編輯推薦: |
该套丛书精选国外文学经典,由著名翻译家宋兆霖、李玉民等倾力翻译,打造出这部既保留外国文学特色,又适合国内青少年读者阅读的经典名著,力图为青少年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外国文学盛宴,使其能够汲取精华,不断的提升和强大自己。
为了实现这一宗旨,该丛书提倡深阅读,进行最有意义的价值阅读。诸如经典阅读中的《鲁滨逊漂流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名人传》等著作,最直接地探讨“什么是人”以及“人可以是什么”等自我价值、人生意义的主题,它对一个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另外,借助经典名著的价值阅读,还可以培养青少年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爱心、专注、勤俭、坚韧、自信、自立、勇敢等一生受用的优秀品质,使名著阅读真正回归自我成长与素质提升本身。这也是该套丛书的主要价值体现。
该套丛书得到了教育界和文学界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中国教育协会副会长,新教育实验发起人朱永新作序,十余位教育专家审定,多位文学家以及著名评论家对该丛书给予厚望并为之寄语。
|
| 內容簡介: |
|
《小橘灯》是冰心的代表作之一,它如一颗闪烁的启明星,在人生旅途中指引着不知归途的旅人找回心灵最深处的爱与感动。本书还收录了冰心众多优美的文章,如《我的中学时代》《只拣儿童多处行》《一只小鸟》《还乡杂记》等,穿梭于童年到暮年,跨越大江南北,她歌颂家国,热爱自然,赞美可爱可敬的人儿,寄托了她最高的真善美的理想,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世间万物细致周到的关注。冰心把这种关注转化为一种非常美丽,极易亲近的文字,用这些可爱温婉的文字来还原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一个充满爱,充满信心,充满希望的世界……也正由于冰心散文的这种清新婉丽,语言融白话文的流畅、明晰与文言文的洗练、华美于一体,“冰心体”才得以流传于世,影响之后数代人的阅读和写作。
|
| 關於作者: |
|
冰心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女士,男士等。原籍福建长乐,生在福州。冰心幼年时代就开始广泛接触中国的古典小说和译作。1913年印度诗人泰戈尔写成散文诗《飞鸟集》,冰心的诗受他的影响很深。20世纪初,冰心开始写作无标题的自由体小诗。这些清新淡雅、轻柔隽逸的小诗,后结集为《繁星》和《春水》出版,并由此推动了新诗初期“小诗”写作的潮流。
|
| 目錄:
|
目录
难忘事·难忘人
小橘灯
我的中学时代
我的童年
腊八粥一饭难忘
童年的春节
在火车上
我的一天
回忆“五四”
只拣儿童多处行
五月一号
祖父和灯光管制
六一姊
观舞记
我的同班
我的同学
一个忧郁的青年
像蜜蜂一样劳动的人们
忆意娜
感谢我们的语文教师
一代伟大的女性
“人难再得始为佳”
老舍和孩子们
追念振铎
我所钦佩的叶圣陶先生
追念闻一多先生
纪念印度伟大诗人泰戈尔
情之所系
明子和咪子
我们把春天吵醒了
火树银花里的回忆
我喜欢下雪的天
我喜爱小动物
除夕
一日的春光
我和玫瑰花
玻璃窗内外的喜悦
绿的歌
一只小鸟
灯光
丢不掉的珍宝
话说萝卜白菜
故乡的风采
海恋
忆烟台
我家的茶事
奇迹的三门峡市
说梦
一个奇异的梦
书给了我快乐和益处
家国之爱
小家庭制度下的牺牲
离家的一年
每逢佳节
还乡杂记
我到了北京
我和北京
仰望天安门
美的北京街头
记广州花市
花光和雪光
归来以后
莫斯科的丁香和北京的菊花
祖国母亲的心
桥
文学艺术
怎样欣赏中国文学
写作经验琐谈
我的文学生活
元代的戏曲
画——诗
延伸阅读
本书名言记忆
读书笔记
心灵深处的那盏灯
品读思考
|
| 內容試閱:
|
难忘事·难忘人
导读
“青春的岁月像条河,岁月的河汇成歌。”这支深情的歌时时拨动着我们的心弦。我们难忘“紧张而规律”的中学时代的同学,更难忘年少时那次嬉戏。又猜想自己会不会遇到机巧豁达的“L大姐”,还有那盏照亮前行路的小橘灯……
小橘灯
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她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走上一段阴暗的仄仄(zè,狭窄)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她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她临时有事出去,叫我等着她。
我在她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地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我掀开帘子,看见一个小姑娘,只有八九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我问她:“你要打电话吗?”她一面爬下竹凳,一面点头说:“我要××医院,找胡大夫,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我问:“你知道××医院的电话号码吗?”她摇了摇头说:“我正想问电话局……”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就又问她:“找到了大夫,我请她到谁家去呢?”她说:“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她就会来的。”
我把电话打通了,她感激地谢了我,回头就走。我拉住她问:“你的家远吗?”她指着窗外说:“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一下子就走到的。”说着就登、登、登地下楼去了。
我又回到里屋去,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又拿起一本《唐诗三百首》来,看了一半,天色越发阴沉了,我的朋友还不回来。我无聊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橘子,塞在手提袋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门口。
我轻轻地叩着板门,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抬头看了我,先愣了一下,后来就微笑了,招手叫我进去。这屋子很小很黑,靠墙的板铺上,她的妈妈闭着眼平躺着,大约是睡着了,被头上有斑斑的血痕,她的脸向里侧着,只看见她脸上的乱发,和脑后的一个大髻。门边一个小炭炉,上面放着一个小沙锅,微微地冒着热气。这小姑娘把炉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不住地打量我。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她说:“来过了,给妈妈打了一针……她现在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我问:“她吃过东西吗?这锅里是什么?”她笑说:“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橘子,就拿出来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她没有作声,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橘子来,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揉捏着。
我低声问:“你家还有什么人?”她说:“现在没有什么人,我爸爸到外面去了……”她没有说下去,只慢慢地从橘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橘瓣来,放在她妈妈的枕头边。
炉火的微光,渐渐地暗了下去,外面变黑了。我站起来要走,她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橘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像一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橘灯照你上山吧!”
我赞赏地接过,谢了她,她送我出到门外,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她又像安慰我似的说:“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显然地,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
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橘灯,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橘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
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看见我提着小橘灯,便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从王春林家来。”她惊异地说:“王春林,那个木匠,你怎么认得他?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做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
当夜,我就离开那山村,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
但是从那时起,每逢春节,我就想起那盏小橘灯。十二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
我的中学时代
因为整理信件,忽然翻出我的一位中学同学,在七十年代给我写的末一封信。她写:
小谢:
记忆力真是一件奇妙的东西!你的声音笑貌和我们中学时代的一切,在我病榻上的回忆中,都是那样出奇的活跃而清晰……
这几句话又使我十分激动,思潮久久不能平静下来!
的确的,在我十几年海内外的学校生活中,也就是中学时代,给我的印象最深,对我的性格影响也最大。
我的中学生涯是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度过的(那时的中学是四年制)。十四岁的年纪,正是感情最丰富,思想最活泼,好奇心最强,模仿力和可塑性也最强的时候,我以一个山边海角独学无友的野孩子,一下子投入到大城市集体学习的生活中来,就如同穿上一件既好看又紧仄的新衣一样,觉得高兴也感到束缚。我用好奇而谨慎的目光,盯着陌生环境中的一切:高大的校舍,新鲜的课程,如音乐、体操,和不同的男女教师……但是我最注意的还是和我同班的年龄相仿的女孩子。她们都是梳髻穿裙,很拘谨,守纪律,学习尤其刻苦。一同上了几天课,她们就渐渐地和我熟悉起来。因为我从小听的说的都是山东话,在课堂上听讲和答问都有困难。她们就争着教我说北京话。(那个头一个叫我“小谢”的同学,是满族人,语音尤其纯正。)我们也开始互相谈着自己的家庭和过去的一切。她们大多数是天津、通县、保定等处的小学升上来的(她们都是寄宿生),数学基础比我好,在国文上我又比她们多读了一些,就这样我们开始互帮互学,我觉得我有了学习和竞赛的对象。那时我是走读生,放学到家打开书包,就埋头做功课,一切“闲书”都顾不得看了。
就这样紧张而规律地过了四年中学时代。我体会到了“切磋琢磨”的好处,也得到了集体生活的温暖。四年之末,我们毕业的同学才有十八个人。毕业后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参加了工作,我们约定大家都努力学习,好好工作,还尽量保持联系。此后的年月里,我们风流云散,也都有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但无论在天涯在海角我们惊喜地遇见,共同回忆起中学时代这一段生活时,我们总会互相询问:我们每一个人是否都完成了中学时代的志愿,做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益的人?
我的童年
我生下来七个月,也就是一九○一年的五月,就离开我的故乡福州,到了上海。
那时我的父亲是“海圻(qí)”巡洋舰的副舰长,舰长是萨镇冰先生。巡洋舰“海”字号的共有四艘,就是“海圻”、“海筹”、“海琛”、“海容”,这几艘军舰我都跟着父亲上去过。听说还有一艘叫作“海天”的,因为舰长驾驶失误,触礁沉没了。
上海是个大港口,巡洋舰无论开到哪里,都要经过这里停泊几天,因此我们这一家便搬到上海来,住在上海的昌寿里。这昌寿里是在上海的哪一区,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母亲所讲的关于我很小时候的故事,例如我写在《寄小读者》通讯十里面的一些,就都是以昌寿里为背景的。我关于上海的记忆,只有两张相片作为根据,一张是父亲自己照的:年轻的母亲穿着沿着阔边的衣裤,坐在一张有床架和帐楣的床边上,脚下还摆着一个脚炉,我就站在她的身旁,头上是一顶青绒的帽子,身上是一件深色的棉袍。父亲很喜欢玩些新鲜的东西,例如照相,我记得他的那个照相机,就有现在卫生员背的药箱那么大!他还有许多冲洗相片的器具,至今我还保存有一个玻璃的漏斗,就是洗相片用的器具之一。另一张相片是在照相馆照的,我的祖父和老姨太坐在茶几的两边,茶几上摆着花盆、盖碗茶杯和水烟筒,祖父穿着夏天的衣衫,手里拿着扇子;老姨太穿着沿着阔边的上衣,下面是青纱裙子。我自己坐在他们中间茶几前面的一张小椅子上,头上梳着两个丫角,身上穿的是浅色衣裤,两手按在膝头,手腕和脚踝上都戴有银镯子,看样子不过有两三岁,至少是会走了吧。
父亲四岁丧母,祖父一直没有再续弦,这位老姨太大概是祖父老了以后才娶的。我在一九一一年回到福州时,也没有听见家里人谈到她的事,可见她在我们家里的时间是很短暂的,记得我们住在山东烟台的时期内,祖父来信中提到老姨太病故了。当我们后来拿起这张相片谈起她时,母亲就夸她的活计好,她说上海夏天很热,可是老姨太总不让我光着膀子,说我背上的那块蓝“记”是我的前生父母给涂上的,让他们看见了就来讨人了。她又知道我母亲不喜欢红红绿绿的,就给我做白洋纱的衣裤或背心,沿着黑色拷绸的边,看去既凉爽又醒目,母亲说她太费心了,她说费事倒没有什么,就是太素淡了。的确,我母亲不喜欢浓艳的颜色,我又因为从小男装,所以我从来没有扎过红头绳。现在,这两张相片也找不到了。
在上海那两三年中,父亲隔几个月就可以回来一次。母亲谈到夏天夜里,父亲有时和她坐马车到黄浦滩上去兜风,她认为那是她在福州时所想望不到的。但是父亲回到家来,很少在白天出去探亲访友,因为舰长萨镇冰先生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派水手来叫他。萨镇冰先生是父亲在海军中最敬仰的上级,总是亲昵地称他为“萨统”(“统”就是“统领”的意思,我想这也和现在人称的“朱总”“彭总”“贺总”差不多)。我对萨统的印象也极深。记得有一次,我拉着一个来召唤我父亲的水手,不让他走,他笑说:“不行,不走要打屁股的!”我问:“谁叫打?用什么打?”他说:“军官叫打就打,用绳子打,打起来就是‘一打’(量词,十二为一打。打,dá),‘一打’就是十二下。”我说:“绳子打不疼吧?”他用手指比划着说:“喝!你试试看,我们船上用的绳索粗着呢,浸透了水,打起来比棒子还疼呢!”我着急地问:“我父亲若不回去,萨统会打他吧?”他摇头笑说:“不会的,当官的顶多也就记一个过。萨统很少打人,你父亲也不打人,打起来也只打‘半打’,还叫用干索子。”我问:“那就不疼了吧?”他说:“那就好多了……”这时父亲已换好军装出来,他就笑着跟在后面走了。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母亲生了一个妹妹,不几天就夭折了。头几天我还搬过一张凳子,爬上床上去亲她的小脸,后来床上就没有她了。我问妹妹哪里去了,祖父说妹妹逛大马路去了,但她始终就没有回来!
一九○三—一九○四年间,父亲奉命到山东烟台去创办海军军官学校。我们搬到烟台,祖父和老姨太又回到福州去了。
我们到了烟台,先住在市内的海军采办厅,所长叶茂蕃先生让出一间北屋给我们住。南屋是一排三间的客厅,就成了父亲会客和办公的地方。我记得这客厅里有一副长联是: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我提到这一副对联,因为这是我开始识字的一本课文!父亲那时正忙于拟定筹建海军学校的方案,而我却时刻缠在他的身边,说这问那,他就停下笔指着那副墙上的对联说:“你也学着认认字好不好?你看那对子上的山、竹、三、五、八、九这几个字不都很容易认的吗?”于是我就也拿起一支笔,坐在父亲的身旁一边学认一边学写,就这样,我把对联上的二十二个字都会念会写了,虽然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究竟是哪几本古书。
不久,我们又搬到烟台东山北坡上的一所海军医院去寄居。这时来帮我父亲做文书工作的,我的舅舅杨子敬先生,也把家从福州搬来了,我们两家就住在这所医院的三间正房里。
这所医院是在陡坡上坐南朝北盖的,正房比较阴冷,但是从廊上东望就看见了大海!从这一天起,大海就在我的思想感情上占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我常常心里想着它,嘴里谈着它,笔下写着它;尤其是三年前的十几年里,当我忧从中来,无可告语的时候,我一想到大海,我的心胸就开阔了起来,宁静了下去!一九二四年我在美国养病的时候,曾写信到国内请人写一副“集龚(截取龚自珍的诗句或文句拼集成一副对联。龚自珍,清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的对联,是:
世事沧桑心事定
胸中海岳梦中飞
谢天谢地,因为这副很短小的对联,当时是卷起压在一只大书箱的箱底的,“四人帮”横行,我家被抄的时候,它竟没有和我其他珍藏的字画一起被抄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