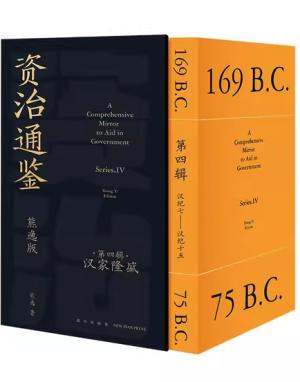新書推薦:

《
逃不开的科技创新战争
》
售價:HK$
103.3

《
漫画三国一百年
》
售價:HK$
55.2

《
希腊文明3000年(古希腊的科学精神,成就了现代科学之源)
》
售價:HK$
82.8

《
粤行丛录(岭南史料笔记丛刊)
》
售價:HK$
80.2

《
岁月待人归:徐悲鸿自述人生艺术
》
售價:HK$
61.4

《
女人的中国医疗史:汉唐之间的健康照顾与性别
》
售價:HK$
10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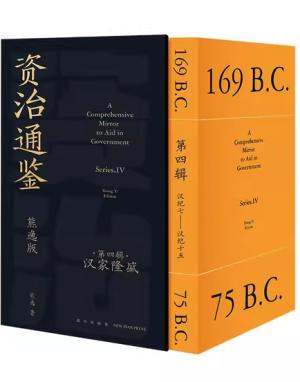
《
资治通鉴熊逸版:第四辑
》
售價:HK$
470.8

《
中国近现代名家精品——项维仁:工笔侍女作品精选
》
售價:HK$
66.1
|
| 編輯推薦: |
在冯秋子的散文中,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网织在静默而崇高的笔触里,土地和生长、苦难和坚韧、困顿或忧思、悲泣或欢颜……不断敲击读者的内心,共同创造出人间最平凡的精神和永恒的诗意。
本书选文将文学性与社会性巧妙结合,在读作者作品的同时,使中学生意识到生态建设,情感、素质教育等的重要性。在不经意间使人在散文阅读中得到思想、认识的升华。对学生的散文写作、阅读有很大帮助。
|
| 內容簡介: |
|
《丢失的草地》本书稿从作者对其家乡内蒙古的感悟切入,分别从人、自然、社会、历史、生活等多种角度,抒发了作者对这些的看法。体现了散文的抒情性,很独特、敏锐地诠释了作者的思想、才情和感受。本书请文学硕士编写随文赏析、总评等,使学生更易理解。
|
| 關於作者: |
原文作者:冯秋子,原名冯德华。著名作家,1983年大学毕业,先后当过教师、出版社编辑、报社记者。出版有散文集《太阳升起来》《寸断柔肠》《生长的和埋藏的》,主编过1990年至2002年全国优秀散文随笔集《人间:个人的活着》。《没有土地的村庄》荣获《人民文学》优秀散文奖。
导读作者:刘颋,湖南长沙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1997年至今,历任《文艺报》文学部编辑、副主任,200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评论集《文学的表情》,与人合作编著有《末路狂花--世纪末小说选粹》(四卷)、《百年中国中篇小说经典》等。
|
| 目錄:
|
蒙古人
白音布朗山
额嬷
丢失的草地
荒原
老人和琴
草原上的农民
1962:不一样的人和鼠
少年巴顿
阎荷
我跳舞,因为我悲伤
生育报告
一个女人的影像
我与现代舞
在我心里,有一条通向你的路
|
| 內容試閱:
|
丢失的草地
1999年7月,巴顿放暑假,我们去了河北丰宁县坝上草原--大滩镇元山子东道自然村,住进一个旅游站的蒙古包。
丰宁满族自治县,紧挨过去的察哈尔蒙古八旗的"四牧群"中的三大牧群,出产著名的"口马""口羊""口蘑"。我们所在的东道自然村,耕地稀薄,沙地牧场放任。它西邻河北沽源,东接森吉图,往北,连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太仆寺旗、正蓝旗和多伦。而正蓝旗是蒙古语标准语言基地,元朝时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元朝迁都大都(北京)后,正蓝旗境内的元上都改为陪都,每年夏季,元朝皇帝率领众臣僚回到这里处理政务、连带避暑。上都和大都并称两都,13世纪时,上都这座名城通过《马可o波罗游记》远播四海。到明代,此地属北元云需部万户游牧地。清乾隆元年,清廷于察哈尔左翼四旗置四旗直隶厅,四十三年改为丰宁县。以后丰宁划归卓索图盟,成为当时内蒙古地区六个盟制之一,民国以后丰宁分归属热河省。新中国成立国后,1955年热河省建置被取消,所属丰宁等县市划归河北省。
巴顿比较熟悉西北部的内蒙古,每次乘火车回去,兴奋不已。从低海拔的京城,攀旋进入中国北部山脉紧缩、沟壑纵深的断块山地,海拔一千米到一千五米高处。而姥姥家,是在蒙古高原上,隶属察哈尔右翼旗部,位于海拔两千四五百米处,山势相对和缓,间有望不到边涯的草场、荒野。在那里,开垦的农田,要么沉闷于风雪,要么奄息于风沙,村庄与村庄之间,相距非常遥远,被戈壁草原隔断在寂寥的北方。巴顿想在那里上学,我没同意,做母亲的不能放弃抚养孩子的义务,他就说上完学要到那儿当一名体育教师。但愿他的想法能够持久,他在北京住的院子里踢球,"撩了一下脚"--他这样向我解释,就把邻居的玻璃踢碎了,有两次玩儿得高兴和小朋友喊叫出声,被占地建房的一家公司的领导抓住揍了一个耳光。我怀疑,有一天,他忘记了在北京踢球的遭遇,还会不会想去内蒙古当一名他称作的"自由奔放"的体育教师。
这是巴顿第一次坐长途汽车,不去姥姥家那边的草原,而去另一片草原。这片草原也坐落在那么多高山上,他感到惊奇。他说,原来所有的草原都是在高山上,所有的草原都离太阳更近。
傍晚,我和巴顿出去骑马。这片低山丘陵草场,蒲公英、黑麦草、羊草、散落的野蘑菇和杂类草,让我和巴顿像置身在察哈尔家乡的草甸子上。
草地里只有两个当地人,牵着两匹马,一马雄健,站着就想往出蹿;一马低矮,闷着头吃草。巴顿提出他骑大马,他七岁时在内蒙古学会骑马,嫌小马跑不快。小马的主人刘亚飞是借马来让客人骑的。骑到半途,原主人又送来一匹马,刘亚飞上马,和我并排,一边骑马一边拉呱。刘亚飞租出借来的马两匹,所得的二十元费用归马主人(其中两元交税),他另得小费十元。我上马前他跟我讲定价格。刘亚飞是满族人。我问他,现在还保留了哪些满族人的习俗。他说现在没什么忌讳了,讲究也没有了。看了电视剧《雍正王朝》,老辈人讲起过去的礼节,他们就听,只剩下听的份儿。
满天满地的乌鸦,在夕阳的残红里追逃,那些站在电线上、跟着电线荡漾两下的乌鸦刺刺啦啦地叫唤。我来坝上前一天,跟母亲通长途电话,她说腿疼,又不能下地走路了,坐在炕上看天上的乌鸦。乌鸦刚把旗里的广播线扯断,把母亲喂狗的食物也带走了,母亲给院子里那窝麻雀洒的米麻雀都没吃着。现在她下不去地,出不了院子,她窝在炕上等人来帮她给小鸟送点粮食……
我交了坐骑。返回驻地已是黄昏。微光照射,浅草疲惫地喘息。而乌鸦成群结队踞守在草地里吵嘴。刘亚飞说这是不吉利的东西,但猫头鹰更不吉利一些,老乡从不伤害这些个东西,怕惹出什么麻烦。他们到冬天打一种叫斑什么的鸟……是国家保护鸟类?他说管它保不保护呢,到城里,一只可以卖到二十几元。还有山兔,冬天多,夏天也不少,但夏天的兔子有青草味,不好吃,老乡一般不打,到冬天家家下套子……当然不能伤到马。还有狐狸,现在人们不太打狐狸了。但是打山羊……这里没有黄羊,他们打黄羊要到北面一百多里外的内蒙古锡林郭勒地界打,可那里规定不让打野生黄羊,这边的人悄悄过去偷猎,那边的蒙古人若是碰到,就把人放倒……
说到短处,我一时语塞。我曾经早出晚归,拍摄纪念抗战的纪录片,拍摄活佛转世的纪录片,但没做过一部牧人和偷猎者之间痛苦交战的纪录片。想过多次,没真正动手去做。内蒙古的野生动物几近绝迹,广袤的草场日暮途穷,悲怆世事时有见闻。说实话,有多年了,深感忧虑、不安。
内蒙古人对偷猎和破坏草场的事无可奈何,只能叹息。但近几年,每次回家,我都能听到发生在家乡的关涉草场的伤人甚至命案,以暴易暴,粗陋、悲惨。在日益退化的草场上,牧人白天喝喊、恐吓偷猎者,夜晚打伤甚或偶尔打死耧地毛(发菜)的农民。除附近的农民外,很多偷掠者是宁夏的农民,他们成群结队潜入草地,将内蒙古的地毛大规模搂耙、运输到宁夏,经挑拣加工,精装成品,上印"宁夏特产"向全国甚至海外出售。耧过地毛的草场从此裸露,不再有混生草芥。昔日繁茂的草场,就这样被人为地损毁、撂荒,沙石泛起,刮得漫天遍野,牛羊无草可食纷纷倒毙。悲苦的牧民拿起猎枪保护牧场。一俟案发,警方去现场走一趟,草草询问一番走人了事。死者扔弃荒野,任狼和秃鹰分解。
一个人自生,就此自灭了。一个家走出去一个人,这个人再没能回来。一个村庄二三十人和别的村庄的二三十人结伙……很快组合起二三百人的队伍,每隔十来天就出发,去草地做发财的梦。白天像人,躺在坡地低洼处挖掘的等身长的地洞里睡觉;黑夜似鬼,悄悄潜进白天侦探好的草地耧一夜地毛,天亮返回地洞,在睡觉的地洞边上埋伏好裹着杂草的地毛,一觉睡到黑,等待下一个黑夜降临。返回村庄时也许某个同伴已经不再……我曾经跟踪采访内蒙古地域一个耧地毛的青年农民和他的妻子。那位叫郭四清的农民彻底丧失了昔日天不怕地不怕的"二不愣"气概,记忆消退、目光呆滞。他的妻子劳花对我说,她丈夫"一走十几天,哪有吃的带呢,一天顶多吃一个窝头,有水喝一口,没水就干着,实在渴得耐不住了,喝草地的水泼洞积的绿毛水。怕被人发现不敢四处走动,一白天尽窝在地窖里头。能回来算事,回不来那就回不来了……能怎么着呢。"她在地里锄草,顺带瞭望出去耧地毛的男人们回还的身影。"没钱交税,孩子们上学也没钱给学校。"
牧民与草依稀生长,对草场一般不有暴殄、暴利之心,其后生晚辈从小被灌输"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和心脏那样爱护草原"。劳花说,这些她知道。"咱们的铁耙子真的把人家的草败倒了。铁耙子下去,草就连根拔出来。"她丈夫跟村里的男人们冒险在深夜耙耧草地,所有耧到的乱草都塞进编织袋,等逃出牧民的领地,再粗粗挑拣。回家后浸泡,梳理,一根根把地毛细挑出来。耧二十多亩草地能得到一斤地毛,专门有人走村串户收购地毛,卖到南方一斤地毛能得二三百元。她说她只能挣个小头。我说郭四清会不会再去?她吭哧了一会儿,说要是没办法死也得去耧哩。
河北丰宁大滩镇元山子东道自然村的刘亚飞说,这些,他们这儿也有人干,去的就是北面的草原。
刘亚飞家兄妹四人,他是老大。他有两匹马,靠租马乘骑一年可以收入两到三千元。他们村满族居多,汉人、蒙古人也有,哪族人都学会了种地。一百多年前,这里是一片深草地--我想,这儿跟我家乡一百年前也许一样,是风吹草才能低下那种景气。刘亚非说,他们县的地盘在河北是第二大。他笑着说,他们迁移到此地时,这里更大。快有一百年了吧,迁到这儿。他们在关里受不了欺负出来的。我推算,正是清朝帝虎落平川、下岗歇菜的时候,满族人那时节万马齐喑。
结束骑马,我付他多一倍小费。他很高兴,说明天八点他等我们"娘儿俩"。
第二天,我和巴顿按时出了木栅栏。有农民走上前来让"骑马",我们说不行,约定下了。栅栏前面都是马,都是当地人,还有拴马的一米半高的木桩子。我们从他们身边穿过,没有看见刘亚飞。终于见到头天借给刘亚飞马的老乡,他一指西北方,说刘亚飞的马在那儿,有人骑呢。那是一片看不见马和人的草坡地。我和巴顿一面等待,一面在草地里晃悠。捡了几个小蘑菇。巴顿问:"我们必须等那个刘叔叔和他的马吗?"我说,头天说好了,得守约。我们踩着露水走到草场深处,希望能够碰到刘亚飞和他的马。直到中午,没见人和马影儿,我们只好返回。在木栅栏前的集中地,见刘亚飞在跟抽税的人高声交涉。
周末,旅游站举行篝火晚会。百里以外的内蒙古正蓝旗乌兰牧骑的散兵游勇赶过来包场演出,一场晚会,一个队员挣一百元左右,而旗乌兰牧骑日下已经开不出他们每月降至二三百元的工资。这群特古斯(时任正蓝旗旗委宣传部长,算是我的朋友)的兵,唱《青藏高原》,嗓音条件比李娜天然、宽厚,颤音悠远,但那位姑娘把歌仅当声音发出,而且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声音,她又还给了别人。自己的声音有没有生长呢?一定的,她一出生,就坐进一种长草的土地,坐进长了草的内心,若按正常情况发展下去,会日益地丰腴,日益地博大,一生一世,再一生一世,轮回成长。但一段时间以来,她忽略了自己的草地,她的心或许已经从草地脱落得远远的了,她唱出的歌像流泻出来的冷空气一样,在听众心里一下、一下地顶撞,直至冷却。她的心和声音驳离了,不相关联了。一个人的"自己的声音"到了哪里?她的眼睛是迷茫的,虚妄的,冷若晨霜。
从灵魂里截止了自我意识的那种感觉,是怎样发生、怎样发展的呢?原始的,像土地一样沉重的分量由于什么原因减少了?原本的激情,真心诚意的活法和态度,消失了。人变得不那么单纯、不那么踏实,不那么自信,不那么相信他人,不那么快乐,不那么幸福,不那么安于现状……她只是一味地播放颤动的嗓音,她的声波在夜空来来去去地滚动。歌曲的内容和她发出的声音的内容已然间歇、消逝。这是我从西部到东部内蒙古不时听到的年轻一辈人里的没落声息。
听着驳斥了诚实的歌声,像有一根皮鞭抽打身心,疼痛,羞惭,难耐。
我闷着头发呆,然后进去跳舞,又坐下来喝了一些啤酒。见巴顿正和几个半大不小的孩子在沙土地里、在空旷的乐音里,欢歌笑语。跟孩子在一起,在我是很幸福的事,现在我一个人在那里悲伤。
回到草地确实是好。多年离家在外,现在这些草场,这些原来北方各少数民族,匈奴、东胡、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回纥、契丹、女真……割据活动的地区,真实地铺展在眼前。这片经年流渗鲜血汗水的土地,被一盏高高悬挂的电灯叠映出一些花样,忽忽然然闪动,让人欢喜,又不由得哀痛。默饮了一些生啤酒,感觉稍好一点。可这时,千年古话真就黯然照映了……
许多真实确实已经消失,真实的幸福,真实的悲苦,真实的拥抱,真实的哀悼……还有真实的爱恨恩仇。一种真实谢世,另一种真实还生,好比真实的绿色牧场几十年间一下子消退,冷酷的黄沙走石漫天遍野。
人活着,还有什么比这更干燥、残酷的事呢。
突然想到忽必烈和其兄弟之间的征战。成吉思汗之子拖雷的第二个儿子忽必烈,对中原的制度和文化嗜好很深,在他身为亲王时,奉兄长蒙哥大帝之命多次率众南征,每战必胜,每胜必使新征地的新臣民归心于他。1256年,他命人在桓州之东、滦水北岸的龙冈营建宫城,三年后完工,命名为开平府,就是今正蓝旗元上都遗址--此地离我们所在的旅游站仅有一百公里之遥。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府被推举为蒙古合汗,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几乎是同时在西部大汗都城哈刺和林被支持者推举为合汗,于是兄弟二人多次兵刃相向。开平府升为都城、定名上都的第二年,即1264年,大败的阿里不哥和他的同党诸王前来向他的兄长忽必烈投降、请罪。兄弟二人在御帐里相隔阒望,潸然垂泪……不幸,元帝国末了,到继元代遗业、统一蒙古各部的鞑靼国,以及各部随后几百年的聚散合分,无不败于蒙古后人间不休的争夺、离析、内乱。生灵失声、景致荒芜。
有一句蒙古谚语,翻成汉语大意是:覆灭的火焰自燃。
草地连起的城郭,像人的耳朵。它能完成什么呢。只为让人躲在窝廓那里?我的家人是在那里。我听不见他们的声音,他们也听不到我的。我的忧郁,在这轰鸣着幸福的时刻那么多地充盈到我的心里。我的心境是那个草地的城郭所不能窥见的。
人与人是不是有另一种渠道可以连接,像草地那样式的?草地有生命,和人一样,但也和人一样,颓萎,没落,虽有犹无。谁愿意注意它,倾听它呢。需要草地的人,是些顽冥之人,无力地依附于草地,想请草地倾听他、帮助他,而非他倾听草地、帮助草地。人何时能够自觉地顾忌到草地呢?
草地的秘密如同人的秘密,随从季节生成和泯亡。
我在这里,等待一个声音。而我母亲正在察哈尔西部草原,等待一个人来帮她给院子里的麻雀送一些粮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