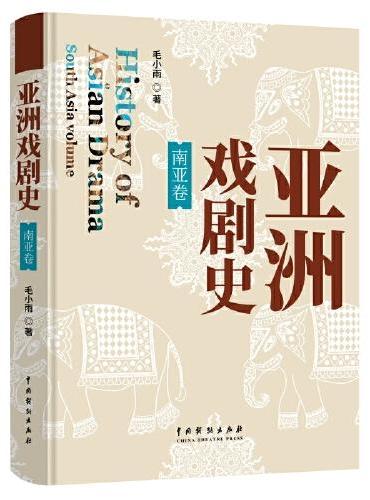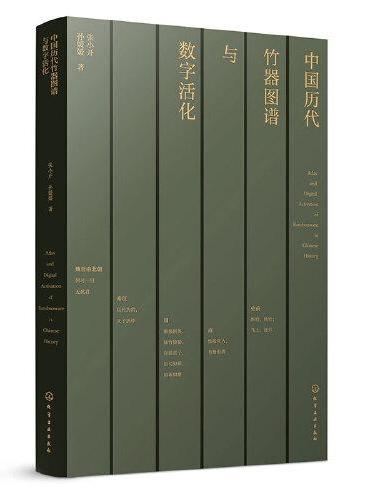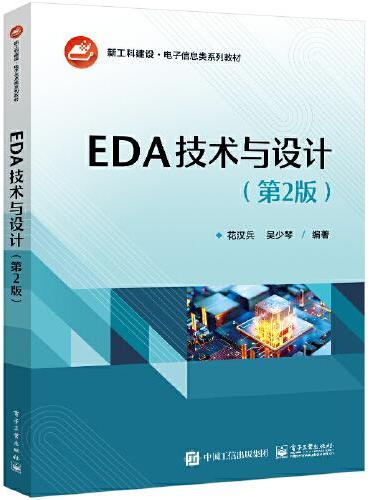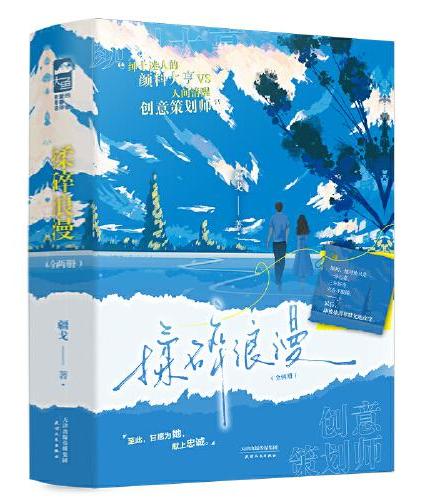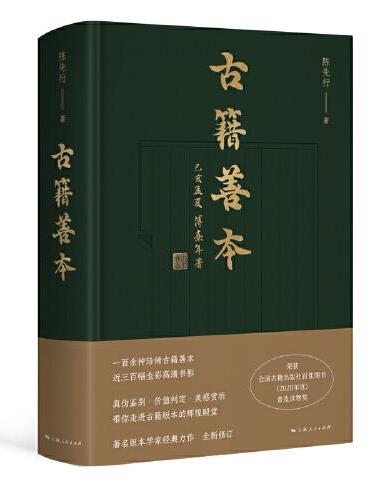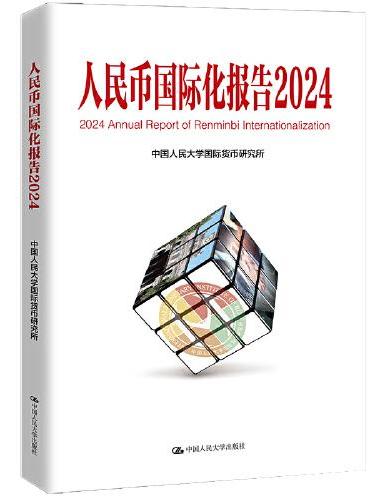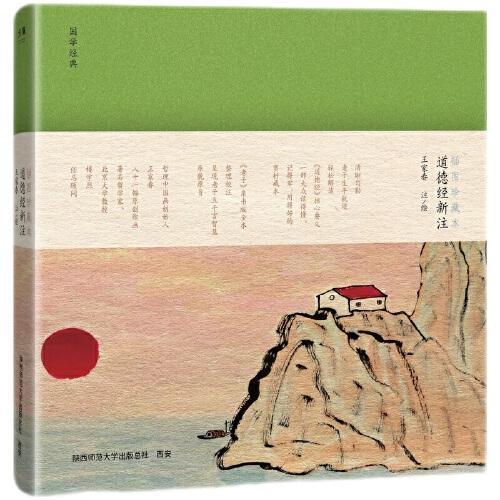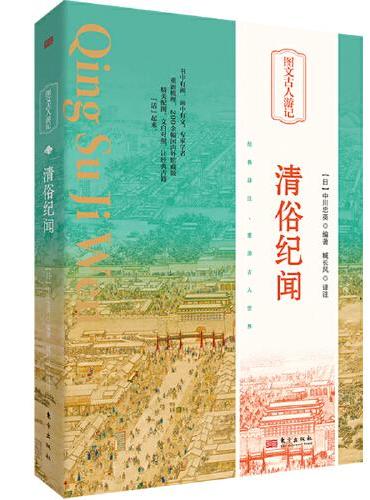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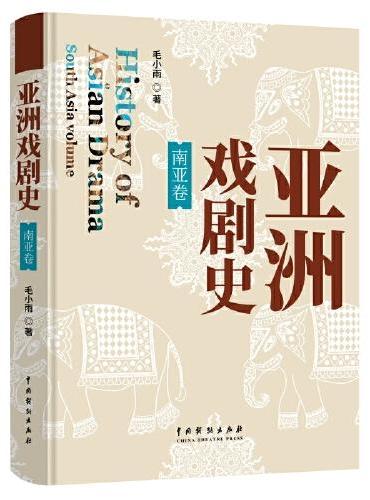
《
亚洲戏剧史·南亚卷
》
售價:HK$
14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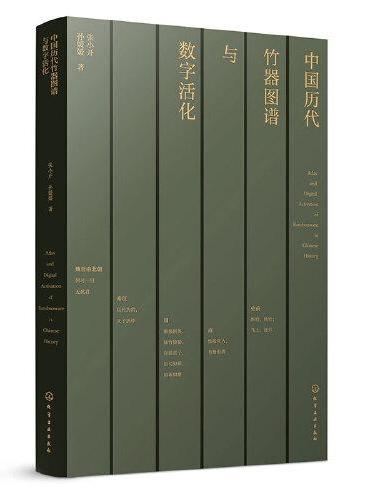
《
中国历代竹器图谱与数字活化
》
售價:HK$
55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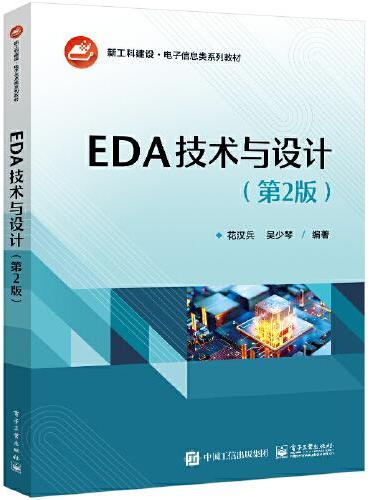
《
EDA技术与设计(第2版)
》
售價:HK$
8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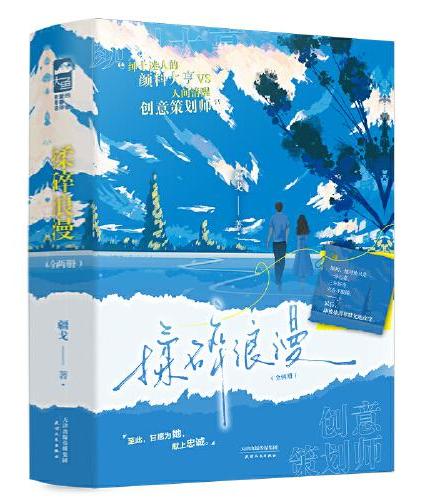
《
揉碎浪漫(全两册)
》
售價:HK$
7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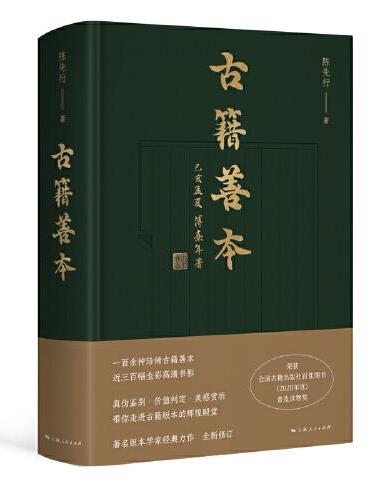
《
古籍善本
》
售價:HK$
53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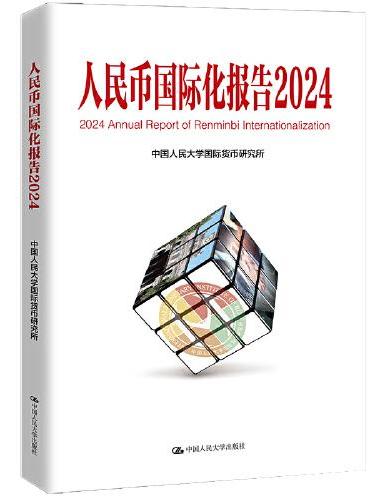
《
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4:可持续全球供应链体系与国际货币金融变革
》
售價:HK$
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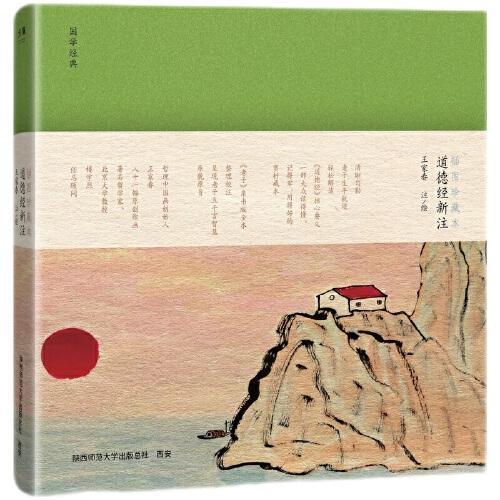
《
道德经新注 81幅作者亲绘哲理中国画,图文解读道德经
》
售價:HK$
14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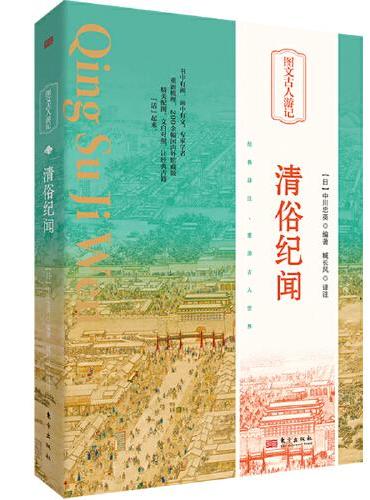
《
清俗纪闻
》
售價:HK$
98.6
|
| 編輯推薦: |
|
作为前中国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对当代中国新闻出版改革与发展的重大作用和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通过他对亲身经历的回忆,我们得以更清楚和真切地看到整个当代中国出版业的发展脉络和诸多重大决策背后不为人知的细节。
|
| 內容簡介: |
|
《思念与思考》是前新闻出版界领导宋木文的一部回忆性文集,共收录思念故人文章和有关出版的论文30余篇。该书联系历史背景,以回忆人物为主题,如胡乔木、徐光霄、陈翰伯、王益、陈原、吴阶平、范敬宜等,回顾了作者同他们的交往以及他们为中国出版事业改革、开放和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作者长期担任我国新闻出版事业领导人,本书从多方面反映了他的出版观和情理观。
|
| 關於作者: |
|
宋木文,吉林榆树人。1929年生。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东北大学政治经济系肄业。1972年起从事出版工作,历任国家出版局研究室副主任、办公室主任;文化部出版局副局长、代局长,文化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国家出版局局长、党组书记。1987年任新闻出版署副署长、党组副书记兼国家版权局局长。1989年至1993年任新闻出版署署长、党组书记。著有《宋木文出版文集》、《中国的出版改革》(日文版)等。
|
| 目錄:
|
俞晓群序
胡乔木对新时期出版工作的历史性贡献
姜椿芳和梅益的大百科总编辑署名纷争是怎样化解的
周巍峙的崇高人品长在永存
徐光霄和石西民"文革"中为恢复出版尽心尽力履步维艰
王匡率先开展出版领域的拨乱反正
陈翰伯推动出版拨乱反正全面展开
王子野的学者与战士品格
王益对出版印刷发行改革发展的重要贡献
许力以稳健推进出版改革开放与骨干出版工程建设
边春光为国家出版与版权管理机构建设谋划操劳
陈原是学识渊博著述丰厚与时俱进的编辑出版大家
陈荒煤对新时期文学评论事业的深情牵挂
感受吴阶平医学大家的历史观
感受叶至善"我是编辑"的人生定位
向《续修四库全书》主编顾廷龙致敬
向老一辈革命家和著名学者匡亚明致敬
宋木文与范敬宜"两个老头儿"的交往与心声
我与竹内实携手为中日文化交流添砖加瓦
我的出版观
出版业科学发展之探索
作者编后小记
|
| 內容試閱:
|
1977年5月,中央派王匡、王子野主持国家出版局清查"四人帮"及其影响的工作,随后被分别任命为党组书记、局长,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同时被任命为副局长的还有陈翰伯、许力以、王益;稍后又增补常萍为副局长。
王匡1917-2003,1931年起参加革命活动,1937年赴延安,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作为新华社记者随军从事采访工作。1949-1966年历任新华社华南总分社社长和南方日报社社长,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候补书记,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宣传部长。从1978年7月起在国家出版局任职一年多后即调到香港任中共港澳工委书记、新华社香港分社第一社长。
在王匡主持国家出版局一年多的这段时间里,"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还束缚着广大干部,全党拨乱反正的大气候尚未形成,被搞乱和颠倒了的思想理论路线是非还未清理,一大批出版业务骨干还没有从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政治帽子和枷锁中解脱出来,大多数建国以来出版的图书还被封存着。
批判"两个估计"
以批判"两个估计"为出版界拨乱反正的开端,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王匡到任后即决定成立出版工作调研小组,由陈原主持,由我协助,以国家出版局研究室谢宏、包遵信、李炳银等为工作班子,另调李侃、张惠卿、倪子明、谢永旺等同志参加。调研小组主要清理"左"的指导思想在出版工作中的表现,弄清路线是非。经过三个多月的调研,形成了清理出版工作路线是非若干问题的意见。在王匡亲自指导下,从调研小组到局党组,取得了共识:要纠正出版工作"左"的影响,分清路线是非,扭转出版工作窒息、萧条局面,一定要批判、推倒强加于出版界的"两个估计"。
"两个估计",出自1971年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给中央的报告,并经毛主席批示同意颁发的中央文件。其内容是:建国以来出版界是"反革命黑线专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统治地位"。这个文件对恢复处于停顿状态的出版工作起了积极作用,但其中的"两个估计"却成为正确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工作、解禁一大批被封存图书和解放整个出版队伍的严重障碍。在粉碎"四人帮"后的那段徘徊时期,"两个凡是"影响很大,由一个业务部门去纠正与毛泽东有关的决策是很困难的。恰逢此时,邓小平提出要纠正对科学和教育领域的"两个估计"出自1971年8月中央44号文件,同出版领域的43号文件几乎同时发出,内容同样是"黑线专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占统治地位,对出版界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经调研小组查阅当时有关材料,1971年中发43号文件也是经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在讨论43号文件的一次会议上,周总理曾提出文件中要"讲红线的作用",还说对出版队伍"要作分析,不作分析不行"。但张春桥立即说:"先肯定专政,然后再分析","从领导权来说,是专了我们的政";从队伍的世界观状况来说,"也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会议文件的修改稿和定稿都按这个调子敲定了文字。
以上述查证的资料为依据,经过充分准备,国家出版局党组决定在1977年12月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从揭批"四人帮"入手,着重批判"两个估计"。这是粉碎"四人帮"后,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出版工作会议。王匡在会议的报告中指出:这"两个估计"从此成了"四人帮"打击革命干部、打击知识分子、颠倒敌我、颠倒是非的"两根大棒",是"镇压广大出版工作者的紧箍咒",一直影响到现在,必须彻底批判,把"长期压得抬不起头来的广大出版工作者解放出来"。与会代表普遍认为:"''两个估计''就像两座大山,压在我们的头上,使我们透不过气来。对''两个估计''的批判,是一次思想解放,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收获。"这次会议对"两个估计"的批判,限于历史条件,没有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极"左"路线紧密联系起来,但还是在全国出版界甚至在文艺界(当时文艺界尚未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正像会前预计的那样,会上也有不同的意见,说这样做是否批了毛主席?是否批了主持出版座谈会的周总理?会后有人把这种意见向中央报告了。当时中央分管文化出版工作的吴德曾过问此事。王匡找我商量,我建议写一专题材料,以《出版工作情况反映》增刊的形式向中央和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汇报。此期"增刊",除着重汇报了"四人帮"如何对抗周总理指示精神把"两个估计"写入会议文件外,还引用王子野在会议总结中说的在"会议一开始,我们就明确地表示过,集中批判''四人帮''塞进文件中的''两个估计'',而不涉及整个文件"。这样,这次批判产生的余波才得以平息。
会后,国家出版局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报告》,谈到"这次会议着重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炮制的''黑线专政''论。国务院于1978年7月18日以141号文件批准并转发了这个报告。这就表明,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这次对"两个估计"的批判得到了国务院的确认和批准。
集中重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
为缓解当时的严重书荒,初步满足广大读者如饥似渴的需求,王匡主持的国家出版局作出了一项有重要影响的决策,就是调动全国出版、印刷力量,集中重印建国以来出版的35种中外文学著作。主要是:五四以来现代文学10种,有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的代表作,以及《红旗谱》、《铁道游击队》等;中国古典文学9种,有《唐诗选》、《宋词选》、《古文观止》、《东周列国志》、《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外国古典文学16种,有《悲惨世界》、《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安娜·卡列尼娜》、《牛虻》、《一千零一夜》,以及契诃夫、莫泊桑、莎士比亚、易卜生等大家的作品选集等。在此之前,也曾重印《红岩》、《青春之歌》、《暴风骤雨》、《林海雪原》等少数几种,但那都是报请中央政治局分管出版的领导同志批准的。所有这些在"文革"中惨遭厄运的中外古今文学名著能够重见天日,无疑是对"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禁锢政策的否定,而广大读者在各大城市(只能先供应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新华书店门外通宵达旦排队和在店堂内摩肩接踵抢着购书的前所未见的景象,则表明国家出版领导机关拨乱反正落实党的文化政策的举措是深得人心的。在当时,这可是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书荒的大举动。
做好《鲁迅全集》新版的注释编选出版工作
王匡这期间还直接领导和策划了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出版工作。1975年11月1日,毛主席对周海婴关于鲁迅著作注释出版问题的信作了批示,石西民任局长时也曾努力做了贯彻,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一重大出版任务未能顺利进行。为了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纠正编选工作的错误指导思想,完成毛主席生前批准的鲁迅著作出版计划,在王匡主持下,国家出版局于1977年9月11日向党中央报送了《关于鲁迅著作注释出版工作的请示报告》。王匡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强对编选新版鲁迅全集的领导,建议请胡乔木过问全集的编选工作,掌握方针和对注释中的重大问题加以指导和审定(胡乔木提出注释中的重大问题要请示中央审定);将"文革"中受"四人帮"迫害,尚在江西一工厂劳动的林默涵("文革"前任中央宣传部分管文艺工作的副部长)调回北京主持编选工作,并借调冯牧、秦牧来加强原注释工作的班子;约请郭沫若、沈雁冰、周建人、王冶秋、曹靖华、李何林、杨霁云、周海婴担任鲁迅著作注释工作的顾问。二是确定全集收书范围和编选注释原则,除1958年版的内容外,拟增入全部书信、日记,辑录古籍和译文的序跋,以及1958年以来所发现的全部佚文,并附鲁迅年谱和注释索引于末卷。新版全集注释以1958年版为基础,原注释凡能用的尽量采用,错误的加以改正,不足的加以增补,繁琐的加以删减,体例不一的加以统一。总之,力求准确、简明、通俗易懂。人们不会忘记,对1958年版《鲁迅全集》,"四人帮"在"文革"中颠倒黑白,横加指责,特别是以一条关于30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的注释向周扬、林默涵兴师问罪,大举挞伐。王匡主持的国家出版局报请中央批准,由林默涵主持新版全集的编选工作,以1958年版全集作为新版注释的基础,这也是一项重大的拨乱反正。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了新版《鲁迅全集》(16卷本),这是学术界、出版界有关专家卓有成效工作的结果,而王匡同志对此事的策划与决策所起的作用也是很重要的。
恢复稿酬制度
王匡还决定恢复在"文革"中停止的稿酬制度,并报请国务院批准后于1977年9月发文实施。当时曾为此事征求过一些同志的意见,由于"文革"批判资产阶级法权造成的紧张心理尚未消除,有的受"文革"迫害的文学界老同志也不敢明确表示赞同。可见,王匡下此决心的勇气和胆识了。这次恢复稿酬是低标准的,后来曾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指责,1980年4月国家出版局报请中央书记处批准提高了稿酬标准,然而我要说,当初能迈出这一步,的确是很有胆识的拨乱反正之举。
大约在1978年五六月间,王匡同我谈起他做出这几项重要决策的心情时,郑重、坚定而又亲切地说:木文!看到出版界的同志那么压抑,出版事业那么萧条,我宁愿再一次被打倒也要这样做,也许有人要打倒我的时候我已经去见马克思了。
王匡主持国家出版局的工作,也就一年多一点时间,然而他为打破禁锢,恢复和发展出版事业所做出的几项重要决策,不仅受到当时出版界的普遍赞誉,并使压抑多年、尚未开展拨乱反正的文学艺术界为之振奋,至今还受到人们的称道。25年后,王匡真的去见马克思了,我想,如果马克思有知,他会对他的门生给予嘉奖的。
王匡同志,我想念您
王匡离开国家出版局后,在北京的住所,在广州的家中,我都多次前去探望,表示敬意。
1996年1月春节前,我用特快专递给王匡在广州的家中寄去贺年片和我回忆王匡在国家出版局那段工作的文章。王匡女儿王晓吟(任职广东省委宣传部)在2月1日给我的回信中转述了王匡对那段历史的回顾。信中说:"您寄来的贺年片和您用特快专递寄来的文章都收到了,而且都交给了我的父亲。父亲看到您还在惦记着他十分感动和欣慰。他让我告诉您,这些事不是他一个人就能办得了的,是因为大家都有这个共识,所以才能成功。他心里一直感谢你们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给他以支持。父亲还说当时印那些中国古典名著、世界古典名著还有一个困难就是没有印书的纸。纸都在汪东兴同志手里。那些纸是准备印毛泽东全集的(笔者注:毛泽东逝世后,中共中央决定出版《毛泽东全集》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为此储存了一批专用纸)。在那种情况下毛泽东全集还能不能出,不能出的话,纸能不能动,这可是要冒风险的。我父亲就毛泽东的书(指全集)能不能出的问题去问过吴冷西同志,吴笑而不答。问胡乔木同志,他说恐怕很难。于是我父亲便连夜赶到中南海去请示吴德同志,要求动用印毛泽东的书的纸印中国和世界文学名著。经批准后,就动用了这个纸把书印了出来。这是一个技术问题,弄不好也是一个路线问题,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可是要被打倒的"。晓吟对她父亲这段经历还作了一点评论。她在信中说:"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可是中国人的历史感却不怎么强,容易遗忘过去。在后来人看来一切都很容易,可是对当事人来说真是迈一步也不容易,这是一场生死存亡、宠辱枯荣的考验。"
1996年5月29-31日,我应约去广州参加出版协会成立大会,说是实话,借此机会看望王匡也是促成此行的重要因素。5月30日上午,我来到王匡的住处,他的女儿王晓吟在门前等候。她告诉我,昨晚她父亲知我要来看他,心情很不平静,一夜未睡安稳。我听后感到不安。一个多月前,我在北京曾同王匡通过两次电话,从交谈中我感到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身体状况有些变化,这虽然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也使我更加惦记他。这次见面,的确要比我在1992年夏在广州他的住处看他时,行动不很方便,说话有些缓慢,但思路清楚,特别是在回忆往事的时候,这多少也给我带来一些安慰。他问我,他的文集《长明斋诗文丛录》收到了没有?我说收到并读过了,深得教益。晓吟接着说,她父亲对自己的文章总是不满意,不愿意向别人送书。这也使我更加珍视有王匡签名的赠书。王匡问起我的文集出版了没有?我说正在编选的那本文集水平不高,可读性不强,但出版后一定呈送王匡同志指正。他重述晓吟给我的信中所表示的意见,说他在国家出版局所做的工作是靠大家的支持才做成的,他特别提到已逝世的陈翰伯、王子野,还郑重地让我代他转达对他那段工作同样给予支持的王益、许力以、陈原和范用的问候。同去的潘国彦还拍了几行照片留作纪念。
王匡2003年12月14日逝世后,我写了《王匡同志在国家出版局的岁月》一文,在《中国新闻出版报》发表。在悼念王匡的日子里,我先后收到他的女儿王晓吟的三次来信,向我通报在广州的悼念情况和寄送刊载悼念活动的报纸。12月25日信中说:"岁月匆匆,30多年过去了,但是当年你们的胆识、勇气依然令人钦佩不已,在出版史上这一段应当大书一笔。"过了几天,也就是2004年1月8日,她来信讲王匡出生地虎门镇的报纸两次出版纪念专版都通栏印着"深切怀念虎门人民的好儿子王匡同志",1月5日的专版还以通栏标题发表了《王匡同志在国家出版局的岁月》。
在王匡逝世后,我找出王匡生前签名赠送的他的文集《长明斋诗文丛录》,翻阅收入各个时期的照片,阅读战争年代在前线采写的新闻作品和部分诗文,都被他的人品和文品所感动,使我更加怀念这位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奋斗一生的老战士,更加敬仰这位在国家出版局任职虽然短暂却使人长久难忘的老领导。
我现在只想说,王匡同志,我想念您!
(选自《王匡率先开展出版领域的拨乱反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