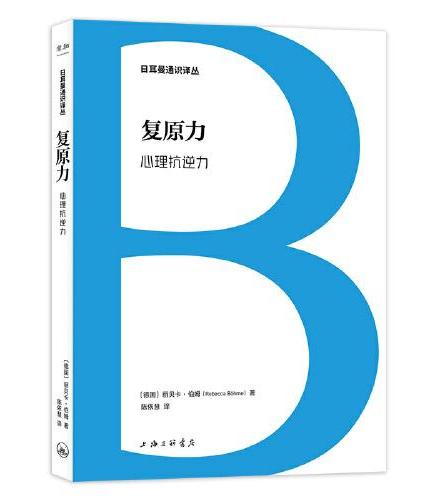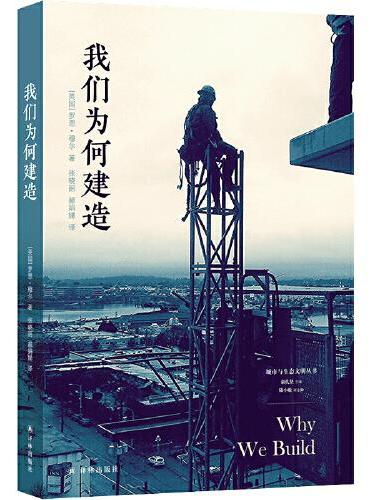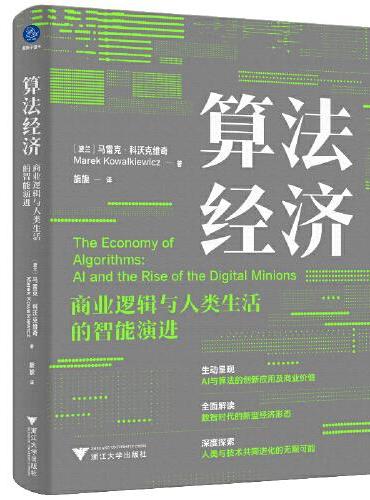新書推薦:

《
没有一种人生是完美的:百岁老人季羡林的人生智慧(读完季羡林,我再也不内耗了)
》
售價:HK$
5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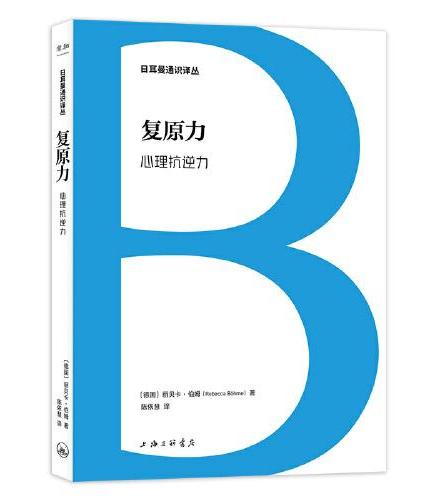
《
日耳曼通识译丛:复原力:心理抗逆力
》
售價:HK$
34.3

《
海外中国研究·未竟之业:近代中国的言行表率
》
售價:HK$
13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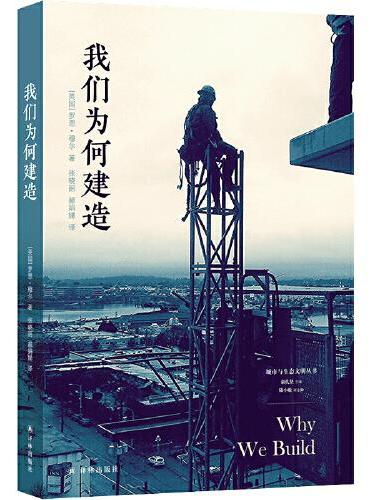
《
我们为何建造(城市与生态文明丛书)
》
售價:HK$
8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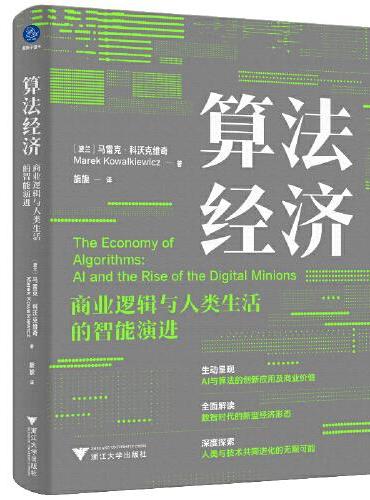
《
算法经济 : 商业逻辑与人类生活的智能演进(生动呈现AI与算法的创新应用与商业价值)
》
售價:HK$
79.4

《
家书中的百年史
》
售價:HK$
79.4

《
偏爱月亮
》
售價:HK$
45.8

《
生物安全与环境
》
售價:HK$
56.4
|
| 編輯推薦: |
|
伯林曾表示本书将这三位作者联系在一起的是他们对法国启蒙运动基本思想的厌恶,以及他们对于这一思想深刻而又影响深远的批判性反思……在今日,启蒙的拥护者和其批评者之间的争论至少和刚开始时一样至关重要,并且在开始时,双方文章中的观点表达方式比后来都要更清晰、更简单、更大胆。
|
| 內容簡介: |
|
《启蒙的三个批评者》首次掘取以赛亚·伯林思想史研究项目中的三块宝石,通过对启蒙运动的三个批评者的共情视角和深层解读,阐释了这一充斥着过度科学思维的运动是如何遭到反对的。这三位批评者所做出的贡献均无与伦比,维柯确立了人文科学,说明了它何以必然与自然科学不同;赫尔德开创了民粹主义、表现主义和多元主义(伯林把这一观念发扬光大);反理性主义的哈曼则点燃了浪漫主义之火,这一重要的运动在对启蒙运动的反对声中发展壮大。
|
| 關於作者: |
|
英国哲学家和政治思想史家,20世纪最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出生于俄国里加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0年随父母前往英国。1928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和哲学,曾任牛津大学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沃尔夫森学院院长,1957年获封爵士。主要著作有《卡尔·马克思》、《俄国思想家》、《概念与范畴》、《反潮流》、《个人印象》、《扭曲的人性之材、《现实感》、《浪漫主义的根源》、《观念的力量》、《自由及其背叛》、《自由论》、《苏联的心灵》等。作为接触的思想史研究者,先后被授予伊拉斯谟奖、利平科特奖和阿涅利奖。
|
| 目錄:
|
编者前言
参考文献说明
维柯与赫尔德
作者前言
引言
维柯的哲学思想
维柯的知识理论及其源头
赫尔德和启蒙运动
北方的巫师
编者前言
德语版前言
作者前言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生平
第三章 核心
第四章 启蒙运动
第五章 知识
第六章 语言
第七章 创造性的天才
第八章 政治
第九章 结论
附录
参考书目说明
索引
|
| 內容試閱:
|
赫尔德和启蒙运动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我们自己创造的世界里。
一
赫尔德的声誉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之上:他是民族主义、历史主义和民族精神这些相互关联的思想之父,是对古典主义、理性主义以及对科学方法万能的信仰进行浪漫反抗的领袖之一,一句话,他是法国启蒙哲学家及其德国门徒的对手当中最令人生畏的人。这些启蒙哲学家当中最知名的有达朗贝尔、爱尔维修、霍尔巴赫,还有伏尔泰、狄德罗、沃尔夫和赖马鲁斯,他们相信现实是根据普遍、永恒、客观、不变的规律来安排的,而这些规律是可以通过理性的研究得到发现,但是赫尔德坚信每个活动、条件、历史时期或文明都拥有一种它自己独特的个性;企图把这些现象归结为一些相同的因素的结合,或者根据普遍的法则来叙述或分析它们,恰恰容易抹煞构成研究对象(不管是自然中还是历史中)的特殊品质的那些至关重要的差异。对于伦理学或美学、物理学或数学中的普遍规律、绝对原则、最终真理、永恒的模式和标准这种观念,他反对在适用于研究物理性质的方法和人的变化发展的精神所要求的方法之间作根本区分。人们相信他已把新的生命注入到社会模式、社会发展的观念中,他指出质的因素和量的因素一样具有极端重要性,而这些难以碰触、难以考量的因素正是自然科学的概念忽视或否认的。他沉醉于(不管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创造过程的神秘之中,对有着概括、抽象、同化另类、统一异物之倾向的理性主义,发动了一场全面的进攻;这种进攻尤其是针对其标榜的目的:创立一个包罗万象的知识体系,原则上它能够回答一切可理解的问题,即一门关于现存万物的统一的科学理念。在宣传反对理性主义、科学方法和可理解的规律的普遍权威的过程中,他被认为激发了特殊主义、民族主义以及文学、宗教和政治的反理性主义的发展,从而在改造下一代人的思想和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种在一些关于赫尔德思想的最著名的论著中可以发现的描述,大体上是正确的,但简单化了。他的观点的确对后来的思想和实践产生了深远和具有革命性的影响。一些人称赞他是一名旗手,用信仰反对理性、用诗意和历史的想象反对法则的机械应用,用洞见反对逻辑,用生命反对死亡;另一些人则把他划入混乱、倒退、甚或是反理性主义的思想家行列,这些思想家误解了他们从启蒙运动那里学来的东西,并且滋养了德国沙文主义和蒙昧主义的浊流;还有一些人试图在他和孔德、达尔文、瓦格纳或现代的社会学家之间找到共同的基础。
我这项研究的目的并非直接针对这些问题发表看法,尽管我倾向于认为他对当时自然科学的熟悉和忠诚程度经常被严重地低估了。科学发现对他的吸引和影响一点也不比歌德受到的吸引和影响小,并且他像歌德一样,认为错误的一般推理经常来自于它们。他毕生都对百科全书派提出尖锐和坚定的批评,但是他接受科学理论,甚至为它们欢呼,而百科全书派的社会和伦理学说正是以科学理论为基础;赫尔德只是认为从最新确立的物理学或生物学的规律中不能够得出这些结论来,因为它们明显与任何敏感的观察者从社会自我意识一开始就认识到的确凿无疑的人类经验和活动相矛盾。但是我要讨论的不是赫尔德对当时自然科学的态度。我希望把自己尽可能限定在(有时不然)赫尔德真正具有原创性的观点,而绝非将他的一切思想尽收眼底;我尤其试图考察其汹涌思想中的三个主要观点,这些观点在两个世纪中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它们本身也是新颖、重要和有趣的。这些观点是与他那个时代的主流背道而驰,我把它们叫做民粹主义、表现主义和多元主义。
让我从指认赫尔德受惠最显著的其他思想家开始。历史科学的恰当主题是共同体的生命而不是个人(政治家、士兵、国王、王朝、探险家和其他著名人士)的业绩,赫尔德的这个论题已经被伏尔泰、休谟和孟德斯鸠,被施洛策尔和加特雷尔,以及被他们之前的16世纪和17世纪早期的法国历史作家,尤其是被维柯以无可比拟的想象力和创造性陈述过。就我所知,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赫尔德读过维柯的《新科学》,直到他自己的历史理论形成至少二十年之后他才读了这本书;但是即便说他没有读过维柯,他还是听过说维柯的,而且很可能读过韦格林,以及切萨罗蒂那荷马式的评论。此外,伟大的诗人们表达了他们所处社会的思维和经验,是它们最真实的代言人,这种思想在赫尔德的成长年代广为传播。沙夫茨伯里把艺术家颂扬为他们时代的神灵之声。瑞士的冯穆拉尔特、博德默尔和布赖丁格把莎士比亚、弥尔顿和古德国的吟游诗人远远置于法国启蒙运动的偶像之上。博德默尔在这些论题上的观点是与维柯忠诚的崇拜者彼得罗卡莱皮奥伯爵一致的;在赫尔德的青年时代,巴黎及其德国追随者在文学上的历史主义与新古典主义之间的斗争激战正酣。这也许足以说明维柯和赫尔德之间的观点何以惊人地相似,也足以排除对更为直接的线索的漫长而无望的寻求。无论如何,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文化模式说绝非什么新鲜玩意儿,就像他早期的《另一种历史哲学》的题目所着意强调的。而这个主题也已经被他的主要敌人伏尔泰在其著名的《风俗论》中以及在其他地方以概括的术语有效地展现了。
同时,文明的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物理和地理因素的差异(通常用“气候”这个一般术语来指代),这种观念自孟德斯鸠以来已成了陈词滥调。在孟德斯鸠之前,它出现于博丹、圣埃佛尔蒙、迪博神父及其追随者的思想中。
至于文化上的傲慢,即根据现代价值来评判古代社会的倾向,其危险性已经由比赫尔德年长的同时代人莱辛(尽管莱辛很可能受到他的影响)作为一个主要的论点提出。没有谁比伏尔泰更尖锐地批评了欧洲的习气:把偏远的文明,诸如中国的文明,看作是低等的,而他为了揭露除了自身之外不承认任何价值的“野蛮的”犹太—基督教世界观的排他性和疯狂,却对这些偏远的文明大加赞扬。赫尔德把这个武器转向伏尔泰自己,责备他犯了18世纪巴黎人观点上的狭隘,这样一个事实并不能改变如下事实:一切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源头都是欧洲本身。伏尔泰称赞了古埃及,而温克尔曼称赞了希腊人;布兰维利耶提到了北方民族的优越性,而马莱在其著名的丹麦史中持同样观点;贝亚特路德维希冯穆拉尔特早在1725年就在他的《关于英国人和法国人的通信》中把瑞士人的独立精神和英国人进行了对比、尤其是把英国作家和法国人的习惯上的矫揉造作进行了对比;赫德、米勒,以及在他们之后的尤斯图斯对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当作黑暗时代而不屑一顾的中世纪的欧洲唱起了赞歌。诚然,他们是少数,而且尽管尤斯图斯默泽对古代撒克逊人被查理曼大帝残酷地文明化之前的自由生活的赞歌可能受到过赫尔德的影响,但它们毕竟不是赫尔德原创的。
历史上确实存在着对文化差异的重新重视,以及对永恒的一般规律和法则的反抗。拉辛和高乃依在历史感上的缺乏,使得他们给古典或异域的东方人士穿上了路易十四时期朝臣的服装,由此被迪博批评,也被圣埃佛尔蒙冷嘲热讽。在天平的另一端,一些德国牧师,其中最主要的是阿诺德与青岑多夫,着力强调这样一种见解:每种宗教都有一种专属于它的独一无二的洞察力,基于这种信仰,阿诺德勇敢而充满激情地呼吁宽容对路德正统的偏离,甚至宽容异端和不信教者。
一个民族或一种文化的精神观念不仅对于维柯和赫尔德有着中心意义,而且对于著名的出版家弗里德里希卡尔文莫西尔(赫尔德认识他并读过他的作品),对于博德默尔和布赖丁格,对于哈曼,以及对于齐默尔曼都具有中心意义。博林布罗克曾提到人们在彼此之间划分出不同的民族,这一行为深深地扎根于自然本身当中。到本世纪中叶,有许多凯尔特狂和哥特狂,其中特别是爱尔兰人和苏格兰人,他们赞扬盖族部落或日耳曼部落的优点,认为他们不仅在道德上和社会上比古希腊人或者罗马人优越,甚至比现代拉丁和地中海地区民族的颓废文明更优越。卢梭著名的致波兰人的信建议他们通过顽固地坚持他们的民族风俗和特点来抵制俄国的武力同化,这封信表现了同样的精神,尽管对于当时的世界大同主义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
至于伯克和赫尔德强调的社会有机体的观念,此时已是陈词滥调了。有机体的隐喻这种用法至少与亚里士多德一样古老;没有谁比中世纪的作家们运用得更滥了;它们是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政治小册子的灵魂和中心,是胡克和帕斯卡有意识地用来反对新的科学—机械观的武器。这种观念确乎毫无新颖之处;相反,它代表了一种向更旧的社会生活观的蓄意回归。对于伯克来说,情形也是如此,他同样倾向于运用从新的生命科学中得出来的类比;我没有见过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伯克读过或听说过尤斯图斯默泽或赫尔德的思想。
什么使得人和社会幸福?有关这一理想的不同版本已被亚当弗格森在其具有高度原创性的《论公民社会的历史》一书中生动地阐明了,赫尔德曾读过该书。
在赫尔德用自然主义的术语解释事件的过程中,他采纳了洛克、爱尔维修和百科全书派乃至整个启蒙运动的追随者所采取常规的方法。赫尔德不像他的老师哈曼,他受到了自然科学发现的决定性影响;他给予它们一种活力论的解释,尽管与赫姆斯特赫斯、拉瓦特尔和其他“直觉主义者”赞成的神秘的或神智学的解释并不相同。
自然那单一、伟大的宇宙力体现在有限、动态的中心,这种古代观念被莱布尼茨赋予了新的生命,并成了他的全部门徒的共识。
神圣计划在人类历史中得到实现,这一观念也被不间断地传递着,从《旧约》及其犹太解释者到基督教神父,再到波舒哀的古典阐释。
时空上彼此相隔绝的原始民族(一面是荷马时期的希腊人和早期的罗马人,一面是印第安人或日耳曼部落),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已经被丰特内勒和法国的耶稣会士拉菲托神父指明;18世纪早期这种方法的鼓吹者,尤其是像布莱克韦尔、托马斯沃顿与约瑟夫沃顿这样的英国作家,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这些猜测。这已经成为了在英国以及意大利(在维柯的推动下)兴盛的荷马学的一个部分。当然,切萨罗蒂觉察到了这种方法对于比较语文学和人类学文献的更为广泛的意义;当狄德罗在编撰《百科全书》时,他在写作一篇古希腊哲学的总论的过程中,把荷马贬作“一个神学家、哲学家和诗人”,他还引证了一个“众所周知的人”的观点,认为在将来不可能有多少人去阅读荷马,这是一种典型的帮派主义的怪想,吻合了笛卡尔和皮埃尔培尔的精神,反对膜拜过去和无聊的博学,是古代人和现代人之间的纷争的迟到回声。维柯不敢触及的《圣经》本身,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从先前的斯宾诺莎和西蒙神父就已开始的对这个文本的哲学和历史批评被小心地延续下来——尽管遭致了一些来自基督教正统的反对,既有天主教的,也有新教的——按照世俗学术的规则进行严格的考量。法国的阿斯特吕克,英国的洛思,以及在他们之后德国(和丹麦)的米夏埃利斯,他们都把《圣经》看作是在几个不同时代合力完成的东方文学的纪念碑,大家都知道吉本受惠于莫斯海姆对早期基督教教会史的冷淡的世俗态度。作为一个并非训练有素的研究者,赫尔德可以借鉴的东西有很多。
同样,这也适用于赫尔德语言学上的爱国主义。对德语的捍卫自17世纪早期以来就被马丁奥皮茨坚定地承担起来,自那之后,它已经构成了神学家、学者和哲学家有意识的计划的一个部分了。门克、霍内克、莫舍罗施、洛高,以及格吕菲乌斯的名字对于今天的英国读者来说也许没有太多含义;但是在宗教改革之后的两个世纪,他们坚定并成功地在路德的旗帜下开展了反对拉丁语与法语的斗争;一些更为著名的人士,如普芬多夫和莱布尼茨、哈曼和莱辛,也参加了这场很久以前就开始的运动。赫尔德开始于在那个时代已经作为一种传统的德意志态度确立下来的东西。
还有著名的价值转向,即具体对抽象的胜利,向直接、给定、经验的东西的转向,尤其是远离抽象、理论、概括和程式化的模式;质先前高于量的地位,以及直接的感觉材料高于对物理原始性质的地位都得到了恢复,而正是在这项事业中,哈曼得以成名。这种价值转向构成了拉瓦特尔的“面相学”研究的基础;它至少与沙夫茨伯里一样古老;它与年轻的伯克的著作也密切相关。
在赫尔德登上舞台时,人们反对通过对理性主义和科学原则的应用重组知识和社会的活动正值高峰。卢梭在1750年用他的《论科学与艺术》点燃了这把火。七年后,他致达朗贝尔的那封反动的书信谴责了这个阶段,标志着与法国启蒙哲学家决裂,而这一点双方都立刻注意到了。在德国,这种情绪被牧师运动的内省传统有力地强化了。在这些小的群体中,人们的团结和相互尊重被他们炽热的新教信仰激发起来了;他们对朴素的真理、对善的力量、对内在之光的信仰;他们对外在形式的蔑视;他们对责任和纪律的坚定不移;他们永无休止的自我检讨;他们对恶的存在的狂迷(有时采取歇斯底里的或虐待狂的形式,并产生了大量虚情假意的伪善);尤其是他们对精神生活的全神贯注(只有它能够把人们从血肉和自然的纽带中解放出来)所有这些品性在这种严酷的氛围中长大的人们的身上都是非常强烈的,尤其见于东普鲁士人、克努岑、哈曼、赫尔德、康德那里。尽管一条巨大的理智上的鸿沟把康德和赫尔德分开了,然而他们也共享着一个元素:追求精神的自主性,反对迷迷糊糊地跟着未经批判的教条(不管是神学的还是科学的)随波逐流,追求道德的独立性(不管是个人的还是群体的),尤其是道德的救赎。
如果赫尔德所做的仅仅是从这些态度和信条中完成了一种综合,并且利用它们建构了一种(即便不是某种体系)连贯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注定会对他的国家的文学和思想产生决定性影响,那么仅此就足以为他在文明史中赢得一个独一无二的位置。发明不是一切。如果要一个人在洛克或卢梭、边沁或马克思、阿奎那甚或黑格尔的学说中寻找严格意义上属于他们自己独创性的内容,那么用不着费多大劲,他就可以把他们的所有学说都追溯到早先的“源头”。然而这无损这些思想家的原创性和天才。“拿破仑金币等额的零钱不等于一枚拿破仑金币。”然而,从整体上评价赫尔德并非我的目的,我只是要考虑他所创造的某种独树一帜的学说;讨论它们不仅是出于历史的公正,而且也是因为它们是些与我们这个时代特别相关和富有兴味的观点。如果我是对的,那么赫尔德的最终地位不必依赖于他思想中最独创的东西。因为他的巨大影响有时反而导致遮蔽了他真正投射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