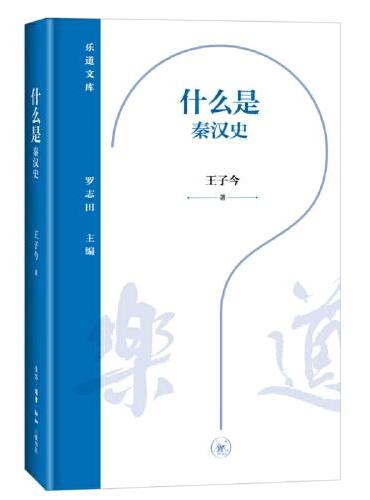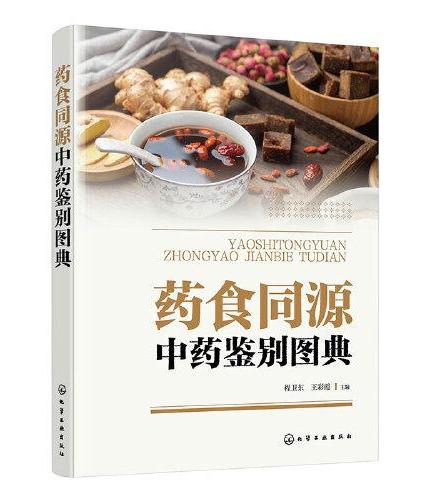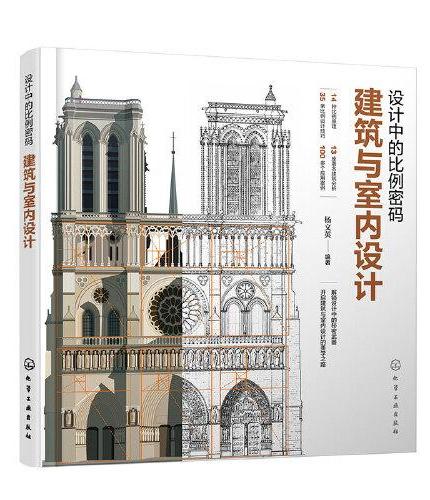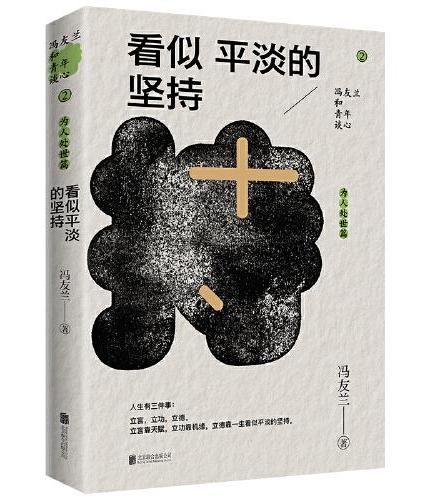新書推薦:

《
读书是一辈子的事(2024年新版)
》
售價:HK$
7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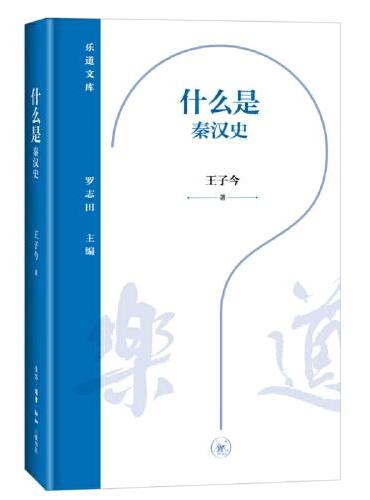
《
乐道文库·什么是秦汉史
》
售價:HK$
80.6

《
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 : 自由、政治与人性
》
售價:HK$
109.8

《
女性与疯狂(女性主义里程碑式著作,全球售出300万册)
》
售價:HK$
1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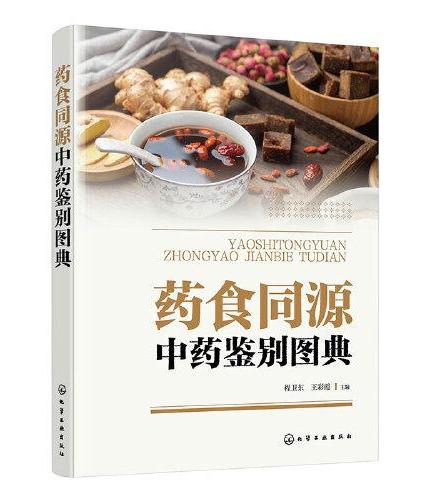
《
药食同源中药鉴别图典
》
售價:HK$
6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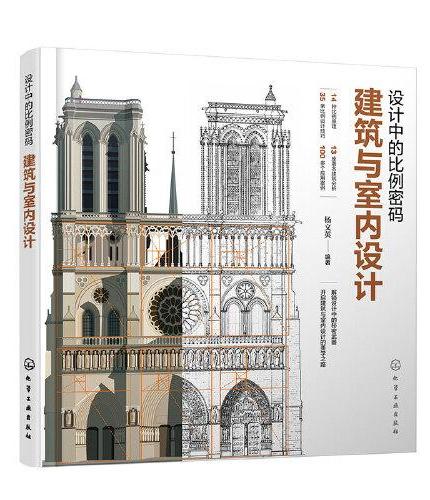
《
设计中的比例密码:建筑与室内设计
》
售價:HK$
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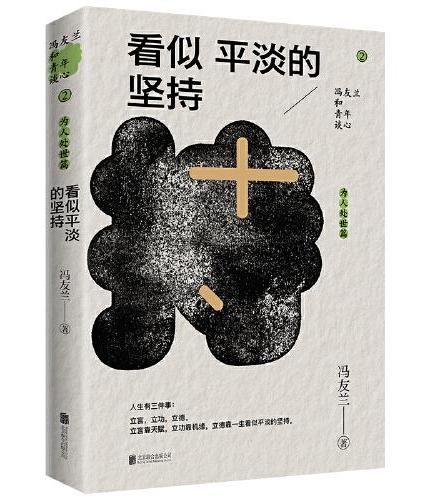
《
冯友兰和青年谈心系列:看似平淡的坚持
》
售價:HK$
55.8

《
汉字理论与汉字阐释概要 《说解汉字一百五十讲》作者李守奎新作
》
售價:HK$
76.2
|
| 編輯推薦: |
"★史诗再现滇西惠通桥遭遇战,现场还原中国远征军英雄壮举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致敬作品
★叙写大时代的国仇家恨,勾描小人物的悲欢离合
★谍战喋血 家仇国恨永生铭记
赴死重生 浴血军魂光耀千秋
"
|
| 內容簡介: |
" 本书取材于历史上著名的滇西惠通桥遭遇战。在切断了中国接受国际援助的唯一通道后,日军于1942年5月2日从畹町进入中国境内,沿滇缅公路快速往昆明推进,直逼怒江上唯一的大桥——惠通桥。此桥一过,昆明无险可守,重庆岌岌可危。
远征军工兵总指挥马崇六将军所部在畹町失守后且战且退撤往昆明,5月5日经过惠通桥时,留下一队工兵负责炸毁惠通桥,将日军挡在怒江西岸。
夹杂在潮水般涌过的华侨、难民和远征军散兵中,工兵马长友和他的队友们开始在惠通桥上安装炸药。马长友和他的战友们却不知道,紧咬着马崇六将军一路追来的日军已经派出了数倍于他们的精锐先遣队化装成难民混入其中,企图抢先一步占领惠通桥。
敌暗我明,实力悬殊,一场恶战在所难免……
"
|
| 關於作者: |
"何晓
女,常用笔名赵晓霜,回族,四川阆中人,现居北京,任《军嫂》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出版有《迷徒》《佛心》《路在手下延伸》《等一个人》等长篇小说及短篇小说集。曾获第三届四川省少数民族优秀作品奖、第四届全国微型小说年度一等奖。有作品入选《新中国60年文学大系》《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并收入全国多省市高考模拟试卷、高考试卷阅读题。"
|
| 目錄:
|
楔子
第一章 亲人
第二章 兄弟
第三章 情报
第四章 遗物
第五章 参军
第六章 阴谋
第七章 误会
第八章 插手
第九章 离家
第十章 浮桥
第十一章 允婚
第十二章 收买
第十三章 隐情
第十四章 暗斗
第十五章 绝路
第十六章 迎战
第十七章 身世
第十八章 炸桥
|
| 內容試閱:
|
"
楔子
“急,贵阳。薛副主任伯陵弟:霆密。下月初旬,滇省抗日部队决定出发,由黔入湘。所经公路及沿途粮秣,盼吾弟先事注意……兄龙云。灰。秘。印。”
这封密电发出去后的第二天,也就是1937年9月11日,一夜未曾合眼的二级上将、云南省主席龙云不等对方回电,再次督促省府秘书处给驻兵贵阳的薛岳将军发出真酉密电:“滇出省部队三个步兵师十二团,约二万人,经黔入湘,沿途所需粮秣,应请费神先予饬属代为准备,所经各地不得抬高市价。部队中稍携富滇纸币,并请转饬照价通行,兄当饬银行负责收回不误。”
这封电报发出去后,龙云心里才稍微踏实了一些,转身问刚从训练场赶来的卢汉:“举行阅兵式的具体时间,通知地方了吗?”
卢汉抹着汗答道:“已经通知了,就在10月5日。地方各界早就在准备盛大的欢送仪式了。”
“10月5日……那就快到重阳起义纪念日了吧?”龙云问着,走到窗前眺望五华山下的昆明城。
“是。今年的重阳节在10月12日。”卢汉站在原地,望着龙云说。
“你们要在去贵阳的路上过节了,好在昆明到贵州盘县的公路已经在3月通车……”龙云沉吟了半晌,突然接着公路通车的话题,对这位即将带兵出滇抗击日寇的60军军长说,“自民国十七年以来,我大多数时间所顾虑的,不外乎治安、金融财政、云南建设三个方面的问题。现在前面两个已经不是大问题了,唯有云南的建设,在这个时候越发显得重要了。这些建设,重中之重是交通建设。我们现在只有一条滇越铁路和几条联不成网的简易公路,姑且不说云南的长远发展,单就目前国内的战局而言,就不堪设想啊!”
“您这是想起委员长的那句话了吧?”做了四十多年的兄弟,卢汉深知龙云的心思,笑道,“‘我们本部十八省哪怕丢了十五省,只要川滇黔三省能够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的强敌,恢复一切的失地,复兴国家,完成革命。’这是委员长两年前在峨眉山上说的原话。”
“巩固无恙!真的到了委员长说的那一天,作为中国千百年来连接东南亚各国的重要陆路通道,云南的作用恐怕是我们谁都难以预料的。”龙云转身对卢汉说。
阳光从龙云的背后射进来,使他的整个面庞都处于阴影中,让卢汉看不清他的表情。然而,毕竟多年来一直跟随在龙云身边,卢汉很清楚,治安也罢、金融财政也罢,其实都是龙云不惜一切代价、不放过一切机会建设云南的手段。而且,同为军人,他更理解龙云此刻的忧虑和难处。因此,他试探着问:“上个月您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不是已经向军事委员会提出了建设滇缅公路和滇缅铁路的计划吗?委员长的意思……”
龙云打断卢汉的话,对他说:“对于我的这个建议,中央还是非常赞成的。委员长和所有人一样清楚,我们不可能完全孤立地打赢这场战争。目前除了沿海,与外埠相通的唯有西北一线和云南。8月20日,日本海军省已经宣布封锁中国沿海。出海口一被切断,抗日所需各种物资运输必然受损。这种情况下,把所有希望都放在西北一线,显然是不明智的。所以,我向中央建议,国际交通应预做准备,即可着手修筑滇缅铁路和滇缅公路直通印度洋……”龙云说到这里,迟疑了一下,又说:“不过,委员长依然认为建设滇缅铁路的条件目前还不成熟,当务之急,是立刻着手在滇西省道的基础上,赶修滇缅公路,接通缅甸腊戌。而且,按照我的提议,这条公路由云南负责,中央补助。”
“工期如何?”其实,无论是修铁路还是修公路,在云南,早都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了,龙云也不止一次和大家商讨过,但真的要动工了,卢汉还是替龙云捏了一把汗,“战事瞬息万变,60军的3个师出滇之后,紧跟着会不断补充兵员、组建后续部队。精壮男丁都上了前线,家里剩的多是老人和妇孺,修建滇缅公路之难,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我已经计划好了,准备派人去缅甸与英国人洽谈相关事宜。至于工期嘛,当然是越快越好。永衡,你放心地带60军出征吧。不管是给你们配备目前国内最精良的武器装备,还是争取早日修通滇缅公路,我们所要做的,其实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尽云南地方的所有人力财力贡献国家,以救危亡。”
龙云的声音不大,音调也很平和,但在这初秋的清晨,却如同大古楼上的鼓声,在天地间激荡,撞击着卢汉的心、撞击着所有人的心。
“以牺牲的决心,做破釜沉舟的抗战!”
卢汉迎着阳光走近龙云,两人相对侧身站在窗口,听着远处传来的口号声,把目光投向光复楼外乱云翻滚的辽阔天空……
第一章 亲人
1.茶姑的袖弩
也不知道是因为多数精壮男儿都出滇打仗,还是因为在家的人都把力气耗在了滇缅公路上,1938年的秋天,从昆明到大理、保山,再到龙陵,一路上都让人觉得异常地萧条和寒冷。
此时,来自昆明的辅元堂周家老少掌柜父子两人,正跟在一个名叫茶桂的冷面年轻人后面,沿着一条窄窄的山路,走进茶马山寨的内八卦密林;他们的药材、马帮和其他随行人员,则被留在了外八卦的木楼上。
茶桂一声不吭,只是在前面疾走,麻草鞋踩在落叶上“沙沙”地响;腰刀碰到路边的树枝上“咔咔”地响。周家父子在后面,一溜小跑才勉强跟得上。还好,虽然林子看起来又密又深,但茶桂路熟,左拐右拐,很快就走出密林,进了一片开阔地。周家少爷周弥生和山寨的少爷茶朴是大学同学,以前听茶朴说起山寨的内外八卦密林时,他一直以为内八卦的中心是山顶。可真的站在内八卦中心了,他才发现,这里并不是山顶,而是山腰的一大片平台:平台靠山的一边是木楼,临崖的一边竖着一根木杆,木杆顶上吊着一截粗短的木桩,木杆下面有一个枯塘一般的巨大凹槽。
比起外八卦密林合围着的那一大片木楼,这里数得过来的几座木楼虽然紧凑、高大、精致得多,但看起来却依然只是单纯的木楼,根本没有一点儿衙门的样子,实在没法和其他地方的土司府相比,更丝毫不能让人想到,就是在这样一个地方,几百年前的老土司曾经因为帮助朝廷平叛有功,得到过后人至今仍不知到底有多少的赏赐;也同样是这个地方,二十多年前的老土司因为先开垦水田、后争取进入了民国政府特许的鸦片种植地区,获得了让其他土司眼红的收成。尽管如此,按茶朴的话说,山寨几十年来做过的唯一奢侈的事情,就是送他去昆明读中学、去上海读大学;而最大的支出,就是修滇缅公路……
想到茶朴,周弥生有些奇怪:茶朴牺牲不过才几个月的时间,这里的人怎么就没有一点儿伤心的样子呢?看上去,竟好像没有这回事儿一样—他们已经忘记了这个老土司唯一的儿子吗?他们已经忘记了茶朴曾经答应毕业后要回来办学校吗?
周弥生正胡思乱想着,猛然听见有人在头顶喊:“贵客驾临,有失远迎!”他抬起头,看见几位老人并排站在不远处的木楼上,正举着竹烟筒微笑着跟他们打招呼。被簇拥在中间的那位,中等身材、凸出的额头、大而明亮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周弥生一下子就认出来,那是茶朴的爹爹,而且在心里认定了:茶朴要是活着,再过三四十年,一定也是这个样子!
周弥生的父亲周鉴塘拱手答应着,朝楼上走去。看样子,他和楼上的各位都很熟悉。临上楼梯,就着抓扶手的机会,周鉴塘回头看了一眼周弥生,轻轻咳嗽了一声。
周弥生明白父亲在提醒自己不要东张西望,忙收回眼神儿,跟着父亲往上走。走了几步,他听见身后有脚步声跟上来。不用回头看,他也知道是茶桂。对于这个茶马山寨的第一勇士,周弥生并不陌生:几年前茶朴和周弥生一起离开昆明的时候,茶朴的行李就是他送来的。当时,茶朴便对周弥生说,这是他的堂兄,当年,就因为他,当然主要是因为他的母亲,茶朴的伯父丢掉了继任土司的机会,最后甚至丢掉了性命。
这一路走来,他已经熟悉茶桂重重的脚步声了。上了楼,要转身进屋时,周弥生果然看见茶桂背对着他们站在楼梯口,却没有跟进来。
虽然周弥生和茶朴是多年的同学,可茶土司和周鉴塘却还是在去年年底修建滇缅公路时才认识的。
滇缅公路刚开工不久,公路沿线的民工中就开始流行瘟病,云南各地的药房、医馆、医院都响应龙主席的号令,拿出了看家本领来工地上各包一段、分段义诊。当时,周鉴塘对应的,正是茶土司这一段。山寨里的人对付寻常的刀伤、摔伤倒是没有问题,可遇到瘟病却是一点儿办法都没有。眼看着人一个个倒下,出力气修路的人越来越少,工期催得又紧,茶土司一着急,自己也病了。还好,因为辅元堂的药丸对症,茶土司这一段发病虽然最早、生病的人也最多,但病好得却最快,所以也最先复工,好歹算是在龙主席规定的日子里,把那段路给修好了,没有披枷带锁地被关进昆明的大牢里。
不过,茶土司和周鉴塘能成为好朋友的根本原因,并不在医治瘟病这件事情上,而是因为两家孩子是同学,而且是大学同学。就算是昆明借着滇越铁路这条大动脉,有了一些逼近香港的气势,但昆明毕竟还是昆明,能把孩子送出去读洋学堂的人并不很多,这不仅仅是因为钱,还因为两个字—“见识”。所以,在治愈瘟病之后,周鉴塘和茶土司还能继续往来,甚至每隔一段时间,周鉴塘都会给茶土司捎带一批自家特制的“辅元丸”,直到滇缅路修通,依然隔一段时间就给山寨送一次药,以备茶土司不时之需。
周鉴塘这一次来,表面上也是因为这个原因,但他内心的真正愿望,却是想把儿子引荐给茶土司:一来,周弥生和茶朴有同学之谊,茶朴牺牲了,他理应来拜望茶朴的家人;二来,自己老了,以后这条线会逐渐交给周弥生,送药的事情,自然也要他来办了。人与人之间的很多事情,其实就是隔着一层纸,但这层纸却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捅得破的,学医的人尤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至于以后周弥生和茶姑、辅元堂和山寨之间如何发展,就不是他们所能决定的了,周鉴塘更不想生硬地去为孩子们、为辅元堂的未来做任何不必要的打算。
被茶土司迎到火塘边,一行人说着客套话,分宾主坐下。周弥生刚把装着药丸的包裹双手呈给茶土司,突然听见外面传来“嗵”的一声巨响。随即,他就看见茶土司把包裹放在旁边的桌子上,和几位老人一起全都站了起来,急急忙忙地往外走去。
周弥生猜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情,见周鉴塘也是一脸的茫然,忙将父亲搀扶起来,也随着几位老人往门口走去。好在他虽然瘦,个子却比较高,还没出门,就知道了声音是从临崖的木杆那里传来的。因为他一眼就透过窗户看见:木杆上面横着的木桩掉了下来,正好砸在了地面专门接它的凹槽里。这时候他才明白那木杆上的木桩和地下凹槽的妙处。
“茶桂,哪里来的箭?”茶土司边往外走边吆喝。
“是茶姑的袖弩。”一直站在楼梯口的茶桂此时已经一溜小跑赶到凹槽边了,正仰着头看木杆上的箭,一听土司开口,马上回答。那小小的袖箭射断了栓木桩的绳子,箭头射进了木杆里,若不是箭头系了红色的丝线,任你看得多仔细,也看不出来。
“走,下去看看。”
老土司说着话,“噌噌噌”地快步下楼,朝密林走去。茶桂箭一样跑回来,走在老土司前面,为他开路。
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大家都屏着呼吸跟在老土司的后面,急匆匆地往山下走。
周弥生比走在他前面的所有人至少都高出半头,所以,一出密林,他就看见自昆明出来就始终跟着他们的日本民俗专家山口岩,被绑在对面木楼前的拴马桩上,拴马桩的左右两边各站着几个山寨的小伙子。这些小伙子腰里都有刀,但手里依然握着又粗又长的棍棒,有的还端着土枪;而他们周家的老家人阿忠,则站在茶姑面前,正不停地点头哈腰,解释着什么。
“茶姑,不要对客人无礼!”还隔着老远,茶土司就举起手臂高声呵斥他的小女儿。
“爹,他不是客人。”茶姑转过身,面对父亲和父亲身后的人,一字一顿地说,“他是日本鬼子!”
茶姑的话音一落,整个山寨一下子像被谁施了魔法,所有的人都被定在了原地。刚才还一路慨叹山寨为什么如此平和宁静的周弥生,真切地看见山寨里所有人眼里闪着的火苗,正在聚成火海,他还真切地听见拳头捏紧时发出的“咯咯”声,正响成雷鸣……
2.傻子也晓得他是日本人
“姑爷、小少爷,对不起、对不起,都怪我没把木六看住。”阿忠看到周鉴塘和周弥生来了,一边低声表示着歉意,一边退了下去,和马帮里那个叫木六的伙计站在一起。
阿忠本名田定忠,是周弥生的妈妈从娘家带过来的老家人,同辈的人都叫他阿忠,晚辈们都叫他忠叔;而又瘦又矮的木六此刻却噘着嘴站在旁边,一脸无辜的样子。
周弥生看了父亲一眼,见周鉴塘没有要说话的意思,便站出来,走到阿忠面前,问道:“忠叔,这是出什么事儿了?”
“小少爷,你和姑爷去了内八卦后,我们在外八卦的木楼上喝酒。喝了一会儿,我不放心,就下楼来看我们的药材,正听到茶姑在跟木六说话,问这次一起来的山口先生叫什么名字、是做哪样的……”
阿忠说到这儿,把头转向木六。木六也就只有十六七岁的样子,又瘦又矮,一副还没有开始发育的样子。见阿忠和周弥生都看着自己,他硬着脖子仰起脸说:“名字嘛,就是被人喊的,哪能不让人知道?她问我,我就告诉她了。她又问,那人的名字怎么这么怪啊?我就说,日本人的名字嘛,哪能不怪?她一听,就像爆竹一样,炸了,火冒三丈地叫山寨的人绑了这个日本人,说是要砍了他的头给她哥报仇。”
“你怎么知道山口先生是日本人呢?”阿忠盯着木六问。
“我一路上听他们说的。”木六回头看看身后的伙伴,嘀咕道,“我们这里哪里有人叫这样怪的名字?傻子也晓得他是日本人。”
父亲担心的事情果然还是发生了!
周弥生暗想着,看了看父亲,又看了看茶土司,见他们都暂时没有想要说话的意思,便走到茶姑面前,轻声对她说:“茶朴牺牲在战场上,是被战场上的日本鬼子杀害的。但是,山口先生和那些战场上的日本鬼子不一样。他是学者,是个民俗专家,他也敬佩茶朴、憎恨那些侵略我们国家的……”
“弥生哥,你不要再说了!这个时候,你说什么都没有用。哼!你说他是学者?学者嘛,就该像我哥那样,包包里装的都是书,可他身上为什么有这些东西?”茶姑说着,把手里拎着的一堆东西高高地举了起来。
那是一台照相机和一支手枪。
山口岩随身带着相机,这事儿周鉴塘、周弥生、阿忠还有马帮的人都知道;可他居然还带着枪,大家却真的不知道。所以,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跟茶姑解释。
“刚才弥生已经告诉过你了,我是民俗专家。民俗专家嘛,研究的就是民俗,经常要穿过那些人烟稀少、野兽出没的地方,经常要去偏远的山寨。相机是用来拍照的、枪是用来防身的。不信你们问问周老板,我和他认识二十多年,什么时候用枪伤过人?”一直没有开口的山口岩知道自己不能再沉默了,故作轻松地说,“小姑娘,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好人和坏人,就像你们中国不一定全是好人,我们日本也不全是坏人……”
“呸!哪个听你胡说八道,臭日本鬼子!你就是害死我哥的凶手,所有日本人都是害死我哥的凶手!”茶姑丝毫听不进山口岩的解释,不等山口岩把大道理讲完,就骂着打断了他。骂完了,茶姑还不解气,对旁边拿着棍棒的随从喊道,“你们还直愣愣地站着做什么?打啊!打死这个臭日本鬼子!”
“慢着!”就在那几个随从准备动手的时候,茶土司大喝一声。随从们一听,立即收了棍棒,围着山口岩站住。
“爹,你为哪样不要他们打?你晓不晓得,这是日本鬼子,是害死我哥的日本鬼子!”一副任性模样的茶姑冲到父亲面前,跺着脚,尖声喊叫。
茶土司没有理会暴怒的茶姑。他转过身,脸色阴沉地面对周鉴塘,嗓音有些沙哑地说:“周老板,我一向敬重你的为人。我也明白,这个人虽然是日本人,但未必就是害死我儿子的日本人。不过,也请你理解我,老来丧子,有些弯弯是绕不过去的。你今天带来的礼物我已经收下了,请你们回去吧。下次走滇缅公路、从茶马山寨经过,欢迎你再来,只是……不要带任何日本人来了。这样的客人,我们茶马山寨招待不起!”
周弥生听得很仔细,和刚才那一声洪亮的“贵客驾临,有失远迎”相比,茶土司这几句话显得格外低沉、无力。
茶土司显然注意到了周弥生的神色,说到这儿,他把头转向周弥生这边,从茶姑手里拿过枪和相机,信手扔到了山口岩面前。周弥生以为茶土司突然面向自己,必然有话要对自己说,却不想,茶土司根本没有搭理他的意思,眼睛明明看着他,说出来的话却是:“茶桂,这里的事情,你处理吧。茶姑,你跟我回去。”
话音一落,茶土司带着几位老人进了内八卦的密林,把傻呆呆的周弥生、一句话都没有说的周鉴塘撂在了身后。
茶姑瞪了周弥生一眼,不甘心地跺跺脚,跟了上去。
茶桂的脸上一直没有表情。等茶土司他们的背影消失之后,他才慢慢地往山口岩那边走。
茶桂从周弥生面前经过的时候,周弥生看见茶桂抓着腰刀的手还在发抖,而且,他的腰刀已经抽出了一半。
茶桂的脚步越来越快。
眼见茶桂大步走近山口岩,“唰”地抽出刀来,周弥生不由自主地一个箭步冲了过去:“请不要杀他!”
但周弥生还是慢了半步—等他把手伸出去打算推开茶桂的时候,茶桂的刀已经落下去了。
周弥生只觉得眼前一道白光闪过……
“牵上你们的马,带上你们的药材,走吧。”茶桂冷冰冰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周弥生这时才回过神儿去看刚才捆绑山口岩的柱子:柱子旁边零散地落了一地断成了一小节、一小节的绳子,绳子的两头全是齐刷刷的,可见,茶桂的刀该有多快。
矮矮胖胖的山口岩,此时正利索地从地上爬起来,好像并没有受到什么惊吓,弹了弹身上的土,甚至还转过身去,朝茶桂微微地躬了躬身子,这才慢悠悠地走进了马帮的队列里。
周弥生暗暗佩服山口岩的定力。同时他还听到,在几步之外,父亲周鉴塘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3.惠通桥上的枪声
马帮出了茶马山寨之后,一行人似乎觉得山路后面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他们,所以,全都一声不吭,只是埋头往前走。终于走完了山路,上了滇缅公路,大家这才松了口气。
周弥生原本和木六一起走在最后面,此时,他跑过其他人,来到周鉴塘和山口岩的身边,有些不好意思地对山口岩说:“山口叔叔,茶姑他们太冲动了。我真没想到,这次您跟我们出来,莫名其妙地替人背了仇恨。”
山口岩正要接话,周鉴塘却阴沉着脸,看着前面的路说:“一场误会,你们也不要想得太多。只是茶马山寨的人都是性情中人,耿直得很,一向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恐怕以后山口教授再从这一带经过时,要多加小心才好—当然,不仅仅是这一带,云南出滇抗日、没能回来的将士很多啊。换了我,要是弥生去打仗,有个三长两短,我也会恨你、也会恨所有日本人的。就算我们认识二十多年,有交情,我也一样会恨你。亲手把你的头砍下来的事情,我也许做不出来,但绝交却是一定的。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杀戮,被欺凌的人会把个人的仇恨记在整个敌对民族的头上,尤其是那些耿直的乡野之人,这种仇视会表现得更直率,而且不加掩饰。山口教授,你研究民俗,应该很了解这些山民的。如果你这样想的话,茶土司今天对我们已经算是很客气了。”
自从听山口岩对茶马山寨的人说“不信你们问问周老板,我和他认识二十多年,什么时候用枪伤过人”,周鉴塘心里就开始犯嘀咕了:他的确是二十多年前认识的山口岩,但也就只相处了不到一年时间,山口岩父子俩在周家养好伤后,便离开了昆明。今年春天,这父子俩突然又出现在自己面前,两家人不过是二十多年来的第二次见面罢了。虽说这期间也有些不足为外人道的渊源,可他们哪里谈得上有什么深交?至于山口岩是否用枪伤过人,他根本不可能知道,怎么能出面作证?更何况,这一次,他原本就没打算带山口岩来茶马山寨,可一路上,从昆明到畹町,再到回来的路上,山口岩都不请自来,一步不落地跟着自己的马帮,总不至于到了山寨外面把他扔下吧?原打算去茶马山寨见见茶土司,给山寨送了药,跟茶土司叙叙旧,就继续赶路的,谁知道,因为山口岩这个日本人,差点儿毁了他和茶土司的交情……周鉴塘越想觉得今天这事儿有些不对,可到底是哪儿不对,他一时半会儿又想不明白。
山口岩听出了周鉴塘的话外之音,有些委屈地替自己辩解:“是的,我记得中国有句老话,‘神仙打仗,百姓遭殃’,打仗这样的事情,我们小老百姓怎么弄得明白?我不过是想安心做学问,你不过是想踏实做生意,茶土司不过是想太太平平地过日子,本来一团和气,互不相扰,可到头来,却因为两国的军人打仗,搞得我们彼此之间像仇人一样。”
“对了,山口教授,你今年春天怎么突然又来昆明了呢?二十多年前你走了以后,我还担心我们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了。”周鉴塘毕竟也是经历过家国不幸的人,很多与自己和家人无关的事儿,他都尽量不放在心上;况且,像昆明这种早几十年就有火车、汽车通几个国家的地方,每天因为各种原因来来往往的人太多了,客人来了就把新茶泡上,客人走了就把剩茶倒掉,这是人之常情。但现在,因为茶姑这一闹,他真觉得自己有必要问个明白了。
山口岩听到周鉴塘问他这样的话,自然明白是什么意思,于是,便把以前零零散散给周鉴塘说过的相关的话,再次详细地说了一遍:“年初,几个国家的相关机构联合成立了一个关于古老民俗研究的课题组,我有幸被邀参加。分配给我的研究课题是傩戏。‘云披红日恰衔山,列炬参差竞往还。万朵莲花开海市,一天星斗下凡间。只疑灯火烧元夜,谁料乡傩到百蛮。此日吾皇调玉烛,更于何处觅神奸。’这首诗是贵国元代一位云南官员写的,可见,那时候云南民间就有傩戏了。”山口岩说起自己的专业,口若悬河,而且充满信心,“以我多年对贵国古老民俗的了解和对各类相关史料的勘察,云南的傩戏类型众多、源远流长,极具研究价值。所以,这次我专门带了学生过来,打算把这个课题做深、做透,争取拿出几篇有较大影响的论文来。”
“这一点,你和二十多年前还真是没什么变化。”周鉴塘想起往事,长叹一声。
“哪一点?”山口岩饶有兴趣地问。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啊。”周鉴塘依然面无表情地说。
山口岩干笑两声,不再接话。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