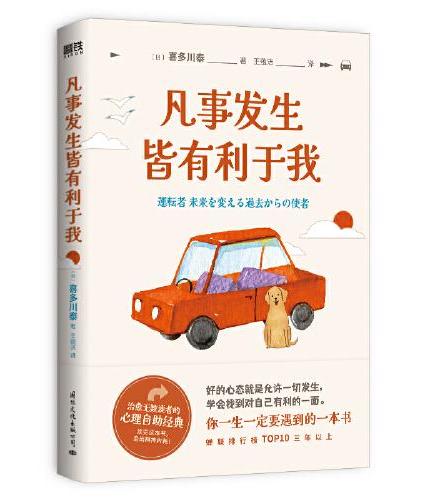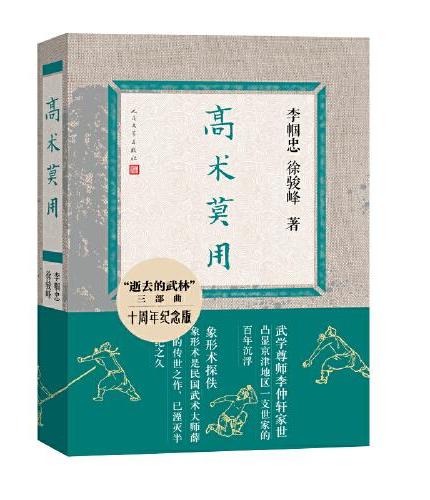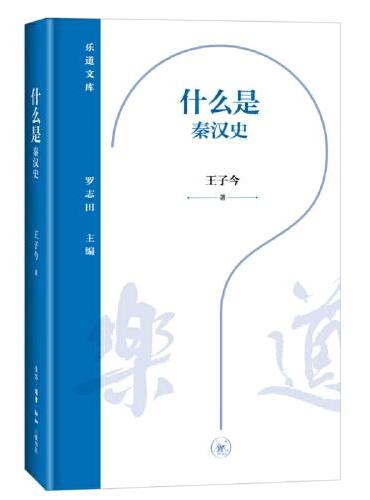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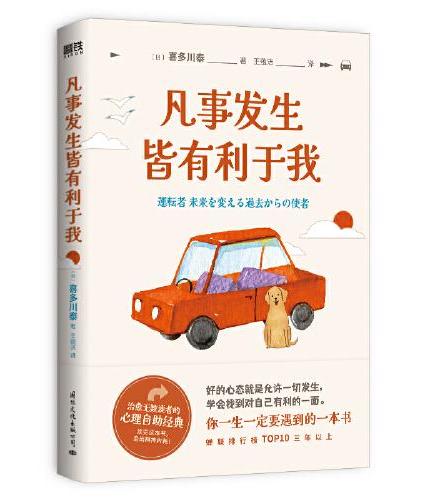
《
凡事发生皆有利于我(这是一本读了之后会让人运气变好的书”治愈无数读者的心理自助经典)
》
售價:HK$
44.6

《
未来特工局
》
售價:HK$
5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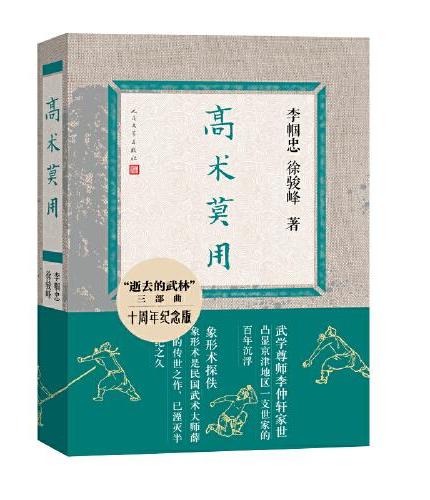
《
高术莫用(十周年纪念版 逝去的武林续篇 薛颠传世之作 武学尊师李仲轩家世 凸显京津地区一支世家的百年沉浮)
》
售價:HK$
54.9

《
英国简史(刘金源教授作品)
》
售價:HK$
98.6

《
便宜货:廉价商品与美国消费社会的形成
》
售價:HK$
77.3

《
读书是一辈子的事(2024年新版)
》
售價:HK$
7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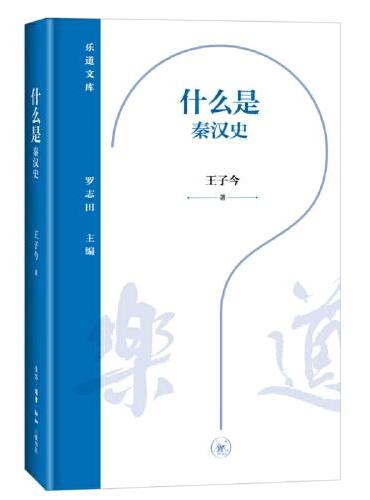
《
乐道文库·什么是秦汉史
》
售價:HK$
80.6

《
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 : 自由、政治与人性
》
售價:HK$
109.8
|
| 內容簡介: |
吴绫蜀锦,绮年玉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幼失所恃,兄弟阋墙,父子相忌,君臣倒戈。
权力之下,何枝可依?离恨之间,何情可托?
遇上你,并非我之所愿。
既已遇上,就请你点一盏灯来,为我照亮这丛锦绣地狱。
到那时,也许我可以同你,在暮春时节,携手登上南山。
去看杂花生树,去看群莺乱飞。
去听那鹤唳的声音,看它们蹈碎琉璃般的水面,振翅飞入青天。
|
| 關於作者: |
雪满梁园
书生一枚。嗜历史、文学、考古、艺术。认真工作,懒散做人。严谨治学,粗心齐家。爱好广,心得无。良心多,勇气寡。普罗大众,芸芸众生。牢记旧日校歌,想做文章气节少年人。
五年埋首只一部《鹤唳华亭》,但一部已成经典。
|
| 目錄:
|
目录
第一章
靡不有初 001
第二章
念吾一身 006
第三章
岁暮阴阳 012
第四章
孽子坠心 020
第五章
已向季春 025
第六章
惨绿少年 031
第七章
金瓯流光 039
第八章
所剩沾衣 045
第九章
白璧瑕瓋 051
第十章
桃李不言 059
第十一章
白龙鱼服 065
第十二章
胡为不归 073
第十三章
微君之故 079
第十四章
逆风执炬 085
第十五章
千峰翠色 091
第十六章
碧碗敲冰 097
第十七章
将军白发 103
第十八章
悲风汨起 109
第十九章
铉铁既融 120
第二十章
绳直规圆 127
第二十一章
天泪人泪 134
第二十二章
棠棣之华 141
第二十三章
孤臣危泣 146
第二十四章
舍内青州 153
第二十五章
父子君臣 163
第二十六章
草满囹圄 170
第二十七章
不谢不怨 177
第二十八章
恩斯勤斯 184
第二十九章
歧路之哭 192
第三十章
日边清梦 197
第三十一章
莫问当年 205
第三十二章
大都耦国 214
第三十三章
我朱孔阳 222
第三十四章
锦瑟华年 230
第三十五章
十年树木 238
第三十六章
百岁有涯 246
第三十七章
露惊罗纨 254
第三十八章
薄暮心动 264
目录 下册
第三十九章
一树江头 001
第四十章
风雨鸡鸣 009
第四十一章
丹青之信 015
第四十二章
万寿无疆 020
第四十三章
雪满梁园 027
第四十四章
玉燕投怀 032
第四十五章
急景凋年 039
第四十六章
三边曙色 046
第四十七章
襄公之仁 052
第四十八章
终朝采绿 057
第四十九章
树犹如此 063
第五十章
谢堂燕子 070
第五十一章
夜雨对床 074
第五十二章
蓼蓼者莪 080
第五十三章
亢龙有悔 085
第五十四章
荆王无梦 091
第五十五章
竹报平安 095
第五十六章
岂曰无衣 101
第五十七章
言照相思 107
第五十八章
青冥风霜 113
第五十九章
西窗夜话 118
第六十章
茶墨俱香 124
第六十一章
纱笼中人 132
第六十二章
盛筵难再 138
第六十三章
铜山西崩 144
第六十四章
室迩人远 152
第六十五章
林无静树 157
第六十六章
婢学夫人 164
第六十七章
卑势卑身 172
第六十八章
觉有八征 179
第六十九章
拂帘坠茵 187
第七十章
金谷送客 195
第七十一章
青眼白云 203
第七十二章
梦断蓝桥 208
第七十三章
临江折轴 215
第七十四章
车相望 221
第七十五章
护摩智火 229
第七十六章
孰若别时 237
第七十七章
澧浦遗佩 243
第七十八章
鹤唳华亭 247
附录一 年表 251
附录二 章节名出处 254
|
| 內容試閱:
|
内文试读一:
那个眉目清秀的少女,捧着自己的手,抬头笑道:“我的心殿下摸得到,殿下的心事我却不敢去揣测。”可是他的心思,她却到底看得比谁都明白。
你究竟是什么人?缘何会来到我的身边?那金钿明灭的光彩,是你在笑还是我眼花?那颊畔起落的红云,是你有心还是我多情?你说给我听的那些话,到底是伪是实?你袖管中的那线暖意,究竟是幻是真?阿宝啊,脱去朝上的那身衣服,我其实也只是个凡人。棰楚加身,一样会让我感到疼痛;没有孤灯的暗夜,一样会让我感到害怕;满院残阳,一样会让我感到孤寂;觱发朔风,一样会让我感到寒冷。神佛并不眷爱于我,亦没有给我三目慧眼,能看穿这些喧扰世态,纷繁人心。就像此刻,我也一样会犹豫彷徨,因为我不知该拿你如何。
拖了这么久,这件事情也该有个了结了,最简单的那个办法其实他心中一直都清楚。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个道理,卢先生不知跟他讲过多少次。她当时其实是不该跟来的,宫墙外有高空长川,大漠瀚海,莺声鹤唳,雪满群山;这片他无缘亲近的壮丽江山,她本可以亲眼见到,如果那样,她不知道自己会有多么羡慕。
定权走到窗前,极目东望,从那里看不见延祚宫,从这里一样也看不见宗正寺,但是就在这宫墙的某个角落里,有一个人或许还在等候着他回去。定权慢慢捏紧了手中的符袋,食指突然跳跃着作痛,就像那指尖上也生了一颗心一般。
定权移开了视线,枕边小巧的翠叶金华胆瓶中,正斜斜插着一枝大红的松子山茶。他突然想起了张陆正的长子,去年四月的那场宫宴上,二十六岁的新科进士,幞头上簪着一朵大红色的芍药,带着少年意气的笑容,仰首饮尽了皇帝赐下的御酒。于他仰首举杯的那一瞬间,自己心内竟隐隐生出了些许妒忌。着青袍,骑白马,琼林赴宴,御苑簪花,夹道万姓欢呼,不是因为权势,而是真心叹服;楼头美人相招,不是为了缠头,而是为了年少风流。他那时断然不会想到,这锦绣前程会在一夜间化为风烟;独生妹妹,也会在一夜间粉面成土。都是这般的好年纪,都是因为自己。那位女公子的模样,想来跟眼前人也相差无多吧?只是不知道这笔罪过,到头来应该算到谁的头上。
定权从枕函中摸出那只符袋,交还给阿宝。阿宝略略一惊,将它托到手中,突然浑身颤抖,不可遏止。定权叹了口气道:“本来就是已经给了你的,如今还是给你。你只要好生当你的顾孺人,不要再搅和别的事情,本宫保你的平安。”
这一对少年夫妻,在锦绣世界中一卧一跪,相对无言。皆还是亭亭春柳一般的身躯,头发乌得发绿,肌肤就像新鲜的纸张。这本是鬼神都可饶恕的年纪,但是所谓情话,却只能说到这里。有些承诺,有些愿景,好比与子偕老,好比琴瑟在御,他们永远没有勇气,也没有福气说出口。
如是我闻,不可说,不可说。
内文试读二:
他将不住挣扎的阿宝轻轻放在了榻上,帮她脱了脚上的鞋,见她睁着一双凤目惊惧地看着自己,转身在榻边坐了下来,温声道:“你挪进去些,咱们好好说话。”阿宝迟疑片刻,终是动了动身子,给他移出了一席之地。定权提脚上榻,将双手枕在头下,侧首瞥见她背靠的那面描金山水的枕屏,信口开河,笑道:“江山美人,此刻叫我占全了—我还有什么不知足?”
她听着他说这样的傻话,眼神温柔而哀伤。但是她嘴角的笑容怪异,如讽刺,也如怜悯。她垂下了眼帘,这样看出去,满目全是星星点点的华彩。金色的是香炉,碧色的是茵褥,朱色的是帷幄,以渐入佳境的香气衬托,便是一场纸醉金迷的繁华好梦。她想起了很久以前,读过的那些诗句:“河中之水向东流,洛阳女儿名莫愁。十五嫁作卢家妇,十六生儿字阿侯。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苏合郁金香。头上金钗十二行,足下丝履五文章。”那时候,不过对着白纸黑字,如何能想见真正的兰室桂梁是个什么模样?又何从知道,自己十六岁的这一年,会在金阶白玉堂上,苏合郁金香中,陪伴这个卢家郎?那时的她,要何从得知,其实自己的卢家郎没有青春狂放,自怜碧玉亲教舞的福气;而她,也没有在一旁带着大度的笑容击节观赏,其实暗自拈酸吃醋的福气。她不知道丝履下踩的将是薄冰,头上的金钗有朝一日会与匕首无异。至于那个名叫阿侯的孩子,今生今世都成了梦中也不敢有的妄念。她想起了此刻还静静地躺在自己妆奁中的那包药粉,于是在他的眼中,她唇畔笑容中的怜悯加深,讽刺也加深。
如果人生,真可如诗文一样优美,一样凝炼,过滤掉一切妨碍优雅的杂质,那么诗中的她可以年华老去,她的卢家郎可以继续爱怜别的碧玉美人。她可寂寞,可怨恨,可指责他负情薄幸,将年少时在观月赏花、赌书泼茶时的誓言完全忘在脑后。但在前篇中,他们彼此一定都倾心相信那个誓言,他们可以两情缱绻,可以把此刻这样的春宵,看成真正的千金不换。
内文试读三:
待乘上舆轿,返回延祚宫,定权用过了早膳,忽而想起一事,转头吩咐身边宫人道:“你去看看顾娘子起来了吗,叫她到暖阁中来。”那宫人应声出去。片刻之后,阿宝便随她进了暖阁,见定权展手立于阁中,两宫人正在为他更衣,敛裾行礼道:“妾给殿下请安。”定权含笑点头,问道:“这几日还住得惯?你那边今日才拢炭盆,前两日夜里风大,可觉得冷了?”阿宝笑道:“不冷的。”定权摆了摆手,令两名宫人退出。阿宝笑着走上前,将他两手按了下来,嗔道:“只顾搭着好大的虚架子,不知道疼吗?”一面帮他穿好了夹袍。定权皱眉笑道:“你倒是轻些,若是方才那两个人手脚也是这样,我早就叫人拖下去打了,你如今真是……”阿宝扬首笑道:“真是怎么?”定权笑道:“真是恃宠生骄了,本宫得好好想想怎么再找个由头给你点颜色看看,否则连家都齐不了,日后怎么治国平天下?”
他是信口调笑的话语,阿宝的双颊却一瞬间红得旖旎,衬托得眉心双颊的翠色花钿越发明艳醒目。阁内原本一暖如春,定权略一恍惚,竟觉春花已绽,帘外便有燕声啾鸣,莺语呢喃,不由伸手摸了摸她的面颊,道:“万红丛中一点绿,动人春色不需多。”阿宝不语,代他围好了玉带,掉过头便走。定权好笑道:“站住!回来。”见她不为所动,只得自己走了两步上去,在她耳边低声问道:“就这两句话,你便听不得了,日后要怎么做夫妻?”他仍没有正经言语,阿宝头也不回,提脚刚要离去,便已经跌入了定权怀中。她慢慢抬起头来,见他眼角含笑,眉目舒展,与平素的模样全然不同,年少风流到了极致,竟无一语再可形容。一颗心突然怦然而动,声音竟大得吓人。她别的都顾不得了,只是害怕他也听见,连连挣扎了两下,浑身却都已经酸软了。定权低下头看她,她时常会脸红,那副模样不能说不是可怜可笑又可爱,只是此刻却不寻常到了极点,连双眼睑上都跟涂了一层胭脂一般。一双清澄眸子,也亮得如同两注春水,风过时被吹皱了,春阳投在那层波澜上,一闪一耀,跃动的竟全都是睦睦情意。这大约是做不了假的罢?他却忽然间愣住了,呆呆地放开了双手。
二人尴尬对立半晌,定权清了清嗓子道:“叫你过来,是想带你去个地方。”他转身便走,阿宝默默跟随。及出殿几个内侍忙迎了过来,定权摆手道:“我到后面走走,不用人跟着。”又吩咐一宫人道,“去给顾娘子取件大衣裳来,送到太子林那边去。”
阿宝面颊仍旧炽热,被殿外冷风一激,走出许久才逐渐冷却,这才开口问道:“太子林是什么地方?”虽已悄悄清了半日喉咙,此时话说出口,仍隐隐带着一线走音,又觉得脖颈上热得难堪,心中也不由暗暗懊悔。定权却似并未在意,笑道:“你看见就知道了。”
二人一前一后,一路走去,越过穿殿,到达延祚宫后殿最北的一片空地上。他处地面皆铺青石,唯独此处用白玉阑干围出一大片裸土,其中散植着六七株侧柏,最大的已经参天,小的不过十数年的树龄,一臂可环抱。时已隆冬,宫中他处的草木早已摇落殆尽,唯有此处,尚余一片黯淡绿色。定权从围栏开口处走入,伸手摸了摸那棵小树灰白色的树皮,向阿宝笑道:“这就是我种的。”
阿宝走上前,好奇地问道:“就是这里?”定权点头道:“不错。”阿宝仰头望望定权种的那株侧柏,修修直立,只觉它可爱非常,也伸出手去轻轻碰了碰。定权笑道:“你怕什么?又摸不坏的。”阿宝“嗯”了一声,到底不再动作。定权看着树木,向她讲解道:“本朝自太宗皇帝始,就有了个不成文的规矩。但凡在这延祚宫内住过的储君,一定要到这里来植一棵侧柏,宫里的人私底下就把这里叫作太子林。”见她面露疑色,又笑道,“你已经看出来了,是不是?”阿宝扳着指头算道:“若是不算太祖皇帝,加上今上,也应当只有四棵树。”定权点点头,向前走了两步,指着一株树干稍粗的树道:“这是文宗皇帝的太子,因失德被文庙废为庶人。”又指着其旁一株道,“这是我的大伯父恭怀太子,先帝的定显七年因病薨逝的。这棵和我那棵差不多大,是陛下的,他只比我早种了几年。”
阿宝轻声呼唤道:“殿下。”定权笑道:“历朝历代,太子都比皇帝要多,这是一定的事。只不知道我的那棵树,日后会不会也成了多余。”阿宝偏头看着阑干边那棵最小的侧柏,默默走到他身边,两手颤抖不止,迟疑半日,终于咬牙轻轻握住了他的右手。定权讶异地看了她一眼,却也并没有避开。两只手皆是冰冷的,只是此刻,却连对方手指上每一个微小的颤动都能够清楚觉察。
静默良久,定权终于开口道:“今天清早,我过去给陛下请安,陛下还是不肯见我。我站在晏安宫外头,又饿又冷,风刮得浑身生疼,手脚全都木了,还要听那些小人在暗中指指点点,忍不下去的时候,真是恨不得掉头就走。我心里明白,陛下是不会见我的,可是到了晚上,我还是要去。”阿宝没有说话,微微地攥紧了那只手。定权笑道:“他们想让我像这棵树一样,在角落里慢慢枯死,我是绝不会遂了他们的心愿的。阿宝,你不是想看白鹤吗?等到春天,天气暖和了,草也长出来了,咱们就到你说过的那座山上去。那时候站在山顶上,就可以看见万里江山,美得跟画一样。如果有朝一日……我还要去趟长州。”他虽说是在和她说话,却更似自语,及至最后,声音竟带哽咽。但是一双眸子,却于这黯淡冬日陡然亮了起来,灼灼的就像燃烧的两簇小小火苗。阿宝几欲落泪,只答了一句:“好。”
送衣的宫人早已站在了远处,犹豫良久,不敢近前。这样遥遥看去,是一对璧人,正在那里携手而立,喁喁私语。顾孺人得到的宠爱,已是阖宫皆知。
内文试读四:
风停了,人也定了,当整个延祚宫内外一片沉寂时,就可以听见更漏中水滴的声音,顺着铜漏嘴,一点一点滴下,绵绵如檐间春雨。顾孺人放下手中书册,起身慢慢走至几前,伸出一只手掌来轻轻封住了更漏的漏嘴,转首望向窗外。窗外是深不见底的夜色,壶中的木箭也已经指过了亥时。她移开了手掌,那聚堵在掌心的光阴之水又开始重新下坠,冰凉地,沉重地,淌过指缝,滴落到铜盘上,积成一汪小小水潭,在烛光照不到的地方,荡漾着深渊才具有的青黑色光泽。
阿宝抽回手,随意在裙上拭去了掌中水渍,转身走入内室,在妆台前坐下。两侧宫人欲上前来服侍,她只是轻声吩咐道:“不必了。”看着她们都退了出去,这才一个人慢慢卸除了簪珥,又将一头青丝解散,放到了肩上。发了片刻呆,方欲起身就寝时,忽见眉间颊上数枚花形金钿仍未摘除,及待举手,又滞于半途—这是他最喜欢看的东西。就在这一刻,她终于明白了自己的心思。那样的明白,就像隔岸观火一样。
清晨起身,当对着铜镜细细贴上这小小花黄的时候,究竟是想起了什么,才会莫名地喜悦?日间频频向窗外顾盼,又究竟是在盼着什么,书中的字句都模糊成了一团?傍晚时风停了,这颗心缘何也随着天色空暗?闭起了双眼,他的眉目清楚得仿佛就在身边。他言笑晏晏,嘴角弯成了一道精致的弧线;他忽然又不笑了,眉间有了一道直立的折痕。睁开了双眼,又似隔着几世人生,他不过是轮回转世后剩下的一个模糊影子,他长什么模样,穿什么衣服,脾气好不好,竟然半分也记不真切了—这世上真的存在这么一个人吗?街市的午后,西苑的黄昏,宗正寺的暗夜,他不来时,这些就只是她自己支离的幻梦;他来了,站立在眼前,它们才会蓦然新鲜起来。
原来这便是相思,这便是爱悦,原来这便是室迩人遐的煎熬,是求之不得的痛苦。原来事到如今,自己想要的东西已经越来越多,不单想活下去,还想看到他,想给他暖手,想陪他说话,想和他再去看一次鹤翔青天。因为有了这些妄念,所以惊怕的东西也越来越多,怕他生气,怕他难过,怕真的看不到乌发成霜的那一日,怕自己想要的更多。
铜镜中的少女对着她冷冷一笑,那笑容里的嘲讽之意像锥子一般刺痛了她的心。连这虚无之人都清楚,这世上最荒唐的奢念也莫过于此。神佛虽慈悲无边,若是得知,只怕也会掩口葫芦,嗤之以鼻。
内文试读五:
垂拱殿内诸臣守着一语不发的皇帝,站得两腿发木,终是等来了皇太子。在有司“皇太子入殿”的提引下,众人目光皆毫不避忌地迎向了已逾月未见的储君。皇太子于大殿正门缓缓步入,远游冠,朱明衣,手捧桓圭,腰束玉带。清俊的面孔虽仍显苍白,却波澜不兴,足下的步履也沉稳端方至极,仿佛他只是从延祚宫刚刚走出来,而之前不过是去听了一席筵讲,赴了一场宫宴。他们预计要看的一切都没有看到,皇太子已经穿过了朝堂,走到墀下向皇帝俯身下拜。
就在以头触地的那一瞬间,身上的伤口因为大幅度的牵动再次齐齐撕裂,但是无人看得见那层层锦缎掩盖下的一身伤痕,无人知道皇太子的双手正在微微颤抖,他年轻的身体内正有鲜血慢慢涌出。就如同无人知道他曾经因为惊怕在暗夜里痛哭失声,因为寒冷在一个仆婢的袖管中暖过双手。
然而这都不要紧,要紧的是他们看见了这一身锦绣公服。犀簪上的鲜明红缨正于他白皙的耳垂边摇动,革带鎏金的铊尾折射起点点微芒华彩,四色绶带上所结的玉环随着下拜的动作撞击出清越响声,而乌舄的鞋底不曾沾染半粒尘埃。如此的繁琐,也如此的堂皇。朝堂无外乎是,天下无外乎是,你穿上了锦绣,便是王侯;戴起了枷镣,便是罪囚。
定权朗声报道:“臣萧定权叩见陛下。”皇帝自他进殿伊始,便在默默打量,此刻见他端端正正,行礼已毕,也开口道:“平身吧。”
先王大道,圣人危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无上庄严,无上完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