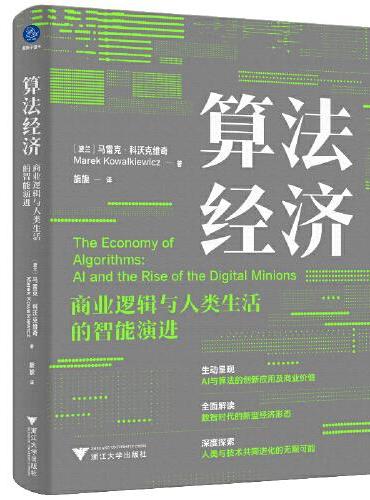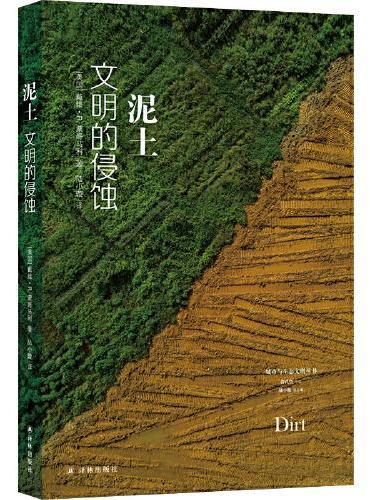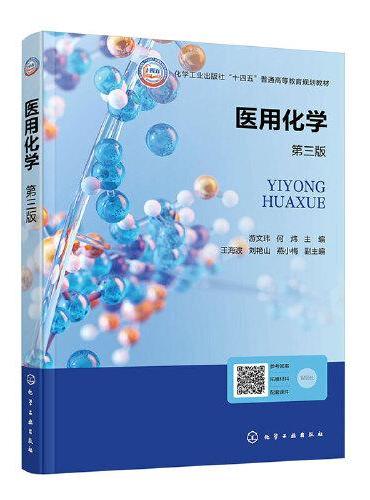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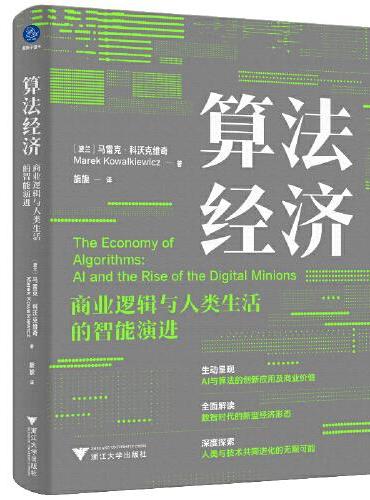
《
算法经济 : 商业逻辑与人类生活的智能演进(生动呈现AI与算法的创新应用与商业价值)
》
售價:HK$
79.4

《
家书中的百年史
》
售價:HK$
79.4

《
偏爱月亮
》
售價:HK$
45.8

《
生物安全与环境
》
售價:HK$
5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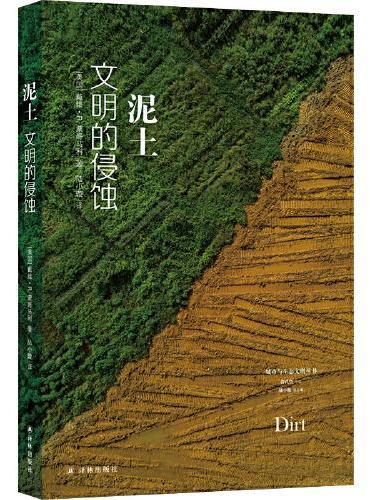
《
泥土:文明的侵蚀(城市与生态文明丛书)
》
售價:HK$
8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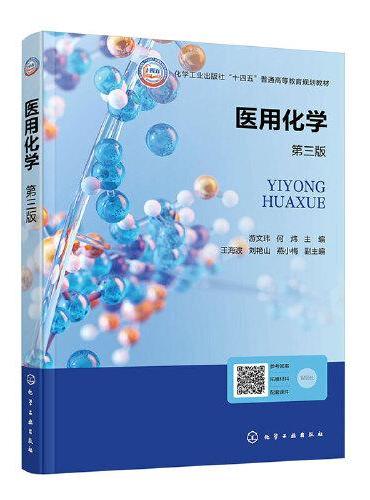
《
医用化学(第三版)
》
售價:HK$
57.3

《
别怕,试一试
》
售價:HK$
67.9

《
人才基因(凝聚30年人才培育经验与智慧)
》
售價:HK$
103.4
|
| 編輯推薦: |
卡洛斯·富恩特斯与马尔克斯、略萨、科塔萨尔并称“拉美文学爆炸”四主将,是20世纪以来世界纯文学的标杆,2012年5月病逝,再次成为全球文学界关注的焦点。富恩特斯是一位“入世”的文豪,是21世纪“360度的大知识分子”
(墨西哥著名学者埃曼努尔?卡瓦略
语)。他的作品无不与墨西哥的社会和历史相关。本书《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几乎融合了墨西哥从1905年至2000年的各大重要历史事件,展现了这个处在拉丁文化与美国文化交流和冲突的边界地区的国度近百年的风云变幻。
|
| 內容簡介: |
|
本书《与劳拉?迪亚斯共度的岁月》是富恩特斯1999年发表的作品,讲述了德国移民的后裔劳拉?迪亚斯丰富的生活和精神追求、她与亲人和朋友们的悲欢离合,以及她所见证的墨西哥从1905—2000年的各个重大的历史事件。通过劳拉的一生和家世,展现了这个处在拉丁文化与美国文化交流和冲突的边界地区的国度近百年的风云变幻,揭示了有着特殊历史、文化和种族渊源的墨西哥人民的苦难,他们的生活和内心世界。
|
| 關於作者: |
卡洛斯·富恩特斯,当代墨西哥国宝级作家,也是西班牙语世界最著名的小说家及散文家之一,与加西亚?马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胡利奥?科塔萨尔并称“拉美文学爆炸”四主将。
1928年11月11日出生于巴拿马,父亲是墨西哥外交官,自幼跟随父母辗转世界各地,深受不同文化熏陶。16岁返回墨西哥生活。1950年赴日内瓦深造,利用业余时间勤奋写作。1972至
1976年,出任墨西哥驻法国大使。
1959年首部长篇小说《最明净的地区》出版,一举成名,由此开始了被他称为“时间的年龄”系列文学创作过程。一生著有六十余部作品,曾获拉丁美洲最富盛名的罗慕洛?加列戈斯国际小说奖、西班牙语文学最高奖项塞万提斯奖,以及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多年来都是呼声很高的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2012年5月15日,病逝于墨西哥城。墨西哥以国丧礼遇向其致敬。
|
| 目錄:
|
第一章 底特律:1999年
第二章 卡特马哥:1905年
第三章 韦拉克鲁斯:1910年
第四章 圣卡耶塔诺:1915年
第五章 哈拉帕:1920年
第六章 墨西哥城:1922年
第七章 索诺拉大街:1928年
第八章 改革大街:1930年
第九章 洋际火车:1932年
第十章 底特律:1932年
第十一章 索诺拉大街:1934年
第十二章 水藻公园:1938年
第十三章 巴黎咖啡馆:1939年
第十四章 各地,个地:1940年
第十五章 罗马区:1941年
第十六章 查布尔特佩克-波朗科区:1947年
第十七章 兰萨罗特:1949年
第十八章 索诺拉大街:1950年
第十九章 奎尔纳瓦卡:1952年
第二十章 特博斯特兰:1954年
第二十一章 罗马区:1957年
第二十二章 里约热内卢广场:1965年
第二十三章 特拉特洛尔科:1968年
第二十四章 罗萨区:1970年
第二十五章 卡特马哥:1972年
第二十六章 洛杉矶:2000年
|
| 內容試閱:
|
第一章
底特律:1999年
我知道历史,却不知道真相。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谎言。我来底特律是为了拍摄一部关于墨西哥壁画家在美国的电视纪录片。说心里话,我对拍摄这个曾是第一座汽车之城的大都市的衰落更感兴趣。就是在这座城市里,亨利·福特拉开了汽车批量生产的序幕,从此这种机器比任何一个政府都更牢固地控制了我们的生活。
1932年,墨西哥艺术家迭戈·里维拉〔1〕应邀前来装饰底特律艺术学院,当年这座城市的影响力从中可见一斑;而今,1999年,我在这里,官方名义上是为了完成一部关于里维拉和其他墨西哥壁画家在美国的电视系列片。这部纪录片将从底特律的里维拉开始,然后拍摄加利福尼亚和达特茅斯的奥罗斯科;之后我将被派到洛杉矶寻找一幅西凯罗斯的神秘作品,以及里维拉的一些失传之作:洛克菲勒中心那幅因为在上面出现了列宁和马克思而备受非议的作品,还有新学院的组画,这几幅大型的镶嵌画同样已不存于世。
这就是我所承担的工作。我之所以坚持在底特律开机,是有原因的。我想摄下一个伟大的工业城市的废墟,作为我们生活着的这个恐怖的20世纪当之无愧的墓志铭:我既不是为了警世,也不想记录贫困和畸形启迪后人,更不是出于人道主义。我是一名摄影师,我既不是神奇的塞巴斯蒂安·萨尔加托,也不是威严的黛安·阿布斯。如果我是一名画家,我情愿拥有安格尔那无忧无虑的透明和培根〔4〕内心的痛楚。我曾试图作画,但没有成功。我并没有屈服。我认为镜头是我们这一时代的画笔,我在这里受雇去完成一个目标,但是当前——我预感到——是为了实现另一个全然不同的目标。
我起得很早,想在摄制组到达迭戈的壁画以前做好准备工作。这是2月份的一天,早晨六点左右,我等待着黑暗,我守望着它。然而这漫漫长夜让我心神不宁。
“如果您想购物或者看电影的话,旅馆可以派专车接送。”前台告诉我。
“商业中心离这里不过两个街区。”我又好气又好笑地回答。
“我们可不想担责任!”侍应生虚伪地笑着,他长相平庸,没有什么值得记住的地方。
这家伙不知道我要去很远的地方,要去一个比商业中心远得多的地方。我将无意中到达这满目疮痍的地狱的中心。我疾步行走,把像一面面镜子一样堆聚在一起的摩天大楼甩在身后——这是一个为抵御野蛮人的进攻而新建的中世纪的城市——十余个街区过后,我便消失在这片遍
布垃圾堆的贫瘠的土地和黑暗的荒野中。
我每迈一步——由于持续的黑暗,这每一步都是盲目的,因为我唯一的眼睛是镜头,我是一位现代波吕斐摩斯,我的右眼贴在莱卡相机的单目镜上,左眼紧闭,像个盲人,我的左手前伸,如同一只警犬,摸索着,有时双脚磕磕绊绊,有时深陷进一种闻不到又看不见的东西里——陷入一个不但持久而且再生的黑夜中。在底特律,黑夜生生不息。
突然,照相机在我的胸前跳了一下,我感到光圈干涩的撞击——这里有两个光圈,一个是我的,另一个是莱卡相机的——我的感觉更加深刻了,笼罩着我的并非冬日黎明前的漫漫长夜;想象使我懂得,那也不是新生的黑暗,白昼不安的伴侣。
这是持久的黑暗,与城市不可分离的黑暗,是它的伴侣,它忠实的反映。我兜着圈子在一片灰色的旷野中央沉思,那里水洼遍布,胆怯的步履踏出转瞬淹灭的小径,光秃的树木比战后的景致更加幽暗。远方,荒废的房子幽灵般若隐若现,上世纪的住宅屋顶破烂不堪,倒塌的烟囱、残破的窗户、斑驳的门廊、支离破碎的大门。有时,一棵干枯的树木温柔又轻佻地挨近满是尘垢的天窗。一把摇椅孤独地摇摆着,发出咿咿呀呀的声音,使我隐约想起了记忆中的其他时刻……
这孤独的田野和寥落的山丘,重现了我学生时代的记忆。我的双手拿起相机,而我思想的相机在咔嚓咔嚓回放着:墨西哥城,因河而闻名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因海而闻名的里约,混账的加拉加斯,可怕的利马,没有神圣信仰的波哥大,和无可救药的圣地亚哥〔2〕。在这个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在这个汽车之都,密歇根州的底特律,这个流水作业与最低工资的摇篮,就在此刻,我拍摄着我们拉丁美洲城市的未来。一切都是我拍摄的对象,一辆辆旧车被遗弃在最为荒凉的牧场里,突然出现的街道洒满了碎玻璃片,零售店闪烁的灯火……那里卖的是什么?在这座巨大漆黑的坟墓中,这些唯一光明的角落里卖的是什么呢?带着几分疑惑,我走进了一家小店,想买一杯冷饮。像天色一样灰暗的一对夫妇看着我,他们的眼神里交织着嘲弄、顺从与邪恶的好客。他们问我要什么,并且告诉我,这里什么都有。我有点不知所措,也许这是一种习俗,但我还是用西班牙语要了一杯可乐,他们愚蠢地笑着。“我们迦勒底人只卖啤酒和葡萄酒,”男人说,“可不卖毒品。”“还卖彩票。”那女人补充说。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回到旅馆,换下那双被忘却的污秽弄脏的鞋子。我看看表,就要开始第二天的拍摄了。摄制组在大堂里等我。准时不仅是我的好名声更是我服众的法宝。我一面穿衣,一面看着窗外的风景,在底特律,这个既属于基督又属于真主的城市,阳光照在摩天大楼和清真寺的顶部。世界的其他部分依旧沉浸在茫茫黑暗之中。
我们的摄制组来到了艺术学院。首先,我们穿过了那片无际的荒野,荒野上街区连着街区,时而可见维多利亚式建筑的废墟,在城市沙漠的尽头(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它的中心)有一座建于世纪初的宏伟建筑。她保存完好,宽敞整洁。顺着宽阔的石头阶梯拾级而上,穿过玻璃与金属的大门,便可以进到内部。她仿佛是充盈着不幸的匣子里的一卷幸福的弥撒经文;她是一位老人,肃然而又欣悦,因为她比自己的所有后代都长寿;她是无泪的拉结〔2〕,这就是底特律艺术学院。
高高的天窗遮掩下的巨大中央庭院,正是一场花卉展览的舞台。今天早上,这里就挤满了观众。“这么多花,是从什么地方运来的?”我问摄制组里的一位美国佬。他耸耸肩,算是给了我一个回答,看也不看那些争奇斗艳的郁金香、菊花、百合和黄菖蒲。这些花卉摆在庭院的四周,而我们正好从此匆匆而过。影视是这样一种工作,一旦剪辑的铃声响起,就要立刻丢下。不幸的是,以此为生的人们无法想象还能用他们的生命做其他的事情,只能日复一日地拍摄……我们是来工作的。
迭戈·里维拉,迭戈·马利亚·德·夸纳华托,迭戈·马利亚·康塞普西翁·胡安·涅波穆塞诺·埃斯塔尼斯拉奥·德·拉·里维拉·伊·巴利恩托斯·阿科斯塔·伊·罗德里格斯(1886—1957)曾经生活在这里。
请原谅我笑了,这是善意的笑,是出于认同和思乡的无法抑制的哈哈大笑。为什么笑呢?我想笑的是失落的天真和对工业的虔信;由于工业的发展,进步、幸福和历史才能相辅相成。里维拉已经在底特律歌颂过了这一切荣耀。中世纪的那些无名的建筑师、画师和雕刻匠人为歌颂唯一的、永恒的、无可质疑的上帝而修建和装饰了宏大的教堂,里维拉满怀着信仰来到了底特律,就像古时的朝圣者去往坎特伯雷和康普斯特拉一样。我笑了,因为这墙壁就像卓别林的黑白片《摩登时代》里面活动舞台的彩色明信片。同样是光洁如镜的机器,同样是严丝合缝的齿轮,在马克思主义者里维拉看来,这些可靠的机器是进步的可靠的象征;而在卓别林看来,这些机器就像是吞咽的咽门,如同铁胃一样吞食了工人,最后,再把他们像粪便一样排泄出来。
这里却不同。这里曾经是一首工业的田园诗,是里维拉在30年代所认识的那个富有城市的写照,当时底特律给大约五十万工人提供了工作和体面的生活。
这位墨西哥的画家又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呢?
这幅壁画里有一种很奇怪的东西,画面充满了人的形象,犹如蚁群。机器光洁蜿蜒,没有尽头,就像一根缓缓地爬向现时的史前生物的肠子。我颇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了这奇怪的感觉的缘由。我感到由创造性的发现带来的不安和激动,而在电视工作中,这一点是极不寻常的。我在迭戈·里维拉的壁画前停住了脚步,里维拉依附于他的赞助者,就像我依附于我的观众一样。然而,他却敢嘲笑他们,在资本主义的堡垒里,在他们的鼻子尖下,他插上了红旗,歌颂了苏联的领袖。而我正相反,审查和丑闻都和我无关,观众决定了我的成功和失败,如此而已。咔嚓,愚蠢的盒子关上了。现在,这些赞助者已经消逝了,谁还在乎他们呢?谁又会记得自己一生中看过的第一部和最后一部电视剧呢?
但是站在这幅如此出名的壁画面前,这奇怪的感觉使我无法平静,更不能随心所欲地拍摄。我上下打量着,借口要选取最好的角度、最好的光线,摄影师们很耐心,他们尊重我的努力,直到我最终一锤定音。迭戈·里维拉所画的所有的美国工人都背对着观众。艺术家只画工人的脊背,除了那些为了防止受到焊花伤害而戴着玻璃面具的白人工人。美国人的脸是匿名的,他们一个个都戴着面具。美国人这样看待我们墨西哥人,里维拉也如此看他们。只有脊背,不知姓名,没有面孔。因此,里维拉不笑,他不是夏洛特,只是一位敢于告诉美国人你们没有面孔的墨西哥人。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告诉他们,他们的工作既没有名字又没有面孔,他们的工作不是他们自己的。
那么,又是谁在看着观众呢?
黑人。他们有面孔。1932年,里维拉前来绘画的那一年,他们有面孔。那年,弗里达住进了亨利·福特医院,而里维拉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因为他执意将圣家庭画在壁画里。当时,弗里达怀孕了,但不幸流产。在画里,里维拉没有画圣婴,而是画了一个布娃娃,鹦鹉、猴子、鸽子、一只猫和一只鹿参加了孩子的洗礼。在画中,里维拉不让美国人正面朝向世界,是想嘲笑他们,还是对他们心怀恐惧?
艺术家永远不会知道观众所知道的事情。我们了解未来和里维拉的这幅壁画,他敢正视黑人的脸,黑人也敢正视我们,而他们的拳头并不只是为福特制造汽车。里维拉不知道这一切,他只是凭直觉在1932年画了这些黑人,而他们在1967年6月30日——这个日子被铭刻在城市的心脏里——放火,抢劫,烧光了城市,为停尸房留下了四十三具尸体。难道这四十三位未来的死人才是壁画中唯一正面看着的人?1932年,他们被迭戈·里维拉画在了壁画上;1967年,在画家死后的第十年,在他们被画入壁画的四十五年后,他们消失了。
猛一看,你能见到的只是一幅壁画,而它的实质需要一种深远而又耐心的目光。这种欣赏不能停留在壁画的空间里,而是要延伸到无限。这壁画有着一种外延,凝住了画中人物和观众的目光。我觉得有点怪异,不得不将目光投到壁画之外再突然折回,好像电影全景镜头箭一般猛然切入,转向女工们脸庞的特写。短发和工作服使她们变得男性化,但毫无疑问,她们是女性。弗里达就在其中。然而她的同伴,画中的另一位女子,她有着线条犀利的五官,与她高挑的身材相得益彰。她的目光忧郁,眼眶幽深,她的嘴唇很薄,却又很性感,稍纵即逝的唇线仿佛宣告着一种绝对而充分的优越,不着口红,节制并因此活力无穷,在说话、吃饭、爱恋中都充满了神秘。
我看着这双欧洲和墨西哥混血的金色的眼睛,很多次我在一张护照上也是这样地看着这双眼睛,而那张护照和放护照的抽屉已经同样被人遗忘。我看到的这双眼睛和在我年轻的父亲——他在1968年10月被暗杀——家里四处丢弃的照片上的眼睛一模一样。我那死去的回忆不认识这双眼睛,而我鲜活的记忆却把它们珍藏在灵魂的深处。三十年后,我快要满三十四岁了,20世纪也正在渐渐地离我们而去,我颤抖地看着这双眼睛,涌起了一种几乎是神圣的惊慌。见到我如此的失态,我的同事们不由得停了下来,来到我面前,问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我回忆起了什么?我看着这位工人打扮、美丽而又奇特的女子的面容,我一看到它,所有的回忆、记忆或所谓生命里的特殊时刻,一齐涌进了我的脑海,它们仿佛一片汹涌肆虐的海洋,层层波浪永远雷同却更迭不休。我刚刚看过劳拉·迪亚斯的脸,这张暴露在墙上芸芸众生中的脸,是一位孤独女性的脸,她的名字叫劳拉·迪亚斯。
摄影师泰瑞·霍普金斯,我的一位老朋友——尽管他还很年轻——给壁画打上了最后一抹蓝色的灯光,仿佛在与它作别。泰瑞是一位诗人,他的照明光线与1999年2月这一天夕阳西下的实景浑然一体。
“你疯了吗?”他对我说,“你要走回旅馆?”我不知道自己看他的表情是怎样的,但我没再说什么。我们分了手,他们背起讨厌而又昂贵的摄影器材,坐着汽车走了。
我一个人待在底特律,这座卑躬屈膝的城市。我慢慢地走着。
我浑身充满了一种青年手淫的疯狂,自由自在地四处拍着照片。我拍摄黑人妓女和黑人女警察;我拍摄头戴破帽、衣衫褴褛的黑人孩子;我拍摄蜷缩于垃圾箱——街头暖气——里的老年黑人;我拍摄那些荒废了的房子——我觉得我进入了所有的房子——里居住的一些无家可归的穷人;我拍摄那些瘾君子,在角落里,他们把快感和污秽注入体内。我懒散而又无耻,挑衅般地拿着照相机拍摄着每一个人,好像我正走在一条漆黑的走廊之中,而那个看不到的人不是他们中的一员,而是我自己。突然之间,对一位女子的柔情、思念和亲密感一齐向我袭来,我一生从不认识这个女人,而此刻却充满了对她的各种回忆。她的无意识,她的意志,她的天赋和她的危难:记忆同时是对家的排斥和对家的回归,与敌人的鲁莽遭遇和对巢穴的怀念。
一个人手拿火把,呼喊着走过废弃房屋的走廊,点燃了所有可燃的东西。我的后颈被打了一下,倒在了地上。我看到一幢孤单的摩天大楼在患黏膜炎的天空下昂首挺立;我触摸到了夏天燃烧的热血,尽管它还未到来;我喝下了无法洗净黑色皮肤的眼泪;我听到了清晨的喧闹,却听不见渴望的寂静;我看到孩子们在废墟中玩耍;我检视着这座躺卧的城市,毫不愧疚地给它下了断言。砖与烟的灾难,城市的燔祭,无人居住的城市的诺言,压迫着我的全身。在这座空城里,人类无家可归。我倒在地上问自己,能否像一位逝去的女子那样生活,发现她记忆的秘密,并回忆起她所能回忆的一切。我看到了她,想起了她。她是劳拉·迪亚斯。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