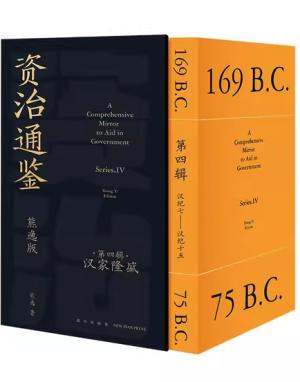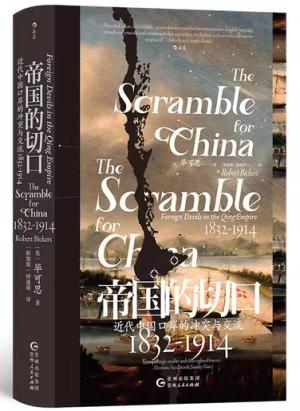新書推薦:

《
希腊文明3000年(古希腊的科学精神,成就了现代科学之源)
》
售價:HK$
82.8

《
粤行丛录(岭南史料笔记丛刊)
》
售價:HK$
80.2

《
岁月待人归:徐悲鸿自述人生艺术
》
售價:HK$
59.8

《
女人的中国医疗史:汉唐之间的健康照顾与性别
》
售價:HK$
10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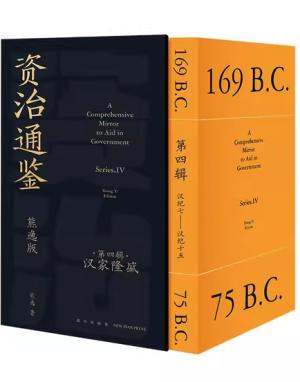
《
资治通鉴熊逸版:第四辑
》
售價:HK$
458.9

《
中国近现代名家精品——项维仁:工笔侍女作品精选
》
售價:HK$
66.1

《
宋瑞驻村日记(2012-2022)
》
售價:HK$
1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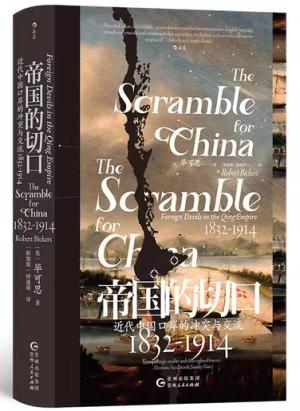
《
汗青堂丛书138·帝国的切口:近代中国口岸的冲突与交流(1832-1914)
》
售價:HK$
124.2
|
| 編輯推薦: |
作者周作人生前亲自编定,学者止庵穷数年之力精心作校,增补从未出版作品,为市场上最全面最权威的周氏文集。
鲁迅评价,周作人的散文为中国第一。
胡适说,大陆可看的唯有周作人的作品。
|
| 內容簡介: |
|
《老虎桥杂诗》是周作人自编集中仅有的一本旧体诗合集,大部分写于南京老虎桥狱中,故名。集中《苦茶庵打油诗》及补遗写在一九四五年之前,前者曾收入《立春以前》;《炮局杂诗》《忠舍杂诗》《往昔三十首》《丙戌岁暮杂诗》《丁亥暑中杂诗》均作于狱中,内容涉及往昔读书心得、咏史、忆往怀乡等,“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反思生平,表白心境,至为深切;《题画绝句》为咏物之作;《儿童杂事诗》则以诗的形式讲儿童生活、故事,表达儿童观,清新别致,在香港及内地曾以各种形式多次出版,广受欢迎。
|
| 關於作者: |
|
周作人(1885-1967),现代作家、翻译家,原名櫆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绶,自号起孟、启明(又作岂明)、知堂等,笔名仲密、药堂等。浙江绍兴人。青年时代留学日本,与兄树人(鲁迅)一起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五四时期任教北京大学,在《新青年》《语丝》《新潮》等多种刊物上发表文章,论文《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诗《小河》等均为新文学运动振聋发聩之作。首倡美文,《喝茶》《北京的茶食》等创立了中国美文的典范。在外国文学艺术的翻译介绍方面,尤其钟情希腊日本文学,贡献巨大。著有自编集《艺术与生活》《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等三十多种,译有《日本狂言选》《伊索寓言》等。
|
| 目錄:
|
题记
炮局杂诗
忠舍杂诗
往昔三十首
丙戌岁暮杂诗
丁亥暑中杂诗
儿童杂事诗
题画绝句
附录一
苦茶庵打油诗
附录二
苦茶庵打油诗补遗
附录三
老虎桥杂诗序
附录四
知堂杂诗抄序
|
| 內容試閱:
|
题记
我于前清光绪甲午(一八九四)年进寿氏三味书屋读书,傍晚讲唐诗以代对课,为读旧诗之始。辛丑(一九○一)以后在南京水师学堂,不知从何时起学写古诗,今只记得有写会稽东湖景色者数语,如云,
岩鸽翻晚风,池鱼跃清响。又云,
潇潇几日雨,开落白芙蓉。此盖系暂任东湖学堂教课,寄住湖上时所作,当是甲辰(一九○四)年事。昔有稿本,题曰“秋草闲吟”,前有小序,系乙巳年作,今尚存,唯诗句悉已忘却,但记有除夕作,中有云,
既不为大椿,便应如朝菌。一死息群生,何处问灵蠢。又七绝末二句云,
独向龟山望松柏,夜乌啼上最高枝。龟山在故乡南门外,先君殡屋所在地也。丙午(一九○六)年由江南督练公所派遣日本留学,至辛亥返国,此六年中未曾着笔,唯在刘申叔所办之《天义报》上登过三首,其词云,
为欲求新生,辛苦此奔走。学得调羹汤,归来作新妇。
不读宛委书,却织夗央锦。织锦长一丈,春华此中尽。
出门有大希,竟事不一吷。款款坠庸轨,芳徽永断绝。此盖讽刺当时女学生之多专习工艺家政者,诗虽是拟古,实乃已是打油诗的精神矣。
民国二年,范爱农君以愤世自沉于越中,曾作一诗挽之,现在已全不记得,虽曾录入记范爱农的一篇小文中。六年至北京,改作白话诗,多登在《新青年》及《每周评论》上面,大概以八年中所作为最多,十年秋间在西山碧云寺养病,也还写了些,都收集在《过去的生命》一卷中,后来因为觉得写不好,所以就不再写了。这之后偶然写作打油诗,不知始于何时,大约是民国二十年前后吧。因为那时曾经于无花果枯叶上写二十字,寄给在巴里的友人,诗云,
寄君一片叶,认取深秋色。留得到明年,唯恐不相识。这里有本事,大意暗示给他恋爱的变动,和我本是无关也。又写给杜逢辰君的那一首“偃息禅堂中”的诗,也是二十年一月所作。但是真正的打油诗,恐怕还要从二十三年的“请到寒斋吃苦茶”那两首算起吧。这以后做了有不少,其稍重要的曾录出二十四首收入《苦茶庵打油诗》那篇杂文中。关于打油诗其时有些说明,现在可以抄录一部分在这里:
“我自称打油诗,表示不敢以旧诗自居,自然更不敢称是诗人,同样地我看自己的白话诗也不算是新诗,只是别一种形式的文章,表现当时的情意,与普通散文没有什么不同。因此名称虽是打油诗,内容却并不是游戏,文字似乎诙谐,意思原甚正经,这正如寒山子诗,它是一种通俗的偈,用意本与许多造作伽陀的尊者别无殊异,只在形式上所用乃是别一手法耳。”又云,
“这些以诗论当然全不成,但里边的意思总是诚实的,所以如只取其述怀,当作文章看,亦未始不可,只是意稍隐曲而已。我的打油诗本来写的很是拙直,只要第一不当它作游戏语,意思极容易看得出,大约就只有忧与惧耳。”
这回所收录的共有一百五十首以上,比较的多了,名称则曰杂诗,不再叫作打油了,因为无论怎么说明,世间对于打油诗终不免仍有误解,以为这总是说诨话的,它的过去历史太长了,人家对于它的观念一时改不过来,这也是没法的事。反正我所写的原不是道地的打油,对于打油诗的名字也并不真是衷心爱好,一定非用不可,当初所以用这名称,本是一种方便,意在与正宗的旧诗表示区别,又带一点幽默的客气而已,后来觉得不大合适,自可随时放弃,改换一个新的名号。我称之曰杂诗,意思与从前解说杂文时一样,这种诗的特色是杂,文字杂,思想杂,第一,它不是旧诗,而略有字数韵脚的拘束,第二,也并非白话诗,而仍有随意说话的自由,实在似乎是所谓三脚猫,所以没有别的适当的名目。说到自由,自然无过于白话诗了,但是没有了韵脚的限制,这便与散文很容易相混至少也总相近,结果是形式说是诗而效力仍等于散文。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固然由于无能力之故,但总之白话诗之写不好在自己是确实明白的了。白话诗的难做的地方,我无法去补救,回过来拿起旧诗,把它的难做的地方给毁掉了,虽然有点近于削屦适足,但是这还可以使用得,即是以前所谓打油诗,现今称为杂诗的这物事。因为文字杂,用韵只照语音,上去亦不区分,用语也很随便,只要在篇中相称,什么俚语都不妨事,反正这不是传统的正宗旧诗,不能再用旧标准来加以批评。因为思想杂,并不要一定照古来的几种轨范,如忠爱,隐逸,风怀,牢骚那样去做,要说什么便什么都可以说,但是忧生悯乱,中国诗人最古的那一路思想,却还是其主流之一,在这里极新的又与极旧的碰在一起了。正如杂文比较的容易写一样,我觉得这种杂诗比旧诗固不必说,就是比白话诗也更为好写。有时候感到一种意思,想把它写下来,可是用散文不相宜,因为事情太简单,或者情意太显露,写在文章里便一览无余,直截少味,白话诗呢又写不好,如上文所说,末了大抵拿杂诗来应用,此只出于个人的方便,本来不足为训,这里只是说明理由事实而已,原无主张的意思,自然更说不上是广告也。
我所做的这种杂诗在体裁上只有两类,以前作七言绝句,仿佛是牛山志明和尚的同志,后来又写五言古诗,可以随意多少说话,觉得更为适用,则又似寒山子的一派了。可是事实上并不如此,他们更近于偈,我的还近于诗,未能多分解放,只是用意的诚实则是相同,不过一边在宣扬佛法,一边乃只是陈述凡人之私见而已。诸诗都是聊寄一时的感兴,未经什么修改,自己觉得满意的很少,但也有一二篇写得还好,有如《岁暮杂诗》中之《挑担》一首,似乎表示得恰切,假如用散文或白话诗便不能说得那么好,或者简直没法子说,不过这里总多少有些隐曲,有的人未必能一目了然,但如说明又犯了俗的病,所以只能那样就算了。又如《丙戌岁暮》末尾云,
行当濯手足,山中习符水。《暑中杂诗》中《黑色花》云,
我未习咒法,红衣师喇嘛。又《修禊》一首末云,
恨非天师徒,未曾习符偈。不然作禹步,撒水修禊事。这些我都觉得写得不错。同诗中述南宋山东义民吃人腊往临安,有两句云,
犹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这可以算是打油诗中之最高境界,自己也觉得仿佛是神来之笔,如用别的韵语形式去写,便决不能有此力量,倘想以散文表出之,则又所万万不能者也。关于人腊的事,我从前说及了几回,可是没有一次能这样的说得决绝明快,杂诗的本领可以说即在这里,即此也可以表明它之自有用处了。我前曾说过,平常喜欢和淡的文字思想,但有时亦嗜极辛辣的,有掐臂见血的痛感,此即为我喜那“英国狂生”斯威夫德之一理由,上文的发想,或者非意识的由其《育婴刍议》中得来亦未可知,唯索解人殊不易得,昔日鲁迅在时最能知此意,今不知尚有何人耳。
《花牌楼》一题三章,后记中已说明是用意之作,唯又如在《往昔》后记中所云,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咏叹淫泆,乃成为诗,而人间至情,凡大哀极乐,难得写其百一,古人尚尔,况在鄙人,深恐此事一说便俗,非唯不能,抑亦以为不可者也。”这三首诗多少与上文所说有所抵触,但是很悭的写下去,又是五十年前的往事,勉强可以写成那么一点东西,也就是不很容易了。有些感怀之作,如《中元》及《茶食》《鲁酒薄》等,与《往昔》中之《东郭门》《玩具》与《炙糕担》是一类,杂文中亦曾有《耍货》《卖糖》等篇,琐屑的写民间风俗,儿童生活,比较的易作,也就不大会得怎么不成功。此外又有几篇,如《往昔》五续中之《性心理》,《暑中杂诗》之《女人国》《红楼梦》以及《水神》,凡与妇女有些相关的题目,都不能说得很清楚,盖如《岁暮杂诗》之《童话》一篇中所云,
染指女人论,下笔语枝离。隐曲不尽意,时地非其宜。昔时写杂文,自《沟沿通信》以来,向有此感慨,今在韵文中亦复如此,正如孟德斯鸠所言,帝力之大有如吾力之为微矣。
但是这问题虽是难,却还是值得而且在现今中国也是正应当努力的。杂诗的形式虽然稍旧,但其思想应具有大部分新的分子,这才够得上说杂,而且要稍稍调理,走往向前的方向,有的旧分子若是方向相背,则是纷乱而非杂,所以在杂的中间没有位置,而是应当简单的除外的。直截的说,凡是以三纲为基本的思想在现今中国都须清算,写诗的人就诗言诗,在他的文字思想上至少总不当再有这些痕迹,虽然清算并不限于文字之末,但有知识的人总之应首先努力,在这一点上与旧诗人有最大的区别。中国古来帝王之专制原以家长的权威为其基本,家长在亚利安语义云主父,盖合君父而为一者也。民为子女,臣则妾妇,不特佞幸之侍其君为妾妇之道,即殉节之义亦出于女人的单面道德,时至民国,此等思想本早应改革矣。但事实上则国犹是也,民亦犹是也,与四十年前固无以异,即并世贤达,能脱去三纲或男子中心思想者又有几人。今世竞言民主,但如道德观念不改变,则如沙上建屋,徒劳无功,而当世倾向,乃正是背道而驰,漆黑之感,如何可言。虽然,求光明乃是生物之本性,谓光明终竟无望,则亦不敢信也。鄙人本为神灭论者,又尝自附于唯理主义,生平无宗教信仰之可言,唯深信根据生物学的证据,可以求得正当的人生观及生活的轨则,三十年来此意未有变更。《暑中杂诗》之《刘继庄》一首中有四句云,
生活即天理,今古无乖违。投身众流中,生命乃无涯。此种近于虚玄的话在我大概还是初次所说,但其实这也还是根据生物的原则来的,并不是新想到的意思。我的意思是看重殉道或殉情的人,却很反对所谓殉节以及相关的一切思想,这也即是我的心中所常在的一种忧惧,其常出现于文诗上正是自然也是当然的事。这几篇不成其为诗的杂诗,文字既旧,其中也别无什么新的感想,原不值得这样去说明议论它,现在录为一编,无非敝帚自珍之意罢了,上边的这些话也就只是备忘录的性质,俗语云,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此之谓也。三十六年九月二十日,知堂自记。
十二月八日大雪节重录迄。
寒暑多作诗,有似发疟疾。间歇现紧张,一冷复一热。转眼严冬来,已过大寒节。这回却不算,无言对风雪。中心有蕴藏,何能托笔舌。旧稿徒千言,一字不曾说。时日既唐捐,纸墨亦可惜。据榻读尔雅,寄心在蠓蠛。卅七年一月廿七日知堂。
卅七年一年间不曾作诗,只写了应酬之作数十篇耳。去老虎桥之日始作《拟题壁》一首,今附于《忠舍杂诗》之末。卅八年二月一日,记于上海虹口寓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