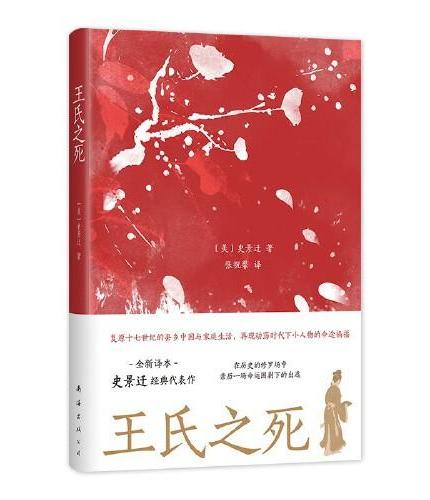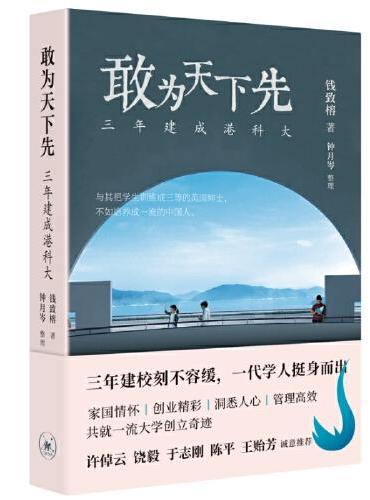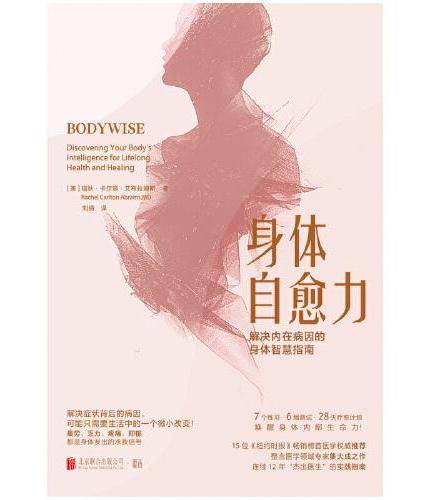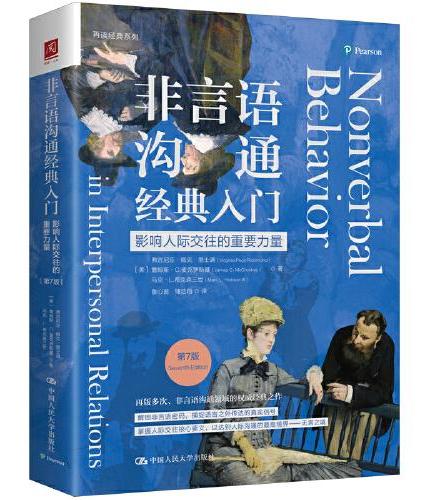新書推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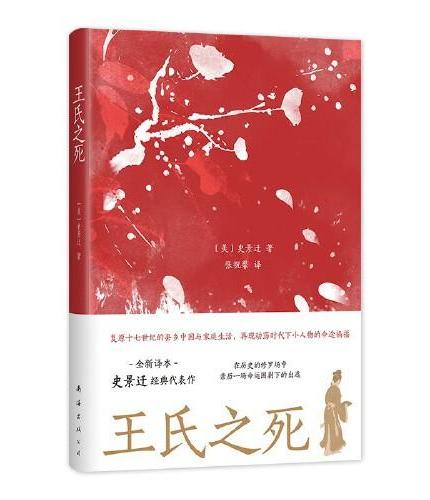
《
王氏之死(新版,史景迁成名作)
》
售價:HK$
5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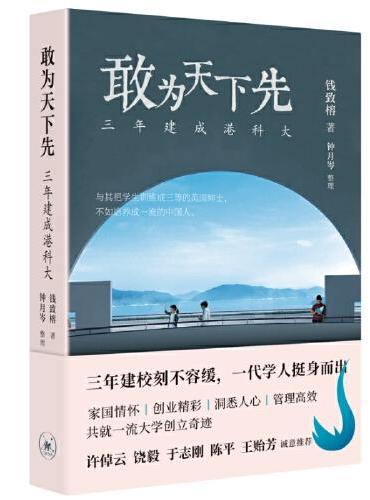
《
敢为天下先:三年建成港科大
》
售價:HK$
77.3

《
长高食谱 让孩子长高个的饮食方案 0-15周岁儿童调理脾胃食谱书籍宝宝辅食书 让孩子爱吃饭 6-9-12岁儿童营养健康食谱书大全 助力孩子身体棒胃口好长得高
》
售價:HK$
4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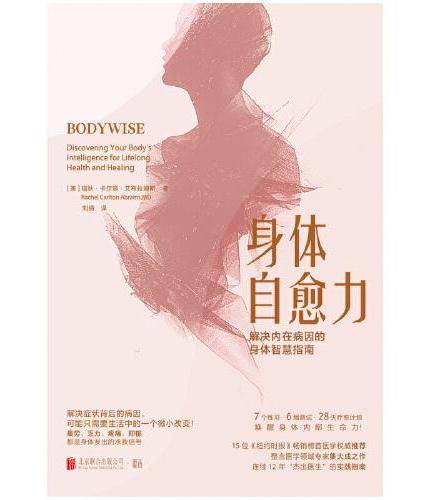
《
身体自愈力:解决内在病因的身体智慧指南
》
售價:HK$
9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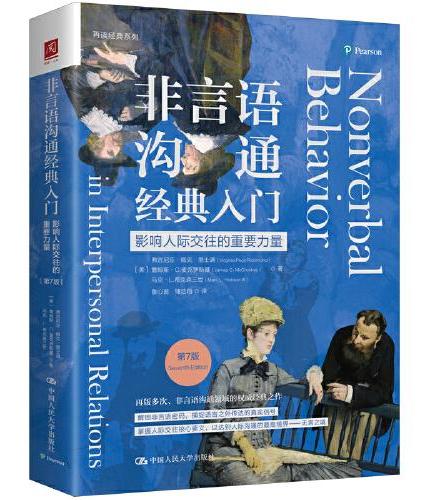
《
非言语沟通经典入门:影响人际交往的重要力量(第7版)
》
售價:HK$
123.1

《
山西寺观艺术壁画精编卷
》
售價:HK$
1680.0

《
中国摄影 中式摄影的独特魅力
》
售價:HK$
1097.6

《
山西寺观艺术彩塑精编卷
》
售價:HK$
1680.0
|
| 編輯推薦: |
作为中国基督教史和近代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理雅各漫长的一生可谓中西方交流的典范。这位文化巨人的传记呈现了19世纪全球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景观——西方人向东方文化的朝圣之旅。
1. 名师主编,史学奠基。本书隶属“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传记丛书”,丛书主编为周振鹤教授,他在历史地理、中西交通史上的深厚学养,保证了这套丛书的高质量,已出版的《花甲忆记》、《卫三畏生平及书信》、《马礼逊回忆录》、《李提摩太在中国》、《千禧年的感召》等,获得学界、出版界一致好评,为基督教传播史、中西交流史研究作了奠基性工作。
2. 第一手史料,弥足珍贵。作者与传主同时代,其视角和笔触能够带给现代人以现场感,在叙述中提供了书信、日记等第一手资料,使我们对晚清的许多历史事件有了感性的认识。
3. 西方视角看晚清中国社会,极具启发性。作者不仅描述当时的历史,也从西方学者的视角提出精辟见解,具有学术启发性。
4. 译笔流畅,充满宗教感情。这既是基督教史学著作,也是通俗生动的人文读本,适于大众阅读。
|
| 內容簡介: |
|
《朝觐东方:理雅各评传》将精炼娴熟的传记叙事与扎实严谨的学术考证相结合,系统评述了著名来华传教士—学者理雅各漫长而多姿多彩的一生。在19世纪传教士传统、汉学东方主义和比较宗教科学的理论语境之中,作者将理雅各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化生涯分解为传教士、朝圣者、异端者、阐释者、比较学者、翻译者、教师等几大侧面,对理雅各的传教士生涯和作为汉学家的学术经历、精神历程进行了条分缕析式的探究,由此呈现了理雅各这位文化巨人外表平静、内心丰富的一生,还原了19世纪东西方文明交流与碰撞的宏阔历史面貌。附理雅各的女儿海伦?蔼蒂丝?理 所著《理雅各:传教士与学者》,提供大量书信、日记等珍贵史料。
|
| 關於作者: |
作者:吉瑞德(Norman J.Girardot),美国理海大学Lehigh University杰出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比较宗教学家、中国宗教史论家。
丛书主编:周振鹤,1941年生于厦门,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读研究生,师从谭其骧院士,1983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为我国首批两名文
|
| 目錄:
|
中文版序翻译之道001
插图目录001
前言联结东西方的传教士生涯:1815—1869001
第一章朝圣者理雅各和他的回归西方之旅:1870—1874059
第二章理雅各教授在牛津大学:1875—1876111
第二章附录理雅各:牛津的一个大人物156
第三章异端者理雅各:打通儒教与基督教,1877—1878159
第四章阐释者理雅各:在《中国经典》中找寻圣经,1879—1880209
第五章比较者理雅各:描述并比较中国宗教,1880—1882244
第六章开拓者理雅各:翻译佛教和道教经典,1886—1892292
第七章教育者理雅各:高扬人的完整责任,1893—1897358
附录一:理雅各主要出版著述406
附录二:理雅各在牛津大学的讲座与课程(1876—1897)409
注释415
外一种理雅各:传教士与学者
第一章早年生活489
第二章决定终生的选择496
第三章在马六甲499
第四章香港与《中国经典》509
第五章在香港的生活524
第六章“术语问题”538
第七章有关中国人生活与工作的一些事件543
第八章太平天国的干王554
第九章车锦光,第一位华人殉教者561
第十章理雅各夫人信札摘录574
第十一章溯西江而上588
第十二章在香港的最后岁月595
第十三章华北之旅610
第十四章英格兰的最后时光626
译名对照表647
译后记651
|
| 內容試閱:
|
1873年,随着法国汉学家儒莲的去世,理雅各成了西方世界唯一一位最有影响的中国经典的翻译者—阐释者。在欧美学术圈子中,理雅各所完成的那些中国经典,足以拓展并明确过去由耶稣会士和启蒙运动时期的有关中国经典和儒家学说的那些老生常谈式的说法。与此同时,理雅各的《中国经典》也强有力地支持了一般东方学家的相关论点,他们认为中华文明是困陷于古代的伟大文明,尽管这种文明的发展被阻止了,而且也是非宗教的。但是,很平常地——引用理雅各的侄子约翰?理(John Legge)的说法——“面部为黄褐色,两眼闪烁着不真诚的蒙古人种”,他们并非“进化了的文化所散发出来的芬芳”,但理雅各的《中国经典》却将中国列入“人的普遍历史”之中。甚至令人更为惊异的是,理雅各给维多利亚时代的宗教和知识传统所带来的某种改变性的力量的冲击在于,中国文明的古代成就精华,尽管同样包含着《圣经》中所讲述的某些原始启示,但它是自我驱动的,是“未经神圣启示之触动的,而且也没有因为与其他种族的人民之交流而发生改变”。意识到中国的对外隔膜和“令人难以忍受的对外孤绝”,随之而来的是他同样沮丧地意识到,即便没有《新约》和《旧约》中所提供的那些神圣知识,古代中国人也已同样意识到“真正的上帝”,并且已经实践了类似于基督教法则的道德。《中国经典》因此打开了人类历史和宗教的多色彩的地平线,它超越了已经发现了的那些族群的相似性,在一个更高的或者比较文献学的科学基础之上,而被列入所谓印欧语系的种族传统之中。
在最后一次逗留香港和中国期间,理雅各准备结束与伦敦传道会的定期联系的决定,乃为保持他作为一个固执独立的福音派新教会的苏格兰人,和一个将传教士身份与学者身份大胆地联系起来的神职人员的完整生活方式。甚至当理雅各最终将中国古代的那位孔圣人翻译成一个道德楷模和文化英雄的“孔夫子”的时候,与此同时,那些中国经典文献同样也逐渐将那个“好的基督徒”转化成为理雅各。理雅各与孔子二人,他们的一生都令人惊奇地产生出共鸣,因为两人都被不得要领的范例(福音派基督徒和耶稣会士)理解为这样的人,那就是能够平抑住人格修养过程中不断出现的反复挣扎。借用《论语》(II.iv.6)中已经确立了的有关孔子个人传记性的材料,可以这样说,还在“年十五”的时候,孔子和理雅各二人都“志于学”。他们都“三十而立”(有时候立得太坚定了!),坚守着各自内心中的道德精神原则。“四十”之时,他们对于自己作为古代文献的教育者—阐释者—传承者的终生工作都已“不惑”。而且“五十”之时,两人也都清楚地断言,他们已“知天命”——即便是在有关术语学(天,上帝)方面和相关上天的使命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严重的不一致。
经过多年远离亲属邻里的在外漂泊,在按照自己医治世界的方式来皈化他人方面,他们也很少取得长久的成功,无论是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还是传道者—圣人孔子,他们最终都返回了故土,并在“六十”岁左右的时候,他们已能够做到“耳顺”——有时候这样做并不舒服而且伴随着巨大的悲哀——哪怕是对于人类交往过程中那些最微弱的声音。两人最终都离开了自己对更大世界所承担的使命生涯,转而去接受在编撰和宣扬那些被忽略的古代经典过程中可怜的欢乐和间接的影响。两人在人生暮年,都拥有足够的智慧献身于“完成其文学劳动”。跟孔夫子一样,传教士—汉学家理雅各,正在从经典文献的学习和人生进化的过程中汲取一种伟大的道德教益。这是一种艰难的努力,如果你希望成为一种谦逊而且富有智慧的人、一种已成就的人、一种具有复合身份的人、一种不断进行自我修正的人的话,而这一切只可能来自“道”,或者终其一生才可能实现。尤为重要的是,道德洞察力乃哲学知识和存在转化这两者共同之秘密。正如在理雅各的《论语》译本中所说的那样,一个“君子”,七十而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而理雅各在年近古稀的时候,是否能够达到这种风范和智慧,我们可以翘首以待。
中国的特殊孤独。尽管在文明和文学的“孤独”上印度与中国存在着科学上的相似性,但印度还是比中国享有某些特权。因为印度与西方拥有共同的印欧兄弟血缘,而且只有中国最终才被完全视为绝对孤独。特殊的问题总是关涉中国在语言和文化上无法抗拒的特殊性,及其无可比拟的“可怕的孤独”。因此,尽管有了新兴的职业化的汉学东方学研究,但这些努力不过如同雏鸟试飞而已,对于中国语言和文学的研究,并不像专门涉及印度和闪米特人的东方学那样,在语言与比较研究上处于先进的地位。在向亚洲学会所作的演讲中,缪勒提到,中国研究的问题,是它迄今依然“局限于少数学者之间”。不同于印欧传统和闪米特传统(这些传统通过一种共同的语言和一种单一的神圣典籍与欧洲联系在一起),“在西方与古代中国之间,并不存在知识思想上的联系”。
甚至更具戏剧性的是,缪勒宣称,“我们从中国人那里什么也没有接受到。在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令人激动兴奋的接触。它从来不曾被带到靠近我们心灵的地方。中国只是古老而已——非常古老——显得遥远而奇特”。通过间接批评理雅各在《中国经典》和“中国圣典丛书”中展现的努力,缪勒指出,有关中国之孤立的问题有可能会缓解,只要“中国学者把他们的古代文学带到我们面前,如果他们愿意向我们展示,这些文学著述中确实有某些关系到我们的东西存在,这些东西不仅古老而且永远年轻”。此外,缪勒还谈到,“不知是什么原因使中国一直保持如此的独特性,一直如此远离我们共同的兴趣”,缪勒实际上表明,这种不幸的现状其实主要归结于当代汉学研究者的失败。缪勒如此言说,好像理雅各从来不曾耗费半个世纪的时间和心血来完成儒家和道家经典(翻译)似的,似乎他也从来不曾撰写过《中国的宗教》。看上去理雅各已经变得完全过时了,作为一位上了年纪的前传教士,他已经提供不了什么用处,缪勒觉得自己有权宣布“中国宗教”这一课题从来就没有得到过真正“严肃的关注”。缪勒甚至暗示,与理雅各的那些发现相反,西方传统与中国宗教和哲学之间的“差异”,“将让我们至少懂得这样一个有用的教训,那就是在我们的哲学中还有更多值得我们去学习和梦想的东西”。对于这些尖刻的评论,理雅各作出了怎样的回应,迄今已经没有任何现存的记录可供我们查对,但我们可以大胆地想象,那位高龄的苏格兰人一定从中感觉到了某种特殊的伤害。
理解征服与统治。缪勒的大会演讲中带有预言性的观点,包含在演讲的结尾部分:在提示了亚历山大大帝曾经试图“重建西方与东方的联合”这一先例之后,缪勒宣布,如今,这一神圣的使命落在了大英帝国的肩头,要让它“伫立于整个世界之中央”。缪勒像个吹鼓手一样宣称,“英格兰已经证实了它不仅懂得如何去征服,同样懂得如何去统治”。英格兰已经“意识到——不止是意识到了——亚历山大关于东方与西方联姻的梦想,而且已经将世界上主要国家民族拉拢在一起了,这种密切的程度超出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不过,缪勒用一种渐强的口吻说道,“去征服和统治是一回事,去理解(东方民族和国家)则是另外一回事”。当然,缪勒的整个职业生涯,以及他的这次大会发言中暗含的主题,都倾向于表明征服、统治以及理解实际上不过是大同小异而已。
这一时期,东方研究开始在大英帝国带有军事色彩的神圣政治使命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它对所有西方人都担负着义务,尤其是英国人,让他们成为“东方化的东方热爱者”。不幸的是,英国在东方语言和文学方面“难以为西方人提供基本的指导”,英国人应该遵循着维多利亚女王的榜样,她最近“不惜将其宝贵的闲暇时间利用起来学习印度语言和文学”。缪勒自己极有可能就是女王在东方研究方面“非常宝贵”的导师,但他只是说,“知识上的亲密”有助于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建立起一种和平的关系。如果这种现实的包容和理解早点成为事实的话,“也就不会有印度人的反叛了”,而且毫无疑问,对在华传教士的暴力攻击也会少得多。
缪勒从更普遍的意义上宣称,东方研究应当通过汇聚“历史事实”而不是“预先的推理”,来鼓励即将到来的东方与西方的重新联合。这将有助于“解除”白人与有色人种之间的“偏见”。那些发现可能只是来自一些“业余者,一些胡说八道之人,还有半瓶子醋的学者”,这样的风险总是存在的,但是,缪勒也说道,对东方知识的真正“征服”,是“坚实而安全的”。所有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勤勉努力的东方学家,终将显示他们是人类相互理解和团结的战斗中的“勇者”。
1856年,车锦光已经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当时他是博罗(Poklo)一座孔庙的监护人,博罗是广东省境内一个拥有15000人口的小镇,距离香港100英里。车锦光此前从来不曾听说过基督教,也从来没有见过传教士。一天,圣经会的一个《圣经》叫卖者路过博罗,见到车锦光,给了他一份中文版《新约》。车锦光读后,整个心灵为之触动。他决定到一个能够让他对这部令人惊奇的书提出更多问题、能够让他知道更多内容的地方。车锦光听说有一个传教士住在香港,于是他来到香港,向理雅各博士作了自我介绍。
不久,车锦光就要求像一个基督徒那样受洗。最初,理雅各博士犹豫了。获悉车锦光将重回内地,理雅各觉得他还需要在给车锦光施洗之前花更多时间来了解他,并且让他能够作为基督教的一个典型回到他的乡邻中间。车锦光的态度变得更为迫切。一天傍晚,在一个祈祷会之后,人们正在散去,车锦光在门口等着传教士。天正下着雨,他就站在雨地里,说道:“你还不相信我,担心给我施洗。可是我是一个真正的人,而上帝知道我,你瞧,上帝的雨水正下到我的头顶上。”说到这里,车锦光摘下他的帽子,任凭雨水淋到他的裸露在外的头顶上。“瞧,上帝正在给我施洗。”
更多本书信息请登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网站:http:www.bbtpress.com
|
|